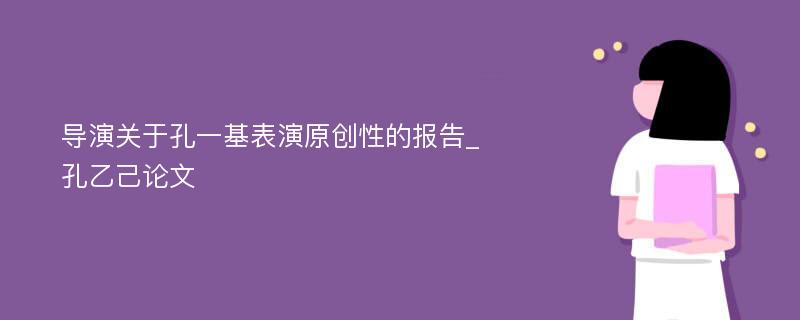
关于《孔乙己》演出创意的导演报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创意论文,导演论文,演出论文,报告论文,孔乙己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关于鲁迅的《孔乙己》
关于《孔乙己》这篇小说,鲁迅自己所谈不多,小说从头到尾给人一种对孔氏文人的讥讽。但看到最后,会发现鲁迅对人物寄予很大的同情。孔乙己也是个多色调的人,毛病不少且供人取笑。但讽刺的同时,周围的人也同样被讽刺,包括鲁迅本人那摇摇不定的价值灵魂,让人感受到了步履蹒跚的沉重的背影。这一背影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
一种不被社会所关怀没落悲惨的文人命运。
孔乙己象是穿着长衫的阿Q,社会待他不公平,他对社会也没用。但孔乙己又确实有那么唯一的一点价值,那就是自始至终他在努力地捍卫自己“独立的人格,自由的思想”。这也正是鲁迅将千百年中国文人用一种形态加以归结的典型:廉价的傲骨。这是知识分子最可贵之处,是小说唯一闪光的性格特征:孔乙己用生命维护着自我表现的精神天地。但由于所固守的旧文化的“廉价”,也就显得最可悲。
孔乙己是一个和善诚实,有善良心、同情心的人。一个不与人争又很会脸红的人,一个很“君子固穷”又常自己丢脸面的人。沉浸于自我(文化)而不思改变,耽于懒散、无聊,借酒度日,以字充文的虚幻人生。他偷书是原于贫困(精神的、生活的),他救人又出于儒学、孔孟之道。在他身上表现了众多知识分子中的一种心路历程,延续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整体命运。什么是孔式中国知识分子命运?——对传统文化的执迷和绝望,对新文化无从接受和不理解。孔乙己所处的时代,动荡不安,他无权可依,无势可附。科举的废除,又使他开始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悲剧历程。
二、关于剧本
1、结构分析
A、什么是剧本的情节核心
首先,作者选择、演绎出二十世纪中国发生得最早、最重大的事件——科举制度废除,发生在孔乙己踌躇满志将赴考场之际,安排了一个年轻人“恰逢末世之变,跌入精神死谷”的尴尬命运的前提。这一前提决定了孔乙己全部戏剧动作开展的精神依据和状态,并开始了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中国读书人的悲剧历程。我们可以将这一情节命名为:“赴考惊变”。(戏曲擅长给场面、动作或剧情以命名,目的是让演员、观众明了将要演出的内容和任务。命名又分为几种,如“环境命名”:秋江,三岔口,定军山等;“动作命名”:如劈山救母,夜奔,挑滑车等;还有“情绪命名”:如贵妃醉酒,黛玉葬花,霸王别姬等等。我们兼而有之)。
接着又发生了与孔乙己心境、处境极不相符而不得不面对的重要情节:寡妇求救。这一情节对一个心灵刚刚遭受重伤的人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一个连自己的生途都不知何在的可怜人却要站起来解救另一个脱险境。如此嘲弄,如此悲惨而又如此严峻。救不救,怎么救?最后还是孔乙己萌动了善心。月光下,苍茫人世孤寂无助,悲惨命运对影成双。这段戏,有待调整,要更准确地描写孔乙己从不救人到救人的心理过程。使悲惨的更加悲惨,可怜的更加可怜。使人从情感上更加理解、同情孔乙己,当然还要为夏瑜、女戏子的登场铺垫好情绪。这一段戏,可以命名为“怜己怜人”。
第二幕,当孔乙己以“回”字的几种写法无聊度日时候,迎面走来了夏瑜。这似真似幻的相见,对映出两种截然相背的人生态度。一个是投身社会变革,不惜抛头颅的巾帼女侠,一个是恹恹,倦倦,迷茫而又颓废的沉沦之人。两人相对,一红一白。红的那么热烈,白的那么虚无。但他们又有一种沟通,一种可以靠近的相互间的吸引,那就是良知。这良知是女侠拯救国人于危难的动力;是孔乙己人格中最为闪亮的价值——他也因此而救夏瑜。一个救人,一个救国。救国者伟大,救人者也不渺小。同时,相见这一情节还是承上(寡妇)启下(女戏子)的象征性过渡阶段,也是下面几段戏的动因和根源,所以应属于核心性质的情节。我们可以命名为“相见如幻”。
二幕二场,孔乙己先盗书后挨打,再救人。三幕里,孔乙己从钱奚为手中接过夏瑜留下的香扇。刹那间,周身热血沸腾,相形之下自觉形惭。于夏瑜革命一事,孔乙己懵懵懂懂,不知所云。他更重的感伤是对夏瑜的惋惜与可怜。香扇转递于他,他接过来的绝对不是革命者的嘱托,而是一种情愫,一种留恋,一种言不明的暗示和联系。转而他回转祠堂,面对古人痛斥自己不如。可他毕竟是孔乙己,他不可能象夏瑜那样自我涅槃,以换得民众的新生。他只有倚祠堂一角,暗落伤心泪。他毁书焚经,意在渲泄。他是在悲哀的时世中悼念自己,他也只有悼念自己的权力了。
这一系列情节,均属于核心情节的部分。我们可以分别命名为“祸起书香”“仗义救人”“法场”和祠堂一场的“桃花源梦”。
第四幕,孔乙己进入清醒的颓废期,他看破世间冷暖,感受自我沉浮。夏瑜之死,让他品悟出一次人生的无奈。用夏瑜的血浸过的馒头,没治好栓子的病,却给众人蒙上了一层腥红的恐怖。而对孔乙己,则引起情感上的自责和哀叹。遭遇女戏子,让他最终选择了放弃。
面对一个指天骂地,笑侃人生的女流,孔乙己再一次地愧叹不如,转而心动:为何不将香扇赠于她?面对香扇,他只有自我折磨,抛将出去,岂不解脱。孔乙己自知此扇与他不配,持来心重情悲,全然不见扇面之豪情,但他也知道,他赠交与女戏子的,不仅是一把扇子,他交出去了责任、自尊,交出去了那份良知,交出了自我。从此他甘愿混沌,甘愿醉酒。孔乙己从香扇中释然,又从释然中沉沦。最后,连骨头带魂一古脑地泡进酒坛之中了。
这一重要情节,我们命名为“在释然中颓废”。
B、 剧本结构基础层面的第二大定义是:以众多次要人物为存在主体,构成主要人物的依附性存在。
小栓子最小,却是揭示主题不可或缺的人物,相信是留给观众深刻印象的段落。掌柜、老栓、华大妈穿梭往返于各种人物之间,举重若轻地平衡着杂乱、多阶层的人物关系,来维持自己的生意;丁举人名士风流,地方一霸,丁少爷则代表了一个阶层:阔少加恶少。钱奚为举止欧化,西装革履,与咸亨及众人极不协调,显示出另一种文化的轻浮;半疯子疯中有智,醉中有醒。而红眼阿义,蓝皮阿五、康大叔、孟老二等短衣帮又形成社会低层的鲜明和纯粹。
寡妇、夏瑜、女戏子,各为存在实体又互为象征:三个人涵盖了整个封建社会女性的命运,用作者的话说,是“美丽中的苦难和苦难中的美丽”,认为这是传统文化给予中国女性唯一的馈赠。我们再加上一种解释,就是“屈辱中的抗争与抗争中的屈辱。”寡妇逃命,夏瑜抗争,女戏子在没有女性存在价值的道德体系中以捐出尊严和人格为代价,换得一份存在。结构离奇,内在深刻。
C、规定空间
咸亨酒店是鲁镇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是鲁镇人交流和集会的场所。大清国的国事、家事、天下事无不在此被关注和讨论。鲁镇人走进咸亨,就可以证明自己身在鲁镇的存在和价值。从早到晚,从春至冬,一年四季每时每刻人们都在叙说着历史的兴衰荣辱,演绎着时代的喜怒哀乐。咸亨,是鲁镇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
从咸亨酒店的外在象征上,可以看出它的开放性特征。历史现实的对立与融汇,思想与行为的矛盾与互通。以及不同阶层、地位、身份、出身的人都可以举杯交错,来而又返。在这个“酒香宾咸集,人耒事亨通”的酒肆里,人们可以忘却一下时间,迎杯送盏地以酒会友,打发些许无聊的生活和疲累的劳作。从戏一开始咸亨庆祝十周年的气氛之中,可以感受到它那表层热闹的景象。
但从咸亨酒店内在考察,又可以窥见它深层次里封闭性的特征。封建的道德观念,专制的社会制度以及保守落后的文化思想构成了它整体精神氛围,笼罩着来到咸亨的每一个酒客的所言所行。加之形成的社会规范,咸亨实际上是封建社会的缩影和堡垒。在这里,阶级的划分会传递压抑、冷落的感受,老酒的香溢也难以消解穷富的差异。所来者未必都是乘兴,饮酒者多数不得开怀。潦倒的文人墨客,做小生意的穷困商贩,唱戏、打杂工、出苦力和沿街乞讨的叫花,都挤进身来饮一碗酒,为的是歇一下脚,暖一下心。孤独者以酒消闷,无聊者借酒滋事,麻木者醉生梦死。更多的是集中在一起的酒客,熬不过精神的空寂,借一杯苦酒,醉一下精神。这里是沉沦、绝望和麻木的滋生地,这里的穷人会借着酒劲发出一两声狂饮后的呐喊。迷狂和混沌,让酒客们乘着醉意更深地浸泡在悲惨的生活之中……
咸亨酒店,又象一个文化的废墟,让所在其中的人都手捧腐朽书卷,低头诵念找不到生之出路的死亡之经。咸亨酒店,实际上已是一个丧失价值体系,暗藏腥风血雨,致人精神沉沦、意志颓废的牢狱。
这也正是剧本通过对咸亨酒店的描写,对以鲁镇为代表的清末社会的整体概括。
2、剧作中的“中心事件”
中心事件,即“夏瑜之死”。它是围绕主要人物而生发意义的事件,是可以集中改变规定情境,改变主要人物动作、态度和引起冲突的事件。孔乙己从认识夏瑜而建立起来的好感(不是主张而是良知的),到偷书、被打,到让半疯子去报信再到孔乙己法场接扇,这些均源于夏瑜而起。包括第四幕孔乙己将扇子转赠女戏子,也应看作与中心事件的辐射性关联。这个事件比较集中,关联了很多人,特别是事件的性质直通主题,是由新旧文化的观念而引起的冲突,相比其它场次,这一事件最为强烈。但这个事件只成为中心事件而不可能贯穿到底,原因有二:一个是事件在孔乙己身上发生转折,他将扇子转赠别人,于是中心事件到此结束。主要人物完成终极任务只是将中心事件作为阶段通过——把夏瑜之托转赠旁人才是主要人物奔向主题的最后过程。第二个原因,在于对剧本主题的把握和解释。
简单地说,夏瑜这条情节线,是激进、革命性的代表和象征,但却不能成为剧作的思想主导。因为鲁迅对此有原始态度,剧本作者亦持同样的思想倾向。
在我们这个戏里,如果要对夏瑜过多关注,未免将孔乙己拔高和概念化了。作为守旧的他,不会理解夏瑜。他会惋惜夏瑜的英烈,但不会同情革命。这一点,剧作不动情,演员也不能过分投入。否则,孔乙己有于革命前仆后继之嫌疑。
3、确定主要矛盾
概括地说,剧作确立了的主要矛盾,是人与文化的矛盾。可以分为三个层面:新旧文化的矛盾,贫富之间的矛盾和自我的文化矛盾。
每一个人物均被这三组矛盾所裹卷,全剧情节也围绕这三组矛盾而进行。孔乙己则身在这三组矛盾的对立旋涡之中碰撞并形成最大的矛盾焦点。
首先他被存在的阶层所困扰。考取功名可以富禄可以显贵,但科举废制了,一下子他潦倒得只能寄居祠堂。他恨忧时世,却不思劳作,因为他认为自己有文化,有价值。他唯一没有的是生存的能力。文化不是铜钿,学问换不得老酒。这一点,连短衣帮都嘲笑他不如。无产者看不起还可以自慰,可有钱人对他嗤之以鼻最让他难过。满以为凭借之乎者也可以赖以生存,偏偏又碰上个反传统、崇西学,否定旧文化的新时尚,他眼看着自己跟不上,听不懂,更难以接受。他开始痛苦不堪,因为他无法选择。旧的无法放弃,新的无从适应。没有精神准备更没有精神承受,剪不断理还乱,说不清,道不明。最后他终于选择了千百年来历代文人骚客的同一归途:精神大逃亡。
认清主要矛盾,可以通达主题的范围。分析身处主要矛盾旋涡中的孔乙己,也就逐步廓清了这样一种知识分子的生命理想及国家、与权利、文化的关系:从势与依权,反之恐惧与麻木。他们不敢也不能对历史、民族、国家、未来作出整体思考与自我调整,没有批判与超越的意识,没有挽救文化衰落的勇气。他们有的只是消沉,有的只是精神的逃亡与颓废。
由此,我们可以对剧作主题作一归纳了。
4、主题、主题思想
改写一下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名言,即是这部戏的主题:
凡一种文化价值衰落之时,被此文化所化之人,无论是启蒙者、救亡者、逃亡者、麻木者,无不感到苦痛。
主题是剧作提出的问题,那么主题思想该是我们对这一问答的回答。
主题思想:凡社会的激变,总以新旧文化、观念、情感和思想的碰撞为代价的。在碰撞的苦痛中选择和建立可以超越旧文化精神体系的新秩序,提高素质,重塑人格。历史才能发展,民族才会自强,人类才能进步。
5、全剧的形象立意
一群游荡在文化废墟里的精神乞丐,找不到走出废墟的生路。呻吟出阵阵酒醉的悲歌。
6、孔乙己的形象立意
一个甘愿在旧文化泥沼中沉醉而不思自拔的儒子。
7、全剧的现实意义
这个戏没有什么离奇的情节,但它提出的话题却是凝重的。百年前的文化阵痛,百年前华夏民族的精神创伤,仍有被我们关注的必要。剧本生发于鲁迅小说,但又更为浓缩和提纯,它对以孔乙己为代表的人物群体从灵魂到存在作了深刻概括和解剖,使今天的我们更加廓清了中华百年史的演绎和变化。明确了所谓国民性里尚存的那么一种对生活和社会的变革不去适应、不关心的麻木心态一直传递、影响着后人。这种文化的遗传正是鲁迅先生所痛心疾首的。我们深思发生在身边的事物,时有这样的文化幽灵在作用着我们现代人。在改革、经济发展的今天,面对下一个世纪,我们也站在了历史的交道口上,百年轮回,别无选择。因为任何一次社会的变革,知识分子都是站在最前面。我们不能以固有的文化传统原则来看待日新月异的社会变化,以不变应万变的僵化心态是错误的;以守为攻的抵触心态是消极的;而固步自封,不承认社会变革的规律性,不接受先进思想技术的进步性,一味地坚持旧观点旧意识而不思进取的人,终会被历史所淘汰。所以,面对未来的社会发展前景,最需深切反思的问题,首先是我们自己,以及我们赖以生存,依托着的文化的观念。
那么,这个戏的现实意义可以这样来框定:
历史赋予我们责任,这责任包括要求我们敢于从精神层面否定自己并将自己置身于社会发展的激变洪流之中。
三、关于演出
当我们对剧本完成了政治的、哲学的分析鉴定之后,我们进入最本体的话题,开始对未来演出总体形象进行思考与设计,这也是我们奔赴演出目标的起点。
第一个问题,剧作演出的风格、样式:
通过对鲁迅小说风格和剧本结构的分析,我们认识到剧本创作是对鲁迅作品精神的深化和补充。鲁迅的创作风格是集多种艺术流派之大成者,可以用现代主义这个词来概括他。因此,剧本的创作风格也不拘泥单一而呈多项融合,如三个女性的象征意蕴,戏场法场、血溅咸亨的表现色彩等。因此,剧作的风格本质决定了样式选择的定位标准。应该是:以现实主义为原则,突出象征手段,追求表现功能,强调写意精神的多种艺术观的综合与统一。
舞台上最能够展示剧作风格本质的是空间(包括舞美、色彩、音乐)、体裁感和人物基调(包括表演)。这是观众进入剧作迷宫的入口。所以,我们应就这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空间
这个戏,由于鲁迅思想的原始厚重,由于表现剧作精神的需求,对意念空间的自觉应大于物质空间的把握。我们将依循这样的理念来确立形式的内涵。
在对空间的视听组合过程中,色彩和音乐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构成情感的直观和外化冲击力。色彩(包括灯光、服装还有道具化妆)和音乐,都要以历史感和现代感的最佳契合为切入点。所谓历史感是要求传达沉闷、压抑、陈旧的印象,所谓现代感是对这一印象的变形——寻找现代人的诉说方式。空间里弥漫着灰蒙蒙的感觉,黑影、黑衣、黑的廊柱,黑的发辫隐隐浮动。灰、黑的色彩意象是基调,要做旧,要鲜明,要成为主印象。而孔乙己的一件白色长衫,相当夺目,要完成一种对人物的象征性表达。当然孔乙己也可以有一件黑色长衫,哪一位人物也可以有红色点缀。如一个讨饭女孩,在堂里穿过,夏瑜拉住她,教她几句儿歌。这个小女孩,就可以穿一件红袄,来暗喻未来的希望。也可以风格化一些,如三场“秋”,表现清兵不用人,而是用红缨枪头,黑衣上白色“勇”字,白帽红翅的道具组合成很多人。而三场里的三种色彩的灯笼来推动戏剧内质的表现:红灯笼是闹戏台的热烈气氛;黑灯笼是对阴森法场恐怖的预示;而白灯笼则是对夏瑜之死的悼念之情——这一情愫直接可以延宕到观众席里的内在激情。
音乐也是从历史性入手:地域的陈年老调,人物的特点和颓废,沉沦的情绪传达。但也要变形,变现代之形,找似与不似。音乐主题在起势、落势上可以研究,不易明亮不易低沉,否则概念化。要有怪诞之情,理念之意。
大幕拉开,要让咸亨内外的吵嚷、叫卖、饮酒猜拳、小曲高调声形成庄严的风俗交响诗。我们要先声夺人一下子把观众拉入百年咸亨热烈、喧闹的酒肆氛围之中!
2、演出的体裁
剧本的形象立意是:一群游荡在文化废墟里的精神乞丐,找不到走出废墟的生路,呻吟出阵阵酒醉的悲歌。
形象立意提供出一个情绪的场,一个几近悲凉、悲惨的生存氛围。这是一种规定:它规定了创作者理性的介入,要以这样的整体感情趋向为选择条件,从而创造出符合剧作气质需求的行为动作和状态。
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剧。它严峻地提出,百年前封建、落后的社会体系和文化价值,在民众对生存的绝望中失落和崩溃了。它又象一出讽刺的喜剧:因为生存于其中的人物又是那么执着,令人产生一种忍俊不禁的同情。而那种愚顽、守旧、冷漠、麻木的精神状态,又不能不让人失望和遗憾,甚至唾弃。但它又是一出悲剧:人物越呐喊也就越可怜,越麻木也就越可悲。我们回视于它,不免从心底生出暗淡的哀愁,不得不悲切地将老祖宗传下来的这种尚未健全的国民性裸露在观众面前痛惜地展示,悲怆地评说。
由此,在体裁定位上,它应包括:以人物性格中被嘲弄着的喜剧因素为基础,在充满悲剧氛围的社会和文化的桎梏中,演绎了一个时代消亡,价值崩溃的严峻话题。
3、人物基调
这是一个必须明确概念,把握严谨的创作环节,决定着演出的成败。我们先从孔乙己谈起。
作为历代知识分子的人生终极,孔乙己也无例外地将自己赌押于科举会考的人生一搏之中。他初进咸亨,踌躇满志,满面春风。给寡妇铜钿,送乞丐吃酒。对旁人的对联不屑一顾,看自己写的得意洋洋。他自信当年赴考,已非他莫属。贺庆题诗,正好小试牛刀。虽嫌酸腐,却也光彩。你看他提笔、扬袖、凝神、亮腕,表现出儒雅和潇洒,占尽得意之风头。然末世惊变,一下子孔乙己断了背脊骨。他迷钝昏沉,心口在流血。他摇晃颤粟,腰弯如暮年。从此,他生不知方向死不知归途。失魂丢魄,任风吹着躯体在荒野里飘舞、沉浮。
孔乙己读了不少的书,但他的学问已学而无用。只在咸亨以文兑酒,聊以度日。他已跌入了精神的死谷,翻翻旧书,讲讲回字有几种写法是他唯一可为之事。他越执意于对旧文化的迷恋与陶醉,越显得滑稽、可怜和萎琐。又常被短衣帮当成嘲弄的把柄。面对凄惨的生活,只有用酒来填充思想的空白,麻醉不死的心灵。
孔乙己有一件做工很象样的长衫,这件长衫给了他无穷的遐想。他只要身着长衫便梦寐功名,便自觉有身份。这长衫是自尊和价值,是他的理想和他赖以生存的自信,这长衫给了他孤傲和蔑视旁人的眼神和举动。但现实中他只能与短衣帮为群体,而他着实不能与短衣帮在一起。他时而抬脚想跨上“雅座”的门槛,可一阵嘘声使他忐忑不安、心虚气短地缩了回来。他回头鄙视短衣帮,昂首走到一旁,可眼光仍留恋于雅座。长衫是他心灵的寄托和外化,也是他最心酸的伤情之物。一介书生,四壁皆空,仕途暗淡,唯长衫与之为伴。夜里,长衫被风舞动,他伫望良久,不知在想什么。此时此境,格外悲惨。
长衫是孔乙己人物基调的一个活见证。
在对孔乙己的分析中,可以归纳这样一些可把握的情态和逻辑:他得意则忘形,失意则丢魄;他习惯在自嘲中谐趣。有时他卖弄文墨,不知所云,有时他又穷酸,可怜地拿学问换酒喝。他以有文而倨傲,可倨傲中受屈辱;他也因不公而冷峻地愤怒,可愤怒后是消沉,最后,他舞动长衫,似我非我,一口气倒出肚子里的经典和文化,在清醒中颓废,在理智中沉沦。
这个戏,孔乙己有两件极有价值的道具,长衫和扇。我想,这是外化他内在情感、性格、思想的手段和形式,相信从中可以找到角色——人物的感觉。
4、表演的要求
(1)根据内容和形式的要求, 创造只属于这个戏的肌体运动方式。
戏曲表演艺术,已经走入怪圈:受益于程式,也受制于形式。继承容易发展艰难。其实我们每排一个新戏,都应慎重地提出这个问题,那就是都要竭尽全力地去解决一下这个戏的表演问题。从选择剧本开始就避免同义重复,避免复制和克隆。但是,由于戏曲表演艺术的相对规范,由于艺术的技术性创造实在是困苦艰难,使得我们沿袭大于创新。如果说寻找戏曲艺术落后于时代的主要责任,一是文学,二是技术。文学观念缺少现代意识(不是有了现代戏就有了现代意识),技术缺少现代性。现代意识和现代性的问题应该可以看成是戏曲艺术自觉发展、进步最关键的两个问题。
剧本严格地规定了时代、人物、情节、环境,就必须在这种规定下寻找相对应的表现——表演方式。晚清末年,似现代非现代,所有的固有传统不可套用。怎么办?唯有建立新程式。如何建立?这正是全剧组通过排练所要摸索的课题,排戏,就是摸索和建立体现手段的过程。
(2)努力追求技术性突破
这一点,特别针对越剧,针对主要演员而言。越剧的技术性,少于京昆,承于京昆。越剧自身的完善和发展受到技术性局限。那么,怎样才能确立剧种的表演技术系统?怎样才能形成剧种自身的表演体系?又怎样才能从小剧种向大剧种过渡?这仍然必须通过每一次的实践都解决一些问题、创造一些经验为方法,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剧种。
这个戏,我对茅威涛提出技术上的严格要求。要从长衫、扇子、圆场等方面入手,创造一些人物的新程式,其他演员也同此理。因为某种意义上程式的发展决定着戏曲艺术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完成剧本的和剧种的要求,创作才有意义。《寒情》也许有许多不足,但《寒情》在创造表演新程式的观念上,解决了一些问题,突破了一些戒律。
(3)避免概念化、脸谱化
这一点,仍需从程式表演说起。行当划分、训练外部技巧的同时,演员的表演内部素质也同样被训练和定型,于是戏曲演员掌握了习惯性、技术性调度表情的技巧。这一技巧随手拈来无需体验,人物性格创造被归于某种类型。技术是先成的,技术引发情感也是先成的。概念和脸谱相应产生。
解决的办法是重新感受和体验,让情绪、态度、舞台行为都变成有机整体。让清新的创作感觉流通演员的心身,暂时忘却程式,从人物出发去动作,去适应,去感受。依据规定情境的要求重新组合,筛选程式和创造程式。这也是作为演员毕生创作的行为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