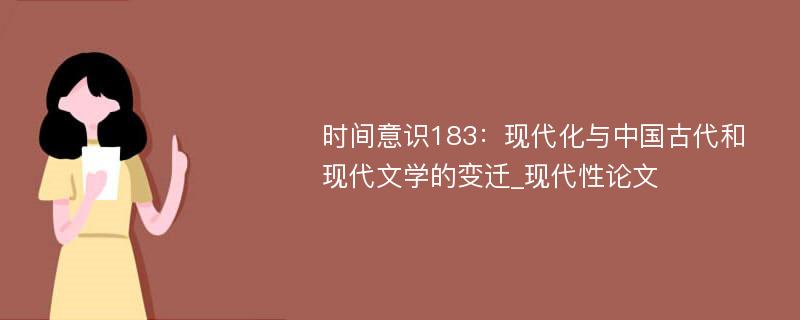
时间意识#183;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的古今之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代性论文,古今论文,中国文学论文,之变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对于时间的本质、属性、结构以及时间与人的关系问题的追问是在追问一个无解的难题,正如世界著名作家博尔赫斯所言“我想时间是一个根本之谜。其他东西也许是神秘的。空间并不重要。你可以想象一个没有空间的宇宙,比如,一个音乐的宇宙。当然,我们是听者。不过,说到时间,你有一个如何给它下定义的问题。我记得圣奥古斯丁说过‘何谓时间?若无人问我,我知之,若有人问我,我则愚而无所知。’我想时间的问题是一个真正的问题。时间问题把自我问题包含在其中,因为说到底,何谓自我?自我即过去,现在,还有对于即将来临的时间、对于未来的预期。所以这两个不解之谜,正是哲学的基本内容,而我们很高兴它们永无解开之时,因此我们就能永远解下去。”①正是这种对时间和自我问题的好奇与追问推动着他的创作,他在一篇题为《时间的新反驳》的文章里,在描述了使时间成为一种错觉的观点以后,断言:“否定时间的连续,否定自我,否定天体宇宙,表面上是冒险,实际上是慰藉。时间是组成我的物质。时间是冲着我顺流而下的河流,但我就是河流;时间是毁灭我的虎,但我就是虎;时间是焚烧我的火,但我就是火。不幸,世界是真实的;不幸,我是博尔赫斯。”②博尔赫斯在其小说《沙之书》中曾想象出一个无限时空的世界,在其中时间既无开端也无结束,向两端无限延伸,但这样的世界带给主人公的感受是始而新奇,终而厌恶:“我觉得它是一切烦恼的根源,是一件诋毁和败坏现实的下流东西。我想把它付之一炬,但怕一本无限的书烧起来也无休无止,使整个地球乌烟瘴气。”小说开头作家引了英国十七世纪玄学派诗人乔治·赫伯特的诗句:“你沙制的绳索”,显然具有点题的意味,即该作表达的仍是作家持之以恒的对于时间问题的追问,所谓“沙制的绳索”,盖指人赋予世界的人为时间秩序——有始有终的线性时间线索的脆弱、易断,犹如“沙”做的绳索一样若有若无、若断若续。这本“沙之书”作为一本神秘的《圣书》与基督教有始有终的《圣经》时间观具有某种对应关系,但它的“页码是无穷尽的。没有首页,也没有末页。”而且其页码也不是按照数字顺序排列,你这次打开书看到的东西,下次再也无法找到。这是一个完全无序的、无因果的、变幻无常的、不可理喻的世界,人生活在这样的世界正像迷失于广袤无垠的沙漠一样,会陷入茫然失措,不知身在何处的境地。所以主人公为了消除其带来的困扰和不安,最后只好把书藏到了图书馆的群书之中,用一种被追赶的鸵鸟式的自欺方式来消除这样一种可能的世界图景带来的眩晕,因为“隐藏一片树叶的最好的地点是树林”。同样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先锋小说家余华的实验小说也是从对常识、流俗时间的怀疑与颠覆开始的,他认为时间构成了世界的结构,“世界是所发生的一切,这所发生的一切的框架便是时间。因此时间代表了一个过去的完整世界。当然这里的时间已经不再是现实意义上的时间,它没有固定的顺序关系。它应该是纷繁复杂的过去世界的随意性很强的规律。当我们把这个过去世界的一些事实,通过时间的重新排列,如果能够同时排列出几种新的顺序关系(这是不成问题的),那么就将出现几种不同的新意义。这样的排列显然是由记忆来完成的,因此我将这种排列称之为记忆的逻辑。所以说,时间的意义在于它随时都可以重新结构世界,也就是说世界在时间的每一次重新结构之后,都将出现新的姿态。”③因此,时间意识的变化是引发世界观、人生观乃至整个文化、文学变化的根源,本文试图对中国清末民初以来时间意识的嬗变做一个考察,既借此探索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的文化心理根源,并以此诀发现代人的心灵变迁,展示在现代时空意识中所呈现出的世界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他们又是如何通过文学想象来重新进行自我定位,以应对这个变化了的世界。 一般来说,对时间的研究和思考以两条线索展开,一种类似于空间形式组织起来的时间观念,一种近乎以内在心理体验为基础的时间观念,前者偏于客观和外在,而后者偏于主观和内在。从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来看待时间属于前一种,所谓“时”是对物质运动过程的描述,所谓“间”是指人为的划分。在阿里士多德那里,时间是通过空间来呈现的,所谓“时间就是变化了的数”。但这种对时间的理解至二十世纪的柏格森而得到彻底的改变,他创造性地将“空间时间”和“真实时间”区别开来,从而使时间得以摆脱对空间的依赖而呈现出其持续绵延的本质,最能体现时间这种绵延本质的是人的意识。因此,所谓“真实时间”“也就成为了一种心理时间,一种无须遵循客观时间的规则,也不依赖钟表测度的人的内在生命体验的时间”。在这种“真实时间”经验中,过去、现在、未来可以相互叠加,历史、梦幻、现实可以相互交织,时间与个体生命体验达成了同步和一致,由此促成了“个人时间”“心理时间”对“历史时间”和“客观时间”的疏离、对抗和挑战、重组,影响所及使心理时间、梦幻时间成为世界现代文学艺术中的主导时间。二十世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更打破了古典的趋于凝固的绝对、客观的时空观念,为重新理解时空问题敞开了大门,爱因斯坦认为:我们的宇宙由时间和空间构成,时间与空间一起组成四维时空,构成宇宙的基本结构。他所理解的时空关系,是在空间的架构上比普通三维空间的长、宽、高三条轴外又加了一条时间轴,也就是说时间会影响到空间,两者并非毫不相干的。而量子力学与经典力学的不同在于:在经典力学里,一个物理系统的位置和动量,可以同时被无限精确地确定和预测。在理论上,测量过程对物理系统本身,并不会造成任何影响,并可以无限精确地进行。而在量子力学中则不然,测量过程本身会对系统造成影响。量子力学认为物质是由快速振动的量子组成的,量子的运动方式和形态具有波粒二象性,也就是它们既是一个个的粒子,又是一团函数波,在没有被观测的时候它们是没有精确的运动方向和轨迹的,只能以概率的形式分布在它的函数范围内,同时存在于各个点上。当有意识观测量子的时候,量子才会表现出粒子的形状而具有确定的位置。这种对量子的认识也就彻底颠覆了古典的以牛顿为代表的绝对时空观。 与爱因斯坦相似,在时间问题上引发巨大变革的哲学家是马丁·海德格尔,他同样颠覆了传统形而上学的时间观念,激发了人们对于存在与时间问题的新的思考。海德格尔认为只有从时间性出发才可能在生存论上对此在产生整体的和本真的理解,时间性构成了此在的原始的存在的意义。此在的生存结构以时间性为其统一的结构,它把过去、现在和将来的时间统一在一个先验的视域当中。而此视域呈现的可能性,则是由“先行到死”的“死亡意识”来提交的。海德格尔关于时间的理论,强调了人与时间的内在联系。时间不再是外在于具体的生存着的人现成自在地存在着的,它不再是主体所去寻求的客体,它首先和必然地与存在相关,此在所由出发之域就是时间,把时间作为理解存在的视野,是海氏存在论意义上的时间观一大特点。 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和认识总是立足于自己的时间经验之上的,时间经验可分为两类④:一类是作为一种对事件的度量的时间,可称为是一种标度时间,这是一种客观时间;另一种则是与人的心理体验或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时间,如对逝者如斯、人生短暂等时间流变的感悟等等,它可以称为是一种侧重于人的内心对时间的感知的主观时间经验。时间之所以与文学关系密切,因为时间与人的生命体验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生命即时间,而文学所主要表达的也正是人对于生命的感悟和理解。人对于人终有一死的体悟,将人与其他生物区别开来,所以时间意识也就成为人之为人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如弗雷泽所说:“人只是表面上看起来是一种理性动物,实际上,他是有死亡意识从而有时间意识的生物”⑤。其他生物虽然也生活在时间中,但只是凭本能生存,没有对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追问,所以也就不会相应地产生死亡意识和生命的有限感。只有人类能够意识到时间并从而唤起人的生存的自觉。 人的时间意识在进入现代社会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现代性与一种特定的时间意识密切相关,正如福柯所说现代性突出地表现为一种对时间的偏执,“十九世纪最重要的着魔(obsession),一如我们所知,乃是历史。”⑥自然时间的历史化,成为推动“现代”成为“现代”的内在动力,它突出表现为一种社会现代性的追求,一种立足于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单向、线性、不可逆的历史时间观念,与传统循环论时间观的圆形想象不同,在这种现代性想象中,时间就如射出的飞矢一样一往无前,社会的进步也是如此,不断前行、臻于至善。由此,“新世纪”“新天地”“未来的召唤”“历史的要求”“进化的铁律”等时代信仰开始取代永恒不变的上帝或天道,被人们奉为圭臬,成为衡量和决定人们的善恶是非、思想行为的规则和标准。进化论及其演化出的进步主义的时间观认为人可以改变未来,由此未来成为建构人们的“历史”意识的最为关键但永不在场的要件,由此,现代性突出表现为一种态度,一种把个人、群体与当下和未来连接在一起的生存态度,正由于这种当下与未来的连接、自然时间的历史化,个人、民族的生存才被赋予了目的、价值和意义。莱茵哈德·科塞勒克(Reinhart.Koselleck)把“历史时间”出现的根源归之于“过往经验”和“未来期待”之间的断裂,人们开始期待一个不同的未来,而非期望过上祖先曾经经历过的生活。过去与未来就此被线性地连接起来,但后者与前者却并不相同甚至完全相反,只有实现了与过去的一切的彻底决裂,才能完全实现未来的目标。由此现实就成为留恋过去(永恒)的保守论者与瞩望未来的进步论者激烈争夺的战场;前者可以说是文明退化论者,即认为人类文明是由黄金时代向白银时代、英雄时代和黑铁时代的不断堕落和退化,与佛教所说的“末法时代”相似;后者则是从尚未实现的未来、终点来看世界的末世论者,他们所看到的现实是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巨大反差,只有未来才能拯救现在,进步主义的历史观赋予了他们一种“黑暗终结者”式的坚信,他们相信自己身逢一个光明与黑暗进行最后决战的紧要关头、面临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事因缘”,因此投身于这种推动历史车轮进步的神圣的事业开始取代对传统天道的信奉,而使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得到实现和升华。由此,自然、客观时间开始向社会、历史时间转换,个体生命的轻重之分、泰山鸿毛之别开始由历史的天平掌控、估定,正如1907年徐锡麟、秋瑾、陈伯平等反清革命志士牺牲后,在法国出版的革命刊物《新世纪》杂志在刊登他们遗像时的冠名,分别是“新世纪中国开幕大人物徐伯生”、“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女豪杰山阴秋竞雄君瑾”、“二十世纪中国开幕大人物陈先生伯平”,这种前所未有地将过去现在未来连接在一起的宏大历史意识,成为现代文学中的宏大叙事的来源。向超越过去的未来挺进的时代为这些把握先机、在历史中去创造历史的英雄提供了脚本和舞台,也赋予他们奋斗、牺牲的价值和意义。由此,效法自然、从天而颂的天道宇宙观开始为人所主宰的历史进程所取代,人类开始自编自演自己的戏剧,按照自己的意愿和目标在历史中创造历史,由此属于人自身的“真正的时间”开始了。 通过对时间意识的考察来揭示现代性观念的生成与演化是将该问题引向深入的一个途径。现代性首先表现为一种现时的观念,也就是要唤起人们对其生活的时代的正视,波德莱尔将浪漫主义者眼中的失望现时转变成了一种英雄现时,并由此使现代性成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现代性的时间意识依赖于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伊夫·瓦岱认为“亨利·梅绍尼克将现代性变成了既与主体的历史性又与意义的无限性相关的现时特质,也就是强调现代性既不存在于事物之中,也不存在于技术创新和历史断裂(否定过去或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创新)之中,而是‘存在于创造主体和主体的目光之中’,它是‘主观性的历史表现模式’是‘存在于我们自身的主体’,具有现代特征的东西,指的是那些在一系列不确定的现时中出现的东西:这就使时间发生变化,使时间成为主体的时间。正如波德莱尔所说:‘几乎我们所有的独特性都来自时间打在我们感觉上的烙印。’”⑦如此,当现代性没有一个客观的参照对象,只有一个主体时,“我们就会理解我们为什么不能像谈论一个自我封闭的概念一样去谈论现代性,也不能像谈论一种具有某些明显特征的价值观或某个具有明确时间标志的时代那样去谈论它。这就是现代性这一术语之所以在我们不仅要把被视为具有现代特色的不同现实,尤其是要把理解一系列不同现时的特殊方式称为‘现代性表现’时需要以复数的形式出现的原因。如果说现代性存在于主体的目光之中,那么,理所当然,有多少现代性就有多少种目光。”⑧也就是说对现代性的认定不能简单地求之于外,更重要的是要求之于内,它既与客观世界有关,更依赖于人的主观体验。阿拉贡在1929年为现代性所做的定义是,现代性是“一种表现某些事物情感时事的时间职能,这些事物的特性并不在于它们所表现出的创新之处本身,它们的有效性归因于它们的表现价值最近才被发现这一事实。”⑨伊夫·瓦岱激赏这种把现代性视为是一种“时间职能”的看法,认为“没有比这更好的说法。从定义上而言,现代性的价值表现在它与时间的关系上。它首先是一种新的时间意识,一种感受和思考时间价值的方式。为什么是新的方式呢?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就现代性一词所区分的两个主要含义相互发生联系:一个是波德莱尔赋予它的含义(‘短暂的、易失的东西’……也就是说不断变化的现时,它必然要给作品打上自己的烙印),另一个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范畴上的‘现代性’。正是这个社会的新面貌(自文艺复兴末期以来逐渐在西方形成)、它与旧世界和传统社会之间的决定性差异、它在其特有的动力作用下不断发生的变化,正是这些事实上在文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特点引发了一种更加敏锐的时间意识——一种使人对进步进行思考的发展的时间意识,也是一种对每个被迅速发展的历史运动所左右的时刻所表现出的独特性的意识。我们正是通过对这种现代时间意识的不同表现方式(正如它在造型艺术,尤其是文学作品中所体现的那样)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理解现代性这个概念所包含的那总是捉摸不定的内容。”⑩既往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往往偏于客观性的方面,往往将西方现代性设想为一系列的硬性指标,来核查自己是否达到了这种外在的标准,这显然忽视了现代性的主观性因素的作用。作为文学艺术中的现代性,它更多地为主体的不断超越的意志所左右,正如诗人兰波所言“必须绝对的现代!”作为一种时间职能,它将“新”与“好”之间画上等号,使其合二为一,以新奇、超前攻城略地,更新人对世界的感知,占据时代艺术的制高点。 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从三个向度来理解时间,第一个向度是物理时间、第二个向度是心理时间、第三个向度是人文社会时间,如此可以把时间的自然客观性和主观内在性、社会文化性结合起来,在深入把握时间本质、属性的同时,反顾人类自身的生存状态。时间观念由人类在实践中创造出来,它又会反过来又成为支配人类活动的一种观念的力量。所以在社会化的时间中又存在着一种权力关系,使人们无法摆脱其支配和主宰。一般来说,自然科学对时间的研究都属于自然时间范畴,心理学、文学、艺术等对时间的理解可以归为心理时间的范畴,社会学和历史学、文化研究等对时间的考察可以归为人文社会时间的范畴。三种时间是相互渗透、无法分离的,其中社会时间尤为重要,因为其“作为人的协同节律和共同规则,一方面体现为人们自然形成的生活节律,一方面体现为人们自觉遵守的共同规范。”(11)有论者认为自然时间主要体现着一种“物之关系”;心理时间主要体现一种“物人关系”;而人文社会时间主要代表一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深入理解时间问题的复杂性不无裨益。(12) 进入近代之后,关于时间的这三种维度都开始发生变化,近代以来中国人的时空观的巨变首先经历的是一种自然时空观的变化,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记》作为1900年首先被译为中文的西方科幻小说,代表着一种鲜明的现代性的时空观念,即时空分离、压缩意识,它突破了传统社会时空是与具体和特定的社会行动的地点相关联的概念,使时空分离并重新组合,使时间与空间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统一协调。用八十天时间环游地球这种时空经验对于栖息在自己的狭小生活时空中的人是不可想象的,这种时间对空间的征服也正是一种现代性的体现。而中国人自己所创作的第一部科幻小说、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1904年发表,主人公漫游亚、欧、美、非四大洲,都未能寻到得以安身的乐土,恰好偶遇来地球游历的月球人,于是决定乘气球前往文明程度更高的月球。这种自然时空视野的展开,也代表着现代性的征服自然的意向和信心。再就是社会时间的变化,不同于传统循环时间观的单向线性时间观与现代进步主义的历史时间观念的确立,表明追求无限进步的浮士德时间观占据了现代文学的主导地位,其源头可追溯至1891年传入中国的贝拉米的乌托邦小说《回头看:2000-1887》,该书用过去将来时倒叙未来的时间叙事模式成为大多近代中国乌托邦小说的摹本;严复的《天演论》则从自然进化论推导出社会进步观念,由此将人类历史纳入线性历史进步序列之中,中西方的空间性差异开始转换成时间性的历史阶段差异。政治文化上的西化诉求代表的是吉登斯所言的社会关系的超地域的抽离化倾向,它所呈现出的是现代性的普世性的一面。近代作家的历史意识大多属于初萌阶段,在以描摹世相为主的谴责小说中,那种具有现代救赎意义上的历史时间意识尚未确立,因为人们对未来会如何尚无定见,对于未来,人们多是如李伯元所言“大雨要下、太阳要出”而已,带有某种听天由命的宿命论色彩。至于像吴趼人那样坚信未来中国会像其在《新石头记》中想象的“孔道”国家那样保持固有儒家文化的连续性者,已属另类,在庚子之变后的崇洋、西化潮流中,难免迂腐之讥。那种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处在重大历史的拐点和开端,自觉的创造历史的时间意识主要是在五四时期确立的,即鲁迅所说的开创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人的时代的自觉意识,这是现代性意义上的时间开始了的标志;小说中的现代性叙事主要表现为一种将一切人类历史视为一部历史,在连贯意义上将过去和将来统一起来的元叙事,这种叙事经历了启蒙主义的个人——人类叙事和理想主义政治的集体叙事的过程,发展出一种社会决定论的全因果式的现实主义小说,一种将个人生活时间纳入到普遍历史时间中来叙述的模式。对现代文学中占据主导性的历史进步主义的时间叙事形成补充的是审美现代性的当下、刹那主义和注重表达个人内在感性体验的心理时间观。至新感觉派等都市文学兴起,空间性开始压倒时间性而出现一种祛深度化的将时间空间化的平面模式,这与都市化景观社会出现密切相关,在其后的文学中现实主义的历史时间观开始遇到挑战,时空体验趋向于个人化、内在化、心理化,由此表现出小说叙述时间的空间化倾向。时空体验与人的自我意识、生命意识、历史观、价值观的形成密切相关,它也成为文学表现的核心内容。 现代文学是相对于古典文学来确定其现代属性的,如此,从时间意识的角度考察现代文学的发生情境就很有必要。近代中国时间意识的古今之别突出表现为由儒家慎终追远的道体循环论的时间观,向现代瞩目于未来的时间观以及专注于当下的时间观的转换。传统的儒道释的时间观在这种现代时间观冲击下开始瓦解,而表现出从道的永恒本体向历史生成转变的趋势。儒家的时间观表现为一种以“天地之化”为宇宙“道体”的循环论的时间观,而“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周易·系辞传》,所谓道也就是指生生日新的大化之流,正如朱熹对孔子“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一语的阐释“天地之化,往者过,来者续,无一息之停,乃道体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见者,莫如川流,故于此发以示人。”(13)或如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所言:“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曰:由此,道是超越时间的流变的,时间对道并无本质性影响,由此“太阳之下并无新事”,而人生的意义就在于顺应天道,达至天人合一。由天之道推至人之道,就形成了儒家以人类世代生存为导向的血亲、继嗣的时间观,它以孝悌为基础,将人的血缘递擅神圣化为“天理”之外现,由此建构起一种人类普遍的伦理准则。这种由孝悌构成的时间连续性将宇宙时间和人文时间连接在了一起,构成了一种世代延续的道统时间观。它在现代遭到的最大的冲击来自于人的自我的发现,个人意识的觉醒,正如郁达夫所言“五四运动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的,现在的人总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无,何有乎君,道之不适于我者,还算什么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没有我,则社会、国家、宗族哪里会有?”(14)郁达夫的观点明显受到了斯蒂纳唯我主义哲学的影响,比较趋于极端,但即使是一贯站在“为中国文化说话”立场上的梁漱溟,也曾经尖锐地指出,“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上说话机会,多少情感要求被压抑。”(15)由此可知个人的发现,已成为时代文化的一种普遍趋势。这种反孝道、反传统的文化从清末即已开始发源,康有为在其《大同书》中就提出只有去掉“九界”,即国界、级界、种界、形界、家界、产界、乱界、类界、苦界,就可以使人类乃至众生到达美好的“大同”世界。蔡元培发表于1904年的乌托邦小说《新年梦》已提出取消婚姻、姓氏、家庭的“数字人”“配偶室”“幼稚园”的设想。到“五四”时的张申府更进一步地提出了“废国、灭产、绝婚姻”的理想,他在《新青年》发表了《个人不负罪恶责任》等文章,认为“社会是万恶之成就者。人性是罪恶之教唆者。吾们只有:革社会之命;调理人之性。”(16)由个人之不负罪恶责任,就可推导出“私德”在现代之无足轻重,重要的是改造社会、重塑人性,才是治本之方。由此他转向对理想社会的探求,结论是“对于社会主义自然要绝对的信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间,更没有第三者……现在摆在眼前的,已只有共产主义与资本帝国主义两条路”,“吾想创造的少年中国,乃是无产阶级的少年中国。”(17)由此可知,在现代性的文化进程中,传统慎终追远的继嗣时间如何转换成历史进步时间,而历史进步时间又如何重塑了人的自我认同,从而为人提供一种新的人生目标,造就一种新的人生态度,形成新的自我意识,由此产生出一种带有“超未来”色彩的理想主义的时间观,这种时间观也是未来指向的,但它与现实完全决裂,不再是与过去和现实保持连续性的将来,而是一种横空出世式的“新天地”的到来,这种跨越鸿沟式的历史化的乌托邦追求为现代中国的转型增加了巨大的变数和不可预测性。这本身也正是现代性的一种体现,因为现代性的本质也正在于“运动加不确定性”。 与历史主义的理性化的时间观不同,五四时期还出现了以朱谦之为代表的更为激进的虚无主义的时间观,他所追求的是个人的绝对自由和根本解决,由此他从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直推至宇宙革命,比无政府主义更进一步,他认为与国家、政府相比,天地才是最大之强权。消灭天地,政府与国家等强权便无枝可依,自然就消亡了。所以他呼唤“虚空粉碎、大地平沉”的虚无主义革命,“几时革到无天无地,无人无物,这才是归宿”。(18)他认为宇宙是从我心变见出来的,“情”为宇宙本体,“宇宙就是‘情’之化为理知者,因情化自身为客观、相对,有限的东西才为宇宙的森罗万象而现,故宇宙的存在,是因理知做背后的护持力,而理知这个东西,则不外分别彼此,其本身就是罪恶,和情根本相违,所以我们的宇宙,不是真情的实体,实为一种占有冲动的世界。而我们所能做的,也只是要脱离这虚伪的世界,到那本原的究竟的真实的本体去。”(19)他认为现在宇宙正处在“自有到无”的进程当中,要回归本体“无”,只有进行宇宙革命,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以他倡导一种“真我本位的人生观,就是我道主义,所以真正的革命者,都是肯定自我,而含有主张情热与破坏的无道德的性格,然这无道德,却是有道德的最大者,故只是一个真我,而真伪分明,只要在我确以为是,就要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真便存,伪便去,该爱时便爱,该憎时便自然憎他,憎呵!爱呵!都纯粹是一种真情的流露,也是真我的表现,由此可知我就是情,情就是我,因为情我合一,所以人生观上要实现真我,正是宇宙论说的‘复情’罢了。”(20)“我只知最有价值的是‘真我’,无论什么信仰,什么神,什么道德的义务,一切限制‘真我’的自由,阻碍‘真我’的前路的,革命者为着真理的向上努力,都要打破他,征服他了。”(21)他的“真我”本体论具有超宇宙、反宇宙、主宰宇宙的指向,因为“我比宇宙还大,宁可为我而牺牲宇宙;只有宇宙投身于我中,我决在宇宙中实现”(22),这种宇宙万有都挡不住我的我道主义显然是一种彻底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主张,但这正是时代个性解放精神的一种极致性表达,他的宇宙革命理论发表之后,在青年知识界得到了热烈的呼应,袁家骅、郭沫若、郑伯奇、郑振铎分别为之写序、赋诗,以表赞成,这是一种现代性的主客对立哲学的浪漫化表达,也就是确立自我和人类的绝对主体性、至高无上性,自我之外的一切都从属于我的存在,正如郭沫若在《自然与艺术》一文中的宣告:“二十世纪是文艺再生的时候,是文艺从科学解放的时候,是文艺从自然解放的时候;是艺术家赋予自然以生命,使自然再生的时候……艺术家不应该做自然的孙子,也不应该做自然的儿子,是应该做自然的老子。”(23)与老子的“复归于道”不同,朱谦之强调他的“新虚无主义”,它“不但如老子所说将精神真如出斯世,还要举宇宙的存在物悉灭尽之”(24),他不但要自有而无,还要自无而有,毁灭一切,重新再造一切。由此,朱谦之的时间观可称之为一种自我本位的真情流注的时间观,表现为时为情之感,空为情之应,“时间的意义就是现在”(25)时间与人的生命具有内在的关联,其时间导向则是当下体验。这种时间观可视为是清末以来的唯情论文学、哲学思潮的一种发展,清末言情派突破“理”(性)对“情”的束缚,转向“情”对“理”(性)的统领,都表现出一种自我本我的时间观对伦理本位的时间观的叛离,正如符霖《禽海石》把主人公的情爱悲剧归之于“周朝的孟夫子害的”。在唯情论者那里,所有时空体验都被情感渗透、主导,所以小说结构也表现为一种心理情感结构,主人公对时间的感知也是情感化的体验,典型如郁达夫的心理情绪结构小说。情本位者的时间体验是主观的、内在的、指向当下的,集中表达的是哀乐好恶,时间体验由此被染上了鲜明的情感色彩,如曹禺《北京人》中主人公愫方所言:“我们活着就是这么一大段既凄凉又甜蜜的日子啊!叫你想想忍不住要哭,想想又忍不住要笑啊”,这种真情流注的时间体验,也正是情本论者的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所在。 传统道家的时间观的特点是将道作为是超越时空等一切的无限本体,正如《道德经》所言:“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所要做的则是“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26)对道的体悟并将其贯彻力行,成为其哲学核心。而要体道,则需要致虚极,守静笃,与道合一,其极致之境则是“宇宙在乎手,万化生乎身”(27),即时空可自由掌控于手,万化萃乎一身,直至道成肉身。道家学说对中国古典的山林隐逸文学影响甚大,由此营造出一个超越于现实之上的审美逍遥之境。隐逸特别强调虚静的功夫,因为“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苏轼,《送参廖师》),只有“不撄人心”,才能感悟“天心”。而新文学则将这种人与天齐的自然时空引向社会时空,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28)由此传统“心应林鸟、情感林泉”隐逸逍遥的山林文学开始为“上与大陆争进化,下与动物争生存”(29)的竞存、抗争的文学所取代,人与自然的亲和性、精神性联系也为一种对立性、功利性的态度取代,这也正是现代性世俗化本质的体现。 佛教的根本在于其缘起性空观,所谓“缘起”,就是说世上万物都是因缘和合所生,由此因缘和合所生起的是假有,本性是空;如果自性不空,则不能有,所以说“真空生妙有”。佛教唯识宗将第八识“阿赖耶识”视为宇宙万有之本,因其能含藏生长万有之种子,故亦称种子识、藏识;而眼、耳、鼻、舌、身、意,以及末那(我识)七识都是由根本识即阿赖耶识变现而出,所以被称为“转识”,靠它们是把握不住宇宙间真实本体,即真如本相的,而真如本相则是“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心经》的,所以它是超越于时空的变化的永恒本体,故而佛教注重的是“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的当下共时性;《金刚经》中也强调:“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佛教把指向过去和面朝未来的人生态度都视为是一种颠倒幻想,它讲的是“当下即是”“日日是好日”,强调的是向内的“自净其意”才是解脱之道,而非外求,将希望寄托于未来外在的变化。这种面向“净土”的彼岸的时间观显然与现代性的将人间改造成“净土”的理想主义信念迥然异趣,所以它在现代受到冲击是可以想见的,现代性采取的认识世界的方式恰恰是佛家所视为虚妄的“眼耳鼻舌身意我”这前七识,即以自我身体性的存在为基础的主观体验和以物观物的客观知识,在其中超越个人主观意见和客观知识之上的“道体”“真如”已被视为无稽的“玄学”,失去立身之地;或者说人们开始只信赖“现量”和“比量”,而对“圣言量”失去了兴趣。 总之,在走出了儒道释的永恒本体论的时间观之后,现代性主要发展出两种时间体认模式,一种是在过去、现在、未来组成的时间维度中以指向未来为导向的时间体认模式,也就是说它强调的“现在是未来的现在”,未来决定了现在的选择,赋予现在以价值和意义,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时间观;现代文学的主流代表着这样一种时间观,它是一种致力于推动社会进步的时间观;另一种这是一种活在当下的时间体认模式,它与过去、未来都失去了从属关系,既无意做过去的嗣子,也无意做未来的先驱,时间在它那里表现为一种内在的当下的心理体验,只有先后顺序,而无与过去和未来的有机关联,如朱自清所提出过的“刹那主义”的人生观,就是这样一种带有审美主义的现代性倾向,两种时间意识构成了一种对立互补性。 2015年3月18日于天津 ①[美]巴恩斯通编:《博尔赫斯八十忆旧》,西川译,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134页。 ②[阿根廷]豪·路·博尔赫斯:《博尔赫斯全集·散文卷(上)》,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 ③余华:《余华研究资料》,洪治纲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6页。 ④吴国盛:《时间的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⑤"Introduction",The Voice of Tmze,The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81. ⑥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⑦⑧⑨⑩[法]伊夫·瓦岱:《文学与现代性》,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1-42页,第42页,第42页,第43页。 (11)(12)汪天文:《时间理解的三个向度》,《深圳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 (13)朱熹:《论语集注》,四书五经上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8页。 (14)赵家璧主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序》,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 (15)梁漱溟:《梁漱溟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83页。 (16)(17)张申府:《新青年》第9卷第6号,1922年7月。 (18)(19)(20)(21)(22)(24)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第一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91页,第397页,第383页,第382页,第381页,第396页。 (23)郭沫若:《〈文艺论集〉汇校本》,黄淳浩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9页。 (25)朱谦之:《朱谦之文集》第三卷,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页。 (26)(27)任法融:《黄帝阴符经、黄石公素书释义》,三秦出版社,1999年版,第44页,第52页。 (28)陈独秀:《新青年》2卷6号,1917年2月1日。 (29)白叚:《十五小豪杰序》,舒芜等编选:《近代文论选》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