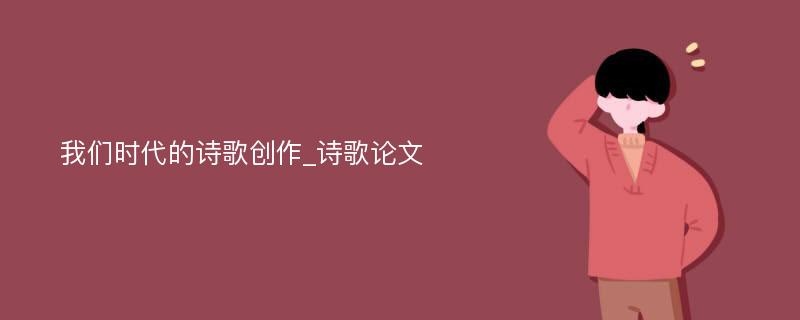
我们时代的诗歌写作,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0、开头
在一个理想的时代,这篇短论是不可思议的。阿兰·谢里登(AlanSheridan)说:“在博尔赫斯的完美世界里,惟一可能的评论也许是把某学科的著作汇集起来的手抄本。”(注:阿兰·谢里登:《求真意志》(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页。)遗憾的是,这在今天无论如何已经完全不可能了。这是个碎片的时代,关于时代的真知灼见以碎片、断章而不是以整体的形式散居各处。歌德曾以轻蔑的语气对时人说:“谁不倾听诗人的声音,谁就是野蛮人。”想一想吧,歌德是多么的幸运,他出生在一个诗歌满怀信心的时代。那时,上帝还以慈祥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缪斯女神正值青春妙龄之际,诗歌呢,则有如秋天成熟的果子,自动落在牛顿——对他我们无以名之,只好将他称做开天辟地的宇宙世人——的头上。因此,这位宇宙诗人才说:“我们呼他为‘我主上帝’。”(注:H.S.塞耶编《牛顿自然哲学》(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49页。)这也就是海子曾经说过的,诗在更多的时候是实体在倾诉;你也许会在诗里听到另一种声音,海子说,这就是“它”——实体——的声音。这里用得上象牙塔里的写作者张爱玲的一句话来描述海子,不过得反过来用:他比时代来得更晚。实际上,对于今天的时代而言,诗人就是来得太晚、搭错了时代之车的“怪物”,有如圣·伯夫满怀惋惜地说波德莱尔:他是个未赶上趟的浪漫主义者。在圣·伯夫眼中,波德莱尔就是一个在浪漫主义早已完结的时代来到人间进行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好汉。
诗歌已经湮灭了,这是时下许多人的共同看法(注:参阅辽南、荣炯《太阳老了》,载《艺术广角》,1990年第1期。)。我不敢有其它奢望,只想在这里唱唱反调:把散见在各处的碎片穿起来,也许我们可以由此描出一张关于这个时代的“地下地图”。能否达到这一目的,全要仰仗我的运气了。
1、晚报时代/小品心态
抓住自己的头发就想飞离地球,白痴都知道这是“痴”人说梦、“痴”心妄想。时代和地球一样,也有它自己的周期、恒量、加速度和引力场。我们的时代呢?且听海子的幽默吧:
猛兽:要知道,我们都是反王的儿子。
二人:我们在沙漠上就知道了。
猛兽:兄弟,你们聊吧,我下去练一会靶子。
(海子《太阳·弑》)
我们的时代就这样成了“靶场”(这样说或许有“误读”海子之嫌)。它最直接也最容易被发现的物质体现是晚报。晚报是我们时代的象征。晚报不仅顺应了这个时代,而且还部分地开创了这个时代。有人说,这是一个信息的年代;假如此说还有几分真实的话,晚报的出现恰可谓生逢其时:今天的信息是明天的垃圾,明天的新闻恰好是今天的方糖,也就是挂在驴脖子上、能让驴子忘我赶路的那截萝卜。在中国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晚报时代随着商品大交换的来临而来临了。而以晚报为舞台的则是铺天盖地的小品文,生、末、旦、净、丑躬逢其会,少长咸集,恰可谓新一轮的兰亭集会或藤王阁赋诗。
原始儒学经董仲舒、二程、朱熹的精心打磨后,原先那点微乎其微的鲜活(比如“天行健”、“知其不可而为之”、“人定胜天”等等)早已成为过眼云烟,正所谓“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禁锢已久、早已心怀不满的人们则另辟途径。道、玄、禅的互相需要以至于“哥俩好、三桃园”似的联手,至迟在明清之际就完成了新一轮的“桃园三结义”:以表达性灵为幌子,把一切重大、严肃的主题通通转化为“趣味”。严羽说得妙极了:“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注:严羽:《沧浪诗话·诗辨》。)活活为桃园三结义充当了开路先锋。况周颐则心平气和地呢喃:
人静帘垂,灯昏香直。窗外芙蓉,残叶飒飒作秋声,与砌虫相和答。据梧冥坐,湛怀息机。……乃至万缘俱寂,吾心忽莹然开朗如满月,肌骨清凉,不知斯世何世也。(注:况周颐:《蕙风词话》。)
果然是老僧禅定、内心恬静,却了无沉重生命的大欢叫,更不用说灵魂在繁复事境面前的巨大战栗了,有的只是轻描淡写的小情小趣。性灵、空灵、舒卷……等等小品特征,把发自人生骨殖深处的悲惨特质视若无物,把时代深处蕴涵的苦难骨髓置若罔闻。我们从不缺少灾难,也从不缺少痛苦,缺少的只是对灾难和痛苦的深入审视、仔细思考与详加咀嚼。如果考虑到传统的惯性作用,那么,从历史上传承下来的“小品心态”就是晚报时代改头换面的典型心态。小品心态是道、玄、禅结义的结果,其特征是将生命在繁复事境面前的一切反应仅仅转化为小猫小狗似的趣味。——这是一种典型的嬉皮士作风,是超前了几百年的“后现代主义”,假如还可以这样比喻的话。据说中国文化是什么“乐感文化”,“日新之谓盛德”,“天人合一”,“天行健”,“日日新”,“苟日新”,“又日新”……云云,言犹在耳。李泽厚据此认为中国没有真正的悲剧精神。李泽厚是对的——假如我们把小品心态拉在一起来考虑的话。
如果小品心态在明清之际是以反击宋明理学的面孔而出现,今天的小品心态则是和晚报时代合谋的一个爪牙,它以文化人的参与、写作者的主动献身为标志。晚报心态的特征是:它快速地展现晚报时代中人的平面化的情感,以及与此情感相关的一切——诚如鲁迅所说,它压出了晚报时代中人的皮袍下的“小”来。一个时代注定需要某种心态,某种心态也注定需要对应某个时代。两者的不合拍,固然是双方的扑空;而一旦握手言欢、青楼梦好,则分明是皆大欢喜,“大红灯笼高高挂”了。M.Scheler在《死与永生》中说,世界不再是真实的有机的家园,不再是爱和冥想的对象,而是冷静计算的对象和工作的对象。正是在这一点上,晚报心态与我们的时代有了一拍即合的地方。
表面看起来,晚报心态是对“物吃人”、“商品拜物教”的逆动,实则不然。晚报心态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心态在新时期的改头换面,一切事境甚至堪称惨痛的事境,仅仅被当作快速处理的对象,有如晚报新闻的快速一样,并将这一切盛在“趣”的痰盂中,却对晚报时代的“噬心主题”(陈超语)充耳不闻。想想看,人们从“商品交流”、“情感交换”之余买一份晚报,在公共汽车上,在餐桌边,甚至在厕所里,在悠闲的饭后的茶桌前展开报纸,读一读上面的小品文章,大多时候人们会对之报以会心一笑,然后抛到一边,直至化成纸浆。这种种动作也许恰好反证了小品写作者是把小品写作当作了“茶余饭后”,读报人的心态与写作者心态恰是同一个心态。晚报时代豢养了小品心态,小品心态也是聪明人选择的晚报时代的最佳对应物。有词为证:
记得当时,我爱秦淮,偶离故乡。向梅根冶后,几番啸傲;杏花村里,几度徜徉。凤止高梧,虫吟小榭,也共时人较短长。
今已矣!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无聊且酌霞觞,唤几个新知醉一场。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吴敬梓《儒林外史·篇末词》)
不排除这种呻吟中有令人感慨的内容,但也恰好道出了晚报心态的心声。甚至这中间的许多词汇的各种变种正是时下晚报小品文的共同遗产。更重要的是,既然“百年易过”,当然也就无须“愁闷”,只闲情逸致地饮些朝晚霞罢了;既然颇“费商量”,当然不用去关心什么“千秋”事业,否则“断肠”之势就在所难免,实在有些犯不上。清人沈复曾自述说,他父亲在家宴上点了一出《惨别》,而沈复的妻子居然不忍心观看。“余曰:‘何不快乃尔?’答曰:‘观剧原以陶情,今日之戏徒令人断肠尔’。”(注:沈复:《浮生六记》卷一。)小小的离别,不惟在沈复笔下能令人“断肠”,在今日的晚报上也同样表演得凄凄惨惨切切。饭后的蒙太奇,小恩小惠的思想火花,对生活的一汤勺感悟,吃饱了撑的似的闲情逸致,顶多再来点“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一首流行歌曲的唱词)的不痛不痒的呻吟——这差不多就是与晚报时代相对应因而能适者生存的晚报心态的全部内容了。
后现代主义据说早已来到了中国。小品心态通过和晚报时代的结盟与合谋后,再加上一个平面化、能指化的后现代主义,其“三位一体”取代了“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似乎已成必然之势——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小部分在新时代的借尸还魂,其“解构”能力、“颠覆”爆破的本事也由此可见。在这种情况下,诗歌也在向晚报时代靠拢;汪国真不是第一个标本,出于同样的原因,他也决不是最后一个。
完整的、整体的歌德不会再出现了;但碎片的歌德还在真正的诗人身上安家落户。柏桦就以略带羞涩的口吻说:“我是歌德/不是吃饭。”(柏桦《家人》)是“歌德而不是吃饭”的人显然是晚报时代的异数,是拒不向晚报时代投诚的“刁民”。普罗提诺说:“伟大的和最后的斗争在等待着人的灵魂。”(注:参阅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中译本),三联书店,1988年,第13页。)这里所说的灵魂,当然不是指小品心态,而是指和晚报时代作对的人以及他们身上碎片的歌德。
2、诗歌意志/诗歌时代
人是否能脱离自己的时代引力而飞翔,也就是说,能否抓住自己的头发飞离地球?不管对此设问的回答如何,却正是晚报时代里真正的诗人要努力做的事情。一位无名的诗人写道:“流浪诗人是万物的领唱者,他敢于歌颂虚无/并把万物的歌唱缩为一句!”正是在“敢于歌颂虚无”的最成功的时刻,诗人脱离了时代的引力并向上飞升。然而,正因为时代是晚报的时代,他们的成功相对于主流时代,不过是一次超常、脱轨,归根结底也只能是碎片。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渴望的、幻想的时代因而只能以碎片的方式呈现出来;但这些闪光的碎片,恰好是晚报时代覆盖下的诗歌时代。诗歌时代是晚报时代的反动,是晚报时代浅薄空气里的深度,是骆一禾所谓的“世界的血”。假如说人类发展是一个不断由史前时代向现代化时代过渡的过程,因而时代的世俗化、晚报化在所难免,那么,诗歌时代则是一个逐渐从“地面”转向“地下”、从整体转向碎片的过程,如同卡夫卡曾精心描绘过的地洞和地洞中人。但是,诗歌作为人类精神,以整体形式(即与主流时代合拍从而成为地面运动)出现也好,以碎片方式(即主流时代疏离从而成为地下运动)现身也罢,却始终生生不灭。“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注:《庄子·养生》。)因此,谢林才说:“不管是在人类的开端还是在人类的目的地,诗都是人的女教师。”
和晚报时代对应的是小品心态,与诗歌时代对应的则是诗歌意志。诗歌意志先于诗歌文本而存在,它是诗人潜在的内心要求,独立于客体对象和艺术创作方法而自为存在(注:参阅沃林格《抽象与移情》(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2~40页。)。不过,说它“自为存在”并不是否认它有形成的原因,仅仅是指它与诗歌文本的先后关系。事实上,诗歌意志的形成取决于诗人的世界感;而世界感则来自于人的日常应事观物所形成的世界态度。最重要的也许还在于:诗歌意志与小品心态不同,前者更关心来自人生骨殖深处的精神丝缕,更关心隐藏在时代底部的宿命特质,以及潜伏在时代和人生内部的苦难光芒。它关心的是人,尤其是人在时代中的命运。
命运是永不衰竭的常动之物,所以诗歌不会消亡;晚报时代不大关心命运,因而诗歌时代只是碎片的时代。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女诗人写出了晚报时代平凡人生的伟大素质:“光线是共同生活的象征,/……光聚合在一起/神圣的事物就胜利了。”她对一位死去的老妪怀有压抑不住的颤栗般的情感:“通过对生命的遗忘/她将活着的荣誉保持到了老年。”(汪怡冰《光的荣誉·沉默的安慰》)这些“光”,这些“荣誉”,早已被晚报时代和小品心态上下其手给打发掉了。晚报时代在这个时候是粗线条的,而诗歌时代则从细节起航:它要从光、从荣誉开始。
以经典展开的形式展开人生演义的诗人在此感到了深深的震撼,他们与晚报时代之间的紧张关系也更加显而易见。欧阳江河写出了这样的句子:“告诉那些吸水者,诸神渴了/知识在燃烧,像奇异的时装/紧身的时代,谁赤裸得像皇帝?”(欧阳江河《最后的幻象·书卷》)没有担当命运,没有和命运相撞击,没有进入苦难的神髓,所谓观察时代其实也就是过目无心,视而不见。我们说,只有拥有了强大的诗歌意志,才可能写出欧阳江河那样锋芒毕露的句子。正如刘翔赞扬梁晓明那样:“他一开口就落下一个白昼。”(注:参阅民刊《北回归线》1993年号,第162~170页。)对于欧阳江河,我们有必要再追加一句:“他一开口就落下一个夜晚。”是的,夜晚。那是休息和酣眠的软床,却是命运和苦难的演兵场。造物主想得真周到,在不休息的命运和苦难面前,他为一部分人设置了休息的黑夜,让他们有时间舔舐伤口,以待来日再战。难怪海子要把夜晚称做自己的同母兄弟,要把黑夜当作自己的口粮;而荷尔德林则称夜晚为“神圣的黑夜”,难怪茨维塔耶娃在给里尔克的信中要神情亢奋地喊道:“为了让高山和夜晚押韵!”
命运和苦难在上下其手。曼德尔斯塔姆写道:“在自杀者高大严肃的办公室里/响起了电话铃声!”这是朴素的然而也是精妙绝伦的句子。它昭示出,命运和苦难正在召唤人们,正在追赶人们;它永远都是现在进行时。马丁—布伯曾说:“祈祷不在时间之中,时间却在祈祷之内;牺牲不在空间之中,空间却在牺牲之内。”(注:马丁—布伯:《我与你》(中译本),三联书店,1988年,第20页。)布伯是对的:祈祷与牺牲最终是超越时空的,因为祈祷和牺牲是苦难与命运的永恒主题,或者说是苦难和命运的两叶翅膀。苦难、命运根植于人性深处;祈祷和牺牲则是以反击它们的姿势出现。没有了祈祷和牺牲,诗人就休想在苦难和命运中发现更深的东西,或者说,发现让人心痛的希望、“把活着的荣誉保持到了老年”的生命特质。
3、批判/精神传记
晚报时代从各个方面渗入了我们的生活。诗歌在夹缝中以碎片的方式闪光。诗歌时代要想拥有合法的时空,批判就是不可或缺的。批判首先是一种观察世界与时代的角度和思维方式,是与诗歌意志紧密相连的精神气质。诗人正是携带着批判进入晚报时代,并因此走出晚报时代而进入诗歌时代。是批判最终使诗歌时代在晚报时代生成,尽管它以碎片的方式存在;诗歌时代也因此成为关于人间命运和苦难永恒的精神传记。
周伦佑说得好:“深入老虎而不被老虎吃掉/进入石头而不成为石头/穿过燃烧的荆棘而依然故我/这需要坚忍。你必须守住自己/就像水晶守住天空的透明。”(周伦佑《石头构图的境况》)的确,批判的前提是“坚忍”,是“守住自己”,是拥有“水晶人格”;是始终用变动不居的“我”去探索变动不居的晚报时代,在晚报时代强大的惯性与火力面前,回答它的提问,使它有局部败退的可能。批判因而能重建诗歌时代的合法时空。诗歌写作必然是“红色写作”。从书本转向现实,从摹仿转向创造,从逃避转向介入,从水转向血,从阅读大师的作品转向阅读自己的生命、阅读自己生命中固有的命运和苦难特质——如周伦佑所说:只有这样,诗歌不但拥有了自己的时代,也健全了自己的使命。
但首先要从天空转向大地。曾经飞翔的梁晓明如今用老练的口气谦虚地说:“我要写一首诗/一首超越翅膀的诗/它往下跌/不展翅飞翔。”(梁晓明《夜》)而“往下”就是泥土,就是坚实的大地,就是凡人们生息的场所。王家新则说:“一切来自泥土/在洞悉了万物的生死之后/我再一次启程/向着闪耀着残雪的道路。”(王家新《诗》)是的,大地和道路,这联体的双胞胎。海德格尔则这样指称:“是诗歌作品使大地成为了大地。”但是,我们的大地不是西餐式的神性大地,而是生息着的中国人的道路,是海子所说的“地母”。在大地上,最生动、最震撼人心的就是跨越苦难、跨越命运而又始终在这两者之间迈动的双脚。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一开篇就曾深沉地说过:“世界不是事物的总和,而是事实的总和。”而“事实”不独是时间性的概念、物理性的概念,更是大地上的人,是长在大地上的脚和腿的森林。海子曾担心地指出:由于丧失了土地,人们只找到了肤浅的欲望。海德格尔是对的:大地需要重新被发现。而欲望,在我们的时代,正可以说成是晚报时代的固有属性;将欲望斥之为“肤浅”,明显就是锋芒直指的批判了。因此,要找到干净一点的大地,我们只有对土地首先采取批判的姿态,并试图从中清除晚报时代中广泛的污秽物。批判的方式也因此成为对时代进行精神分析最主要的方法,是对时代进行认证的良策。这种精神分析的精髓仅在于:它试图从晚报时代里诱发出诗歌时代的精神自传,并且通过对被忽视的插曲的发现和事件关系的澄清而改写它们,这样,就会使诗歌时代的精神自传从晚报时代的肢体上分离出来。诗歌时代的精神传记:晚报时代枕边遗落的梦呓。在小品心态“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独眼里,那也只不过是梦呓罢了。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巴尔扎克忘记了补充一句:诗歌更是一个民族更为隐蔽的秘史。“秘史”的首要涵义就是潜藏的和被覆盖的。中国是个缺少史诗的国家,要想在今天这个晚报时代重建史诗似乎是痴人说梦。但是,我们有权利、有责任、也有能力提供一个时代的“秘史”,一个时代碎片式的精神传记。精神传记就是秘史。而所谓诗人,就是那类对人类和时代困境与困乏有着无法摆脱的内疚心情的人,所以他们以批判的姿态面世;在今天,晚报时代君临天下,小品心态四处流播,命运、苦难、屈辱被抛掷一边已经成为时尚,乐观地向“前”看和向“钱”看已经是心照不宣的事实,而诗人则想对“内疚”进行反思和抒写,对命运和苦难进行批判与吟咏,并以此为潜在的时代——这正是亘古以来同一个命运的时代——画像,为我们提供一份活生生的秘史,这既是诗歌的光荣,也是精神传记的潜在要求。
4、生命/理想
在晚报时代构筑诗歌时代,最基本的起点就是阅读自己的生命,阅读人的生命。阅读生命同时也是从天上转向地面的根本要求。从天上转向地面,其实正是人对大地的批判;阅读自己的生命,其精义也在于批判生命,因为没有批判性内涵的生命是不足取的,也是不足为凭的。生命是一个谜,也许永远都是一个谜。它将作为茫茫宇宙的中心问题困扰我们,直至人类的终结。但生命并非一个不可言说的问题。迄今为止,对生命有两种最主要的看法:一种认为生命是具体的、历史的;另一种则认为生命是超时空、超阶级的,生命大于它的时代,是一切时代的主宰和目的。
其实两者都不完备。第一种看法最大的缺陷并不在于它的机械主义性质,而在于它可怕的逻辑:既然生命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范畴,它理所当然要受到具体时代的规范,所以,生命作为祭品、作为供奉时代的牺牲,也就获得了合理性、可能性甚至现实性。第二种观点最大的毛病并不在于它浓厚的形而上学特性,同样在于它可怕的逻辑:既然生命是超越时空的,没有历史内容的,生命也就一下子被推入了没有存身之处的尴尬境地。对我们来说,假如事情真的如此,我们又何谈在晚报时代构筑有关命运和苦难的诗歌时代呢?
正如辩证法充满喜剧色彩所认为的那样,两者都有可取之处。第一种看法正确地道出了生命的具体性;第二种则点明了生命的绝对性。也许,只有将生命的绝对性和具体性统一起来,才能构成生命的真正内涵:生命的具体性因为强调了历史/时代内容,使生命的绝对性有了在现实环境中的立身之地;生命的绝对性因为高度强调了生命的绝对价值、神圣尊严,使生命的具体性没有任何理由假借时代的要求、历史的冰冷旨意来强迫生命作为祭品,或者使生命作为薄情寡义的晚报时代用以交换的商品。如此,我们就可以得出一副生命的全息图来:生命的绝对性的实质是,它始终包含着生命的恒向上性。恒向上性横跨古今,与生命相始终。由于有生命的具体性存在,与具体的苦难战斗和杀伐的对手——生命的恒向上性——也因此有了具体的对象、具体的性质,从而成为具体的、有着鲜活时代内容的恒向上性。比如说,在晚报时代,生命的恒向上性就体现为对苦难和命运深度的关心,它极力想建筑自己的诗歌时代,描绘自己的精神传记,它所杀伐的对象就是和晚报时代相对应的小品心态,当然,更是晚报时代本身。
所谓苦难,就是阻止恒向上性的完成与升华。苦难是恒向上性所有羁绊之物的总和。恒向上性是生命的根本特征,它首先体现为纯粹的生物性的求生意志,其次才体现为渴求价值赋予的求生意志。恒向上性和苦难一样亘古长存,和人类相始终。由于苦难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容,作为抗体的恒向上性也因此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面貌。海子问道:
你们抚摸自己头颅的手为什么要抬得那样高?
你们的灶火为什么总是烧得那样热?
粮食为什么流泪?河流为什么是脚印?
屋梁为什么没有架起?凝视为什么永恒?
(海子《传说》)
这几个问号既是对生命恒向上性的逼问,也是对苦难的逼问;有生命的恒向上性在,就有苦难的立正侍候;当然,反过来说也一样。
恒向上性的实现就是自由的实现。自由是发自生命底部的渴求;但是,自由的实现永远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梦想,它的完成只有阶段性、具体性,却没有终极性。但人对自由的渴望却永恒存在,这只要我们回忆一下历史上许多哲学家乐此不疲地给我们开设的有关理想国、乌托邦、大同世界、上帝之城……的清单和处方就可以明白了。它表现在人的本质上是绝对自由的梦想,表现在诗歌中则是真正的浪漫精神,是构筑我们的诗歌时代、精神传记的主要法宝。真正的浪漫精神就是由于生命的恒向上性和具体的苦难相互杀伐、搏击而渴望胜利的永恒冲动。
人类对绝对自由的渴望虽然归根结底只是虚幻的,但又是不灭的。我们可以把这种重新定义过的浪漫精神的核心称做理想。理想是诗歌时代的精神传记的内核。它的实质是人对现时代所持的超越态度。理想诚如许多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将人和动物最终区别开来的明显标记。在此,理想有着双重身份:对人来说,它可以被看做结果;对诗来说,它又是一个需要不断重临的起点。由于诗歌在骨殖深处和人的联系,使理想在人那里作为结果而在诗这里作为起点;而起源于生命深处的浪漫精神直接转化为诗歌的真正内涵,浪漫精神与理想在诗歌的起点处也就紧密相契与相合。
理想是自由的实质。自由在此也有双重身份:对人来说,自由的实现只有阶段性、具体性;对诗来说,它却可以帮助人在批判性的想象中,构筑这种理想的境地,也就是我唠叨了多时的诗歌时代。在诗中,自由不仅作为人的目的,而且作为浪漫精神的目的,同时也作为诗的目的而出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浪漫精神与起源相同的悲剧精神才得以彻底区分开来:悲剧精神表征的是恒向上性和苦难人生相搏杀的过程,它无力达到、体验和构筑作为结果的自由。
在我们这个晚报时代,真正的诗人选不选择浪漫精神(即理想与自由)来构筑自己诗歌时代的精神传记和秘史,最终也许只有一种回答。
5、结束语
当乌鸦高叫的时候,必定是夜莺闭嘴之时(注:参阅EricThompson:T.S.Eliot,SouthernIllionoisUniversityPress,1963,p3。);而在小品心态、晚报时代、生命被通俗化解释、恒向上性被极力减缩的今天,必定是诗歌转入“地下”之时。一边是看不见的硝烟广被四野湮没的商场,一边是与之相呼应的小品心态,在此情况下,深得游击战术精髓的地下诗歌的兴起,不过是“敌”对双方都能理解的战术而已。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有一个惊人的预言,这个预言曾经让已故诗人骆一禾惊愕不已:光在大质量的地方偏转。晚报时代就是大质量的,其引力足以使所有的光回到时代的大质量本身,而地下诗歌仅仅是凭着强大的诗歌意志侥幸逃逸出来的几束光罢了。是地下诗歌组成了诗人自身的诗歌时代,这个时代注定只是碎片式的;但它并不是海子所说的失败,倒不如说是某种成功。
民间诗刊的兴起标志着地下诗歌的兴起。曾几何时,最纯正的诗歌作品都首先是在民刊上出现的。民刊的出现,是诗人构筑自己碎片式诗歌时代的有力武器,使吟唱命运的诗歌时代承续了自人类始祖那里就点燃的诗歌之火、命运之火。民间诗刊不仅仅是刊物,更是一种特殊的观察世界和时代的思维方式。它从一开始就和晚报时代作为主流思维方式的小品心态划清了界限,以来源于命运本身的诗歌意志为触角重新观察命运。这是一个刚刚兴起的晚报时代,却又是早已兴起的民间诗刊的时间段落。一大批民间诗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纯粹晚报时代中人不可能看见的另一个时代。它选择了近乎宿命的现代浪漫精神和批判性的理想主义。这里用得上马克斯·韦伯的高论:如果我们不是反复地追求不可能的东西,我们也无法实现看起来可能的东西。民间诗刊早就弄懂了这一命题。从各种意义上说,民间诗刊都一直在追求那种不可企及的、不可能的东西。但它们终有所得。最起码它们已经贡献出了一大批诗歌杰作。作为晚报时代的陪衬物,这批傲视王侯的杰作让我们感到了真实的惊讶。
许久以来,人们或好心或恶意地抱怨我们时代已经没有了诗歌的存在;“诗歌已经奄奄一息了”就是最常见的说法,雨果曾说,不是没有美,而是缺少发现。对于好心抱怨的人,他们只需要“往下看”就行了。那里是诗歌产卵的地方,是新的时代然而又是亘古长存的时代再次怀孕的居所。(1997·4·上海)
通讯地址:中央民族大学文学院中文系邮编:10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