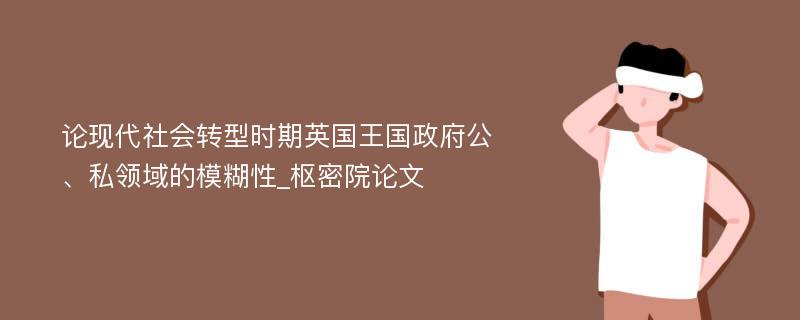
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英国王室政府公域和私域的模糊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英国论文,王室论文,近代论文,模糊论文,时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56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8X(2007)05-0058-04
伴随着民族国家的逐步建立,中世纪阙如的“公共领域”开始形成并逐步发展。但中世纪以来英国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私人领域”仍有强大的生命力。在政府形式和政府管理层面则体现为“公域”和“私域”的相互渗透、交叉和重叠,由此而造成英国王室政府公域和私域的模糊不清,并使得近代初期英国王室的政府体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政策具有鲜明的特色。学界关于公域和私域的理论阐释多见于哈贝马斯的著作。哈氏在论述公域和私域问题时,主要着眼于公众舆论、社会团体和公共信息,且时段也是从17世纪晚期始[1]。近代早期特别是都铎和早期斯图亚特时期英国政府中的公共空间的阐述所见不多,本文论及的公域和私域模糊性的问题,学界更是鲜有涉及。
在欧洲中世纪,“公”和“私”在罗马法里虽然截然对立,但没有约束力。封建社会里不存在古典(或现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对立模式。在封建领主所有权(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采邑所有权)作为一切统治权的总和的前提下,私人占有和公共主权这一对矛盾并不具备。王权有高低之分,特权有大小之别,但不存在任何一种私法意义上的合法地位,能够确保私人进入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引用布鲁纳的话说明这一情形:“如果我们把国家看做是公共领域,那么,我们在庄园和领主所行使的权力中遇到的就是一种次一级的公共权力,相对于国家的支配权力,它是一种私有权,但是,它和现代私法制度所规定的私有权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在我看来,‘私人所有权’和‘公共所有权’在封建社会显然是融为一体的,它们同源同宗,都依附于土地,因此,也可以把它们当做私有权对待。”[1]5也就是说,在中世纪不存在所谓的“公共领域”,或者说“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是一体的。
14、15世纪欧洲持续不断的经济、社会危机标志着封建生产方式发展到中世纪后期陷入困境并达到极限,最终促成了16世纪绝对主义国家的出现,法国、英国和西班牙集权化君主政体是与金字塔式的君主制及其领地制、封臣制这一整套中世纪社会结构的决裂。[2]3因此,从16世纪开始,欧洲,包括英国进入了一个历史转折时期,学界也称之为近代社会转型时期。这是一个动荡变化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社会文化方面都在从中世纪的特性中剥离出来,日显近代特征。时代的转变促使英国政权形式和性质发生了变化,以王权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逐渐建立,近代意义的政权架构初具雏形,民族国家初步形成,但中世纪时期的政权统治观念及统治模式依然存在,因此,其政权性质带有新旧社会的双重痕迹。
亨利八世时进行了“政府革命”,基本上建立了近代早期的英国政权模式。这一政权基本上是建立在旧封建贵族和新兴阶级的基础之上的。恩格斯将这一形式的政权称之为旧贵族和新城市资产阶级之间力量平衡的产物:互相斗争的各阶级达到了这样的势均力敌的地步,以至国家权力作为表面上的调停人而暂时得到了对于两个阶级的某种独立性。”[3]168正因如此,在这一时期,英国国家政权中的权力分配呈多元化趋势,并通过一定的政权组织形式表现出来。各种权力都在不同程度的发展,由此,各种权力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并由此造成政治权力的斗争,引发出政治危机。[4]27-51
在这一政权之中,国家与君主、公域和私域的界限模糊不清,甚至混为一谈。都铎到早期斯图亚特的君主们尽管没有提出“朕即国家”的观念,但是,把王室与政府视为一体。然而,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就是国家性质的转变过程,人们对国家的公域性也开始有所认识。在政权的实践过程中,公域观念虽然不明晰,但已有所体现。如,关于王室财政的界定:王室日常开支是王室自身的事情,应主要由王室领地收入来解决,也就是传统的“国王应该以自己的收入来生活”(the King should live of his own)的观念,[5]33而战争等开支被认为是国家的事情,因此,须由议会通过从公共经济领域征收税收加以解决。而议会特许税不是随意可以征收的,这种税金的征收“只有在专门的事务上,主要是国防的事务上才是合法的”,如,“1540年代,为了对法国作战,议会同意亨利八世征收补助金,总数在650 000镑。”[5]35,65一方面,这一时期王权越来越多地通过掠取公众资源来满足王室的需要,可以说是掠夺公域资源,满足私域的需要;[4]64-67另一方面,作为王室政府而言,所建立起来的行政制度又有管理公众事务的功能,在当时作为以公众事务管理为主要功能的枢密院,到早期斯图亚特时期,枢密大臣增加,各种专门的常务委员会及其附属委员会成立,[6]23-24显示了政府又是公域和私域的混合体。因此,一般情形下,无论是政权的构架、权力的配置还是对资源的占有,在这一时期,公域和私域是含糊不清的,这就是近代早期英国国家政权的特点。
政权的这种特点决定了政府亦或王室行政、经济制度的性质。
近代早期英国王室政府的行政、经济制度充分凸现了公域和私域的模糊性。
从都铎到早期斯图亚特,英国王室(政府)的行政、经济制度的性质是由政权性质和状况决定的。
从行政制度看,王室政府把行政管理事务由私域向公域扩展,建立起具有近代意义的行政机构,政府管理领域从王室领地向社会公共领域延伸。这表现为中央行政性机构枢密院地位的增强及公众事务鼓励领域的扩展;中央对地方联系的紧密及其政府行政性质的显现。在沃尔西当政后,枢密院才开始成为名正言顺的行政机构。到伊丽莎白时期,枢密院的人数大大减少,但其功能却增强了,枢密大臣基本上都是王室政府的重要大臣,如,财政大臣等。而早期斯图亚特的国王不仅增加了其功能,而且细化了枢密院的结构,使得枢密院已具备了近代科层的雏形。
枢密院从国王的咨询机构发展到功能完备的真正的行政机构,是早期斯图亚特才完成的。几乎王室和政府所有重要大臣都是枢密大臣,包括:大法官、财政大臣、掌玺官、国务秘书、坎伯雷大主教、内务主管、内务大臣、海军大臣等。[6]22,23早期斯图亚特的枢密院从1617年开始,不断增设专门委员会。专门委员会基本上都是管理公众事物的专门机构。[6]23-24
这一时期的地方权力结构的基本框架是:由枢密院派出的军政官任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因军政官是由枢密大臣担任,所以,并无精力进行管理,因此委派其亲信任代理军政官实际管理地方行政事务;治安法官位居军政官之下,由国王直接任命,是地方权力构成中的中坚力量;教区官员一般由治安法官任命,为最基层的行政官员。在中央统领下的各级地方行政从事着各类公共事物的管理。[7]133-137
但是,行政管理官员从选拔、任命到收入的获取却停留在私域,庇护制的存在就是这一状况的反映。在庇护制之下,贵族官员的选任是依靠个人与个人的连接,官员的提名、任免权私人化,官员管理社会的活动以对个人的忠诚和服务为宗旨,官员服务的报酬以国王私人的名义通过各种赏赐给付,中央官员基本上都有薪俸这类的常性收入,但这种收入在官员的总收入中所占比例极少,贵族官员必须依靠王室的补助性的赏赐维持与其地位相应的生活。而地方官员大部分是无俸的,完全依赖王室的赏赐。[8]当王室财政无法直接向贵族官员给付现金时,将政府公域权力转让给私人成为了维持官员收入的主要办法,也是政府维持行政机构运转的重要手段。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英国王室政府行政管理的公域化和行政官员管理的私域性相互交错,从制度层面而言,“公”与“私”含混不清。
这一时期的经济制度特点笔者主要从财政方面予以说明。都铎王朝建立初期,由于对贵族和教会地产的掠夺,王室领地规模不断扩大,领地收入增加,所以,在财政方面仍然沿袭了中世纪晚期的制度。王室财政收入主要来源于王室领地等私域范围,但是,从亨利八世后期起到早期斯图亚特,由于物价上扬、通货膨胀、对外战争、王室人员增加、行政机构的扩展及相应的行政开支的增长,王室财政不堪重负。为维持政府机构的运转,王室只有拍卖王室领地和借贷款项。在王室领地减少、私域收入下降、政府借贷增多的情形下,王室财政的征收越来越多地向公共领域渗透。[4]144-153另一方面,由于行政上的庇护制的存在,造成了王室开支的公域和私域的混糊不清,也使得国王对公共领域财富的掠取理直气壮,到斯图亚特早期,王室财政的征收甚至可以不通过议会强行进行。其实,议会尤其是下院议员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公私不分的状况及其严重后果,于是,提出改革方案,试图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现状。1610年议会提出的“大契约”希望理清这种财政上的公域和私域交杂在一起的混乱状况。依据“大契约”,议会同意每年给予王室200 000镑,但是,必须取消一系列因王室特权所获得的收入,如通过监护、政府采买等获得的收入。同时,议会负责偿还国王欠下的所有债务。并且,政府主要官员的收入由议会通过向公共领域征税来提供。[5]277-278这一提案已经初步将公域和私域的财政收支分清,真正确立国家财政的独立性和财政收支的公域化,较为符合近代政府的财政模式,因此,尽管在早期斯图亚特这一提案由于国王的反对而被迫流产,但是,1660年后的复辟时期以及“光荣革命”后的财政制度基本上是按照“大契约”的原则确立的。都铎晚期和斯图亚特早期财政制度上的公私不分使王室权力渗入公共经济领域的现象越来越多,导致了财政制度上公域私域的模棱两可。
面对16世纪以来社会经济变化,为维持社会秩序、保障王国安全、积累足够财富以满足不断增长的行政开支的需要以及在一定范围内提供家长式的社会福利,都铎晚期到斯图亚特早期的英国王室不断地对社会经济政策进行调整,其特点是,王室政府越来越多地进入社会经济领域,干预社会经济活动,但其公域和私域的界限并不清晰。
就社会政策方面而言,在都铎后期和斯图亚特早期,王室政府在社会下层和社会上层两个层面的政策都发生了变化。学界认为,都铎尤其是伊丽莎白时期针对社会下层的政策,如,济贫以及关于流民问题的处理等,总的来讲,还是比较积极的,也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效果。[9]73-84并且,早期斯图亚特基本上沿袭了都铎时期的有关社会下层的社会政策。“从伊丽莎白一世的逝世到长期议会的召开,学徒制,济贫法,工资和物价法规,在枢密院控制和鼓励下的治安法官的经济和行政管理功能都和以前大致相当。”[10]221也就是说,从政策层面看,王室政府对社会下层的管理的近代政府的性质较为明显,也就凸现了公域性。
但是,关于社会上层的政策却在斯图亚特早期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在整个都铎时期特别是伊丽莎白在位期间,尽管由于社会阶层的经济地位的变化引起了各阶层对社会地位的追求,但是,基本保持了社会等级制度的严肃性。斯图亚特早期的滥封和出售爵位以及新增爵位的政策,导致了上层贵族数量的增加和等级制度的混乱。[4]77-83此外,行政机构的扩展,给各阶层进入上层社会提供了又一通道,成为政府官员也是体现社会地位的显著标志,早期斯图亚特的出售官职的政策进一步扰乱了社会上层的秩序。都铎时期政府对上层社会的谨慎政策和早期斯图亚特时期对上层社会的“慷慨”而秩序混乱的政策,都是建立在以君王为中心、各级官员层层的个人依附基础之上的,其“私域性”是显而易见的。
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源自于这一时期的经济制度。王室私域财政收入的不足,使其不择手段地掠取公共领域的财富,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是要进入公共经济领域。从都铎晚期开始,王室政府加强了对市场、行业的控制和规范,[4]144-153剥夺了原来由公共经济领域组织的自我控制、规范和调节的权力,国家权力通过超经济的强制性手段渗入到公共经济领域的每个角落。在获得对公共经济领域的控制后,王室政府将控制权转化为王室经济特权,王室所颁布的各项经济政策就是这种特权的反映。通过对经济领域的控制,王室政府从中掠取经济资源,增加王室收入,使得公共领域的资源大都为王室私域而用。
近代转型时期英国王室政府公域和私域的模糊不清,是这一时期英国社会的显著特征。认识清这一特征,使我们可以能更准确地把握近代早期英国历史的脉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