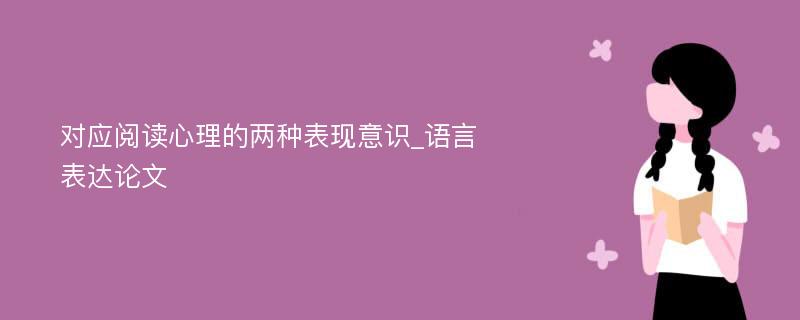
对应阅读心理的两种表达意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两种论文,意识论文,心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语言大师们能够将简单的内容说得“貌似”复杂,叫你不懂。反之,又能将复杂的内容说得非常简单,使你豁然开朗。前者是有意给我们的阅读设置了点障碍,读者似乎不能即刻把握其要义,但稍微品味分析一下,转而就又了悟,于是产生阅读的快感,获得一种阅读能力的自信。后者不是要设置什么阅读障碍,而是机智快捷地为读者铺就了阅读的坦途。几句话就清楚明白地解决了我们面对复杂事物时无法表达的语言痛苦,而且说得那样轻松自如,那样准确简明,于是我们由衷地佩服。
一般学生的写作情状可能正好与此相反。往往将简单的东西说得更简单,让读者觉得太浅太俗,没有阅读悬念,或者只看开头两句就能猜到下面是什么内容,使读者没有阅读乐趣;或者将复杂的东西说得更复杂,东一句西一句,半天也说不到点上,使阅读滞涩不畅,阅读者感到阅读的厌烦,终不能卒读。
这里不妨举名家名作为例,具体说明这对应阅读心理的两种表达意识。
其一,将简单说得复杂。例如:苏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中刘心武的《错过》,全篇均属于这种状况。这里仅摘录两节,将分析深入一下。
没有意识到错过,或许能产生一种自足感,但那意味着灵魂堕入了颟顸的渊薮。
能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什么,在追悔中产生一种真切而细微、深入而丰厚的情愫,则意味着灵魂具备了升腾的能力。
其实这段文字要表达的意思,如果把它说“白”了,是很简单的。没有意识到错过为糊涂,能够意识到错过则为清醒。但作者稍微运用了一些语言技巧,摆了点文,效果就不一样,就显得复杂而深沉起来。
何以将这简单表述为复杂?此时应努力将句子写得对称工整,进而形成排比。即使是议论性的表达方式,也可智慧而坚定地嵌入一点喻体,甚至不动声色地兼着点拟人。同时还要适当地换词,有意避开一些浅俗的话语,精心选用几个典雅的“词汇”,稍事点缀,力求准确。所录刘心武《错过》的章节,就显示了我们概括的此三点变简单为复杂的语言艺术。
它是对称工整的。关于错过意识有与没有两种状况的表述,不仅对称工整,而且构成了正反对比。面对一个简单的事理,不是随意地用一个简单又粗糙的句子一语道完,而是特意地在内容上有所延宕,或同类并列正反对比说,或前后顺接远近相承说,或轻重并举大小包含说,句式上则是对称工整精致地说,进而扩展为排比重叠地说。如是,内容与形式均丰富起来,简单自然被说得复杂。
它暗含着一个借喻,也沾了点拟人的边。“渊薮”就是一个喻体。渊本为深水,鱼所聚处;薮则为水边草地,兽所聚处,渊薮后指人或事物聚集的处所,这里却是借喻精神堕落的不好地方、深暗无助的所在之处。喻体的介入,使议论从抽象走向形象。
事理的形象化能给我们的阅读造成更多联想与想象的空间,读者可将自己的人生经历、思想情感融入语言文字,作者的简单不觉已转化为读者的复杂。“灵魂”的一次“堕入”,与“灵魂”的一种“升腾”,都具有了拟人的因素。“灵魂”是虚拟的物象,“堕入”与“升腾”则是实有的人的活动行为,所以说沾了点拟人的边。拟人有时是在先行比喻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形成的,我们的引文即如是。议论中的拟人,可以轻松便利地给静态的理性文字平添动态的感性色彩,行文即刻活跃,充满情感。
它明显可见换词的痕迹。不用“糊涂”用“颟顸”,不说“情感”说“情愫”。这是作者在刻意地避开常用的俗语,苦心地选用雅致甚至冷僻的“大”词,给我们的阅读设置了点障碍,但这是个机智而虚设的障碍,一般读者稍作努力,即刻就能顺利克服。“情愫”这个词我们虽然不常用,但望文望“情”,即可生义。一看这个“情”字,就能估计到是“情感”之意。最初的阅读,知道指“情感”就行了,并不需要放下书来去查阅字典,弄清“情愫”是“真实情感”的意思。“颟顸”这个词较为生僻,有的读者可能根本就没见过。但只要读完其意与之相反的下一句,在这上下两句正反对比的具体语境中,略为思考,还是能够猜读到“颟顸”为糊涂之意。意识到错过是清醒明智的,那么未意识到错过的“颟顸”大约也就是糊涂不明智了。即使仍不能猜测这“颟顸”之意,也无关大碍。你可以当时或过后翻看字典,验证一下你的预测,于是你清晰地解读了“颟顸”的含义,你会有另一种阅读的收获与快感。如此适当地换词,也许有故作深沉、生造词语的嫌疑。但究其实,写作有时还真需要“生造”词语,以为“深沉”。或造得有出处,经典准确;或造得无出处,但适时恰当,关键看你会不会造,造得好不好。不会造、造得不好是生造,造出的是话语垃圾;会造、造得好是创造,造出的是语言精品。在语言的实际运用中,抑或正是这所谓的“生造”,使我们的语言生动鲜活、丰富深厚起来。我们不再说“要跟上时代的步伐”,而说“与时俱进”;我们有意避开俗语“思想观念”,而时尚地将“理念”一词挂在嘴上;我们将“心理”置换为“心态”,将“感情”倒装为“情感”,该用“考虑”时,偶尔也会像港台人那样道作“考量”。这古为今用外为中用、这生活原生文本独创、这所谓的词语“生造”,也许正为语言的发展进步推波助澜,助了一臂之力。这有点扯远,就此打住。
其二,将复杂说得简单。苏教版《语文》八年级下册中臧克家写的《有的人》,全诗说得都很“白”,语言十分简朴,但意蕴却非常深刻。特别是开篇两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最能见出作者将复杂的内容说得看似简单实则很不简单的语言真功夫。此时要写的内容甚多。这首诗是纪念鲁迅有感而作,有感鲁迅的去世,牵涉鲁迅的人生经历、思想成果、学术著作、人格品行,同时又有感社会现实中一些高高在上活着的人们,其思想的腐朽、行为的丑恶,与鲁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要描述的人物事件、要抒发的思想感情、要议论的主题意旨太多太多,可谓思绪感慨纷至沓来。但奔涌至笔下,却化为这样淡淡的两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情感的沉淀,归于宁静;这语言的锤炼,回至淡出。作者举重若轻,似轻实重,化深沉凝重为浅易平淡。这凝重而平淡的文字,鲜明地对举着两种完全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深刻地揭示了一个生活与生命的永恒哲理。
怎样将这复杂道白为简单?此时应有空白省略意识,学会跳跃闪回,敢于中途单刀直入,半道一笔杀出;不避俗语口语,多用短句单句;力求简明朴实,却总能透露生活哲理。所引《有的人》开篇,即可见这三点化复杂为简单的语言技巧。
突兀两个“有的人……”便是半道一笔杀出,中途单刀直入。作者没有从纪念鲁迅去世十三周年开笔,所有的感念构想本应从这里出发;也没有从《野草》的《题辞》道来,引用文字“我自爱我的野草……地火在地下运行……将烧尽一切野草……于是并且无可朽腐”,当是先生祭日的最好诠释;更没有铺陈那两句被人们传为经典的名言“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无疑是其伟大人格的真实写照。此诗却是简单不能再简单,平淡不能再平淡地来了这么两个“有的人……”,这是在闪回跳跃,这里有空白省略。这闪回空白,或许让人感觉没头没脑,莫名其妙。其实不然,要相信读者,不要唯恐其不懂。当你以为内容复杂,难以表述时,读者也正感到事物纷繁,一时道不清楚。你的筛选重组,使读者一下觉得简单明白起来。你“蓄意”省略留下的空白,读者即刻就能心领神会,在文本客体与阅读主体的意念虚拟园地里填充补白。读者既佩服你简明的表述才能,也欣赏自我的阅读智慧。
这里的“有的”、“有的”,“活着”、“死了”,可以说相当浅俗,十分口语化。我们不能小瞧俗话,轻视口语。相声、小品里所用的语言主要是俗话口语,那种生动性、丰富性、表现力、感染力,人们想必都充分而切实地领教过。我们对语言的学习运用掌握,或许有这样一个过程:先是简单,继而复杂,最后又回归“简单”。前一个简单是真简单,是话语的浅显、词汇的贫乏,中间的复杂则指词汇开始丰富华美、绚丽张扬,后一个“简单”就不是真简单,是真不简单,是简练精准,是纯正质朴,是成熟老到。对付复杂的内容,最好的方式是采用简单的语言,不事工笔浓墨,而用写意白描,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把它说得很“白”,这时口语俗话便特别具有表现力。
此处的句式多为短句,几个词的组合就是一次停顿;而且这些短句,竟是将前后一些词语颠倒置换、紧承相连地回环重复了一番。句式的短小、节奏的明快、叙述的平易,读者很快就能把握其语意,产生阅读的轻松,感觉复杂中的简单,以为并无什么深意。但这简单的变化重复,又引导着我们的注意,唤起了阅读的警觉,意识到简单里的复杂。
重复本是语言运用的缺点,但有意重复,稍有变化的重复,就是语言的“蓄谋”、语言的机智、语言的策略了。这口语短句、这变化重复,分明蕴含着深刻的哲理、人生的真谛。所谓的哲理,就是将矛盾对立的事物放在一起理论,实现了融合与统一。看似颇为矛盾,想想很有道理。开篇这两句,将“活”与“死”、“虽生犹死”与“虽死犹生”进行了对立而统一的论述,生成出了深刻的哲理。
一言以蔽之:从阅读的心理、表达的意识分析,读者既然有一种轻视简单、畏难复杂的阅读心理,作者就应该有一种变简单为复杂、化复杂为简单的表达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