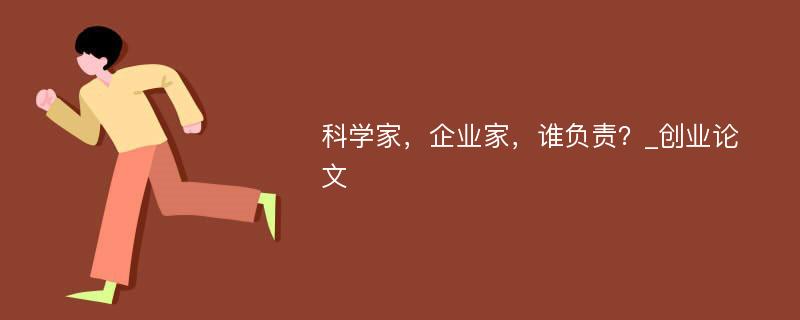
科学家,企业家,谁说了算?,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企业家论文,科学家论文,谁说了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著名大企业,相继大爆冷门——谁说了算?
面向知识经济时代,北京市倾力建设中关村,21世纪中国的硅谷若隐若现,变化无常。但一切外部的变化都比不上中关村心脏的不均匀跳动所引起的震动更大。中关村三家最具影响力的企业相继爆冷。四通产权置换和人事安排双管齐下,爆出的问题是,企业究竟是谁的?北大方正,王选正欲淡出,却遭“逼宫”,技术专家和管理专家,谁主沉浮?待到联想炒了院士,媒体更把问题归结为:科学家,企业家,谁说了算?
谁出了钱,谁说了算,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不正是这样,才所以有了企业家的吗!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让谁说了算,谁就说了算!那时这就是天经地义的;而那时却没有企业家。
在中国社会转轨前期的准工业化社会里,科技活动远离经济活动,民营经济尚处萌芽,不会出现此类问题。只有当经济形态发生改变,即知识和民间资本登堂入室,才会有这种问题。而中关村知识型企业的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在产品中知识含量如此之大,知识所有者难道不该说了算?但在产权虚置状态下,谁又能说了算呢?企业尚且还不成为现代企业,又何来企业家说了算!
如此说来,中关村的知识型企业竟然就没有人能说了算,这岂非荒唐。十几年来,中关村的发展有目共睹,能够没有人说了算?其实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人说了算,也就会有人被别人说了算。亚里士多德说过,人天生是政治动物;所不同的只不过是看权力是通过哪种管道行使的。
所有上述事件折射出一个现象,即一种以知识的生产和交换为主的企业已客观存在,技术专家在其中起重要作用。技术专家当然也参与决策,但技术专家最终能否成为企业家?
究竟谁说了算?科学家抑或企业家?这一问题既表现出旧体制的羁绊,也是新企业形态初建的一种阵痛。还须向深层次问题扩展。
当下各方讨论的目标直指企业制度,即产权不明确是导致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但事情绝不仅止于此。产权是重要的,但仅仅有产权是不够的。否则,怎么会出现科学家能否说了算的问题呢?
因此,我们要问的是:
为什么这类产权不明晰的公司在一段时间内也会是成功的企业,它们的成功是否有其合理性?
为什么中关村纯民营的公司成功做大的不多,这种鲜见现象是否意味着知识型企业仅有产权是不够的?它与中关村的小环境和中国的大环境之间有着什么关联?
此次三家联爆,目标直指产权,那么是否意味着如果明晰了产权,即可万事大吉,诸事顺利,不再存在谁说了算的问题?
谁说了算的问题,是否暗含着知识型企业中技术专家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而非简单的资本家权力的问题?而且,这种知识型企业的运行机制又有何特质?
当舆论异口同声地说应当企业家说了算,是否该问一下这该是一种什么样的企业家?真正意义的知识型企业的企业家应当具备怎样的素质?
最终,我们要追问,在中国社会转型期,新型企业家如何才得以涌现?
这一系列的问题需要回答。
首先是现实问题,而非理论问题
已经出现的争论,首先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实实在在的现实问题,这种争论今天刚刚浮出水面,但实际上一直伴随着企业的成长。如果我们不在历史过程中追寻它们成功和失败的原因和后果,就不能谈到真正的理解。
中关村知识型企业快速发展的缘故至少有以下三条。
一是技术专家在产品开发上曾经起过主导作用。王选发明的三代激光照排系统,成就了方正的由小到大,王选也由技术专家升华为方正的精神领袖,并就此埋下了方正发展模式的种子,以后方正的发展不过是王选思想的展开;联想曾经有过倪光南发明的汉卡,并靠着它度过了第一个难关,但联想并没有把赌注全押在自有技术身上,而是眼光向外,走贸、工、技发展的路子,可这恰恰成了联想两巨头分道扬镳的起点,也由此使联想不情愿地戴上了技术含量不高的帽子;而四通靠中英文打字机独步天下,之后又步入多元化经营,致使主业不明显。
二是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中筛选出一批技术出身的管理专家。这方面较为成功的当属联想集团,柳传志的“搭班子,定战略,带队伍”九字诀,成了业内尽人皆知的经典名言;在同国外知识型企业的合作和竞争中,学习、消化并发展出自己的知识管理模式;夹缝里求生存,在有限的制度空间内设计企业的激励机制,以尽可能地调动员工的积极性,将人力资本积淀下的智力资源转变成经济资源;关键时刻则靠个人魅力扭转乾坤,故在特定的条件下可以称他们为魅力型知识管理专家。
三是有幸碰到了好“婆婆”——原来所归属的科研部门和大学。这也是中关村之所以为“中关村”的特殊所在。当年中关村的许多科技人员出来创业,目的很简单,就是不愿意再荒废时光,希望能做点事情,至于有多大的利益,可能当时考虑得并不太多。后来,事也做了,钱也挣了,就涉及到实质性问题:谁来花,怎么花。这时就要看所谓的上级主管部门(中国特有概念)的态度如何了,事实上目前还生存并得到发展的知识型企业,都证实了那些“宽松”的上级“婆婆”们是多么地高明。
技术和管理的相互扶持成就了企业的长大,同时也孕育着相互间的较劲。可是,技术和管理之争绝非一场代价不大的角斗士游戏。
联想、方正、四通三个中关村成功企业为此遭受到三种有代表性的“损失”。
联想两巨头由发展路向之争不幸地转变成个人的恩怨之争,贸、工、技,抑或技、工、贸以及人和事都搅到了一起。不管当事人怎样掩饰回避,几年来为处理经常不期而遇的纠缠和各类盘查,一定耗费了相当多的精力;同时,不可避免地客观上形成了公司决策层对技术专家的排斥,导致研发投入比例低,自主开发的产品稀少,进而导致联想利润额与销售额的不匹配。这种情况下,联想发展的潜在危机,在于再建与企业发展相得益彰的研发队伍,势将困难重重。
方正的研究院模式实际上浓缩了知识型企业创业之路,以某种技术产品开路,再由产品的市场垄断导致企业规模急剧膨胀,接连不断的产品创新支撑着企业,但企业制度和组织行为并没有随之相应调整,当创新枯竭时,企业就可能一蹶不振。王选的深刻总结“成功也是失败之母”,道出方正唯技术是瞻的致命弊端。方正重整的最困难之处,就在于内部已经无法生长出管理专家,而引进外来的管理专家又很难避免为母体所排斥。
四通则是特定历史境遇挤迫下的变形体,所以四通变成了“四不像”,发展没说法,管理没样式,技术没定型,产权没着落。摊子铺出去了,想“壮士断腕”都难。特别是企业核心技术能力的丧失,不能不说是最大的损失。这种损失该如何计算,谁来负责?大概都是一笔糊涂账。这直接导致四通的社会形象受损。四通重新脱胎换骨就不仅是产权明晰的阵痛,而将是能否真正健壮地活下去的长痛。
工业公司与知识企业的异同
中关村的公司不是工业公司,而是知识型企业。工业公司,竞争优势在于生产和制造物品的能力,其中机器设备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而在知识公司,竞争优势在于思想和思想的流动,它们蕴含在研发活动中,这常常导致公司的结构性变化,乃至决策、管理、权力、利益、分配的动态变化。
研发活动在变化。研发由部门职能性工作向企业整体性工作转变。在日本,企业研发活动内化企业决策机制的演进,一种情况是研发专家经由生产、销售部门的遍历式培养而逐步升入决策层,这一现象又与日本企业终身制度相一致;另一种情况是研发小组制度的形成,其组成就包括了研发人员、生产现场的工程师、销售人员等,而知识官员在其中起主导作用。因此知识型的公司在很大程度上将是由少数固定员工组成的一个小核心。他们与供应商以及外部专家保持着联系,并且能够为共同生产某种产品将这些人组成一个网络。
等级结构让位于网络组织。等级制阻碍思想交流,信息的逐级传递必然会导致信息噪声的递增,最高决策者几乎不可能筛选出有益于其决策的有意义的信息。因此企业组织结构必须根据不断更新的项目进行整合,因为每一个项目都要求不同的知识、能力和经验的组合,这些小组必须具有高度的独立性和企业家精神。日本的野中自称其为“自中而上而下式管理”,企业的内部和外部边界越来越模糊,决策者与执行者的严格分工正在逐渐消失。企业内的部门之间可能形成某种契约关系,企业同企业之间的合作形成的联盟性组织又可能像一个企业那样行事。
企业学习能力的增强。知识在组织中传递的一个主要渠道就是学习。学习过程是创新过程最重要的特点。企业就像一个生命体一样,伸着触角,变换着身体,从外界吸取营养。企业通过学习,“习得”对特定环境适应性的生存能力。所谓的“战略规划”往往变得越来越不起作用。面对变化的市场,按功能和等级划分的传统组织结构正在被由许多规模较小但自主性增大的单位组成的网络取代。这样的组织形式具有更强的学习能力。
分工和专业化,导致一种反转现象——“高度分工基础上的合作”的出现。信息的快速交流,公司的外部市场的交易效率提高,必将导致公司的经营决策和生产组织的脱钩。数字革命为大规模数据传递和更有效地互动通讯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美国触发了新的组织方式的发展,合作更为加强了。硅谷流行的模式是:技术专家有市场前景的技术,吸引风险投资家的创业资本,再接纳管理专家参与管理。“铁三角”支撑着知识型企业。
钱德勒指出现代工业企业的特征之一是高级经理阶层实际执掌企业。加尔布雷思则进一步认为,近50年来,主导生产要素逐渐从资本转移到专门知识,企业权力和社会权力随之从资本所有者的手中转移到“技术专家体系”的手中,细究这个技术专家体系,仍然是以管理见长的经理们为核心。人们过分强调现代工业企业的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却都没有注意到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态在悄然出现,这即是在战略和结构上都予以更新的“知识型企业”或者“高效能组织”。这种模式的变换也改变了企业的内部结构,更多地强调“组”的作用,强调专项任务的高度集成、分散式决策体系、持续性创新、组织自身的学习过程,等等。
知识企业,其根基仍是企业
知识型企业,本质仍是企业,而企业当然应由企业家说了算。不要忘了,离开资本,知识并不能自动变成规模收益的商品。
经济学家弗兰克·奈特最先指出企业家精神:“实施某种具体的经济活动成了生活的次要部分;首要的问题或功能是决定干什么和如何去干”。张维迎在奈特的企业家理论上提出他的“企业的企业家”理论,即资本雇佣劳动,而不是劳动雇佣资本。但我们似应注意到他的分析仍然仅立足于新古典经济学完全信息的假定和谁对不对称信息握有得更多这一观点。当我们看到知识型企业的组织形态发生的变化时,应领悟到知识企业的企业家也一定超越了工业企业资本家,他们是资本和技术知识的结合体。我们称其为技术专家型企业家。
技术专家型企业家,是超越熊彼特式的、甘冒风险的企业家,是他们在“创造性毁灭”中实现创业的,因此,他们首先是创业家。当日本企业开始把人的新生活方式“创造性、舒适、欢乐”作为产品开发的宗旨时,当微软、戴尔为代表的美国公司使个性化服务成为商业时尚时,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对企业的作用有多么强大就一目了然了。而这一切又为造就新型企业家提供了何等广阔的活动空间!
这里,我们尝试着给出技术专家型企业家的必备条件。
出身 有技术背景,善于掌握企业的核心技术能力。硅谷的创业公司的创业家们大多出身于理工专业。
嗅觉 能发现市场机会,把握市场中的不确定性因素。这是企业家的首要能力。“经营能力可以想像为企业家的天赋。”(张维迎语)
创新 通过研发制造产品的不确定性与市场的不确定性叠加而消解未来的不确定性。苹果电脑公司的艾仑·凯指出:“预测未来的最佳途径是发明未来”。
管理 保持对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权,懂得业务发展和产品开发上的“管”和“放”,善于团队管理。
我们还应当对这种企业家需具备的素质作一番挖掘。
素质1——生存 自己能生存,亦可使企业生存。 企业的存在不仅仅是科斯企业理论所说的“契约的联结”。企业家是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同样,企业亦是生命体,成功的企业家会把它凝结为企业的理念。生存能力对人而言是本能,在企业而言不是本能,它需要塑造,流行的语词叫“型塑”。
素质2——控制 斯特劳斯说人“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野兽”, 会控制就是控制兽性。企业家的兽性表现在同野兽一样的征服扩张的本能上,但狮子本能上都只维持一定的领土生存半径,企业家就更应懂得“通吃”在商场上是不可能的。技术产品的可解构和知识传播的无成本决定企业无法独占任何市场。
上述两种素质可以归结为企业家必须懂得生存竞争“博弈”的成功法则——“一报还一报”,或者艾克斯罗德所说的“你竞争我竞争,你合作我合作”。
素质3——自信 企业家之所以优秀在于首先有平民意识, 而不是贵族意识。这是自信的基石。对技术专家而言,“聪明绝顶”这种社会评价常造成专家的孤芳自赏,却恰又成了阻碍企业家成长的顽症。超人意识隔绝了与社会打交道的通道,到头来只能是自我肯定、自我欣赏、自我崇拜直至自我毁灭。
素质4——应变
知识专家管理企业的最大问题往往在于他不是把企业当作一个生长着的不断解决问题的活的机体看待,而是把企业当作一架机器。技术专业背景使其时常处于事件的“真”和处理事件的妥协手段之间的困惑之中。组织管理的所谓“软技术”,根本不可能生根内化为主导性知识,因此管理知识只能是第二位的。
解决的出路——制度、体制、产业在试错进程中胜出
解决的思路,寄希望于制度变迁中的试错机制,即让市场经济体制和知识产业在试错中胜出。通过中国制度的整体试错,知识型企业的局部试错,大量科技专家为主体的创业公司才会得以涌现。试错过程中将形成游戏规则。这种机制的建立,将自然形成新的权威,即全新意义上的企业家——技术专家型企业家。日本经济学家松山公纪说:“我把‘企业家’定义为一个为了促进协调而设计和试验新制度的当事人。”这种新型企业家将是中国新产业——研发主导型知识产业的创建者。
怎样使得他们大量涌现?可以设想分三步走:
第一步,民营科技企业的普遍生长。鼓励科学家毅然走出高墙深院,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办企业。促使以技术产品开路的中小型创业公司活跃在经济舞台。
第二步,资本运营中开始吸纳新技术,出现以经济手段搜寻高技术项目的风险投资公司和技术市场前景咨询公司,实现金融资本和知识资本的融合。
第三步,通过市场竞争的残酷淘汰选择,使掌握最为稀缺资源——知识的技术专家成为企业家,促使研发专家型企业家成为知识产业的主导力量。
上述几步发展过程的结果是,一种新的社会主导型人才,即技术专家型企业家普遍孕育而生。他们先是在技术领域灵感迭出,继而在商界纵横捭阖;而风险基金的年轻的投资经理们伸着嗅觉灵敏的触角搜寻着,不同类型的企业家为着追逐超额利润结合到一起,随之,科技创业公司必将如雨后春笋般生成,由技术和资本的结合而形成的专家型企业终将成为社会变迁的主导力量。他们背后所获得的主要支撑不再是权力和财富,而是知识和知识网络。这些新型企业家又被称为“无限制资本家”。身处这个剧烈变革的时代,他们毫不畏惧地迎接时代的挑战,实际上,正是他们揭开了这个时代的帷幕。流行于硅谷的一则笑谈:“硅谷的数字脑袋一有可笑的念头冒出,便会迅速传播开来并影响美国企业界的心理”,颇为传神地道出了时代发展的源泉。
企业家是中国的财富。他们正在催生,还将更快催生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
专家型企业家,更是中国的财富。他们不仅为制度变革创立新的规制,他们更将在创业中,创立中国的朝阳产业——研发主导型知识产业。
标签:创业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