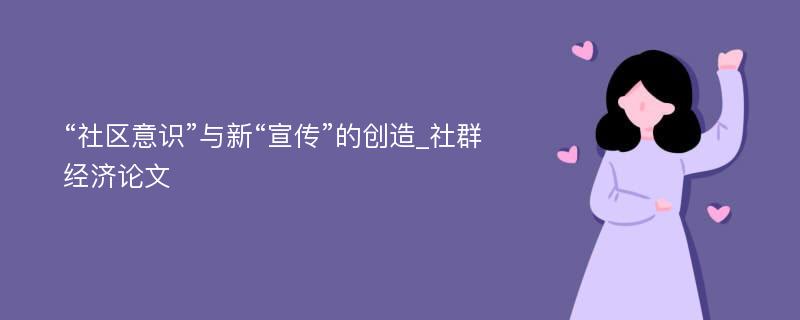
“社群意识”与新的“公共性”的创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群论文,意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
当下的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发展”,这一发展正在以极大的“速度”改变着我们的空间结构与日常生活。“全球化”与“市场化”的进程业已进入了我们每个人的语言/生存之中,变为了当下本身的展现。如果说,在九十年代初叶,这种文化空间的变化尚未引发人们的关注,一些人尚可以延续旧的话语的表述策略的话,那么九十年代中叶的历史情境已完全证实了“后新时期”文化的新的格局的生成。[①]这一格局的生成无疑昭示了中国的全球化与市场化所带来的大转型的巨大的活力与可能。我想由两个来自近期小说中的片断来开始我的探讨。这两个片断分别来自两位九十年代以来最有活力的青年作家徐坤和刘醒龙的小说。这两个片断所彰显的正是一个新的社会与文化空间的生成。
第一个片断选自徐坤的《热狗》。在这里,知识分子陈维高看到他所在研究机构周围正在崛起一个新的空间:
东边,巧克利大楼滴着褐色的奶油蜜汁儿,馋得人人都恨不能上去舔一口。
往北,亚太大厦昼夜都散发着印度的檀香味儿,熏得人都差点儿去皈了依了。
对面,海关大楼那两座生动的钟式建筑隔条马路,就在那儿脸对脸儿的叫着板呢,亮堂堂的制服们神气活现地出出进进,愈发显得他们棺材壳子里的的确良衬衫们的古板寒碜。
西边,国际饭店富丽堂皇的旋转餐厅,则干脆就紧挨着科研大楼的脑袋顶上趾高气扬地转哪转,根本上就是构成了一个鸟瞰。
这才几天哪,也就是一转眼。
再往远点,什么凯莱、建国、王府、皇冠……一批批大酒店以看不见的速度比着赛往起蹿。
这里有趣的是一个巨大的“看不见的速度”改变了当下的空间结构。以科研大楼为中心的视点下,却发现了中心离散的、飘浮的新的空间。昔日科研大楼刚建成时,它是城市的枢纽点,是城市的精神与话语的中心。但当下“中心”却被消费者化与商品化的多中心的“拼贴”式的形态所替代。知识与话语的权力在空间的位置上变得异常的自我封闭和狭小,而向公众敞开的迷人的光晕淹没了神圣的权威。这是一幅“现代性”分崩离析的空间景观,一个璀璨的后现代的迷宫淹没了昔日的枢纽点。
第二个片断引自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其中的镇党委书记孔太平前往乡镇企业家洪塔山的水产品养殖场。这个养殖场传奇般的发展也同样凸显了“速度”在当下的功能:
“养殖场占地有一百多亩,大小几十个水泥池子里放养的差不多全是甲鱼,据说这是全省最大的专门的甲鱼养殖场。从前这儿的规模很小,只能从别人那里买来幼甲鱼自然喂养,两三年才长到半斤以上。所以养殖场总在亏本。洪塔山来了以后,第一年就建起了甲鱼过冬暖房,不让甲鱼冬眠,一只幼甲鱼一年时间就能长到一斤多,养殖场也有了丰厚的利润,接下来洪塔山就动手扩建养殖场的规模,并创出了西河镇养殖场有限公司这块响当当的牌子。”
这里养殖场的急剧的的发展使它由一个边缘的空间变为了这个乡镇的中心。它以惊人的发展速度改变了一个乡镇的社会结构。这个“养殖场”变为“有限公司”的传奇之中的戏剧性正在于一个相当僻远的乡镇的变化恰恰与徐坤所描述的北京这样的超级城市的变化相似。历史的戏剧似乎正在中国的各个角落中“共时”地出现,尽管其表现形态有相当的差异。
徐坤与刘醒龙所发现的似乎是两个惊人的相似的不同的空间。这里一是超级的国际化的城市,一是僻远的乡镇;一是全球资本与信息流动的中心,一是依赖农副产品寻求机会的边缘;一是徐坤眼中的跨国性的全球形象(亚太大厦、国际饭店、海关大楼),一是刘醒龙笔下的充满发展焦虑的小小的养殖场。但这些看似充满了断裂性的空间都有着无可争议的同质性,它们都卷入了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浪潮之中,承受着巨大的“速度”带来的新的文化经验。这里被徐坤所言的“看不见的速度”支配、控制的空间充满了一个第三世界社会在进入全球体系后的发展的“冲动”。徐坤与刘醒龙勾勒了一幅当下的“地图”。这幅地图标识了新的领域、新的座标、新的自我想象。在这两个不同的“区域”的互为镜象的反射中,我们却可以辨认到一个处于“速度”的笼罩之下的“中国”本身。
所谓“速度”,乃是一个物理学上的概念,它指的是距离向量与时间之比。而在徐坤、刘醒龙这里,“速度”不仅是一个有关移动的概念,而是一个本地空间发生巨大变更的过程的标志。中国所获得的巨大“速度”无情地宣告了八十年代的依靠对西方的“模仿”而获得的“现代性”幻想的终结。中国的历史进程并未按照那些乌托邦式的幻想发展,而是寻找了一个新的选择。另一面,中国的市场化的进程也以相对平和的方式推进,它一面保持了发展的速度,但另一方面也避免了大的断裂与社会的冲突。这种新的“速度”正是在这种格局下获得的,它所喻示我们的是在这个新的空间之中如何去面对“速度”所构成的语言/生存状态,正是当下本身的最为巨大的挑战。
保罗·维希里奥在讨论“速度”对于当代世界的影响时指出:“随着速度支配型进化的实现,人类不再是各色各样。人类现在只区分为有希望的人群(他们拥有一个希望,在未来的某一天,他们将会达致他们正在积累的速度,这将使他们得以通向一切可能:计划、决策、无穷无尽……),以及绝望的人群,他们被低劣的技术运输工具所阻,在一个有限的世界里生存和维生。”[②]而“中国”正是业已无可争议置身于一个“有希望的人群”之中了。无论中国面临着怎样的挑战与困厄,但发展的巨大的“速度”所希望带来的活力和可能正是这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前提。这不是一个崩剥断落的“废墟”,而是一个生命的空间正在创生之中。在徐坤和刘醒龙的表述之中,这种新空间的活力与可能被展现得格外强烈。目前文化与文学所面对的一个中心的问题是,如何在这个新空间之中寻找一种介入与参与的勇气和力量。历史似乎将这些在九十年代的“后新时期”文化的语境中出现的作家们放置在一个戏剧化的抉择的关口上,而他们正是在这个关口上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抉择。他们的写作正在以无情的力量告诉我们,和那些阴郁黯淡,充满着不安与狂躁的吼声不同,这些来自当下的声音从未拒绝对当下的人们的发言,从未拒绝与人们一同走入今天,也从未用媚俗和取悦搭起一个幻觉的世界。他们提供了对这个“新空间”的新的表意策略。我们无权忽视这些来自我们的共同的中国内部的新的声音。
二
在“后新时期”已经历了一个相当长时段的演进的今天,我们从文学写作中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的趋势,即一个“换代”的过程业已展开。在文学界内和当下文化潮流中已出现了一批无论是创造力或影响力均相当强劲的新的作家。这批新的作家与“新时期”文化之间联系较少,在“新时期”也并未产生影响,完全是置身于当下文化现实之中。这批作家与当下的发展“速度”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们能够切入到新的空间的脉动的深处,进行深切的文学表达。这批作家显示出两种发展的趋向。一是“新状态”文学,我指的是以何顿、韩东、张旻、述平、刁斗等为代表的文学潮流。这些作家注重内在/外在、表现/再现间的平衡,力图由个人的感觉与体验出发表达急剧转变社会的诸多“状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由强烈“个人化”的写作追求出发的本文,却并未走入一种强烈的语言实验之中,而是重新回到了具体的历史与情境之中,由此获得了一种对于个体的历史置于社会之中的“状态”的表达。有关“新状态”文学的讨论自1994年开始以来,尽管对这一文学现象有不同的表述,但它对于“当下”本身的强烈关注是任何人也无法加以否认的。这种具有强烈的“个人性”的书写也投射了这个社会置于“速度”之中的多重矛盾、困境与挑战。[③]“新状态”文学业已受到了相当广泛的探讨,这里不再展开,我只想指明,“新状态”写作所喻示的乃是一个由“个人性”向“公共性”的过渡性的空间的确立。它的发展也提示人们,任何语境之下的文学想象均无法脱离自身所处的“状态”的作用与影响。在今天中国社会面临着“速度”所构成的多重挑战时更是如此。“新状态”文学显示了“个人性”写作在当下的情势之下的自我调整与自我更新的能力。
在近期的文学发展中显现出更为充实的活力的乃是一种“社群文学”的新的创作潮流。这一潮流包括一批开始写作较早,但一直未能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家。这批作家的近期创作也最终显示了在目前文学中发生的“换代”现象的扩展与延伸。这批作家包括谈歌、刘醒龙、关仁山、陈源斌、何申等,他们近年来一直保持着较为旺盛的创作力,但并未引起人们的关切和文学界的广泛的读解和分析。自1996年初,谈歌的《大厂》和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发表以来,这批作家的写作开始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业已形成了较为明显的、大体趋近的创作潮流。《大厂》等本文不仅受到了当下读者广泛的关注,亦引起了文学界内部的结构性变化,被媒体认定为一股强劲的“冲击波”。[④]我以为这一潮流乃是一种新的“社群文学”的崛起。它从“基层”回应了全球化与市场化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彰显当下中国社会在大转型之下的诸种深刻的脉动与走向。在这里,“新状态”所开创的对于“当下”的强烈关注的空间化的风格业已被扩展。当下文化的一幅由“社群文学”/“新状态”文学共同勾勒的“地图”业已成形。
所谓“社群”,原是一个社会学中的概念。它在希腊语中原有“友谊”与“团契”之意。自柏拉图以来,“社群”就被视为探索和研究人类社会的重要单位。19世纪的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更开创了这一研究领域。“社群”作为一个对于社会的描述的概念有多重的意义。但其基本的取向仍是十分清晰。它指的是“生活在同一地理区域内,具有共同意识和共同利益的社会群体”。[⑤]“人们至少可以从地理要素(区域)、经济要素(经济生活),社会要素(社会交往)以及社会心理要素(共同纽带中的认同意识和相同价值观念)的结合上把握社群这一概念”。[⑥]社群中的人们生于斯、长于斯,守望相助,互相扶持,凝聚成一个共同的存在。“社群”也随着“文化研究”的崛起而成为考察当代文化状况的一个关键概念。它意味着在一个激变的大时代中,在一个全球性的资本的流动、信息的扩张与传播无限发展的时刻,“社群”似乎成了一个认同和归属感的最后的停泊之地,一个跨出个人及血缘关系网络的人与人之间“公共性”建构的空间。正象英国思想家西格蒙特·鲍曼所指明的:“正因为社群以其敏锐的防御机制提供了某种后现代关怀的焦点,因而它吸引了那么多智性的和实用的注意力,并且在后现代性的哲学模式与一般的意识形态中显得极为突出”。[⑦]“社群”在当代生活中的关键性的意义在于,人们可以通过“社群”建构一种“公共性”,而这种“公共性”能够让人们发出面对生活共同抉择的呼声,可以使他们在面对急剧变化的“速度”时不致失掉方向感和生存的力量。
在当下中国所出现的“社群文学”,正是重新赋予了我们的文学一个社群的历史向度。这正是中国发展的“速度”本身的强烈的“询唤”的结果。它的特征正是在一个极为纷乱复杂的社会状况之中凸显出作为一个本土的中国的发展只能来自自身内部的凝聚力与创造力,来自一个社群之中的全体人民对于发展的参与。因此,“社群文学”所呈现的世界乃是对当下历史经验的直接性的反应。它主要呈现出下述一些特征。
首先,“社群文学”的中心乃是提供了对于中国当下日常生活的新的描述。这些本文所表现的空间与“新状态”文学有所区别,它们所关注的往往不是最直接、最迅捷地体现出当下发展“速度”的大城市中心区域,也并未直接表现跨国企业及私人企业的生活状态,而是着眼于中国社会的“基层”,着眼于乡镇社会及几十年计划经济运作的结果——面对巨大转型挑战的国营企业。这些表现均显示了中国的全球化与市场化进程所带来的社会的深刻的结构变化。昔日的社会中心业已被冲击,而昔日的边缘或不曾存在过的新的机构占据了新的空间,成为社会的中心。“速度”所带来的并非中国社会的所有部分的匀速的发展,而是极度的多样性及区域或不同机制机构的不平衡性。“速度”既引发了高度的发展,促成了若干社会部分的加速度成长,但也导致了一些部分的困难与失序。“社群文学”对此均作出了极为深切的表现。谈歌的《大厂》中党委书记贺玉梅的丈夫谢跃进的私营公司的活跃恰恰与贺玉梅所在的“大厂”的困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也喻示了极其强烈的不平衡性的存在。传统的、稳定的“公”的部门,其发展的速度无法与相对灵活的“私”的部门相比,它们既承担着维系社会的安全运行及提供巨大社会保障的功能,又支撑着经济活动的一大部分,因此,国营部门及社会公共系统正面对着严峻的挑战。无论是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中西河镇党委书记孔太平对于企业家洪塔山的隐忍,还是何申的《年前年后》中乡党委书记李德林的漫游经历,无不说明着当下社会的结构变化的深刻性。而在表现这种结构性变化的同时,并未将这一变化的后果浪漫化,而是直接面对这一后果的极度的复杂性。中国变革的速度带来了无法否认的成就,但也带来了新的冲击和问题。在这里,问题的症结正是公共部门的不灵活,缺乏新的动力与私人部门的极度活跃的不平衡。而在这种不平衡之中,“社群文学”把自身的关注点放在了在目前利益及精神上暂时受到损害的人们身上。它们不象许多“新状态”本文,往往表现在经济上得到了“速度”所构成的成果的人们的精神的焦虑,而是探索那些尚未充分享受这些成果的普通人的命运;探索这些曾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却并未得到巨大收益的人们的痛苦与尊严。在这里,“社群文学”揭示了新的市场经济及文化潮流的转折的巨大成就之中,也存在着的不适应,这种不适在此绝不仅仅被化约为一种心理行为,而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社群文学”在此具体地勾勒出了不平衡及不适应的存在,以及这种不平衡与不适应所造成的对于“速度”的挑战。在这里,“速度”不是一个浪漫的概念,而发展本身也必须付出代价。在这里,中国所面对的国际及国内的挑战不是个体命运的偶然的随机性,而是当下“冷战后”新世界格局下的具体的存在。
其次,这些本文均从一个新的“社群”的创生的过程出发,凸显了一种新的“公共性”的不可或缺。无论是《大厂》中处于困境的大厂工人及干部的坚韧的奋斗,还是刘醒龙的《分享艰难》中的那个西河镇所面对的极度错综化的矛盾和问题;或是毕淑敏的《预约死亡》中的“临终关怀”医院中的种种故事及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何申的《年前年后》等本文,均将“公共性”推上了表现的前沿。它们显示给我们的是公共生活本身的不可或缺,人们无法摆脱公共事物,它与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息息相关。在这些小说的表述中,公共生活业已被多种不同的利益面向所极度地错综化了。它表现为不同的利益面向与社会关系的交错配置。在这里,中国社会的复杂性及“速度”带来的不平衡与不适应不再仅仅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经验,而且是当下公共生活面对挑战的标志。这既不像五、六、十年代的小说中将公共生活单向化为对国家的认同及国家对公共事物的全面介入与管理,也不象“新时期”文化中以个人的私生活空间的再确立去闪避与疏离于公共生活,而是清楚地认识到随着社会分层的加快,社会的利益面向的差异日趋明显,而随着体制的改革(特别是如医疗保险、住房制度等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方面的变化)所导致的旧的国家“包”起来的领域的缩小,国家开始退出一些领域,都引发了旧的公共生活的形态的急剧改变。这些本文发现公共生活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是如此地不可缺少和不可疏离,它不仅是国家管理下的空间,而是在相互的交往中形成的一个市民社会/个人/国家之间互动的场域。在这些本文中,私生活仅仅是来自后景的,每个人的境遇都被置于一种面对公共生活时的反应之中。如《年前年后》中李德林与妻子于小梅的冲突及最后矛盾的缓解并不是私生活的矛盾,而是公共生活对私生活的投射与支配的结果。他们的争吵起于对于李德林的两个下属的接待不好,而和好却是由于于小梅的社会关系对李德林工作的帮助。在这些本文中,公共事务所面对的挑战既无法简单地通过国家的管理,也无法通过私人的努力得到解决。“乔厂长”式的浪漫的幻想已不复存在。象《大厂》中这个矛盾重重、负债累累的工厂的多重问题,不是其厂长或任何一个人能够在一瞬间加以解决的。而《分享艰难》中党委书记孔太平面对的矛盾,既来自经济及社会结构的深刻转变,又有价值选择上的困惑。这些状况都使“公共性”在此面对着危机。人们发现今日的“公共性”的获得不能象五六十年代一样在国家的全面管理之下,而“公共性”也不可能被取消或忽略。所有的“社群文学”作家都并未将“公共领域”浪漫化,而是真切地表现了“公共领域”正是充满了利益、权利、价值观冲突的场所。无论是孔太平所面对的洪塔山的权力的挑战还是《大厂》中吕厂长与承包人赵明之间的冲突,都凸显了当下“公共”所面对的严峻挑战及重建“公共性”的极度的紧迫感。这也是一个发展中的第三世界社会的焦虑与困惑的表征。
其三,“社群文学”正是由重建“公共性”的寻找中发现了一种新的“社群意识”的创生。这种“社群意识”正是寻找一个共同的情感空间的努力,寻找每个人参与与介入“公共性”之中的可能。这种寻找无疑是以在社会的“基层”的新的人际关系的纽带的生成为前提的。“社群”超出了既有的网络与结构,在情感的向度上超越了利益的面向,它不是建立在冰冷的利益争夺之上的,而是以人们之间的情谊、信任和相濡以沫为前提的。它是社群中的每一个人清醒地认知自身的处境,了解自身与这个共同的社群之间的共同命运之后的理性与情感的选择。这是一种共同体之中的强烈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在《大厂》中工程师袁家杰原本想调离工厂,但最终却卖掉了自己的专利,为厂里获得了一笔资金,并留下与工人们一起奋斗。而党委书记贺玉梅则在家庭面临破裂的苦痛中仍坚持在厂里工作,吕建国厂长带头为小魏的女儿捐款及被赵明打了以后的激动的陈词,无不显示了这个工厂业已不再仅仅是企业,而是重新创生的一个社群,它已超出了一个生产单位的界限而变成了一个相濡以沫、互相扶持的社群。这里已不再有那种自上而下的体制性结构,因为维系这种结构的那种经济的纽带业已削弱,它更具有了一个共同承担与分享的社群的特征。在这里,昔日《乔厂长上任记》中自上而下,由雄才大略的厂长支配的变革已被一种同舟一命、分享艰难的共同参与与共同认知所替代。“社群”的创生改变了既有的结构,显示了全体人民分享艰难,试图在公平的“和而不同”的环境之中共同奋斗的愿望。在这里,“社群”不是处于历史进程之外的空洞之物。“社群文学”不但不象某些文化冒险主义者那样消极地抗拒经济发展,抗拒“速度”,而是清醒地发现只有中国的发展才是全体民众的最高利益之所在,只有发展才可能为民族赢得尊严和利益,才可能为个人带来巨大的机会。因此,这些本文所期望的正是这种发展被全体人民所参与和分享。在这里,社群乃是一个过程,一个呼唤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的不是敌意与仇恨,而是一个“和而不同”的协作与共生意识的生成。
其四,“社群文学”也表达了一种新的价值和伦理的选择。在这里,它提供了一种新的道德感。这种道德选择既不同于五六十年代的完全放弃个人利益及相当严厉的道德要求的设定,又不同于八十年代强化个人利益与私生活空间的倾向,而是立足于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新的文化格局,以“社群”发展为最高目标而重新设定的价值观。它是面对多重矛盾、冲突对立的新的选择。在这里,任何“小葱拌豆腐”式的解决方案,只能导向一种危险的结局;而面对目前的道德状况采用一种猛张飞式的“毕其功于一役”的策略也只能是一种对我们共有的社群的轻浮和不负责任。因此,为了社群发展的更高的原则和利益,人们不得不容忍一些事,也不能不寻找妥协与对话。“社群”的发展不需要那种哄闹和谩骂,也不需要那种在社群内部制造的强烈的“敌意”与“仇恨”,这里不需要任何的自我陶醉和自我标榜,而是需要在具体的实践中捍卫公众的利益,保护我们的共同的社群不受到内外的压力和损害。这就需要一种“韧”的精神,一种高度的智慧与理解。无论是对中国发展的来自外部的“遏制”的喧嚣,还是中国内部所承担的种种问题,都要求这个社群中的人们充分地认识到中国当下挑战的严峻性,任何对我们这个社群的承诺都必须来自“基层”的人民的历史自觉性的呼唤,来自一种真正的当下的关怀。而“社群文学”则是抓住了这一社会转变中的关键。这些小说中的主角往往是身处中国社会的基层,承担着上下多方的压力,在国家/市民社会/个人之间寻找一种对话和妥协的“点”的人物。他们置身于“公共领域”之中,力图以多方面的沟通来寻找凝聚社群共识的可能,他们并不是振臂一呼、慷慨激昂的当代英雄,也不是随波逐流、贪图个人私利的无聊之徒,而是认知了自身责任的沉重和无可逃避之后,作出了理性的选择。无论是《大厂》中的吕建国还是《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或是《年前年后》中的李德林都是在众多矛盾汇聚的点上寻找各种不同的价值与利益间的协商与对话的可能性。他们都是一些置身于社群之中的俗人,他们并不以自身的价值和道德选择强加于人,也不试图按照一个早已预设的理想的蓝图来改造世界,而是拒绝将“发展”从任何角度的浪漫化,拒绝任何乌托邦式的幻想,立足于当下,立足于“发展”的最高利益。这是一场葛兰西所说的“阵地战”。他们注重力量的对比,注重在实现某些重要价值时放弃一些次要价值的坚持。他们异常清醒地看到了历史并不是一个以善取代恶的单向过程,市场经济也并不是一种理想化的模式,在这里仍然迫切地需要智慧,需要坚韧,需要明澈的理性。“速度”所造成的复杂的结构要求着一种“新人”。他们能够努力地在重重矛盾中寻找历史的契机,他们有坚持却又有机变,能够在极度复杂的环境中为了一个社群的承诺而不懈努力,但又能够了解历史不是由那些在群众之外的“英雄”在幻想中创造的,任何一点点真正的进展都需要最高度的技巧和最精明的策略。因此,当《大厂》中的吕建国不得不请公安局的人吃饭,请他们了解工厂的困难,放出那个因嫖妓而被拘押的大客户时;当《分享艰难》中的孔太平为了保住全镇经济的命脉而不得不容忍和袒护那个劣迹斑斑的企业家洪塔山,甚至为此跪在受害者的面前。这些行为绝不是一种放纵和随波逐流,而是为了社群的最高利益而做出的极度痛苦的选择。“社群文学”在此提供了一种新的、具有力量的价值观。
“社群文学”通过这样四个方面的新的表述,凸显了一种以“社群”为基础的新的“公共性”的生成。它的最为重要的展示在于,尽管在同一社群之中的人们之间有巨大的差异,但他们最终仍然需要建构一种共同文化。只有有了这种共同文化,一个社群及其中间所有的人才会有所希望。而“社群文学”所提供的这种共同文化乃是我们最高利益上的一致性所决定的。中国民族的“发展”仍然是当代的巨大的历史主题。只有以一个社群为认同去应对市场化进程的种种问题,“民族的承诺”才会有其前提。而这种“社群的承诺”的紧迫性在于,中国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私人空间的自主性的扩大,社会分层的发展,中国社会的“私”的领域已极大地扩大了。个人的力争上游的“成功”的观念已开始融入了社会的价值之中。公共领域早已不再是国家单向对于社会的支配与管理,而是一个国家/市民社会/个人的多重对话的场域,是冲突、妥协的空间。因此,只有在温暖的、直接的对话中凝聚共识,以“民族的承诺”作为“社群的承诺”存在的依据,化解内部的分化与冲突,建立一种“共同文化”才是“社群文学”的选择。因此“社群文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立场,也就是由一个社群的共同性出发,走向一种对于社群内部差异的理解及寻找一种真正的共同性。
三
在讨论“社群文学”及“新状态”文学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发现“后新时期”文化正在建构一个新的自身的话语,这个话语就是今天的新的共同文化。这种共同文化的关键是在我/你之间以社群为基础的“公共性”的创生。这也为“后新时期”文化打开了一个真正具有历史性的未来。在五六十年代的文化中,我们曾建构了一个同质性极强,差异性极小,人们在极度强烈的“我们”的单向群体想象之中的的“我们”文化;而在“新时期”,我们曾建构了一个差异性极大,以个人主体为中心,很大程度上拒斥群体性的“我”/“他”对立的文化;那么“后新时期”的“社群文学”则建构了一个以“我”/“你”之间的差异为前提,却又“和而不同”地建构共同性的社群的文化。“我”/“你”虽有利益、价值上的多重差异,但却仍以民族的承诺/社群的承诺为前提凝聚成一个社群,去承担共同的艰难,分享共同的欢乐,探索共同的未来。
这种新的文学形态,也为当下知识分子的选择提供了一个宝贵的路径。在这个充满变化的世界上,一个从事写作的人只有和他自身的社群拥有一个共同的命运,他才能是一个“有机知识分子”去面对社群的痛苦、艰难和挑战。他需要沟通各个阶层不同的愿望和需求,体察和关切普通人的命运。他需要一种“世俗关怀”。这种关怀使他的存在不是虚妄而无聊的。他不是以某种狂想的名义仓促地采取行动,而是关注不为人所注意的现实;他不是为别人“代言”,而是揭示“状态”,让别人自己发言。他乃是强烈“入世”的,是“公共性”的表达者。
1996.8.13京郊魏公村
注释:
①有关“后新时期”文化的详细讨论可参阅谢冕、张颐武《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②Paul Virilio,Speed and Politice:An Essay On Dromology,trans,by Mary Polizzotti.New York: Semiotext.1986.P47
③有关“新状态”文学的详细讨论可参阅同①112—121页
④张新颖《文坛涌动现实主义冲击波》1996年8月2日《文汇报》
⑤《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357页,在中国社会学的传统中“ Community”一词多译为“社区”,但在近年的“文化研究”中,此词多译为“社群”。我以为第二种译法较合乎此词的所指,故从此译,在所有引文中均以此作了变动,以求一致。
⑥同⑤
⑦Zygmunt Bauman,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RoutledgePress,1992 P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