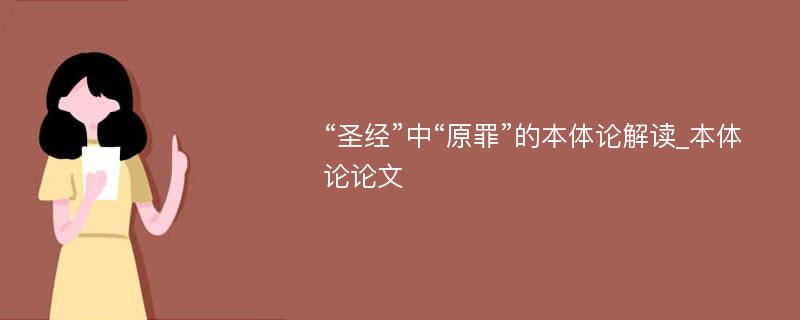
《圣经》中“原罪”的本体论释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本体论论文,原罪论文,释义论文,圣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希伯来文化作为西方文化的渊源之一,至今仍深深影响着西方文化的内在精神。《圣经·旧约全书·创世纪》中揭示的“原罪”则更深地溶入西方文化的底蕴,造就了一种典型的“罪感”型文化。因此,正确阐释“原罪”概念,对于把握西方文化的本质特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关于《圣经》的阐释学理论中,关于“原罪”的阐释众说纷纭,本文试图把“原罪”同人的本体论的分裂联系起来,对“原罪”概念提出另一种解释。
《旧约全书·创世纪》中说,上帝耶和华依据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并建造了伊甸园供他们生活。上帝告诫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了必死。”然而,狡猾的蛇却引诱他们偷吃了禁果,违背了上帝的戒律。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乐园,并被罚受无穷的劳役和痛苦,于是人类作为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便都带上了“原罪”。
在这里,《圣经》的作者以神话的形式告诉我们,人类摆脱自然状态,由自在到自为的根本标志只在于某种“原罪”,此后人类便永远与“罪”同在,直到获得拯救。这揭示了人类在现实生活中某种无法摆脱的负重感。那么,《圣经》中的“原罪”究竟是什么?对此,神学家和哲学家做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对《圣经》中的“原罪”问题作了系统的阐释。柏拉图主义者和摩尼教徒曾认为人的灵魂是纯洁的,而肉体则是罪恶的根源。奥古斯丁否认这一点,他认为人类的罪恶来自于灵魂,来自于自由意志。上帝造亚当时,亚当是纯真的,具有自由意志,但这时的自由意志是善良的意志,如果亚当能保持这一点,上帝就会赐给他恩惠,使他和他的子孙们享有天使们的幸福。然而亚当却堕落了,他滥用了他的自由意志,从而丧失了向往善的能力,因为屈服于魔鬼的人,他们的意志除了作恶之外,别无其它能力。于是人的意志自由便成了作恶的自由。亚当的罪不仅把上帝向他宣判的死刑(“因为你吃了必死”)带给了他的后代,而且也把罪本身传给了他们,哪怕是刚出生的婴孩。人类始祖的罪,实质上就是他所有后裔的罪,因为他们都在他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奥古斯丁在此把罪与人类的主观性(自由意志)联系起来,这实际上看到了罪是随人的产生(主观性的生成)而产生的;但他却大大限制了“原罪”的含义,在伦理学意义上去理解罪,把罪与恶等同起来,削弱了“罪”在人的存在中的本体论意义。这甚至不符合《圣经》的原意。《圣经》中的“原罪”仅仅是人知道了善恶,而非必然作恶。
中世纪哲学家雅可布·波墨试图从人的内在冲突中理解人的痛苦。他认为人是具有二重性的,人的精神始终处在“否”和“是”的对立之中,没有对立就没有理解,只是这种对立才产生了头脑中的斗争、痛苦和不满。因此,人的精神就被迫要摧毁感情的任性,以摆脱灾难和痛苦,进入永恒的宁静。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十分赞赏波墨的论述,他自己关于原罪的理解显然吸取了波墨的思想。
黑格尔认为《创世纪》中关于人类堕落的神话实质上表达了人类精神的发展过程。最初,精神生活在其朴素的本能阶段,表现为婴儿式的“无邪天真”和“淳朴信赖”;但这种自然朴素的境界绝不是至善境界,它只不过是自然的惠赐。人类毕竟不能永远生活在襁褓里,人类的精神本质上包含有曲折的中介阶段,“精神的本质在于扬弃这自然素朴的状态,因为精神生活之所以异于自然生活,特别是异于禽兽的生活,即在于其不停留在它的自在存在阶段,而力求达到自为存在。”在人的分裂阶段,人的每一个片面分别来说都是罪恶;自然的人对精神来说是恶的,“只要就人作为自然的人,就人的行为作为自然的人行为来说,他所有的一切活动,都是他所不应有的。”反之,人能超出他的自然存在,成为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个人。这尽管构成精神发展的一个环节,但也不应是人停留的地方,就它与共同体的对立来说,“他便陷于罪恶,而这个罪恶即是他的主观性。”于是从对立的两极来看,自然人即是个别人:表面看来人所具有的双重的罪恶,实质上却是一回事。因此,扬弃这种分裂境地返回统一便成为必要。
黑格尔看到了人的“原罪”根源于人的本体论分裂,但他却从所谓“两极相通”的辩证法出发,把个体的人、把主观性当作自然的人,由此他的克服分裂的途径也只能是客观主义、逻辑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还原方法,即把个人还原为社会、历史,把主观性还原为规律性,用他的话来说,“自然就是认识了的必然。”
现代存在主义者海德格尔则把罪归结为人的纯粹主观性的存在的根本方式。他指出,所谓人的原始的罪并不是日常所说的法律上的罪,如拖欠、剽窃、拒付、巧取豪夺之类的事;同样它也不是道德意义上的罪,不能用道德来规定。海德格尔认为应当抛开这些日常的罪的观念,因为通常所谓法律和道德的罪都是以这一原始的罪为根据和存在条件的。
那么,这一原始之罪究竟是什么呢?海德格尔认为,人的原罪就在于“此在”本质上的空虚,在空虚的意义上,即在“此在”没有能从根本上掌握自己存在的意义上,“此在”是有罪的。这里的空虚主要就在于人的存在的二律背反的性质:人一方面必须自己设置自己存在的根据,因为作为可能的存在,作为各种可能的集聚点,他必须自我决断,自己决定自己的意义;但是另一方面,人发现自己已经被抛在世,事实上存在着,他已经失去了某些可能性,由此他决不能完全支配他自己。海德格尔说:“自身之为自身不得不为自身设置它的这根据;这自身决不能控制这根据,而是不得不生存着接受根据性的存在。”用萨特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人不得不自由”,“人没有不自由的自由”。这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原罪。
在海德格尔那里,罪既不是善也不是恶,而毋宁说是人的不可摆脱的悲剧命运。人是被抛在世的,不得不自我决定,他唯一不能支配自己的正是他的被抛在世。于是原罪成了单纯主观性的属性,而人就是主观性,就是自由,因而罪也就成了人的本体论存在的根本方式。
可以看出,以往人们对“罪”的理解并不一致,他们有的把“罪”等同于伦理学的善恶,有的把“罪”归之于人的主观性或自然性,有的尽管表面承认“罪”的冲突意义,却又在实际上把冲突还原了。当然这其中也不乏对真理的揭示。如果我们返回到《圣经》,就会发现“创世纪”中的原罪是超越所有这一切之上的。
首先,人类的“原罪”是形而上意义的“罪”,是人类生存的本体论状态的“罪”,这种“罪”不是别的,正是人的根本分裂,即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矛盾冲突,它是超越伦理学的善恶的。在《创世纪》里,上帝禁止亚当和夏娃去吃智慧树上的果子,是想使人类永远处于与自然同一的和谐状态。当人类分有了这种智慧时,他便与外在的自然和自己的自然状态分离开来,于是分有了上帝的智慧,这意味着人类主观性的生成。主观性的生成、人与自然的分裂在某种意义上说确实给人类带来了灾难。人类不再简单地适应自然,那种足以满足其需要之物俯拾即是的时代过去了,上帝永远封闭了通往伊甸乐园之路,人类必须通过劳动,必须汗流满面地劳作,才能满足需要——这是上帝对人的惩罚。
当然,我们这时对《圣经》的援用仅仅是“借用”而已。因而,如果说基督教的“原罪”说对我们追寻人类本性有所启迪的话,那么启迪只在于它以神话的形式告诉我们,正是人类的祖先偷食了智慧之果,萌发了人的精神世界,才从此结束了人与自然混沌一体的原始状态;而与此同时人类便堕入了由此而来的一系列冲突之中,结束了人类的“乐园”时代。于是人的“原罪”不是别的,正是这种在人真正成为人的时候便深深刻在人类本性上的本体论冲突。当然,事实上,人类主观性的生成,人与自然的分裂,以及人类意识的自我分裂(生命意识与精神)并不能归之为外力作用的结果(蛇的引诱),而是人类以劳动为前提自身发展的结果。单纯的自然、单纯的肉体不是“罪”,单纯的精神、单纯的主观性也不是“罪”。人类的“原罪”只能是精神和肉体、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冲突和矛盾本身——这正是人类的本体论存在状态。
作为人类本体论存在状态的“原罪”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因而这种“罪”是超越道德和法律意义的,毋宁说道德上的“罪”和法律上的“罪”在某种意义上都是以此为根基的。从总体上说,道德和法律规范是人安身立命的根据,人们在这些规范中获取某种安全感,获得某种确定性。道德和法律作为社会规范犹如一个坐标系,人们希望自己能够进入这一坐标系,获得一个确定的位置;甚至可以说,这些规范的产生也与人类的理性和现实性紧密相关,与人类在实践基础上的自我分裂紧密相关。但是另一方面,人类的主观性又总是不会满足于既定的确定状态,总是要超规范地自由创造,——这种创造对于具体规范来说就产生了善和恶的问题。如果规范永远不被超越,社会就会永远处于停滞状态。所以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曾强调过恶对于历史发展的推动意义。
以往人们都从表面上理解《圣经》的“原罪”理论,把《圣经》伦理化,把“原罪”等同于道德和法律意义上的罪恶,把“原罪”说看作是人的性恶论,以此来贬低人,否认人有自我拯救的可能;而另一些人则在此意义上来反对“原罪”教义。这实际上都未能进入到问题的实质,未能了解“原罪”教义隐含的人类学意义。
其次,人类本性中的根本分裂和矛盾作为人的本体论存在状态,作为人类的“原罪”是充分个体化的,是每一个自我固有的“罪”,因而对于“赎罪”——解决这种分裂——每个人都是有责任的。
当把“原罪”与日常的罪恶等同起来的时候,人们便把亚当的“罪”当成伦理的罪,而伦理的罪是不可传递的,亚当的罪只能由亚当来承担,上帝对亚当的惩罚是正当的,但是作为亚当的后裔却没有任何理由接受“原罪”;而且“原罪”作为一种伦理的恶,具有极大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淹没了个体性,削弱乃至取消了个人的责任:性恶是人的普遍性,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很多神学家无法解决这一问题,他们担心人们会由此丧失在凡世努力的动力。
事实上,人类的“原罪”并不是伦理上的罪,它只是人类的本体论的分裂状态;它是从亚当(人类祖先的象征)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时候开始的。它并不是人类的堕落,而是人之为人的根本特征。它既是普遍的又是充分个体化的,是具体化于每一个人的现实存在之中的,是每个人面临的现实困境。换言之,每个现实的人都能够切身地体验到其与自然和社会的分裂和冲突;体验到生命与精神、理性与非理性、理想与现实的分裂和冲突;体验到主观性与客观性的分裂和冲突。从消极意义上说,它使得人在现实生活中,总是无法使分裂了的多重自我同时获得满足,使人在行为中进退失据、左右为难。在这种境况下,人们就会切实地感到相对于统一的、和谐的完满状态,自己是不能自足的,是有缺陷的,这本身正是人类的“罪”的意识,正是人类的“罪感”。然而从积极意义上说,只有有“罪”才产生了“救赎”的必要,只有缺陷才赋予人类以追求完满,追求统一、和谐,追求大全的本质意义。因此人类追求自身的和谐完美、追求自身的全面发展,追求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格的要求正是在“原罪”意识中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