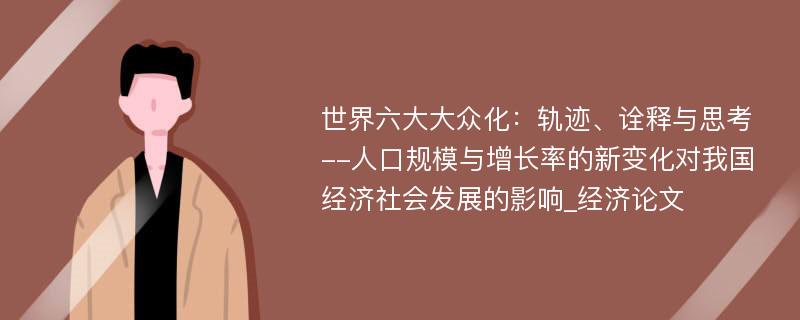
世人瞩目的六普:轨迹、解读与思考——我国人口规模及增长速度的新变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经济社会发展论文,增长速度论文,轨迹论文,世人论文,新变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0年末我国总人口约为13.4亿,仍是目前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9.4%。但是,人口增长速度下降明显,年平均增长率从1990-2000年的10.7‰下降到2000-2010年的5.7‰;净增人口进一步减少,从1990-2000年均每年的1279万人减少到2000-2010年的739万人。我国人口增长速度的新趋势以及由此引发的结构性问题将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事关我国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地位,应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给予重视,并作出相应的制度和政策安排。
1 人口规模及增长速度变化的历史回顾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医疗卫生条件得到改善,死亡率迅速下降,而出生率则一直保持较高水平,使得人口快速增长,形成了1949-1958年的第一次增长高峰和1962-1975年的第二次增长高峰。在第一次增长高峰期间,平均每年净增1221万;而在第二次增长高峰期间,平均每年净增高达1947万人。相应地,人口规模从1949年的5.4亿增加到1981年的10亿,面临巨大的新增人口的压力。一是少儿人口对教育的压力,二是年轻人口对就业、住房等方面的压力,三是满足新增人口的刚性消费对资本积累的制约。这一阶段,我国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处在“劣性均衡陷阱”中,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很大。从人口问题的角度看,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困难的时期。
1970年代初,我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快速人口增长的势头很快得到遏制。人口出生率从1970年的33‰下降到1980年的18‰,10年间下降了15个千分点,一举奠定了人口转变的基础,也开启了“人口红利期”的窗口。这一时期,平均每年净增1523万人,大大减轻了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压力。虽然受经济体制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以及第一次和第二次人口增长高峰的周期性影响,1981-1990年间,人口增长率有所回升,形成了第三次人口增长高峰。但与前两次人口增长高峰相比,这次人口增长高峰的波动幅度不大。这期间,平均每年净增1587万人,大致与1970年代持平,没有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明显的冲击。1992年,妇女总和生育率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增长的动力出现“拐点”,开始进入惯性增长时期。1998年,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10‰以下,标志着人口转变基本完成。1990-2000年间,平均每年净增1279万人,人口负担进一步减轻,形成了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人口红利期。
进入21世纪后,我国人口规模继续扩大,但增长惯性明显减弱。这一时期,我国总人口中劳动力比重处在最高峰,人口负担系数达到了最低点,人口处在最有活力的时期,是最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好时机。在良好的人口环境下,我国经济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2000年的1000美元以下,提高到2010年的4000美元以上,跨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人口规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在内涵上发生了变化。在人口转变的初期,特别是1949-1975年间,多数年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高居20‰~30‰,人口规模压力的主要表现是每年新增的经济成果很大一部分要用于满足不断扩大的人口规模对基本生活消费的需求,妨碍了生产要素的形成和资本的积累。目前,满足基本居民生活消费的生产能力已经不成问题,问题是随着人民消费水平的提高,人口规模的压力逐步转向对资源和环境的压力。
2 人口规模及增长速度的新趋势
1970年代,随着世界人口转变进程的加快,发达国家的生育率纷纷下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人们开始关注人口增长下降对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对经济增长可能带来影响。发达国家人口已经低速增长多年,但出现零增长的国家为数不多。目前人口零增长主要发生在东欧和南欧。按照联合国的预测,到本世纪末,世界人口仍将继续低速增长,而我国几乎与发达国家同时在2030年前后出现负增长。当然,我国人口何时出现零增长、峰值是多少、零增长后的人口形态如何则取决于未来一个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以及人口发展战略选择和相应的政策取向。从目前几个影响人口规模的要素看,人口零增长到来的时点或许比以往预期要早。
一是育龄妇女人口规模即将达到峰值。由于第二次人口增长高峰时出生的妇女即将退出育龄期,而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的“80后”、“90后”人口成为生育旺盛期的主体,育龄妇女总量在“十二五”时期达到峰值后开始缓慢下降。其中,20~29岁生育旺盛期的育龄妇女将从2011年的1.08亿下降到2020年的0.85亿,平均每年将减少200万人以上。在同样的生育水平下,育龄妇女,特别是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的减少意味着出生人口的减少。
二是生育水平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按照国家统计局年度公报的出生人口数推算,近几年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65左右。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加之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特别是城镇化的进程将进一步促进人们婚育观念发生变化,实际生育水平会逐步接近政策生育水平。在育龄人口略有增加的情况下,“十一五”出生人口比“十五”时期略有减少,表明我国生育水平总体上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
三是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速度。人口自然增长既受出生率影响,也受死亡率影响。一方面,我国人口出生率从1999年的15.23‰下降到2009年的12.13‰;另一方面,由于人口老龄化,自1976年后一直保持在7‰以下的人口死亡率在2008年首次回升至7‰以上,年死亡人口从1999年的810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943万人。在出生率和死亡率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99年的8.77‰下降至2009年的5.05‰。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2030年前后我国将出现人口零增长,开始进入负增长阶段。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人口增量将越来越小,走向零增长的步伐正在加快。今后人口规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更多是人口存量及其内部素质、结构和分布问题,而净增人口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人均指标的影响力将进一步减小。在世界人口仍将继续增长30亿的形势下,如果我国过早地出现人口零增长现象,既不利于人口均衡发展,也将影响国际竞争的人口条件。人口规模从膨胀到萎缩,必将引发一系列的人口变化,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新一轮的影响,带来一系列结构调整和重新适应问题。因此,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及时做出战略调整和政策反应十分必要。
3 几点思考
在联合国《2010年世界人口展望》所统计的230个国家或地区中,人口超过0.4亿的有34个,其中1亿以上的有11个。我国人口规模大约相当于那些人口少于0.4亿的190多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总和,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而且是超级人口大国。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面对和承受着规模庞大的人口增长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压力,对于如何应对人口增长已经有了很多办法,而对趋近零增长的人口发展,对人口减少所带来的问题还不太适应。在此,仅就人口规模及增长速度的新变化,提出以下几点思考。
第一,人口规模与综合国力。从一般的经济发展规律看,人口规模在不同时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生产力不发达时期,劳动力是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人口规模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国力的最重要指标之一;在工业化时期,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了“人手”,人口规模的大小与综合国力不一定成正比,人口大国不意味着综合国力强大;而在现代社会,人力资本带来的技术、知识、创新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人口素质与结构是综合国力的决定性因素。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知识传播速度的加快、科学技术共享程度的加深以及人口素质的普遍提高,各国生产力水平逐步趋同,劳动力资源趋于“同质”,一个国家或地区占世界人口比例与综合国力的关系再次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第二,人口高速增长与低速增长。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历人口高速增长后,都要逐步完成人口转变的过程,先是孩子的减少,而后是劳动力的减少,最后进入老龄化的常态社会。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人口规模曾经高速增长,从5.4亿增加到13.4亿。在巨大的人口规模压力下,我国应对措施得当,不但实现了人口转变,而且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中国奇迹。犹如恐惧“人口爆炸”一样,面对趋近零增长的人口发展,新的担忧再次出现。我认为,这种担忧十分必要,但担忧的不仅是人口规模的压力,更主要的是,在未来几十年内,在继续承受巨大人口规模压力的同时,人口的低速增长会带来一系列的结构性问题,包括人口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性别结构、年龄结构、家庭结构等等,将成为影响我国从中等发达国家向发达国家迈进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低速人口增长也没那么可怕。发达国家人口低速增长多年,经济社会发展并没有出现严重衰退,而是稳定在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事实上,许多人口现象是中性的,比如劳动力资源丰富的人口红利期,利用好了就是机遇,而处理不好就是挑战。因此,人口零增长只是人口转变的继续,是人口发展的一个过程,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如何适应。
第三,人口低速增长与经济增长动力。目前,发展中国家面临人口高速增长问题,而发达国家则要应对人口低速增长带来的影响。在低速人口增长条件下,人们最担心的是经济增长的动力问题。从一般的发展规律看,在低速增长的人口环境中,很难看到高速经济增长的现象,只有中国是个例外。我国虽然处于人口低速增长状态,但人口数量大,有利于形成规模经济。城乡发展不平衡可以使我国经济发展形成区域互动的发展模块,产业可以进行不同层次和梯度的转移,回旋的余地大。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扩大、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及人口走向零增长,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会逐步减慢。这就要求我们不能过度依赖劳动力数量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充分开发人力资源,加快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过程,向人口素质要红利,再造人口资源新的比较优势,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持久的动力。同时,我们可以利用人口流动和迁移产生投资和消费的机会,向人口城镇化要红利,弥补人口低速增长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第四,规模结构矛盾与人口均衡发展。我国今后将长期面对人口规模庞大,但增长速度很低的局面。在这个过程中,结构和分布将发生巨大变化。因此,我们既要承受人口规模的巨大压力,也要面对复杂的人口结构性矛盾。我认为,应对规模压力和结构矛盾的关键是要逐步完善人口与经济社会政策,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按照联合国对中国人口发展前景的预测,如果目前总和生育率1.64保持不变,总人口峰值为14.1亿;而将总和生育率从2010年的1.64逐步提高到2030年的更替水平,总人口的峰值为14.8亿,比生育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增加7000万人。从近期看,会使人口压力有所增加,但是从长期看,这部分人口将有助于人口均衡发展和家庭功能稳定,也有助于缓解低速人口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因此,在低速人口增长的形势下,要转变调控人口的思路和方法来应对人口规模压力问题,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指出的,“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缓解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
总之,在过去30多年,我国很好地解决了人口规模的压力问题,并充分抓住用好人口资源的比较优势,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奇迹。未来几十年,在人口低速增长新趋势下,我国人口发展形态将发生巨大变化,进而对经济社会产生长期而深刻的影响。如果能够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充分考虑人口因素的新变化,因势利导,再造新的人口资源比较优势,会极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跃上一个新台阶。因此,把人口发展战略作为最基础的战略,采取一揽子的措施,逐步完善人口与相关经济社会政策,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积极应对人口的新变化给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