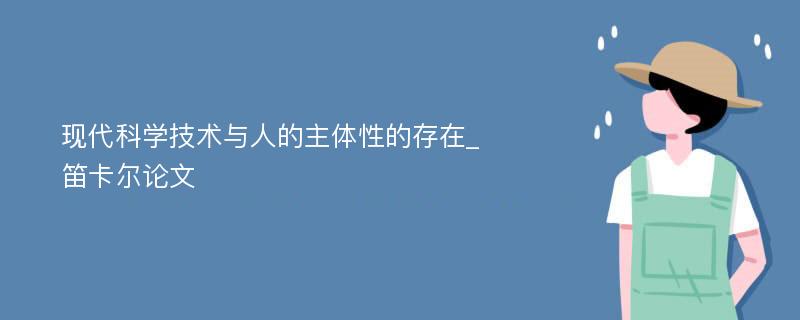
现代科技与人的主体性存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主体性论文,现代科技论文,与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03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018X(2005)02-0026-04
一
“主体”一词向来被看做一个认识论范畴,指认识者,而被认识的对象则是客体。现代技术理性就建立在主客二元对立基础上。古希腊人的认识是一种主客不分,浑然一体的认识。他们既不把自己看做是外在于自然事物并对自然事物进行观察的“主体”,也不把自然事物当做独立人之外、与人意识无关的“客体”。在古希腊人那里,自然界是渗透或充满着心灵的,自然界的规则和秩序源于自然界心灵的存在。因而,才有了古代的“泛神论”和“万物有灵论”。中世纪的人也不把自然事物与人划分为互相对立的两端。在中世纪,自然事物与人都是上帝的造物。将人与自然事物分隔开来最早体现在伽利略的物理学方法中。伽利略用实验证明,自然界无非是由一些可按数学处理的物理特性所组成,宇宙这本书“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字母是三角形、圆和其他几何图形”,[1](P74)从而清算了把主观意识融入自然的“泛神论”和“万物有灵论”。在人面前,自然界成了一个“对象”,一个与人的主观意识活动格格不入的“对象”。到牛顿的物理学大综合,在伽利略那里还未曾明确作出物理学解释的质量和惯性得到了澄清。牛顿用万有引力理论“把日月星辰的运行、地上物体的运动、潮汐涨落、光的折射、物质的微观结构等等,统统纳入一个可以用数学加以定量分析的和谐体系之中。”[2](P18)自此,自然界完全成了一幅数学和力学的图景,人的精神因素被从自然界中剥离出来,人与自然完全对立起来了。
与科学上把人和自然完全对立起来相应的是哲学上笛卡尔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二元论。笛卡尔是西方近代哲学始祖,同时他也是一个著名的数学家。作为一个数学家,笛卡尔与伽利略、牛顿一样,把自然界看成是一种数学实在。笛卡尔尤其在认识论上致力寻找一些确实而自明的真理。传统经院哲学不能提供这种确实自明的真理,因为经院哲学用来解释自然界的“本质”、“原因”等术语本身就不确定,就有着种种的分歧。从经院哲学发展来的其他科学既是基于这不稳靠的东西,那么它们也就不可能提供给我们坚实可靠的知识。我们的感觉也不可靠,感觉常常会欺骗我们,这在哥白尼的“日心说”中已得到证实。笛卡尔说:“于是我想我所看见的一切事物都是假的;我相信我的欺诈的记忆所提供给我的那些东西,没有一件是真的;我想我没有感觉;我相信物体、形状、广袤、运动和位置不过是我心灵的虚构。那么,还有什么可以以为是真的呢?也许只是这样,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确实的。”[3](P308)在笛卡尔看来,惟一确实的、不能怀疑的就只有“我怀疑”或“我思考”本身了。“在思维者进行思维的时候,设想思维者不存在,这是矛盾。”[3](P309-310)于是,笛卡尔从逻辑上推论出“我思,故我在。”在笛卡尔这里,不仅与伽利略、牛顿一样把人的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对立起来,彼此完全独立,而且还进一步提出思维着的人是存在的起点和基点,这就为他在《方法论》一书里曾谈到的通过新物理学,“使我们成为自然界的主人和统治者”的希望提供了哲学思辨上的支持。康德批判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命题,从先验的我直接推论出经验的我,从而混淆先验的我与经验的我的界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物质世界不能只从客体的自在形式方面去理解,而且还要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在康德那里,任何经验之物,都是先验自我与感觉材料结合而成。这一思想表明,人作为物质世界的观察者,并非消极被动地接受现成的给予,而是积极主动地参与了物质世界的形成。如果说,把人与物质世界区分开来只是人成为一种主体性存在的第一步的话,那么,强调人积极主动参与认识对象的生成就进一步确立于人的主体性存在的地位和作用。
二
但人成为主体绝非仅仅是一个认识论事件,它更是一个存在论或本体论事件。海德格尔说“世界之成为图像,与人在存在者范围内成为主体是同一个过程。”[4](P89)在海德格尔那里,世界成为图像是指存在者整体(包括宇宙、自然和历史等)被定位为技术生产体系的物质性要素和功能性要素,并且惟有被具有表象和制造作用的人定位为这种技术生产要素它们才是存在着的。这里“表象”一词至关重要,海德格尔说:“这种对存在者的对象化实现于一种表象”,[4](P83)表象不同于古代认识论意义上的觉知。在古代,被觉知的事物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它乃作为涌现者和自行开启者而遭遇觉知的人。它不仅不是通过觉知的人才获得自己的存在,而且人和被觉知的事物一样,都“被牵引入存在者之敞开领域中并且被扣留于其中,从而被这种敞开领域所包涵”。[4](P87)现代的“表象”意指完全不同的东西,“表象在这里的意思是:把现成之物当作某种对立之物带到自身面前来,使之关涉于自身,即关涉于表象者,并且把它强行纳入这种与作为决定性领域的自身的关联之中。”[4](P87-88)在现代表象关系中,首先被表象的东西被表象者作为对象带到面前,而不是像古代那样人和物都作为涌现者和自行开启者在敞开领域彼此相互遭遇。其次表象者与被表象的东西不是作为在场者都归属于存在,为存在所要求和规定。而是被表象的东西“被摆置到人的决定和支配领域之中,并惟有这样才成为存在着的。”[4](P86)被表象的东西归属于表象者,为表象者所要求和规定。更重要的是惟有如此这般地成为表象者的对象,被表象的东西才被视为存在着的。在表象关系中,表象者即人成为主体,而同时世界成为图像并且惟有成为图像世界才是存在着的。因此,表象更倾向存在论,表象者成了一切存在者之所以存在以及如何存在的原因。
海德格尔认为。图像的本质在筹划、计算。筹划乃对世界基本轮廓的描画,这种描画开启了一个敞开区域,使自然事物以这种方式、这般模样来与我们照面。因此,世界成为图像意味着人与世界打交道之前,已经有了了解某事物的准备。海德格尔曾谈到在发现桌子上三个苹果之前,我们一定有了关于三这个数字的知识,这种数字知识构成我们接触和理解苹果的基本框架,决定了我们与苹果打交道的方式以及苹果以如此这般数量关系的模样来与我们照面。清词人纳兰性德《蝶恋花》“唱罢秋坟愁未歇,春丛认取双栖蝶”,用“认取”两字写人与事物打交道的方式。认取乃一种选择,妻子死后给词人留下的孤独和愁苦是人与事物打交道前的准备。现代科技的筹划建立在计算基础上,“这种表象的目标是把每个存在者带到自身面前来,从而使得计算的人能够对存在者感到真实,也即确定。”[4](P83)一切事物必是在计算、在数量关系的基本轮廓中来与我们照面,而且惟有在这种基本轮廓中它们才是存在着的。
世界成为图像是近代科技的产物,古代和中世纪不存在这种世界图像。中世纪,存在者乃上帝的造物,“那时,存在者存在意味着:归属于造物序列的某个特定等级,并作为这样一种造物符合于创造因。”[4](P86)中世纪的存在者既不是作为对象被带到人面前,更不是由人所决定和支配并由此才成为存在着的。古代的存在者就更是如此了。古代人与物都是涌现者和自行开启者,他们都归属于存在。尤其“存在者并不是通过人对存在者的直观——甚至是在一种具有主观感知特性的表象意义上的直观——才成为存在着的。”[4](P87)在古代,存在就是在场,而不是被表象。
作为存在论事件的人成为主体与作为认识论事件的人成为主体有着重大的区别。在后者,人的地位和作用仅局限于认识论范围。但在前者,人成为主体不仅影响着人的认识,尤其影响人以及一切存在者的存在。
三
人成为一种主体性存在的意义并非仅仅是人摆脱了以往物质世界和神的束缚而成为了自身,而是人成为主体之际人的本质发生了根本变化。首先,作为一种主体性存在,人从其他一切存在者中超拔出来,成为与其他一切存在者相对峙的另一端。“现代意义上的‘主体(Subjekt)’源自拉丁文的subjectum(一般主体),后者是对希腊文的hypokeimenon的拉丁翻译,意为一切存在者的基础、基体,而并没有特指人。只是在现代的开端,即在笛卡尔那里,人才成为突出的决定性的‘主体’……。”[5]即是说,技术时代以前的“主体”并非指人,而是指一切偶然、多变的存在者中一以贯之的东西,是一切存在者的主干、基体。这种主干性、基体性的东西既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物。桌子、植物、鸟和人都可以是“主体”。但在技术时代,“主体”的内涵被缩减了,它只指人的存在。人从桌子、植物、鸟等其他事物中超拔了出来,“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惟一坚持到底的,成为一切存在者的关系的基础。”[6](P44)现在,人不再把自己看做是众存在者中的存在者,而是看做与其他存在者相对峙、并在存在论意义上具有其优越性的主体,因而人在其他存在者面前就具有了特殊地位。
其次,人成为表象者,即成为决定其他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的基础和根据。在现代表象关系中,人虽然仍“被牵引入存在者之敞开领域中并且被扣留于其中,从而被这种敞开领域所包涵”,但更重要的是,作为表象者的人还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主动性、决定权和支配权。现代表象使事物与人发生关联,而且惟有与人发生关联,事物才成为存在着的。“一切存在者从与主体的单纯的‘对峙’而得到自己的地位,成为对象,因而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为存在。”[6](P44)人成了决定性的东西,这样对其他一切存在者来说,只能还剩下对主体来说必要的对象性。因此,作为表象者的人对其他一切存在者的优越性和特殊性就不仅仅在他成为了与其他一切存在者不相同的另一端,更在他在本体论意义上成为其他一切存在者的基础和根据,成为裁定其他一切存在者之存在状态的“法庭”。人如果成了第一性的和具有决定意义的基础和根据,那就意味着:一切存在者以其存在方式和真理方式把自身建立在人这种存在者之上。人成为存在者的中心。
第三,预定者和持存物。人成为主体,事物成为对象亦即客体,是表象关系的第一步。但表象关系不可能结束和停止在这一步。随着表象关系的进一步展开,人和事物的主客对峙关系发展成为预定者和持存物的关系,表象就成为技术展现。在主客对峙关系中,作为对象的客体“总是还有某种程度的自身性、反抗性、相异性、不可捉摸性;而这些东西在日益增长的技术展现中已经看不到了。”[6](P75)在技术展现中,客体不再是自在存在的独立事物,因为它未从技术生产体系中获得它的规定和存在方式,只有进入技术生产体系,它才被看做是存在的。这种失去其自身性、独立性,成为随时供技术生产体系所使用的物质性存在和功能性存在的事物,即“在持存意义上立身的东西,不再作为对象而与我们相对而立。”[7](P935)与此相应,“如果对象消解为持存物,那么主体也必然发生变化”,[6](P78)即人也完全丧失了其自身,不再是独立的主体。他不仅从技术生产体系获得他自身的规定性因而亦成为持存物,而且同时他还参与了对其他物的技术“预定”,即按照技术意志的限定和强求把一切事物物质化、功能化因而成为预定者。主客关系也就成了预定者与持存物的关系,成了“需要和需要满足者这两极的关系。”[6](P76)
惟有人从物质世界中超拔出来,并把物质世界视为有待认识、改造的对象时,现代技术生产体系方才成为可能的。而另一方面,也只有通过现代技术生产实践,主体客体也才得以真正形成。在古代和中世纪,由于人还没有成为主体,世界也未变成图像,人与物浑然一体,因此人的生产实践受到极大限制。反过来,有限的生产实践也越发使人不可能意识和发挥潜存于他自身的力量和主体性。现代技术生产体系则不同,当自然界不再是渗透或充满着心灵的活物,也不再是上帝的造物,而只是由数学和机械规律所组成的外部世界时,人对自然就不再像古代和中世纪的人那样充满了敬畏和虔诚,自然也才有可能成为现代技术生产体系的单纯能量提供者、物质和功能性存在。只有在这个时候,人对自然的大规模进攻才有可能。更重要的是,主体客体的真正形成是通过现代技术生产活动实现的。这不仅指人类最初从原始的自然界分离出来,而自然成为被人所认识和变革的对象都是通过劳动实现的,更指在现代大规模的技术生产过程中,人凭借现代科学技术,对自然进行无限制地拆解、拼凑,将自然打造得更加符合人的实际需要,从而使人的主体性以其前所未有的强劲彰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