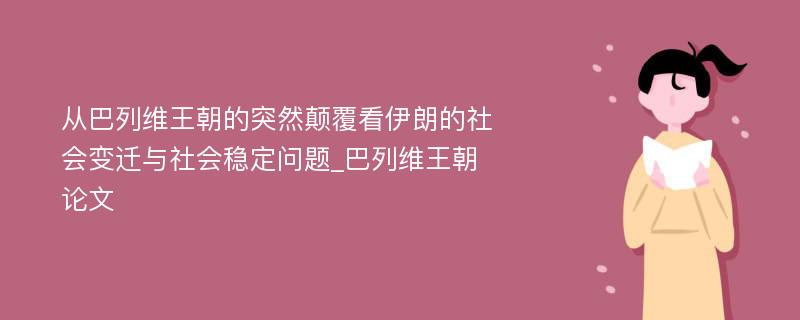
从巴列维王朝的突然倾覆看伊朗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王朝论文,伊朗论文,社会稳定论文,列维论文,社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变革(或谓“社会变迁”)加速进行。广义的社会变革,指的是从传统的农牧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和城市社会演变的过程,涉及经济、社会、政治、外交或国际关系、文化乃至人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方方面面。大致说来,在科学技术的推动下,工业化拉动城市化,进而带动社会的全面变革与发展。不过,对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而言,自上而下地追赶和学习先进的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仿效其发展道路,同时遭遇殖民列强的经济剥削与政治压迫,加之遭遇不平等的国际经济关系和政治秩序,使其社会变革的环境与路径明显地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在社会变革的复杂进程中,维护政治秩序,保持社会稳定至关重要。研究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的辩证关系,对于我们认识当今的世界,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伊朗是海湾乃至中东地区大国,在伊斯兰教世界和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都具有重要影响。在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方面,伊朗在20世纪走过的道路,与许多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一面。比如,以土地改革为核心的“白色革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持续、稳定和高速经济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急剧社会变革。与此同时,伊朗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又明显地具有自身的特点。首先,伊朗提供了一个高速经济增长下政权出人意料地突然倾覆的典型案例,即1979年伊朗革命的爆发;其次,与此相关,伊朗的社会变革进程和社会稳定问题,与伊朗国家与宗教的关系直接关联,以至于1979年革命普遍地被称作“伊斯兰革命”。在中东伊斯兰教世界,伊斯兰教与国家的关系是一个具有共性的重大问题,然而伊朗作为最大和最重要的什叶派国家,什叶派教士(音译为“欧莱玛”)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更加突出。本文在吸纳学术界既有研究成果①的基础上,从革命力量与关键历史人物的视角入手,重新探讨巴列维王朝突然倾覆的原因,进而考察1979年革命前伊朗的社会变革与社会稳定问题。 一、巴列维王朝突然倾覆的原因 20世纪的伊朗,发生了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社会稳定问题亦相当突出。腐朽没落的卡扎尔王朝(1786-1925年),历经立宪运动(1905-1911年)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终于在1920年代中期走到了尽头。军人出身的礼萨汗在大地主的支持下,于1925年建立起巴列维王朝(1925-1979年),强力推进了伊朗的国家统一和民族主权国家的构建,大刀阔斧地实施世俗化、西方化和民族化改革政策,促进了伊朗社会变革。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1953年“八·一九”政变以来,伊朗在美国的扶植与敦促下,依托愈益增长的石油收入,加速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六七十年代,随着“白色革命”的开展和五年发展计划的实施,伊朗经济高速增长,人均收入也显著提高。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以欧莱玛和资产阶级为领导力量,以城市和平示威为主要手段的“和平革命”,却在很短的时间里出人意料地推翻了巴列维王朝,震惊了世界,更凸现出伊朗社会变革对社会稳定的冲击。 1.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主要社会力量 探究1979年巴列维王朝覆灭的根本原因,人们首先想到的是塞缪尔·亨廷顿关于专制王朝推进现代化的“根本性困境”理论。亨廷顿说:“一方面它们必须集权于君主以图推开社会与经济改革;另一方面,集权却又使扩大传统政体的权力和吸收现代化所产生的新集团变得更为困难、甚至不可能。要使这些集团参与政治似乎只能以牺牲君主制为代价。”“传统政体能够改造社会,却不能够改造自己。君主政体之父最终被其现代化之子所吞噬。”②换言之,在现代化浪潮下,君主必须搞现代化改革,以增强政治合法性。改革就必须集权,而改革的成功往往削弱君主政体的合法性,因为初期现代化改革的成功必然培育出要求深化改革、扩大政治参与的新生社会阶层和集团,而君主专制的内在逻辑难以通过扩大政治参与获得稳定的现代政治合法性。 亨廷顿关于君主制政体实施现代化的“根本性困境”的宏大理论,看来言之凿凿,颇有道理。但是结合伊朗实际,细究起来,尚有疑问。虽然1950年代以来快速推进的社会变革,扩大了伊朗中间阶层(或称中产阶级)的规模与力量,但是伊朗中间阶层不是1979年革命的主力军。首先,中间阶层,包括政权体制内的中低级人员、专业人员和国有部门人员,大多是政权的依附者和受益者,缺乏革命的内在动力。其次,中间阶层内聚力弱,组织性不强。虽然部分出身中间阶层的人士成为政治领袖,但中间阶层本身没有组织起来,既不是革命的领导力量,也不是革命的中坚力量。他们几乎没有政治行动的能量,缺乏集体行动必需的组织机构。白领雇员和专业人员在反对派发起行动后一年多没有卷入政治冲突。当他们终于参加进来,大多要求经济而非政治变革。③因此,巴列维国王的垮台,主要不是社会变革中产生的新生阶层渴求扩大政治参与同君主专权冲突的产物。 与中间阶层类似,劳动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在内,内聚力不够,组织性不强,展现出比较低的集体行动能量。工人阶级比较集中,组织程度较高,1977年经济危机以来由于通货膨胀与政府的紧缩政策,他们的经济地位下降,是革命的肥沃土壤。1978-1979年石油工人和其他产业工人的集体行动,极大加剧了伊朗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可以说是葬送巴列维国王的最后一支关键力量。但是,此前巴札④持续不断的坚决斗争迫使国王做出政治让步,为工人阶级的动员奠定了基础。可见,工人阶级加入革命晚,亦不是革命的主力军。 在土地改革中,农民阶级发生分化。少数农民,即享有租佃权的分成制农民,分到少量土地,是土改的直接受益者。由于推进农村资本主义发展,这部分本来受益不多的农民,在合作社和农场企业的发展中受到负面影响。因此,与巴列维国王土地改革的初衷相反,他们没有成为政权的支持力量。占农村人口1/3的没有租佃权的农民和无地农民,在六七十年代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或继续其无奈的悲惨生活,或沦为资本主义农场的雇佣劳动者,或移民城市转变为城市贫困移民。作为“城市示威型革命”,伊朗农村人口“超然”于革命之外。国家的资本积累与分配政策极大地偏向城市,向大资本倾斜,忽视农业和农村地区,导致农民状况恶化,城乡之间和地区间不平等加剧。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移民城市的原农村人口,在革命末期卷入其中,但显然同样不是革命的主力军。 研究巴列维王朝突然倾覆的原因,就必须回到伊朗特殊的社会结构和国家与宗教关系上来。在持久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伊朗资本主义艰难发展,且发展不充分,伊朗产业工人和资产阶级都没有成为伊朗社会发展的主要领导力量。伊朗资本主义的欠发展和资产阶级的软弱,对伊朗社会和政治的影响极为深远。一方面,资产阶级或者依附于政权,成为官僚资产阶级,或依附于国外大资本,成为买办资产阶级,均具有天然的软弱性。与巴列维政权既斗争又合作。因此,虽然伊朗自1906-1911年立宪运动以来形成了某种“民主”传统,资产阶级自由派也在一定程度组织起来,但是资产阶级内部是不统一的。面对巴列维政权的强力弹压,没有成为伊朗政治的主要力量。1978年11月初,资产阶级自由派领袖马赫迪·巴扎尔甘和卡里姆·桑贾比到巴黎拜会霍梅尼,资产阶级与欧莱玛结成推翻巴列维政权的政治联盟,实际上服膺于以霍梅尼为首的欧莱玛阶层。 另一方面,正是由于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伊朗经济和社会中的传统力量,即巴札和欧莱玛相当强大。虽然大工业在六七十年代长足发展,伊朗的传统商业——巴札受到冲击,但是其力量依然相当强大。据估计,巴札控制着当时伊朗国内贸易的2/3和对外贸易的1/3。与资产阶级和中间阶层不一样,巴札具有比较雄厚的经济实力,对政权的依附性低,长期以来是伊朗社会中一支独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而且,巴札内聚力强,组织程度高,在1950年代初期的石油国有化运动和1960年代初期的政治动荡中,都发挥了主力军的作用。1975年政府控制通货膨胀和打击投机倒把运动,危害了巴札的既得利益,把巴札彻底地推向了政权的对立面。1978年1月发生所谓库姆惨案,巴札与欧莱玛在政治上结成联盟,反对派势力壮大。反对派以欧莱玛为主要动员与组织力量,以巴札为主要后盾,发动频繁的大规模和平抗议示威,致使伊朗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社会动乱和政治对抗愈演愈烈。随后,产业工人尤其是控制伊朗政府钱袋子的石油工人加入革命。 作为世界上最大和最重要的什叶派国家,伊朗国家与宗教的关系,明显地不同于伊斯兰教逊尼派国家,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1979年革命的特征与巴列维国王的命运。简而言之,自16世纪初什叶派成为伊朗国教以来,虽然发生过一些变化,但是什叶派欧莱玛始终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阶层和政治力量。宗教是国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源泉,什叶派欧莱玛控制教育和司法部门,并且拥有独立的经济、财政资源。在欧洲殖民势力特别是英国和俄国的经济渗透与殖民入侵中,欧莱玛作为民族主义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成为维护国家独立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尤其体现在1891-1892年反对腐败的卡扎尔王朝出卖烟草专卖权的斗争中。在立宪运动中,欧莱玛再次行动起来,成为运动的主要领导力量。礼萨汗的世俗化改革力度很大,但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欧莱玛的独立地位,欧莱玛积极参加1950年代初期的石油国有化运动。保守的欧莱玛后来撤回对摩萨台首相的政治支持,是这场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 总的来看,礼萨汗的改革没有触及欧莱玛的根本利益,主流的欧莱玛暂时远离政治。事实上,欧莱玛与政权达成了妥协,至少是某种默契。1953年“八·一九”政变后,巴列维国王竭力争取欧莱玛的支持,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是1959年土地改革法案遭到欧莱玛的反对,结束了双方“短暂的蜜月”。阿亚图拉博鲁杰尔迪指出,对土地所有权的任何限制有辱伊斯兰教法,议会两院应当“阻止批准这个法案”。⑤随着巴列维“白色革命”的开展,双方的冲突愈益激烈起来,霍梅尼在这场斗争中脱颖而出,最终成为巴列维王朝的掘墓人。 概而言之,欧莱玛作为一支独立的社会和政治力量,具有很强的政治动员和组织能力,是推翻巴列维王朝的主要领导力量。同时几个关键历史人物对1979年革命的突然成功至关重要。 2.巴列维王朝倾覆中的关键人物 三个关键人物——时任美国总统的吉米·卡特、巴列维国王和鲁霍拉·穆萨维·霍梅尼是巴列维王朝突然覆灭的偶然却极为关键的因素。 自1953年“八·一九”政变以来,美国成为巴列维王朝的坚强后盾,是影响伊朗经济发展、社会变革和政治进程的最为关键的外部因素。数额巨大的美援,加之美国在政治、外交、军事上的支持,使巴列维国王很快巩固了自己的权力,进而推进以“白色革命”为核心的社会变革。在美国与苏联冷战的大棋局中,伊朗成为美国的重要盟友,对于遏制苏联南下波斯湾和维护美国在海湾的战略、能源和经济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时代在变,美国与伊朗的关系也在变。肯尼迪当选美国总统,恰逢伊朗经济危机,强烈要求巴列维国王大刀阔斧地实行经济和社会改革,加速推进伊朗社会变革。快速社会变革与过热的经济,民众过高的期望与现实的反差,给社会稳定带来风险。对于专制独裁的巴列维政权而言,重视人权、大搞人权外交的吉米·卡特当选美国总统后,无疑使伊朗面临巨大的压力。卡特政府内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国务院之间对伊朗政策存在的严重分歧,使卡特总统迟疑不决,左右摇摆。巴列维国王本来就因为曾卷入美国总统大选,阻止卡特当选未果而心生疑虑,卡特的摇摆使巴列维国王怀疑美国有推翻他的意图。华盛顿发出的混乱信息,反倒使反对派深受鼓舞。最终巴列维国王于1979年垮台,美国“失去了”伊朗。 巴列维国王计划通过“白色革命”和强劲的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在极短的时间内把伊朗建设成海湾第一强国、世界第五工业强国,恢复波斯帝国的辉煌。然而,他自挖墙脚,很快就站到伊朗社会各主要阶级、阶层的对立面。从宏观上看,这是因为改革或者不彻底,比如土地改革,既没有培育出强大的受益者群体,又损害了既得利益集团或阶层。或者因为头脑发热操之过急,或者目标过于宏大而超出了国力,比如1974年8月修改第五个发展计划,把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1.4%调高到25.9%。⑥或者资源分配严重失当,比如过高的军费开支,严重忽视农业和对农村的投资。 巴列维国王在执政的最后阶段出现极为严重的政治失误。面对复杂艰难的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和政治危机,巴列维国王顾此失彼,一再发出错误的信息,做出错误的决策。1970年代前期,由于石油美元大量涌入,伊朗发生严重的经济过热,地价飞涨,房租猛涨,通胀率急剧上升,工薪阶层生活成本剧增。于是,政府规定最低工资标准,甚至强制要求私人企业主满足工人提高工资的要求,招致后者的不满。同时,面临严重的财政压力,又提高对工薪阶层的税收。诸如此类矛盾的政策,产生了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 巴列维国王虽然在瑞士接受教育,多少侵染了欧洲的民主之风,但好大喜功,专制独裁。恰逢美国卡特政府高举人权的大旗,深感不堪重负。1977年初开始做出政治自由化的姿态,本意是要消解反对派,结果适得其反,恰恰是巴列维半心半意的自由化政策,为反对派提供了开展合法斗争的政治环境。资产阶级自由派率先发难,1977年8月巴列维国王罢免任职长达13年之久的首相胡维达,让反对派尝到了甜头。 或许,巴列维最严重的决策失误在于处理与什叶派欧莱玛的关系。他深知欧莱玛内部的严重分歧,对于温和派和激进派的矛盾也很清楚。他尽力争取温和派欧莱玛,然而最终没有与温和派领袖穆罕默德·卡里姆·沙里亚特马达里达成和解。“有些知悉内情的观察家相信,假如国王能早些与沙里亚特马达里达成真正的和解,君主制的倒台本来是可以避免的”。⑦更糟糕的是,他向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施加压力,骚扰在圣城纳杰夫的霍梅尼。霍梅尼被送到巴黎,获得了更大的自由,可以更好地操纵伊朗国内的反抗斗争。在巴黎,这位神秘的宗教领袖让记者和媒体着迷,极大地提升了他的曝光率和影响力。 霍梅尼是一个敢于斗争,善于根据形势变化调整战略和策略的宗教领袖,并逐渐确立了克里斯马型领袖的地位。霍梅尼本来只是一个宗教学者和教师,虽然攻击过礼萨汗的世俗化改革,但1950年代归于沉寂,甚至没有卷入石油国有化运动。猛烈抨击和坚决反抗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使霍梅尼逐渐成为反对巴列维王朝的核心人物。1970年前后成为号召推翻巴列维王朝君主制、建立伊斯兰政府的革命家。白色革命遭到大多数欧莱玛的抨击,但霍梅尼对抗白色革命之坚决,立场之鲜明以及遭到逮捕和流放,使他声名鹊起,成为反对巴列维王朝的一面大旗。 霍梅尼的崛起反映出伊朗什叶派欧莱玛力量的强大。或者,反过来说,与强大的宗教力量形成反差,国家政权比较脆弱,王权在与教权的斗争中落败。究其根本原因,还是资本主义欠发展下传统宗教势力未受到巨大冲击。具体到伊朗社会,可以说欧莱玛与巴札互为表里。巴札是欧莱玛的经济支柱,欧莱玛则为巴札提供了精神动力和组织资源。1979年革命的最后进程,就是以霍梅尼为首的欧莱玛高举革命大旗,以神学院学生为先锋,以巴札罢市为坚强后援,通过游行示威与当局进行直接的政治对抗。在资产阶级自由派与欧莱玛结成联盟,工人阶级和城市贫民加入游行示威的队伍后,巴列维国王的垮台也就指日可待了。然而,1970年代末巴列维王朝瓦解,伊朗失去社会稳定的社会动力,其深层原因只能从此前的急剧社会变革中去找寻。 二、伊朗社会变革的不平衡与社会稳定问题 20世纪的伊朗,发生了极为深刻的社会变革。从政治上看,出现了民主与专制的博弈和反复较量。1905-1911年立宪运动开启了伊朗从封建专制王朝逐渐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过渡的长期、艰难探索进程。礼萨汗原本有意仿效土耳其,建立共和国,遭到伊朗社会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对,乃重建专制王朝。 专制集权的强势领袖礼萨汗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他维新图强,发展近代机器工业,建设铁路、港口等基础设施,启动伊朗的工业化进程,推进伊朗社会变革,基础设施建设突飞猛进。1925年伊朗铁路仅250公里,1938年为1700公里,1950年达3180公里。⑧1938年,途经德黑兰、联结里海与波斯湾的长达1400公里的跨伊朗铁路,在没有外国贷款的支持下建成通车。这是礼萨汗时期伊朗基础设施建设的标志性项目。礼萨汗还竭力维护伊朗经济主权,收回关税自主权和货币发行权,以关税保护和适当的货币金融政策,发展近代机器工业。1925年伊朗只有不到20家工厂,其中5家工厂的工人超过50人。1941年工厂数量超过300家,其中28家工厂的工人超过500人。到1941年投资约2.6亿美元,其中1/3由国家投资,一半以上来自私人资本。纺织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得到空前发展。⑨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礼萨汗虽然成功地推动伊朗社会现代化和社会变革,并亲手缔造一支强大的军队,但是主要由于他错误地估计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形势,1941年8月苏联军队和英国军队从南北两个方向入侵伊朗,他被迫退位,把政权交给羽翼未丰的王储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即巴列维国王)。这种政治突变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概而言之,伊朗从强势君主高压下的政治稳定转入多种政治势力,包括苏、英、美势力激烈角逐与争夺的政治动荡时期。从1941年9月到1953年“八·一九”政变,伊朗似乎回到了立宪运动期间的议会民主,但是政治动荡影响到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八·一九”政变后,在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下,巴列维国王逐渐恢复专制权力。 在二战后亚非拉国家普遍推进发展的潮流中,巴列维国王依靠美国的支持和愈来愈多的石油收入,继承其父王的衣钵,着力推进伊朗的工业化,进而带动城市化,伊朗社会变革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巴列维国王的政治目标,当然是利用有利的国内外形势,尽快实现伊朗经济现代化,使伊朗发展成为海湾第一强国乃至世界工业强国,恢复昔日波斯帝国的辉煌。从主观上看,意在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巩固巴列维王朝的经济和政治基础。 “白色革命”的主要政治目的,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废除农村封建生产关系,加快农业和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从而避免发生共产党与左派领导的“红色革命”和欧莱玛领导的“黑色革命”。“白色革命”的核心是土地改革,还包括森林国有化,向公众出售国有企业,工人分享利润计划,授予妇女选举权和建立扫盲队。后来,巴列维国王将其扩大化,把政府的一些重要政策亦列入“白色革命”,从最初的6项原则增加到19项。⑩ 如果说礼萨汗通过现代主权国家的构建,尤其是强迫游牧部落民定居,从而极大地改变了伊朗社会的面貌,那么,巴列维国王的“白色革命”和发展计划,则是促使伊朗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城市与工商业社会转变的强劲动力。1963-1971年分三个阶段实施的土地改革,产生了几个重要效果。第一,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村的地权结构和统治方式。在土地改革前夕的1962年,封建生产关系在伊朗农业中未受触动。居住在城市的占伊朗人口1%的在外地主,拥有全国55%以上的耕地,控制超过65%的乡村人口。(11)这些在外地主把持着农村统治权,占据议会的多数席位并在历届首相中占据绝大多数。因此,巴列维土改的主观目的,是打破大地主对耕地的高度集中的占有,极大地削弱大地主在农村的统治地位,建立起国家对农村的统治。经过三轮不彻底的土地改革,到1971年9月官方宣布土改结束时,拥有租佃权的1 766 625户农民,即92%的拥有租佃权的农民,获得了其所耕种的土地的合法权利。如果以一家平均5口人计算,那么,受益于土改的人口约960万人。(12)占农村人口1/3的没有租佃权的农民,完全被排除于出在土改之外。换言之,介于伊朗总人口的1/3~1/4的人多少受益于土改,但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农村人口不平等的经济地位。第二,改变了农村的生产方式,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发展和农业与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土改鼓励地主与佃农合资组建农业企业,鼓励和推广农业的市场化经营,政府出资并吸收国外资金和国内资金,组建机械化、资本密集型的资本主义农业企业。 经济发展计划则着眼于城市和工业发展,极大地推动了城市社会变革。由于政治动荡和石油国有化危机造成严重的经济困难,第一个七年发展计划(1949-1955年)基本流产。在美国的援助和巴列维权力巩固的形势下,第二个七年发展计划(1955-1962年)基本成功。1963年、1968年和1973年连续制订和实施三个五年发展计划,使六七十年代成为伊朗工业化的黄金时期,以至于有学者称之为“伊朗历史上的工业革命时期”。1963-1977伊朗工业的年均增长率从5%上升到20%,增速相当于发展中国家平均增速的2倍。制造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1%上升到17%。雇佣工人10-49人的小工厂,从1502家增加到7000家以上,雇用工人50-500人的中型企业从295家增加到830家,雇用工人500人以上的大型企业从105家增加到159家。(13) 一方面,土地改革并不彻底和成功。半数农村家庭没有受益于土改,因为他们不是分成制农民。分到土地的绝大多数农村家庭,土地贫瘠,面积太小(7公顷土地被认为是维持一个家庭生计的最小面积)。这部分农民并未如巴列维国王所愿,转变成政权的支持力量,而是在后来的革命中保持沉默。另一方面,由于土改不成功,“到1971年绝大多数村民的经济地位并不好于土改计划实施之前”。240万农民占地不到10公顷,另有70万到140万极为贫困的无地农民。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另一个农村集团,是农村手工业者,如理发师、木匠和铁匠等。农村的贫困问题极为严重:占地3到10公顷的农民,人均年收入仅131美元。占地0到3公顷的农民,人均年收入只有70美元。(14) 农村的贫困、城乡差距急剧扩大与城市工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有力地推动了城市化进程。1956年伊朗城市化率仅31.4%,1966年为37.3%,1976年再提高10个百分点,达到47.3%。1986年增加到53.3%,1996年为60.8%,2006年为68.5%。(15)根据伊朗中央银行发布的数据测算,2010/2011年城市化率突破70%的大关,达到71.8%。(16) 从表面上看,城市化的推进是积极的社会变革。但是,伊朗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快速城市化,与许多亚非拉国家的“过度城市化”相似,是一种畸形的城市化,城市化超越了工业化水平。农村贫民受到城市高收入与各种机会的吸引,大规模移民城市。而城市工业的发展,远不能吸纳这些新移民,他们大多只能从事不稳定、收入很低的服务业工作。因此,他们只是从分散的农村贫民转变为集中的城市边缘阶层,即城市贫民。一旦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成为欧莱玛开展动员的对象。 从统计数据看,六七十年代伊朗的工业化是很成功的。1963-1978年工业年增长率很高,产业结构迅速升级。以时价计算,农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从1962/63年的27.9%,下降到1972/73年的16.9%和1977/78年的9.3%。同期工业和采矿业的比率分别为15.8%、20.8%和22.5%,石油业的比率分别为18.6%、22.2%和31.8%,服务业的比率分别为37.7%、40.1%和36.4%。劳动力的行业分布充分说明了伊朗经济结构的优化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农业、工业和服务业吸纳劳动力的比率,1956年分别为56.3%、20.1%和23.6%,1966年分别为47.5%、26.5%和26.0%,1976年分别为34.0%、35.4%和30.6%。投资取向反映了这个时期社会的急剧变革。投资从购置土地向商业、工业和服务业转移,资产阶级开始壮大。(17) 尽管如此,伊朗社会变革存在极其严重的失衡问题。首先,城乡差距拉大和城市与农村发展严重失衡。从表面上看,伊朗产业结构升级,资本主义蓬勃发展,但实际情况令人堪忧。1977/78年农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3%,但是近34%的劳动力在农业部门就业,说明农业生产率和农业部门就业人员的收入都很低。这反过来说明土地改革的失败和巴列维国王的发展政策忽视农村和农业。其次,石油业的畸形发展,既为伊朗推进工业化提供了充裕的资金,又加深了伊朗经济的对外依附性。石油价格的急剧上升,尤其是1973年石油危机后油价猛涨,造成多方面的严重后果,主要是刺激了人们对生活水平不切实际的期望值和发展梦想。巴列维国王对伊朗跨越式地进入世界工业强国的梦想,就是基于石油收入不断地几何级数的增长,而世界市场上的油价上下波动,伊朗经济极易受世界市场波动的冲击。最终,经济扩张计划超出了国力,1975年后经济过热的负面效果越来越严重,民怨沸腾。这是巴列维王朝垮台的最直接的经济因素。 伊朗资本主义是在传统的封建土壤上缓慢而畸形地发展的。礼萨汗的改革与维新图强运动,在农村加强了大地主的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在城市则在客观上推动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巴列维国王在农村实行土地改革,主观上是为了打击大地主阶级,发展小农经济,促进农村和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与此同时,依托强大的军队和官僚机构,以巨额石油收入为后盾,大力推进城市工业化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国家在宏观规划和资源分配上均发挥主导作用。国家在工业投资中占的比率,从六十年代中期的40%上升到1970年代的60%。私人资本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官僚资产阶级占主导地位,起源于大地主、城市贵族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工业家的民族资产阶级比较软弱。财富高度集中,在1972年的364家最大的企业中,56个家族拥有其中177家的股份。(18)最大的地主和资本家,就是巴列维王室。 专制君主自上而下地推进社会变革,实际上走的是国家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意味着私有部门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受到国有资本和外国资本的严重挤压。私有部门发展受到严重制约,民族资产阶级受到官僚资产阶级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双重压制。这产生了另外一个严重后果,即传统商业和手工业——巴札仍然比较强大。巴札继续控制国家一半手工业生产、2/3的零售业和3/4的批发业。(19)传统城市社会的主要经济力量巴札和传统社会的主要精神力量欧莱玛相结合,对巴列维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伊朗社会变革的严重不平衡,是造成巴列维王朝倾覆的根本原因。这种不平衡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巴列维国王在政治上的专制,政治发展严重滞后于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国王对于继位初期自己政治上的无力与政治动荡心有余悸,因此竭力发展军、警、特等强力机关,对于政治改革尤其是通过民主政治释放政治能量,极为保守。相反,1975年建立御用的复兴党,试图通过复兴党进一步集中权力。复兴党加紧向现代中间阶层、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巴札(传统中间阶层)渗透。这种加强控制的渗透措施侵犯了民族资产阶级和巴札,使二者同当权者离心离德,甚至把后者推到了欧莱玛一面。假如巴列维国王及时实行自上而下的有序的政治改革,把民族资产阶级有效地吸纳到政权体系内,逐渐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过渡,那么,以所谓自由派为政治代表的资产阶级就不会也不必借助于欧莱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和经济利益。事实上,如前所述,只是在1979年革命成功前两个月,资产阶级才最终与欧莱玛结成推翻巴列维政权的政治联盟。 巴列维国王政治上的专制独裁,不能仅仅归结于他个人的专制倾向或独裁欲望。相反,恰恰是他从大地主向大资产阶级的转变很不彻底,在他身上遗留了太多的旧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痕迹,不能自上而下地主动引领伊朗向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转型。因此,他就不能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团结资产阶级自由派。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力量不够强大,不能迫使巴列维国王在政治上妥协,进而迈入民主政治轨道。相反,软弱的资产阶级饮鸩止渴,服膺于霍梅尼,伊朗社会便从急剧的社会变革转变为严重的社会动荡,陷入严重的政治动乱之中。 总之,严重不平衡的社会变革葬送了伊朗社会稳定。 ①有关巴列维王朝突然崩溃的相关专著十分丰富。许多学者强调经济与政治因素的重要性,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阿伯拉哈米安等人的政治与经济二轮逆转论,即巴列维国王大力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却又坚持君主集权统治。塞缪尔·亨廷顿则指出,致力于现代化的君主制国家必然陷入“根本性困境”。伊朗的官方机构——伊朗伊斯兰革命文献整理与研究中心,则主要从宗教因素和霍梅尼的伟大领导两个角度,找寻革命成功的根源。国内学术界也高度重视巴列维王朝经济与政治发展的严重失衡问题,有学者认为巴列维的悲剧就在于把经济改革与政治民主割裂开来,对立起来,这就注定了“白色革命”必然失败的命运。参见张振国主编:《未成功的现代化——关于巴列维的“白色革命”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4页;哈全安认为,巴列维时期伊朗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独裁专制与民主政治的矛盾,参见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上册,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70页;李春放考察了巴列维国王陷入的“根本性困境”,极大地增强了“多因说”的说服力。参见王彤主编:《当代中东政治制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24-236页。 ②[美]塞缪尔·P.亨廷顿著,王冠华等译:《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61、154页。 ③Farhad Kazemi,Poverty and Revolution in Iran,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0,p.6. ④巴札既指传统商业,又指传统商人。 ⑤Mohsen M.Milani,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From Monarchy to Islamic Republic,the second edtion,San Francisco:Westview Press,1994,p.48. ⑥彭树智主编,王新中、冀开运著:《中东国家通史·伊朗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23-324页。 ⑦[美]埃尔顿·丹尼尔著,李铁匠译:《伊朗史》,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中文版,第174页。 ⑧Charles Issawi(ed.),The Economic History of Iran,1800-1914,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1,pp.375,379,381. ⑨John Foran,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Oxford:Westview Press,1993,p.235. ⑩参见穆罕默德·礼萨·沙·巴列维:《白色革命》。[法]热拉德·德·维利埃等著,张许苹、潘庆舲译的《巴列维传》(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收录了巴列维的《白色革命》全文。 (11)M.Karshenas,Oil,State and Industrialization in Iran,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141. (12)Mohsen M.Milani,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from Monarchy to Islamic Republic,p.47. (13)John Foran,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p.326-327; E.Abrahamian,Iran:Between the Two Revolution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p.430.这两本书提供的数据略有出入。 (14)John Foran,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p.319-322. (15)Ali Gheissari(ed.),Contemporary Iran:Economy,Society and Poli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80. (16)根据伊朗中央银行《2010/11年度报告》,2010/11年城市人口为53 638 000人,农村人口为21 096 000人,合计74 733 000[Central Bank of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Annual report(1389 2010/11,p.60]。 (17)Mohsen M.Milani,The Making of Iran's Islamic Revolution,from Monarchy to Islamic Republic,p.60; P.Sharan,Government and Politics of Iran,New Delhi:Metropolotan Book Co.(Pvt.)Ltd.,1983,p.10. (18)John Foran,Fragile Resistance: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Iran from 1500 to the Revolution,p.328. (19)Ervand Abrahamian,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Princeton,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2,p.433.标签:巴列维王朝论文; 政治论文; 霍梅尼论文;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论文; 土地改革运动论文; 伊朗经济论文; 伊朗政治论文; 石油美元论文; 伊朗伊斯兰革命论文; 石油资源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伊朗革命论文; 伊朗石油论文; 国家经济论文; 石油投资论文; 工人运动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