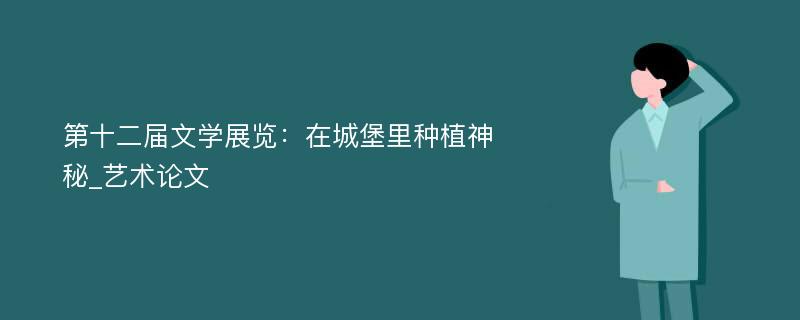
第12届文献展:在卡塞尔种植神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献论文,神秘论文,卡塞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7年3月,卡塞尔是蛰伏在德国边境的一个小城,也是格林兄弟的故乡。这儿几乎没有任何迹象表明,6月16日这里将举行五年一次的世界上最大的当代艺术展:文献展。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是文献展的象征和精神中枢,在它的前方是一览无余的弗里德里希广场,展览期间这里将人涌如潮。桔园宫外面是另一个历史上有名的中心,数以百计的金属环栓结在一起,它们将成为水晶宫——这是卡塞尔对1851年英国水晶宫的一种回应。法国人安妮·拉科顿和琼·菲利普·瓦萨尔共同设计了这座临时园艺建筑,但是,目前接近这个1万平方米的透明的金属展示空间的,仅仅是清晨的慢跑者们。然而,在所有看似平静的城市表象之下,倒计时却已经真正开始了。离展览的开幕式只剩不到99天了。在这个夏天,这里将迎来65万参观者。
“我已经准备好了”,罗格·M·比格尔自信地说。他一边指着悬挂中的纸板模型,一边向我概述第12届文献展展示空间的特征:展览将在保留着18世纪风貌的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19世纪创立的新画廊和20世纪建立的文献展厅中展出。提到目前正在搭建的棚架结构,比格尔提醒到,文献展最初是卡塞尔花卉展的一个分支。“尽管将会有数以百计的艺术家,我们不仅知道他们是谁,而且知道将他们的作品(应该是450件)放在什么位置。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改变任何事,或者说我们已经把全部的基金存进了银行。策划文献展有点类似于制作一部电影:你可以把文献展当成是一部电影大片,但是当我开始做时,就不得不一切从零开始,包括组建我自己的团队。尽管这意味着你能够完全按照你自己的愿望去做,但是某种程度上说,如果你能够管理并调度40个深谙自己职责的工人,那么这种自由度自然就会变少了。”
组织工会的方法
2003年底,比格尔在不记名票选中最终胜出。他是一名视觉艺术理论教师,1962年生于柏林,现居住在维也纳,他曾是澳大利亚当代艺术中心奠基人约翰尼斯·加赫南格的学生,也曾给赫尔曼·尼奇做过秘书。比格尔还是第一个获得梅尼基金会颁发的策划奖的人,此奖是梅尼基金会为纪念了策展人沃尔特·霍普斯所设立的。世纪之交以来,比格尔和他的同伴——艺术史学者和展览组织者鲁思·诺雅克共同组织策划了多个展览。2000年,他们得到了维也纳杰纳勒利基金会的赞助,策划了第一个展览《我们不理解的东西》,该展览通过展示一些以实践政治为核心的艺术家的作品,如巴黎的亚历亨德亚·里拉、德国的电影制作人哈伦·法罗克以及1970年代的美国的女权主义者埃莉诺·安廷的作品,荒谬地呈现出艺术家对艺术自主性的捍卫。作品对旁观者产生的影响暗示了这种自主的要求,仿佛它们是从远方制造日常的社会经济学和政治条件的一种方法——可选择的却是“占优势的想象”。如果今天还能看到当年的那个展览将是大有益处的,因为比格尔将同样的理念和原则用在了第12届卡塞尔文献展中。
然而,比格尔和诺雅克最具挑战性的展览是2003年到2005年间在吕讷堡、巴塞罗那、鹿特丹和维也纳四地展出的名为“政府”的展览,展览展示了一些色情的作品,例如,上文提到参加过2000年那个展览的两位艺术家的作品,以及马哈·巴耶维奇(巴黎),伊内斯·杜雅克(维也纳),德克·施密特(柏林),艾伦·塞库拉(洛杉矶)的作品,玛雅·德瑞恩和吉恩-卢克·戈达德的电影。展览借用了米歇尔·福柯政府至上(权力机制对人民和大众的控制和规诫)的观念,在艺术领域中检验了“工会组织”这一形式。这一观念对于第12届文献展是至关重要的。比尔格和诺雅克要让大家知道,他们将从“基础”着手,在杜阿拉或里加,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以什么样的方法,“远离传统的商队路线”。比格尔将考察几个大洲主要城市和文献展杂志编撰的任务同时委托给了维也纳人乔治·斯科汉默尔。他的任务是从世界各地精选一百本期刊,以此来保证文献展在理论和批评上的学术性,并坚决远离“艺术家的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原型”。于是,在一种民主的模式,或者说,至少比其他模式更民主的知性模式的庇护下,一个有着双重影响的系统被建立起来。
建构,而非表征
同时,比格尔夫妇通过控制展览信息的发布量来尽可能的减小本届文献展的“官方活动”所面临的媒体压力。譬如,一个玩笑揭示了他们的艺术家列表中的第一个艺术家加泰罗尼亚人费伦·阿德瑞和最后一个艺术家波兰人阿图尔·兹米耶斯基的名字。后者创作了影像作品《格卢兹·巴赫》,视频中的音轨是一首由唱师班演唱的晦涩的加泰罗尼亚语歌曲——而这很可能促成新闻媒体对这件作品进行额外的吹嘘。而这个玩笑的作者在卡塞尔通过电话与《艺术新闻》的职员不屈不挠的争论,直至我到了卡塞尔的时候,文献展的工作人员才同意公布一个7名艺术家的名单。比格尔和诺雅克之间展开了一场即兴的口头比赛,诺雅克在听众席上向在站在讲坛上的比格尔发表了长篇演说。而这种竞赛促使他们把一小部分组织好的幻灯片展示成图像。第一张幻灯片展示了1943年盟军大轰炸后的卡塞尔的景象,图中的弗里德里希阿鲁门博物馆始建于启蒙主义时期,是用当时贩卖雇佣兵到美国打内战得来的资金修建的,这张图片揭示了现代化和暴力行为之间的辩证关系。接着展示了1955年首届文献展悬挂的标牌,黑色塑料展墙掩饰了衰败,同时也让观看者回想起了文献展最原初的目标:重建分崩离析、满目疮痍的公共场所,并将其整合成文化博览会的一部分。接着,展示的是一组尼日尔管道爆炸的图片,以及中国的援助,上海的一处建筑工地和“穷人的卡塞尔”,换句话说,这组图片打破了现代性的承诺。接下来展示的一个挽歌式的户外教学会议的情景,时间是2006年,地点是泰戈尔的故乡圣廷尼科坦,整个场景仿佛是“自然背景中的包豪斯”。在对比信息和教育时,比格尔的结论是“教育并不仅仅是另一种消费品,它带有一种使孩子从父母或保护人的监护中解脱出来的雄心。这正是博览会与迪斯尼乐园所不同的地方,也是大学讨论会与迪斯科舞厅和威登商店的相异之处”。
自2005年起这些幻灯片所承载的问题便渗入比格尔夫妇对第12届文献展的知识构架中,这些幻灯也是展示本届文献展三个主旨的平台:1.现代性是我们的古迹吗?2.什么是赤裸的生命?换言之,借用(意大利)哲学家乔治奥·阿甘本的话,什么是生命的绝对弱点?3.要做什么?根据列宁的话改写就是,“换句话说,对公众教育的关心是时下德国关注和讨论的焦点,教育,这个意味着培养强烈的责任感的术语,成为所有策展人的口头禅。”我们想回到文献展早期的起源和立场,恢复它的质朴。但这也并不妨害我们探求宏大的问题,如“今天,艺术是什么?”和“今天,我们是什么?”最终,当你开始着手策划一个展览的时候,你将会努力地去寻找一些答案。
艺术方案的负责人赖克·弗兰克认为“这些只是乐旨(乐曲中简短而重要的短句)而非主旋律,没有公认的艺术家和情境他们是不会发生的。”事实上,这三个问题正是文献展杂志的正文中富有表现力和引导性的要点,根据这三个问题,杂志被分成了三卷。在鲁思·诺雅克的部分中,她重申了展览本身的可塑性,“我们的媒介就是展览,作品是建构而不是描绘,所以这是一个生产的问题。作为策展人,我们统筹展览的格局就像对待一件产品,我们自始至终要安排好与展览格局相关的规划,从画册到新闻发布会,因为它们也是生产过程中的一部分。”
社会雕塑
1972年哈拉尔德·泽曼策划的第5届文献展与艺术家们的表演密不可分。1997年凯瑟琳·戴维的第10届文献展则直面现代性的历史评价,在充满争论的“一百天”中,她准许大量非西方立场的纳税人参与到其中,表达一些标新立异的观念。那么,接下来会是什么呢?罗格·比格尔的第一个行动就是通过与卡塞尔的公民合作,远离美术馆的传统,远离艺术经营者主宰艺术空间的传统。在展览筹委会中,他的“策展方法”是与工会领袖、教师和社会劳工共同合作。这种当地的联合是如何转化为艺术家们可操作的方法的呢?这种工作过程是否比文献展本身更长期呢? “这是一个责任问题。我们需要建立艺术家和给定空间之间的联系。我们让那些想打听委员会专家意见的艺术家们和委员会成员接触。于是,一个来自蒂森钢厂的工会成员被纳入巴西艺术家里卡多·巴斯包姆于1999年启动的艺术方案中——蒂森钢厂的武器制造曾导致1943年卡塞尔的轰炸。协作的过程是从工会成员的劳动开始的,而生产的过程是这些初学者根本无需弄明白的。这是一种十分有趣的情景。”最后,20来个一模一样的涂有蓝白彩釉钢制钝形物被送往卡塞尔各处,以及拉丁美洲、卢布尔雅那、达喀尔,这些钝形物在接纳了它们的“寄宿家庭”中,被怎么看着舒服便怎么使用了。而这一占有过程正是艺术家想要阐释的经验。手手相传之后,它们被重新归聚到一块儿,作为面向公众的第一次亮相,它们被放在了的“水晶宫”的入口处。这就是2007年罗格·M·比格尔和鲁思·诺雅克对社会雕塑的初始构想。
新的社会形态
比格尔夫妇对艺术方案的初始状态和它的最终的质量十分关注。和比格尔长期合作的艺术伙伴彼得·弗里德尔(他在凯瑟琳·戴维的第十届文展中也占有显著的位置)正在准备他的新作品《动物园故事》,对此,赖克·弗兰克强调说“像往常一样,他通过简单的行为揭示了复杂的地理政治学的发展形势”。《动物园故事》对卡莉拉动物园中的一处涂鸦所作的“个案研究”。当卡莉拉这个黎巴嫩边界的小镇被炸时,动物园中的动物都被电死。动物园中用于饲养动物的水库将被改造成为自然历史博物馆。而动物园中的涂鸦将送往卡塞尔。比格尔的另一位朋友,杰沃德·罗肯绍伯也将在文献展中重量级登场。工作组正在确定罗肯绍伯作品中的全部表演者,尽管他拒绝任何一种形式的回顾——实际上,在维也纳现代艺术博物馆,他的作品既不吸引人也缺乏趣味,艺术家本人最近也证明了他那个命题是如此的不恰当。伊内斯·杜雅克将筹划一个“生物寄生种植园”的作品,并将文献展搭建的大棚架当作暖房。他试图探索植物的环境适应性和收获作为全球化表现形式之一的特殊的本土知识,艺术家制造出一些种子,这些种子都有着反讽的外包装,并且包装上标明了它们是和展览内容有关的人造物。
罗格·比格尔散布了一个14世纪的波斯图像,这个图像“吸收了中国传统绘画的基本原理”。对他而言,这是一个打破欧洲中心主义的条条框框的始料不及的转换,并且在不同的表达方式之间也能产生些许链接的范例。这届文献展中有三分之一数量的作品并不是那么的当代,这也是展览画册不按照字母顺序编排,而是按照年代顺序排列的主要原因。“答案很简单”,比格尔说,“当代意味着相关联性,但是今天柏林,巴黎或者纽约正在做的,还不如一幅14世纪的匿名绘画体现出的关联性那样多,这幅绘画能激起我们对新的社会形态的想象,并且这种形态能够超越受限于市场的艺术家的个体身份”,又避免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的前卫阶级对收藏的垄断。在文献展上,萨丹·阿菲弗和约翰娜·比林的作品构成了比格尔所说的展览中的“抒情的声音”。
比格尔从“形式的世界是有限的”这一观点念出,提出了他的展览方法,一种摒弃了历史限定的普遍主义样式和笼统的后现代相对主义的方法。“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知道一切将如何发展,因此你不得不去旅行,去听、去学习。不久你意识到全球化不只是发生在昨天,跨区域联系的观念是反复出现的,例如,上世纪80年代开始,约瑟夫·库苏斯成了最有影响力的人物。置换一直是艺术家的工作方式,从具体的材料上看,置换是非常具体而实际的方式,它构成了本届文献展的原动力。我们称它为形态的迁移。”这种形态的迁移不是在边缘和中心之间发生的,而是在特定的情境中发生的。巴西艺术家路易斯·萨奇罗托的混凝土艺术与米拉·申德尔(1919-1988,生于瑞士的巴西人)的混合的透明物和拍摄了非洲人发型的照片连接在一起。尼日利亚的建筑和城市设计师戴维·阿拉迪昴,将拉各斯和巴西之间残留的殖民主义的线索编织在一起。这些变异在女艺术家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并不仅仅是巧合,这些女艺术家声称形式本身不同于形式主义,并且走在探求不同之路最前沿。得到公认的艺术家如,阿格尼丝,马丁、特丽莎·布朗、玛丽·凯利、依芳·芮恩娜,玛莎·罗斯勒以及佐伊·伦纳德,她们的名字将与不出名的艺术家的名字写在一起,如,李·洛扎诺,鲁思·沃尔默和玛丽亚·巴图斯佐娃,或者更年轻的艺术家,如,刚果艺术家比尔·库兰尼。有人会质疑涉及这么多人,难道不觉得有一点儿矫揉造作吗?一点儿也不,比格尔回答到,“比方说,纳斯瑞·默哈穆德在印度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作为印度独立之后印度艺术发展史中的关键人物,她已经培养了至少两代人。对于巴图斯佐娃来说也是一样。试图展示这些是不明智的,因为她们的贡献是卓越而超群的。因此,我们只能让现代性远离西方的范例。”
译自法国《艺术快报》杂志第33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