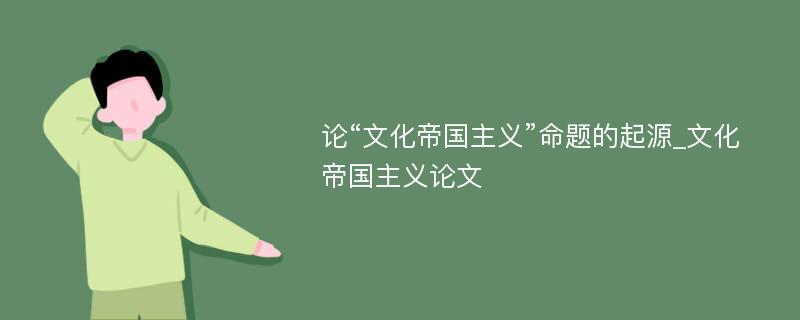
“文化帝国主义”命题源流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源流论文,帝国主义论文,命题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的国际学术界,“文化帝国主义”曾经是一个非常流行的术语,围绕着这一术语形成了解释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对发展中国家“文化渗透”活动的话语。这一命题解释美国对外文化扩张的准确性尽管受到很多学者的质疑,但在战后国际学术史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即使至今依然在国际学术界占据着一席之地。“文化帝国主义”正式在学术界提出大概有半个世纪的历史了,不同研究领域的学者对之有着不同的解释,二战后主要与美国大众文化在发展中国家传播引起“美国化”这一现象密切联系在一起,尤其是美国媒介对世界各地大众生活的影响甚至控制。本文通过对“文化帝国主义”这一命题的渊源与内容考证,试图大致勾勒出其在国际学术界发展的脉络和基本内容。
帝国主义概念中的“文化征服”因素
“帝国主义”概念是研究西方殖民大国向外扩张的学者非常熟悉的一个概念,当然欧美学者和发展中国家或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在对这一概念内涵的界定上存在着明显的甚至本质上的区别。长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在涉及到这一术语所体现的基本内容时,常常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联系在一起。不过,也有学者根据二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列宁概括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提出了质疑。根据《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的界定,帝国主义“概念主要指试图确立或保持对附属政治社会的正式主权,但是也常常等同于一个政治共同体对另一个政治共同体施加政治控制或影响的任何形式”。按照这种界定,在人类历史上,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征服并使之臣服纳贡的帝国主义形式早就存在。如古代东方的亚述帝国、波斯帝国,西方的罗马帝国,以及后来的拜占庭帝国;此外在中东和北非,阿拉伯人和土耳其人都曾建立过较大的帝国。①据有关专家考证,帝国主义正式见诸于文字是在19世纪的法兰西,指拿破仑三世的政治盟友和穿越英吉利海峡之前的第二帝国,在关于英帝国未来的辩论中有人使用了这一术语。1902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霍布森出版了《帝国主义研究》一书,把帝国主义解释为资本主义经济过剩的产物,认为帝国主义是一个国家为了本国的政治和经济等目的而对他国制度与生活的控制。自此以后,“帝国主义”这一词才发展为一个拥有具体含义的概念,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以及国际关系学等研究领域中广泛使用。
在帝国主义概念中,西方列强对西方之外国家的经济剥削或掠夺是中心所在,而实现对这些被征服对象的政治控制也主要是为经济扩张服务的。其实自古至今,那些在历史上炫耀一时的帝国,尽管是靠着武力攻城略地,但要实现对被征服地区的长治久安,显然不能完全靠着军事力量,而是要依赖宗主国的文化对被征服土地上的臣民进行心灵上的“洗礼”,使他们最终对征服者文化的认同。用一位专家的话来说,帝国主义“不只是通过镇压维持其统治,还要通过出口和制度化欧洲生活方式、组织结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语言和文化产品”使其统治具有坚固的基础。这样,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一个多方面的文化进程,为准备接受和采纳很迟到来的媒介文化产品奠定基础”。②非洲几内亚民族独立运动的先驱之一,阿米卡尔·卡布拉尔以自己的亲身体验,谈到了帝国主义统治与文化征服之间的密切关系,他认为实行帝国主义统治“需要文化压制,试图直接或间接摧毁被统治人民的文化的实质成分”。③因此,“文化征服”在帝国主义概念中显然具有很重要的地位。法国学者弗朗茨·法农声称,“分解文化的计划”是帝国主义控制殖民地的根本。
西方殖民主义不会仅仅满足于政治和经济的统治,而且会试图把当地人脑子里所贮存的东西清洗一空,使其语言、饮食习惯以及性行为受到挑战,改变了他们的坐卧姿势、嬉笑言谈和享受生活的方式,并且转变了他们的历史发展方向以及他们自己的人格。因此,在法农看来,当地人必须拒绝欧洲的价值观,抵制它们,把它们彻底抛弃。④法农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严厉抨击了西方殖民主义,并号召受到奴役的当地人完全拒绝接受西方的价值观尽管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却反映出西方殖民主义者通过转变当地文化来达到永久控制殖民地的目的。马克思在谈到英国对印度征服的后果时指出:“英国在印度要完成双重的使命:一个是破坏性的使命,即消灭旧的亚洲式的社会;另一个是建设性的使命,即在亚洲为西方式的社会奠定物质基础。”⑤马克思在这段话中尽管未提“文化”二字,但无论是履行“破坏性的使命”,还是完成“建设性的使命”,很大程度上是要靠着宗主国文化对当地文化的彻底征服。意大利共产党的领导人之一葛兰西提出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便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在革命实践中对这一问题在理论上进行的深入思考。在葛兰西看来,占据统治地位的集团不是通过诸如使用高压的强制手段来使被统治阶层俯首帖耳,而是通过文化制度以及与精英阶层其他成员的结盟保持住权力地位以及使共同阶层的利益不受到侵害,文化制度主要包括学校、政党和媒介等,通过对文化制度的影响和控制比通过使用强制性力量所产生的统治效果更好。也就是说,居于权力地位的统治集团通过潜移默化地灌输维护其统治地位的文化价值观,使被统治集团通过接受这些观念而自愿地接受统治集团的发号施令。葛兰西进而认为,霸权是一种权力的结果。也就是说,不同的社会集团在世界如何运行、什么为公平合理、经济如何被组织以及如何对付犯罪等问题上有着各自的看法。
一般而言,居于权力中心的集团的看法将占据优势,原因在于掌权者往往利用手中的权力加强支持他们维持统治的思想,他们也由此实现了针对被统治者的“文化霸权”。因此,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在工业化的欧洲国家发生主要是因为这些国家形成的霸权文化成功地“消除”了工人的意识形态、自我理解和组织结构。换句话说,统治阶层的文化观念被受到“奴役”的广大工人大众所吸收。这样,在“发达”的工业社会,诸如义务教育、大众媒介和流行文化等霸权文化的革新把一种“虚假的意识”灌输给了工人阶级。在这样一种环境中,工人们不再致力于将真正服务于他们集体需要的一场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而是听从民族主义领袖的花言巧辩,一味地追求消费机会和中产阶级的地位,采纳通过竞争实现成功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接受资产阶级宗教领袖的引导。用一些研究文化霸权的学者的话来说,资产阶级不仅控制了积累财富的大众文化的生产,而且也通过左右工人阶级的信仰体系巩固了其统治。因此,文化霸权是工人阶级不起而反抗自己受压迫状况的原因之一。
革命的成功首先在于瓦解为统治阶层服务的文化价值观,只有这样,革命才能获得道义性和合法性,也才能够以较小的社会成本完成本来需要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才能实现的一场政治革命。葛兰西的这一理论实际上是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革命观点的修正,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美国媒介学家马克·戈特德纳谈到葛兰西对美国学界的影响时指出,霸权理论是美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关于大众文化的主要观点。这种理论实际上综合了媒介研究的各个方面,把大众文化看作是统治阶级的一个基本工具,被用来通过在工人阶级脑海中产生意识形态的“虚假意识”或“矛盾意识”来维护其政治和社会控制。⑥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并未涉及到一个在文化上居于优势的大国利用其手中掌握的各种文化资源实现对弱小国家的控制,但已经具有了这方面的含义,对20世纪60年代以后兴起的“文化帝国主义”话语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在“帝国主义”术语前面加上“文化”这个限定词,尽管具有了特定的含义,但无论从理论上讲,还是从实践上看,帝国主义概念本身显然已经包含着强烈的“文化征服”色彩。美国文化批评家萨义德1993年出版的《文化与帝国主义》一书,把文化与帝国主义的行为直接联系起来,揭示了在帝国扩张的过程中,文化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这本书出版后在学界引起很大反响,单从书名上就可看出,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英国威尔斯大学教授马丁·巴克在其著述中指出:“到底‘文化帝国主义’指的是什么?几乎没有任何精确的定义。它似乎是说,帝国主义控制他国的过程,是文化先行,由帝国主义国家向他国输出支持帝国主义关系的文化形式,然后完成帝国的支配状态。”⑦巴克这里谈到的“文化帝国主义”,指的是一个国家完成对另一个国家支配或控制过程中文化所起的作用,因此它不是与“帝国主义”不同的概念,而是帝国主义概念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讲,帝国主义概念中包含的“文化征服”因素是“文化帝国主义”命题出现的基础。
“文化帝国主义”与西方传教活动
西方国家在非西方世界的传教活动,主要在于教化异教徒皈依上帝,这种活动尽管先于西方大国的殖民征服,但西方传教士大规模地奔赴国外却是在殖民征服之后,这样基督教传教活动显然与西方帝国主义本身的行为有着很大的关系。很多学者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概念中包含着西方传教士在非基督教国家对异教徒的“文化征服”或“文化教化”的活动。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把美国传教使团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认为传教士个人也许从来不向传播基督“福音”的国家行使经济或政治权力,但是,他们的行为反映出美国文化对其他民族的思想和文化有目的的侵犯。⑧美国北伊利诺伊大学历史学教授肯顿·克莱默非常肯定地指出了传教士在美国征服和统治菲律宾过程中起到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他认为美国在菲律宾的传教士“构成了美国殖民人口中的很重要的部分:他们有助于在菲律宾和美国形成对菲律宾文化以及美国驻扎在该群岛的态度;他们偶然也帮助形成政策。他们促进菲律宾人顺从自己的新命运,成为政府的积极支持者,在这两方面都被认为是在履行‘文明的使命’”。⑨克莱默这里显然强调在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统治上传教士通过传播宗主国的价值观念或生活方式而实现对当地人的文化“征服”。
因此,在关于现代基督教传教运动的论著中,“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常见的概念,用来说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通过手持《圣经》的传教士在西方之外转变这些“异教”国家的文化所使用的方式以及带来的结果。加拿大学者瑞安·邓克考察了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在不同学科的使用,通过对新教在中国传播的个案研究,分析了现代世界历史上西方传教运动对非西方国家的影响,他的结论是,传教运动必须被视为在19世纪和20世纪改变西方社会和非西方社会的全球化现代性的一个组成部分,对传教运动进行全球比较的探讨能够有助于阐明现代文化全球化的进程。⑩美国莫海德州立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哈里斯研究了文化帝国主义与19世纪中叶美国新教运动对中国影响的关系。他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解是,作为更好地了解传教史的一个分析概念,“文化帝国主义”仍然证明是非常有学术价值的。不过,他认为迄今为止对这一概念的使用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原因主要有二:一个是学术界对“文化帝国主义”解释不一,缺乏一个广为认可的准确概念。把传教士称为“文化帝国主义分子”主要是想纠正西方学术界过去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观点,即非基督教世界的宗教是“虚假的、骗人的和腐败的体系”,注定要被基督教取而代之。此外,在涉及传教事业和西方帝国主义历史的关系上,这一术语本身究竟包含着什么新的观点,似乎语焉不详。二是许多历史学家反对把传教士描述为“文化帝国主义分子”,因为这一术语暗含着对传教事业的彻底否认,哈里斯对这种看法表示怀疑。在他看来,描述传教士事业的“文化帝国主义”术语显然与西方帝国主义活动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特别强调了“帝国文化”概念,如果以这一概念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那么“文化帝国主义”就会被界定为“是对通过侵略扩张和统治的经历在国外形成的一种文化的积极表述”,这样就有助于对“确定传教士行为的深层文化力量的有意目的和正式政策”做出进一步的分析。更为重要的是,“文化帝国主义”设想传教使团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联系,而又不涉及到“传教士在西方列强的较大行动计划中所起的任何具体功能的作用”。无论传教士在传教过程中是否扮演了“先头军、颠覆者、宣传家和推销商”的角色,传教士可以被认为是文化帝国主义分子,而这个并不取决于传教士的行为直接服务于政治和经济帝国主义的利益。(11)哈里斯对“文化帝国主义”概念的解释,尽管只是一家之言,但传教士所持有的信仰、价值观以及态度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与西方列强在非西方国家或地区的帝国主义行为脱离干系,甚至在文化上起到了为“帝国主义”目的服务的“先驱者”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哈里斯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界定与解释是有很大说服力的。
有些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所带来的结果给予肯定,如美国学者南希·博伊德在对美国青年妇女基督教联合会海外活动的研究中对妇女作为文化帝国主义代言人的作用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她对该联合会是否实际适宜于文化帝国主义范畴提出质疑。在她看来,美国青年妇女基督教联合会是基督的使者,是“美国妇女精神”的传递者,是“全球妇女运动”的先驱。在这一范围内,美国青年妇女基督教联合会的代表改善了印度和中国土著妇女的生活,如试图消除诸如妇女随夫殉葬、童婚和缠脚等陋习。博伊德指出,如果这些妇女因为输出了“妇女应该是领导者和按照自己的方式自由发展等独特的西方观念”而被冠以文化帝国主义者的话,那么“她们很高兴接受这一称号”。(12)不管研究基督教传教使团的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持何不同的看法,这一命题显然是与西方帝国主义者眼中的非西方“落后”地区密切联系在一起,也是对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在文化上试图转换“异教”国家的形象表达。
“文化帝国主义”命题的提出
“文化帝国主义”术语尽管被一些学者用来研究西方传教士对非西方世界异教徒的文化教化,但其在学术界的主要所指并不涉及基督教在非基督教世界传播西方文明的活动,在内涵的界定上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而多是指西方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通过诸如大众媒介等文化产品对发展中国家人们行为的影响。围绕着“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形成的理论观点主要产生于二战之后的西方学术界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与批判,随后也加入了发展中国家一些学者的声音。这些学者的研究尽管有着各自的重点,提出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但在国际学术界形成了一个很重要的学术流派,对研究尤其是美国大众文化在国外的扩张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西方进入激进主义活跃的时代,社会动荡导致学术界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反思,与此同时许多学者对美国的外交活动给予激烈的批评。如美国“新左派”的创始人之一威廉·威廉斯把美国说成是一个“非正式的帝国主义”,他对这一概念的解释是:“当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在一个弱国经济发展中扮演或试图扮演一种单方面的支配角色时,那么力量强大的国家的政策就可以准确公正地被描述为帝国的政策。”(14)威廉斯等人对美国外交活动的激烈批评,在某种意义上是“文化帝国主义”话语出现的先声。20世纪20年代形成的法兰克福学派,本来就对资本主义社会持一种强烈批判的态度,这一在当时已经很有影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在二战后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矛头直接针对西方世界的“领头羊”美国,把美国视为用大众文化扼杀自由、民主和个人主义的大众社会。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赫伯特·马库斯把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理论糅合在一起,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产生的弊端给予全面清算。他在1964年出版的《单面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一书中勾画了一个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人的形象,这个人不能辩证地进行思考,不能对其所处的社会提出质疑,把自己屈从于受技术的控制以及效率、生产力和一致性原则。这本书不仅使马库斯成为“新左派”的英雄,而且为60年代发生在美国和欧洲的学生抗议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法兰克福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还有马克斯·霍克海默尔、特奥多尔·阿多尔诺、莱奥·洛温索尔以及沃尔特·本杰明等。他们这些人以“批判理论”精神对西方文化的反思把许多学者的目光引向对现代美国消费社会及其对外部社会影响的关注。“文化帝国主义”话语便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出现的,反映出一些持激进观点的学者在研究美国媒介文化对其境外社会发展影响的一种批判精神。正如德国学者杰西卡·吉诺—黑希特指出的那样,在20世纪60年代,“一场新极左运动把资本主义看作是描述20世纪许多特性的典型,这些特性包括消费主义、现代性、组织以及社会与个人的冲突”。受这场运动影响的学者们的“成果将留下研究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深深痕迹”。(15)
很多西方学者对“文化帝国主义”命题进行了探讨,其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的观点表明,在文化向外传递过程中,一些掌握更多信息流动途径的文化表现出对另一些文化的征服,文化之间的交流从来不是在平等条件下进行的。事实表明,在历史的演进过程中,西方国家在经济发展上走到了前边,这就决定了它们国家的文化及其价值体系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对亚非拉国家的殖民活动自然导致西方文化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这些被征服的地区。殖民主义话语基于“西方凌驾于其他地区之上”的文化优越,西方关于经济进步和自由民主的观念通常提供了其他文化衡量它们存在意识的标准。这样,“文化帝国主义”可能被认为一直有意识地和无意识地发挥着作用,试图形成被征服地区的人们在文化上对征服者的认同。第二个层面与西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形成有关。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常常把并非必然是相同的西方价值观和资本主义价值观合而为一。在他们看来,在安排、组织和管理尤其是经济上发达的“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之间的文化交流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有着重要的影响。资本主义的兴起为欧美国家经济崛起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这些国家的大资本家在世界范围内寻求新的商业机会以扩大其贸易,赚取更多的利润。在追逐利润过程中,资本家形成了遍布全球的跨国商业,他们拥有的财富和权力在其足迹所至之处得到急剧的扩大。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资产阶级试图按照自己的形象重构这个世界,它不仅关注经济方面,而且关注文化方面。这样,商品/服务的生产和消费越来越不只是由选择来决定,而是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单一的生产商品的方法。第三个层面与美国文化产品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有关,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不仅在军事上无国可敌,而且在经济发展上远远走到了其他国家的前面,在综合实力上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超级大国。美国的电影、电视节目、快餐、饮料和有限公司被视为传播了使当地产品和价值观边缘化的美国文化。美国化成为西方居于支配地位的一个标志。实现这一点的主要工具是跨国媒介和通讯工业,它们通过诸如《豪门恩怨》等节目高扬了财富与消费,甚至通过描写蝙蝠人、超人以及虚构英雄的影视作品和连环书刊促进了社团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精神和价值观,试图让世界各国人民确信,“美国生活方式”不仅适宜于他们,而且是他们国家的未来。因此,美国的优越是自然的,符合每个人的利益。(16)
关于“文化帝国主义”命题的三个层面,大致涵盖了西方学者在这一问题上的主要看法。从上述学者们所论来看,“文化帝国主义”的涵盖面很广,主要涉及到欧美发达国家利用其文化优势来实现对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控制,也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控制或影响,一个国家把自己的一套信念、价值观、知识以及行为规范及其全部生活方式强加给其他国家。其实,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帝国主义”话语兴起之时,其所指主要针对美国。
大众媒介与“文化帝国主义”
“文化帝国主义”命题的涵盖面越广,大概就越容易模糊不清,更易于引起众说纷纭。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文化帝国主义在范围上很宽泛,原因在于这一概念包括从电视节目到芭比娃娃等每样产品,还包括诸如教育和对美的欣赏这样无形的东西。然而,文化帝国主义的易变本质使之难以明确界定,反倒容易使这一术语成为把第三世界各种不满怨言装入其内的垃圾箱。(17)因此,很多学者就把“文化帝国主义”局限于主要是美国媒介产品中体现的生活方式对世界各地,尤其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的影响与冲击。赫伯特·席勒便是这一观点的领军人物。席勒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传播系教授,他深受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对美国媒介文化产品在海外的扩张持强烈批评态度。1969年,他出版了《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通过批判大众传媒与信息技术领域中的权力运用,对美国媒介文化产品肆虐海外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按照席勒的观点,19世纪英美地缘政治的帝国主义在20世纪已经被一个更富有侵略性的工业—电子联合体所取代。他借用一些非官方观察家的观点说,这个联合体在全球范围内“在空间上和意识形态两方面扩大了美国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力”,依靠这种传播能力,美国“得以发号施令。参与文化交流的不计其数的社会机构无论如何都无法削弱美国社会制度的主要信息。教会、大学、基金会、政府都无一例外地、毫无怨言地传播官方的、工业和政府联合体的观点”。席勒由此得出结论,美国传播媒介联合体“不仅在影响国内人民生活和日常行为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国内并不明显而在国外日益显著的意义就是其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国内传播机构的结果、性质和管理不再完全是国内关注的事情,尽管它们曾经是。这种强大的机构现在已经直接冲击着世界各地的人们的生活”。(18)
这本书出版后影响很大,使席勒一举成名,奠定了其在国际学术界享有的地位。尽管“文化帝国主义”这种提法尚未出现在这本书中,但他实际上已经涉及到了这个当时在学术界非常前沿与敏感的问题。1976年,席勒在《传播与文化统治》一书中,正式使用“文化帝国主义”这一术语来描述和解释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文化发展的控制,其中包括媒介在内的大跨国公司扮演了主要的角色。他对文化帝国主义进行了界定,强调了国家精英在受到来自外部压力下转变本国文化过程中的作用:“文化帝国主义概念今天也许最好被描述为这些进程的总和,通过这些进程,一个社会被带入了现代世界体系,该社会居于统治地位的阶层如何被吸引、受到压力被迫以及有时被收买形成与该体系内处于支配地位的中心的价值与结构相一致甚或促进它们的社会制度。”(19)这本书出版后在学术界引起了不同寻常的反响,席勒提出的观点令人耳目一新,常常被那些研究与文化帝国主义相关领域的学者们所引用,席勒由此被说成是“文化帝国主义”理论的主要倡导者之一。随着全球化的加剧,美国媒介产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向世界各地,美国跨国公司在此过程中起了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这种趋势至今依然没有改变,而且愈演愈烈。席勒在20世纪90年代初就敏锐地意识到了促进美国信息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的“主体”的变化,并通过揭示这种变化的内涵以及趋势向人们展现了一副“美国媒介帝国”的全球图景。还有很多学者更明确地把媒介与“文化帝国主义”联系起来,旨在强调大众媒介产品在传播文化观念或生活方式上的核心作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地亚哥分校语言学教授克里斯·巴克认为,文化帝国主义可从把一种民族文化强加给另一种民族文化的角度去理解,在这一进程中,媒介被视为中心,是渗入和控制从属国家文化的文化含义载体。这样,“文化帝国主义命题的主要立场强调通过传播以全球电视为载体的资本主义消费主义而实现全球文化的同质化”。(20)在这些学者看来,媒介是“文化帝国主义”的核心内容。
学者们不否认大众媒介在“文化帝国主义”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但“媒介帝国主义”是否就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英国学者奥利弗·博伊德—巴雷特在197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首次使用了“媒介帝国主义”这种提法,并对之进行了详细的阐述。(21)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教授李金铨根据普遍性的四个层次界定了“媒介帝国主义”:一是电视节目出口到外国;二是媒介出口由外国人所有并被其牢牢控制;三是传递了占支配地位国家的规范以及媒介商业主义;四是资本主义世界价值观的入侵以及侵犯了被采纳社会的本土生活方式。(22)这样,所谓的“文化帝国主义”学派“尤其把注意力放在美国资本主义经济在南方国家的扩张与美国大众文化和大众媒介以及通讯技术大规模出口之间的关系上。其焦点主要集中在下述方面:首先,这些通讯/文化企业在总体上支持了以美国为基地的跨国公司的扩张;其次,这些企业本身就是日益重要的跨国公司;第三,这些相同的企业是在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以异常速度扩张的军事—工业—通讯复合体的组成部分。据假设,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由通讯结构和文化产业加以补充”。(23)在学术界,研究媒介产品对人们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影响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几乎与“文化帝国主义”命题的出现同步,七八十年代期间,“媒介帝国主义”的提法比较流行,出现了像本·黑格·巴格迪坎、诺姆·乔姆斯基以及爱德华·赫尔曼这样的研究跨国传媒的著名学者,80年代期间这一研究领域曾经历过短暂的沉寂,进入90年代之后再次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另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认为历史事实明确表明“媒介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联系,但还是不能将二者完全混淆。他们并不否认在把美国的信仰体系和生活方式传播到其他国家上媒介所起的重要作用,但不承认媒介是美国向全球范围内传播其文化观念的唯一方式。他们强调“文化帝国主义”更准确的同义词可能是“文化霸权”。(24)英国学者约翰·汤姆林森也不赞成在“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介帝国主义”之间画等号,认为把文化的观念只局限于媒介的实践纯属一些理论家或学者的“误导”。因此,为了理解关于文化帝国主义的各种主张,“我们需要考察媒介与文化其他方面的关系,而不是从一开始就设想媒介处于‘核心’”。(25)汤姆林森的批评主要是针对“媒介帝国主义”观而言的。
毋庸置疑,媒介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媒介并非等于文化或涵盖了文化的一切,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帝国主义”所涉及的范围既包括了“媒介帝国主义”在内,又远远超出了“媒介帝国主义”所限定的内容。二者不是一种等同的关系,但联系却十分密切,大众媒介产品在向外传递文化信息过程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信息传递日益加速的互联网时代,这种作用显得更为突出。全球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为美国快速地传递其文化观念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因为“不管我们是否有所准备,计算机和电信的聚合使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全球共同体。历史上第一次把东西南北的贫富国家联系在一个全球电子网络之中”。(26)美国对互联网的控制不仅给美国带来丰厚的利润,而且使美国人所信奉的文化观念迅速蔓延到世界各个角落,后者对人们思想造成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至今尚很难给予准确的估计。因此,对媒介作用的探讨可以大大有助于对“文化帝国主义”本质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文化帝国主义”与全球“美国化”
美国大众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广泛传播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国际学术界对文化帝国主义研究出现了热潮,“文化帝国主义”所指的对象显然是美国。1977年版的《哈珀现代思想辞典》把文化帝国主义界定为“运用政治和经济力量,在牺牲当地文化的同时宣扬并传播外来文化的价值和习俗”。(27)1982年,法国文化部长雅克·朗把文化帝国主义界定为是“不再夺取领土……但却改变意识、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帝国主义”。(28)这些定义把文化帝国主义理解为一种通过文化来实现控制他国目的的帝国主义形式,在这里政治和经济只是达到文化控制的工具。他们在对所提出的概念进行界定时很少专门提及美国,但在概念的内涵上都程度不同地涉及到以大众文化产品为媒介的美国大众消费主义文化在国外的延伸或传播,实际上与现在人们所谈的全球“美国化”有异曲同工之妙。美国研究文化与外交的著名学者弗兰克·宁柯维奇认为,传统的帝国主义已经被消灭,趋向形成一种“全球文化”成为传播文明的非常有效的力量,这种力量之强大是第一代帝国主义分子所始料未及的。(29)他认为,“世界美国化”与传统帝国主义之间存在着一种传承的关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授德格拉西亚把“文化帝国主义”与美国之梦在世界范围内传播看作是一个“历史进程”。通过这个进程,“美国的经历被转变为基于先进技术之上的商业社会的普遍模式,昭示了正式的平等和无限制的大众消费”。(30)加拿大学者米兰达·纳尔逊说得更为直截了当:“媒介帝国主义似乎是指作为出口的美国文化。随着美国公司对主要媒介流动的控制,美国文化的证据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展现。好莱坞和影星的形象得到全世界的认可,不只是美国人做着‘美国梦’。美国产品理念能够横行全球。可口可乐、麦当劳、耐克等等都恰恰是被出口的美国文化。”(31)因此,90年代中期以后学者们涉及到“文化帝国主义”概念包含的内容时所指的对象就更进一步明确了。到了这时,类似于“文化帝国主义”说法的表述就基本上与全球“美国化”一致了。
在许多研究者看来,“文化帝国主义”与“美国化”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使用不同的词汇来表示美国大众文化向全球扩散并使不同地区的文化向美国文化趋同的过程,“文化帝国主义”的施加对象更倾向于发展中国家。用布鲁斯·库科利克的话来说,在20世纪60年代及其之后的可能15年到20年,许多激进的知识分子把世界的“美国化”贬低为“文化帝国主义”。(32)他们的这种理解尽管残留着那个激进年代的痕迹,但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从理论上讲,文化帝国主义是以文化作为工具通过征服其他国家公民的思想意识来实现征服国的最大现实利益。因此,文化仅仅只是工具而已,实现对他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渗透才是文化帝国主义的真正目的。正如彼得拉斯认为的那样,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有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经济的,另一个是政治的。“经济上是要为美国文化商品攫取市场,政治上则是要通过形成大众意识来建立霸权。娱乐商品出口是资本积累和取代制造业出口的全球利润的最重要的来源之一”。(33)在美国的文化资源中,美国大众文化产品,尤其是媒介产品对外国公民生活方式的影响比较大,它们一方面给美国带来丰厚的经济利润,另一方面可以潜移默化地改变消费这些文化产品的人的思想意识,从帝国扩张的意义上讲,造成了美国潜在的势力范围不断地向外延伸。彼得拉斯以第三世界为例来说明文化帝国主义如何在历史和现实中发挥着这样一种重要作用。在那些对美国大众文化向外扩张持有激烈批判态度的学者的笔下,“美国化”并不是一个常见的词汇,但却是文化帝国主义的外在表现。文化帝国主义是一种主观设想,而“美国化”则是这种设想体现在实践中的一种客观进程。也就是说,如果把文化帝国主义作为一套理论解释体系的话,那么“美国化”就成为说明这种理论体系具有“说服力”的最好注脚。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帝国主义总是和“美国化”密切联系在一起。
“文化帝国主义”是否能够准确地解释当今世界,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美国化”这一现象,许多学者提出了质疑。这也是文化帝国主义解释话语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西方学术界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文化学教授约翰·辛克莱尔等人认为:“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显而易见的是,文化帝国主义话语在理论上以及根据该理论欲要解释的现实有严重的不足。世界电视体系的实际转变使这一理论在经验层面上越来越难以继续下去,包括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主动’观众理论等在内的理论范式使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越来越缺乏可靠的概念基础。”(34)这方面研究的权威学者吉诺—黑希特博士指出:“今天,具有影响的学者不再把美国和西方文化的传播解释为‘帝国主义’,而是解释为种族、地区和民族集团之间一种不断谈判的进程。”(35)荷兰学者梅尔·埃尔特伦也持相同观点,认为“文化帝国主义”概念是关于美国文化对其他社会的影响,但这一概念太“粗糙”了,不能说明“美国价值观和象征出现在不同的文化场景时它们发生的错综复杂的转变”。(36)他们对“文化帝国主义”的批评主要是针对这一话语本身,并不否认文化在构筑美国世界“大厦”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其实,美国政府的对外文化输出活动明显包含着文化帝国主义的内容,即通过强制手段或者威慑性力量要求发展中国家接受美国的文化价值观。这显然是典型的以强凌弱的帝国主义行为。所以许多学者把当代美国称为“帝国”也不是没有根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帝国主义”话语在解释美国海外活动的动机、手段与结果上尽管有很大的局限性,但并没有完全失去其理论构架的说服力。
在当代美国对外关系上,文化帝国主义的意识或行为无疑是存在的,但其的确与“美国化”还是存在着很大的区别。对美国之外的国家来说,这种区别主要体现在被动性和主动性方面。一般来说,“美国化”进程很少涉及到美国对其他国家采取强制性的措施来迫使它们接受美国的生活方式,而是靠着美国文化产品的吸引力对外国公众产生的一种难以抵制的“诱惑”来实现美国价值观的传播。所以对那些追求“现代性”的人来说,他们刻意模仿美国文化产品传递的生活方式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受到了外部的压力,而是自身的一种主动的行为。换句话说,如果人们对美国文化产品采取拒绝和排斥的态度,别人也奈何不得。犹如在商店里购买东西,买与不买,主动性完全在你。法国歌星伊夫·蒙唐就曾说过这样的话:“如果美国在文化上成功地侵害了我们,那是因为我们喜欢它们,即T恤衫、牛仔服和汉堡等。没有人把这些东西强加给我们,我们喜欢它们。”(36)捷克共和国公民达维德·克鲁斯特认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是一个使用不当的术语。正如在这10年期间一些人指出的那样,正发生在捷克共和国和全世界的美国化是自己造成的,所以人们不应该把它归咎于美国。捷克人着迷似的渴望得到和炫耀每件美国的东西,同时却以相同的方式避开和诅咒俄国的一切,这不是美国的错误。”(37)他们的观点当然不可能代表全部,但至少反映出相当一部分人对“美国化”的看法。这些国家的“美国化”过程肯定包含着“文化帝国主义”的因素,但毕竟不是靠着外部施加的强大压力所推动,很大程度上是其他国家内部对美国文化进入的一种主动的甚至积极的反应。这是与通过外部压力把一国的文化价值观强加给另一个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做法的主要区别所在。当然,撇开表面上的现象,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是否真的要沿着“美国化”的进程发展,的确令人怀疑。
注释:
①H.L.Wesseling,Imperialism and Colonialism:Essays o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Expansion,Westport:Greenwood Press,1997,p.ix.
②Annabelle Sreberny-Mohammadi,"The Many Cultural Faces of Imporialism," in Peter Golding and Phil Harris,eds.,Beyond Cultural Imperialism:Globalization,Communication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London:Sage Publications,1997,p.51.
③Merle E.Ratner,"Winning Hearts & Minds:Combating Cultural Imperialism to Defend Independence," Summer Seminar 2001,July 20-21,2001,Université de Provence,Aix-en-Provence,France,p.1.全文可在http://hoithao.viet-studies.org/Aix-Ratner.pdf网址上获得。
④参见Arthur M.Schlesinger,J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Boston:Houghton Mifflin,1986,pp.157-158.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0页。
⑥参见M.Gottdiener,"Hegemony and Mass Culture:A Semiotic Apprcach,"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Vol.90,No.5,March 1985,pp.981-982.
⑦Martin Barker,Comics:Ideology,Power,and the Critics,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9,p.292.引自John Tomlinson,Cultural Imperialism:A Critical Introduction,London:Pinter Publishers,1991,p.3.
⑧参见Arthur Schlesinger,Jr.,"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and Theories of Imperialism," in John K.Fairbank,ed.,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363-364.
⑨Kenton J.Clymer,Protestant Missionaries in the Philippines:1898-1916:An Inquiry into the American Colonial Mentality,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86,p.8.引自Golding and Harris,Beyond Cultural Imperialism:Globalization,Communication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p.51.
⑩Ryan Dunch,"Beyond Cultural Imperialism:Cultural Theory,Christian Missions,and Global Modernity," History and Theory,Vol.41,No.3,October 2002,pp.301-325.
(11)Paul W.Harris,"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ies:Collaboration and Dependency in Mid-Nineteenth-Century China,"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LX,No.3,August 1991,pp.309-312.
(12)Nancy Boyd,Emissaries:The Overseas Work of the American YWCA,1895-1970,New York,1986,pp.57-58.引自Michael J.Nogan,ed.,Paths to Power: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to 1941,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91.
(13)William A.William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New York:W.W.Norton & Company,1972,p.47.
(14)Jessica C.E.Gienow-Hecht,"Shame on US? Academics,Cultural Transfer,and the Cold War:A Critical Review," Diplomatic History,Vol.24,No.3,Summer 2000,p.470.
(15)关于文化帝国主义三个层面的论述,可在http://visar.csustan.edu/aaba/Essay.pdf网址上获得。
(16)Virginia Culp,"The Rat in the Cargo:Cultural Imperialism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Theory,April 22,2000,p.9.
(17)Herbert I.Schiller,Mass Communications and American Empire,Boulder:Westview Press,1991,pp.58-62.
(18)Herbert I.Schiller,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New York: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1976,p.9.引自Colleen Roach,"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Resistance in Media Theory and Literary Theory," Media,Culture & Society,Vol.19,No.1,January 1997,p.53.
(19)参见Chris Barker,Global Television:An Introduction,Malden:Blackwell Publishers,1997,p.183,p.185.
(20)参见J.Oliver Beyd-Barrett,"Media Imperialism:Towards an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an Analysis of Media Systems" ,In James Curran,Michael Gurevitch,Janet Woollacott,eds.,Mas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London:Edward Arnold,1977,pp.116-135.
(21)Chin-Chuan Lee,Media Imperialism Reconsidered:The Homogenizing of Television Culture,Beverly Hills:Sage,1980.引自J.Oliver Beyd-Barrett,"Western News Agencies and the 'media Imperialism' Debate:What Kind of Date-Ba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35,No.2,Fall 1981/Winter 1982,p.248.
(22)Colleen Roach,"Cultural Imperialism and Resistance in Media Theory and Literary Theory," Media,Culture & Society,Vol.19,No.1,January 1997,p.48.
(23)参见Jan Swee,"Cultural Imperialism," September 3,2003,http://tiamat.sakabatou.net/stuffs/imperialism.doc.
(24)Tomlinson,Cultural Imperialism:A Critical Introduction,p.6,p.23.
(25)Walter B.Wriston,"Bits,Bytes,and Diplomacy," Foreign Affairs,Vol.76,No.5,September/October 1997,p.175.
(26)Alan Bullock and Oliver Stallybras,eds.,The Harper Dictionary of Modern Thought,New York:Harper & Row,1977,p.303.引自Gienow-Hecht,"Shame on US? Academics,Cultural Transfer,and the Cold War:A Critical Review," p.472.另见Robert Arnove,ed.,Philanthropy and Cultural Imperialism,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2,p.2.
(27)引自Schlesinger,The Cycles of American History,p.156.
(28)Frank Ninkovich,The United States and Imperialism,Malden:Blackwell Publishers,2001,p.250.
(29)引自Miriam Bratu Hansen,"The Mass Production of the Senses:Classical Cinema as Vernacular Medernism",Modernism/Modernity,Vol.6.No.2,April 1999,p.68.
(30)Miranda Nelson,"Media Imperialism" ,Media Studies 112,April 10,2002,全文可在http://members.shaw.ca/charenton-/media.html网址上获得。
(31)Bruce Kuklick,"The Future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Diplomatic History,Vol.24.No.3,Summer 2000,p.503.
(32)James Petras,"Cultural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Vol.23,Vol.2,1993,p.39.
(33)John Sinclair,Elizabeth Jacka and Stuart Cunningha,eds.,New Patterns in Global Television:Peripheral Visio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7.
(34)Gienow-Hecht,"Shame on US? Academics,Cultural Transfer,and the Cold War:A Critical Review",p.491.
(35)Mel van Elteren,"Conceptualizing the Impact of US Popular Culture Globally",Journal of Popular Culture,Vol.30,No.1,Summer 1996,p.66.
(36)参见Robert K.Ranth,Jr.,"The Myth of Cultural Imperialism",The Freeman,Vol.38,No.11,November 1988.全文可在http://www.libertyhaven.com/noneoftheabove/culture/mythcultural.shtml网址上获得。
(37)参见Rese Anne Sim,"The United States vs.the World:A Theoretical Look at Cultural Imperialism,"全文可在http://www.utexas.adu/ftp/depts/eems/cultimp.387.htm网址上获得。
标签:文化帝国主义论文; 帝国主义论文; 传教士论文; 美国社会论文; 美国政治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文化价值观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世界政治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西方世界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基督教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