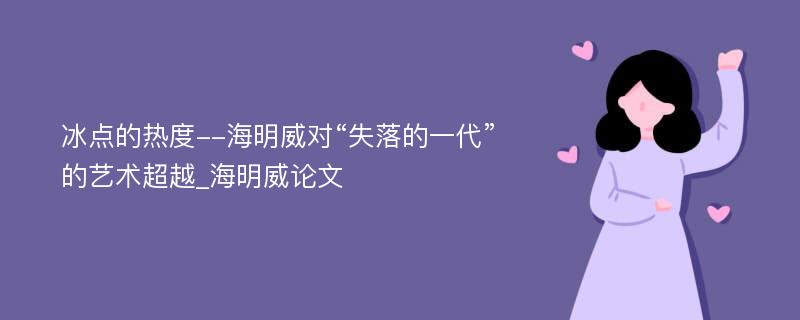
冰点的热度——海明威对“迷惘的一代”的艺术超越,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海明威论文,冰点论文,迷惘论文,热度论文,艺术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是海明威的著名短篇小说,曾被看作海明威“最杰出的短篇”,“最完美动人的故事”;历来受到欧美各国文学评论界的关注。然而,这一作品在我国却鲜见译文与评论。这就容易影响我们对海明威及其创作的客观认识。笔者在此愿意抛砖引玉,就教方家。
一
应当肯定,这是一篇体现海明威艺术转折时期独特风格的小说。它标志着海明威面对悖谬的现实,挣脱了迷惘孤独,重新建立起对人和人性的信心,决意抗拒虚无;进而在人与人的关系层面,找回了人生,找回了意义,终于在30年代初期实现了对“迷惘的一代”的艺术超越,在小说创作上由前期走向后期,在艺术上真正走向成熟。
作品没有多少情节性因素。夜深人静,街头一家干净明亮的西班牙咖啡馆里,顾客只有一位孤独的老人。两个侍者远远守望。他们的简约对话,和其中一位年长侍者随后在回家路上的内心活动,构成了小说的主体。小说仿佛一幅水墨写意,冷峻疏朗,深邃含蓄。没有抒情渲染,没有梦幻寄托,甚至没有多少描写形象;稀稀落落的字里行间,仿佛全然出于不经意,一种人以其尊严抗拒虚无的冷静沉着,一份心如止水蔑视虚无的大无畏气概,力透纸背,传神地体现出来。
对话围绕老人展开。老人是位常客。他喜欢夜深人静后咖啡馆里的那份明亮整洁。时近打烊,他仍默默独饮,迟迟不肯离去。从侍者的对话中我们了解到:他上周自杀未果。他有钱,自重,好酒,不俗,一生历尽沧桑,如今已步履蹒跚,年迈耳聋。他生活孤独,前程绝望,面对着眼前人生的巨大空白,表现了一种坚忍刚毅卓然抗争的气魄。他沉着坚定,体面从容,一丝一毫也不肯丢弃自己做人的尊严。在他身上,我们发现了海明威笔下人物特有的素质:尽管因战争或环境而遭受伤害,行为方式依然保持着体面从容。他们无畏无怨,宠辱不惊,以其教养和克制,面对无可更改的逆境。
相形之下,两位侍者中年轻的一位则自私而庸俗。他得过且过,饱无用心,沉溺于鸡虫之乐,对自己对生活心满意足。这是一种赖自欺而知足,因知足而常乐的庸人心态。他对街灯下匆匆走过的姑娘和她的士兵恋人幸灾乐祸。他急于提前下班,回家上床,沉入那乐不思蜀的黑甜之乡;于是迫不及待,连懵带撵,把老人打发走了事。其实他也并非生性冷酷,只是一味地注重实惠自我中心,与老人活法儿不同。所以他对别人显而易见地缺乏理解,更缺乏同情。谈及老人自杀的原因,他的回答才那么俏皮轻薄:“没什么(NOTHING)”。
难能可贵的是,咖啡馆里连老人仅有三位,居然就有人与老人灵犀相通。那位年长侍者的生活信念不同于年轻侍者:既不那么自我中心,也不那么自满自足。他情愿帮助那些对生活失去了信任与信心的孤独的人,尽管他能做的仅仅是提供一个像样儿的场所,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让他们喝上一杯,借以逃避黑暗、肮脏、嘈杂的现实。他与老人阅历相近,声气相投,有一种人对于人的理解和同情。他能从一句“没什么”的随便应付中,顿悟老人自杀的真正原因:虚无。这是英语语汇NOTHING的又一词义,更是一种痛苦难耐的生命体验,一种刻骨铭心的人生感觉。在他的眼里,生活中的虚无也是那样巨大而沉重,既难以承受,又无处不在,无可避免;而且一经体验便无法忘怀。这正是作者赋予NOTHING的深层含义,也是作品将要揭示的小说内容的关键所在。
年长的侍者作为老人的同类,尊重老人,理解老人,懂得老人的心理需要:那应当是一种特殊的美好感觉,一种只有在夜深人静的明亮的咖啡馆里可以找到的对人生的心理体验。在老人了无生趣的生活中,唯一的安慰只剩了这种感觉。正是靠了这种感觉,老人抗拒着污秽嘈杂的现实和黑暗的虚无,抗拒着了无生趣的风烛残年,抗拒着自己的弃世冲动。
我们看到,年长的侍者对同伴的粗莽冒昧深为不满。他曾这样表白自己的心迹:“每天夜里我都不想关门,因为也许有人需要咖啡馆”。按他的说法,他自己也“属于那种喜欢在咖啡馆里泡到很晚的人”。他和老人有着同样的需要,同样的感情。小说的后半部分,外部描写转为年长侍者以转述方式出现的内心独白。他希望自己也能像老人一样,借助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找到那种美好的感觉;也能像老人一样保持人的尊严,抗拒人生的虚无。遗憾的是,想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干净明亮的咖啡馆可遇而不可求。下班之后,他一路走去,却无法再找到另外一家。他只得来到一家普通的酒吧。然而,那里既没有声气相投的同类,更没有使人留连忘返的所谓“人生的光泽”,借以对抗黑暗、肮脏与嘈杂。他实在找不出聊以自慰的美好感觉,只好回家睡觉。可是,他并不想睡觉。他睡不着,除非天亮。当然,那位老人也睡不着。耐人寻味的是:据说,在这个夜的世界上,许多人都睡不着觉。
二
小说到这里,有意识地运用特殊的艺术处理,着力强调生活阅历给人带来的一种显然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活感受:虚无。看来,它就是导致老人自杀,激起年长侍者共鸣,并使大家都睡不着觉的根本原因。虚无由此成为理解小说的基本线索。海明威借助现代小说技巧,摹仿宗教祈祷的形式,给虚无安排了一个格外引人注目的地位。他以一段特意为它而设计并以它为中心的天主圣母祈祷文,突出强调虚无,竟而至于让它挤占了上帝的位置。
其实,海明威在这里用到的虚无一词,出自《圣经·旧约·传道书》。他此前所写的著名长篇、“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作《太阳照常升起》,其书名连同书前题辞:“一代人过去,一代人又来,然而大地永存”,也都引用于此。
所谓虚无,可以看作是对人生无意义感的一种带有宗教色彩的概括。它根源于悖谬现实,经常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与文学的主题。当然,这种人生感受绝非当代人的专利。《圣经·旧约》中成于公元前的《传道书》即专论虚无。书中说,世间一切皆虚无。阳光之下再无新事。此为人生定数。显然,这是一种典型的宗教人生观。它面对残酷而无奈的外部压迫,借口万象皆空,以超脱退让而自欺,隐约透露出一种万般无奈不得已而弃世的痛切绝望。
海明威对虚无从内心深切认同。他曾认为:“太阳升起,不过是为了赶回日落之处……,人生到头空无所有”(《太阳照常升起》)。这不仅代表了“迷惘的一代”对人生的看法,而且代表了一战后西方人普遍持有的一种对世界对人生深深失望的思想情绪。然而,这恐怕不但不能简单归之为宗教感情,归之为愤世嫉俗的个人看法,而且恐怕主要不能由他个人来负责。我们知道,本世纪前30年,西方社会曾前波后涌危机不断。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更造成了西方民众对社会对政治对经济对文化对人生的深深失望,造成了严重的信仰、信念与信心危机。面对悖谬的现实,许多人的生活一度完全失去了目的和意义。借用梭罗的说法:他们“在默默的绝望中生活”,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空虚。人们身陷普遍的沮丧焦虑,在悲叹“西方的没落”的同时,开始对人生的意义、文化的价值、世界的合理性等等,从根本上产生怀疑。在一段时间里,在相当大一个范围内,各种形式的虚无主义思潮盛行。“迷惘的一代”即是其典型代表。
就个人遭遇而言,这一时期,生活对海明威的确也太残酷了。他自小学拳击即因误伤打坏了一只眼睛。刚刚进入成年,又参加了世界大战。他在战场上曾前后9次身负重伤,其中有一次从身上取出过237块弹片;曾颅骨骨折,脑袋缝过57针;仅膝盖即开刀12次。此外,他曾一次丢失18个短篇和一部长篇的手稿,相当于4年的艰辛创作。后来,他还遇过两次飞机失事,3次车祸,3次婚姻失败。1928年父亲自杀身亡,又给了他一次沉重的打击。他常年患有高血压、肝炎、糖尿病、皮肤癌等重症。有人说他创造了人类承受苦难的世界纪录,信非妄言。尽管他后来战胜了这一切,最终跨越了人生与艺术的巅峰;但这一切确实曾使他一度失去了生活信心,陷于迷惘困惑,绝望悲观。他不相信原罪,不相信理性,不相信阶级和阶级斗争等等说法,甚而至于不相信社会不相信人性与人生。他曾不止一次动念自杀。或许可以这样说,作为当时西方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世界大战既撕碎了海明威的肉体,也撕碎了他的心。他自己也曾说:“战争在一个作家的心灵里留下的创伤是很难愈合的”(转引自丽莲·洛斯《海明威肖像》;见董衡巽编《海明威谈创作》)。
海明威前期作品,侧重描写的正是这种彻底地怀疑社会怀疑人生怀疑现实怀疑历史,“否定一切社会组织结构”(盖斯玛:《危机中的作家》)的“虚无”感受,从而“令人信服地表现了战时和战后的普遍情绪”(康利夫:《美国的文学》)。正是由于这些作品,海明威成为“迷惘的一代”的代表人物。
相信《圣经》中有关虚无的上述议论肯定唤起了作家深层意识的强烈震憾。这篇小说正是以海明威亲身体验过的人生无意义感为基础。
三
问题在于,如果小说仅仅停留在这一水平上,那充其量不过是对《太阳照常升起》和“迷惘的一代”的再次重复,即无创新可言。然而,海明威毕竟是海明威。他有着狮子般的勇气和力量。在持续多年的徘徊摸索之后,他终于设法熬了过来,并最终超越了战后西方精神荒原上一度以他为代表的“迷惘的一代”,跨向了他文学创作的最高境界:以人性抗拒虚无。按照瑞典皇家学院的说法:“他忠实地、不屈地再现了这个严酷时代的真实面貌。在这个充满暴力和死亡的世界中,他看到了勇气和同情。”创作上的有力佐证,是他从《太阳照常升起》(1926)、《永别了武器》(1929)等前期作品,大踏步地走向了思想创作成熟期的《丧钟为谁而鸣》(1939)、《老人与海》(1952)。首次发表于1933年3月号SCRIBNER'S MAGAZING,后收入1933年10月出版的短篇小说集《胜者无所得》(WINNERTAKENOTHING)的著名短篇《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正是这样一部承前启后的要作,一块矗立于两期创作之间的重要里程碑。
海明威的这篇小说继续发挥了他一贯的勇气与力量的主题(参见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他既没有简单地否认虚无的存在,又绝非无条件地屈从无可抗拒的虚无,更不肯全盘地接受它的悲观出世消极逃避,尤其不肯在命运面前低下他高傲的头颅。他以明确的抗争态度,以深切的人生和艺术体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创造出独具风格的海明威式的小说主题:人为其人性的尊严,在血泪淋漓中迭仆迭起,抗拒逆境,抗拒虚无。就是说,哪怕整个世界与人为敌,人生真的没有意义,生活就是虚无,人不得不遭受荒谬现实的残酷压迫;人仍应借助人性的力量,勇敢地抗拒虚无,竭力保持“压力下的风度”。愈是逆境,人愈不能退让,愈不能弃权,愈要高扬人性的旗帜,保持人的尊严。面对别无选择的虚无,人只能别无选择地生存下去。人不能放弃生活的权力,放弃人的身份。理所当然,人还必须“像人一样地生活”。或许,这正是海明威心目中人性的深层内涵,人生意义的真谛。这一倾向,最终发展成为《老人与海》的著名主题:“人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消灭他,但是你打不败他。”
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在这一篇幅不大的短篇中异乎寻常地引入了第二主人公,并着重通过那位年长侍者的形象,明确表达了海明威艺术探索的重大调整,即:作者开始清醒地自觉地重视来自他人的理解与同情,重视这种处在独立个人之外的,从人与人之间关系萌发出来的新的人性力量。
抗拒虚无依靠的正是人性的力量。人性重新成为海明威价值中心。在海明威看来,人性具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人正是以人性的力量对抗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对抗着黑暗无边的虚无。小说中的那位老人即拥有这种力量。所谓的人性力量,首先为特定的个人所拥有,其内容是以人的尊严为核心,包括勇气、自尊与刚强,以及有赖勇气、自尊与刚强来激励来开发的人的全部潜能。这种潜在的能力在海明威笔下既体现为人的坚强意志,也体现为人的非凡的智能体能。除此之外,我们看到,小说在表现人性方面获得了令人瞩目的突破,那就是它已经有意识地将人性与真正属于人的物质性的生活条件联系在一起,并将人性的范围扩大到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领域。
作品精心营造了一个小说艺术境界: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它作为人性的象征,成为小说主人公的精神家园。老人,年长的侍者,都对这个地方一往情深,留连忘返。推想起来,恐怕作者以至作者所代表的众多西方读者,对这样一个理想境界也会产生类似的美好感觉。正因为如此,作品利用小说中这唯一的对于环境的集中描写,利用开头、结尾以至小说的标题,或明或暗地对这一物象加以反复强调,并使之具有了象征意义。于是,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便与真正属于人的生活方式,与生活中值得留恋的美好事物和生活的美好方面产生了密切联系,显示出这类富于人性的生活条件,这类“人生的光泽”对抗拒虚无培育人性的重要性,以及作者对于生活的深深眷恋。客观地讲,这一小说境界的营造,事实上还肯定了人性与这类物质环境的依存关系。人的生活之所以称之为生活,而非动物般的生存,这种真正属于人的生活环境,当是必要条件。它属于一种人为的创造,自然须由人自己来实现来完成。作者由此提出了人生的又一意义:为自己和他人创造属于人的生活环境。
小说的难能可贵之处还在于,作者把对他人的理解与同情,当作人的生存环境的前提,当作人性的重要内容,加以重点描写。这就使小说所描写的互助友善息息相通的人际关系,越出了人性必要条件的范畴,直接融入人性,加强了人性抗拒虚无的力量。小说中的老人,如果没有侄女的搭救,早在作品开始之前便已死去。而作为老人形象在艺术上的补充与拓展,那位年长侍者的形象恰是由此获得了极其重要的艺术价值。
年长侍者形象的另一艺术作用,表现于小说结尾处的几行文字。作者通过其内心活动转述,通过他在平静超然中透露出的信念,使抗拒虚无的行动超越了偶然的个人行为的局限,进而赋予抗拒虚无的小说主题以普遍意义。正因为如此,小说人物都没有名字。他们可以是每一个人。在这里,文学暗示的涵义无疑超越了人的个体存在,突破了个人的软弱与孤独,沟通了众多的社会成员,进而扩大了抗拒虚无的队伍,增强了抗拒虚无的信心、勇气与力量。综观整部小说,其中有关年长侍者的描写,几乎占到了小说近一半的篇幅;年长侍者在小说中的地位,也几乎占到了可与老人平分秋色的程度;其安排之独特,亦足见作者匠心。
至此,一个干净明亮的地方,作为小说的理想境界,作为人性的象征,便肯定地包含了对他人的期望,对同情与理解的吁求,进而打破了绝望与孤独,形成了某种依靠人与人性同现实抗争同虚无抗争,并将希望寄托于抗争的大无畏人生格局。
四
至于抗拒虚无这一小说主题的最终实现,除了依靠对理想人物与环境的正面描绘之外,还有赖于作家对年轻侍者、对过路情侣、对普通酒吧的对照性描写,特别是小说结束前的一处强有力的点睛之笔。这就是小说以虚无的名义对天父圣母祈祷文作滑稽摹仿的那一段反讽文字。小说的内涵由此显得既明朗确定,又含蓄深沉。
滑稽摹仿是一种常见于现代小说的文学手法。它对传统风范做开玩笑式的摹仿,借助摹仿中有意识的艺术变形,抒写作家对生活的复杂体验,突出强调摹仿对象的弱点、做作和自我意识的缺乏。它以袤渎成规为目的,以意在言外为特征,以戏谑调侃为效果;以笑写悲,含蓄简约,声东击西,生动有力;常常在充分调动读者经验召唤读者参与的基础上,鲜明地揭示出艺术描写与其对像间的内在矛盾内部冲突,刺激诱发读者的心理活动。运用得好,能够在冷漠平淡的行文中给读者造成强烈的印象。滑稽摹仿可以戏拟庄重高雅的文体,借以描写卑微低贱的内容,如《尤利西斯》摹仿史诗写俗人,《阿Q正传》摹仿纪传写雇农;也可以戏拟俚俗油滑的风格,用以描写严肃郑重的题材,如《第22条军规》利用通俗小说探讨社会机制,《高祖还乡》借助勾栏套曲揭露帝王本相。
在小说的相应段落,作者有意套用了上述宗教神圣意味的祈祷文,只是把其中天父圣母的名字,统统换成了虚无。在这里,反差强烈的祈祷形式与特定内容,造成了滑稽摹仿;而冷漠平淡的上下文语调,则强化了有意袤渎神圣,有意拿虔诚开玩笑的心理意向。这段文字的意义由此变得生动而复杂。它产生了一种多层次迭加的艺术效果:既借助宗教祈祷形式,对虚无予以突出强调,使之显得地位煊赫,不可一世;又通过摹仿的滑稽效果,先是否定宗教神圣不可侵犯性,解除了上帝的权威,指出虔诚心态的滑稽可笑,促使小说人物、小说作者与读者从心理上摆脱了对宗教的义务感责任感;跟着便转移矛头,嘲弄虚无刚刚挤占得来的神圣地位,剥夺其严肃性郑重性,并利用这一新的地位赋予虚无以迷信荒谬的色彩,对虚无表示怀疑,使之沦落到与宗教为伍的不光彩不足道的地位。于是小说人物也好,小说作者与读者也好,对虚无自然也就不必如同过去对上帝一样虔诚信奉,膜拜屈从了。
滑稽摹仿还在一定程度上给小说带来了自嘲的意味。它同时指向作者,指向摹仿行为本身。因而它无意于故作姿态以否认作者的局限,这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旧日读者心目中作者居高临下指手划脚的印象,融洽了双方的关系,拉近了两者间的心理距离;它也无意于回避摹仿自身可能造成的局限,这就为小说这一人为创造物涂上了一层凡俗切近的人性光泽,使人在感情上觉得它更自然更真实更容易接受。而自嘲所仰赖的勇气、自信与从容,自嘲所造成的冷静、超脱与宽容,更给人以成熟、达观、堪与信任的印象,有助于突出海明威小说独有的审美特色。
综上所言,滑稽摹仿用在这里既有意袤渎神圣,嘲弄虚无;又以自嘲来解脱自己,实现了心理超越。它在小说中针对的主要是一种对虚无的迷信与盲从,作用在于为小说画龙点睛。
应当看到,有意无意地在虚无与上帝之间搞顶替接班,给虚无创造出类似于上帝的那种化育万物至上至尊的地位,实在是20世纪西方哲学思潮搅起的一堆思想泡沫。虚无一度沦为现代人自欺欺人的借口,一种用来蒙蔽世界蒙蔽自己的类似于宗教迷信的东西。然而,文化的真正意义应当是帮助人们改造悖谬现实,以求更好地生活,而不是在生活中鼓吹逃避。正是在这里,海明威终于与“迷惘的一代”分道扬镳,转而探讨“他那一代人如何忍受并非他们所创造的、而且不为他们所喜欢的世界”(魏兰德·索普《20世纪美国文学》),探讨人应该怎样面对现实,抗拒虚无。
用自己的方式把握现实,抗拒虚无,帮助自己帮助人们鼓起勇气,熬过20世纪最难熬的一段时光;或许,这才是海明威的创作初衷。
五
实事求是地讲,滑稽摹仿并非海明威小说创作的主要手段。他只是根据需要偶一为之,就像《乞力马扎罗的雪》使用意识流一样。总的说来,这篇小说所体现的仍然主要是现实主义的特色,只不过达到了艺术大师别具一格的境界。
海明威毕生追求写得真实,坚信客观冷静是真实的条件,人的感觉是真实的源泉。因而他在小说叙述中奉行的是作家退出小说的叙事原则,字面上绝不留个人参与的痕迹,体现出所谓的“零度风格”。他在行文中长于运用极度简洁极度准确的文字来描写行为和对话,进而刺激视觉思维活动,给读者造成真切鲜活的感觉。或许是受庞德影响,他的小说还刻意追求传神意境的营造,从中使作者、对象和读者的心理距离缩短到最低限度,并为象征意义的生发提供催化氛围。通过这篇小说,我们确实看到,“海明威在艺术上孜孜以求的,是眼睛和对象之间,对象和读者之间的直接沟通,造成一种光鲜如画的感觉”(赫·欧·贝茨《现代短篇小说》)。
客观冷静的“零度风格”,简洁含蓄的真切感觉,心理沟通的意境营造,三者合一,构成了海明威小说的艺术特色。作家自己把它概括为著名的“冰山原则”。
艺术上的“冰山原则”,实际上与海明威对悖谬现实接近全面否定的态度,对人生坚持抗拒虚无的看法具有内在一致性。这使得海明威的小说表现出一种严酷冷峻的色调。然而,海明威又是一个毕生对世界做不倦探索,对社会对生活积极参与执着追求的作家。他一直认为:“作家的任务是不会改变的。作家本身可以发生变化,但他的任务始终只有一个,那就是写得真实,即在理解真理何在的前提下,把真理表现出来,使之作为他自身经验的一部分,深入读者的意识”(《在第二次美国作家大会上的发言》,1937;参见《美国作家论文学》)。他的记者生涯、小说实践,以及对两次世界大战和其间的西班牙战争的主动参与,即是明证。这中间,我们发现,作家对于生活又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热情。
上述这些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或可称之为“冰点的热度”的艺术风格。或许,这中间多少透露了海明威小说艺术的某种内在统一性?
当然,在我们看来,小说仍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恐怕还是对生活的理解。虚无即无意义。尽管这种概括事出有因,但终究失之于抽象普泛,算不得科学合理。它毕竟属于主观感觉,派生于悖谬的现实。要在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需要变革现实,需要从具体的社会改造入手。与此相关,抗拒虚无,仅仅依靠人的尊严人性的力量,哪怕再加上干净明亮的地方,仍然显得软弱无力。要想真正有效地抗拒不合理的社会存在,还得依靠社会物质性的力量,着眼于社会体制和结构。诸如此类的一系列事关重大的选择,应该说海明威都没有找到我们认为正确的答案。不过,对于一位文学家,尤其是对于现代西方一位超越了“迷惘的一代”的优秀小说家,我们不应也不会过分苛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