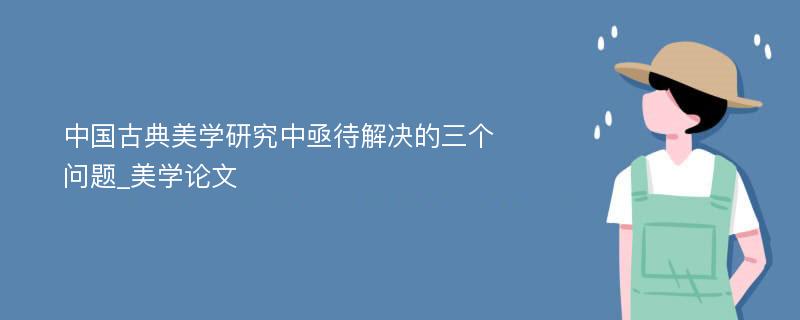
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亟须解决的三个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中国古典论文,亟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重新审视阐释中国美学的理论元话语
佛教传入中国时,曾有一个“格义”阶段。这个用来“格义”的话语体系,叫做“元话语”(meta-dis-course)。和佛学传入中国时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典籍成了西方美学话语“格义”的对象,而当年则是用中国话语“格”佛典的“义”。
这种特殊境遇导致的结果是,我们越是用西方术语来说明中国古代有美学,就越发觉得中国古代美学存在的可疑。理论之所以为理论,就是因为其解释功能。一旦中国古代美学理论本身成为待解释的对象,那就会在解释领域失去发言权。上世纪80年代中西美学比较的兴起、90年代对中国美学话语“失语症”的揭示都说明了我们对这一危险的警觉,也是我们试图摆脱这种悖论处境的努力。但其成果极为有限,因为中西美学比较的“元话语”仍需重新审理。
比如,我们常说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天人合一,西方文化的根本精神是天人对立。然而“天人合一”却是一个多义词,各家的解释差别很大。最为我们熟知的一种解释就是,中国人与自然是亲和的关系,而西方人则与自然对立。这个概括是有问题的。环境美学的开创者阿诺德·伯林特系统地梳理了西方的自然观。他发现,从哲学上讲,西方的自然观有截然相反的两派:一个是洛克学派,认为自然始终外在于人;一个是斯宾诺莎学派,认为自然之外无一物。至于在实际生活中,人对自然的看法则有一些过渡形态。于是西方的自然观就有这样四种基本观点:1、完全对立的自然观。2、比较温和的分离观。3、比较温和的统一观。4、完全一体的自然观。同样,我们在中国古代思想中也可以看出这种层次来。所以,所谓在自然观问题上的中西差异,其实是一种文化内部两种倾向的对立。其他诸如中国人重群体西方人重个体、中国文学是抒情表现的西方文学是叙事再现的等等概括,都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因此,这里所说的重新审视元话语的问题,不仅是指审视将“文”与“文学”或“美”简单等同,而且要审视中西美学比较本身。事实上,我们上一个世纪所作中西比较,大都流于“大而化之”,而未能“具体而微”。我们往往习惯于一种“宏观”把握,即首先将一组对立的概念看作中西文化的根本精神,然后借此执一御万,以解释中西美学的其他差异。与这种宏观把握相反,我倒更看重一些微观的考察。因为,我一直相信中西文化的差异是具体而微的,而不是大而化之的。无论中国还是西方,都不是可以“一言以蔽之”的。所以,重新审视理论元话语,也包括重新审视这种“一言以蔽之”的叙述策略。
构筑中西美学对话的平台
20世纪的中西文化比较,大多是在中西对立中作出的。所谓中西对立,就是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一文中所说的“欧洲输入之文化,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根本性质极端相反”。这种简单化的思维模式,近来又受发源于西方并迅速席卷全球的“后”学的推波助澜。我们知道,“后”学以解构“西方中心主义”为理论鹄的,很多学者也自觉跟进,以为中国古典美学研究之所以在20世纪陷入困顿,是因为西方中心主义的压迫。我们撇开这种观点的火药味不论,只分析其理论偏颇。
我们承认中西差异,承认西方美学思想有西方学人率先揭示的“西方中心主义”立场,我们也承认用西方学术传统来阐释中国古代学术使得中国传统话语患上了“失语症”,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这样的一个事实:“西哲东渐后,令研究中国传统学术者眼界大开,也是事实。中国传统思想,在西洋哲学观念、术语、理论之参照与对比之下,被看得更清楚,同样也是非常常见的”(龚鹏程语)。
我们之所以在西方“后”学的影响之下,采取一种激烈地“反西方”的学术姿态,是因为我们一直将中西近代以采的学术互动单方面地理解为“西学东渐”,而忽略了“东取西学”的方面。墨哲兰说:“‘西学’而‘东渐’这样一种说法,太以‘西学’为主词谓述了,颇落了西方人眼中的‘东方主义’言筌。对中国人来说,应是‘东取西学’,事实上,历来中国人的‘拿来主义’,就在一个‘取’字上。”可以说,整个近现代学术史,在更大层面上是一个“东取西学”的主动接受史,而不是一个“西学东渐”的被动受影响史。重建中国学术的关键,不在于慷慨激昂地“痛陈西哲东渐的结果已使中国传统思想之研究产生了严重的异化现象”,而在于平心静气地重新审视中西。
就像任何人的自立不是靠消解他人来获得的一样,中国美学的自身地位也不能靠“解构西方中心主义”来获取。“解构西方中心主义”的呼声和“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在世纪之交同时出现,并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中西对立这种思维方式所导致的必然。所以,21世纪中国学术要超出20世纪,一个基本的前提就是要超越中西对立。
R·威尔金森在《东方和西方:“深刻”之概念》一文中说:“我花了大量的时间比较了东西方思想体系中的美学观念,结果我所发现的大多是体系中的差异……但是当我比较东、西方思想体系中蕴涵‘美学深度’概念的各个观念时,我所发现的却只是体系中的共同点。因而似乎存在着某种真正跨文化的经验。”这种所谓的“美学深度”,就是对于“深刻”的追求,对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味外之味”的偏爱。所以,他坚信“存在着某种跨越文化界限的东西,某种仅仅属于全人类的东西,某种——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的东西。”我们从事美学研究,不就是为了寻找这种我们每个人都能理解的东西么?不然,美学何以为“学”?
王国维在上一个世纪之交说:“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中西二学,盛则俱盛,衰则俱衰”。钱钟书在《谈艺录·序》中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这些说法,并非出言愚远,而是用心良苦。
从中国美学走向中国美学
在“后”学的视野里,中国美学的价值在于其民族特殊性,他们正是要用这种民族特殊性来解构西方。这种看似积极甚至激进的学术姿态,其实是在消解中国美学本身。
美国汉学家列文森曾不无沉痛地说,中国人“视儒教为中国的‘国性’这一浪漫思想剥夺了儒教自身精髓:一个理性的假定,即无论何时何地,路就是路,而不仅仅是特殊的中国人的生活之路”。片面强调儒学的中国特性,其实就是把它看成是“特殊的中国人的生活之路”,而不是“路”。王晓朝说:“柏拉图的对话不仅属于西方人,而且也属于全人类。”其实对于孔子、老子、庄子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奇怪的是,西方汉学家把他们视为“伟大思想家”时候,我们却在寻找他们思想中的中国特质,将他们变成一个“伟大的中国思想家”。
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美学,不要将重点放在“中国”上,而应当放在“美学”上。这就是本节标题所说的“从中国美学走向中国美学”的第一层含义。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兹说,一切理论“如果它们不具备普遍性,它们就不具备理论性”。只有发掘中国古代美学中的人类普遍性,中国美学才会真正拥有和西方美学对话的资格。即使我们想解构西方中心主义,也要用中国美学的人类普遍性,而不能用中国美学的民族特殊性。否则,我们解构的将是中国美学本身。
本文所主张的从“中国美学”到“中国美学”的另一层意思,是让中国美学成为更为开放的学问。中国美学成为开放学问的一个逻辑前提就是,中国美学应当成为人类的普遍学问,而不是一个民族的特殊学问。
成中英区分了中国哲学的“近代化”和“现代化”。他认为,“近代化”是指学术转型,而“现代化”则意味着中国哲学的“世界化”和“落实化”。所谓“世界化”,是指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应当有一个“世界心态”,而不是为了追求民族身份认同;“落实化”是指中国哲学应当对人类难题提供可能的答案。成中英所说的这个“现代化”,则是从“中国美学”到“中国美学”的第三层含义。
我们研究中国古代学术,并不是为了满足一种思古之幽情;我们研究西方学术也不是为了满足一种好奇之愿望。实际上,我们之所以必须要构筑中西美学对话的平台,其理论根据在于人类的共通性,其实践根据则在于我们现在处在同一个世界,面临着同样的危机。这就是我们所耳熟能详的“全球化”。其实“全球化”之所以能成为一个学术问题,并不首先是它所带来的福祉,而是它所潜藏的危险。弗洛姆指出,现今“世界之所以成为一个统一的世界,那是就世界作为一个潜在的战场而言的,并非就它是一个世界公民的新体系而言”。在这样的时代里,“中国古典美学”何为?我们如何为日趋分裂的人类精神建构一个可以人类共享的感性精神空间?这是中国古典美学研究应当始终关心的一个课题。回答这个问题的前提就是,让“中国美学”变为“中国美学”。
中国美学的存在永远不是现成的,西方美学也不是。不然,今人做什么?美学“永远存在于解读与诠释之中。换言之,存在于建构之中”(戚国雄语)。此为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