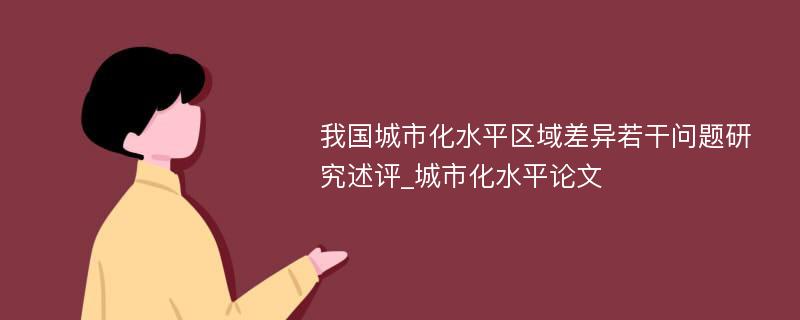
中国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异若干问题研究述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述评论文,中国论文,若干问题论文,差异论文,水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9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6547(2007)04—0009—03
城市化地区差异的研究,是以城市化内涵的确定和城市化水平测度指标的选取为基础的。鉴于中国城市化内涵界定的多样性和城市人口数量界定的多口径性,使得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问题成为一个颇难解决的问题。本文在对城市化内涵、城市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的多样性进行分析评论之后,对中国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异的相关研究进行了系统的归纳和梳理,并做出简要的评论。
一、城市化内涵的讨论
城市化一词的出现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然而,对于城市化内涵的界定,不同的学科和学者根据各自的研究范围和问题处理角度的不同,采用了不同的定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研究中国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异的文章中,不同学者根据文章采用方法的不同对城市化给出了不同的定义。许学强、叶嘉安在研究过程中没有明确提出城市化的内涵,但在计算中使用了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1] 刘耀斌、陈志、杨益明在研究中采用了《中国大百科全书·地理志》中城市化的定义。[2] 即城市化是人口向城市地区集中和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市地区的过程。文余源在分析了学界对城市化的不同定义后,提出了一种综合性的观点,认为城市化是一种综合的发展过程,包括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的过程、产业结构逐步升级的过程、城市文明向广大农村传播与渗透的过程以及农村生活行为方式、物质文化逐渐向集约高效转化的过程。[3] 张同升、梁进社、宋金平采用了城市化是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过程的定义。[4] 刘盛和在文章中没有明确提出城市化的定义,但是其在对城市化区域差异影响因素的因子分析中从人均GDP、人均工业产值、人均农业产值等等许多因子入手,[5] 可以看出,他也是采用了城市化的一种综合性的观点。
笔者认为,在研究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的过程中,城市化如何界定是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尤其在我国城市化的定义和指标体系纷繁复杂的情况之下更是如此。所以在研究的开始,文章至少应该用简明的语言阐述对城市化内涵的理解,在此基础上再开展地区差异的研究便会顺理成章,否则便会给读者造成一头雾水的情况。
二、城市化水平测度指标
城市化指标体系的选取对于计算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指标选取的不同可能会带来分析结果的不同。张同升、梁进社、宋金平对中国城市化水平测定方法做了一个研究综述。[4] 对于城市化水平的测度,学术界提出了多种方法(如庄林德;[6] 辜胜阻,简新华;[7] Zhang L,Zhao S X B;[8] 邹农俭;[9] 张耕田;[10] 代合治,刘兆德;[11] 王慧[12] 等提出方法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单一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两类。
1.城市化水平测度方法
单一指标法即通过某一最具本质意义的、且便于统计分析的指标来描述城市化水平。目前通常采用的指标为城市人口比重指标、非农业人口指标、城市用地比重指标。
复合指标法是考虑到城市化的内涵非常丰富,它不仅体现了一个地区人口性质的变化,还体现出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演变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只以单一指标来衡量城市化水平的方法存在一定的片面性。应该从城市化质量的角度出发,建立起一组指标体系,予以综合分析,力求较为全面准确地衡量城市化水平。[10、11、12] 综观国内外学者对复合指标法的研究可以发现,用该指标计算城市化水平时,程序是基本一致的,一般采用线性加权和法计算各地区的城市化水平,选取一组指标并且确定组内各指标的权重,计算城市化的综合值。由于不同学者所研究的地域不同,获取指标数据的难易程度也不同,因而选取的指标也各不相同,具体采用的计算方法也各种各样。[4] 国内学者张耕田、[10] 代合治、刘兆德、[13] 叶裕民[13] 等在这方面做了尝试。
在中国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异的研究中,许学强,叶嘉安在研究中运用了市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这一单一指标。[1] 刘盛和利用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以及相关社会经济统计资料,采用单一指标法进行研究。[5] 张善余主要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也是运用单一的人口指标法。[14] 刘耀斌、陈志、杨益明确定了城镇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和非农业从业人口占社会总从业人口的比重两个指标的复合来衡量中国区域城市化水平。[1] 文余源采用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模式,选取产业结构的城市化指数、人口城市化指数、现代城市文明指数和生活方式城市化指数4个一级指标以及相应的二级指标进行加权复合,得到某一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综合指数。[3] 王良建等采用单一指标法,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城市化水平。[14] 丁雪莲、董明辉采用了复合指标法,选择了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体系计算城市化水平。[15]
2.对城市化测度指标的评价
单一指标法中的城市人口比重指标是目前国际上比较通用的测度城市化水平的指标,相对而言,非农业人口指标和城市用地比重指标较少被运用。计算城市化水平并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在我国城镇人口定义发生多次变动的情况下,我国的城市化水平的计算成了一个人为制造的难以逾越的障碍。
1955年我国公布了第一个城乡划分标准规定,城镇人口包括设有建制的市和镇辖区的总人口(非农业和农业人口)以及城镇居民区的人口。当时市和镇的郊区较小,城镇人口中包含的农业人口只有15%左右,规定还是比较切合实际的。1963年规定城镇人口只计算设有建制的市和镇的非农业人口,不再包括农业人口,这种偏小的城镇人口统计口径一直使用到1982年的“三普”。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时重新使用1955年的标准,但是由于当时普遍推行的“整乡改镇”、“以镇管村”和“撤县建市”、“县并市”的行政措施,市、镇辖区范围迅速膨胀,使我国的城镇人口统计出现了数量上的超常增长。这时候我国有关城乡的概念和城镇人口的统计已完全失去实际意义。1990年的“四普”对城镇人口的口径做了修改,规定城镇人口由市人口和镇人口两部分组成。市人口是指设区的市所辖的区人口和不设区的市所辖的街道人口;镇人口是指不设区的市所辖镇的居民委员会人口和县辖镇的居民委员会人口。2000年的“五普”对“四普”口径作了一定程度的改善,即对设区的市原来偏大的统计予以收缩,对不设区的市和建制镇原来偏小的统计予以放大,使之趋向于可比。[15]
我国城镇人口定义的多次变动使得我国城市化水平的计算异常困难,特别是纵向时间分析变得似乎没有可比性,这也是单一城市人口指标法在研究中的最大缺陷。许学强、叶嘉安利用了1978年的数据(1963年城镇人口标准)来计算各因子与城市化的关系。由于没有涉及纵向的时间序列分析,没有对城镇人口的标准进行调整。[1] 刘盛和利用了第四次和第五次人口普查的资料,探析1990年和200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省际差异的形成因素。[5] 在研究中,文章借用区位商的概念弱化了“四普”和“五普”统计口径的影响,通过分别计算各省区城镇人口在1990年和2000年时相对于全国的区位商及其变化的方法来比较其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快慢。王良建等直接用“三普”、“四普”、“五普”和2003年各地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和统计年鉴中的有关内容计算各省市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14] 由于统计口径不同,使得城市化水平的可比性不是很强。
复合指标法是对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衡量,侧重对城市化质量的考察,通过多指标加权求和得到城市化水平的综合得分值。这一方法最大的好处是使得城市化的纵向分析变得可行。刘耀斌、陈志、杨益明在研究中以城镇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和非农产业的从业人口占社会总从业人口的比重两个指标的综合来衡量中国区域城市化水平,[2] 分别计算了1985、1990、1995、2000、2002五个年份的省区城市化水平实际值。文余源建立了更全面的城市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采用了4个一级指标和12个二级指标,加权求和得到城市化水平的得分值。[3] 文章计算了1996~2002年七年的城市化得分值,并进行了纵向的比较分析。丁雪莲、董明辉在计算湖南城市化水平时采用复合指标法,选取了20个指标计算湖南各市的城市化水平。[15] 然而,复合指标法也有一定的缺陷。在计算城市化水平得分值的时候需要对每个指标的权重进行人为的估计和赋值。人为赋值是具有很大危险性的,在研究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异成因的过程中有可能造成“原因解释原因”的窘境。刘耀斌、陈志、杨益明[1] 和文余源[3] 的研究都采用了人为赋值的方式。
单一的城市人口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在计算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缺陷。单一指标法无法进行纵向的比较和分析,复合指标法人为味道太浓。笔者比较认同周一星,于海波的观点,[16] 认为应该在“五普”口径的基础上确定城市人口规模。由于“五普”把城镇人口和乡村人口分别归为“市人口”(以建制市街道办事处为基本单元的城镇人口)、“镇人口”(以建制镇居民委员会为基本单元的城镇人口)和“县人口”(以村民委员会为基本单元的乡村人口)。在计算建制市地域的人口城镇化水平的时候,我们可以选取“市人口”加“镇人口”作为“城市人口”。我们可以利用“五普”的统计标准分别计算2000~2004年“市人口”和“镇人口”,也可以回推90年代的数据。这样我们就可以分析比较“纯自然”的城市化水平的变动趋势和地区差异。
三、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异测度方法研究
一般文章在明确了城市化的定义和取得城市化水平的得分值之后,便开始对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情况进行分析,并对差异形成的原因做出判断。
1.学者对城市化地区差异采取的研究方法
许学强、叶嘉安认为,我国城市化水平的省际差异是自然、政治、经济、历史等因素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综合作用的结果。[1] 文章利用1978年的资料,以各省的人口数、人口密度、土地面积和工农业总产值比例,以及人均工业产值、人均农业产值、人均国民总产值等来分别代表各省区人口和经济的特征,检验它们与城市化程度的省际差异之间的关系。
刘盛和利用第四次和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采用限定性再定量的研究方法,探析1990年和200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省际差异的形成因素。[5] 在定量分析中,文章选取了自然环境、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工业化或非农化水平等四类12个指标作为自变量。
刘耀斌、陈志、杨益明在构建区域城市化水平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后,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法从动态的角度,分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若干时期的省区城市化水平的主要影响因素。[2]
文余源在计算出城市化水平的综合指数后,利用锡尔(Theil)指数对城市化的区域差异进行了分解。[3] 通过数据计算和分析,文章认为中国城市化区域差异很大,区域城市化发展不平衡突出,区域差异明显。
丁雪莲、董明辉采用了主成分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方法,采用方差极大正交旋转法计算载荷矩阵,并用现行回归法求得主因子得分,从而得出城市化地区差异的主要因子。[15]
王良建等采用极差系数、极比系数、锡尔指数、标准差系数、变差系数和地理集中系数等,分别计算了东、中、西部的城市化相应的数值。[14]
2.对城市化地区差异测度方法的评价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许学强、叶嘉安、[1] 刘盛和、[5] 丁雪莲、董明辉[15] 在分析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异时才采用因子分析的方法导出影响城市化水平区域差异的主要因子。所不同的是,许学强,叶嘉安选取了7个指标作为自变量得出1978年影响中国区域差异的两个主要因子。刘盛和选取了四大类12个指标作为自变量,在对数值进行标准化之后导出了1990年和2000年影响城市化水平差异的主要因子。丁雪莲、董明辉确立20个指标计算湖南各地市的城市化水平。因子分析最大的优点是解释力强,通过计算得出主要的解释变量,而不是单纯地采用多元线形回归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一些主观因素的影响,但也存在着因子选取比较主观或遗漏较重要解释变量的可能。
因子分析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缺陷,就是它主要是基于自变量与因变量存在着线形关系,然而影响城市化水平趋于差异的众多因子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并不一定是线性关系。刘耀斌、陈志、杨益明[1] 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这一缺点。文章采用25个指标作为自变量,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进行分析计算。这种方法可在不完全的信息中,对所要分析研究的各因素通过一定的数据处理,在众多的随机因素序列中找出它们的关联性,发现主要矛盾,找出主要特征和主要影响因素,而不必基于解释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存在线形关系。
四、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1.2004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41.76%,人均GDP达10561元,城市化已经进入一个关键的发展机遇期,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问题已经成为当前城市化进程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如何正确分析、计算、评价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以及如何正确分离出影响中国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异的主要因素,成为城市化研究的当务之急。
2.如何正确测度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是个十分重要的问题,纷繁复杂的城镇人口统计标准使得城市化水平的研究成为一个人为制造的难以逾越的障碍,在研究中国城市化水平地区差异的动态变化的时候,究竟采用哪一种城市化指标,仍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我们应该寻找新的方法计算出各地区真实的城市化水平,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单一指标法和复合指标法。笔者比较赞同周一星、于海波[16] 计算城市化水平的方法。
3.目前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及其变动和差异的形成原因等方面,对成因的分析多采用因子分析和灰色关联分析等计量方法,在新方法创新上少有突破。另外,对如何改善中国城市化水平地区差距的研究少之又少,然而这相对来说显得更为重要。
4.如何看待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差异和中国城市化水平的地区差异?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一定关系?这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目前相关研究还十分鲜见。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部分研究成果,项目名称:走向2020年的中国城乡协调发展战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走城乡互动、工农互促的协调发展道路问题研究,项目批准号:05&ZD0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