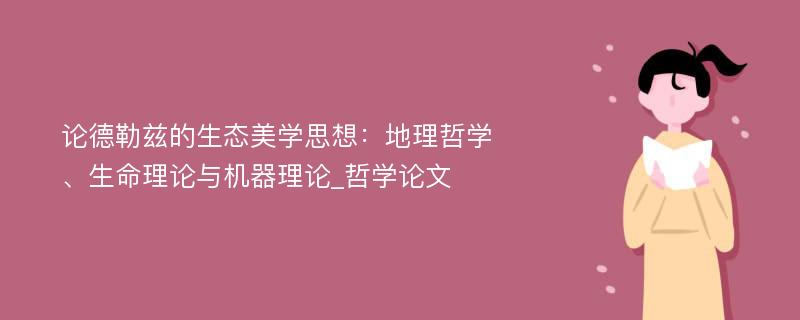
论德勒兹生态美学思想:地理哲学、生机论与机器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生机论文,哲学论文,地理论文,生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自1960年代美国女作家卡逊出版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寂静的春天》,中经1970年代罗马俱乐部提出“全球化”问题,到新世纪西方未来学家里夫金所倡导的“后碳”时代“第三工业革命”观念,宇宙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的博弈、平衡与和谐关系一直是当代哲学、美学、诗学、文学与科学等多学科的重大题旨。法国哲学家德勒兹在生态问题上体现出后人文主义的审美取向,特色斐然。本文拟从地理哲学、生机论美学与机器论诗学三个维度探讨德勒兹生态美学思想及其当代意义。
一、地理哲学:德勒兹大地观的意蕴
德勒兹是从哲学视角进入生态问题框架的。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哲学名著《千高原》《什么是哲学?》中,他们并不直接提“生态学”,而是称之为“地理哲学”(geophilosophy),大地是其中的核心概念。翻开《千高原》,可以发现与大地相关的“原”、“解辖域化”、“块茎”等概念俯拾皆是。加塔利个人还著有《三种生态学》(提出生物圈生态学、社会生态学和精神生态学)和《混沌界》等名作。德勒兹和加塔利多次强调的“新大地”概念甚至可视为其理论焦点和战斗口号。
国外德勒兹研究较为关注他们的地理哲学与生态美学思想。德国法兰克福大学赫尔佐根拉斯主编的《德勒兹、加塔利与生态学》(2009)从地理哲学、机器论、生态哲学、本体论、主体性、大地艺术、技术生态学、生态美学、政治、伦理、音乐、身体、风景、动物等多个维度或关联域阐发德勒兹与加塔利的生态哲学和美学思想。①德勒兹与生态问题研究的关系主要体现为:第一,尽管德勒兹并没有直接考察哲学与生态学原理之间的关系,在严格意义上或许不是生态哲学家,但他看待自然的方式重塑了关于基本哲学问题的观念,尤其是那些关于人类与非人类、自然与人为、有机体与环境、观察者与语境、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哲学观念。第二,尽管德勒兹没有直接参与生态伦理学的建构,但他却是生态哲学家,因为其思想具有生态伦理承载与审美价值取向。第三,尽管德勒兹显然不属于从事经验性研究的生态学家,但是他关于大自然的思想具有确凿无疑的生态学取向,其机器论促进了作为一种复杂的有机体—环境互动系统的自然观念。最后,德勒兹的整体观具有多元论、生成论的内涵,因为开放、动态、多元的世界无法简缩为一统天下的视野和封闭的系统,而是可以衍生出生态哲学和美学的千高原,生成新的聚合性,创造新的大地。
德勒兹与加塔利“千高原”的文化哲学观念启迪了罗纳德·博格“千面生态学”之思,他辨析了生态学(ecology)、生态哲学(ecophilosophy)和生态论(ecosophy)三种概念。在词源学意义上,生态学的希腊词源oikos意为“住宅、家庭财产、栖息地、自然环境”,“生态学”意指人类与非人类际遇的发生之地与互动环境,因此生态学关注有机体之间、有机体与无机体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方法论上是聚拢万物于一体的整体论;生态哲学的领域是研究生态学与哲学所共同面对的问题,是一种“描述性的研究”,不作出基本价值优先性的选择,而仅仅是结合生态学与哲学来考察某种特定的问题;生态论则从个人价值编码和世界观的角度关注人类与自然的问题。②德勒兹地理哲学的特征在于:传统“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将自然主体化,浅层生态学(shallow ecology)将自然客体化,而德勒兹的平台生态论(flate ecologics)则通过把'哲学主体'向非人类机器、情感、此性领域……开放而强化自然”。③德勒兹与加塔利既是“地理哲学”的理论家,又是“生态哲学”的实践者和创新者。马克·邦塔等人从地理学与哲学交叉学科视野提出:德勒兹是我们时代的康德。恰如康德的三大批判之于欧几里得空间、亚里士多德时间和牛顿物理学世界那样,具有特定的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的意义,德勒兹提供的哲学概念使我们的世界呈现复杂动态的意义。这个世界充满着碎片空间(曼德布洛特集合的分形、黎曼空间的“拼贴”)、扭曲的时间(系统接近阈限意义上的所谓的预期效应)和远离平衡态的热力学非线性效应。笛卡尔—康德框架为近两百年西方几乎所有的地理学探索奠定了基础,而德勒兹和加塔利的《千高原》则是创建当代地理哲学的关键著作,具有多维度效用,它熔铸了康德对地理科学重要性的强调和笛卡尔绘制新制图学的努力,可视为一种新唯物论的地理学范式。德勒兹的差异哲学和复杂性理论一道,可以用来对大地进行重新思考。④
概言之,德勒兹地理哲学关涉复杂性空间(如光滑空间、条纹空间)和运动图式(如辖域化、解辖域化、再辖域化)和美学观念(如游牧、流)。德勒兹曾对数学上的黎曼空间加以解释并且将其运用到现代电影研究领域。⑤德勒兹和加塔利在《什么是哲学?》第四章以“地理哲学”为题,讨论各种庞杂的问题,进行了天马行空式的生态美学的思想游牧。
在西方生态批评和环境美学理论中,大地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生态批评是关于文学与物质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恰如女性主义批评从社会性别意识的视角考察语言与文学、马克思主义批评把生产方式与经济阶级观念带入其文本阅读那样,生态批评把一种以大地为中心的理论方法(an earth-centered approach)用于文学研究。”⑥而在德勒兹地理哲学中,“大地”(Terre)概念占据了核心位置。
马克·邦塔等合著的《德勒兹与地理哲学》(2004)和阿·帕尔主编的《德勒兹词典》(2005)专门设置了“Earth/Land”辞条,他们认为:在《千高原》英译本中,译者使用两个英语词Earth/Land来翻译法语Terre一词,因为这个法语词既指天文学意义上的星球“地球”(Earth),又指地理学意义上属于文化训育的“土地”(Land)。前者主要是一种充满生成力量的光滑空间,而后者则由超编码的辖域构成,囿于意义域和国家机器,专属条纹空间,可以拥有、分配、租赁,用于生产、纳税……⑦这种语际辨析,有助于我们理解德勒兹地理哲学深邃微妙之处。汉语“大地”一词的意蕴,似乎更吻合于法语Terre。
德勒兹地理哲学的大地观可以大致归纳为几点:其一,大地是一致性的虚拟平台,是可以生成万象的光滑空间;其二,大地是辖域系统的组成部分,是博弈、竞争、辖域化的条纹空间;其三,指“新大地”,是强度的虚拟生成和“宇宙力量”的叩击。
二、生机论美学:大写而流变的生命
在语言学意义上,生机论(vitalism,或译“活力论”)是“一种认为生物的机能和活动产生于物理学和化学均无法解释的生命力的理论”,其名词形式vitality的释义是“生命力、生机、活力、生动性”等。⑧德勒兹的研究者很早就关注其生态美学中的生机论思想。约翰·马克斯《吉尔·德勒兹:生机论与多元性》(1998)认为生机论是德勒兹美学的重要维度之一,“内在观是德勒兹超验的经验论核心,包含生机论与多元性”,纯粹的内在性是大写的生命。⑨德勒兹本人在哲学访谈中曾言,“符号、事件、生命、生机论之间有着深刻的联系。这是一种非有机生命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存在于绘画的线条、文学的陈述和音乐的乐句里……我写的一切都是主张生机论的”。⑩生机论关注生命的存在方式和活力,具有重要的哲学和美学维度。黑格尔曾经提出“生气灌注”的美学概念,其含义为:(1)主体的自由体现在自然形象中;(2)自然形象的各组成部分在主体性的作用下融化为一个有机统一的生命整体。(11)一般辞典意义上的生机论解释和黑格尔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的二元论古典美学,在德勒兹这里有了重要的、革命性的发展。德勒兹的生机论充盈着迥异于黑格尔美学的特征。
德勒兹生机论敬畏宇宙大化的力量和公正无私,关注有机生命或非有机生命力量的存在,强调流变与差异的丰富生命形态。德勒兹的形而上学之思“强烈地聚焦于内在性(对峙超验性)、生产(对峙再现)、物质性(对峙语言)”。(12)黑格尔主客二分(主体精神灌注自然客体)、内外辩证(理性内容与感性现象的有机统一)的美学模式,在当代西方哲学,尤其是在德勒兹生机论美学这里遭到扬弃,从而嬗变成为以内在性为基础,蕴涵着丰富复杂的差异性、多元性、流变性的模式。德勒兹差异哲学对在二元论中处于宰制性地位的主体性加以解辖域化,从而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其生机论昭示着浩瀚的宇宙因纷繁多姿的生命形态而呈现出多元流变、互动博弈的美学景观。
从哲学和美学渊源来看,德勒兹的生机论主要受到柏格森、斯宾诺莎、尼采与福柯的影响。柏登斯《撒哈拉:德勒兹美学》(M.Buydens,1990)认为德勒兹生机论主题首先源于柏格森的直觉主义美学,柏格森曾把“élan vital”(生命冲动,一译生命之流)描绘为一种规避分析的“生成”(becoming)的形式。德勒兹认为柏格森之于哲学有如维吉尼亚·伍尔芙或亨利·詹姆斯之于小说,雷诺之于电影。柏格森生机论的美学旨趣在于:多元、绵延和运动。受此影响,德勒兹生机论呈现为流动的、块茎式的多元结构。斯宾诺莎也启悟了德勒兹生机论中的流变思想。德勒兹在斯宾诺莎语言理论那里发现了“流……语言作为内容和表达的持续流系统”的特征;他欣赏斯宾诺莎伦理学有如一股喷涌而出的激流,“一些断裂、独立、相得益彰、产生强烈效果、构成一种断裂火山山脉的'支节'。”(13)在关于尼采—福柯—德勒兹的思想关联域中,可以看到尼采永恒回归论、系谱学、强力意志论和福柯权力话语的影响。德勒兹认为,尼采与福柯表达了“某种生机论”——“当权力成为生物—权力时,反抗成了生命权力,即与生命有关的权力”,“来自外部的势力难道不是福柯思想达到顶点的某种生命观和生机论吗?生命难道不是反抗势力的能力吗?……福柯与尼采在这一点上并无二致”。(14)正因为德勒兹生机论以尊重多元生命形态与物质存在为旨归,因此他倡导社会文化生态和自然生态的和谐互惠、互动流变,甚至表达了“耻为人类”(shame at being human)的思想。
这种“耻为人类”的生机论题旨蕴含深刻,体现出关注社会文化生态的政治批判性与尊重自然生态多样性的美学观,包含了生态美学的两层蕴含:社会文化生态层面的反法西斯主义;大自然生态层面的反人类中心主义。
第一个层面反映了德勒兹在西方社会文化背景下所进行的哲学思考。当代欧洲哲学与美学一直在为“奥斯维辛”的幽灵所萦绕。德勒兹认为:纳粹和集中营玷污了人类,资本主义市场化、商品化时代的价值观念、理想和舆论同样使我们感到做人的耻辱。“我们并不觉得自身超越于我们的时代之外,我们不断地同它作出种种可耻的妥协。这一羞耻感正是哲学的最强大的动力之一。”(15)在某种意义上,斯宾诺莎的哲学肖像赋予了德勒兹生机论以伦理与政治色彩。斯宾诺莎关于为什么人们易于甚至乐于屈从禁锢生活的力量、受制为奴问题的探讨,激活了德勒兹关于压迫、灾难、奴役、微观法西斯主义的思考,并且反映在福柯关于德勒兹/加塔利的《反俄狄浦斯》的著名序言之中:德勒兹提醒人们,不仅要反对外在的、硕大无朋的法西斯主义,更要警惕每一个人内心深处的微观法西斯主义欲望。德勒兹深刻地质疑全球资本主义秩序中金钱公理化、贫富差距扩大、人性扭曲的倾向,因此,“耻为人类”的话语挑战西方志满意得的“社会民主”价值,(16)锋芒指向文化政治生态层面的法西斯主义意识与心理机制。
第二个层面反映了西方后现代哲学后人文主义的理论维度。美国学者吉尔兹曾经把提出“人之死”的福柯称为一个反启蒙的启蒙学者、反历史的历史学家,反人本主义的人文科学家,反结构主义的结构主义者。约翰·马克斯则认为:德勒兹的生机论是与他的“反人本主义”(anti-humanism)观念相关联的。从古希腊哲人的“人是万物之尺度”到莎士比亚《哈姆雷特》“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西方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的人本主义脉络和贡献不容抹煞,在挑战西方中世纪神本主义思想专制统治和矫正近代以来工具理性主义偏颇等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如果从当代生态美学的视野审视“人本主义”,则易于揭示其隐匿的“人类中心主义”理论陷阱。人类是目前进化程度最高的生物,但神奇的生命进化史难保不会出现问题:焉知日后没有更为高等的新生物取代人类成为新的“中心”。(17)哲学意义的二元论往往隐含等级制、中心主义特征,对立的二元项大都不是平等关系,如人类与自然、中心与边缘、男性与女性、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等,其中一元会宰制性地压倒另一元,若单纯强调后者对前者的颠覆,则并未突破二元论的逻辑陷阱,改变中心主义的属性。在当前的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的讨论中,究竟是“人类中心”还是“自然中心”的辩说颇为流行,难以脱离对立性二元论思维的窠臼。而按照德勒兹的多元论、生机论生态美学思想,人与自然万物之间、艺术与世界之间是一种连续性的生命流(flux),无所谓谁是中心,而是一种多元互动、生成流变的生态关系。德勒兹的生机论美学据此否弃人类中心主义,颇为重视动物、植物等非人类实体的生命体悟或功能,其褶子论、生成论皆是重要的理论支撑。例如,德勒兹认为褶子是宇宙存在方式和生成形态。万象的打褶与展开褶子(fold-unfold)意味着生命意义的丰富形态,包括生命全息、进化和退化、异质和异形等生态变化,并导致德勒兹思考主体性生产和非人类形式问题。
德勒兹的生机论美学启迪人们突破人类中心主义和主客二分的传统模式,把人类与非人类(动植物、无机界)的空间与关系构想成为互为依存、彼此链接的生态圈和生物链,互动共生,不可或缺。植物—食草动物—食肉动物—人类构成的不仅是弱肉强食的食物链,更是互相依存的生态链乃至生态圈。在特定情况下,包含人类在内的生物多样性形态可谓“牵一发动全身”,俱损俱荣。非洲草原上的掠食动物狮子居于生态链的顶端,威风凛凛,但是它们必须依赖猎杀食草动物如角马、羚羊、斑马等才能生存和繁衍,而食草动物又必须靠动物世界之外的植物世界草木繁茂才能种群庞大,满足生态需要。狮子貌似是中心,可一旦天气变化,草木凋零,整条生物链就会受到影响,甚至断裂,从而使得狮子中心主义瓦解。因此,这不是谁为中心的问题,而是生物链、生态群、生态圈的问题。
三、机器论诗学:大地艺术的链接与装配
《德勒兹、加塔利与生态学》一书首页从后现代理论语境提出一个饶有兴趣的测试题:若言及“后现代主义”,那么你会说什么?或许会说“解构”或“作者之死”;而“大自然”一词几乎不可能出现。因为在后现代主义那里一直是“大自然”的艰难时世。福柯、德里达、拉康、巴特勒的理论往往将自然本身的物质性遮蔽,或用文化、语言和社会的话语将自然加以边缘化。如福柯关注的是权力话语而不是自然的物质性;拉康的鲍罗密欧结(The Borromean Knot)的想象—象征—真实三种秩序扑朔迷离,其中并无大自然的一席之地;巴特勒的社会性别表演论终究不过是文化与语言的构成论。耐人寻味的是,该书紧接着又提出了另一个测试题:若言及“德勒兹”,那么你会说什么?或许那个嗡嗡作响的词会是“机器”,尽管也可能有其他选择,如“块茎”一词已暗示了在德勒兹和加塔利的著作中某种“生态铭记”。(18)这意味着在德勒兹生态美学思想中,“机器论”(machinism)具有核心意义。
美国杰出的生态社会学家康芒纳(Barry Commoner)认为:生态学的第一律则是万物皆关联。这个看法很适于阐释德勒兹的机器论与生态学的关联域,德勒兹差异哲学将宇宙视为千重平台,具体的万物万象皆处于具体机器与内在抽象机器(an immense Abstract Machine)川流不息的链接与联系之中,具有不断生成新质或新空间的可能。德勒兹和加塔利在《反俄狄浦斯》第一章“欲望机器”生动地描述了这种作为关系概念的无所不在的机器及其装配功能:
机器到处都在运作……它呼吸,它发热,它吃喝。它拉屎和性交。言说那种本我(the id)是多么的荒谬。到处皆是机器——真实的机器,而不是比喻的机器:机器驱动着其他的机器,机器被其他的机器驱动着,伴随着必然的搭配与联系。(19)
这种抽象机器,显然不是纯技术的工业制造的机器,而是一种哲学与美学的链接与装配观念或机制。人类与大自然充满了无数的这样的具体机器,它们不断地进行着组合、装配、生产。例如人的嘴巴就是一个小型机器,装配功能多样化,可以说话、呼吸、吐痰、吃喝、接吻、口交、表演,在不同的境况中呈现出不同性质的搭配(如婴儿的嘴巴与母亲的乳房)、联系与意义(如情侣接吻与爱情)。具体的机器是小写的、可数的、形而下的存在,而内在的抽象机器则是大写的、不可数的、形而上的存在。这种抽象机器是内在性的平台,是无器官身体,蕴含着自然界虚拟的潜力和伟大的生成力量。在这个动力学机器系统中,自然与人为、人类与非人类等关系界限变得模糊,“整个世界是由各式各样的机器组成的,例如自组织的机器、秩序与静态的机器、动态机器、生物学机器、还有话语与文化机器……自然界犹如一种内在的抽象机器……其片段是各式各样的装配与个体,它们每一个都群聚在一起,形成粒子的无限性,进入一种或多或少互相联系的无限性”。(20)德勒兹生态哲学意义上的机器论,以联系与生成为特征,包含属于同一连续性的文化与自然两方面,是理解世界作为开放性生态系统的复杂机制的理论。这就是不在人类与非人类系统二元模式内进行基本的区分,而是强调人类生成他者,生成动物,生成无感知,促进生物多样性和多元之美,德勒兹机器论由此避免了技术欣快症和技术厌恶症,体现出创造“新大地”的诗意特征。
由此,德勒兹机器论可视为一种哲性诗学,“新大地”的概念则蕴含着人类创造性与物质系统潜力之间的新型耦合,是艺术创造的新潜力的表征。由此审视当代西方大地艺术(earthworks or landart),可以略窥其生态美学的特质之一斑。
在20世纪欧美艺术界,一些醉心自然、富于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不满于传统艺术表现手法和商业化的艺术实践,走出画室与艺术堂馆,以广袤大地为艺术作品的载体,依靠自然环境和风土结构创作巨型艺术品。这些与大地水乳交融的艺术作品被称作“大地艺术”。大地艺术可以分成场地作品(Sites Work)和非场地作品(Non-Sites Work)两类:前者是在特定的户外空间(通常是废弃的工矿或与世隔绝的自然角落)运用原始的自然材料所创作出来的作品。后者是通过影像拍摄和记录,将这些作品和少量实地材料(如泥土、石块、瓦砾等)移至艺术场馆展览的作品。人和自然的关系是人类历史中最强烈的文化表现形式,因此与地球环境密不可分的大地艺术可以给观者带来震撼人心的神秘感和神圣感。(21)美国大地艺术家史密森(Robert Smithson,1938-1973)的代表作“螺旋形防波堤”(Spiral Jetty)享有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品之一的盛誉。(22)这件艺术巨制于1970年4月用黑礁石、泥土、盐晶体等自然材料,在美国犹他州大盐湖完成,以重达6600多吨的黑色玄武岩堆砌而成,螺旋长500米,宽约5米,直径50米,呈现出逆时针的螺旋形几何图形,从天空鸟瞰,宛如湖畔延伸出的巨蛇的卷曲尾巴。史密森的“螺旋形防波堤”是一件石破天惊的作品,几乎就是大地艺术的代名词,它嵌入大地,挑战传统的画廊艺术范畴,其自然材料的色彩层次丰富,蛇形的几何图形犹如通向神秘天穹的人类符号。这件里程碑式的大地艺术作品为他赢取了国际声誉,它既是象征某种昔日文明精魂的伟大纪念碑,又在概念和制作上充盈着当代艺术创新精神。沧海桑田,空间变幻,时间川流不息,无论是人类的活动还是艺术创作都将终归尘土,这种宏阔的思想空间,必须由大地艺术才能更好地呈现。
在德勒兹机器论诗学意义上,艺术是一种抽象机器,也是美学机器,大地艺术“螺旋形防波堤”堪为佳例,呈现出人类文化艺术与自然环境链接和装配的“新大地”景观。这种艺术与大地交融的巨型实景杰作,利用多种自然材料来艺术重构宇宙间的神秘螺旋形,远离都市,坐落于苍凉的湖泊山野,往往处于人迹罕至之地,从而打破传统的观赏旨趣,具有新的审美意蕴和非商业化的属性,充分利用艺术家自由创造的光滑空间,不易成为充满规训的条纹空间,听凭他人占有、分配、租赁和近距离玩赏,反映了自塞尚以来艺术家关于自然与艺术之源的沉思。艺术对大自然感性力量的物质化是通过机器而运作的。这不仅指“螺旋形防波堤”使用具体机器如自倾货车、推土机来营建,而且还因为这是抽象机器的链接与装配。德勒兹机器论认为人类艺术与自然生态并非是彼此对立的,而是宇宙抽象机器(同一连续性)中异质元素的互相链接、嵌合,并且生成新质或“新大地”。艺术家借重造化之功,融天地之精华,在光滑空间与条纹空间的张力中,对大自然和传统室内艺术进行双重的解辖域化,生成人心与自然耦合的艺术强度,体现出大地力量的聚集、艺术机器的强度装配和“宇宙力量”对心灵的巨大叩击力。
在欧美大地艺术中,热寂论的“熵”(entropy)是一个重要议题。史密森曾著有《熵与新纪念碑》(Entropy and the New Monuments),螺旋是最让他着迷的图案,充分体现了宇宙中熵的概念。史密森终其一生,都在持续挑战熵这个关涉颓败与新生、混沌与有序、自然与文化的主题。在艺术、人类与自然的三维关系中,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千高原》中把艺术视为一种抽象机器,认为艺术能够与熵的混沌耗散作斗争。
在“热寂论”意义上,“熵定律是自然界的最高定律”,熵指体系的混乱的程度,它在控制论、概率论、数论、天体物理、生命科学等领域都有重要应用。熵的概念由克劳修斯(R.Clausius)提出并应用于热力学;香农(C.E.Shannon)则将熵的概念引入到信息论中来。(23)在理论上,当代美国著名社会学家里夫金和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对熵作了精辟的描述:宇宙的能量总和是个常数,总熵是不断增加的。热力学第一定律就是能量守恒定律,虽然能量既不能被创造又不能被消灭,但它可以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如一块煤烧掉后,能量并没有消失,而是转化了,随着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一起散发到了空间。虽然燃烧过程中能量并没有消失,但我们却再也不能把同一块煤重新烧一次来做同样的功了。如果我们需要考虑的仅仅是热力学第一定律,那我们滥用那万世不竭的能源也没有什么奥妙了。热力学第二定律解释了这个现象。它告诉我们每当能量从一种状态转化到另一种状态时,我们会“得到一定的惩罚”。这个惩罚就是我们损失了能在将来用于做某种功的一定能量。这就是所谓的熵。熵的增加就意味着有效能量的减少,被转化成了无效状态的能量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污染。许多人以为污染是生产的副产品,但实际上它只是世界上转化成无效能量的全部有效能量的总和。耗散了的能量就是污染。既然根据热力学第一定律,能量既不能被产生又不能被消灭,而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能量只能沿着一个方向——耗散的方向——转化,那么污染就是熵的同义词。“机械论世界观以持久的物质增长为出发点,而熵的世界观则以保存有限资源为思想基础……非再生能源时代的结束,注定工业时代也要结束。当非再生能源储存告罄,以其为基础的全部经济上层结构便将开始土崩瓦解。”(24)有鉴于此,美国学者里夫金的未来学新著《第三次工业革命》(2011),(25)推进关于熵问题的思考,认为人类已经步入“后碳”时代,根本出路在于把互联网技术与可再生能源相结合,形成全球共享网络,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德勒兹作为生态哲学家,对耗散结构中的熵问题的思考别具一格。泽帕克在《生态美学:超越罗伯特·史密森、德勒兹和加塔利作品的结构》一文(26)中,用砂漏(sandbox)的意象与熵的关联性来论析史密森的大地艺术,认为时间元素居于史密森艺术作品的中心,时间视野的永恒性与史密森大地艺术的熵主题发生共振。史密森曾言“最终的纪念碑是砂漏”,砂漏以衰变为原理,是熵的隐喻。在作为熵的大自然中,一切存在犹如恒河沙数,白骨与石头在时间的流逝中化为尘埃,形成巨大的历史沉积。粒粒尘沙,皆为死亡之喻,与永恒等值。熵是一种完全超越结构主义对位法的自然力量。一旦熵把场地艺术与非场地艺术皆化成尘埃,一旦熵主宰了时空边界,则那种虚拟的与遗传的结构就崩解了。面对史密森这类关于熵的线性时空观和耗散结构论,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进行了思想反拨,他以尼采永恒回归论驳斥关于熵“末世论”幻象,认为熵只能解释现实世界发生的事情,而无法解释“另一种秩序的众多事物”,如艺术哲学与生态美学,再如地球气候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循环系统。诺贝尔奖获得者薛定锷(E.Schrodinger)等科学家曾经指出热寂论之谬误在于滥用物理定律,把经典热力学中关于熵的概念拓展成为宇宙万象的热寂论。
围绕着熵的主题,自然科学领域呈现出“热寂论”与“热环论”之争。德勒兹的这种思想反拨,是具有热环论特征的生态哲学回应。所谓的热寂,指宇宙的所有物理活动都是朝着热动平衡的单向变化过程——最大熵状态耗散发展的,这一过程称为宇宙的热寂,也就是宇宙之死。所谓的热环,指任何星体与太空间都存在着相反的热循环转移过程,这是宇宙生机勃勃、持续发展、永不死寂的真谛!鉴于此,泽帕克从德勒兹研究的角度指出:“螺旋形防波堤”是大自然平台的制图学,一种从熵的解差异中浮现的致幻景观,充盈着鲜活的感觉。
从马克思主义美学角度看,德勒兹是宽泛意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他认为一切皆生产:生产力与反生产力、生产与再生产、熵与负熵构成复杂的张力与强度。他的机器论直接引申自马克思的机器理论。马克思认为机器的出现作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标志着生物政治学的开端,因为异化就是活的劳动者被机器资本主义所僭越和扭曲。循着马克思对劳动价值基础的思考路径,德勒兹和加塔利把对技术机器关注转移到对社会体或社会机器的关注,揭示资本主义对人的原初精神压抑与社会压抑的双重机制,并称之为“俄狄浦斯”异化。一般认为,史密森《螺旋形防波堤》等大地艺术名作的旨趣在于耗弃的矿场所体现出的熵的热寂论主题,警醒人们回归大地生产的“原始过程”。而在德勒兹哲性诗学的视域中,史密森大地艺术名作尝试将资本主义机器转化成美学机制,并非是意在回归“大自然”,而是转向美学意义上的熵的工业生产。因此可以把史密森的作品视为创造未来的一种方式,体现出“热环论”的主题。这是尼采“永恒回归”和德勒兹“重复与差异”美学思想的回响:没有毁灭就没有创造。大地艺术是对已然热寂毁灭的工业生产废墟的一种艺术生产的重复,重复体现出差异。经由这种艺术和美学范式的再生产,可以警醒人类调适物质生产与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德勒兹著名的重复与差异的哲学命题由此将大工业时代的热寂论主题转化为全球化时代热环论的生态美学题旨。史密森的大地艺术与德勒兹的生态哲学之间既存在断裂带,又构成了社会生产与艺术生产的新型张力。一旦跨越这种断裂带,理解了不同生产方式的重复与差异的张力,我们就可以看到:大地艺术将自然荒野和工业废墟转换为生态美学,从而体现出人类创造性与物质系统潜力之间的新型耦合,表征了德勒兹倡导的“新大地”美学图式或面向开放性的新未来的思想取向。
注释:
①Cf.Bernd Herzogenrath,Deleuze/Guattari & Ecolog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9,pp.1-4.
②参见Ronald Bogue,A Thousand Ecologies,in Deleuze/Guattari & Ecology,pp.42-55。
③John Marks,Gilles Deleuze:Vitalism and Multiplicity,London:Sterling,Pluto Press,1998,p.11.
④参见Mark Bonta and John Protevi,Deleuze and Geophilosoph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4,vii-viii。
⑤参见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140页。
⑥Cf.Bernd Herzogenrath,Deleuze/Guattari & Ecology,p.2.
⑦Mark Bonta and John Protevi,Deleuze and Geophilosophy:A Guide and Glossary,pp.80-81; A.Parr ed.,The Deleuze Dictionar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5,pp.80-82.
⑧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第2126页。
⑨John Marks,Gilles Deleuze:Vitalism and Multiplicity,p.30.
⑩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第163页。这里对译文有微调。
(11)参见蒋孔阳主编:《哲学大词典·美学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1年,第211页。
(12)Bernd Herzogenrath,Deleuze/Guattari & Ecology,pp.9-10.
(13)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第24、188页。
(14)参见吉尔·德勒兹:《福柯·褶子》,于奇智、杨洁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98页。
(15)参见吉尔·德勒兹、菲力克斯·加塔利:《什么是哲学?》,张祖建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7年,第352—354页。
(16)John Marks,Gilles Deleuze:Vitalism and Multiplicity,p.28.
(17)18世纪英国小说家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曾经塑造了智马“慧骃”的著名形象以反讽“耶胡”式人类。前国际美学协会主席穆尔《赛博空间的奥德赛》(2007)曾经讨论电子传媒与后人类形式的问题。
(18)参见Bernd Herzogenrath,Deleuze/Guattari & Ecology,pp.1-3。
(19)参见Deleuze and Guattari,Anti-Oedipus: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0,p.1。
(20)Bernd Herzogenrath,Deleuze/Guattari & Ecology,pp.4-5.
(21)参见《大地艺术在景观中的实践》http://www.dreagon.com.cn/ddyszjgzsj.htm,2010-7-6查阅。
(22)参见关于史密森和大地艺术家群体的介绍,可浏览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1938-1973)的网站http://www.robertsmithson.com/introduction/introduction.htm。
(23)http://baike.baidu.com/view/936.htm?fr=ala0_1_1,2010,7,13。
(24)里夫金、霍华德:《熵:一种新的世界观》,吕明、袁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167—168页。
(25)参见杰里米·里夫金:《第三次工业革命——新经济模式如何改变世界》,张体伟、孙豫宁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年。
(26)Stephen Zepke,Eco-Aesthetics:Beyong Structure in the work of Roberte Smithson,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in Bernd Herzogenrath,Deleuze/Guattari & Ecology,pp.200-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