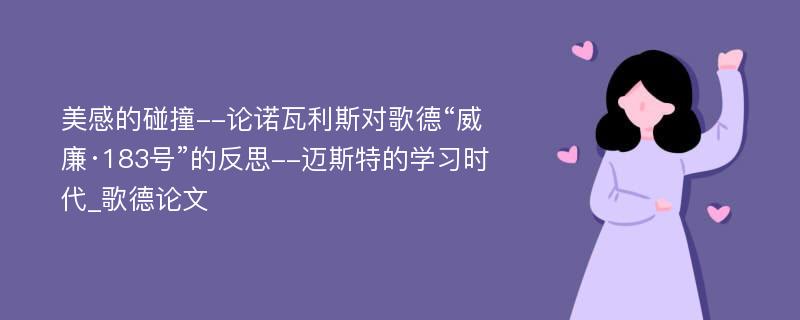
审美感知的碰撞——评诺瓦利斯对歌德《威廉#183;迈斯特的学习时代》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歌德论文,斯特论文,威廉论文,利斯论文,时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10)06-0044-10
18世纪末,德国文学进入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发展时期,伴随着古典主义的兴盛和发展,以反思启蒙运动为主要宗旨的浪漫派文学异军突起。在一个可谓百家争鸣的文学氛围中,古典主义与浪漫派之间形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年轻一代浪漫派作家对歌德的长篇小说《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以下简称《学习时代》)的接受上。无论是褒扬还是批评,都说明了这部被誉为德国“成长小说”(Bildungsroman)典范的长篇大作,给新生代所带来的强烈影响和深刻思考。早期浪漫派代表人物F.施莱格尔甚至把歌德的这部小说与法国大革命和费希特的“知识论”一起,视为“当代最伟大的三种倾向”。(F.Schlegel,1979:366)而同为早期浪漫派代表人物的诺瓦利斯则对此持批评态度,尽管他开始也加入了对浪漫派赞美的行列之中,并视歌德为“当今世界上诗学精神的真正化身”。(Novalis,1989:318)但是热情的赞许不久便转化成了尖锐的批评,在潜心研究了这部小说以后,诺瓦利斯认为《学习时代》不过是一个“诗化了的市民和家庭故事”,(Novalis,2000:226)他要与之相对,决定写一部自己的小说来表现不同的诗学认识,这部小说“或许包含着一个民族的学习时代”。(Jens:531)诺瓦利斯因此而创作的小说,就是他未竟的传世之作《海因里希·封·奥夫特丁根》(以下简称《奥夫特丁根》)。
从此以后,无论在文坛上还是在评论界,《学习时代》和《奥夫特丁根》似乎成了不可或缺的对立参照物。在对《奥夫特丁根》的研究中,大都停留在小说创作层面上来认识,认为诺瓦利斯自觉地接受了歌德这部小说的影响,把它当作自己从事小说创作的对立面,“在形式上模仿歌德的成长小说,在内容上却反其道而行之”,从而创作了一部“反《迈斯特》小说”。(范大灿:110)当然,歌德这部小说对浪漫派作家的影响是不可否认的,然而他们的接受绝对不仅仅停留在对小说认识的范围内。诺瓦利斯对歌德小说的批评是对传统的审美意识的挑战,具有更为广泛的针对性,《奥夫特丁根》是其追求新的审美主张的必然实践。如果说古典主义时期的歌德立足于现实主义的审美原则,完全采取启蒙理性的认识模式,力图使主人公迈斯特在实实在在的现实人生经历中成长为完美的人的话,那么诺瓦利斯则是要以理想主义的审美原则克服歌德的时代现实主义,超越《学习时代》这个“理性的产物”,(Novalis,1989:475)在充满幻想的诗意世界里去追求“蓝花”的神奇和美妙,去追求无限的彼岸。歌德的审美感知是现实的,而诺瓦利斯的审美感知是浪漫的。
审美感知的冲突:诺瓦利斯与歌德
18世纪末,歌德已经成了蜚声文坛的大师,而诺瓦利斯才崭露头角。虽然他们有过几次短暂的见面,但由于文学取向不同,他们之间难以形成真正的交往和深层的交流。
众所周知,经历了狂飙突进的歌德坚决反对文学主体化倾向,称其为矫揉造作,从而走上了古典主义的创作道路,其诗学原则一反青年时期个性和情感的张扬,主张表达情感、和理性的和谐,以典型化来对抗个性化。在这种诗学观念中,现实是文学创作的基础,个别或特殊的东西中隐含着普遍的东西、体现着整体的东西,并且因此赢得了道德、精神和教育的责任。审美的程序化成为新的审美模式。
而在同一时期产生的德国浪漫派,其诗学观的指向是很明确的,那就是反对艺术对现实世界的绝对依赖、尤其是把道德和理性当作感觉和主观的规则。浪漫派作家们既不赞成启蒙运动的理性独尊,也不赞成狂飙突进无限张扬个性自由的狂热,同样也不认同古典主义主张的理性与情感的和谐。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费希特的哲学思辨方法,奉行的是二元对立的认知模式,即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和变化原则。A.W.施莱格尔批评启蒙运动由理性所决定的实用主义思想限制了人的一切超越逻辑的感觉,他强调事物的双重性,即光明与黑暗、可理解性与不可理解性、有限与无限的对立关系,特别是世界混沌而神秘的一面应该成为浪漫艺术关注的焦点。(A.W.Schlegel:22-55)诺瓦利斯在其早期的断片中就区分了自然诗和人工诗(Natürliche und Künstliche Poesie),其中人工诗服务于确定的理性逻辑和“一定的意图”,而自然诗则不受任何限制,这才是真正的浪漫主义和诗人应当追求的方式。(Novalis,1981:393)浪漫派理论家F.施莱格尔把“浪漫文学”看成是“动态的万象文学”,这种文学包罗了一切文学类型和存在领域,始终处在变化中,永远也不会终结。如果说迄今的文学都追寻着一定的表现意图的话,那么诺瓦利斯则同其他浪漫派作家一样,在无限中看到了一切文学的目的。他把文学不再看作是对世界的模仿,而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主体的产物。诺瓦利斯的审美意识赋予小说创作以独立的地位和空间,把艺术主体的想象力和美的独立性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对他来说,文学艺术应当脱离传统的规则,抛弃所有模仿、再现和实用的观念。由此可见,诺瓦利斯的诗学意识与歌德的美学理念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他们的审美感知必然是对立的。可以说,在批评歌德的《学习时代》和创作《奥夫特丁根》时,诺瓦利斯立足于已经确立的审美感知基础之上,始终以歌德这部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小说为参照,要表明的是一种与古典主义不同的新诗学观念,而《奥夫特丁根》正是这种诗学理念最集中的体现。
当然,由于两人截然不同的诗学取向,他们对于所谓“古典的东西”(das Klassische)和“浪漫的东西”(das Romantische)这两个核心概念大相径庭的认识,也表明了他们在审美感知上不可避免的对立。诺瓦利斯认识世界的基础就是内化式的“浪漫化”原则,但他并不拒斥理性、纯粹向往神秘的黑暗。他把理性同样看作是自我完善能力的基础,因为对他来说,“理性是最值得播种的——它为我们指明道路”。(Novalis,2009:276)他只是坚决反对纯粹用理性决定一切的方式来解释世界。诺瓦利斯认为,“我们还不了解我们精神的深处——神秘之路是通向内心的”。(Novalis,1989:298)从这种个性化原则出发,他提出了自己诗学的核心思想:“这个世界必须浪漫化。只有这样,人们才会找到本原的意义……所谓浪漫化,那就是自我给普通的东西赋予崇高的意义,给平凡的东西披上神秘的外衣,使熟悉的东西获得未知的尊严,给有限的东西以无限的表象。”(Novalis,2000:51)诺瓦利斯的“浪漫化”,就是要让个性去认识自身内在的秘密和诗的力量,在内心世界中寻找外部世界的“本原意义”,这无疑构成了诺瓦利斯审美感知的核心。在他看来,人本身就是充满神奇的秘密王国,理解自己就是理解世界,而外部世界杂乱无序,像一个阴影世界。诗走向内心就是要让人预感到一个无限的领域,以及超理性和超经验的东西,而理性所捕捉到的外部世界只是经过概念和逻辑过滤过的、毫无神奇可言的东西。因此,诺瓦利斯在他的断片中多次强调要以诗来呼唤读者批评的判断能力。正因为如此,诺瓦利斯把“浪漫化”的诗看成是个性化的、有创造力的,而“一切古典的东西都是非个性化的”,都是经过实用原则加工而成的,是不自然的。(Novalis,1989:306)在《花粉》断片集中,他把浪漫的人和理性的人分别称为“迷惘的人”(der Verworrene)和“有序的人”(der Geordnete):“迷惘预示着超常的力量和能力,是不完善的关系;有序则预示着完善的关系,是可怜的能力和力量。因此,迷惘的人是不断发展的,有能力达到完美的境界,与之相反,有序的人则早早就作为庸人停滞不前了。”诺瓦利斯又特别强调:“迷惘的人通过自我认识能够达到那美妙无比的透明性、自我的大彻大悟,这是有序的人难以企及的。真正的天才把这些极端有机地联系起来。”(Novalis,1989:305)
诺瓦利斯所主张的浪漫审美感知无疑是对理性原则的挑战和超越。而歌德对“古典的东西”和“浪漫的东西”所持的态度,也完全显示出他们在诗学思想上截然不同的认识。尽管歌德的创作与浪漫派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始终把“古典的”与“浪漫的”对立起来。在他看来,“古典的东西是有条件的(实实在在的、人性化的)”,而“浪漫的东西不是自然的东西、本原的东西,而是一种矫揉造作的东西、可以追求的东西、故意拔高的东西、夸张无比的东西、奇异古怪的东西,甚至是滑稽可笑和漫画式的东西”;古典的东西是“理性的”、“和谐的”,而“现代的东西是彻底无节制的、想入非非的;古典的东西只是展现为一种理想化的现实,而浪漫的东西则展现的是不现实的东西、不可能的东西”;古典的东西是“真实的”,而浪漫的东西是“迷惑人的”;“古典的东西是近乎严肃的东西、有价值的东西”,而“浪漫的东西是近乎可笑的东西”;古典的东西既“有风格”,又“有品位”,而浪漫的东西也许“有风格”,但“没有品位”。从歌德这些充满对立的议论中不难看出,正因为古典的东西具有这么多无与伦比的优点,是现实的结晶,所以它才成为歌德艺术追求的最高目标。而浪漫的东西之所以被否定,被视为不可取,因为它是脱离了现实基础的“矫揉造作”。(Goethe:500)就是到了晚年,歌德也始终坚守着自己这种美学评判标准,“把‘古典的’叫做‘健康的’,把‘浪漫的’叫做‘病态的’”。(歌德,1997:188)。
显而易见,在如何对待“古典的东西”和“浪漫的东西”上,诺瓦利斯与歌德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凡是歌德赞成的,正是诺瓦利斯要批判的;凡是歌德排斥或者否定的,也正是诺瓦利斯要主张和坚持的。从这些议论似乎可以看出,在审美感知上,歌德偏爱的是一种静态的和谐,而诺瓦利斯倡导的则是一种对立变化的冲击。所以说,诺瓦利斯对《学习时代》的批评绝对不是直接针对这部小说本身的,而是源于他与古典主义不同的诗学理念和审美感知。
对《学习时代》的批评:诺瓦利斯审美感知的自白
如果说诺瓦利斯的浪漫诗学思想,是对以歌德为代表的古典现实主义原则的反思和挑战的话,那么诺瓦利斯对《学习时代》的批评,无疑是建立在这样的审美感知基础上的。当然,诺瓦利斯的批评不像F.施莱格尔,他并没有撰写过专门的文章来系统地评论歌德的这部小说,而是有意地采用了断片形式。
断片是德国早期浪漫派作家最钟爱的、独一无二的表现形式,构成了他们阐述艺术理想、审美感知和价值观念的核心。断片体现的是开放性,不讲究铺垫和过渡,不看重因果和推导,它以直接而简洁的方式表现出思想灵感的火花,因为浪漫派的审美原则就是反对和排斥一切封闭的体系。浪漫派推崇的万象诗从根本上说是动态的、发展变化的,这种开放性也正是浪漫诗的生命力所在。可以说,断片就是这种开放式体系的缩影。尤其是F.施莱格尔,他在《雅典娜神殿》中以其无与伦比、充满哲学思辨和震撼力的断片,奠定了浪漫派诗学思想的基础。同样,作为早期浪漫派代表之一,诺瓦利斯始终把断片视为诗学理想的摇篮、容纳百川的大海,要让思想在其中自由自在地奔涌,让诗在其中永远保持生机勃勃的活力。他的断片表面上显得缺乏关联,凌乱驳杂,但其彼此相通、息息相关和灵动多变的内在思想,绽放出诗人对诗的独特理解,是引发与读者互动的契机。
诺瓦利斯对歌德《学习时代》的批评同样散见于他的断片中。诺瓦利斯的批评表现出他对世界、对人和对诗的理解。在这些断片里,诺瓦利斯批评的一个焦点就是把歌德及其这部小说与启蒙理性联系在一起。他称歌德是个“实用的诗人”,因为歌德的文学创作是由“天生的实用”意识和“通过理性而赢得的高贵品位”所决定的。诺瓦利斯尽管承认“这部小说的哲学和道德是浪漫的,最普通的东西以浪漫反讽的手段被看作和表现为最有意义的东西”。(Novalis,2000:226)然而,他从根本上认为它就是“为了理性和从理性出发而创作的”。(Novalis,1989:224)因此,他把这部小说看成是“理性的产物”,是按照由理性“这个奇怪的概念”结构起来的,其中“想象、机智和判断力都不过是用来为之当陪衬的”。在批判地分析这部小说时,诺瓦利斯始终意识到浪漫诗学新时代的到来,这种新诗学反对把理性当作普遍的认识原则,用现存的自然法则来解释世界。他深信,从新一代浪漫派作家中将会“涌现出美妙无比的艺术作品”。(Novalis,1989:474-76)
诺瓦利斯批评启蒙理性原则的核心,是不赞成把世界上的一切都片面地看成是有限的、可以理解的。他认为,世界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是可以理解的,又是不可以理解的;二者相互对立,充满了神秘和未知,纯粹靠理性是解释不了的。诺瓦利斯思考和认识世界的方法,主要源于浪漫哲学家费希特在其《知识学》中对自我与非我对立关系的论述。他专门研究了费希特的哲学,可以说是费希特的哲学唤醒了他对诗的思考,为他打开了一个崭新的思想世界。他把费希特二元对立的哲学方法创造性地运用到他的诗学理解中,在理性与情感、有限与无限的相互制约和影响中超越了片面和偏见,感知到了那开放而灵动的浪漫诗所要表现的对象。诗成为其认识和把握世界的手段,是诗人的使命,更是诗人存在的意义。诺瓦利斯在《夜颂》中表现的昼与夜和光与暗的对立,就是其诗学理念非常经典的表现。在这里,他更强调夜的神秘和伟大,因为夜是无限的,既预示着昼的必然来临,又包含着昼的归宿。夜与昼对立,又不可分割。夜既象征着人的内心世界,又是融合万物的本原状态,同时也是世界作为整体的体现。夜无疑代表着浪漫派永远追求的精神境界,这个伸手可及却又神秘莫测的本原状态,单凭理性逻辑是不能完全认识和理解的:“我们永远都不会完全理解自己,可是我们将会和能够认识的自己则远远超越对自己的理解。”(Novalis,1989:296)
正是在这样的诗学思考基础上,诺瓦利斯在断片中往往以歌德的《学习时代》为例,来进一步阐述自己的诗学观念和感知模式。他批评这部小说的表现“无诗意”,因为“浪漫的东西”、“自然诗”、“神奇的东西”在其中消亡了,“自然和神秘彻底被遗忘了”,“理性像天真的幽灵一样”无处不在。在他看来,“艺术的无神论”成为贯穿这部小说始终的内在精神,“实用”和理性战胜了诗,诗意地表现了“无诗意的素材”,是用“稻草和木屑”烹饪了一道“可口的菜肴”,组合起了“偶像”。因此,歌德的迈斯特在他的成长旅行中每前进一步,诺瓦利斯就看到他越来越远离了青春的幻想、目标和理想,最后在理性的生存中成长为所谓完美的人,也就是歌德希望每个有教养的人要达到的最高目标。在诺瓦利斯眼里,歌德利用小说来美化这种理性的生存,甚至是在滥用诗。《学习时代》结尾,随着纳塔利亚作为美的象征出现,与追求完美境界和商人地位的迈斯特融于一体,实现了作家的真正理想。诺瓦利斯则认为这是由理性所决定的“二律背反的合二而一”,对他来说,这种关系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不是迈斯特必然脱离商人身份,就是追求诗的境界必然趋于毁灭”,二者必居其一。(Novalis,2000:225-26)基于二元对立的认识原则,诺瓦利斯始终认为这样的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更不可能达到歌德所主张的完美和谐。
诺瓦利斯在批评歌德这部小说的同时,他所理解的诗与F.施莱格尔的如出一辙,就是要超越传统的诗学界线,重新统一诗被割裂的各种类型,成为不受理性原则限制、包罗万象的浪漫诗,因为“只有浪漫诗才是无限的,正如只有浪漫诗才是自由的、才承认它的第一法则,那就是诗人的想象力容不得任何凌驾于自己之上的法则”。(F.Schlegel:22)诺瓦利斯尤其强调诗与哲学的融合:“哲学把诗升华为基本原则。它教诲我们去认识诗的价值。”(Novalis,2009:378)他打破了诗与哲学的界限,让诗的表现呈现出哲学的思辨,使哲学成为“诗的哲学”。他把诗的绝对真实看成是自己“哲学的核心”,而且“越是诗的,越是真实”。(Novalis,1989:481)对诺瓦利斯来说,理性和想象只有通过诗才能以神奇的方式在更高的层面上融为一体。诺瓦利斯的浪漫诗是走向内心的,是对神秘的探寻,是理想主义的,与歌德的《学习时代》格格不入。它创造了施莱格尔所说的“新神话”,使自我在精神的深处领悟到一切现实;它诗化了生存,使自我在创造性的精神活动中感受着存在的神秘和诗的力量,“因为诗构建起了美好的社会——世界家庭——宇宙美好的生存家园”。(Novalis,2009:401)
《奥夫特丁根》:浪漫诗的典范
不言而喻,诺瓦利斯对《学习时代》的反思和批评促使他在创作中去实现自己的浪漫诗学思想,小说《奥夫特丁根》即是如此,力图在诗学追求上超越和克服歌德的小说。在诺瓦利斯看来,“浪漫小说”是“神奇的”、变化多端的,它包容了一切形式,是实现浪漫派“不断发展的万象诗”最合适的形式。尽管这部小说在结构形式上或多或少地模仿了歌德的《学习时代》,但从根本上它表现出了一个与之截然不同的艺术视角:歌德的小说世界是现实的,故事情节是由理性逻辑结构而成的,而诺瓦利斯的则是浪漫的,是由放纵的想象力的断片组合起来的,相互独立的事件穿插交错,没有发展,也没有因果,显得杂乱无序;迈斯特是在与现实的融合和磨练中作为人成长起来的,而海因里希则是在心灵感知中作为诗人走向成熟的;前者追求的是现实的生存,后者则向往幻想的家园。在诺瓦利斯的小说中,自我和世界与对一个充满爱、和平与和谐的无限王国的意识相互渗透,相互交融。诺瓦利斯在这里不是要把所谓有限的东西理想化,而是要使无限的东西成为诗的现实。小说开卷的“献词”展现的就是一个完美的诗的境界,也奠定了这部浪漫诗表达的基调:诗唤起了“我”内心的艺术灵感,使“我”摆脱了“尘世的痛苦”,让“我”“吮吸着生命的乳汁”,插翅“飞向”诗的“怀抱”。(Novalis,1997:7)
像年轻的迈斯特一样,年轻的海因里希也踏上了旅程,这是父母给他安排的旅程,是要指给他进入成人生存之道的旅程。但就在这漫游之中,表现出了诺瓦利斯对于人的成长所特有的态度。如果说迈斯特的旅程是为了脱离开狭隘的市民生存而去闯荡社会的话,那么海因里希则是在用心灵经历和感受着一切天然的契合,因为他天生就是诗人;迈斯特在社会现实中经历了持续的成长过程,而海因里希则是在神奇的“断片”世界里追求着诗人的理想。
与《学习时代》相比,首先,《奥夫特丁根》的故事不是发生在一个普通的世界里,而是一个理想世界里。在这个世界里,没有生存的艰难曲折,一切都自然而然地趋向完美。这里要表现的“不是理想化了的现实,而是现实化了的理想”。(Schulz:691)歌德的迈斯特满脑子装着各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步入艰难坎坷的世界里闯荡人生,伴随着一次次失望和失败,最后从理想中留存下来的,无非就是在现实中可以实现的东西,经历的是理性不断决定一切的成长过程。正如黑格尔所说,“这样的学习时代,到头来就是主体变得成熟起来,带着自己的愿望和看法熔炼于现存的环境及其理性之中,连接到世界链条里,并在其中求得合适的立身之地”。(Hegel:568)而海因里希理想的实现可谓一帆风顺,没有经历挫折,也没有经历失败,一切都以神奇的方式无可挑剔地顺应着他的愿望。其次,迈斯特的旅程是幻想不断被新的经历打破的旅程。他离开父母后,外出经商的目的日益淡漠,相反,他组织起一个剧团,直到剧团散伙。他遭到形形色色的女人欺骗,历尽周折,最终达到了目的,却又放弃了。迈斯特的旅程错综复杂,就像扫罗一样:“他外出寻找父亲的驴,而得到了一个王国。”(歌德,1999:538)而海因里希所谓的成长旅程从头到尾都是如愿以偿,他的成长不是在自己的幻想与生存现实的冲突中实现的,而是一个在幻想中所瞄准的计划自然有序地深化。在开始的蓝花之梦中,他预感到一个确定的目标,那就是诗与爱向他的召唤。他井然有序地先后穿越过神秘的远古时期、东方之国和战争、大自然、人类的历史、诗的境界和爱情,这样的成长几乎是毫无例外地通过别人的讲述和谈话实现的,而不是通过亲身的经历和感受。既无抗争,也无失望,是童话般的感知,天堂般的存在。再则,从爱情方面来看,迈斯特的爱情经历了一连串的挫折和失望。当他无奈地看着玛丽阿纳处于金钱的诱惑而与商人诺贝格保持着关系时,第一次爱情便随之破灭了。放荡的菲利纳戏弄他;迷娘让他晕头转向,不知所措;心灵阴暗的奥莱利利用他,直到他最后作为一个饱经世故的成熟男人找到了娜塔利亚。海因里希则截然不同。他在第一章里梦见了玛蒂尔德,第六章里就把她搂在自己的怀抱里,第八章里他们就为永久的爱情海誓山盟。其中没有观望,没有犹豫,没有情感交流,也没有真正的性爱,一切都自然而然。海因里希的爱是柏拉图式的,他看到和渴望的不是个体的玛蒂尔德,而是透过她窥见了一个原始图像:“你的尘世形象不过是这个图像的影子……这个图像是一个永恒的原始图像,是那个未知而神圣的世界的一部分。”(Novalis,1997:119)梦幻和童话成为理想世界存在的基础。蓝花之梦、大西岛童话和柯灵索尔童话,这三个断片式的叙述似乎构成了海因里希诗的境界的核心,也与《学习时代》的表现方式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梦中的蓝花是贯穿小说始终的一条主线,蓝花象征着诗与自然融为一体,是诗的最高境界。小说一开始,海因利希听到一个陌生人讲述了神秘的远方和神奇的蓝花,内心突然升起了一种强烈的渴望,于是蓝花成了梦中吸引他的目标:他唯独只看到这蓝花,怀着不可名状的神情,久久地注视着它。他终于想去接近它。这时,它突然开始动起来,变化着;花瓣越来越光彩夺目,偎依在长起来的花茎上。这花向他探过来,花瓣变成了一个敞开的蓝衣领,中间浮现出一个娇柔的面庞。(Novalis,1997:11)
海因利希觉得,蓝花之梦“像一个巨大的轮子旋转在我的心灵之中,催人振奋”。对他来说,蓝花的出现绝对不是偶然的,而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契合,意味着神秘的召唤和启示、一种冥冥之中更高的生存境界,于是他朦胧地感到一种使命感,作为天生的诗人,对蓝花的渴望与追求就是诗的使命。然而,海因里希走向成熟的道路不同于迈斯特,他没有主动采取行动,没有陷入冲突,也没有经历坎坷。整个旅程中,他听到的各种远古的传奇和美妙的童话、他经历的各种事件,这一切都在海因利希的内心深处呼唤着一个充满图像的渴望,使他越来越意识到诗的神秘和力量。海因里希到达目的地奥格斯堡后,认识了诗人柯灵索尔和他的女儿玛蒂尔德。他一下子就被玛蒂尔德吸引住了,因为她就是自己梦中曾经看到的蓝花:“她将是我那深不可测的灵魂、我那神圣之火的守护女神。我在内心深处感觉到多么永恒的忠诚啊!我就是为崇拜她、永远效力于她、思念她和感知她而生的。”(Novalis,1997:105)从“崇拜”、“效力”、“思念”和“感知”这些用意深刻的词语可以看得出,在海因里希眼里,玛蒂尔德显然是一个融诗、爱和美于一体的化身,代表着诗人灵魂的“原始形象”(Urbild),把他带到了诗的境界里。当然,玛蒂尔德的死无疑是诺瓦利斯浪漫反讽表现的必然结果,因为对于他来说,玛蒂尔德同时也是一个幻想的化身,幻想则永远是虚构的,是不可能变成现实的;浪漫化的诗的境界永远只是追求的目标,却永远不可企及。正因为如此,小说下部的“实现”则发生在一个“新神话”里,所有的人物都变成了“黄金时代”里的童话形象。
如果说梦中的蓝花象征着海因里希所追求的诗的理想境界的话,那么他在童话中对诗的经历就是这种象征的延伸。小说中,陪伴海因里希及其母亲回奥格斯堡的几个商人朋友首先充当了诗的教诲者,他们讲述的神奇故事深深地打动了海因里希的内心,让他明白了世界的伟大关联,促使他形成了展示“诗的精神”的内在力量,给他指出了浪漫诗人的使命。尤其是大西岛国王童话,使他感悟到了诗与权力和自然的融合。童话中,逃出宫门的国王独女和一个远离尘世、在大自然怀抱里成长并深谙其神奇的小伙子结合。公主从小伙子那里知道了这个世界是怎样通过神奇的和谐产生的,而小伙子则从公主身上学到了美妙的音乐艺术,唱出了悦耳动听的歌声。他们后来带着自己的孩子,即艺术与自然融合的结晶,出现在孤独的国王面前。歌曲《回归永恒的黄金时代》成了诗与整个世界融合的象征;诗人的歌谣绽放出美妙的和谐。
这个童话所表现出的诗的境界与诺瓦利斯在“信仰与爱”的断片中所阐释的认知和内在一脉相承:只有诗的精神与权力如此结合起来,才会产生“诗意的”国家、“美好的”社会。而这对年轻夫妇带给国王的孩子才是真正意义上诗的境界的象征,因为他是自然与诗的精神融合的结晶,又是与权力或政治结合的中介。海因里希在倾听着这个童话时,越来越意识到了自己作为诗人的使命:“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仿佛只是在他内心开启了一把把新锁,为他打开了一扇扇新窗户。”(Novalis,1997:43)诗的童话使他感悟出世界上的一切都着眼于那个在诗人们的吟诵中一再召唤的伟大的和谐,因此,他越来越清楚地感受到诗的境界就是他追求的最终目标。
小说上部结束时,诺瓦利斯把诗的全部意义都融汇到诗人柯灵索尔讲述的童话里。柯灵索尔教诲海因里希什么是诗的完美境界:“诗人不可或缺的就是对自然的感悟。”因此,“无智性的激情是无用和危险的。如果诗人自己为奇迹而惊叹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创造出太多的奇迹来。”(Novalis,1997:110)柯灵索尔讲的是一个通过诗的力量拯救世界的童话。大角星王国自从把战神之剑扔到尘世、王后“智慧”下凡人间传播永恒的意识以来,王国就被冰雪封冻,女儿“和平”沉睡不起。代表理性的书记员乘虚烧死爱神的母亲,霸占了王国。“寓言”作为诗和爱的化身成为这场伟大的行动真正的组织者,因为她的每句话都经受住了神灵的考验,闪耀着逢凶化吉的光芒。他与爱神兄妹联手战胜了书记员,平息了理性的叛乱。爱神的母亲心灵尽管免不了火刑的命运,可从火刑场上喷发的火焰吞没了太阳。于是时间停滞了,永恒来临了。大家饮着母亲的骨灰化作的圣水,一个充满美好的春天立刻弥漫在大地上。沉睡的“和平”被唤醒了,爱神与“和平”作为国王和王后登上了王座。而“寓言”此刻吟诵着:“永恒的王国建立了,/争战在爱与和平中结束了,/漫长的痛苦之梦过去了,/索菲永远是心灵的女神。”(Novalis,1997:151)
在这里,一切在思想和情感上、意识和下意识上打动了诺瓦利斯的东西,都以神奇的方式汇聚在大角国童话里,诗的精神体现为“永恒王国”的核心。诺瓦利斯以不同凡响的艺术形式,从精神的深层创造了一个施莱格尔所说的“新神话”。这个新神话“一定是从精神的最深处形成的,必须是一切艺术作品的佼佼者,因为它要包容其他一切艺术,它是那古老永恒的诗的本原的新温床和容体,而且本身是无限的诗,隐含着其他一切诗的萌芽”。(F.Schlegel:83)柯灵索尔的童话既是神秘的,又是开放的,它为海因里希进一步感悟诗的境界提供了一个无限的空间。可以说梦和童话构成了海因里希感悟诗的境界的核心。诺瓦利斯借着主人公从内心感知诗的真谛而走向成熟,成为读者解读其诗学理想和审美感知的范例。这种感知像神话一样,既神秘,又富有内涵,因为诺瓦利斯同样认为:“神话与诗,二者为一体,不可分割。”(F.Schlegel:83)
无论是诺瓦利斯对《学习时代》的批评,还是他的小说《奥夫特丁根》,都不是直接针对歌德的,而是两种诗学思想的对立、两种审美感知的碰撞。作为浪漫派作家,他反思的是传统,挑战的是以歌德为代表的启蒙理性和古典现实主义诗学思想。他批评理性的片面性,强调在无限中感悟诗的真谛。他从诗学观念和创作实践上把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浪漫化了。可以说,歌德的诗学思想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立足现实,又直接作用于现实;而诺瓦利斯的诗学观念则是浪漫的,因为它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无限而神秘的王国。歌德的审美感知是理性的,因为它深深地扎根于对具体事物的观察中,始终在追寻着普遍存在的逻辑原则;而诺瓦利斯的审美感知则是非理性的,因为它把想象力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步,让生存获得了无限的空间。歌德的迈斯特是个现实中的人,因为他在实实在在的生存环境中追寻着走上完美的成长之路;而诺瓦利斯的海因里希则是理想中的人,因为他在完美的幻想中不断在内心感悟着彼岸的家园,“永远走在回家的路上”。
诺瓦利斯的诗学理想充满“夜”的神秘和美妙,就像他那些睿智而神秘的断片一样。他认为现实不是首先可以通过行动改变的,而是可以通过全面地反思重新给以解释,也就是说,生存的改变是在个性和意识中进行的。他在《基督教或者欧罗巴》一文开头所描述的那个“光辉灿烂的时代”、那个充满无限信仰和伟大神奇的基督教世界,就是他理想化的天堂、梦想的家园、诗的境界。可对“永远走在回家的路上”的诺瓦利斯来说,这个完美的境界过去不存在,现在不存在,将来也不会存在,而只存在于他内心的渴望中。这也正是构成浪漫派作家认知核心的浪漫“反讽”的根本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