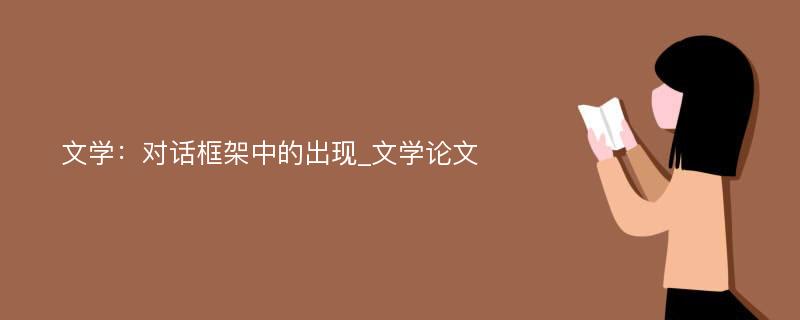
文学:在对话框架中呈现的状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状貌论文,框架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对于文学,我们可以有不同角度来作出的界说,如反映说、表现说、象征说等等,这些不同界说如果不是作出极端性的结论,那么它都可能揭示文学的某一特质。然而,这些界说都基本上是作的静态分析,如果换从动态的描述,将文学作为一种言说的话语来看,则我们就还可看到文学的新的特质。基于这一考虑,笔者从文学活动及其产品的对话性上作了一番探析。以下,我们从几个方面加以论说。
一、本文内部与本文相互关系的对话
对话(dialogue),即一种交谈、会晤。它必须要有晤谈的双方乃至多方。这里说本文内部的对话,说得通俗一点,即本文内部的上下文关系,本文显义与隐义的层接关系,本文题材与主题间的照应等。
这种对话关系必须落实到本文的物化形式上才能较好地说明。如杜甫诗句“两个黄鹂鸣翠柳”,单此一句也很平常,没有什么特出的值得赞赏之处,但又接一句“一行白鹭上青天”,这样,“两个”与“一行”的数字对称关系就出现了,而“黄鹂”与“翠柳”,“白鹭”与“青天”,又呈现出一幅色彩斑斓的图画,再又有“鸣”所处的静态与“上”所显示的动态构成动静平衡的张力结构,再又有两句诗中体现的近景与远景交错的既有镜头景深感又有近物特写的美学透视效果,由此,两句诗之间形成了一种互相以对方为依托,又都反过来呈现出对方的微妙的对话效果。这一对话,不是以一方来说另一方,而是双方互对对方加以言说并也对对方的言说予以反应。这一对话关系与其说是作为作者的杜甫头脑中拟构的,毋宁说是语言规则本身的规定,也毋宁说是人们的接受心理上具有的“格式塔质”的惯性,人们在感知外物时往往是将它们看成一个联系着的整体。
本文内部的对话关系也可以采用较为隐晦的形式。鲁迅小说《药》中,华老栓一家与夏瑜一家的悲剧故事,由两家的姓氏可以简读为“华夏悲剧”,即由具体的人物和故事写出了中国的社会悲剧,而由小说末尾的坟上的花环又暗示出悲剧之后可能有的新的希望。在这里,小说的具体生动性与整体象征性,语意义与象征义之间就有了一种对话关系,象征意蕴要由具体描写衬托才有血肉,具体描写又得靠象征意蕴才有深度。对此,我们当然也还可以说这是鲁迅在构思、写作该小说时就有的思想,但是我们也应该考虑到这一追溯作者“原意”的思路在大多数场合下是行不通的,譬如《红楼梦》的主题探讨,就可以从政治到宣淫,从影响国家大事的“反清复明”思想到写作者的个人情感遭际等方面作很大跨度的跃动,我们最好还是将“原意”这一几乎无法稽考的问题搁置起来,将其看做是本文内部的一种意义的对话关系,它可以有一经写出就独立于作者控制的能力,这样才能给各种对文本的释读敞开一道大门,使对本文的阅读有更多意趣。
本文内对话关系的物性特征还可从文学语体上见出。钟嵘曾标举五言体诗居文辞之要,也有好些论者提出附议,称五言诗“独秀众品”,〔1〕“佳处多从五字求,解识无声弦指妙”〔2〕等,这种对诗歌五言句式的推崇实际上是在七言诗盛行的背景下提出的,按王力的说法,“多数七言诗句都可以缩减为五言,而意义上没有多大变化,只不过气更畅,意更足罢了。”反之,“每一个五言句式都可以敷衍成为七言。”〔3〕由此,我们从五、七言可以互相转换中见出, 写五言诗的诗作有对意义更含蓄隽永的追求,写成七言的诗作有对抒情写意更酣畅的追求,每一种语体方式都对另一种方式进行了一种“应该这样”的对话。
同时,本文与本文之间还有一种“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即本文作为一种话语来显示它的存在时,各个本文之间也就有了对话,其中一个本文的状况对另一个本文的状况就会有直接或间接影响,相互都以对方作为本文,自己则成为描述的话语,如从李白写三峡的两首诗就可见其互文性。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这是有名的《朝发白帝城》,单从字面看,这只是记山水、写游记的诗,李白的另一首《上三峡》单独来看也同样如此:
巫山夹青天,巴水流若兹。
巴水忽可尽,青天无到时。
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
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这两首诗分别写于李白被流放去贵州的归程和去途,那么了解到该写作背景后,就可以看出遇朝廷大赦而“一日还”的欣快与大赦前作为被流放者“三暮行太迟”滞重的对比,其中一篇诗作就是对另一篇诗作的诠释。
在当代作家中,高晓声创作的“陈奂生系列小说”也体现了本文间的互文性。第一篇《漏斗户主》发表后虽也得到了个别批评家的关注,但作者并不满足,认为没有达到该创作应有的社会反响程度,于是又写了第二篇《陈奂生上城》,写农村实行责任承包制后早先老吃补助也老吃不饱的陈奂生,在改革的大背景下的变化,作者自叙是想以第二篇小说来“救活”反响不大的第一篇小说,〔4〕结果真的遂愿。 要读透《陈奂生上城》,就应先看以前发表的《漏斗户主》,而看了《漏斗户主》,也应再看《陈奂生上城》才有完整的人物性格的把握。可以说,两作品构成了互衬的对话关系。
其实,在文学史上,任何新的巨著的问世都可能追溯到一个古老的源头,从而使整个文学影响史应作出局部的甚至是根本性的改写,这也都是本文间对话关系的体现。罗兰·巴特曾说:
所有写作都表现出一种与口语不同的封闭的特性。写作根本不是一种交流的手段,也不是一条仅仅为语言意向的通行而敞开的大路……它根植于语言的永恒的土壤之中,如同胚芽的生长,而不是横线条的延伸。它从隐秘处显现出一种本质和威慑的力量,它是一种反向交流,显示出一种咄咄逼人的势态。〔5〕写作出的本文一方面确实可以用于交流,另一方面又如巴特所说是“反向交流”,即本文不断接纳诠释者围绕它作的诠释,本文在显示自己意义的同时又不断形成新的意义。这一特性,从“对话”以外的角度是无法窥见的。
二、本文创作与接受上的对话
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来看,每一部文学作品都只是在被读者、听众等接受者接受之后才成为现实的作品,既然如此,那么对文学本文的界定就应联系到接受问题。反过来说,文学接受又是在本文创作的基础上来进行的,接受状况得受创作状况的影响。这样,通过文学本文,创作与接受之间就有着一种对话关系。本文经由创作才得以产生,它呼唤接受;而接受后对本文的诠释又向创作提出了某种诘问,从而成为“二度创作”,成为在本文之侧的副本文,它们共同构成了文学的“作品”。
在这样一种对话关系中,文学接受的重要性是很大的。特里·伊格尔顿曾说:
一部文稿可能开始时作为历史或哲学,以后又归入文学;或开始时可能作为文学,以后却因其在考古学方面的重要性而受到重视。某些文本生来就是文学的,某些文本是后天获得文学性的,还有一些文本是将文学性强加于自己的。从这一点讲,后天远比先天重要。重要的可能不是你来自何处,而是人们如何看待你。〔6〕这就表明,文学本文作为一种审美意识的物质载体,它是由创作决定的;文学本文作为一种艺术的话语体系,其话语的含义则是由创作与接受共同厘定的。离开了接受,也就没有了文学。
应该说明的是,文学本文的对话与日常语境中的对话是不同的。早在柏拉图就意识到二者的区别,他指出在面对面(face to face)的交谈中,可借助于语气、声调、手势及一定演技来辅助谈话,以辅助话语表达的不足,但对于书写来说就没有这一条件了,它只能依靠对书写出的本文的解释来“补救”。单从柏拉图这一区别来看似乎是指出了书写的不利,不过,由于书写的话语在面对读者时缺乏面对面交谈的语境,就解放了言说主体与收听主体。阐释学家保罗·利科尔据此说明:“由于书写,本文的‘语境’可能打破了作者的‘语境’。”“书面材料对于话语对话条件的解放是书写最有意义的结果。它意味着,书写和阅读之间的关系不再是说和听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情形。”〔7〕
所谓“本文的语境”不同于单纯作者写作时的语境,是因为本文作为书写物存在时,作者已只是一种缺席的存在,本文话语同读者构成了语境中的双方,本文作为发话者的一方,或者说作为读者提问的回答者的一方,它的内涵可能小于也可能大于作者所意识到的思想,在此状况下,根本就不可能用作者的虚构来说明问题了。当然,本文的话语世界毕竟只是话语而不是现实的物质存在,但我们仍可说它是物质性的。本文接纳了作者意图,本文对于读者也形成了一种召唤结构,这样一种关系是作为现实存在而需要我们去探讨的。
三、本文历史语境的对话效应
前文已提到了“本文语境”的术语,它是指文学本文在同读者接触时,本文同读者之间形成的对话交流关系,那么,要更深刻地理解本文语境的问题,还应从本文的历史语境来作考察。
本文是作者的书写物,但这种父子式的关系在写作过程终结时就算了结了。作者有权对原先的书写进行修改,但该本文如是发表了的话,就可说修改之作一定意义上已是新创之作,作者没有权力对别人手中的原有版本也加以改写,也无权宣称其为非法的,本文被作者写成发表后也就是被抛向了历史,听凭历史的潮汐来主宰本文浮沉和走向。
这里提到了“历史”一词后,就有了一种深度的时间维度,更主要的是一种时代维度的厚重感。但是对“历史”一词也有必要在此作新的理解。海登·怀特曾说:
已故的R·G·柯林伍德认为一个历史学家首先是一个讲故事者。他提议历史学家的敏感性在于从一连串的“事实”中制造出一个可信的故事的能力之中,这些“事实”在其未经过筛选的形式中毫无意义……
柯林伍德没有认识到,没有任何随意记录下来的历史事件本身可以形成一个故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历史事件只是故事的因素。事件通过压制和贬低一些因素,以及抬高和重视别的因素,通过个性塑造、主题的重复、声音和观点的变化、可供选择的描写策略,等等——总而言之,通过所有我们一般在小说或戏剧中的情节编织的技巧——才变成了故事。〔8〕海登·怀特在这一大段论述中体现出这样一种历史本体观,即作为真实的过去的历史本文是一去不返,已不复存在的;我们所说的“历史”只是对历史本文的记录、阐释和评价,它是从历史本文中捕捉到一些“事实”碎片,再把“事实”碎片按照一定的历史观串接起来。同样的事实,从一个角度可以写成悲剧,从另一角度可以写成喜剧,甚至是滑稽剧。
因此,从这种对“历史”的理解来看历史,历史浮现在我们的意识中时,已不是中立的客观的本文,而是一种虚构出的话语,这并不是说历史容许人们去随意篡改,而是说观察记录历史的立足点和使历史事件体现出某种蕴含的认识都是人为的因素使然。所以,本文的历史语境其实就是本文读者与历史话语的一种“共谋”或者称之为“联手行动”。
笔者在此试以一则《论语》中的对话来看本文历史语境的对话效应: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一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9〕这是说孔子与学生子游等到武城时听到音乐后的一段对白,孔子认为该乐曲太一般化,而演奏时就显得过于正规了,所谓用乐队的“牛刀”来割乐曲的“鸡”。但学生子游反诘,说以前听老师关于学道的教诲,明确了音乐也是道的表现,现在何故要非议它呢?孔子马上承认了自己的失言,指出刚才的评论是不合适的。这里我们可以读出一个矛盾的方面,即单从个人感受来讲,孔子对该段乐曲是有微词的,但从孔子的“礼教”、“乐教”的思想来讲,则还是应对这一活动本身给予肯定。两者相较,孔子是更倚重后者,所以坦然地向学生认错。这里我们只是对该段本文的引述和解释,但要将其放置到历史语境中去就还可以读出更多的东西。
笔者想从中国农业文化上来设置这一历史语境。众所周知,中国古代农业是在黄河流域一带发展起来的灌溉农业,这里就涉及到家庭化的小农生产与家庭之外的防洪与灌溉工程如何配套的问题。小农生产是以家庭中的长幼秩序定尊卑的,以此产生一个头领来引导家庭成员分工合作,而防洪灌溉的公共工程则要在联合诸多家庭实体的基础上才有可能。马克思曾说:
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10〕明确了东方农业的水利化特色后就可以对问题作进一步的描述了,即作为公共工程的水利建设,它必须合作进行,而单靠家庭之间、村落之间的合作还不够,它有赖于一个中央政府调动上万、上十万甚至上百万的民工来修筑、养护水利设施,有赖于一个权威机构来作统一的水利规划,但这种大一统的集权统治同小农生产的个体性之间有着矛盾,这就需要一种文化来调适它。在中国,它就以家国一体的政治伦理观念来充任了这一角色,它是把家庭中的父子主从关系推广到国家范围的君臣主仆关系,这一关系的维系除了以军队作为暴力的物质的保证以外,就是以礼、乐等文化仪式来固化它,使人在既定文化秩序中潜移默化地认同它的合法性。所以,孔子对“乐”所发的那段议论的矛盾放置在这一历史语境中就不难理解了。“乐”是作为承载家国一体文化的仪式来显示其权威性的。孔子认错时讲“前言戏之耳”,并非真是前面说了一句玩笑话,而是个人的真实感受比起社会的文化惯例来说微不足道,在社会的“道”面前,个人的思想感情只有“戏”的位置。这就是该段本文所体现的历史语境中的文化蕴含和意义。
应该说,本文历史语境的对话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已超越了本文的范畴,更不用说它超越了作者的创造或虚构的范畴。这一历史语境是由批评家设置的,但在此设置中又有着客观依据。它有似于几何证明题的辅助线勾绘,通过它可使证明过程更顺利。
四、本文与文化审美图式的对话
文学本文是一个符码系统,同时它更是在某种文化图式中的审美符码系统,因此,对于文学的研讨,就有必要从本文与它所处的文化审美图式的对话关系来看待。在此,我们可以先从一则绘画实例来引入话题。
明代时,曾给《水浒》人物绘像的著名画家陈洪绶少时以北宋画家李公麟的画法为师。他曾到杭州拓印了李公麟的《七十二名贤》画来作临摹。“闭户摹十日,尽得之。出示人曰:‘何若?’曰:‘似矣。’则喜。又摹十日,出示人曰:‘何若?’曰:‘勿似也。’则更喜。”〔11〕陈洪绶绘画由摹仿前人到不摹仿前人的事例,可以从艺术创造或其它什么角度来讲,我们这里则是要指明,他同前代画师画法的相似是进入了前代画师构筑的审美图式,而后来他又脱离了这种相似,则是在原来进入该图式的基础上又来同该图式展开对话。由相似而喜,是表明了对话的前提已经产生,由不似而喜,则是对话的格局已经形成。可以说,了解文学本文同某种文化审美图式的对话关系,既是了解文学发展中沿革关系的重要锁钥,也是了解文学本文自身特性的一个重要门径。
文学本文同某种文化审美图式的对话,是文学美感魅力的重要来源之一。从前人诗论中所谓“移情入景”的事例我们可以见出这种撇开外形,直指心性的对话关系,如:
竹未尝香也,而杜子美诗云:“雨洗涓涓静,风吹细细香。”雪未尝香也,而李太白诗云:“瑶台雪花数千点,片片吹落春风香。”〔12〕在这一论析中,我们可以从“移情”、“通感”等心理美学的角度来作分析,但在这里我们则是从对话角度来看它的价值。应该说,竹、雪之类本来都没有香味,而且即使对有香味的物品,文学也不能描绘出它的情状的具体方面,这是文学形象的间接性所决定了的。诗人在这里写无香之物的“香”,这本身就是对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悖逆,看起来是不通的,但这一悖逆实则是一种超越,即它写出了竹、雪一类景物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的意味。竹的正直、虚怀若谷、节节向上的姿态,雪的素朴、翩翩而落时的飘逸,正是中国文人士子所追求的人格理想范型,在这一文化图式衬托下言其为“香”可以说是非常精致贴切的。由此,两首诗中的“香”就是在无理和有理的两重语境中滑动,它不通却又通,它通却又不通,这种滑动就体现了文学本文同文化审美图式之间的对话关系。
这种对话其实还不局限于个别词语的或者某种创作意图的方面,它还可以体现为整个本文的涵义与文化审美图式之间,构成一种既相契合又相分离,既有合作又有抵牾的矛盾关系。
俄国批评家巴赫金在他的对话理论中,把陀斯妥也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说成是一种“复调小说”,是小说中的人物之间、小说中人物同作者之间,以及小说作者的各种思想之间的一种“杂语”,它们构成了一个多声部的对话场景。他又把拉伯雷的《巨人传》视为一种“狂欢节”式的揶揄,从而对当时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进行了嘲弄。在这类小说或诗歌本文中,只有将其视为作者创作出后已具有独立秉性的存在才有可能见出它的内在底蕴,而且不管作者是怎样想的,本文都对于某种文化氛围展开了一种对话。
这种本文与文化审美图式的对话也可以是在众多本文构成的某一风格类型或流派的规模上进行。如对于五四新文学性质的认识,郁达夫和周作人就看法迥异,郁达夫认为:中国现代的小说,实际上是属于欧洲的文学系统的。〔13〕但是周作人却持另一种意见,他说:我已屡次地说过,今次的文学运动, 其根本方向和明末的文学运动完全相同。 〔14〕两人的看法壁垒分明,但对于五四新文学来说都不是没有根据的妄论。可以说,郁氏见解是指出了五四新文学的横向移植,它主要体现在文学的创作观念上;周氏见解是揭示了五四新文学的纵向继承,它主要体现在文学的语言口语化上。如果这样的折衷之论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就连带地引出了下一个问题,即五四新文学是在本土文化传统与西方舶来文明的双重影响下出世的,而这两方面的文化矛盾又非常大,五四新文学处在这一夹缝中,就既有着以西方科学文化的普罗米修斯之火来烛照东方伦理文化的启蒙任务,又有着以东方国情、民情的不同特性来创造性地转化西方文艺精神的要求,处在这一夹缝中的地位就决定了它是不断地对此二者进行对话的。五四新文学的文学品貌既不同于明末文学,也不同于欧洲的启蒙主义文学,但同该二者都可以分别加以比较,而明末文学则与欧洲文学之间很难简单地加以比较。实际上,比较是在同一中见出差异的观察,两者缺一不可。同一代表了共同的话语系统,差异则表明了在此系统中对话的进行。
总括来说,文学作为对话的涵义是丰富的,它既是文学本文内部,文学作者同本文,以及作者与读者的关系复杂性的体现,也是文学本文同所处文化交互作用的一种体现;它既是客观性地存在着的文学特性,也是有赖于研究者从特定视角来设定的;它既是文学研究中一个先在的前提,也可以是研究过程结束之时呈现的结果。这里的关键已不在于如何来看待文学的对话性,而是要将其对话张力揭示出来,并分析在此对话中文学的状貌。
注释:
〔1〕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
〔2〕王士祯:《戏仿遗山论诗三十六首》。
〔3〕王力:《汉语诗律学》,上海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234页。
〔4〕高晓声:《谈谈有关陈奂生的几篇小说》, 《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3期。
〔5〕罗兰·巴特:《写作的零度》, 引自《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43页。
〔6〕特里·伊格尔顿:《文学原理引论》,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版,第11页。
〔7〕保罗·利科尔《解释学与人文科学》, 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2~143页。
〔8〕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本文》, 引自张京缓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页。
〔9〕《论语·阳货》。
〔10〕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64页。
〔11〕[明]周亮工:《读画录》。
〔12〕[宋]葛立方:《韵语阳秋》。
〔13〕郁达夫:《小说论》第一章,上海光华书局1926年版。
〔14〕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北平,人文书店,1934年版,第1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