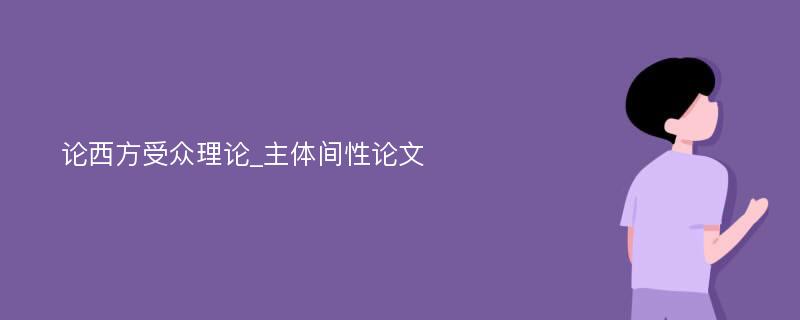
评西方受众理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受众论文,理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是什么?这个古老的斯芬克斯之谜,一直困扰着历代的思想家。而在传播研究中,最令人困惑的研究莫过于受众研究了。受众是什么?是同质的还是异质的?是群体(group)还是聚合体(aggregates)?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或者说是被媒体操纵的或是等待媒体“迎合”的?在这些问题上,人们一直争论不休,未能达成一致意见。当受众被想象成大众时,人们表现出想吸引和操纵尽可能多的人的一厢情愿;当受众被置于传播过程的中心时,人们又表现出“收购”或“捕获”受众的热情。但是,理性化的思考却被悄悄地扭曲了,到头来只得出一些关于受众的零星的、经验化的解释。
现在看来,人们以往对受众问题的设计要么抛弃了对传递者与受众关系的理解,要么长期误解了传递者与受众的关系。一方面,人们把传递者看作传播主体,把受众看成传播对象,这种“主-客”意义的建构实际上割裂了传递者与受众的关系。其实,传递者与受众的关系应该说是一种“共生现象”(coexistence or symbiosis),是“互构”(co-configuration)和“协商”(negotiation),而不是传递者主宰受众。另一方面,人们又认为受众是主导传播过程的中心,具有某种固定的主体本质,传递者所要做的事情只不过是顺应这种主体本质,这样一来,受众就被理解为孤绝的主体,这就不可避免地带来偏狭的传播运行机制和片面的传播实践动力。因为此时的受众实质上被想象成有主体性的物,而成批地“收购”或“捕获”这种有主体性的物,就会给媒体带来巨大的商业利益。
很明显,西方主流传播理论中的受众理论有一个基本的缺陷,就是直接或间接地把受众对象化进而物化,通过科学化、市场化思维“肢解”了受众。随着法兰克福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采用批判与诠释的方法研究受众,受众被看成是公众和公民,开始从“物化”的境地中解放出来,其不断被成批“出售”的商业化现实得到有力的揭示和批判。但一些研究者仍将受众视为需要改造和提高素质的“他者”,忽略了他们的判断力和对文化商业化的抵制力,依然没有真正理解受众。值得注意的是,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交往理性”、霍尔(S.Hall)的“编码-解码”理论以及由此展开的一系列论说,实现了主体性思维的转换,即告别主客对立意义上的单一主体,转向“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一方面坚持主体间存在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另一方面强调交往、对话和理解是弥合主体间差异的基本方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人的传播活动向社会历史文化开放了,传递者和受众都从抽象的单一的主体转向处于社会交往过程中的有生命的主体。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将不再局限于“受众是什么”的知识性问题,而是关注“受众如何在传播过程中创造自身”的哲学问题,并寻求一种创造性的解释。
一、受众是传播关系中的主体
一般说来,“主体”是西方近代思想的产物,它是从笛卡儿那里起步的。主体性哲学的核心范畴——主体的自主性、自主意识性和自为性,是在与客体的相关中规定的。它用“主体-客体”结构思维,认为与主体相对的只能是客体;在主体目光的审视下,一切对象——不管是他人或物都将变成客体。应该说,这种思维模式是人的理性精神和理性能力的体现,它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物的关系时是行之有效的,但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时,就遇到了“他人不是客体”的困窘。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就曾一再讨论“他人的目光”之可怕,因为一旦目光加身,自我便成为他人的客体。(注:任平,“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可以想象的是,在日常交往中,如果我成为他人的客体或他人成为我的客体,交往是难以真正达成的。可是,主体性哲学是从自我出发的,主体首先是自我,以主体为基点,即以自我为基点,这就免不了他人被当作客体的命运。虽然主体性哲学家希望“他的我”就是“普遍的我”,希望解读者这一“我”能读懂“他的我”,但问题是:我的世界何以能超越我的界限而达到他者?我的话语何以能成为共同的话语?主体性哲学家并未给予圆满的解答。事实上,从单一的主体出发,并不能找到圆满的解答。
按照“主-客”模式思考传播问题,就必然坚持传播过程中的“单一主体论”或“自我中心论”,认为任何传播都在主体与客体的范围内进行,主体是传播的主动者,客体是传播的对象,传播过程就是主体作用于对象或他者的活动过程。显然,这与"communication"(传播)所包含的“沟通”、“交流”、“交往”、“交际”等本质内涵是相对立的。
其实,传播是人与人之间平等交互作用的过程,其基本前提是传播各方的主体地位的相互确认,而“主-客”模式破坏了这一前提,强化了传递者与受众的主客关系。例如,在著名的拉斯韦尔公式中,传递者与受众是对立的,受众被当作劝服过程中不能作出任何反应的对象;而“刺激-反应”模式则把传播过程表述为:信息(即刺激)——接受者(即有机体)——效果(即反应)。在这里,传播者制作的媒介内容被看作是注入受众静脉的针剂,受众则被假定为以可预见的方式作出反应。(注:丹尼斯·麦奎尔、斯文·温德尔,1987年,《大众传播模式论》,祝建华、武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第59~60页。)后来,美国传播学家德福勒(M.L.DeFleur)对此作了部分修正,提出“大众传播的个体差异理论”,认为媒介信息包含着特定的刺激性,这些刺激性与受众成员的个性特征有着特定的相互作用,尽管有了一些新内容,但依然没有突破“主-客”思维框架,只不过成了更加精细的个人劝服理论。在这种貌似科学的“修正”里,有着背离传播活动本性的理论危机。
人是在交往中存在的,现实中的人是处于主体间关系的人,如黑格尔所说,“不同他人发生关系的个人不是一个现实的人”。在“主-客”思维模式中,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存在的,因而主体性是在“主-客”关系中的主体属性,而“主体间性”则表达了现实的人所存在的主体间关系的内在性质。它向我们昭示了这样的哲理:主体之所以能够面对另一极主体,主体之间的交流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存在着中介客体。这一客体是中介化的客体和客体化的中介,它向多极主体开放,与多极主体同时构成“主-客”关系,因此成为“主体-客体-主体”三极关系结构。其中,任何一方主体都有中介客体作为对应范畴,符合“主-客”相关律的定义规则;同时,异质的主体通过中介客体相关和交往,相互建立了主体的关系。(注:任平,“走向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1期。)在这里,既扬弃了传统的“主-客”关系,由主客对立、主客分离发展到主客合一,由科学理性精神提升至创造精神,又超越了单一主体性的缺陷,进入到平等、自由、多元的现代交往实践领域。其实,“主体间性”早就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致思取向,如儒家所讲的“仁”即解为“从人从二”,也就是多极主体或主体间之意,意指主体间的人伦关系。马克思一方面以热情的人文眼光批判人的异化现象,另一方面又以冷静的社会历史眼光分析资本运行与人类交往实践的关系,认为资本运行使各个生产者在分裂的状态下生产商品,以主体自然力作用于物质客体,实现着“主-客”双向物质交换;同时又通过普遍的商品交换来形成世界市场,构成多极主体间交往关系体系。当人类进入大众传播时代后,马克思的这些分析显得越来越有价值,批判学派和文化研究学派的部分学者程度不同地发挥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遗产,在这两个方面都做了独到的研究,既揭示了文化工业背景下文化消费的负面效果,又告别主客对立意义上的单一主体。在转向“主体间性”时,一方面坚持主体间存在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另一方面强调交往、对话和理解是弥合主体间差异的基本方式。其热情的人文眼光直面大众的生存状态,其冷静的社会历史眼光又使大众在主体间性中得以重构。
马克思曾从主体间的交往实践角度指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也许我们应该更直观地说,人是传播关系的总和。这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第一,人与人的关系总是同传播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可分割;第二,人与人的关系的性质由成员之间的传播所界定;第三,人与人的关系是在参与者的协商谈判中发展的。(注:参见小约翰·斯蒂文,1999年,《传播理论》,陈德民、叶晓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451页。)由此可见,传播是整个人类存在过程的生命,没有传播活动就无所谓主体,就无所谓文化创造;作为一种普遍的、内在的活动,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的行为方式。
从这个角度来思考问题,我们就不难看出,传递者与受众的关系根本不是什么传播主体与传播客体的关系,而是同一传播活动中共生的两个主体。“主-客”思维方式歪曲了事实,使我们错误地认为,人的传播活动,就是传播主体向作为传播对象的传播客体传达信息以期达到某种影响;大众传播就是一种媒介指向性交流,在这种媒介指向性交流中,传递者与受众之间的“人际关系”不复存在,而只表现出信息流向的“单向扩散”和“大范围传播”的特征;有些人甚至认为传播是征服大众、权力赖以行使的机制。这些对传播活动的片面的建构直接体现为“传递者中心论”,而“传递者中心论”的实质就是单一主体论、主客对立论,就是传播主体征服客体、改造客体使之符合其意愿的自我建构。这就使我们常常把传播的假象当真相,把自我建构的传播当作普遍存在的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受众当然免不了被物化的命运。在专制时代,受众是思想统治者的玩物,在推行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时代,受众是宣传家手中的政治砝码,而在消费主义时代,受众成了媒介向广告商兜售的商品。(注:参见Smythe,W,1993,Illuminating the blindspots:essays honoring Dallas,Norwood,N.J.:Ablox Pub.Corp.)要摆脱令人尴尬的处境,准确理解受众,仅仅有文化批判眼光是不够的,还必须回到主体与主体的传播关系中,亦即在“主体间性”中把握受众。我们的思维逻辑是,首先,传播是由对一切人都能相通的语言来表达的,这种语言在任何地方都是主体间性的语言。通俗一点说,传播在某种意义上是“感觉的”,是与不同主体的经验相符合的,任何传播都必须具有主体间性,才能成为主体之间交往的内容;其次,传播中的主体和主体之间共同分享着经验,进而形成意义分享,由此形成了主体之间相互理解的信息平台。可以说,传播中的意义不是在主体自身形成的,而是在主体和主体间形成的;其三,在人际传播中,每个人都从他人身上看到自己,也从自己身上看到他人。在这种主体间的传播中,既确定了对于自身而言的自我的存在,也确定了对于他人而言的自我的存在。从这种意义上说,受众是传播关系中的主体,其主体性在传播主体间延伸,亦即在传播主体与主体的相互理解、相互承认、相互沟通、相互影响中延伸。只有这样,受众才能存在并有可能实现其生命存在的意义。
二、公众的类主体化
按照麦奎尔的说法,西方的受众概念起源于戏剧、竞技和街头杂耍的观念群,起源于不同文明、不同历史阶段所出现的所有不同形态的参与“演出”的成批观念。在他看来,尽管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前媒介”受众的某些基本特征仍然保留了下来,并影响到我们的理解和期待。受众是这样一种大众的集合,通过个人对愉悦、崇拜、学习、消遣、恐惧、怜悯或信仰的某种获益性期待,自愿作出选择性行为,在一种给定的时间范围内形成。它受到统治者可能的或实际的控制,因而是一种集合行为的制度化形式。印刷问世之后,受众概念首次重大的历史补遗是“读者大众”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个人阅读行为产生了对特定作者和风格类型(包括报纸)的崇尚和趋附。当社会在印刷时代开始经历社会的和政治的变革时,读者大众还促进了利益、教育、宗教和政治共识等方面的总体分化,帮助奠定了正在形成的公众概念。(注:丹尼斯·麦奎,1995年,“媒介受众理论”,王瀚东译,载《新闻学探索录》,武汉大学出版社。此文译自麦奎尔的专著《大众传播理论概述》的第六章。)其实,"audience"(受众)最原始的词义是“倾听”,特指注意所听的话。它是在主体间的传播过程中存在的,恰当的译法应该是“阅听人”。麦奎尔所述表明它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被重构,媒体越来越迷恋于吸引、操纵阅听人,使他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按利益、教育、宗教和政治共识组合成“接受影响的公众”。而媒体的职业兴趣就在于以多种方式记录一系列数据:从一个信息的“可能公众”,到实际出席的“有效公众”,到其中的“特定信息的公众”,再到被传播实际“影响”的公众。至于意义的分享、相互的理解、文本的诠释等内在于传播过程中的因素,则完全忽略不计,以致越来越远离传播的性质。
在越来越精致的传播理论中,这种把阅听人视为大众的方式可谓令人眼花缭乱,大致包括4种形态,即作为读者、听众、观众的受众,作为大众的受众,作为公众或社会群体的受众,作为市场的受众。(注:丹尼斯·麦奎,1995年,“媒介受众理论”,王瀚东译,载《新闻学探索录》,武汉大学出版社。此文译自麦奎尔的专著《大众传播理论概述》的第六章。)这些探讨都表现了“类主体化”的倾向。所谓“类主体”,就是强调主体的集约性、群体性和人类性。对此,有两种对立的思考方式,一是把“类主体”看作是“许多单个人本质的抽象直观”,通俗一点说,就是类的聚合;一是把它看成是内含各种关系于自身的整合形态。前一种思考方式既取消了主体间性,又因为类的聚合而消解了主体性。如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就在社会学层面上把人分为“局外人”和“局内人”,即一般的公众和少数“社会贤能”,认为公众仅仅是一个幻影,一个抽象的东西,“仅仅是那些对某件事感兴趣的一些人而已”。它没有知识和理性判断能力,其能够影响政策制定的惟一方式就是支持或反对那些有权力和知识去采取行动的人。(注:罗纳德·斯蒂尔,1982年,《李普曼传》,于滨等译,新华出版社,第329页。)后一种思考方式注意到主体间的整合,只是类主体如何由主体间整合而成,还是付之阙如。例如在杜威(Dewey)看来,公众是“个人间通过对公共问题和解决方法的共识而形成的作为社会单位的政治集合”。它需要开放、自由的传播,以便提供当前事实的报道,在分享公共利益方面讨论个人行为和协作行为的价值。他相信传播扮演着重要的认识角色,不是把知识从一个人传播到另一个人的简单角色,而是创造知识的丰富意义。这源于他对传播的独特理解:
“传播是人类生活惟一的手段和目的。作为手段,它把我们从各种事件的重压中解放出来,并能使我们生活在有意义的世界里;作为目的,它使人分享共同体所珍视的目标,分享在共同交流中加强、加深、加固的意义。……传播值得人们当作手段,因为它是使人类生活丰富多采、意义广泛的惟一手段;它值得人们当作生活的目的,因为它能把人从孤独中解救出来,分享共同交流的意义。”(注:转引自Carl,Bybee,1999,Can Democracy Survive in the Post-Factual Age?A Return to the Lippmann-Dewey Debate about the Politics of News,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Vol.1,No.1,Spring.)
在这里,公众存在于“分享共同体所珍视的目标”、“分享共同交流的意义”之中,它通过参与式传播融入到共同体生活之中。由于注重参与式民主,他提升了主体间意义分享的价值,并反对利用公众的惰性、偏见与冲动,以达到宣传控制的目的。
如果说杜威告诉了我们公众通过参与式传播融入到共同体生活的过程,那么,李普曼则无意中触及了孤立的个人与被群体化的个人的一种生活结局。在他看来,公众与生俱来是非理性的,其大脑机能中存在的“固定的成见”(stereotypes),使得它常常通过人的感情、习惯和偏见来认识客观世界;同时,它在现实交往中是被动的,它只能根据人家的报道所提供的情况来采取行动。其实,应该反过来思考,在一个民主的社会,恰恰是人外在于主体间的传播关系,处于孤立的状态,或者人被群体化和失去自我,才产生了他所说的这些现象。
随着媒介环境的改变,特别是美国新闻自由委员会和英国皇家报业委员会均观察到,无论是媒介的私人垄断还是媒介的公共垄断,都已逐渐威胁到了个人自由,并认为要把媒介办成公共论坛,广泛吸收民众参与,形成人与人、媒介与受众的互动,以此使媒介负起社会责任。与此同时,电视、电脑等新传播技术已把传播推向社会变革第一线,其互动性、个人化、小众化的特性已迫使研究者不得不去关注传播系统中的信息交流过程,并且在一个高度互动的传播系统中,已经不可能划分出“来源”和“受众”,相反,每一个人都是“参与者”。尽管如此,受众的类主体化现象并未消失。
三、在生产意义过程中消费的受众
上述“受众商品化”的分析部分地借鉴了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W.Smythy)提出的“受众商品论”。他曾描述了这样一种事实:大众媒介生产的消息、思想、形象、娱乐、言论和信息,不是其最重要的产品,只不过是引诱受众来到生产现场——媒介前的“免费午餐”,最重要的产品其实是受众。媒介根据受众的多寡和质量(年龄、性别、文化程度、收入等人口指标)的高低(也就是购买力的强弱)向广告客户收取费用。因此,媒介公司想做的其实就是将受众集合并打包,以便出售。而对于“免费午餐”的享用者——受众而言,他们不仅仅在消磨时光,还在创造价值,这种价值最终是通过购买商品时付出的广告附加费来实现的。与此同时,受众在闲暇时间付出了劳动,为媒介创造了价值,但没有得到经济补偿,反而需要承担经济后果。后来,又有人补充说,广播电视生产的商品并不是实际的受众,而只是关于受众的信息(观众的多少、类别的形成、使用媒介的形态)。媒介与广告客户之间的交易,是通过收听收视率进行的商品交换,而由这种交换过程中产生的商品,是收听收视率这种信息性、资料性的商品,而不是有形的商品。(注:参见郭镇之“传播政治经济学理论泰斗达拉斯·斯迈兹”,载《国际新闻界》2001年第3期。)这样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受众被物化的政治经济学背景。然而它仅仅是在经济决定论的思维框架内看到了受众被降低为无生命的商品的事实,在“主-客关系”范围内把受众当作被动的客体。显然,这并不能真正达到我们批判受众商品化的目的——恢复人的主体性,进而恢复人的主体间性传播关系。也就是说,虽然批判了受众商品化现象,但没能真正地拯救受众。
类似的现象在法兰克福批判学派那里也存在。如阿多诺(Theodor W.Adorno)、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等人曾作出批判性发现,所有的大众媒体均为具有相同的商业目的和经济逻辑的企业体系。不仅政治经济结构决定媒体意识形态,而且媒体意识形态又决定受众的意识形态。在他们看来,文化工业的产品对受众具有绝对的决定力量,人们在文化工业面前是那样的无助,甚至无法知觉自己所相信的意识形态就是奴役自己的意识形态。(注:参见张锦华,1994年,《传播批判理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第12~14页。)他们所要批判的是,大众文化的商品化、标准化、单面性、操纵性、控制性的特征压抑了人的主体意识,压抑了人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自由发挥,助长了工具理性,进一步削弱了在西方业已式微的“个体意识”和批评精神;同时,由于现代社会组织和意识形态长期推行的非个性化和单一化,大众已经变成了一种固定不变的、单质的群体。他们清楚地意识到,文化工业正处心积虑地将消费者纳入它的统一框架之中,它无疑是在悉心探究千百万大众的意识和无意识状态,但大众在文化工业中占据的不是主位而是客位,他们不是主体而是对象。对崇尚主体性的人来说,这是极为“有力”的批判。但是,只要我们仔细想想,就不难发现,他们所得出的结论其实早就蕴涵在前提之中,也就是说,他们在前提里就认为受众已失去主体性,或者只剩下单一的经验主体,只能被外物或外在的政治经济结构所驱使,只能是文化工业统治的对象。正如有些人所批评的,真正的受众在阿多诺眼中或许是退化过头了,返回到了婴儿水平。(注:参见陆扬、王毅,2000年,《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第62~63页。)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原因恐怕在于他们把批判限制在意识和精神领域,相应地,主体也被局限在自我意识、自我精神的表现之内,不再有实践主体,也不再有主体的创造。这种既远离传播实践活动又不能超越自我的“主体”,当然是易于被媒介摆布了。其实,这样就取消了人的传播实践,取消了主体间的传播关系。
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在对“公共领域”的早期研究中也曾陷入这种理论困境,假设在政治经济结构势力的工具理性的渗透之下,受众的自主性逐渐消失,不自觉地走进大众文化包装精美的价值观及假象中,成为被动、驯化、非理性批判的主体。
后来,“交往理性”(communication rationality)概念的提出使他摆脱了这一理论困境。他大胆假设人类理性不仅只是目的理性(或工具理性),而且同时具有“交往理性”。前者假设人们有意识地影响他人,以成功地达到其目的为宗旨;后者则假设主体皆具有普通的“交往理性”,自主并真诚地愿意在互动沟通的过程中追求真实,若没有压迫性社会力量的介入,所有参与传播的人都能有相同的机会,自主地选择及使用言辞行动,相互质疑言辞内容的真实性或合理性,即可达到有效的沟通。(注:Habermas,Jurgen,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Vol.I,(trans.)Thomas,McCarthy,Boston:Beacon.转引自张锦华,1994年,《传播批判理论》,台湾黎明文化事业公司,第218页。)由此看来,虽然媒介在商业化背景下强化了工具理性,目的性很强地“捕获”受众,但并不能否认媒介工作者和受众均具有追求自主、真实的理性基础,能应对大众文化的商品化、标准化、单面性、操纵性、控制性的压力。在这里,他所强调的交往理性主体,并非工具理性中的以自我为中心的主体,而是相互沟通的主体,即处于相互尊重、相互开放的意见论辩过程中的主体。这就呈现了人类传播活动的本质和理想境界,树立了具有主体间性基础的传播价值理念,同时,又对社会压迫性力量的介入所造成的“扭曲传播”(distorted communication),以及弱势群体的传播能力受到压抑而导致的“假传播”(pseudo-communication)构成了有力的批判。
霍尔的“编码-解码”理论虽然是针对媒介文本的,但其理论贡献却主要表现在改变了实证主义研究对传递者与受众关系的线性理解,提出了一个重要的理论模式,即意义不是传递者“传递”的,而是接受者“生产”的,从而也在主体间传播关系中重构了受众观念。用他的话来说,在传播过程中,“不赋予‘意义’,就不会有‘消费’”;在一个信息“产生效果(不管如何界定),满足一种‘需要’或者付诸‘使用’之前,它首先必须被用作一个有意义的话语,从意义上被解码”;被实证主义研究所孤立理解的效果、使用与满足,都是“由理解的结构来构架的,也是由社会经济关系来生产的”。(注: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王广州译,载罗钢、刘象愚主编,2000年,《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46~348页。)从这一理论观点出发,霍尔认为编码与解码没有必然的一致,并提出了三种假设的解码方式。其一是“主导-霸权立场”(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的阐释方式,即从信息所提示的预想性意义来理解,意味着编码与解码互相和谐,受众“运作于支配代码之内”;其二是“协商代码或协商立场”(negotiatedcode or position),这似乎是大多数受众的解码立场,既不完全同意,又不完全否定。一方面承认支配意识形态的权威,另一方面也强调自身的特定情况,受众与支配意识形态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商议过程;其三,受众“有可能完全理解话语赋予的字面和内涵意义的曲折变化,但以一种全然相反的方式去解码信息”,也就是根据自己的经验和背景,读出新的含义。(注:斯图亚特·霍尔,“编码,解码”,王广州译,载罗钢、刘象愚主编,2000年,《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56~358页。)这种视角的转变不仅仅意味着发现了积极“生产”意义的受众,而是把受众纳入到了主体间传播关系之中,揭示了阐释过程中所隐含的社会经济关系。通常的受众研究只把受众当作信息的消费者,而把意义生产的权利天然地赋予信息制作者。所谓收视率调查,常常只表明观众“消费”了某一节目,很少说明观众如何解读节目的意义。显然,霍尔的研究使这一问题显现出来,直接成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受众接受行为的理论背景。如莫利(D.Morley)的《全国报道的观念》(The"Nationwide" Audience)、《家庭电视》(Family Television),莱恩·昂(L.Ang)的《观看达拉斯》(Watching "Dallas")等,都对霍尔的这一理论做了进一步的注解。
菲斯克(J.Fiske)则详细阐述了一套建基于“编码-解码”理论之上的通俗文化理论,对受众问题做了有价值的发挥,首先,他提出大众并不是一个单质的整体,而是包含了各种由于利益关系、政治立场和社会联系而形成的群体,是一个复杂的多元的组合;其次,他认为,大众文化不是一般的商品,它不仅在财政经济体制中流通,也在与之平行的文化经济体制中流通,前者流通的是金钱,后者流通的是意义与快感。这一区分体现了灵活的批判意识,使人明确受众的两种处境:一是在财经经济体制中,媒介生产的商品是受众,受众成了被动的角色;二是在文化经济体制中,媒介向能产生意义和快感的受众播放节目,这时的受众成了意义的“生产者”,成了文化创造者。这就构成了对大众文化的双向批判;第三,他把文化定义为特定社会中社会意义的生产和流通,这种生产和流通既依赖于文本提供的意义框架和空白,又依赖于读者或观众积极的参与和创造,因此,受众与文本的关系必然十分复杂。由于受众千差万别的社会特征,必然会产生千差万别的“生产性文本”。所谓文化是一个充满生命力的积极过程,就是在这种互动中显现出来的。(注:此处参阅罗钢、刘象愚主编,2000年,《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34~36页;陆扬、王毅,2000年,《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三联书店,第111~117页。)
我们看到,文化研究学派的学者过多地关注文本,局限于语言交往层面,多少限制了他们反思受众主体的深度和广度,难以涵盖人类的传播实践。对于他们的受众学说,我们还有一个超越的方向,就是把多极主体及其互动当作人类传播活动的价值之源,在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的多维层面上,探寻受众存在的奥秘与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