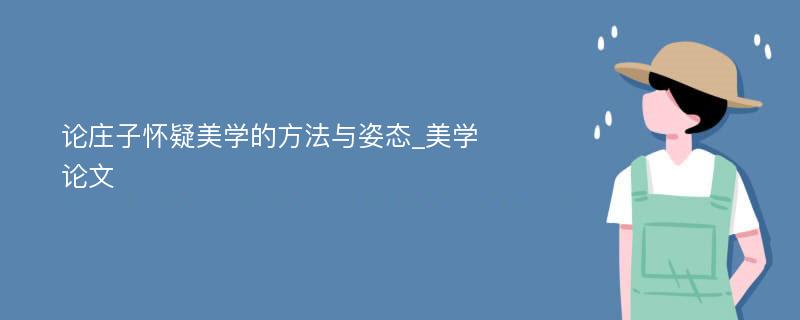
论庄子怀疑论美学的方法与姿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怀疑论论文,庄子论文,美学论文,姿态论文,方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安宁”(Ataraksia)和“无言”(Aphasia)既构成怀疑论的精神象征之一,也为怀疑论者超脱世俗生活诸多负累的心灵工具。怀疑论者以“安宁”与“无言”达到领悟生命价值与意义的哲学境界,并澄明他们美学化的人生态度。作为一个伟大的怀疑论者、诗人哲学家的庄周,他阐发出一系列怀疑论的概念和方法,希冀实现对生命存在的诗意超越,从而达到精神的绝对自由和最虚无化的美。本文从方法论和审美论的视角,探究庄子怀疑论美学的方法与姿态。
一、悬解心灵之蔽
庄子认为存在者在世界上生存,由于物象的干扰和内心的欲望必然面临着诸多的精神苦闷,而由于物质和知识的限制又使主体处于不自由和非审美的境遇。精神哲学的首要责任就是悬解心灵之“蔽”和消除精神的痛苦,因此必须寻觅某些方法和策略去承担这种责任。于是,庄子通过自我的哲学运思寻求出一系列的悬解心灵之蔽的方法论,并使这些方法论进一步转换为生命存在的审美论。
a.“县解”。《养生主》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县”,《道藏》林希逸本作“悬”。宣颖云:“人为生死所苦,犹如倒悬,忘生死,则悬解也。”[1] 陈深云:“‘悬’,如‘倒悬’之‘悬’,困缚之义。”[2] “悬解”并非如诸多注家认为的那样,仅仅作为解脱生死之烦的专用工具,它还兼有其它的重要功能。如同怀疑论的“悬搁”(Epoche)方法一样,它可以承担对诸多问题的存而不论的态度。庄子哲学的悬解,既蕴含对生死问题的超越,也包括对于知识形式的存而不论;既有对情感“哀”与“乐”的加括号,也有对价值观念的中止判断。庄子的悬解可以阐释为怀疑论的“安宁”或“无言”的超越方式,因此可以摆脱现象界的矛盾,从种种对立的命题之中抽身而隐逸,进而获得心灵的平静和愉悦,达到无差别的审美境界。
b.“心斋”。庄子对付心灵之蔽的另一药方为“心斋”。庄子借颜回请教孔子的问答描述了“心斋”:“回问:‘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人间世》)对此,杨安仑先生有精辟之论:
所谓“心斋”就是“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要能做到物我兼忘,用“道”来指导和统摄自己,而“道”的特点就在于“集虚”,要使个人的心境也能“集虚”,这就要去“名”去“知”,因为“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不为名,就不会与人相倾轧,不为知,就不会与人争辩。这样一来,就去掉了一切物欲,去掉了一切好胜心,做到和光同尘,形如槁木,心如死灰,才达到了“心斋”的境界。[3]
的确,庄子消极回避一切人世的名利和知识的纷争,希望逃逸到一个无知无欲的超然境地。然而,其隐蔽的哲学蕴意还在于,庄子设置了一个“虚无”的思维境界,既让思想者悬搁心灵的成见或偏见,达到精神的澄明和空诸一切,又通过以它来消解一切意识形态的聚讼,化解名利和知识的争斗,因此实现精神界的的和解和大同,使心灵回归原初的纯净状态,从而使审美在人世间得以可能。所以,庄子之“心斋”,既是哲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也呈现了美学的超越旨趣。
c.“坐忘”。庄子的怀疑论充盈着机敏和智慧,喜好以隐喻的方式陈述深邃的思想。《大宗师》云:
颜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谓也?”曰:“回忘仁义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也。”曰:“何谓也?”曰:“回忘礼乐矣!”曰:“可矣,犹未也。”他日复见,曰:“回益也!”曰:“何谓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蹴然曰:“何谓坐忘?”颜回曰:“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仲尼曰:“同则无好也,化则无常也。而果其贤乎!丘也请从其后。”
王夫之解道:“先言仁义,后言礼乐者,礼乐用也,犹可寓之庸也,仁义则成乎心而有是非,过而悔,当而自得,人之所自以为君子而成其小者也。坐忘,则非但忘其物,而先自忘其吾。”[4] 今人曹础基认为:“《人间世》的‘心斋’,《刻意》的‘养神之道’,本篇的‘息之以踵’、‘坐忘’等等,已不属于养生方法的范畴,而成为书中理想人物的处世为人的基本态度。借以宣传消极的人生观,引导人们进入一种寂静颓丧的精神境界,企图排除世事的‘骚扰’,强作清淡无为、神乎其神的姿态,藉以慰己,藉以骗人,其实一部《庄子》,不知多少悲哀、多少牢骚、多少仇恨,又哪能忘!又哪能斋!”[5] 还是王夫之体悟到庄子的思想精髓,“坐忘”并非限于忘物,而首先在于忘却“自我”,怀疑不仅仅在于怀疑物象而首先在于怀疑“自我”,这才是怀疑论的逻辑起点和思维特征,也是庄子玄思的风韵所在。而后者的解释则以价值论的狭隘眼光估衡庄子,凭借当今语境的社会学的实践意志要求古代的思想家确立一种理性化或理想化的人生态度,未免存在着苛求古人的嫌疑,也呈现当代学者受意识形态的制约而难免流于思维的机械刻板。
庄子此处语境的“坐忘”,依照当今的话语,就是屏弃虚假的意识形态,它至少隐含着如此的思想结构:其一,“坐忘”道德意识和价值准则。庄子以他特有的思维幽默,虚设出道德象征者孔子与颜回的对话,解构了儒家的价值中心“仁义礼乐”,他借颠覆传统的道德意识来澄明自我的思想:存在者所信仰不移的精神偶像往往也是毫无意义的东西。其二,“坐忘”感觉机体或知觉器官。在怀疑论者看来,存在本体所攫取的任何感知都是相对性质的,因而依赖生物性的有机体所得到的心理经验的结果当然也是可疑的,所以庄子主张“堕肢体”。其三,“坐忘”精神上的“聪明”,因为它恰恰构成了心灵的“累”,导致意识形态的纷争和种种因此而来的社会悲剧。其四,“坐忘”知识形式和认识活动,因为知识和认识必然是有限的和不自由的,并且带来精神的苦闷和烦恼,只要抛弃了它们才可能使存在者获得彻底的绝对的解放和自由,同时消除掉精神的苦痛和忧愁。倘若达到以上的境界,就可以“同于大通”,消解现象和精神的所有差别,从而接近“道”的混沌境界,获得真正意义的幸福和审美愉悦。其五,在《庄子》的其它语境,“坐忘”还包含忘却死亡之忧的思想内涵。所以王夫之云:“坐可忘,则坐可驰,安驱以游于生死,大通以一其所不一,而不死不生之真与寥天一矣。”[6] “坐忘”之术,也是庄子的“养生之道”的组成部分。超越死亡的忧思符合于心理健康的目的,荣格认为:“我深信把死亡当作是人生之目标则是最卫生的,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那处处想逃避死亡的人则是不健全的、不正常的,这样做就等于丧失了后半生的目的。因此,我认为,相信宗教的来生之说是最合乎心理卫生的。”[7] 荣格的论断导源于西方文化语境,因为西方存在着普遍的宗教意识,因此宗教的来生之说是芸芸众生借以宽慰死亡之忧的精神工具。而庄子采取“坐忘”的方法超越死亡的忧悒,更具有哲学的形而上意味和东方的诗性智慧。其六,“坐忘”还潜藏着忘却“情感”之累的思想。《德充符》云:“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所以庄子主张理想人格状态:“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德充符》)对于情感,庄子表示出怀疑的意向,认为它构成对人的本真存在的遮蔽,限制于精神于是非的苦恼之中,而唯有通过“坐忘”消除情感之累达到“无情”境界,人才能获得自我的解放。看来,庄子的“坐忘”构成了其怀疑论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环节,借助于这种“坐忘”的精神方法,从而达到他否定道德意识和感觉经验,抛弃聪明和知识形式,超越死亡恐惧和情感之累的哲学目的。
二、超越物质之限
人作为生命的存在个体,生存于世界之中,除了受到精神的蔽惑之外,也必然受到物质的限制,因此,人面临着双重的不自由和烦恼。庄子哲学以自我的怀疑论方法同样展开对物质之限的抗衡,从而寻觅一个审美的诗性境界。庄子认为主体受物质之限主要指向这几层面:时间空间,器物工具,语言文字。等等。而他则发明了对付这些限制的相应手段,诸如:
a.“逍遥游”。时间与空间构成生命存在的首要的物质束缚,有鉴于此,庄子首先采取对时空的哲学否定。庄子对于时空的否定体现出一定的哲学智慧,他没有采取逻辑的思辨方式,而是借助于诗意想象和直觉体验的方式。因为作为客观存在的物理时间和物质空间是绝对的和无限的,采用逻辑实证的方式不可能得出否定的结果,唯有借助于生命的情感体验或者想象力虚设的精神境界,去抗衡它们的物质性存在,以诗意的和审美的方式去征服它们的实体性结构,从而达到虚拟性的情感否定的结果。
《庄子》首篇即为“逍遥游”,也为其哲学旨趣的出场和澄明。“逍遥”一词,出现较早,《诗经·郑风·清人》中就有“河上乎逍遥”。《楚辞》多次出现“逍遥”,如《离骚》中“聊逍遥以相羊”。《湘君》中“聊逍遥兮容与”。《远游》中“聊仿佯而逍遥”。《文选·秋兴赋》李善注引司马彪语云:“言逍遥无为者,能游大道也。”唐人陆德明认为以“逍遥游”名篇是取其“闲放不拘,怡适自得”[8] 的意思。罗勉道云:“神游寥廓,无所拘碍,是谓逍遥游。”[9] 庄子“逍遥游”的物质承载者为“鲲鹏”,笔者以为它们实际上届于神话思维的象征品,或者称之为诗意思维的审美符号,只是庄子精神的虚拟化的想象果实,也就是怀疑论美学所宣称的具有精神无限可能性的直觉品,为最高的虚无化的和纯粹的美,象征着绝对的心灵自由。晋代阮修作《大鹏赞》云:“苍苍大鹏,诞之北溟。假精灵鳞,神化以生。如云之翼,如山之形。海运水击,扶摇上征。翕然层举,背负太清。志存天地,不屑雷霆。莺鸠仰笑,尺鷃所轻。超然高逝,莫知其情。”[10] 以诗意的语言对“鲲鹏”予以赞美,领悟了《逍遥游》这则“寓言”所寄寓的审美超越的精神内涵。庄子依赖“鲲鹏”首先去征服空间的限定,“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逍遥游》)这里所谓“三千里”和“九万里”及“六月”绝非是实数的概念,而寓意空间和时间的无限,鲲鹏在转瞬之间可以达到无限速度的空间运动,而一旦飞翔了“六月”,物理空间的制约无疑被征服和消解,主体实现空间的自由运动的审美愿望。随着空间限制被消解,必然带来对时间的逻辑超越。速度无限的空间运动使时间延缓和拉长,从而使有限的生命存在得以延伸。再者,庄子设置了超越时间限定的对象:“楚之南有冥灵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和上面一样,这里的数字仍为“虚数”,实际是蕴含“无限”的意思。庄子借助于神话的或诗意的象征品作为超越时空之限的心灵工具,以此领取一张进入无限自由境界的通行证,同时也获得纯粹意识的审美愉悦。然而,无论是“鲲鹏”还是“大椿”,它们的对空间和时间的克服仍然还是有限度的,因为它们本身仍然是物质性的,以物质去克服物质依然属于“有待”,因为它们必然受到物质形式的限制,庄子的思维方式里,克服时间和空间的最为理想的工具是精神存在,因为绝对的虚无精神(道)是“无待”,庄子凭借“无待”抗衡物质的限制,这一点为郭象《庄子注》所阐释。王夫之对此也有精湛之论:
寓形于两间,游而已矣。无小无大,无不自得而止。其行也无所图,其反也无所息,无待也。无待者,不待物以立己,不待事以功,不待实以立名。小大一致,休于天均,则无不逍遥矣。逍者,向于消也,过而忘也;遥者,引而远也,不局于心知之灵也。故物论可齐,生主可养,形可忘而德充,世可入而害远,帝王可应而天下治,皆脗合于大宗以忘生死;无不可游也,无非游也。[11]
王夫之以自我的阐释进一步拓展了“无待”的思想内容。清人胡文英云:“无所待,故得逍遥;若有所待,便是倚着于物而不能逍遥矣。”[12] 清人王先谦也云:“无所待而游于无穷,方是《逍遥游》一篇纲要。”[13] “道”是“无待”,它属于纯粹的精神本体或混沌化的存在者,可以完全地克服时间和空间的制约,使物质本体和精神存在都能够获得绝对的自由和纯粹的审美。有学者甚至超越庄子哲学的历史语境,凭借现代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进行言说:
庄周希冀通过主体的超越意识,冲破时间与空间的樊篱,跨越无限的历史长河从而获得个人的解脱和精神上的自由,这种借助主体精神的提升,直接打通天人之路的构想,有益于人的自觉。但是现实的人与人的现实社会割不断的,个性的解放是与解放人的社会割不断的。现实的解放,只有通过革命性的实践,打破私有制的闭锁以及所引发的异化,才能实现至仁、至贵、至富、至愿的大同理想。人的自由本性,也只有在实践中,在人对自然的改造和自然的人化过程中,才能历史地得到确证,庄周从纯粹的个人因而也是抽象的人出发,当然无法消除灵与肉、道与物、明与知的裂谷,他错误地对有限和无限进行量的比较,终于陷入相对主义,这使得他顺物——游心的人生哲学充满了矛盾。[14]
这不免于诸多“偏见”。且不说真正有价值的哲学往往包含矛盾或悖论,西方如康德哲学,中国如庄子哲学。客观地说,前面的看法,如“庄周希冀通过主体的超越意识,冲破时间与空间的樊篱,跨越无限的历史长河从而获得个人的解脱和精神上的自由,这种借助主体精神的提升,直接打通天人之路的构想,有益于人的自觉”。确有一定的合理内核。然而,其后认为只有借助社会革命的方式和实践理性的态度达到庄子所期待的人的自由和解放,这实际上依然社会历史意义上的“革命情结”或“征服癖”的无意识流露,这是以实证的方式解决审美的问题,以政治学的理论来阐释美学的命题,以逻辑主义的知识论来取代庄子的生命存在的智慧论,因此存在着一定的思想弊端。其实,革命性的社会实践,如消灭私有制并非能随之消除人性异化,兑现神话式的理想社会的神圣承诺,更不能由它充当人的精神的无限自由的审美工具。因为就历史上的残酷事实而论,社会革命的“自由”往往蜕变为非理性暴力和欲望满足的本能释放,招致人性的毁灭和美的沉沦,不但不会有助于人性或存在本质的理想状态,达到所谓虚假意识的“大同”或者乌托邦式的“理想国”,反而会走向理想的反面:人性的溃灭和美与诗意被流放。倒是庄子的纯粹精神的方式或审美乌托邦式的“逍遥游”,似乎比社会革命的方式更完善更合适,因为它的确还能部分地承担起拯救人性、恢复良知的神圣责任。
还有学者认为:“庄子及其后学思想中尚没有形成明确的‘无待’概念,因此不可能提出这样的概念范畴。”“事实上,用‘无待’来解释庄子的思想也并不十分贴切。”[15] 而另一位学者则反诘道:“似乎没有充分注意到‘观念、概念、范畴’这三个概念间的分别。”[16] 其实,所谓“观念”、“概念”与“范畴”之类,均是西方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思维结果,为知识论哲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抽象产物,只能有限度地运用于中国古典哲学的语境。生存于20世纪乃至于21世纪的中国学者实在面临着西方话语的悲剧性压抑,我们有限地借鉴于西方某些的话语和思维方式,还可以承受也可以理解,因为整个人类的思想文化具有相对的通约性。遗憾的是,我们众多的学者将西方思想界的观念和结论作为自我思维的前提和结论、理论标准和价值准则就是知识与思想的双重悲剧了。而上述两位学者均未能逃脱扮演如此的知识悲剧的角色,而笔者似乎也无法完全超脱如此可悲的境域,但希冀于绝望和顽强地抗争,因为怀疑论美学拒绝接受思想鹦鹉的角色。
b.“吾丧我”。物体和器具构成生命存在的另一层物质限定,庄子斥拒其限制的方法之一为“吾丧我”。自然物象或者人工制作的器具、工具等等,对人的存在具有二重性:一方面它们成为人类生存的资料或工具,给人类带来维持生命存在的物质条件和必需品,另一方面,它们又势必导致对人类自由和审美活动的束缚。因为物质会引诱其本能化的欲望,从而使人心堕落,同时,器具或工具是知识或心智的产品,会使心灵失掉宁静和澄明,走向目的性和欲望意志。《齐物论》云:
南郭綦隐机而坐,仰天长嘘,荅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侍立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子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
“吾丧我”超越知识、逻辑、语言、情感、欲望等遮蔽的非认识形态的精神方式,是无思和无知之境,栖居于这一境界,部分类似于海德格尔所云“我们可以想象诗人有时诗意地居住”。[17] 庄子的“吾丧我”的精神策略,虽然蒙上一层消极和神秘的精神阴影,然而也不失为抵御物质压抑和诱惑的心灵工具。所谓“地籁”为物象存在与诱惑,“人籁”为心智发明的器具或工具,都构成对心灵宁静和超越的限制,唯有领悟“天籁”的意蕴的心灵,才知道自然之道是“无为”和“自己”,才可能逾越物质的制约和诱惑。另一方面,“吾丧我”还表现为庄子否定所有的人的心智及其所发明的器物或工具,认为对它们的彻底的毁弃才可能消解内心的欲望和使精神达到“无知”和平静。
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擿玉毁珠,小盗不起;焚符破玺,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争;殚残天下之圣法,而民始可与论议;擢乱六律,铄绝竽瑟,塞瞽旷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聪矣;灭文章,散五彩,胶离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毁绝钩绳而弃规矩,攦工捶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胠箧》)
“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天地》)
从常识上看似乎荒谬和偏激,庄子不仅否定物质存在和技术工具,还否定知识和权力的力量,否定道德价值和法律准则的应有社会作用。然而,这正是庄子哲学的思想魅力和美学风度之所在。他恰恰是凭借“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来阐述自我的独特之思,他运用了诗意的和审美的方式对待世俗问题,这种方式当然是不可能解决上述的现实问题,只不过提供一种富有想象力的哲学解答而已,或者在美学意义上,提供一种超越物质存在、技术工具乃至社会准则的审美精神和诗意情怀而已。所以,庄子不可能也拒绝于担当实践的政治家和社会学家之责任,而只能承担一位逍遥于世俗世界之外的诗人和审美者的超人角色。
c.“大美无言”。语言或文字构成了精神存在的另一重物质性遮蔽。他认为“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齐物论》)“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齐物论》)“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外物》)“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语言既乔装了思想也偷换了思想,当然也必然会歪曲心灵和难以担当传递心灵所在的任务。所以,庄子对语言或文字采取怀疑论的态度。这一态度,也可以视为文化的继承,因为《易·系辞》中就是“言不尽意,书不尽言”的言论。然而,庄子对于语言的遮蔽性是着眼于美学意义而言的。在庄子看来,语言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它只能属于精神的外壳或碎片,或者是心灵被扭曲了的幻象形式,因此它不可能反映精神深处的本质性结构,所以,庄子认为“得意而忘言”才是思想者的终极目标。而对于精神无限可能性的审美活动来说,更不能依赖语言这个孱弱的物质工具。因为攀登神秘奇丽的美的峰峦,语言只能是一个残破的拐杖。更重要的缘由在于,作为精神的最高的虚无化存在——美,不能借助于语言这个物质符号进行传达,唯有依赖于生命中最深层的直觉和体验来把握,依赖于生命存在的智慧和诗性来进行自我领悟和自我提问。所以,庄子提出“大美不言”的美学命题。这一思想影响到后来的魏晋玄学,尽管欧阳建写作了《言尽意论》和“言不尽意”论进行争论,然而无论其思维深度还是精神张力均逊色于同时代玄学家们的“言不尽意”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就是他忽略了语言在审美活动和艺术活动之中的局限性,忽略了它对于生命个体的智慧和想象力的束缚机能。而庄子以其生命的大智慧和想象力,领悟到了语言对于审美的限定性,所以他意识到审美活动必然要超越语言这个物质符号或物质工具,并且藉此获得诗性智慧和心灵直觉之可能。庄子的思维似乎存在着偏激的倾向,我们也许会从其表层意义上得出庄子主张完全抛弃语言工具或文字符号的结论,然而,这属于他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的修辞美学的策略,并非是他深层的思想。其实,庄子对于语言与文字的作用或功能极其注重,他本人就是操纵语言魔方的高手,尤其是他与挚友惠子的之间的对话,上演了精妙绝伦的语言游戏。而《庄子》一书,至少“内篇”和部分“外篇”由他亲自撰写,其运用语言文字的水准达到近乎神化的妙境。有鉴于此,我们如何能轻易断言庄子彻底否定语言的传达思想的功能。
[收稿日期]:2007—01—20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怀疑论美学”的阶段性成果之一,项目编号:01ZXB0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