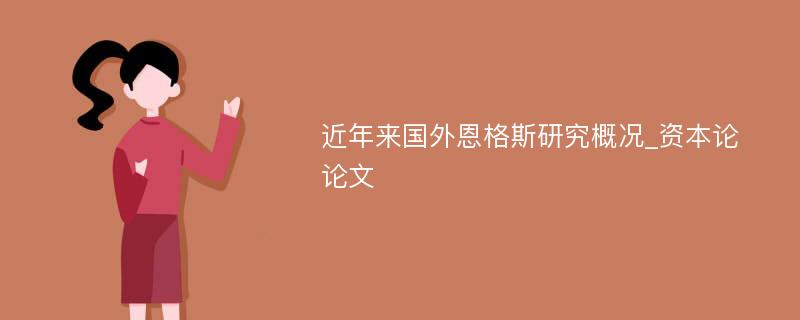
近年来国外恩格斯研究概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恩格斯论文,概况论文,国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马克思的终身合作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恩格斯的历史地位和理论无疑是不可质疑的。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前,他们的思想不仅遭到资产阶级学术界的歪曲和攻击,而且也受到来自马克思主义者内部的曲解。在马克思逝世后尤其在恩格斯逝世后,西方学者中(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和马克思学学者)逐渐形成反对恩格斯的浪潮。按照美国学者诺曼·莱文的界定,历史上曾出现了两次反对恩格斯的浪潮:第一次浪潮形成于1897—1914年;第二次浪潮形成于1923—1939年。(注:诺曼·莱文《辩证法内部的对话》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页。) 实际上,自从1961年英国马克思学学者乔治·利希海姆(George Lichtheim)出版《马克思主义:一个历史和批判的研究》,系统地阐述马克思思想和恩格斯思想之间的对立之后,就逐渐形成了以乔治·利希海姆、吕贝尔(M.Rubel)、诺曼·莱文和特雷尔·卡弗(Terrell Carver)为代表的马克思学学者的第三次反对恩格斯的浪潮。当然,相应地,西方学者也形成了与反恩格斯浪潮相对立的维护恩格斯的浪潮。在恩格斯逝世后的百年里,在西方学者中,逐渐形成了“马恩对立论”和“马恩一致论”两种主要观点相互对立的局面。从历史上来看,在20世纪60年代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这种观点是西方学者的主流观点。但是,从60年代开始,强调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存在重大的差异乃至对立的观点开始形成并占据了主导地位。进入90年代之后,西方学者又回到了最初的观点,认为“马恩对立论”的解释严重低估了两人“人道主义、改良主义、决定论和实证主义等重要问题上基本一致的思想看法”。(注:B.Manfred Steger and Terrell Carver,eds.Engels after Marx.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1999,p.6,pp.6—7,p.137,p.197,p.182.)
近十年来,西方学者对恩格斯的兴趣日益增强。在1995年恩格斯逝世100周年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发表150周年之际,西方学者频频召开纪念恩格斯国际研讨会(1995年在德国乌泊塔尔、法国巴黎和日本东京召开了国际恩格斯研讨会,在英国曼彻斯特召开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国际研讨会),左翼杂志纷纷开辟恩格斯研究专题(例如,英国《国际社会主义杂志》1995年第181期纪念恩格斯专辑和美国左翼杂志《科学与社会》1998年第62卷第1期纪念恩格斯专辑),关于恩格斯的书籍亦不断出版(例如,《今天的恩格斯:一百周年之际的评价》、《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科学家与革命者》和《在空想与批评之间:百年之后的“大师”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等等)。在当代西方学者中,在研究恩格斯的意图、方法、观点和领域等方面都发生了新的变化,同时,对恩格斯的评价也开始变得积极起来。关于当代西方学者的恩格斯研究,可以用英国马克思学学者斯蒂芬·瑞吉比(Stephen Rigby)的话来概括:“为了发现‘最好的马克思’, 马克思学学者已经教会我们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或许现在我们不得不学会不再读出最坏的恩格斯。”(注:Stephen Rigby,“Engels Revisited”,in History Today,Vol.45,No.8,1995.p.10,p.10.)
具体而言,目前国外学者对恩格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1.为何对恩格斯重新产生兴趣?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管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马克思学学者都不约而同地重视对恩格斯的研究,这里存在着众多的复杂原因。固然,1995年这个重要的年份是西方学者纷纷开始重新研究恩格斯的重要原因,但这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自从苏东剧变后,新自由主义横扫整个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体系逐渐形成。与此同时,西方的反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也逐渐高涨,在西方左翼学者中出现了“社会批判的复兴”,分析和批判资本主义成为西方左翼学者的主要理论任务。马克思作为批判资本主义的思想体系由此获得了时代的相关性。因此,作为马克思的终身合作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恩格斯显然是“复兴马克思主义”无法绕开的人物。而且,恩格斯晚年对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的理论分析和概括,对于分析当前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毫无疑问,当代西方的马克思学学者重新研究恩格斯的原因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截然不同。在西方马克思学学者看来,恩格斯尤其是晚年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思想关系问题虽然经过百年的研究,但仍然悬而未决。英国马克思学学者特雷尔·卡弗认为主要有三个问题没有解决:在恩格斯晚年的著作中,恩格斯是否对马克思著作进行了实质性的再解释,从而离开了马克思的思想活动?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解释能够与列宁和斯大林相当简单化的实证主义和唯物主义的教条主义的混杂联系起来吗?是否存在着本真的马克思主义,它可以按照系谱学的方式从当代社会主义者那里追溯到马克思和恩格斯那里?就这些问题来说,卡弗认为,虽然经过了一个世纪,现在仍然只是研究恩格斯文本丰富性的开始。(注:B.Manfred Steger and Terrell Carver,eds.Engels after Marx.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1999,p.6,pp.6—7,p.137,p.197,p.182.) 所以,有必要引入新的方法尤其是欧洲大陆哲学的解释学和英国语言哲学的发展。此外,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历史考证版《资本论》及其手稿部分的陆续出版,西方学者认为终于可以回答考茨基在1926年提出的问题了:“当恩格斯整理和出版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时,是否完全符合作者的思路,必须公开马克思的全部手稿。”
2.如何研究恩格斯?
在恩格斯逝世后的100多年里,在对恩格斯的研究上, 基本上存在两种简单化的倾向:一是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中的极端美化倾向,二是一些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极端丑化和妖魔化倾向。与此相应,在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关系上,具有这两种倾向的西方学者分别持“马恩一致论”和“马恩对立论”的观点。当然,这两种倾向也遭到另外一些西方学者的批判和反驳。当代的西方学者在研究恩格斯时一方面拒绝随意的反恩格斯主义,另一方面也反对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提高到宗教式的权威地位上。荷兰学者约斯特·科尔茨(Joost Kircz )和迈克尔·洛易(Michael Lowy)认为,要想对恩格斯进行正确但又是批判性的评价和研究,必须避免这两种极端的美化和丑化倾向。在恩格斯逝世100多年之后的今天, 恩格斯不仅仍然是一位最迷人和最有启发性的思想家和组织者,而且仍然是真正卓越的历史人物之一,因此,不可能简单、一笔带过地来描绘他。恩格斯的人格魅力及其活动和研究的丰富性和广度仍然是继续研究的主题。(注:参见Joost Kirez and Lowy Michael,“Friedrich Engels-A Critical Centenary Appreciation”,in Science & Society,Vol.62,No.1,1998.)
另外,卡佛和英国马克思学学者斯蒂芬·瑞吉比都提出要运用解释学方法来研究恩格斯。瑞吉比认为,在马恩逝世后,作为具有生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因此,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不仅存在一个意义的传递:即从恩格斯Ⅰ(真人恩格斯)到恩格斯的著作再到读者,同时也存在一个意义的接受过程:即从读者到恩格斯的著作再到恩格斯Ⅰ/Ⅱ/Ⅲ……,具体图式如下(注:Rigby,Stephen,Engel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History,Dialectics and Revolution.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p.1,p.2.):
恩格斯(现实的人恩格斯)→恩格斯的著作→读者
读者→恩格斯的著作→恩格斯Ⅰ/Ⅱ/Ⅲ…(特定读者的解释)
毫无疑问,历史上曾经存在一个真实的恩格斯,他留下了大量的文本。从文本到读者的过程中,读者基本上都相信存在一个真正的恩格斯,通过文本解读还原出一个真正的恩格斯是可能的。因此,读者在接受恩格斯的文本时,必然带有具体的偏见、问题和假设,即不同的读者都是带着不同的“问题结构”来研究恩格斯的,因而,在不同研究者的视域中,就会呈现出恩格斯Ⅰ、恩格斯Ⅱ……说到底,研究恩格斯是一个解释学问题。每一个读者都必定带着先见和目的来解读恩格斯的文本,在解读的过程中并非消极接受恩格斯的文本所传递的意义,而是根据自己的先见和目的积极地进行文本的建构,而且都相信自己的解读符合原本的恩格斯。因此,“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现在对读者开放的解读多元性来说,在读者从文本获得意义和文本限制了对读者开放的意义这种辩证法中,读者无疑占据了上风”(注:Rigby,Stephen,Engels and the Formation of Marxism:History,Dialectics and Revolution.Manchester and 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2,p.1,p.2.)。研究恩格斯和马克思的目的不是为了找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意义”是什么,而是为了评价他们的多重含义,找出最有利于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实践的意义。因此,马克思学学者曾经为了找到“最好的马克思”而教会我们如何阅读马克思的著作,现在我们必须学会不再为了“最坏的恩格斯”而进行阅读。(注:Stephen Rigby,“Engels Revisited”,in History Today,Vol.45,No.8,1995.p.10,p.10.)
3.反驳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重新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致性。
在20世纪90年代初,一些西方学者向流行的马恩对立论发起了挑战。他们认为在20世纪最后的30年里,一些知名的恩格斯传记严重地低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基本思想上的一致性。在《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1992年)一书中,英国学者卢比(Rigby)认为,为了把恩格斯的著作与马克思的著作对立起来, 马恩对立论者对恩格斯的著作进行了选择性引用。这种对立有时是合理的,有时是错误的,但是主要的动机始终是想取得对马克思本人进行批评的先机。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留下的这些著作是在漫长的时期里写作的,形式和风格不同,是对各种各样环境的反映,而且写作的目的也不同。这样一来,“通过选择性的引用,人们可以很容易地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大多数问题上是不一致的”,因此,“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毫无意义”。(注:B.Manfred Steger and Terrell Carver,eds.Engels after Marx.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1999,p.6,pp.6—7,p.137,p.197,p.182.) 在《恩格斯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 英国学者约翰·瑞斯(John Rees )批评马恩对立论者忽视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的终生合作这一事实,因此,为了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对立论者为了消除马克思和恩格斯生平中的基本事实而进行了相当多的思想歪曲,卡佛和莱文就是其中的代表。瑞斯从历史事实的角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然与历史的关系、辩证法、认识论和革命观上的基本观点进行了历史的分析,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存在所谓的对立,从而反驳了马恩对立论者对恩格斯的指责。(注:see John Rees,“Engels' Marxism”,in International Socialism,No.65,Winter,1994.)
4.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
恩格斯是否是体系哲学——苏联辩证唯物主义的建立者?在《恩格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法国学者乔治·拉比卡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过程中,恩格斯晚年的《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源头。但是,恩格斯晚年哲学介入的后果之一是体系哲学思想的延续。因此,在恩格斯的自然科学研究和列宁的历史辩证法和唯物主义一元性之间,马克思的思想变成了宗教式的教条,变成了无法认识的启示真理。这在斯大林的唯物辩证法中达到了顶点。虽然拉比卡认为恩格斯不应该为这种辩证唯物主义的体系哲学负主要责任,但是他的确是在暗示恩格斯与之也脱不了干系。(注:see Georges Labica,“Engels and Marxist Philosophy”,in Science & Society,Vol.62,No.1,1998.) 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封闭体系的建立者?》中,德国学者格特·沙菲尔(Gert Schafer)指出,恩格斯不幸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这种虚假的“封闭的意识形态”的主要证人,把恩格斯当作是体系哲学的建立者,显然是贬低了恩格斯。因此,沙菲尔认为应该把恩格斯的评价与苏联对他的评价区分开来。
5.恩格斯与修正主义的关系。
恩格斯晚年是不是修正主义者?这个问题也是当代西方学者关注的热点问题。美国学者曼弗雷德·B·斯特格认为,恩格斯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一贯支持者,但在晚年时期,却断定暴动战略已经过时并且是自杀性的行为,由此致力于找到革命起义论与永久选举主义之间的中间道路,即“革命选举主义”战略。(注:B.Manfred Steger and Terrell Carver,eds.Engels after Marx.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1999,p.6,pp.6—7,p.137,p.197,p.182.) 一方面,恩格斯努力坚持革命原则,另一方面又概述了适应非革命环境的策略。因此,恩格斯1895年的立场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矛盾。政治民主是获得权力的手段,但是,在代表旧统治阶级的国家或反革命运动进行先发制人的进攻的情况下,就要用革命暴力来捍卫那种权力。问题出在如何应用这个一般原则上。那种认为恩格斯是“第一个修正主义者”,应当为庸俗马克思主义负责的观点,“未能把对核心文本的解读与对这些文本的特定政治环境的彻底分析联系起来”,“如果没有对这种重要环境因素的严肃思考,那么,关于恩格斯所谓的修正主义的争论就呈现出相当抽象的性质”。(注:B.Manfred Steger and Terrell Carver,eds.Engels after Marx.University Park,PA: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1999,p.6,pp.6—7,p.137,p.197,p.182.) 因此,要正确评价恩格斯晚年的主要政治著作,就必须把这些著作放到历史环境中。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就很容易解释恩格斯晚年著作中的张力。伯恩施坦抛去了革命的外衣,坚持了自由主义、现实主义和改良主义的内容,从而沿着实证的方向解释了恩格斯著作中的那种张力。
6.恩格斯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在经济学上的一致性和差异性,西方学者基本上存在两种倾向。一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加区别地当作一个人。例如,1967年,在《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方法》一文中,英国学者罗纳德·L.米克(R.L.Meek)无意识地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当作是一个人,不仅随意地引用恩格斯的话来支持马克思的观点,而且误把恩格斯的观点和论述当作是马克思的。(注:参见Ronald.L.Meek,Economics and Ideology and Other Essays,1967,pp.96—98; Studies in the Labour Theory of Value,‘Introduction to the Second Edition’(1973),p.xv.) 随后在1973年,M.C.霍华德和J.E.金在他们影响广泛的教科书《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也犯下了同样的错误。另一种倾向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立起来,例如,在1975年的《悲剧性的骗局: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对立》一书中,美国学者诺曼·莱文(Norman Levine)声称,恩格斯对马克思手稿的态度一开始就是实证主义的。莱文指责恩格斯不仅没有正确地解释《资本论》第二卷第472—476页的内容,而且为了出版《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而对马克思的手稿进行了改动,但又未在脚注中注明,因此,莱文认为,这些未被承认的改动是对马克思手稿的歪曲,使《资本论》这两卷比马克思的手稿具有更多的决定论和实证主义色彩。杰洛德·塞吉尔(Jerrold Seigle)在《马克思的命运》(Marx's Fate:The Shape of a Life)一书中认为,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发现了一些未被承认的改动,而这些改动沿着反实证主义的方向改变了马克思原来的论证。塞吉尔发现,恩格斯重新编排了第13章和第14章一些段落的顺序,从而使一些反对利润率下降规律的因素比在马克思的手稿中拥有更加独立的地位。这弱化了被马克思认为是影响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的东西。通过编辑的改动,恩格斯强调了利润率下降规律中的矛盾,而马克思虽然承认这些矛盾,但往往不予重视。
在20世纪90年代之前,关于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整理和编辑工作改动了马克思手稿的哪些内容和如何评价恩格斯的工作等问题,由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所有手稿没有全部出版,所以,西方学者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更多是从学理上进行的,并没有得到文本的支持和证明。因此,恩格斯的文本修正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本人的意图,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1993年,当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第二部分出版了《资本论》全部三卷本及其所有手稿时, 西方学者认为终于可以回答考茨基在1926年提出的问题了,从而掀起对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与马克思手稿进行比较研究的热潮,相继出版了《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编辑本》(1995)年和《资本的循环:〈资本论〉第二卷论文集》(1998)等书,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恩格斯对马克思手稿的改动有多大?西方学者通过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与马克思手稿的比较发现:恩格斯对马克思手稿的改动有两个方面:(1)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手稿作了大规模的手术。例如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的改动包括:结构的改变、个别文章段落的修改和补充以及恰当的术语等等。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改动:标题的设计、小标题的插入以及原文的移动、删除和插入。(2)恩格斯自己的补写部分。
第二,恩格斯对马克思手稿的改动在多大程度上符合马克思的意图?关于《资本论》第二卷,西方学者认为,恩格斯没有忠于他在三卷本前言中所提出的出版原则,对文字的改动远远地超出了目前所能接受的程度。关于第三卷,恩格斯的改动对原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尤其在信用理论和资本主义与商品生产关系的部分。
第三,如何评价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编辑工作?在这个问题上,西方学者持有以下几种观点:
(1)德国学者迪特哈德·贝伦斯(Diethard Behrens)、于尔根·容尼克尔(Juergen Jungnickel)和卡尔-埃里希·沃尔格拉夫(Carl-Erich Vollgraf)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手稿的编辑工作歪曲和改变了马克思的思想,实质上插入了他自己的许多思想。最明显的表现是,恩格斯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对立环节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从而把马克思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的概念化方法降到次要的地位。(注:see Carl-Erich Vollgraf Sperl and Rolf Hecker eds.,Engels' Druckfassung versus Manuskripte zum Ⅲ.Buch Des' Kaptial' Argument-Verlag,Hamburg,1995.p.20,pp.56—57,p.95,p.58.)
(2)日本学者田中菊二认为,恩格斯对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手稿的编序,从他不得不解决的巨大分析裂缝来说,是建立在正确的理论逻辑上的。(注:see Carl-Erich Vollgraf Sperl and Rolf Hecker eds.,Engels' Druckfassung versus Manuskripte zum Ⅲ.Buch Des' Kaptial' Argument-Verlag,Hamburg,1995.p.20,pp.56—57,p.95,p.58.) 德国学者汉斯-格奥尔格·本施(Hans-Georg Bensch)认为,尽管恩格斯的编辑改动非常大,但是通过对比马克思手稿和《资本论》第三卷表明,恩格斯对马克思手稿章节的安排不仅仅是权宜之计,而且是合理的。(注:see Carl-Erich Vollgraf Sperl and Rolf Hecker eds.,Engels' Druckfassung versus Manuskripte zum Ⅲ.Buch Des' Kaptial' Argument-Verlag,Hamburg,1995.p.20,pp.56—57,p.95,p.58.) 米夏埃尔·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认为,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的原稿不能被编为第三卷,它至多代表马克思的初步设想。
(3)美国学者伯特尔·奥尔曼认为, 要想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制造重大的差异,必须要回答五个问题:第一,如果马克思和恩格斯如同人们所说的那样不同,那么他们怎么能合写了这么多著作?最突出的是《德意志意识形态》、《神圣家族》和《共产党宣言》。第二,如果两人之间的差别如此之大,那么马克思怎么可能允许恩格斯以自己的名义写下大量的文章呢?第三,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著作或同其他同志的讨论中没有谈论这些巨大的差别呢?第四,马克思为什么没有对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表示不同意呢?第五,为什么这些重大的差别没有出现在四大本厚厚的《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中呢?因此,除非这些问题得到了满意的回答,否则就绝不可能充分地描述、解释或评判恩格斯的《资本论》编辑工作。(注:see Carl-Erich Vollgraf Sperl and Rolf Hecker eds.,Engels' Druckfassung versus Manuskripte zum Ⅲ.Buch Des' Kaptial' Argument-Verlag,Hamburg,1995.p.20,pp.56—57,p.95,p.58.)
(4)德国学者罗尔夫·黑克尔认为,恩格斯不可能一直追随马克思的思路, 当这条思路连马克思自己都没有清楚地表达出来的时候,自然就没有关于如何整理的指令摆在恩格斯的面前。对于恩格斯编辑了“易懂的”书的功绩,必须给予应有的评价。总之,在恩格斯编辑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与马克思手稿之间的关系上,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看作是完全一致的观点是错误的,同样,那种认为两人之间有不能化解的矛盾的观点也是错误的。
注释:
(14) see B.Manfred Steger,“Friedrich Engels and the Origins of German Revisionism:Another Look”,in Political Studies 45(2).19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