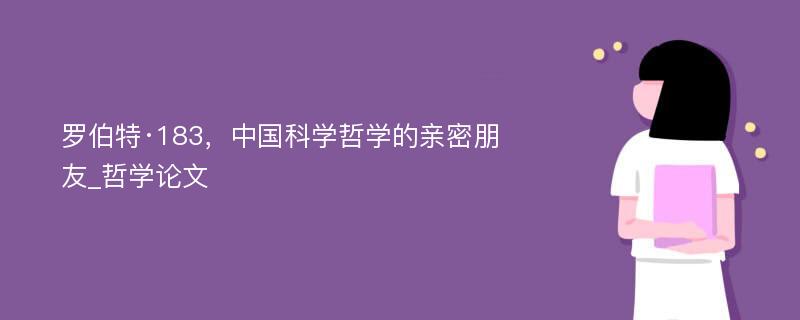
中国科学哲学界的挚友良师——罗伯特#183;柯恩教授专访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罗伯特论文,良师论文,挚友论文,中国论文,专访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罗伯特 柯恩(Robert S.Cohen)的名字是国内科学哲学界十分熟悉的。作为美国波士顿大学的哲学和物理学教授,他曾长期担任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中心主任,主持闻名遐迩的“波士顿科学哲学讲座”,并主编了180余本《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丛书收录了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世界各国科学哲学及关联学科的专著、论文、文章和评论,由此确定了柯恩教授在世界科学哲学界的重要地位。
除此之外,柯恩教授之所以在中国享有盛誉,还在于他对中国人民长期怀有的友好情谊。在他身边一直有一批中国学生学者向他求教或进行合作研究。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柯恩教授与中国科学哲学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合作与交流频繁。他数度访华,并两次在中国组织国际会议。笔者在1988年柯恩教授访问南京大学时担任翻译,有幸求教于他,并在1994年北京纪念洪谦国际会议上再度聆听他的教诲,受益匪浅。并在会上相约次年在波士顿再见。
1995年8月初,笔者以哈佛大学访问学者身份一踏进美国土地,便在波士顿大学主办的国际中国哲学年会上再次见到柯恩教授。他热情地开车载着香港科技大学叶锦明博士和笔者参观波士顿几所著名大学和游览胜地,介绍这座文化学术气氛浓烈、风景秀丽的名城。我们驻足书店大谈哲学、宗教、女权主义,留连忘返。站在刻有波大著名校友马丁·路德·金的名言的雕塑前,柯恩教授邀我朗读这些名句,我们谈起50年代中期他因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为受麦卡锡主义迫害的青年作证而被大学解雇,无人敢再聘他。只有波士顿大学这所有教会背景和自由传统的私立大学聘用了他。当联邦调查局的官员找到当时的校长哈罗德·凯斯,称此人由于共产主义倾向而不得任用时,这位校长回答说:“我治理我的大学,你治理你的国家。”(笔者对这位具有民权、民主思想的已故校长的勇气表示深深的敬意)柯恩教授在波大从此开展自己的事业至今。
国内虽已陆续发表了一些有关柯恩教授的文章,但似乎没有对他作专访,尤其是比较全面地了解他对中国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乃至中国文化事业的印象、看法和建议。当我提议作此专访时,柯恩教授欣然接受并约定了时间。
对中国的持久兴趣
8月15日下午3点,我穿过迷人的查尔斯河来到波大哲学系柯恩教授摆满书籍杂志的办公室,迎面即是晚年罗素的大幅照片。柯恩教授穿着西装短裤象是从运动场上走出来,一点也不像一个已过70岁的老人。我首先问起他何时开始对中国感兴趣,于是引起了他滔滔不绝的介绍和回忆。
柯恩教授说,虽然他在1985年才首次访华,但早在50年前,即他还是本科生时,已经从英语文献中了解中国。他读过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和其他西方作家和政治活动家写的关于中国的书,并在罗素的影响下读了孙中山先生论三民主义的早年英文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以一种“浪漫的乌托邦式的印象”来看待中国和中国革命的,看待中国的民主倾向,看待毛泽东的领导和对马克思主义的独特解释。青年柯恩正是怀着这种浪漫情怀希望找到认识和解决人的问题(包括社会的、伦理的、宗教的、科学的、自然的各个方面)的别种选择或尝试。中国人作出了自己的选择,正象中国之外的印度、阿拉伯等国家也作出自己的尝试和选择一样。
柯恩对中国的另一种兴趣是在科学方面,他一直追踪阅读李约瑟(刚去世不久)的《中国科技史》。他在50年代初认识李约瑟并参与了该书第一卷的某些工作。李约瑟是一位严肃的科学家、科学史家,在政治上是个社会主义者、反法西斯战士,并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他关注科学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科学与其他社会建构的关系,特别关心中国的科技发展及其历史。而李约瑟在这些方面显然影响了柯恩对中国的持久兴趣。
难忘的四国度访华
柯恩教授称自己是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者,但并不是共产党人。他是以科学哲学家的身份于1985年踏上中国的土地的,先后对北京、天津、西安、武汉作学术访问,此后又于1988、1992、1994年先后访问了上海、南京、杭州、广州和香港。这些学术访问的对象主要是科学院、社会科学院,从全国首屈一指的大学到普通院校,与各类人进行广泛接触。他作为科学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学者和中国知识界的朋友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首先接触的是一些兼有政府职务的专家学者,如于光远先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者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经济学家,为中国科学和哲学的发展与复兴作出了重要贡献。柯恩教授强调,中国在哲学和科学哲学上曾经历过照抄苏联的阶段,但即便如此,也对类似李森科事件这样以意识形态及行政方式扼杀新兴学科研究的潮流有所抵制。如在1956年的双百方针时期中国学者即讨论过遗传学的问题,不同观点的人都能发表意见,这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柯恩教授回忆说,他在学术上主要带着三方面的兴趣访华。第一,中国的哲学教授和学生对西方科学哲学有多大程度的了解。他看到,人们不仅了解逻辑经验主义,对一些新的科学哲学代表人物(如托马斯·库恩)也有所认识,翻译出版了一些新书。柯恩教授在此特别谈到每次都见到洪谦教授(已故),他是中国唯一的一位直接参与早期逻辑经验主义即维也纳学派学术研究的学者。柯恩对洪谦先生深怀敬意,并对他生前的境遇表示感慨。前几次均能见到他,而最近一次访华则是专门为开纪念洪先生的国际会议而来的。
柯恩教授访华的第二方面学术兴趣是想了解中国哲学本身发生了哪些变化。通过李约瑟和其他中外学者了解到从道家、法家、墨家和新儒学到毛泽东思想等中国人的哲学。他在学术访问中想实地了解这些思想的影响。他回忆起会见冯友兰教授的经过。冯是位大历史学家,在哥伦比亚大学得到博士学位,三本主要著作均有英文本,在英语世界也有影响。柯恩教授当年去见冯时,一些朋友还不大理解,说这好比是参观一个博物馆。但对柯恩来说,冯友兰是一个活着的思想家。他对冯的坎坷一生感叹不已,知道他多次作检讨,改变自己的说法,但却并未流亡海外。
柯恩教授访华的第三个学术兴趣是想知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正在从事哪些事业,包括其理想社会的理论对中国人的影响。除此之外,他还想了解人们的信仰情况,宗教在中国社会起着怎样的社会作用。当然,在了解这些方面的积极因素的同时,柯恩教授也不掩饰自己对长期极左政策阻碍正常学术研究,对1957年双百方针的被断送,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做法所表示的失望。
带着这样一些兴趣,柯恩教授在中国作长途学术访问,对各个方面有了比较清楚而直接的了解,除了与年长的学者交流以外,也很想与年轻人交谈,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柯恩教授说,他所作的多次学术讲演,听众从40人到300人不等,每次都多少脱开正式讲稿,作即兴演说,尽最大努力把自己的讲演与听众联系在一起,以便引起讨论。所讲的问题从当代科学哲学的发展、科学史,到马克思主义与哲学、科技政策,范围广泛。从所引起的关注和反响可以看出,这些学术访问是成功的。柯恩发现,有些系科的师生提出了高水平的问题,特别是一些年轻的教师和学生思想活跃,对他的讲演当场作出反应,他们既了解也感兴趣于当代科学哲学的新进展。陪同柯恩教授作这些长途学术访问的主要翻译是他的挚友范岱年教授和学生吴忠博士。他们对这些学术跨度很大的即兴讲演和讨论作了很好的现场传译,为讲演的成功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对中哲学研究的印象和建议
在介绍对中国哲学研究的总体印象和建议时,柯恩教授首先谈到对中国哲学机构和系科的印象,当然主要偏重科学哲学方面。他认为,除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和北大第一流机构以外,中国科学院所属的一个独立机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也做了出色的工作。武汉大学的江天骥教授最早曾是洪谦的学生,在他的指导下,武大培养了一些较好掌握西方文献和研究方法的学者,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洪谦先生事业的一个继续。复旦大学哲学系则以严格训练著称。而象人民大学、华东师大、上海交大等校的师生也表现出对科学哲学的浓厚兴趣。柯恩教授仅就当时所记得的几所大学谈了他的一般印象。
除了学术访问以外,柯恩教授还与中国同行进行了其他一些学术交流。如范岱年教授等人翻译了他的一本书《当代哲学思潮的比较研究》。他还与中国同仁合作编辑了英文版的中外学者科学哲学论文集。例如作为《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第169卷的他与邱仁宗教授等合编的《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1992年北京国际会议文集,以及正在编辑中的1994年北京纪念维也纳学派和洪谦国际会议论文集等。他还与范岱年教授合编了一本选自《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1979-1985年的论文集,译成英文出版。柯恩教授对上述两位中国教授严谨细致的学风和工作态度及发展中国科学哲学的责任心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国同仁所做的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除了这些肯定的赞扬评价之外,笔者也想听到批评意见。柯恩教授也不讳言他看到的中国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对中国科技界在数学、逻辑、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基础科学以及工程学等方面的突出成就表示钦佩,这方面的大批人才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成绩卓著。但相比之下,哲学却显得比较单薄,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例如,几十年来未见维也纳学派对中国科学界和哲学界有什么影响,也未见科学家与科学哲学家之间实质性的接触和交流,科学家似乎并不需要科学哲学。这可能是源于科技政策方面存在着的实用和短视的态度,以及教条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的统治。当然,科学史研究在中国开展得较好,也许是一个偶然的缘由,即科学史和科技政策研究所均设在中国科学院,而办得质量较高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也长期属于中国科学院的下属部门。
由此而看到另一个重要的缺陷,即中国科学哲学与一般哲学的分离,互相不交流、吸收、融汇和促进。这是不该发生的门户偏见。此外,柯恩教授还指出,在实用领域已往看到中西医之间的融合吸收,取长补短,没有那么多的偏见,但在思想领域,在理论上,传统中国哲学与西方科学哲学的传统为什么会存在如此互不相容的陈见呢?
近年柯恩教授在北京直接主持过两次国际学术会议,他坦率地说,就中方提交的论文而言,少数除外,达到国际水平的并不多,他为此也与邱仁宗教授交换过意见,形成了共识。相比之下,《波士顿科学哲学丛书》1992年出版的一本由台湾学者编撰的《科学哲学与观念史在台湾》却表现出较高的水准。当然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其作者均在英美取得博士学位。在香港,科学哲学也未形成独立的学科,倒是传统哲学的基础雄厚。柯恩强调,中国人在基础和应用科学方面取得了世界一流的成就,而哲学特别是科学哲学却显得不足,这是个更大的反差。
柯恩强调他对中国人思想从来不存偏见,对研究水平的评价主要是就学理和方法而言。例如,在谈到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论文的主要缺点时,柯恩教授指出,中国科学哲学研究对西方科学哲学家的介绍和了解在量上已经很多,但经常仅仅停留在一般翻译介绍和解释的水平,可以说是一种高级的学术新闻,但缺乏批判的创造性的分析、论证和深入的比较、探讨。虽然对文献了解不少,但有时不能切实把握研究对象。这或许是个普遍的现象,可能与整个学术界缺乏深入激烈的观点交锋、论争和批评有关。这也反映在一些研究中国传统哲学的学者的文风上,他们只喜欢构建大框架体系,讲大话和口号,而缺乏深入细致的论证和对比,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论据。
柯恩教授的这些批评是中肯的;也许不十分全面,也不中听,但良药苦口利于病。就笔者这几年数度或参与组织国际会议而言,能进行深入分析论证,提出引起听众学术兴趣和争议的观点和论文确实不多见。笔者认为,不仅在科学哲学领域,而且在一般哲学,传统哲学、文化学、伦理学乃至政治学、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一些人热衷于大口号、大体系、大题目、大标签、大文章,而不进行扎实的实质性研究。中外学者的交流除了存在文化传统、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以外,在研究方法上的细与粗、深与浅、务实与务虚不能不说是个较普遍的差异(当然外国学者之间也存在这些方面的差异)。这应当引起我国学者高度警醒。这一差异也许可以归结为在中国缺少分析哲学的传统,尽管分析哲学对中国学界也有相当影响。柯恩教授提到例如英文著作《波普在中国》一书。
柯恩教授并无抹杀中国哲学成就的意思,他所提出的批评意见也是审慎的,笔者只是出于忠言逆耳的立场才这样强调地提出问题。柯恩教授建议中国的有关决策人士重视哲学等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教育,克服短视和功利的考虑,投入更多的人力物力。希望中国哲学界的同仁无论在学术会议、刊物上还是在课堂上都养成批评、讨论、交换意见的习惯,克服困难、扎实工作,为推动中国哲学和科学的繁荣作贡献。
两个小时的专访和讨论不知不觉便过去了。柯恩教授还有另外的约见,他微笑着握住笔者的手,让人感到一种长者的关怀、温暖和慈爱。走在跨越查尔斯河的大桥上,桥下帆船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远处波士顿市中心高楼林立,教堂等传统建筑点缀其间,与蓝天白云相辉映,笔者不禁想起柯恩教授1994年在北京会议总结发言中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大意):
“我对中国人民充满友好的感情。任何一个有责任感的中国人都不会忘记本世纪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孙中山的共和革命、八年抗日战争、毛泽东领导的社会革命,以及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美国并非一切都好,无须一切照搬……我衷心希望中国人民幸福进步,学术文化繁荣兴旺……”
笔者愿与国内的同仁一道祝这位可尊敬的前辈、中国科学哲学界的挚友、良师健康长寿。并在此衷心感谢柯恩教授的盛情接待。
标签:哲学论文; 科学哲学论文; 哲学研究论文; 科学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中国哲学史论文; 李约瑟论文; 洪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