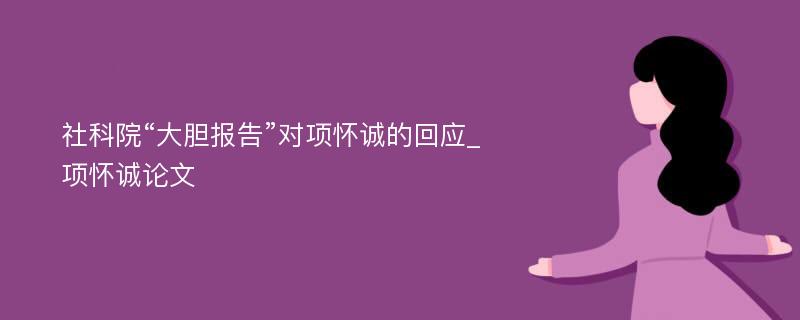
社科院“大胆报告”回应项怀诚,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科院论文,大胆论文,报告论文,项怀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指望民间资本能弥补积极财政政策一旦退出,国有投资增速下降留下的空间,存在相当的难度。”社科院最新的《中国经济前景分析——2002年春季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如此直言不讳。这份报告一出台,即因其对现行积极财政政策的不足之处进行大胆批评而引起广泛关注。
而就在4月16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在回答提问时表示,中国当前的积极财政政策将在今后逐步淡出。“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也没有一个国家的财政部长能够长期地执行积极财政政策而不出问题。”
《报告》的出炉,正与项部长的言论有不谋而合之处。
财政的无奈
自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一直在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据统计,1998年以来,我国用国债资金安排的国债项目总投资规模达到6000亿元,到去年底,累计完成投资总额为19300亿元。作为一项应急性的短期政策措施,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实施确实对国民经济保持适度快速增长起到了重要的拉动作用:据《报告》测算,1998年以来增发国债分别拉动经济增长1.38、1.44、1.81和1.66个百分点。在处于衰退的当前世界经济之中,中国经济一枝独秀,积极财政政策功不可没。
但与此同时,经过连续数年的增发国债,我国国债余额占GDP的比重也由1998年的10%上升到2002年的18.3%,已逼近国际公认的20%的警戒线。中央财经大学的刘桓教授认为:“我国中央债占债务的大部分,不像别的国家,地方和中央分担,我们是地方不允许发债,债务明显地集中在中央。如果按中央债务计算,国债的依存度要大于50%。”
此外,《报告》认为,这种积极财政政策的长期实行,除了引发政府新的或有债务(国债),还会使企业养成依赖政府扩张的习惯,其对经济的刺激作用会日益下降。
特殊背景下的决定
一个事实是中国今年将“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项怀诚对此的解释是“在特殊的国际背景下做出的决定”,美国经济去年以来的衰退使高层不得不继续积极财政的应对。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投资的惯性,前4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开工建设了许多新项目,“如同种树,挖了很多的坑,必须把这个树种完,必须把坑填满,如果基本建设搞半拉子工程,损失将非常大”。
按照社科院这份《报告》的说法,政府决定在2002年继续实行积极财政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原因是如果不实行,一方面,经济自主增长的势头还没有建立起来,因而2002年中国经济回升的基础仍然不稳,从而将无法达到7%的经济增长目标。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长的减速,中国的失业问题、不良债权等问题都将进一步恶化,从而引发更加难以解决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实际上,利用财政的转移支付推进低收入阶层社会保障,维持稳定,正是当前政府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方向。
“一方面国内外经济环境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另一方面,扩张性财政政策的多年连续实施又使得我国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存在的某些问题进一步趋于严重”,“有一种中长期化的趋势”。《报告》这样指出政策的无奈。
刘桓教授的话也说得很明白。“一方面,是一种投资惯性,另一方面,对消费的拉动(如公务员增加工资)也是一个过程,有一个时滞。所以只能实施下去。”
三重建议
“跳出财政依赖的关键有两个,一是完善现有的分配制度,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使大量低收入水准的人群的消费需求真正被激发出来。另一方面,也是更关键的问题,是要提高资本的盈利水平,刺激投资。财政拉动的原因说到底是企业投资不足,而投资不足的原因则是投资的回报率太低。解决这个问题,从微观上讲,是要进行企业治理解构和管理方式的改革,进一步提高资本的利用率,从宏观上讲,则是要进行银行体制和投融资体制的改革,要给予所有的企业以同等的国民待遇,一视同仁。”
余永定,社科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所长,《报告》的参与人之一,感触良多。
社科院《报告》给出的建议基本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发挥财政政策的全面功能,进行结构性减税,同时,注意进一步发挥货币政策的调控作用,保证宏观经济运行有足够的货币供应;二是,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健全社会保障机制,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和刺激民间资本的投入,就业机会得到增加,居民收入得到增强,从而保证社会稳定;三是加强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减缓城乡差别,改变孤立化的工业化政策,从而使今后的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尽可能平稳。
“在今后几年对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进行调整和充实的最重要的政策定位应该是,在通过适度扩大发行国债筹集资金用于拉动投资需求的同时,要注意使投资能通过更短的传导链条最大可能地增加就业和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进而拉动和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报告》这一段话指出了积极财政政策是否淡出,及怎么淡出的核心评判标准。
两种“复归”
社科院财贸所的马栓友是《报告》的参与者,也是“体制性复归”观点的代表。在他看来,长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将引发一种体制复归,强化行政审批。这意味着,虽然我国1994年以来重点培育了市场机制,但由于政府这只“有形的手”过于强大,大量的资金和资源归政府支配,整个经济发展的轮子在一定意义上主要是由政府推动的,从而弱化和阻碍了市场配置资源作用的发挥。
另一种是结构复归,掩盖结构性矛盾。后者意味着中国原有不合理的产业结构的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关注,非但没有解决,反而出现了某些倒退。
“体制复归”实际上表明了一种政府投资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正是由于怀着拉动经济初衷的国有资本的大量进入,中国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压缩。有数据表明,2001年,民间投资再次降速,集体与个人投资分别增长8.1%和12.7%,仍低于国有及其他类型投资增长。这不等于说民间没有资金,统计表明中国民间储蓄已逾7万多亿,却大部分没有进入投资领域。即使是民间投资相对活跃的浙江,目前仍有3500亿元民间资金闲置。
国有资本具有先天的低效特性却被大量使用,这造就了国债运用效率不高的现实。目前的国债使用采取的是财政和银行捆绑式的投资方式,实施的主体不仅有中央政府,而且还包括省、地、市、县级政府及国有商业银行。这就造成财政支出权、责不统一,投资项目审查不力、仓促上马,甚至边建边审的情况时有发生。同时,财政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非程序化操作还会引起不可避免的寻租行为及责任主体缺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