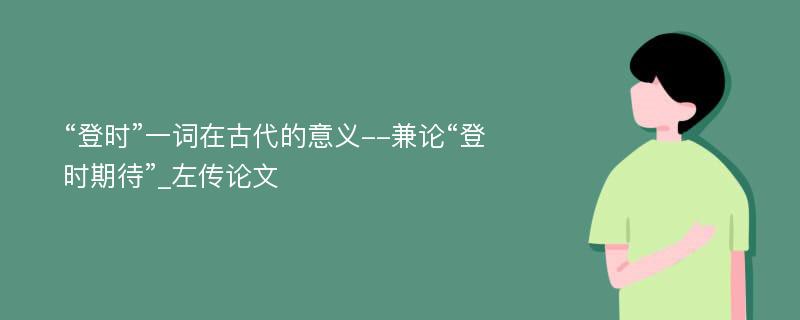
《古“登”字有凭义——兼谈“登轼而望之”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字有凭义论文,兼谈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古“登”字有凭义——兼谈“登轼而望之”》(《中国语文》1997年第4期,以下简称《登》文)认为:古“冯”有登义。由词义渗透律的制约,因“冯”(憑)有登乘之登义,所以“登”也有凭依之凭义。《左传·庄公十年》“登轼而望之”即“凭轼而望之”。
的确,古“冯”有登义。但是,词义渗透并不是无往不适的规律和公式,“登”有无凭依之凭义,关键在于证据是否充分。相比于旧注、成说,《登》文缺乏说服力。例如《左传·哀公十六年》:“子伯季子初为孔氏臣,新登于公。”杜预注:“升为大夫。”杨伯峻注:“据杨树达先生《读〈左传〉》,‘登’即《论语·宪问》‘公叔文子之臣大夫馔与文子同升诸公’之‘升’。子伯季子本为孔悝之臣,卫庄即位即升之为己臣也。”“新登于公”译为“近来升官升到卫侯那里”,被批评为“犯增字为训之病”;而《登》文释作“新近依附于卫侯”——“凭依”变作“依附”,较起真来,不也是偷换概念么?鉴于议论文字比较抽象,如《登》文所列举的《诗经·大雅·崧高》“登是南邦”、《左传·昭公十五年》“福祚之不登”、《左传·哀公十六年》“新登于公”等3例,诗歌词语缺乏语境限定,如《登》文所列举的杜甫诗“四登会府第”、“立登要路津”、“晚泊登汀树”等3例,要确证某词只能释为甲义而不能释为乙义,有相当大的难度。为了有效讨论,此6例姑置不论。而《登》文其他证据皆不能令人信服,谨商榷如下:
一、“登陴”之“陴”并非城上女墙。《登》文认为“‘陴’为城上女墙,非可登者”。其实《左传》所说“登陴”、“守陴”之“陴”已经不是指城上女墙。《宣公十二年》:“楚子围郑,旬有七日。郑人卜行成,不吉;卜临于大宫,且巷出车,吉。国人大临,守陴者皆哭。楚子退师,郑人修城。进复围之,三月,克之。”东汉贾逵明确指出:“陴,城也。”(洪亮吉《春秋左传诂》引)杨伯峻注:“陴,城上女墙也。亦曰陴倪,《墨子·备城门》云:‘俾倪广三尺,高二尺五寸’,是其制也。守城者必登城而守陴,故守陴即守城也。《备城门》又云:‘守法,五十步,丈夫十人,丁女二十人,老小十人。计之,五十步四十人。’此亦当近之。”可见“登陴”、“守陴”之“陴”都是指城墙。至少如王筠《说文句读》所说:“《左传》言‘守陴’者,是女墙;言‘登陴’者,则是城垣之通名。”此外,即使“登陴”之“登”为凭依,也是指凭依于陴,词义不同于“守陴”之“守”。因而说“‘登’有凭守之义”,岂不是有增字为训之嫌?
二、说“‘乘’亦有凭守之义,如《史记》、《汉书》每言‘乘塞’、‘乘边’者皆是”,这不符合《史记》《汉书》语言事实。《史记·黥布列传》“乘塞”司马贞《索隐》:“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汉书·匈奴传下》“乘塞”颜师古注:“登之而守也。”《汉书·韩安国传》“乘边守塞”颜师古注:“乘,登也,登其城而备守也。”虽然“登”的目的是“守”,但词义仍是“登”。否则就无法解释诸如《汉书·贡禹传》“乘北边亭塞候望”这一类的“乘”(颜师古注:“乘,登也。”)。所以李奇释《汉书·高帝纪》“乘边塞”之“乘”为“守”,颜师古就不同意:“乘,登也。登而守之义,与上‘乘城’同。”颜注是正确的。《汉书·高帝纪》“乘城”可为佐证:“宛郡县连城数十,其吏民自以为降必死,故皆坚守乘城。”颜师古注:“乘,登也,谓上城而守也。《春秋左氏传》曰:‘授兵登陴。’”假若“乘”释为凭守,那么不仅重复累赘地成了“坚守守城”,而且丢失了“连城数十”的宛郡吏民登上城墙的情节。同样是“乘城”,“乘”的词义不可能不一样:“望见单于城上立五采幡织,数百人披甲乘城……夜过半,木城穿,中人却人土城,乘城呼。”(《汉书·陈汤传》)后一“乘”只能是“登”(颜注为“登”),而不是凭守。更能说明问题的还有:“京师无故讹言大水至,吏民惊恐,奔走乘城。”(《汉书·成帝纪》)“乘城”是为了躲避大水,与凭守毫无关系,颜注“乘,登也”是也。总之,所谓“乘”与“登”同义,是指升登而非凭守,这在上古汉语中是一贯的。例如《诗经·郑风·子衿》“在城阙兮”毛传:“乘城而见阙。”郑笺:“登高见于城阙。”孔疏:“乘犹登也,故笺申之。”
三、“登木”不是凭木。《礼记·檀弓下》:“孔子之故人曰原壤,其母死,夫子助之沐椁。原壤登木曰:‘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也。’歌曰:‘狸首之班然,执女手之卷然。’”郑玄注:“木,椁材也。托,寄也。谓叩木以作音。”《登》文据郑玄注认为:“‘登木’谓抚据椁木,并不是指登立于椁木之上。若登立于椁木之上而‘叩木以作音’,则只能发出沉闷的音响,且要扣木作音,无需站到椁材上面去,所以此‘登’字亦当训凭,凭者据也。”我们认为,这里的“登”仍是升登。例如《诗经·小雅·角弓》“毋教猱升木”郑笺:“猱之性善登木。”《尔雅·释兽》:“犹,如麂,善登木。”“登木”即上树。《檀弓下》的“登木”指登上椁木,前人已经明言,历来并无疑义:“登木,履椁木材之上也”(宋黄震《黄氏日抄》卷十五),“原壤放达自居而不由于礼。考之《檀弓》,于其母死,升木而歌,则可见其人矣”(宋张拭《论语解》卷七)。置疑的关键,是误解了《檀弓下》原文与郑注所谓的“音”。郑注“叩木以作音”之“音”即“久矣予之不托于音”之“音”。何为“音”?《礼记·乐记》:“凡音者,生人心者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声成文,谓之音。”这是说:“凡歌曲,都产生于人心。感情激动于心中,所以表现为声音,声音变化而成曲调,就叫做歌曲。”[1][p628]原壤所说“久矣予之不托于音”,是说他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用歌声来寄托感情了。显而易见,此“音”指他唱出的歌曲,而不是叩击椁木发出的声响。因而就无所谓叩木的音响是否沉闷,无所谓是否站到椁材上面去扣木。再说,“登木”与“歌曰”可以是先后的动作行为:始而升登于椁木之上,继而叩击椁木而唱歌——谁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呢?应当指出的是,《檀弓下》原文并无“叩木”情节。郑玄注“谓叩木以作音”,“叩木”作为唱歌的方式,也只是郑玄的推测之词。原壤唱歌时可能“叩木”,而非必然如此。
四、说“天子、诸侯巡守出战,一般也都是坐乘”,缺乏证据。《登》文指出:“古人乘车,男子立乘,年七十以上及妇人则坐(跪坐)乘。天子、诸侯巡守出战,一般也都是坐乘。”此话仅只前一半确切。《礼记·曲礼上》:“妇人不立乘。”又:“大夫七十而致事。若不得谢,则必赐之几杖,行役以妇人,适四方,乘安车。”郑玄注:“安车,坐乘,若今小车也。”《周礼·春官·巾车》“安车”郑玄注:“安车,坐乘车,凡妇人车皆坐乘。”《仪礼·士丧礼》郑玄注:“古者立乘。”《礼记·曲礼上》郑玄注:“乘车必正立。”凡此可见男子立乘是公例。因为《登》文不能提供“天子、诸侯巡守出战一般也都是坐乘”的证据,所以其下述推论也就难以成立:“曹刿是坐乘于车,先从车上探身往下察看齐军的车辙,再站起来手扶轼木观望齐军的战旗。”
五、说“登轼”即“冯(凭)轼”,不符合《左传》语言事实。首先,将“登轼”释为冯(凭)轼的逻辑前提是:由词义渗透律的制约,因“冯”(憑)有登乘之登义,所以“登”也有凭依之凭义。但是,《左传》中既有“登轼而望之”,又有“冯轼而观之”:“子玉使斗勃请战,曰:‘请与君之士戏,君冯轼而观之,得臣与寓目焉。’”(《僖公二十八年》)这就清楚地表明:《左传》“冯”“登”分工明确,“登轼”不同于“冯轼”。其次,《左传》有“登丘而望之”:“冬十月,华元自止之,不可,乃反。鱼府曰:‘今不从,不得入矣。右师视速而言疾,有异志焉。若不我纳,今将驰矣。’登丘而望之,则驰。骋而从之,则决睢澨、闭门登陴矣。”(《成公十五年》)“登轼而望之”与“登丘而望之”,句型相同,两“登”字词义应当相同。因而没有理由强生分别,一释为凭依、一释为升登。换言之,将“登轼而望之”的“登”释为凭依,不仅无法解释“冯轼而观之”,而且无法解释“登丘而望之”。
轼的高度也决定了凭之不利远望。《考工记》:“以其广之半为之式崇。”就是以车厢宽度的一半作为轼的高度,郑玄注:“兵车之式高三尺三寸。”根据出土的春秋至秦车舆实物,轼的高度大约为 40-65厘米,左右两旁的輢低于或等高于轼。(注:山西侯马上马墓地出土春秋车舆,2号车车轼高出车底41厘米,1号车车轼高64厘米(《文物》1988年第3期);山西太原金胜村出土春秋车舆,5号车车轼高51厘米(《文物》1989年第9期)。)因而登轼不仅可能而且可行。而“凭(冯)轼”就是“伏轼”,《战国策·韩策三》“伏轼结靷西驰”,《史记·孟尝君列传》作“凭轼”;《史记·淮阴侯列传》“伏轼下齐七十余城”,《汉书·郦食其传》作“冯轼”。可见“凭(冯)”者就其手而言,“伏”者就其首而言。立乘于车上的曹刿若是凭轼,将手扶持在轼上,势必上身前倾、脑袋低俯。
六、《吕氏春秋》“登轼”不足为据。《吕氏春秋·忠廉》:“吴王欲杀王子庆忌,而莫之能杀。吴王患之。要离曰:‘臣能之。’吴王曰:‘汝恶能乎?吾尝以六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满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剑则不能举臂,上车则不能登轼,汝恶能?’”《登》文认为:“这里吴王说要离连拔剑举臂、上车登轼这样容易简单的事也做不了,是极言要离的无能。……如果‘登轼’是指登于轼木之上,便不是轻而易举地能办到的事,更不可能与‘举臂’相提并论。”
诚如《登》文所质疑,要离极其无能。当时的剑有多重?不过720-750克。(注:上海博物馆等单位组成的“吴越青铜技术研究”课题组仿制成功的“越王州句复合剑”,长53.5厘米,宽5厘米,重745克(2002年3月13日新华网);1979年河南淅川下寺11号春秋楚墓出土青铜剑,长54厘米,宽4.2厘米,重720克(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淅川下寺春秋楚墓》306页,文物出版社,1991年)。)手持不足1公斤的剑,要“举臂”是普通人轻而易举的,但是要离做不到。《吴越春秋·阖闾内传第四》的记载与《吕氏春秋》相同:“乃与子胥见吴王。王曰:‘子何为者?’要离曰:‘臣国东千里之人。臣细小无力,迎风则僵,负风则伏。大王有命,臣敢不尽力?’吴卫心非子胥进此人,良久默然不言。要离即进曰:‘大王患庆忌乎?臣能杀之。’王曰:‘庆忌之勇,世所闻也。筋骨果劲,万人莫当。走追奔兽,手接飞鸟,骨腾肉飞,拊膝数百里。吾尝追之于江,驷马驰不及,射之闇接,矢不可中。今子之力不如也。’”
“迎风则僵,负风则伏”的要离,不仅“拔剑则不能举臂”,而且不可能登上车。据《考工记》,兵车和乘车离地四尺(近80厘米),正适合一般人升登。由于车舆距地面有此高度,所以尊者登车时可以借助“乘石”或“几”。先秦车舆,车厢四面置栏杆,后面栏杆正中留有缺口,为登车处。要离并非尊者,没有乘石或几。虽然有绥可执以助(例如《庄子·让王》“王子搜援绥登车”),但是以他的羸弱体质而言,登上近80厘米高的车舆显然不可能,“登轼”更是匪夷所思。说要离不能登车,还有版本依据。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三八六《人事部》二十七《羸》引《吕氏春秋》作:
“吴王欲杀王子庆忌,而莫之能杀。吴王患之。吴王之友曰要离谓王曰:‘臣请杀之。’吴王曰:‘汝拔剑不能举臂,上车不能登足,汝能杀之?’要离曰:‘请必能。’吴王曰:‘诺。’”
宋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七百六十四《总录部·义烈》作“今汝拔剑则不能举臂,上车则不能登”,无“轼”字,与《太平御览》同意。从情理上考察,《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的文字更为可信:拔剑用手,可是无力举臂;上车用足,可是无力登足——这就是“迎风则僵,负风则伏”的要离。
综上所述,所谓“古‘登’字有凭义”难以成立,“登轼而望之”之“登轼”亦非凭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