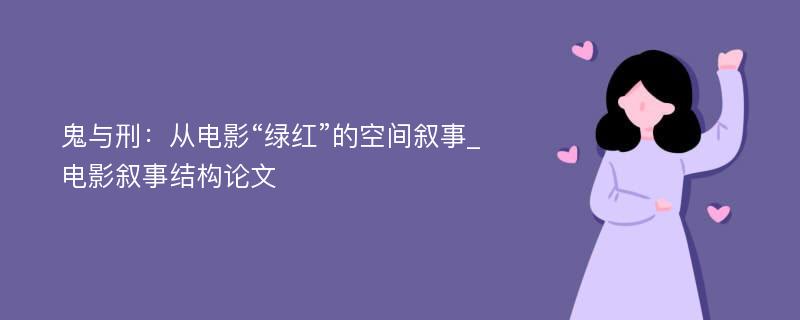
幽灵与惩戒:从电影《青红》的空间叙事谈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幽灵论文,青红论文,电影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5年王小帅凭借《青红》一片荣获第58届戛纳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可以说达到了自己导演事业的第三个高峰。
《青红》之所以成功,在于王小帅充分学习了贾樟柯的绝技,即利用视觉符码和听觉符码对现实空间进行定位,将其置于时间的纵轴上,从而制造出一种仿真的历史空间。
王小帅首先在视觉、听觉方面为我们制造了一个立体的可见空间:贵州大山中的小城,狭窄的街道,破败的工厂,低矮的建筑和封闭的家庭,并利用特定的电影符码赋予这一空间以强烈的时间特性。
在视觉方面,镜头主要呈现出两套带有时间性的视觉符码:一套是由中山装、老款的外套式毛衣、套袖、搪瓷茶缸、房屋中间的蜂窝煤炉、烧水壶、竹子外壳的保温瓶、老式收音机、大众澡堂等所构成的视觉符码,另一套则是由红色高跟鞋(红色高跟鞋作为影片内在矛盾的核心所在,成为一种象征,后面将进行详细论述)、大波浪烫发、喇叭裤、大奔头、衣领翻在外面的白衬衣、墙上的明星照、电影《阿西们的街》、严打中的游街场面等所构成的视觉符码,这两套视觉符码为电影叙事时间进行了基本定位,即故事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听觉方面,影片同样呈现出截然对立的两套带有时间性的听觉符码:一套是第六套广播操、电台播出的评书《三国演义》、严打时的街头广播,另一套则是邓丽君的歌曲、迪斯科音乐,这些对立的声音符码使得影片的时间性得以进一步加强,从而稳定了故事发生发展的四维空间定位。
正是在这样生动、具体的历史空间中,王小帅为我们讲述的故事才显得较为真实和感人。故事讲的是一对父女之间的矛盾冲突:(十几年前)身为上海人的母亲(响应党的号召)要来三线,父亲老吴跟着一起来到偏僻落后的贵州大山中;他们在这里生儿育女并有了一个小小的家;(现在)父母想举家返回上海,但是女儿青红却与一个本地青年小根恋爱了;父亲不准青红在当地恋爱,青红从最初的反抗到无奈的同意,而内心深处仍对爱情有所期待;(最后)青红被小根强奸,老吴到公安局告发了小根;小根被处决,青红一家人在匆忙中离开三线。
影片对这一故事的叙述是以时间为轴,通过画面浏览的方式,将故事按照时间顺序一一呈现出来,并运用大量长镜头和缓慢的移动镜头增强时间流动感,在画面叙述的同时,间或用话语进行倒叙,将故事前史交代出来。
导演在处理青红与父亲老吴的矛盾时,主要借助电影叙事的平行蒙太奇(广义上的)手法,利用现实时间与叙事时间的差异来结构二者的冲突。影片中青红是一条叙事主线,老吴是一条叙事分线,这两条线索在现实时间中是平行发展的,但在电影中则是分别叙述的。现实时间是一次过的,具有自然性、此时此地性和不可变更性,电影叙事时间则是可重复、可延展、可停顿、可变更的。所以,导演将现实生活在平行时间中发生的事件分开来讲述,通过现实时间与电影时间的分离、对位给观众造成一种心理认知上的冲突,从而结构出故事发展的内在张力。
这种现实时间在叙事中的分离使得故事中父女之间的矛盾冲突一步步激化,并最终被推向一个悲剧性的结局——女儿被强奸,父亲报案,强奸者被枪毙,女儿自杀(未遂)。应该说,这种方法较为有效地构建起一个父女矛盾冲突、发展并逐步达至高潮的故事结构。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的话可以看出影片中父女的矛盾冲突似乎只是故事的表面,导演真正聚焦的是作为背景的家庭。
要理解这一点就必须对电影的叙事手段做进一步的了解。电影叙事除了运用时间叙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空间的参与,这一点或许是电影与小说或者戏剧叙事的根本区别所在。
一般来说,戏剧或小说叙事的内核都是时间。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把悲剧定义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经过‘装饰’的语言,以不同的形式分别被用于剧的不同部分,它的模仿方式是借助人物的行动,而不是叙述,通过引发怜悯和恐惧使这些情感得到疏泄”,其中“有一定长度的行动”指的就是要有一定的时间长度,这一界定成为后世戏剧叙事的定规。小说叙事更是如此,伊恩·P·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一书中指出由于现实主义小说突出了叙事时间的现实性,从而使其能够与其他的叙事作品区别开来,而这种叙事时间背后隐藏着的是某种因果关系,它阐释着事物之所以为其所是的必然性或可能性。他说:“小说的情节也因其把过去的经验用作现时行动的原因,使其与绝大多数先前的虚构故事区别开来。通过用时间取代过去的叙事文学对乔装和巧合的依赖,一种因果关系发生了作用,这种倾向使小说具有一个更为严谨的结构”。从这一点上来说,瓦特对小说的认识其实是与亚里士多德对诗人职责的界定是一致的。因此,时间在小说叙事中就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没有时间概念,叙述就是难以理解的……小说这种形式甚至可以视为对一段持续的时间内对人与事的变迁的描述,叙述关心的是时间中的变化因素,以及变化的模式”。
在电影中,时间叙事如同在戏剧或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同等重要,但是空间叙事却获得了其前所未有的重要性。比如大卫·波德莱尔和克里斯汀·汤普森在其经典的《电影艺术——形式与风格》教程中,就特别提出了空间叙事对于电影的重要性:“有些艺术媒介的叙事只重视因果及时间关系,很多事件并不强调动作所发生的地点。而在电影中,空间却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电影的叙事媒介主要是镜头,镜头呈现在银幕上的画面直接作用于人的视觉,所以电影叙事是由具体、生动、可视可感的人物的行为/行动或事物的变化/迁移所构成的。因此,电影叙事尽管内在地包含着时间叙事,但从基本层面来看却是以空间叙事为基础的。对于这一点,罗伯特·考克尔比较清楚地阐释了电影中时间叙事与空间叙事的差别。他说: “剪辑是关于时间的,镜头是关于在特定空间区域内发生了什么的,它是由电影银幕的景框和摄像机拍摄到什么而限定。”
当然,时间叙事和空间叙事二者是不能分开的,但显然空间为电影叙事提供了更为充分的信息,从而能够使电影叙事向更为深广和更为真实的层域迈进,这一点往往是小说或戏剧所不具备的。因为虽然在小说或戏剧叙事中也有空间的参与,但是它们的存在通常是一种想象性的存在,“传统地呈现出笼统、含混的状态”,所以,空间在小说或戏剧叙事中的作用通常不具有指向性和定位性功能,从而使其在叙事中的地位变得飘忽不定。
反观电影,镜头的视觉性先验地要求电影叙事空间具体、明确,且具有连续性,这一点使得电影似乎更接近于现实(当然并非现实)。正因如此,它在叙事中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而具有为电影叙事内涵定位,并为电影叙事的发展提供指向的功能,从而成为电影叙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电影叙事空间主要指的是电影中所表现出来的环境,它一般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电影空间的限定性、空间内外的通透性,以及能让人进入其中或可视可感的内部性。具体来说就是由一定的地理地点、相应的自然景观、具有时代感的建筑物和其他器物道具、人物的行动或行为所涉及的位置,以及声音所引起的方位感等所构成的一个复杂的整体。这个整体构成了电影叙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为电影提供了基本的叙事动力和发展方向,有时甚至还直接参与到电影的叙事中去。所以,“人们必须一再浏览;必须从各个方面走近它,绕着它看;进入内部,在那有条不紊的内部空间里穿行,在变化的距离中看到变化的景物,才能洞察它那真正的丰富性及深邃的启示。”
但是,我们在观影过程中往往注意了电影叙事时间的重要性,而忽视了叙事空间所呈现出来的内在结构,因为我们的感受只习惯于对具体的人和物进行感知,对其存在的空间却不太关注,而且电影空间通常又都是作为背景呈现在银幕上,这就造成我们对它的认知具有片面化和简单化的特性。但实际上电影空间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复杂性从多个层面决定着电影叙事的深度和广度。不了解电影的这一特性,就难以对电影表达内涵有深刻的洞察。所以尽管法国著名的电影理论家马尔丹在其《电影语言》一书中对空间的作用大加贬低,但在分析费里尼的影片时也不得不承认:“空间加剧了人的渺小感和痛苦,许多关键性场面常常是在无穷尽的地平线前展开的;人是空间的俘虏,他们孤独地、默默无言地在那里会面。”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第五代导演的代表影片《黄土地》、《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等都是首先为我们设定出一个特定的空间,并借助这一空间的特性来完成其叙事的。
电影《青红》的叙事空间是由这样一组复合空间构成的:大山中的小城,小城中青红简陋的家,家中狭小的房间。这些空间由大到小一层层递进,进而落脚于青红狭小的家庭空间中,青红的家庭空间无疑构成了电影叙事的真正聚焦点。
的确,在影片中青红的家庭空间是被作为电影表现的主要场景出现的,这一场景投射到银幕上就是大多数的镜头都集中在青红家庭内部一个个狭小、昏暗的空间中,这些空间又以坐落于家庭内外交界处的厨房空间为代表。电影中有两个经典片段是青红在厨房中的镜头:一处出现在影片41′35″—43′41″,青红在厨房中拒绝了小根派青红弟弟送来的口琴,预示着二人的爱情即将夭折;另一处出现在影片85′17″—86′12″,青红从房间走进厨房,又从厨房走出家门,准备去与小根告别。这两个片段都是作为叙事转折点出现的,厨房空间在影片中无疑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它既是一个封闭狭窄的空间,同时又是一个“看得见风景”的空间,它成了连接青红内心世界与外部世界的一座桥梁。
《青红》叙事空间的这种特性决定了整部影片叙事的基本结构,即青红被压抑在封闭、狭小、昏暗的家庭空间中,时时渴望着从家庭中出走和逃离,但又被家庭的无形力量所控制。
家庭问题一直是中国电影关注的焦点,20世纪80年代以后更成为电影表现的一个中心内容,从《牧马人》、 《人到中年》、《芙蓉镇》一直到《心香》、《安居》等,甚至2005年获奖(百花奖)的《我们俩》(尽管不是家庭,但具有家庭的意味),家庭总是作为一个温馨港湾的象征符号出现,家庭对于中国人来说承载了太多太多的文化内涵。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这种承载也有不堪重负的时候,所以从《被爱情遗忘的角落》、《黄土地》到后来的《一声叹息》、《手机》等,家庭越来越受到现代化、个人化、自由化的冲击,家庭的固有结构也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
在电影《青红》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青红的家庭已经承担不起原有的功能和意义,它也正在面临解体的命运。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家庭的基本结构是由父母、子女所构成的一个亲缘组织,在这一组织中父母的权威是必须得到认可的,父母养育儿女,并为儿女决定未来,而子女则应该尊重父母、顺从父母,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指的就是在一个稳定的结构中父母和子女都要遵守各自的职责。
但是影片中这种稳定被打破了,青红渴望自由,期待爱情,所以有事没事总想往外跑,并与父亲(家庭)发生激烈的冲突,导致青红离家出走的结果:青红在父亲监督上学的途中,借口解手不辞而别,直到深夜才由同学的父母陪同回家。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场景,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在特定环境下家庭功能垮塌所导致的家庭内部的不稳定。埃里基埃曾说过: “家庭从本质上是一个组织,它符合个人和人类的根本需求和根本欲望——性欲,生殖欲,抚养、保护子女并将他们引向独立自主的必然性。”因此,家庭要维持稳定就必须实现其基本的功能即维护家庭的权威,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一方面保障家庭内部成员(子女)的安全,另一方面还要承担为家庭成员(子女)选择未来的功能。
然而在当时的环境下,现实不仅对家庭成员(子女)构成直接威胁,而且不允许家庭(父母)为其成员(子女)提供美好的未来,家庭(父母)无法直接解除这种威胁,只好试图设置一道护栏来避免子女受威胁。影片中青红与小根约会的地点被放置在一个有着长长的白色栅栏围着的气象站旁边,白色栅栏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这道护栏是以牺牲女儿的初恋和感情为代价的,所以导致青红激烈地反抗。在反抗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开始家庭的这道护栏是失效的,但最终导演却以这道护栏的成功(尽管具有悲剧性)作为影片的结束。
所以,对于导演来说家庭实际充当的是对家庭成员(子女)的屏障和保护的作用,其尊严和权威尽管受到严重的内外冲击,但仍然是应该获得承认的,青红由于不尊重家庭(父母)的威严而导致最后被强奸的结局。影片中导演巧妙地运用了一个红色高跟鞋的隐喻来表达这种思想:红色高跟鞋本来是为走路准备的,青红接受并穿上了它,象征着青红渴望走出家庭,获得自由;父亲发现后将其扔掉,暗示父亲感受到威胁后加以排斥;青红被小根强暴,红色高跟鞋歪斜地躺在草丛中隐喻出走的失败。在这一隐喻中红色高跟鞋的失败明显地具有一种惩戒功能,是对青红反抗家庭行动的最为严厉的惩戒。
不仅如此,这一隐喻实际上还暗示了影片的主题应该是建立在父女冲突基础之上的传统家庭功能的垮塌。这样一个主题其实是很有深度的一个主题,但是导演却并没将注意力集中在对此问题的深入挖掘上,而是将自己叙事角度悄悄地做了调整,从而使整个故事的内涵发生了根本转变。
为何这样说?其原因就在于《青红》的影像空间背后还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隐在空间,这个隐在空间并没有出现在影片的具象中,而是隐藏在影片的反复叙述之下,这就是与贵阳相对立的上海。
影片中父亲老吴反复地说: “我就是要让他们回家,回上海”,这成为影片故事冲突的起点,青红与父亲的冲突被转换为两个家的冲突。它表现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父母的家与女儿的家的冲突,第二个层面是现实的家与心理的家的冲突,第三个层面是贵阳的家与上海的家的冲突。影片中父母心理的家(上海)与儿女心理的家(贵阳)发生了严重冲突,现实的家只是物理的、空间意义上的家,并不被认作是自己心理的家,父母想要回到他们心理上的家(上海),而女儿更认同现实的家(贵阳),但是这个现实的家显然承担不起心理上的家的功能。
由此可以看出,正是上海这一隐在空间的存在取消了贵阳这一现实空间的价值性,从而导致影片表达主题的改变,即从一个束缚与出走、成长与家庭矛盾冲突的故事变为一个不同空间/地域对立下家庭内部分裂的故事。
因此,导演把我们引入到另外一个矛盾冲突中,我们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空间的冲突,是“在场”空间与“不在场”空间的冲突。
“在场”,从字面上看就是在现场,是某物/人存在、停留、居于、保存于某个特定场所的意思;而“不在场”则意味着不在现场,它可能是纯粹的不在现场。也可能是虽然不在现场,但却通过某种象征物或代言人出场,按照辩证法的逻辑,纯粹的不在场是不存在的或不具有意义的,不在场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地与在场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在日常生活和文学艺术中, “在场”与“不在场”的关系有这样两种:本身一直在场,却不被认知,比如哥白尼提出“天体运行说”以前,地球实际已经并一直在围绕太阳运转,人们不知道但并不妨碍它的在场;曾经在场,现在不在场,却能够通过象征物或代言人在场,比如唐代诗人崔护的诗《题都城南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这里桃花与人面结成一种关系,人面虽然不在,但却可以通过象征物或代言人在场。
不管是哪种情况, “不在场”总是通过“在场”出场,表示自己存在或者曾经存在。因此, “在场”成为存在的基础,也决定着人类之思的方向。
对于“在场”的意义,海德格尔说: “在场意味着:解蔽 (Entbergen),带入敞开(das Offene)之中。在解蔽中嬉戏着一种给出,也即在让——在场(Anwesen- lassen)中给出了在场亦即存在的那种给出”。由此看来, “在场”本义是一种“敞开”,是空,正因为空,它才能将所有在场的和不在场的都显现出来。海德格尔并用大地和世界的关系作比喻,指出:“(梵·高的油画《农鞋》)揭开了这个器具即一双农鞋实际上是什么。这个存在者进入它的存在之无蔽之中。”
就电影来讲, “在场”就是影像所显现的空间,这种“在场”空间构成了影像的现实性和真实性。具体到《青红》一片中,“在场”空间就是大山中封闭的小城和青红狭小的家。如前所述,导演也确实使用了一系列有代表性的空间符码来加以表现,而这恰恰是路易·德吕克所谓的“上镜头性”。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这种“在场”空间的功能和意义就在于显现,显现置身于其中的存在者。他说: “在空间一词中,语言说到什么?其中说到空间化。空间化意味:开垦、拓荒。空间化为人的安家和栖息带来自由和敞开之境。就其本己来看,空间化乃是开放诸位置,在那里,栖息着的人的命运回归到家园之美妙中,或回归到无家可归的不妙之境中,甚至回归到对有家和无家的妙与不妙的冷漠状态中。”
在电影《青红》中,我们可以看出“在场”空间(贵阳)是影像的现实空间,它显现出的是影片的基本内涵,即青红的家的基本情况,简陋、狭小但不乏温情, “不在场”空间(上海)通过代言人(老吴)出场,它是一种想象空间、观念空间,是大城市、开放、经济发达的代名词,尽管它也从始至终存在于影片的叙事中,却只能从另一个层面——经济层面去显现其价值。因而,《青红》“在场”空间与“不在场”空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地域间经济差别的冲突。
这种“在场”空间(贵阳)和“不在场”空间(上海)的冲突如果换一个角度的话,可以看做是暗含了对电影特性的某种否定,即出现在我们眼前的物质影像并不具有真实性和现实性,它可能只是一种假象、幻象或者拟象(波德里亚语),真实并不存在于其中,而存在于其外(这实际上是对克拉考尔和巴赞等人电影本体理论的一种否定)。如果导演在这一层面上进行开掘的话,或许也很有价值(比如安东尼奥尼的著名影片《放大》),但是显然导演并非将目光投注于此,而是将思维定格在这种否定之下的另一重否定中,那就是对影像表达内容——家庭空间的否定。这种否定已经不是哲学层面的否定,而是现实层面的否定,不是空间自然地消解,而是将其人为地擦除。
不幸的是,导演却偏偏用它作为否定电影“在场”空间的工具。正因为这样,在王小帅的镜头中尽管也频繁出现大山、城市、工厂、街道、家庭等一系列空间,却并非将其作为重点来加以表现,也没有深入到这些空间的内部,揭示其中的丰富性和独特性。对王小帅来说“在场”空间(贵州)只具有影像的现实性和真实性,而非影片表现内容的现实性和真实性,它们必然随着电影叙事的深入逐渐丧失了其原有的特性,成为只具有持存性的空洞能指,成为导演用来演绎其故事的视觉代码,只具有一一对应的指代性,而不具备像大地呈现世界一样的象征性。
从这一点来看,影片表现内容的现实与真实不过是一种地域上的冲突,是西部与东部、封闭与开放、落后与发达的冲突,而放置于其中的青红与父亲(家庭)的矛盾则成了这一冲突的一件道具。所以,导演真正想要表现的并非是一对父女情感冲突的故事,也并非是一个家庭与个人冲突的故事,而是借助这些冲突来表现某种外部空间上的冲突,家庭只是承载这一冲突的一个载体,它是在人为的控制下才濒于解体,并非是自身内部所导致的垮塌。影片的主题自然而然地变为家庭与社会、与时代、与环境之间的冲突,是家庭在一个不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发生的变异和扭曲。
所以,作为影片叙事基础的青红的家庭空间成了导演王小帅的一种叙事策略,他只是想要借用某种现实的存在物作为它的叙事起点,并非想要揭示这一空间背后的真正深层喻指。导演之所以要这样做,说明导演对家庭的认知仅仅是将其放置于一个外部的、社会的、环境的、时代的大背景下去认知,却忽略了家庭本身。
或许,王小帅并非真的忽略了家庭,只不过他将家庭放在另一个视域中来看待,他看到的不是家庭的自然解体,而是家庭在受到外部冲击下的无声反抗。尽管这种反抗是悲剧性的,但却是值得崇敬的(片尾字幕“谨以此片献给我的父母和所有像他们一样的三线职工”就说明了这一点)。正因如此,那个被造反过的上海变成一个阴魂不散的幽灵时时来骚扰那对曾经革命过的夫妻,那个要打破地域界限的小伙子被塑造成一个强奸犯,而那个渴望爱情、追求自由的女孩则作为一个受惩戒者被钉上传统价值的十字架。理想、自由、爱情在影片中统统受到无情的嘲笑,家庭、传统、现实成为导演顶礼膜拜的文化图腾。
我在这里并非否定家庭的意义,对于一个人的存在来讲,家庭的功能显然是不可替代的,但无可否认的是现实中的家庭正在趋于解体,它的文化象征意义也越来越趋向于被解构;当然,我也不同意现代意义上个人的完全解放,一个人在家庭中幸福还是脱离家庭幸福,这些本来都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也是值得导演在艺术创作中所审视的问题。遗憾的是,电影《青红》却没有将我们的思维引向这一方面,而是在一个很有张力的空间框架下结构出一个价值单一、视野封闭、思想守旧的家庭故事,这一故事并不具有新颖性(因为它取消了现实空间的“在场性”),它只不过是众多怀旧影片(比如同年顾长卫拍摄的《孔雀》)中电影语言运用的比较完美的一个,尽管它可能会在观众中赢得了一些人情感上的认同,也可能在电影技术方面有些可称道的地方,但在思想上却没有与其获奖相称的深度和敏锐度,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当代电影的一种缺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