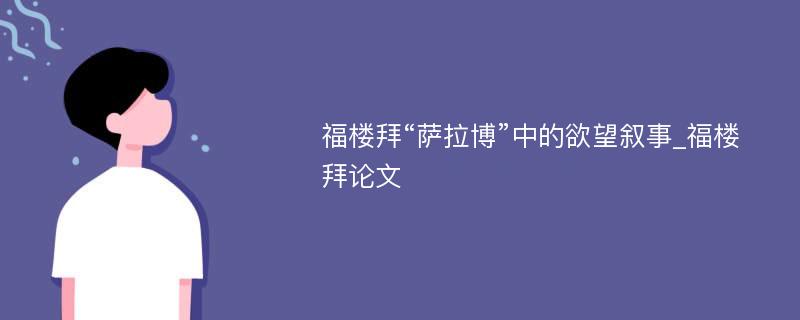
福楼拜《萨朗波》的欲望叙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福楼拜论文,欲望论文,萨朗波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529(2007)02—0087—06
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出版后不久就宣称:“对丑恶的事物和肮脏的环境感到万分厌倦——也许我要花几年功夫生活在一部光辉壮丽的小说里,而且远离现代世界。”(李健吾:34)这部小说就是《萨朗波》。《萨朗波》在我国学界一般被认为是一部历史小说或史诗小说。这种观点认为,小说复活了古迦太基的历史,反映了历史发展的某种本质与规律,(郑永慧:《萨朗波·前记》)“小说描写了迦太基的贫富差距,展示了残忍的战争场面,写出了人与人之间的险恶关系”;(郑克鲁:226—7)作品用“实证”的方法,“再现了两千年前非洲一座城池的氛围,谱写了一首壮烈的史诗”。(李赋宁:240—1)另外,福楼拜为创作这部小说参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特意到北非迦太基旧址游历,寻访遗迹。小说发表后,雨果在给福楼拜的信中赞美小说取得的成就:“你复活了一个以往的世界。”(李健吾:118)
这部小说的成就是否就表现在对古代历史及其精神的复原呢?其主题是历史主义的吗?还有,福楼拜是否真的关心一个公元前3世纪的世界呢?在给圣勃夫的信中,福楼拜曾谈及这部小说:“或许你对于关注古代遗迹的历史小说的观念是对的,而在这方面我是失败了。但是,根据种种迹象以及我自己的印象,我想我毕竟创造出了某种类似于迦太基的东西。可问题根本不在这里。我不关心什么考古学!”(Deppman:28)由此出发,我们必须对《萨朗波》进行重新思考。
一、破碎的历史图像
《萨朗波》对历史环境的描绘是非常风格化的。在某种意义上,这部小说实现了福楼拜在文体方面的追求,即“从日常语言中创造一种散文:模糊,无固定的轮廓,‘硬似青铜,闪烁如黄金’”。(Brombert:103 )“硬”和“闪烁”十分准确地概括了《萨朗波》在环境描写上的特点,前者表现为精确的甚至沦为琐屑的细节描写,后者则表现为一种印象主义风格。小说对于光、色、味、形,大到自然风景和战争场面,小到房间布局、衣着服饰,都一一加以详细描绘,充满了“精雕细琢的工艺”。(Brombert:104)但正如乔纳森·卡勒指出,和巴尔扎克的细节描写不同,福楼拜的细节并不致力于构造一种典型环境,福楼拜“刻画细节的癖好的结果却是一个空虚的主题”,“福楼拜笔下的描述似乎完全出于一种表现纯客观的愿望,这就使读者以为他所架构的世界是真实的,然而它的意义却难以把握”。(卡勒:291)在《萨朗波》里没有解释性的评论,相反,“叙述者的淡出让读者独自面对并解释叙述的意义”。(Danaher:22)没有了解释的细节描写实际上延宕、分解甚至断裂了小说叙述的意义关系,从而使环境的典型性和历史感丧失了。
除了无目的的精确描写以外,《萨朗波》中还充满大量感官印象式的描写。例如描写太阳初升:“地上的一切都在大量扩散的红光中蠢动,因为太阳神仿佛要将自己撕开,把血管中的金丝雨光华煜煜地倾注在迦太基城中。”(福楼拜:20)类似这样的印象主义描写在小说中比比皆是。法国批评家让—皮埃尔·理查指出,福楼拜在这方面具有明显的印象主义风格,他“把总体的感觉化成许多纯净而由相互对照的小感觉”,(理查:258 )小说中这些无数的“小感觉”形成了一个个流动的漩涡,在总体上令人眩晕而使读者丧失了历史环境的确定感。
我们再看小说中的“历史解释”或“历史的真理”问题。事实上,历史叙事往往隐含着一种历史解释,隐含着某种历史哲学,“历史小说”要叙述的也不是毫无联系的历史事件的碎片,它应通过具体的人和事体现出历史事件之间的某种联系和历史发展的意义,即应表达某种“历史的真理”。然而我们在《萨朗波》中却看不到这一点。在《萨朗波》中,最明显的是,正义与非正义的界限是模糊的。福楼拜悬置了道德判断,他并不意在表现某种历史理念,也并非再现特定历史环境下人的悲剧命运。有论者认为正义的一方是雇佣军,因为他们是被压迫者,作者的同情也是在他们的一方。但事实上,雇佣军(Mercenary army)本身的性质就说明了其从事的战争性质的模糊性,替政府或是为反政府或是外来势力卖命都和某种历史进步的观念无关。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卢卡契由此认为,《萨朗波》代表着历史小说的衰落,因为“它将精神的不朽价值非人化,突出事物的图画般的美而不是强调人的境况,充斥着无关紧要的社会和历史语境”。(Lukács:199)
我们还注意到,主人公缺乏一种历史主体意识,他们意识不到其行为的“宏大”意义,其结果是历史主体与事件本身缺乏一种动力关系。男主人公马托除了孔武有力,实在是没有多少优良条件可以作一支30万大军的领袖。他混混沌沌,智力甚至有些低下。“他自己经常优柔寡断,而且处于一种无法克服的麻木不仁的状态中。”(福楼拜:34)他参加战斗,担任雇佣军的首领的唯一目的就是能够进入迦太基,得到萨朗波。他的几乎所有的行动都是由他对萨朗波的欲望激发出来的,对她的幻想成为他唯一的行动指南。他甚至认为,对迦太基的战争是他个人的私事,而他的私事即是得到萨朗波。他把自己封闭在幻想与欲望之中,忘记了战争的目的与意义,或者,战争的目的和意义根本未曾进入他的视野。他对萨朗波说:“难道我关心迦太基吗?它的人群熙来攘往,仿佛消失在你的鞋子扬起的尘埃中……”(福楼拜:240)萨朗波的几次似乎有着重大“意义”的政治性活动,也因行动主体沉没在狂热的宗教玄思与肉体渴望的感觉之中,其意义也被消解。作为一部“历史小说”,《萨朗波》并不缺少历史的“行动”,而恰恰缺少对行动“意义”的意识。这种意识的缺失,“如果归结到它与历史发展或时代的关系上,就是指主人公并不实际介入到历史事变中去,而仅仅将自己封闭在个人的视觉、听觉或内心世界之中”。(王钦峰:88)
但这并不意味着,《萨朗波》缺少“历史观”,而只是说它的历史观并非我们通常所认为的有关历史发展动力和规律的历史观。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批评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的观点对我们颇有启发。他区分了两种历史观,一种是“关于表征的固定观念”或某种“对历史的洞察力的信念”,另一种则是对于历史的欲望投注(a libidinal investment in the past)。他认为,福楼拜恰恰属于后者,他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欲望历史主义者”。(Jameson:77 )福楼拜并不致力于表征历史的真实,也不相信关于历史进步的某种观念。他在1846年给情人路易丝·高莱的信中自称是“宿命论者”,“在为人类进步贡献一切与什么都不做之间,我认为没有什么选择的意义”。而“至于提到进步本身,这种模糊的观念对我来说尤其难懂”。(Jameson:76—7)詹姆逊进而指出,《萨朗波》“对于历史的欲望投注实际上仅仅造成了一种(与历史的)变动不居的关系,其内容是不确定的,尽管其表征框架……仍然试图通过赋予这种关系以某种更为恒定的、似乎是肉体性的象征价值来固化这种流动性”。(Jameson:77)
二、“欲望”起舞
詹姆逊所谓这种“更为恒定的、似乎是肉体性的象征价值”实际上就是指《萨朗波》的欲望叙述。欲望是这部小说的真正主角。小说的第一章即为《盛大的宴会》,写的就是大肆铺张的吃的场面:
桌子上摆的全是肉食,有带角的羚羊,带羽毛的孔雀,用甜酒煮的全羊,母骆驼和水牛的后腿,……鱼鳖腌刺猬,飘浮在藏红花的调味粉中。一切都被卤汁、块菰、阿魏淹没,只露出头来。堆成金字塔形的水果倒坍下来压着蜜糖糕点,而且人们也没有忘记放上几只小狗,这种小狗大肚子,毛色粉红,是用橄榄渣喂肥了的,迦太基人视为美味佳肴,别的民族则嫌恶不敢食用。新鲜的食品让人惊异,也刺激了食欲。把头发高高的挽在头顶的高卢人,只顾抢夺西瓜和柠檬,拿过去连皮放在嘴里大嚼。黑人从来没有见过龙虾,被它们红色的尖刺划破了脸皮。……有些酒已经流成水洼,使人滑跌。各种肉食冒出来的热气同人口里呼出来的气息,一起蒸腾到树叶中间。(福楼拜:4—5)
这场宴会给人的记忆如此深刻,以至到小说的结尾,人们又想起了它:“有些人回忆起雇佣军的那次大宴;人们都陶醉在幸福的梦幻中。”(福楼拜:368)自始至终,食欲的表演成了一个狂欢化的梦幻。
过度的食欲暗示出道德、理性崩溃之后原欲的膨胀。迦太基的元老们表面上宰马敬神,实际上每夜都到庙里来偷吃马肉;被困在绝境的雇佣军,先吃马肉,后吃俘虏,再吃伤病员,
只要有一个人踉跄一下,所有的人立刻嚷起来,说现在这个人没希望了,应该贡献出来为别的人服务。……假装不注意,踏到他们身上,弄得那些濒死的人为着表示自己的精力充沛,勉力伸出胳膊,或者站起来,或者哈哈大笑。有些昏迷过去的人痛醒过来,发觉人们正用破损的铁片在锯他们的肢体……(福楼拜:329)这真有一种黑色幽默的味道。
小说中人物的情欲也是旺盛的,甚至是歇斯底里式的。萨朗波的身体点燃了马托的情欲:“她的胸前除了项链上的钻石以外,凡是裸露的地方都闪闪发光;在她的身后可以闻到一种庙宇特有的香味。从她的整个人身上流逸出来的那点东西,简直比酒更甘美,比死更可怖。”(福楼拜:37)当他触摸到她的时候,食欲与色欲奇妙地融为一体,“他的整个人翻腾起来。他真想搂抱她,吞下她,喝了她”。(福楼拜:238)在生死攸关的行军途中,马托想到的也仅仅是萨朗波带给他的迷醉和痛苦:“一种陶醉的微笑使他的脸上大放光明,仿佛有强烈的光线直射到他的身上;他伸开双臂,在微风中送去无数飞吻,同时喃喃地说:‘来吧!来吧!’”(福楼拜:267)
萨朗波也有无尽的欲望和烦恼:
从我的内心喷出一股热气,比火山口上的烟雾更浓重。有许多声音在呼唤我,一口火球在我的胸中滚动和上升,使我窒息,我快要死了;然后一种甜蜜的东西从我的头上一直流到我的脚下,通过我的肌肉,……这是拥抱我全身的一种爱抚,我觉得全身被压,仿佛有一个天神压在我的身上。啊!我恨不得沉沦在夜雾中,在泉水的波涛中,在树干的汁液中,脱离自己的身体,变成一丝气息,一缕光线……(福楼拜:56)
萨朗波融入了马托的欲望之舞,她感到仿佛被暴风吹走了,被太阳神的威力占有了。她恐惧马托,但对他的渴望与日俱增;她仇恨他,但又觉得这种仇恨可以看作是一种神圣的东西;他强暴了她,但这种强暴使她目眩神迷。卢卡契指出,在《萨朗波》中,陷入爱情的人缺乏“甜蜜和伤感这些恋爱中的人的起码的资质”,尤其是马托,他杀人如麻,只有残忍的野兽的性格。而笔者倒认为,《萨朗波》中的爱情模式是很独特的,“甜蜜和伤感”的爱情模式在《包法利夫人》中已经被当作虚假的、自欺欺人的浪漫主义幻想而被讥讽和抛弃了,福楼拜在《萨朗波》中要寻找的或许正是一种更为本能,更为强烈,同时也更为本真和真实的情感模式。在小说的最后,萨朗波因看到马托之死也倒地而死,似乎正是以情感的强烈程度来保证情感反应的本真和真实。
小说中还处处充斥着一种死亡的气氛。作者似乎陶醉于对杀戮与对丑恶事物进行展览的欲望之中,一种幻灭的、世界末日的情调漂浮于文本的表层。据粗略统计,出现于小说中杀戮场面,包括钉十字架、群体杀戮、折磨然后屠杀、喝人血、吃人肉、烧人、动物杀人、人杀动物等等这些赤裸裸的的血腥场面不少于三十处。① 这对于一部只有二十余万字的作品(中译本)来说是极为惊人的。此外,还有许多对于丑恶事物的不厌其烦的描绘与展览。迦太基军队统帅之一的阿农残忍恶毒,他的麻风病使他的身体溃烂得目不忍睹。小说对他的已烂成一团的身体津津有味地描绘着:他的脸上都是疮,发紫的嘴角里喷出比死尸的臭味更叫人恶心的气息,眼睛烂得没了睫毛。当他最后上绞刑架的时候:
他们把他的身上剩下的衣服剥掉——于是他的怕人的身体就显露了出来。烂疮布满了这个叫不出名字的肉堆;大腿上的肥肉把脚趾都遮没了;指头上悬挂着暗绿色的碎肉;眼泪在他双颊的肿块中间流着,使他的脸上蒙上一层十分可怕的悲惨神情,似乎眼泪在他的脸上比在别的人脸上占据更多的地方。(福楼拜:347)②
小说中的这些对于各种欲望以及丑恶的过度描写,一方面使历史的“真实”隐没在欲望的阴影与暗流中,另一方面也营造出一种浓浓的幻灭情调与虚无色彩。从这个意义上说,“欲望之舞”也是“死亡之舞”。
三、象征意义的构建
在《萨朗波》中,欲望本身还呈现了一种新的意义结构,这种意义结构是由水、蛇和神衣这三个象征性形象组建起来的。柔软、飘忽不定、危险、神秘,是其共同特点。欲望自身所具有的生命力特征及其神秘性、创造性和毁灭性,在其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水作为欲望的象征首先是因为它是欲望之源。月神庙里的大祭司沙哈巴兰这样告诉萨朗波:
在众神面前,只有黑暗,一股气息在荡漾,这股气息同人在梦中的意识一样,又重浊,又朦胧。气息凝固起来,创造了“情欲”与“裸女”,从“情欲”与“裸女”中产生了“原始物质”。那是一团混浊、漆黑、冰冷、深沉的水。(福楼拜:59)
水既是生命之源,欲望之源,同时也有恐怖之处:它混浊、冰冷、漆黑、深沉,把生命置于一片死亡与毁灭阴影的笼罩之中。在小说被称为最令人感到意外的插叙中,马托与庞迪尤斯进入迦太基狭窄的供水管道以进入被困的迦太基城,装水的管道被比作坟墓,水带来了窒息、粉碎、坠入黑洞的感觉:流水又把他们冲着走,一种比坟墓还要沉闷的空气压迫着他们的胸部,他们把脑袋埋在肩膀下面,膝盖碰着膝盖,尽可能的伸长身体,像箭一样在黑暗中向前冲去;他们感到窒息,气也喘不过来,差不多要死去了。(福楼拜:82)
有论者指出,《萨朗波》通篇都沉浸在水的象征主义中。(理查:199)在此,水即欲望。欲望泛滥带来死亡之感,正如水能淹没生命;而欲望自身渴望被超越,正如水的本性也倾向于平衡与稳定。“水”即是欲望的能指符号,欲望需要在无穷尽的、令人疲倦的、毁灭性的漂移中被超越,被赋予某种恒定的所指意义。
蛇在小说中象征着欲望生动的波涛,也暗示着死亡的黑暗与危险,似乎又有着来自于彼岸的神圣与神秘。它的走路的方法使人想起江河的蜿蜒,它的体温使人想起古代膏腴的粘稠的黑暗,它咬着自己的尾巴构成的天体轨道使人想起全部星辰和埃斯克穆斯神的智慧。另外,蛇的表现与萨朗波的生命状态之间有一种神秘的对应关系。萨朗波的生命状态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充满了歇斯底里的欲望——欲望满足且被升华——激情焚毁了她的生命;相应地,蛇则表现为:莫名其妙的生病——充满活力——死亡。蛇的变化既象征了萨朗波的命运,又隐喻了欲望与死亡的关系。而在下面这段文字中,福楼拜更是把欲望充满死亡气息的诱惑力与一种唯美主义③的迷人氛围融为一体:
蟒蛇的脑袋在悬挂着挂毯的绳索上面出现。它徐徐的落下来,像一滴水沿着墙壁流下来一样,在散乱的衣服堆中爬行,然后,把尾巴紧贴地面,笔直地立起身来;它的眼睛,比光彩夺目的深红宝石更炯炯有光,向着萨朗波射过来。……蟒蛇倒折下来,把身体的中间一段搭在她的后脖子上,头同尾巴垂下来,像一条断掉的项链,两端下垂到地上。萨朗波拿它绕在她的胁部,胳膊底下和两膝之间;然后抓住它的下额,把它的三角形的小嘴一直凑到她的牙齿边,并且半闭上眼睛,在月光底下把头向后仰。月亮的白光仿佛一层银色的雾把她裹住,她的湿脚印在石板上发着亮光,星星在水底颤动;它的有金斑点的黑身体更紧地绕住她,萨朗波在过度的重压下喘息不止,她的腰弯下来了,她觉得自己快要死了;蛇用尾巴轻轻地拂打着她的大腿;接着音乐停止了,它也跌了下来。(福楼拜:225—6)
“神衣”在小说中一方面是一种决定战争的胜负与历史进程的神秘象征,神衣被迦太基人视为月神的衣服,而月神则是迦太基人的灵魂。迦太基人丢失了神衣就连吃败仗,得到神衣就反败为胜。另一方面,神衣也是一种决定生命活动的神秘力量的象征,是情欲的“语言”,经由它,情欲从潜意识上升到意识,一种盲动的本能力量就可以上升到精神的领域。大祭司沙哈巴兰这样说:“月神是鼓动和操纵人们的爱情的。”(福楼拜:60)看过月神神衣的萨朗波,一方面觉得这是渎神行为而有种罪感,另一方面却又因为从中读出了自己心底的欲望而又有种愉悦之情,一个美妙神奇的世界正在向她打开:在月神光辉灿烂的皱褶中,隐藏着神秘的事物:那就是环绕中泰神的云霞,宇宙生存的秘密。在福楼拜的笔下,神衣具有一种魔咒般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仅决定着战争的胜负,而且作为一个语言符号赋予了男女主人公盲动的欲望以一种精神意义——爱情,使让人恐惧不安的本能欲望得到了超越,同时也使它成为一种致命的激情。在小说的最后,当萨朗波看到血肉模糊的马托走过来时,她觉得“所有外界的东西都消失了,她所看见的只是马托。她的灵魂深处一片静寂”。(福楼拜:371)马托死了, 而萨朗波“因为接触过月神的神衣”(福楼拜:373),也倒地而死。“死亡”在这里证明着情感的本真,显示了神衣——爱情的魔力。
在一种内在气质上,《萨朗波》可以“被看成一首诗”,它“超越了一般的想像力,它与一种热切的内心音乐相回响,以一种复杂的韵律表达自身,在其语言中,词语自身成为可感知的、色情化的现实”。(Brombert:102)小说中,欲望不仅充满了人物与环境,在历史世界之外营造了一个充满绚烂色彩与流动意蕴的象征世界,欲望还成为弥漫在文本世界的一种情调,使小说的叙述风格在整体上体现为一种欲望化的倾向。福楼拜的欲望叙述消解了小说的历史主义主题,从而使欲望的“色情化的现实”成为小说的真正主角。《萨朗波》是一首欲望的诗,欲望激荡起生命的狂欢舞蹈,又在一种死亡的氛围中传达了生命的空虚与绝望。正如萨特指出,“福楼拜的句子既聋又瞎,没有血脉,没有生气,一片深沉的寂静把它和下一句隔开;它掉进虚空,永劫不返,带着它的猎物一起下坠。”(萨特:183)
福楼拜曾说:“我爱人间的两种东西:第一,物,物的本身,肉;其次,高而稀有的热情。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隐居生涯,也喜欢玩世不恭。”(李健吾:34)在《萨朗波》中,福楼拜一方面用汪洋恣肆的欲望之舞淹没了历史的“客观真实”,另一方面,作者试图以一系列精神与热情的象征来超越这个在他看来毫无意义的世界,试图赋予这个如此混乱不堪的世界以某种精神上的深度。如此看来,萨朗波因马托之死而死,这一充满浪漫激情的死亡,反倒拯救了小说意义的虚无,使得这部小说也发出了一些“高而稀有”的精神微光。
最后还是回到本文的开头。一般认为福楼拜的北非之行是为新的小说作实地考察,但实际上北非之行与《萨朗波》的关系相当复杂微妙。在北非,他一方面感受到了某种特殊的古代异域氛围,另一方面他更在其中投射了自身的欲望和想像。
在埃及,福楼拜见证了人类经验的更为广大的范围;面对那些废墟、腐烂和堕落,他写下了他的恐惧;在超凡的美景和声色之乐那里,他写下了他的迷恋。作为整体经验现实的组成部分,迷恋和恐惧相伴而行;这种种经验的强度和反差,都远比他在自己的国度所能够发现的更为动人。(Zielonka:33)
北非之旅使福楼拜感到了强烈的快乐,使他从现实的压力中解放了出来,从而获得了对欲望的更自由的表达。这一点也为我们的看法提供了佐证。
注释:
① 有论者据此认为在这部小说中存在着非常明显的虐待狂倾向。参看:David Danaher。
② 玛丽·奥尔似乎有些牵强地认为,《萨朗波》中的这段对于男性的破损身体描写具有某种政治寓言的意义,它“是福楼拜对当时法国社会病患的解剖,也是对包括全球化帝国主义在内的从古至今的所有帝国权力病态基础的解剖”。Mary Orr,“Costumes of the Flesh:The Male Body on Display in Flaubert's Salammbo”,Romans Studies,vol.21(3),November,2003.p.176.
③ 法国学者丹尼斯·波特甚至认为,《萨朗波》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唯美主义的宣言书。Dennis Porter,“Aestheticism versus the Novel:The Example of Salammb?”Novel:A Forum on Fiction 4,no.2(winter 1971):10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