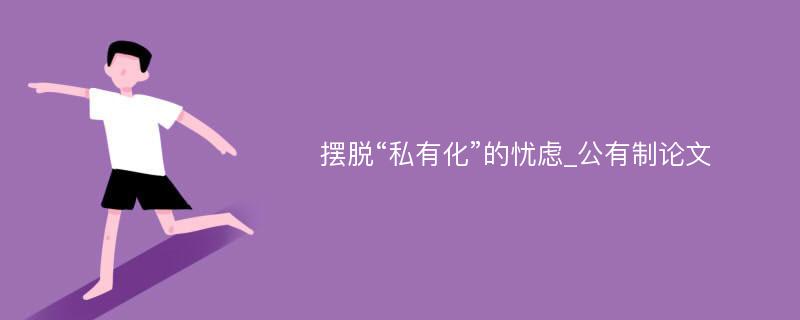
摆脱“私有化”的忧虑,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忧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多年来,所有制改革步履艰难,疑虑非议迭起,根子就在于姓“公”姓“私”的纠缠,这种纠缠使所有制改革几乎成了一块不能轻易触及的“敏感区”甚至是“禁区”。因此,为了成功实现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当前要解决的重大课题,就是学习和贯彻党的十五大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果断地摆脱姓“公”姓“私”的纠缠。
姓“公”姓“私”问题几十年来纠缠得我们苦不堪言;困苦的积累迫使我们猛然醒悟:这个纠缠同其他许多已经摆脱了的纠缠一样,不过是作茧自缚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小平同志制定的改革开放政策使我国的经济生活出现了三个日益突出的现象:一是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三资”企业迅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逐步提高,相应地,原先独占天下的公有制经济的份额逐步下降;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二是国有企业通过租赁、出售、承包经营和股份制改造等措施,一改公有制原先单一的实现形式,逐步出现了实现形式的多样化。三是一部分人迅速致富,积累起令人瞠目的私有财产,连过去的地主老财甚至也望尘莫及。
面对这些现象,人们出现了种种议论和疑虑,理论界更是波澜起伏。有人断言:私有经济的发展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性质已产生严重影响;不仅如此,私有制经济还将成为新生资产阶级政治要求的经济后盾;股份制改造使国有企业面临着不再由国家完全占有的危险;个人收入差距的拉大是可怕的“两极分化”,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被分别称为“小资产阶级”和“民间资产阶级”。就这样,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指出的姓“社”姓“资”的纠缠问题尚未完全摆脱,姓“公”姓“私”问题又被尖锐地提了出来,而姓“公”姓“私”问题的实质仍然是姓“社”姓“资”问题。
这并不是一个新问题。自我国跨入社会主义的门槛,姓“公”姓“私”问题就一直死死地纠缠着我们。对私有制社会剥削和压迫的刻骨铭心和对公有制社会的美好向往,使我们一开始就坚信公有制“越大越公越好”,从而不停顿地追求从一种公有制形式向另一种更高形式的公有制过渡,最大限度地压缩私有制经济的地盘,以至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私有经济达到几近灭绝的程度。这种追求的代价是沉重的:国民经济缺乏活力,综合国力提高缓慢,人民生活难以改善,社会主义“资格”几乎都成了问题。
长期以来,纠缠得我们苦不堪言的不光是姓“公”姓“私”问题。许许多多的问题曾经或者同时或者先后纠缠过我们,使我们几乎一直在没完没了的思想纠缠中过日子。“计划”、“市场”的纠缠,使我们拒绝市场;“产品”、“商品”的纠缠,使我们警惕商品;“资金”、“资本”的纠缠使我们惧怕资本;“竞赛”、“竞争”的纠缠使我们放弃竞争;“集体制”“一长制”的纠缠,使我们排斥一长制;姓“社”姓“资”的纠缠,使我们畏首畏尾,不敢越雷池一步……纠缠的缘起在于凡事都要“对着干”的思维方式;“对着干”的结果使我们几乎把人类迄今创造出来的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济体制、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打入冷宫,而采取了许多落后的、非科学的方法,白吃了多少苦头,内耗了多少精力。今天的实践已经充分证明:所有这类疑虑,都是杞人忧天;所有这类纠缠,都属作茧自缚;所有的这些问题本身,都是不具有真实性和合理性的假问题。我们回顾这些,不是嘲笑这段历史——几乎所有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对这些纠缠都负有这样那样的责任,而是为了吸取教训——做过蠢事不能再做,犯过的错误不能再犯。因此,今天当我们再度面临姓“公”姓“私”问题的纠缠时,首先应当冷静地思考一下问题本身的真实性和合理性,免得我们被它困扰了多少年之后,再去痛惜我们今天的无谓纠缠。
姓“公”姓“私”的疑虑导源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设想,但经典作家设想的条件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并不具备;经典作家为社会主义设计公有制并不是为了公有制本身
消灭私有制,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社会主义的设计。经典作家依据是,资本主义面临的种种困境和危机,根源于它的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自身无法克服这一矛盾,因而也就无法摆脱它的困境和危机。矛盾的尖锐化和危机的加剧只能导致无产阶级革命,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
然而,后来社会历史的这种变革却没有按照经典作家的设想发生在西方那些和平高度社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而是相继发生在生产力十分落后的俄国、东欧和中国。我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小生产如汪洋大海,社会大生产少得可怜,经济极端落后,基本上不具备经典作家所设想的“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条件。我们理应从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建立与多层次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做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能够做到的事情。但是,我们长期忽视这一点,照搬马克思主义本本和前苏联模式,超越历史阶段,不顾生产力状况而片面追求公有化程度的提高和公有制的单一实现形式,严格限制私有经济的发展,其结果,经济建设由于我们违背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而发展缓慢,姓“公”姓“私”的纠缠却成了一种思维模式而固定下来,宁可经济落后也不能进行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方式的改革。
显而易见,姓“公”姓“私”的纠缠并不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应有的问题。如果我们坚持从实际出发,在具备条件实行公有制的那些领域和行业建立公有制,在不具备条件实行公有制的那些领域和行业允许私人占有和经营,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是不可能产生姓“公”姓“私”的疑虑和纠缠的。换言之,疑虑和纠缠并不具有客观的现实性和合理性,而是我们脱离中国国情和把马克思主义的本本绝对化、教条化这双重原因而人为制造出来的,正像前述其他许多纠缠的情形一样。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客观上不该有也不需要有这种纠缠。
同时,今天我们还应该进一步深思,经典作家为什么要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结构。答案非常明确:为了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让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过上好日子。因此,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角色是双重的:相对于社会主义制度诞生前的无产阶级革命来说,它是目的,相对于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以后发展生产力的根本任务来说,它又是手段。那么,社会主义公有制建立以后是不是做到最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了呢?这个问题显然是一个实践问题,而不是靠本本所能回答的。当着我们在实践中发现单一公有制的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实现方式超越生产力水平而制约生产力发展时,理应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极其自然地去进行所有制改革,使之与我国生产力的实际状况相适应,完善它作为发展生产力的手段的作用。然而,长期以来,我们既没有科学地把握和运用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性质的规律,也忘记了目的和手段的辩证转化关系,把公有制永恒不变地置于目的的位置上,为公有制而公有制,不顾它对生产力的实际影响而拼命维持它的既有状态,甚至不顾生产力对它的实际要求而一味追求它的公有化程度。这就使我们不能不犯错误,不受惩罚;这就使我们有些同志面对今天所有制的巨大变革而不能不陷入困惑、痛苦甚至愤懑的思想情绪之中。
公有制可以而且应该有多种实现形式;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是激发公有制活力与生机的必要措施;它动摇的不是公有制本身,而是公有制的僵化单一的模式
我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但是,长期以来,我们所理解的公有制只能有一种实现形式:全民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就是国营经济或国营企业,集体所有制的实现形式,在农业生产中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而它的完善形式就是“大寨模式”;在工商业中基本上则是模仿国营企业的方式去经营。结果,无论是全民还是集体所有制经济,都缺乏足够的活力,而且,越是公有化程度高的经济越是缺乏活力。
经济缺乏活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僵化性、单一性以及由此而产生或与此相伴随的政府职能的错位、生产经营者的利益与生产经营状况的脱节,以及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的不合理,则是主要原因。因此,当着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把“国营”改为“国有”进而允许不同经营主体去经营、把“大寨模式”改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时,经济活力骤然增强、生产大步发展,就是十分自然的了。
然而,这只是一种初步的改革,初步的改革只能收到有限的效果,大批国有企业普遍效益低下的严酷现实迫使我们不得不寻找多种实现方式,对国有企业实行战略性改革,而承包经营、改组、联合、兼并、租赁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便是各地在改革中创造出来的用以搞活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中小型企业的有效措施。这些改革,革掉的只是公有制的僵化、单一的实现形式,而不是公有制本身。例如,国有企业出售,只是改变国有资产的形态——从实物形态变成货币形态;股份制和股份合作制中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仍然是公有制经济;在由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控股的股份制经济中,公有制经济的控制力得到了扩张而不是缩小。公有制通过以上这些大力度的改革和其他必需的配套改革,例如政府职能、金融体制、国有资产代表选拔办法等等改革,就可以大大增强自身活力,增强保值增值的能力,增强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力,因而就会得到前所未有的巩固而不是相反。各地的改革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可见,党的十五大肯定了能对国有企业的种种改革办法,并不是有些人所担心的私有化,而是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的必要措施。在这里,一切关于姓“公”姓“私”的疑虑都应当消除。相反,放弃或阻挠这些改革,听任国有企业按照原有形式和轨道继续滑坡,貌似维护国有经济,实质上是以好心在干损害国有经济的坏事。
如果说有公有制实现形式的改革在巩固和发展着公有制本身,那么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和所有制结构的变革又意味着什么呢?
个人财产和私营经济的激增曾引发出“两极分化”和“私有化”的忧虑;实际上,名义上的私有经济只要管理得当,基本上都以超越自身的社会存在形式而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的原则是共同富裕,但怎样才能实现共同富裕?传统的想法和做法是手挽手,齐步走;不准冒尖,不能先富,谁先富,谁就破坏了共同富裕。但历史无情地宣告:追求同步富裕只能导致共同贫穷,通向共同富裕的正确道路,只能是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个人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去福射、带动、帮助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于是,在“允许先富”政策的感召和激励下,一批又一批个人通过合法途径而变成了“大款”、“巨富”,我国个人差距迅速拉大。这通常被人们误以为是“两极分化”的现实,对于社会主义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只要稍作分析就可以发现,这种名义上的个人财富、私有经济,只要管理得当,基本上都以社会存在的形式存在于我们的国土之上,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银行存款是富有的个人存储财富的常见形式。我国城乡个人存款的巨额增长常被当作洪水猛兽,实际上,银行每天都在把名义上的个人财产转化为实质上的社会财富——存款作为本金,到期获取利息,然后又被合成本金,到期又生出利息,如此循环往复,个人财富在不断增长,但同时也长期游离于个人之外,由银行作为自身资金而投入国民经济的运作过程。个人保存的存折,只是一纸代表其财富的符号,除了给他带来精神上的安慰和心理上的满足外,对他的实际效用等于零。个人财富就这样通过银行的中介而被社会化了。当然,从个人的微观层次看,货币有存有取,储蓄有增有减,不断进行着个人化和社会化之间的双向变换,但从社会整体层次看,我国的个人存款始终在高速增长着,已经很难再成为由个人直接消费的个人财产了,尽管它们仍然记在无数个人的帐上。个人货币财富用于证券投资,对于个人和社会的意义具有类似的情形。
私营企业是私人财富的另一种形式。私营企业的增加和发展使公有制经济的比重逐步下降,改变了我国的所有制结构,因而引起人们的担心与忧虑,实际上,在增加供给、安排就业、提供税收三个方面,私营企业发挥着与国有企业一样的功能,而私营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社会财富,只要那些事关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行业不让私营企业涉足就行了。当然,私营企业比国有企业更有可能偷工减料,偷税漏税,忽视劳动保护,但这并不可怕,关键在于政府科学而严格的管理。而另一方面,千方百计减少成本,提高效益,则始终是私营企业见长于国有企业的地方。至于“三资”企业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小平同志在“南方讲话”中已有明确论述,这里就不多说了。
正因为如此,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明确肯定:“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这是非常正确而深刻的。同样是私有制经济,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功能和作用就完全不同: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私有制经济就服务于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它就服务于社会主义。好比一块砖,把它纳入桥梁工程体系,它就贡献于桥梁;把它用于建造摩天大厦,它就为摩天大厦“添砖加瓦”。这里的关键是它处于不同的系统,服从和服务于不同系统的不同目的,因而发挥着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作用。我们一些同志谈“私”色变,患了严重的“恐私症”,就在于不懂得“私”字是否可怕,关键是要看它服从和服务于何种社会系统。再说,在社会主义社会,私有经济的所有者(除少数违法犯罪者外),都是翻身当家作主的劳动者。因此,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私有经济与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私有经济,同样是“私”,但绝对不可同日而语。
既然个人的富有是社会的财富,既然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在企业的基本社会功能方面可以发挥相同的作用,因此,我们大可不必再惧怕个人的先富,大可不必再纠缠是公有还是私有。无论“公有”、“私有”,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所有。当大部分尚不富有而一部分人先富时,我们与其看作是“两极分化”,不如看作是亿万中华民族分期分批告别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开端。
当然,对于私人财产和私营经济,如同对于国有经济一样需要加强管理。我们所谓的“管理得当”,一是指要引导“先富”们把货币财富用于积累或投资,并且依法经营,节制挥霍性消费,杜绝违法性消费;二是把好出境关,防止一些人把财产转移海外。同时,不言而喻,我们这里所说的个人的富有,是合法的所得,那些采取索贿收贿、走私贩私、坑蒙拐骗等违法手段而致富者,当坚决严惩,不在我们谈论的范围内。
综上所述,对于我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的目标来说,我们的兴趣和兴奋点,不应当纠缠于“公有”还是“私有”,关键是否合乎“三个有利于”。“三个有利于”是我们评判任何一种所有制经济对于社会主义的意义的最权威的标准。因此,江泽民总书记的下述论断,我们要时刻铭记: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当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一切反映社会化生产规律的经营方式和组织形式都可以大胆利用。事实胜于雄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中非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越来越高,公有制经济的比重越来越小。按照纠缠姓“公”姓“私”的传统观点,我国的社会主义应该早就动摇了。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我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我国的国际形象越来越好,国际威望和国际地位越来越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正焕发出越来越令世人瞩目的生机。可见,姓“公”姓“私”问题,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并不具有本质的意义,重要的是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使中国尽早步入世界现代化强国之列——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这才是我们要牢牢把握的根本。
(《中国经济时报》)
标签:公有制论文; 国企论文; 社会主义社会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社会主义革命论文; 所有制论文; 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