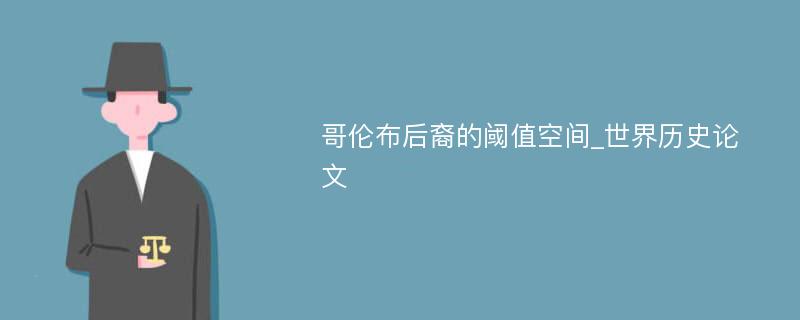
《哥伦布后裔》中的阈限空间,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哥伦布论文,阈限论文,后裔论文,空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492年哥伦布首航美洲,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时代。在随后的五百多年里,世界历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辟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方面,美洲大发现打破了世界各地区间相对隔绝状态,各大洲、各民族间的往来日益频繁,世界越来越成为一个整体,对世界市场的形成和人类社会的进步起了巨大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美洲的发现也开启了世界性殖民掠夺的历史。在随后的几个世纪,欧洲殖民者对美洲大陆进行政治控制、经济掠夺和文化渗透,无数印第安人被杀害,自然资源被掠夺,印第安文明遭到破坏,这些都严重阻碍了美洲社会的发展。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脱殖运动和民族主义的兴起,要求重新评价哥伦布历史功绩的呼声不断高涨。在1991年哥伦布发现美洲500周年之际,许多美洲印第安组织纷纷举行抗议活动,呼吁拉丁美洲人不要庆祝“哥伦布日”,因为哥伦布给他们的民族带来的只是奴役、屈辱和种族灭绝,并将这一天改为“土著抵抗日”①。美国印第安作家杰拉德·维思诺(Gerald Vizenor)的长篇小说《哥伦布后裔》(The Heirs of Columbus,1991)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版的。作为一部重写哥伦布历史的小说,《哥伦布后裔》一反盛典引发的纪念浪潮,以谐戏调侃的方式重新讲述了哥伦布的故事,探讨哥伦布历史遗产所具有的新的可能性。诚然,任何一部关于哥伦布的小说创作都绕不开数百年来哥伦布的话语传统。维思诺重写哥伦布,自然出于对这个传统话语的种种不满,因为无论对哥伦布的历史功绩作何评价,美洲印第安人始终处于受害者的地位,这个话语传统固化了美洲印第安人的刻板形象,强化现行的思维定势、权力结构和社会秩序。为此,维思诺把哥伦布想象为曾经“发现”欧洲的玛雅人的后裔,将其身份和血缘置于多元文化的“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挑战传统历史话语中征服者与受害者、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两元对立叙述模式。依照小说的叙事逻辑,哥伦布不是发现了美洲,而是回归美洲。这样一来,小说不仅颠覆了正统历史话语中文明与野蛮的两元对立,还喻示了美洲大陆多元文化的图景,为重新思考美洲的殖民关系开启了新的思路。本文从哥伦布的话语传统和历史语境入手,探讨小说叙事的“阈限空间”、政治策略、价值取向和现实意义。
杰拉德·维思诺是当代最多产的美国印第安作家之一。虽然维思诺的创作十分繁杂,但他的作品都探讨同一主题,即,如何真实地再现当代印第安人身份的复杂谱系。鉴于土著身份话语的复杂性,维思诺避免使用印第安人这个词,而代之以“部落人民”(tribal people)和“混血”(mixed-blood),前者暗示一种基于血缘和氏族谱系之上的身份概念,后者则指向这种身份的当下状态,这两个词语反映了当代印第安人身份话语中的两个维度。在维思诺看来,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后者既是对建立在血缘和氏族谱系之上的部落身份的补充,又隐含着对传统身份话语(本质主义)的超越和对现实(印第安社区)的承诺,二者之间变动不居、相互渗透的关系构成了维思诺小说中的“阈限空间”。
“阈限空间”概念(liminal space,拉丁文limen,意为“门栏”,指中介性或边缘性),最早由法国人类学家范·盖内普(Arnold van Gennep)和英国文化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提出,指介于分离和聚合的中间地带,代表歧义性、不确定性、边际性和过渡性,后来被扩展到政治和文化意义上使用。在后殖民研究中,特别是在赛义德和霍米·巴巴的著作中,阈限空间是一个重要范畴,与混杂性(hybridity)相联系,对于描述某些社会和文化现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霍米·巴巴在讨论民族与叙事的关系时指出,处于不同身份认同缝隙之间的境况体现了文化的边际性和临界状态,展示了民族作为“文化现代性的阈限空间”(liminality of cultural modernity)(Bhabha 292)。在文学艺术作品中,“阈限空间”还指以混杂性、歧义性、重叠性、异质性和不确定性为特征的文本空间。维思诺的“混血文本”概念(mixedblood text),即源自不同文本传统、由混血美洲人创作的文本,便是集混杂性、歧义性、多元性为一体的阈限空间(Vizenor,The Trickster of Liberty 122)。作为齐佩瓦(Chippewa)部落的混血后裔,维思诺的创作继承了部落传统,同时又突破了传统身份话语的局限。他坚持使用“混血”一词来界定当代印第安人身份,强调土著文化传统在历史和现实中的混杂性,并以此作为一种生存策略。他认为,在当代社会,无论在种族还是文化的意义上,印第安人都是混血。虽然对大多数印第安作家而言,与部落的关系是确立土著身份的前提,但在历史话语、大众文化和文化消费主义的大潮中,印第安人对本真性的渴望已经被所谓“超真实”(hyperreality)所淹没,身份话语也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在社会科学、影院和大众媒体中,部落人民被杜撰成为‘绝对的赝品’”(Vizenor,Crossbloods 55),而土著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对传统的诉求也难以摆脱身份话语的怪圈。为此,维思诺在创作中采取抵制和消解策略,释放凝固于历史影像中的张力,以达到去殖民化的目的(Vizenor,Crossbloods 91)。他指出,“我们被打败了,失去了皮革和羽毛,被凝固于历史之中,我们别无选择。但是,我们可以通过神秘的讽刺手法去颠覆那些虚构和刻板形象,在仪式化的层层剥离中,那些虚构便会自行消失”(Vizenor,Crossbloods 92)。应该说,维思诺对哥伦布历史遗产的处理集中体现了这种去殖民化的写作策略。
关于哥伦布,美国文学中有着悠久的叙事传统,也蕴含着深厚的文化意蕴。正如维思诺所说,“多少个世纪以来,哥伦布在这个崇仰他胜过崇敬自己总统的文化里被奉若神明,人们对其冒险经历的崇仰胜于宗教狂热,他那至高无上的荣耀也使他一直凌驾于那些被他所奴役和灭绝并永远沉寂在历史废墟中的部落人民之上”(Vizenor,"Christopher Columbus" 523)。维思诺在《哥伦布后裔》中调动了全部的叙事资源——真实或虚构、历史或现实、文本或口述——探究美国文化中的哥伦布情结。因此,要解读这本书,我们需要把它放在哥伦布话语传统中来考察。从1492年哥伦布首航美洲巴哈马群岛中的瓦特林岛起至今的五个多世纪里,世界诸国的历史学家、地理学家、政治家对哥伦布及其美洲“发现”之谜所做的研究可谓汗牛充栋。哥伦布的故事也以多重面目出现在文学艺术作品和民间故事中,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以不同的方式被讲述,包括哥伦布的殖民使命、殖民策略、探险以及各种冠以哥伦布之名的地理大发现。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哥伦布的研究徘徊于历史迷宫的一个个误区之中,近代几百年的西方历史也给这一事件套上了“欧洲中心”的光环。西方史学界关于哥伦布航海的动机与目的的各种理论,“已知论”、“天意论”、“亚洲论”、“进步论”或“偶然论”,都没有超出欧洲进步论的范围。近年来,哥伦布更成为一个充满争议但却炙手可热的历史人物。仅《哥伦布后裔》出版的1991年,各国出版的有关哥伦布的书籍就超过以往五百年间此类出版物的总和(Vizenor,"Manifest Manners" 225)。美洲大发现的历史叙事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历史链条,在这个链条上,美洲印第安人始终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在美国,哥伦布往往与美利坚文明的历史相联系,成为民族国家成长的隐喻。19世纪美国诗人惠特曼在《草叶集》中一首题为“哥伦布的祈祷”(Prayer of Columbus)的诗便是这个传统的集中体现。这首诗发表于1874年,当时,惠特曼患严重瘫痪病,诗中的哥伦布也是诗人自己的写照:“一个受够了打击和摧残的老人,/被抛弃在这片野蛮的岸上,远离家乡,/被海洋和阴沉而倔强的双眉紧锁着,沉闷地度过了十二个月,/悲痛,折磨得浑身僵硬,病得差一点死去”(729)。这首诗反映诗人历经坎坷,贫病交加的处境,与当年哥伦布的处境有相似之处。不过,诗人最倾慕的还是哥伦布对上帝的向往和无畏的探索精神。直到诗人逝世前不久写的最后一首诗“哥伦布的思想”,那位“遥远的发现者”始终是他终身缅怀的探险家和最伟大的开拓者:“那种动力、热忱,那种不可战胜的意志,/那种强有力的、能够感受的、内心的决策,比说的话还强大,/上天传递给我的信息甚至在睡梦中都在悄悄对着我耳语,/这些促使我前进”(730)。惠特曼对哥伦布的崇敬和讴歌代表了19世纪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在惠特曼看来,美洲大陆是个人主义精神得以发扬光大、自由开拓的广阔空间。安东尼·德沃夏克创作《新世界交响曲》的1893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哥伦布周年庆典仪式上,哥伦布被誉为美国立国精神的象征,联邦政府还发行了印有哥伦布肖像和“圣玛利亚号”的纪念币。同年,美国历史学家、“边疆学说”创始人弗雷德里克·杰克逊·特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在美国历史学年会上提交了具有轰动效应的“美国历史上边疆的意义”论文,把边疆界定为“文明与野蛮的分界线”,西进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文明征服野蛮的进程。②S.E.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在《哥伦布的一生》中对哥伦布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虽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属于那个业已消失的时代,但他已成为新时代的标志,象征着希望、辉煌和伟业。他信奉中世纪的信仰,却走向了现代的结局。克里斯托弗,基督福音的传递者,将是欧洲复兴谦卑而骄傲的使者”(Morison 5)。一百年后的1993年,美国政府再次发行纪念哥伦布五百周年纪念币,里根总统称哥伦布为“远见卓识、勇气过人、憧憬未来的梦想者。哥伦布就是美国梦的发明者”(Vizenor,"Christopher Columbus" 525)。在关于哥伦布的历史、传记、文学和政治话语的字里行间,充盈着对欧洲现代性的张扬和对欧洲文明的赞誉。
近年来,学界试图从殖民关系角度重新审视和评价哥伦布及其遗产。值得一提的是科克·帕特里克·赛尔(Kirk patrick Sale)的《天堂的征服: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与哥伦布遗产》和兹微坦·托多罗夫(Tzvetan Todorov)的《美洲的征服:他者的问题》。赛尔把哥伦布对土著人的征服、殖民、驱逐和奴役行径视为历史评价中的重要内容(Sale 112);托多罗夫则把哥伦布描写成一个暴君,时而把土著人视为“崇高的野蛮人”,时而视其为“肮脏的牲畜”(Todorov 48-49)。在这两本书里,哥伦布不再是英雄,而是西班牙帝国殖民征服的先行者。这些观点反映了历史评判上的分歧,但无论对哥伦布的评价如何,美洲印第安人要么是欧洲文明的受益者,要么是殖民主义的受害者。这两种地位对当代印第安人来说都成为历史的重负,前者迫使他们放弃传统、融入主流社会,后者则要求他们拒绝主流社会的价值观,沉溺于那个不复存在的理想过去,选择的最终结果都是强化现行的权力结构。因此,如何建构一个既能使土著社会摆脱历史重负、实现其传统诉求的历史空间,就成为时代的要求。
在拉丁美洲文学界,近年来也开始出现了重写哥伦布的文学作品,如阿根廷作家亚伯·普西(Abel Posse)的《天堂的狗》(The Dogs of Paradise)、墨西哥小说家卡洛斯·费恩德斯(Carlos Fuentes)的《未来的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 Unborn)、墨西哥诗人和小说家霍梅洛·亚里吉斯(Homero Aridjis)的《1492:璜·卡贝兹帝恩·卡斯蒂尔的生平记事》(1492:The Life and Times of Juan Cabezdn Castile)和古巴小说家阿罗约·卡彭蒂尔(Alejo Carpentier)的《竖琴与阴影》(The Harp and the Shadow)等。这些作品反思历史再现的问题,不再以受害者的身份讲述殖民历史,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声音,也为我们理解《哥伦布后裔》中的历史修正主义提供了一个坐标。关于小说的写作初衷,维思诺说:“哥伦布并不是个好故事。我并不认为不厌其烦地讲述一个无端地把我变成无助受害者的故事是有益健康的”(Vizenor,"Gerald Vizenor" 157)。《哥伦布后裔》把土著社会从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两元定势和话语逻辑中解放出来,以全新的颠覆意识切入哥伦布的历史遗产。
在维思诺看来,面对持续的殖民压迫,要彻底摆脱殖民主义的影响,必须直面历史,挑战将历史叙述作为真实再现的基本理论设定。虽然逃避或忘却可以缓解创痛,但它会剥夺个体或群体的文化认同。让美国印第安人忘却美国政府对其祖先的战争,忘却无数次背井离乡、流离失所的历史,忘却那惨无人道的杀戮和驱逐,忘却欧洲人带来的病魔在他们土地上肆虐的日子,忘却殖民征服给土著居民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或许可以暂时缓解印第安人作为受害者所承受的历史重压,但这又会剥夺受害者的能动性和责任感,使其自暴自弃。这太多的纠结和困顿渗透了维思诺的创作,因此他选择重写哥伦布,在历史再现的废墟中重新挖掘哥伦布遗产所具有的新的文化意涵。
在《哥伦布后裔》中,维思诺笔下的哥伦布与史书和大众文化中的哥伦布相去甚远,但最出人意料的还是哥伦布的混血身份:“哥伦布是玛雅人……玛雅人把文明带给了旧世界的野蛮人,后来的故事都是众所周知的了。哥伦布最后从死亡的文明逃了回来,把部落的基因又带回到新世界,带回到大河流域。因此,他是一位与我们血脉相连的冒险家,他不过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而已。”③
小说中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玛雅人和西班牙系犹太人的混血后裔(Vizenor,"Gerald Vizenor" 156)。虽然曾有历史学家推断哥伦布可能是犹太人,在15世纪末逃离了西班牙天主教和摩尔人对犹太人的迫害,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把哥伦布说成是美洲人(Sale 358)。维思诺把哥伦布想象为玛雅人,并非耸人听闻,而是执意在历史话语中制造裂隙,具有颠覆性意义。首先,如果哥伦布来自于土著人,殖民者—被殖民者、征服者—被征服者这一近乎约定俗成的两元定势将不再适用于讨论美洲的殖民关系。同时,哥伦布的身份错位还改变了哥伦布航行的目的:不是征服和掠夺,而是带回部落文化的基因。这一改写的直接结果是,土著人不应该、也不需要把所有问题统统归罪于一个邪恶之人,也不应深陷在受害者的身份危机中无法自拔。维思诺对印第安人自视为受害者的做法非常反感:“印第安人不能总是把自身的问题归咎于白人,妆扮成一个自哀自怨、悲天悯人的可怜虫”(Vizenor,Wordarrows 4)。在创作中,维思诺不允许他笔下的人物沉溺于文明冲突前的理想社会,或自暴自弃,成为永无出头之日的受害者。
其次,维恩诺让玛雅人发现欧洲,质疑西方人“发现美洲并教化了美洲的野蛮人”这一说法所隐含的西方文明优越论和欧洲进步论。“发现”一词不仅隐含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探索精神,还体现了西方文明的“世界化”过程,即发现美洲、书写美洲历史中的知识—权力关系:“囊括并限定我们,其本质上是一场战争,而不是语言,这种书写本身隐含着一种权力关系”(Foucault 114)。维思诺认为当务之急是重新考量欧洲中心史观对美洲大发现的历史建构。虽然小说中哥伦布的身份错位和玛雅人发现新大陆的构想出人意料,但如果考虑到哥伦布话语传统的复杂性和争议性,维思诺的构思并非如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荒诞不经。关于哥伦布的“美洲发现”及其历史定位,历来存在争议。维思诺在小说出版的同一年发表了“迷失于再现废墟中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对深陷于历史再现迷宫之中的哥伦布历史和哥伦布之前的美洲发现史做了详细考证(Vizenor,"Christopher Columbus" 525)。在对史料考据、辨伪、论证、假说进行细致分析之后,维思诺的问题是,为什么一个“事实”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并被强加于历史,而其他事件却被贬斥为虚构或传说?历史“事实”得以确立的依据是什么?维思诺把神话、传记、历史、档案、文献等并置于小说的叙事框架之下,以期在各种叙述之间确立一种平等关系,消解话语等级秩序以及史实与虚构的界限:“我的确在所谓历史事件中添加了很多内容。我说‘所谓’是因为一些历史事件是从印第安作家或印第安叙述人那里获得的,还有的是从非印第安历史学家那里获得的,或带有殖民历史的印记,或负载着正统历史叙事的逻辑”(Vizenor,"Gerald Vizenor" 156)。维思诺巧妙地嵌入一种颠覆性历史观,呈现了一个被掏空了的作为西方殖民主义意识形态能指符号的哥伦布。需要指出的是,《哥伦布后裔》并非要修正哥伦布历史,而是为移除强加于印第安人身上的历史重负而采取的文化生存策略:“一个民族要求得生存,他们必须不断地拓展想象的空间”(Vizenor,"Gerald Vizenor" 526)。如果历史书写渗透了殖民文化的权力意识,强化现行的权力结构,矫枉就必须过正。《哥伦布后裔》把受害者的悲剧转化为生存喜剧,正是为了缓解长期殖民压迫所造成的历史重负。对维思诺来说,视角的转换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讲述哥伦布的故事是为了医治创伤,而不是把人变成被动的受害者。受害者的身份作为一种权宜之计固然有其政治意义,但我们切记不可低估叙述的力量,它可以治愈心灵创伤,使人青春焕发、充满活力”(Vizenor,"Manifest Manners" 108)。
当代美国土著批评家阿诺德·克鲁帕特(Arnold Krupat)十分欣赏维思诺轻巧地处理历史的手法:“维思诺对后现代魔法师的形象刻画、戏剧化、开放的形式以及对前现代部落身份的承诺,包括对自然权利和责任的强烈诉求,堪称族裔文学的范例”(Krupat 191)。克鲁帕特看重的显然是维思诺在历史写作中对传统和现代性的双重诉求,这在当代土著作家中的确是难能可贵的。维思诺的风格魅力就在于,在历史陈述中嵌入对历史的批评,同时又把部落主权和文化传统作为终极关怀。作为齐佩瓦族和法裔加拿大人的混血后裔,混血身份使维思诺处于文化批判的制高点。他笔下的齐佩瓦族魔法师很像北美印第安部落中的小丑,对既定社会秩序和成规戒律报以冷嘲热讽或谐戏调侃,在嬉笑怒骂中彰显智慧。维思诺说,魔法师是“万物生灵的翻译者”(Vizenor,"Manifest Manners" 15)。他不仅可以超越种族界限,打破性别和物种的等级和分类秩序,而且魔法师的空间里还容纳了各种声音,界限、范畴、等级和戒律不复存在。印第安作家路易斯·欧文斯(Louis Owens)对维思诺小说中的阈限空间概念推崇备至,认为“混血和魔法师作为一种隐喻,打破了静态的确定性,暗示各种矛盾的事物相互依存的状态”(Owens,Other Destinies 225)。
为了呈现哥伦布文本传统的混杂性,维思诺在小说的情节中让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成为其后裔斯通·哥伦布(Stone Columbus)故事中的一个角色,在部落口述传统中得以延续。斯通叙述道:“斯通(石头)是我的图腾,我的故事就是石头,部落的石头……石头上刻着部落的文字,默默地记载着部落的历史,就像我们聆听血中的故事,在记忆中拥抱我们的过去”(9)。作为哥伦布的后裔,斯通也是记载部落的故事和文字的石头的后代:“最后一位出生的魔法师就是石头,一块坚硬的石头。石头出生后,接下来就是鸟和动物、花和昆虫……石头是最后出生的精灵,从未离开过大地……到了夜晚,兄弟们会对着石头讲述他们的历险故事。石头是故事的神秘集合体……分裂成上千个碎块,四处纷飞”(27)。魔法师石头成为斯通·哥伦布,因为斯通是从最初的石头上分裂出的无数碎块之一,不仅见证了历史,还是两种文化记忆的承载者。斯通把克里斯托弗的尸骨掩埋在密西西比河的源头,他的故事也随着河水流向美洲大陆的各个角落,融入部落的文化传统。哥伦布不再是历史的重负,而是在部落多元文化进程和历史的阈限空间中源远流长的故事。
为了呈现阈限空间的历史渊源,作者采取了多种文类杂糅相间的叙事手法,穿梭于小说、传记、历史、神话、幻想、航海日记、地理杂志、地方志、人物志之间。《哥伦布后裔》秉承维思诺一贯的写作风格,将哥伦布叙事传统置于众声喧哗的历史图景之中。在对哥伦布历史文献和叙事传统的处理上,作者采用混杂和粘合的文本聚合形式,构筑了哥伦布叙事的多元语境。在众多文本中,引用频次最高的要数哥伦布航海日记。这说明,作者不仅对该题材的叙事传统非常熟悉,而且还赋予哥伦布应有的话语权利。尽管维思诺可以通过修正、削弱甚至消除哥伦布在传统话语中的地位来抵制宏大叙事,但这样做的结果会导致对历史本身的操控,而“居高临下的历史姿态”正是传统历史学家的所作所为(Vizenor,"Tricksters of Liberty" 134)。维思诺意在消解历史文献的显赫地位,因为正是对历史的操控确立了主流文化的霸权神话。对关注不同声音,特别是历史见证者的声音的作家来说,哥伦布在多元文化对话框架下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K.M.布雷泽指出:“对维思诺来说,纠正历史叙述的错误、把哥伦布贬斥到历史深处的做法显然过于简单,既不能给人以启迪,也缺少幽默感”(Blaeser 95)。在维思诺看来,哥伦布不仅是历史的,还是当代美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思诺锋芒所向的不是哥伦布本人,而是哥伦布的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影响,这就要求小说家在处理史料时慎之又慎。
哥伦布的话语传统长达五个世纪,其中充满了歧义、纷争和矛盾。维思诺在小说的“后记”中详尽考察了这个芜杂、离散的叙事传统,其中包括学术著作、人物传记、哥伦布航海日记的多个译本、人物志、地方志和史料考辨等,既有反映欧洲进步论的史学著作,如塞穆·艾略特·莫里森(Samuel Eliot Morison)的《哥伦布传》(Admiral of the Ocean Sea:A Life of Christopher Columbus)和《伟大的探险家》(The Great Explorer),也有以新视角探索殖民关系的研究成果,如彼得·休谟(Peter Hulme)的《殖民冲突》(Colonial Encounter)。维思诺还提及科克帕特里克·赛尔与罗伯特·福森(Robert Fuson)关于哥伦布的犹太血统的争论、米兰·昆德拉的《小说的艺术》、艾尔伯特·怀安荪(Albert Hyamson)的《英国的西班牙后裔》(The Sephardim of England),哈特福德·波斯菲尔德(Hartford Bosfield)的《路易斯·瑞尔:暴动与英雄》(Louis Riel:The Rebel and the Hero),杰克·马修(Jack Matthews)的《珍贵图书收藏》(Collecting Rare Books)等不同文类的相关文本,展现了任何单一文本和话语传统所无法穷尽的哥伦布:“当我们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时,我们不过是总结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各种学说和争议的结果而已,我们只是选择了某一种特定社会机制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决定的某个特定的结果。发现的观念是由社会条件所决定的,是一个过程,而非时间上的一个点和事件”(188)。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多元混杂的小说比起为哥伦布树碑立传的政治话语更能够反映哥伦布历史的真实。维思诺在小说和历史中左右逢源,提醒读者注意历史的文本性,挖掘哥伦布遗产所具有的“叙事潜能”(narrative chances):通过渲染哥伦布遗产的混杂性,质询那种以特定政治立场或单一文化视角来再现和评价哥伦布及其历史功绩的思维定势。④
面对如此庞杂的话语传统,维思诺在文本和史料的选择上可谓用心良苦。在小说开头,维思诺引证哥伦布航海日记中记载的哥伦布接近美洲大陆时眺望到的蓝色之光,随后附上莫里森的权威传记《伟大的探险家》中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那是一束自基督诞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启迪人类的灵光”(Morison 36)。莫里森把哥伦布与耶稣基督相提并论,正如基督给基督徒带来了生存意义和道德启迪一样,哥伦布也给美洲带去了文明的曙光。但是,如果我们记得小说关于玛雅文化影响了耶稣基督和哥伦布这个大前提,我们就会明白哥伦布到达美洲是怎样一种回归了:那是土著文明的复兴和土著精神的回归。小说暗示,基督的诞生和美洲大发现并非欧洲人的伟绩,而是反映了作为世界多元文明奠基者的玛雅文明的巨大辐射力。
从小说的叙事结构看,《哥伦布后裔》是一部探讨哥伦布遗产的元历史小说,将哥伦布叙事传统置于多元文化的阈限空间,质疑西方文明的影响力。维思诺强调指出,所有关于哥伦布的知识都是文本中介后的产物,这些文本最终造就了哥伦布神话。因此,小说意在把视线引向哥伦布遗产的建构性,以便重新审视哥伦布与美洲社会现实的关系。关于这一点,布雷泽所言极是:
他[维思诺]的目的显然不是以一种哥伦布的历史叙述取代另一种叙述,以便“重新掌控”(re-possess)历史,而是将历史的领域转移到他所说的“根深蒂固的西方视野”和“殖民凝视”(colonial gaze)之外。他相信,历史不应当被掌控,而应当被想象。历史不应成为社会和政治权力的象征或工具,而是个人和群体强化自身的途径。历史不应奴役他人,而应当解放思想。(Blaeser 96)的确,小说的潜台词可以用维思诺的话一言以蔽之:“哥伦布象征着殖民者的贪婪目光和久远凝视”(Vizenor,Manifest Manners 233)。长期以来,这种“殖民凝视”主导了历史的书写和想象。维思诺将多种文本合而观之的努力意在释放殖民历史中的张力,将哥伦布纳入广阔、混杂、多元的历史时空。从这个意义上说,小说结尾那封被哥伦布放入木桶在大海上随波逐流的信不啻是被放逐的哥伦布遗产的最好隐喻:它属于广阔、混杂、多元的阈限空间。小说的结局似乎暗示了与史学界哥伦布研究的相同趣向:哥伦布发现美洲不是孤立的产物,而是人类历史发展链上的一环,哥伦布本人不是欧洲历史的宠儿,而是世界历史中的一员。只有把握这两个原则,对哥伦布的评价才能走出历史再现的误区,还其在世界历史中恰当的位置。
在小说结尾,维思诺还通过文化谱系学的构想,描写了土著社会创建民族国家的经历。在哥伦布五百周年庆典之日,哥伦布后裔在美国和加拿大之间成立了“阿辛尼卡共和国”(Point Assinika),标志着经历了五百多年文化浩劫的土著社会的生存和延续。在这里,哥伦布后裔试图建立一个能够接纳所有民族和种族的“独立主权国家”,身份不再是排他性的,而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借助这个虚构的理想国,维思诺重申了他一贯的“混血身份策略”:所有美洲人都是混血,我们都是哥伦布的后裔,归属于多元文化的谱系和传统。
关于“阿辛尼卡共和国”,维思诺确有所指。在一次访谈中,维思诺承认阿辛尼卡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罗伯茨岬半岛:“我关注这个地区差不多二十多年了,那是建立部落主权国家最理想的地方。”⑤多年来,维思诺对建立印第安主权国家的可能性给予了诸多关切和思考,《哥伦布后裔》的初衷就是写“一部关于革命的小说,一部描写一个新兴国家诞生的作品”(Vizenor,"On thin Ice" 287)。在阿辛尼卡,人们不需要护照和边检直接入境,因为“哥伦布后裔对任何政治边界不屑一顾”(131),阿辛尼卡的地理政治学旨在消解任何武断的边界划分。路易斯·欧文斯对维思诺的越界思想(阈限空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通过魔法师般的符号运用,打破主流文化自我中心主义的虚幻镜像,消除故步自封的文化边界”(Owens,Mixedblood Messages 40-41)。在美国土著学界,以伊丽莎白·库克琳(Elizabeth Cook-Linn)、沃德·丘吉尔(Ward Churchill)、杰克·弗比(Jack D.Forbes)、安尼特·杰姆斯(M.Anette Jaimes)为代表的印第安分离主义(cultural separatism)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思潮,主张从现存主权国家中分离出来,建立以领土、人口和文化认同为基础的主权国家。在政治自治、文化主权、文化遗产归属等问题上,分离主义要求重新界定印第安人身份,坚持“独立自主的印第安学术传统”等(王建平 27)。后殖民批评家德里克还把“分离主义”与“本土主义”(nativism)和“民族主义”相联系,相信重新获得殖民统治前的本土文化精髓的可能性,并把这种信念建立在超历史的灵性上,这一立场构成了后殖民批评中全球化与本土化冲突的重要方面(31)。维思诺断然摒弃这种文化分离主义立场,小说最后建立在阈限空间概念之上的理想社会就是为了消除基于文化和种族之上的身份建构,提倡世界大同,从更深刻的意义上回归部落文化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哥伦布从生物学、遗传学和文化的意义上连接了欧洲、美洲乃至整个世界,这或许就是《哥伦布后裔》的阈限空间所蕴藏的文化意涵。
注解:
①哥伦布日(Columbus Day):每年10月12日,是一些美洲国家的节日,纪念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492年10月12日(或10月的第二个星期一)首次登上美洲大陆。哥伦布日是美国于1792年哥伦布首航美洲300周年首先发起纪念的,是美国的联邦假日。
②"The frontier is the outer edge of the wave—the meeting point between savagery and civilization," Fredrick Jackson Turner,"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Frontier and Section:Selected Essays of Frederick Turner(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Inc.,1961) 37-62.
③Gerald Vizenor,The Heirs of Columbus(Hanover,NH:Wesleyan UP,1991)9.后文出自本著的引文,将随文在括号内标出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行作注。
④"narrative chances"源自于维思诺的著作Narrative Chance:Postmodern Discourse on Native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s,是指采用各种叙事手法探讨土著美国人的身份、主权和传统的可能性。
⑤罗伯茨岬(Point Roberts)位于美国和加拿大之间,素有美国飞地之称,归华盛顿州管辖。这里三面环海,与太平洋相连,北侧毗邻加拿大三角洲市,与华盛顿州隔海相望。罗伯茨岬最初于18世纪末被西班牙人“发现”,后被英美殖民者瓜分,以北纬49度线为界,南半部归美国,北半部归加拿大。罗伯茨岬最早多为印第安人居住,人烟稀少,被称为“远离文明的荒蛮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