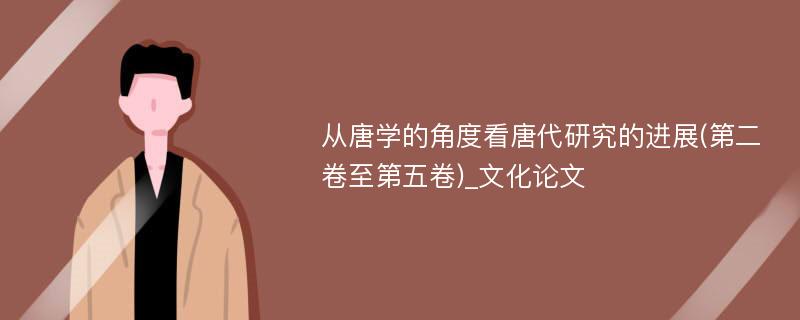
从《唐研究》(二至五卷)看唐代研究的进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唐代论文,二至论文,进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唐研究》是由美国唐研究基金会资助的研究唐代及相关朝代的大型学术专刊,北京大学荣新江教授任主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每年出版一卷。自1995年问世以来,以一种格外引人注目的姿态,至今出版至第五卷了。在研究唐代及相关时代各学科领域的学者中间,《唐研究》受关注的程度在日益提高。它是以书籍形式出版的,按时连续出版。笔者在《唐研究》(第一卷)出版后,曾撰文对其反映的唐代研究动态和办刊特色进行了介绍(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 该文勘误附后)。今将第二至五卷的主要内容按照其本身的分类进行简单的介绍,间或就其体现的近年来唐代研究的进展进行走马观花式的评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介绍的文章并不全面,许多重要的论文并未提及,这完全是由于笔者理解和概括的能力所限;而且对研究动向的分析、对一些文章的评论和内容概括都肯定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诸如此类,敬请编者、作者和读者原谅并指正。所幸随着《唐研究》影响的扩大和发行的增加,读者可直接查阅原刊。
第一类为有关宗教和思想史研究的文章,二至五卷共计发表了12篇。总体来看,此类文章非常专门化,是本刊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努力的重要板块。由于唐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及其对外文化交流的特殊性,有关唐代宗教的研究是国际显学,长期以来积累了大量的成果,但在中国学界却并不广为人知。本刊发表的此类文章,大都注重学术规范,尊重学术史的积累,不仅将这个领域的研究向前推进,而且将国外学者相关的研究方法和理论引入其研究之中,有的本身就是西方学者撰写的英文论文,以极大的信息量真切地介绍了国外研究中国宗教和历史文化的最新动态。
张广达《唐代祆教图象再考》(第三卷),对法藏敦煌文书中一件涉及祆教神祇的淡彩线描画进行图象学的考察,即用图象学的方法解读“或许是人们能够找到唯一的一件反映伊朗或中亚的宗教题材的图象”,分析图象中与宗教有关的各种符号的象征意义及具体所指,并结合宗教发展和东西文化交流的历史大背景,指出这种图象相对于宗教原义所产生的变异。类似的研究,笔者还听过姜伯勤先生所作《山西介休祆神楼古建筑装饰的图象学考察》的学术报告(1998年)。他们的研究,是中国学界对国外有关研究的有力回应。
林悟殊《唐朝三夷教政策论略》(第四卷),通过探讨唐朝对待摩尼教、景教、火祆教三种传自波斯的宗教的政策及演变,考察了唐代统治阶级意识观念的走向。指出三夷教是唐代西域移民的精神支柱,唐季对三夷教的取缔,反映了统治者对外来民族的排斥和恐惧,标志着唐代统治阶级意识观念由对外开放转向对内加强统治。作者此前已经出版《波斯拜火教与古代中国》(1995)、《达·伽马以前中亚和东亚的基督教》(译著,1995)和《摩尼教及其东渐》(1997)等著作,包括本文在内,其在这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前沿。
严耀中《唐代江南的淫祠与佛教》(第二卷)是对地域性民间崇拜与全国性宗教在江南地区关系的探讨,指出二者之间关系演变的结果,一方面是使佛教贴近了民间,另一方面是部分杂神淫祠得到官府的容忍而保留下来。意大利学者富安敦(Antonino Forte)用英文发表的《弥勒教者怀义与道教》(第四卷)及其修订文(第五卷),通过对英藏敦煌文献中两件佛教文献《大云经神皇授记义疏》残卷的考察,分析武则天推行佛教化政策背景下对道教优先权的褫夺,以及佛教异端与正统合作强迫道士改宗佛教的具体原因。
有关唐代宗教史料的梳理和考辨,本刊发表的论文也颇引人注目。包括孙昌武《唐长安佛寺考》(第三卷)、郝春文《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的方等道场与方等道场司》(第二卷)和《关于唐后期五代宋初沙州僧俗的施舍问题》(第三卷)、刘屹《敦煌十卷本〈老子化胡经〉残卷新探》(第二卷)、陈怀宇《所谓唐代景教文献两种辨伪补说》(第二卷)、郑阿财《敦煌灵应小说的佛教史学价值》(第四卷)。这些文章的发表,显示了中国中青年学者在宗教史研究领域取得了新的成就。
第一类文章中,还有葛兆光《盛世的平庸——八世纪上半叶中国的知识与思想状况》(第五卷),是作者从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研究中国思想史的系列成果之一,通过对知识的教条与简化、思想趋于装饰与表面、信仰的边界开始模糊与混乱三个方面的分析,指出八世纪上半叶的唐朝在盛世的表象下陷于思想上普遍的平庸与沦落,进而揭示了在思想史和哲学史上这一时段被当作“空白”的原由。
第二类有关文学和语言文字研究的文章,二至五卷共计发表了17篇。由于唐代文学研究本身已是队伍庞大的、相当成熟的研究体系,尽管有饶宗颐、卞孝萱、郁贤皓、葛晓音、陈尚君等先生的贡献,本刊在文学史界是否得到认可,笔者尚缺乏必要的信息。不过,其中几篇有关文学史的论文,都明显体现出还文学史以本来面目的努力,而对于专门研究唐代历史的人来说,则有着分析角度和叙事方式上的启发。
杜晓勤《从永明体到沈宋体——五言律体形成过程之考察》(第二卷),考察了历时二百多年的五言律体的形成过程,除了分析声律理论的出现和诗体发展等文学规律外,还特别指出齐、梁、陈、隋和初唐的宫廷诗人们在诗歌艺术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强调不能从政治道德性的角度贬低他们的艺术成就和开拓创新的艺术精神。葛晓音《论开元诗坛》(第三卷),对盛唐诗歌革新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考察,指出以兼取“建安骨”和“江左风”为特征的盛唐诗歌革新,是以开元初倡导淳古真朴的政治空气为现实背景的,诗歌革新观念的普及主要取决于开元前期时代精神的变化。开元时代那种蓬勃的朝气、爽朗的基调、无限的展望、天真的情感,是一代文人共同的精神风貌,这是盛唐诗的魅力所在,也是盛唐气象的核心,是盛唐时代性格的代表。莫砺锋《论韩愈诗的平易倾向》(第三卷)是对韩愈诗地位和成就评价的深化。
本刊发表的有关文学和语言文字史料考辨整理的文章,一般都是作者长期研究积累的成果,体现了厚实的史学功底,极便学人。如卞孝萱《刘禹锡诗何焯批语考订》(第二卷),将清代学者何焯阐释刘禹锡诗的批语首次整理问世。郁贤皓、尹楚斌《李白诗的辑佚与辨伪》(第三卷),是作者在重编《全唐五代诗》工作中整理李白卷的总结。徐俊《唐五代长沙窑瓷器题诗校证》(第四卷),荣新江、徐俊《新见俄藏敦煌唐诗写本三种考证及校录》(第五卷),是近年来对唐诗最重要的辑佚考校工作之一。程毅中《唐代小说文献研究》(第五卷),是对单行本《唐人百家小说》、《太平广记》和其它收录唐人小说的辑本或伪书进行的异本校勘,旨在增补佚文、辨明版本和文献价值。
第三类有关隋唐五代历史研究的文章是本刊的主体,二至五卷共发表了39篇,包括政治事件与人物、典章制度、社会史与经济史、边疆史地、中外关系与民族史、史学史与史料学等方面。此类文章反映了当前隋唐史学界的基本状况,体现出的进展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关于社会史的研究在一些专题如家族问题和家族个案方面更加深化,一些文章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好评。如郭锋《晋唐士族的郡望与士族等级的判定标准——以吴郡清河范阳敦煌张氏郡望之形成为例》(第二卷),通过对张氏四个郡望形成历史的考察,提出了郡望与士族的判定标准依据的是官品、家世和宗亲原则,郡望与士族的形成,需要在地域性家族进入政治社会之后经过代际仕宦的积累。王承文《唐代北方家族与岭南溪洞社会》(第二卷),探讨唐代北方家族向岭南的移民活动以及岭南溪洞社会的深刻变迁,分析了这种迁移的背景、主要途径和直接影响,并落实到岭南地域社会和文化被中国大一统文化所整合的历史运动中。吴玉贵《凉州粟特胡人安氏家族研究》(第三卷),大量运用碑志史料,对侨居唐朝的最著名的粟特胡人家族安氏进行个案研究,并用以解释唐朝民族关系中一些重大事件以及粟特人汉化的问题。冻国栋《隋唐时期的人口政策与家族法——以析户、合贯(户)为中心》(第四卷),在其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侧重这一时期国家政权对家族问题干预的措施、背景和影响。
二、关于典章制度的研究,进一步注重制度的动态发展和贯通性,体现出在传统选题上寻找突破口的努力。如吴宗国《三省的发展和三省制的确立》(第三卷)、刘后滨《论唐高宗武则天至玄宗时期政治体制的变化》(第三卷)、叶炜《试论隋与唐前期中央文官机构文书胥吏的组织系统》(第五卷)等,都是分层次从总体上探讨隋唐政治体制贯通发展之研究计划的阶段性成果,对一些传统的看法都有所突破。尤其是主要研究其它断代的学者在溯源追流时对隋唐制度的探讨,在制度研究的贯通性和对于一些具体问题的认识上都提出了新的角度。如邓小南《课绩与考察——唐代文官考核制度发展趋势初探》(第二卷),依托于出土墓志,着重探讨唐代对地方官员考核制度的发展,提出绩效与资历的矛盾决定了考核制度演变的走向,而课绩制度中的务实倾向和考课与考察的结合,又直接影响到宋朝的考核制度和监察制度。阎步克《隋代文散官制度补论》(第五卷),在研究南北朝阶官化宏观趋势的基础上,对隋代文散官变迁原委进行考察,在纷乱的隋唐之际散阶制度演进问题上,理清了发展的脉络,提出北朝文散官呈现的阶官化趋势,是唐代阶官制度发展的前提,唐代贞观年间确立的文散官、武散官和勋官三足鼎立的官员等级制度,是对北周制度的继承和重大发展。此外,王德权《从“汉县”到“唐县”——三至八世纪河北县治体系变动的考察》(第五卷),将对古代国家统治机制的考察,纳入到实际地理空间中,一改过去“重组织,轻空间”的倾向,在制度史和社会史的结合点上做文章,对汉唐间国家体系的变迁进行动态的研究,反映了台湾学界的研究动向。
三、关于唐代军政格局和边防体制的研究,构成了一个相对集中的研究话题。陈国灿《安史乱后的唐二庭四镇》(第二卷),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考察安史之乱后唐朝对西域的统治,以及在西域与朝廷阻隔背景下唐朝地方政府实行有效治理的情况,并考订了吐蕃攻陷北庭、安西的时间。张广达、荣新江《八世纪下半至九世纪初的于阗》(第三卷),通过对于阗文书年代的考订,对安西四镇的陷蕃问题和其它重要史事提出了全新的看法,文末附有《安史之乱后于阗大事年表》,是研究唐朝对西域统治和西域民族关系演进的重要工具。张泽咸《汉唐间西域地区的农牧生产述略》(第四卷),是结合汉唐间相关形势,对天山南北农牧业生产发展特色的具体解说,有利于丰富对西域问题的认识。李鸿宾《唐朝后期的朔方军与西北边防格局的转变》(第五卷),以德、顺、宪三朝朔方军的变化为中心,分析了唐朝边防体系随着西北控御重点民族从突厥到回纥到吐蕃的变化而发生的转变,以及西北民族关系的演进。程存洁《唐王朝北边边城的修筑与边防政策》(第三卷)、马驰《唐幽州境侨治羁縻州与河朔藩镇割据》(第四卷)等,都从不同角度深化了对唐代军政格局的认识。
四、关于礼制研究的深化,成为隋唐史研究中的又一新进展。这方面的主要论文有:史睿《北周后期至唐初礼制的变迁与学术文化的统一》(第三卷)、简涛《略论唐宋时期迎春礼俗的演变》(第三卷)、高明士《隋唐教育法制与礼律的关系》(第四卷)等。
此外,在中外关系史、社会生活史、经济史、史学史及重大政治事件和重要人物的研究中,本刊发表的众多论文,无论在史料运用和分析角度上都有一些重要的成果。如罗丰《萨宝——一个唐朝唯一外来官职的再考察》(第四卷),在论列了有关萨宝问题全部材料的基础上,对萨宝一词在中亚的传播过程及其随着大量粟特人移居中国而被带入中国的情况进行了论证,并指出萨宝府是唐朝管理侨民宗教、政务的机构,萨宝成为唐代唯一的译名官职,但不是作为专门管理祆教的官员。加法尔·卡拉尔·阿赫默德(Gaafar Karrar Ahmed )用英文撰写的《唐代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第五卷),提供了汉文史料外的一些新材料和新认识。黄正建《韩愈日常生活研究》(第四卷),利用诗文资料,通过对贞元长庆间文人型官员日常生活的个案研究,使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走向具体化,揭示了当时社会生活中的一些基本情况,如幕府官员生活水平较高、写碑铭挣钱之多、官员宴会的极盛、租房多而买房不易、出行对仕宦与礼制的冲突等。吴玉贵《白居易“毡帐诗”所见唐代胡风》(第五卷),以诗证史,从居室文化方面探讨唐代社会生活中受游牧民族社会风俗影响的问题。限于篇幅,不能一一介绍。
第四类有关考古、艺术研究的文章,二至五卷共计发表了15篇,包括一些重要文物的图版。分别是:葛承雍《唐华清宫沐浴汤池建筑考述》(第二卷)、《新出唐遂安王李世寿墓志考释》(第三卷)及臧振《西安新出阎立德之子阎庄墓志铭》(第二卷)、周伟洲《唐“都管七个国”六瓣银盒考》(第三卷)、胡素馨《敦煌的粉本和壁画之间的关系》(第三卷)、金维诺《唐代在书画理论上的继承和发展》(第四卷)、杨泓《隋唐造型艺术渊源简论》(第四卷)、罗世平《地藏十王图象的遗存及其信仰》(第四卷)、徐殿魁《洛阳地区唐代墓志花纹的内涵与分期》(第四卷)、苌岚《中国唐五代时期外销日本的陶瓷》(第四卷)、徐庭云《唐“都管七个国”六瓣银盒与“白马羌国”》(第四卷)、沈睿文《唐昭陵陪葬墓地布局研究》(第五卷)、葛承雍、李颖科《西安新发现唐裴伷先墓志考述》(第五卷)、杜文玉《唐慈恩寺普光法师墓志考释》(第五卷)、李志凡《唐张守珪墓志考释》(第五卷)。此外,还应包括置于一般历史类文章中的刘瑞、穆晓军《唐秘书少监刘应道墓志考释》(第四卷)。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几方新出重要墓志的整理刊布,及据原石或旧拓对著录不完整墓志进行的补充和考释,这是本刊对学术界的重要贡献。
书评在《唐研究》中所占分量很重,是其区别于国内一般学术刊物及与国际学术规范接轨的重要特色。二至五卷共发表书评59篇,被评书涉及中外学者有关唐代研究的各个方面。仅从被评书目已可看出本刊的学术前沿性及其营造中外学者进行充分对话交流语境的努力。除了笔者在介绍《唐研究》(第一卷)时提到的书评特色外,二至五卷的数十篇书评在规范学术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第一,书评作者都是对被评书代表的领域有专门研究的学者,他们结合对被评书的介绍或综论、推赏或批评,提出或重申了学术研究的基本原则。如重视对文献和考古资料进行探源索流的辨析,反对简单的罗列和似是而非的截取,以克服某些论著习见的对古代文献进行综合叙述的流弊。通过书评建立此种学术规范的成果,体现到了本刊发表的论文之中。第二,这些书评不仅尽量给被评书以学术史的定位,而且皆直接触及被评书的史料考订和史事论证,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讨论。评论者与原书作者在同一层面上进行研究式的对话,不仅是对学术研究的推进,而且读来条理清楚,令人神清目爽,启发良多。第三,一部分书评还能够站在学术史的高度,对被评书代表的学术领域或整个学科的特点和意义及研究动向进行综合分析,起到了为初学者指点门径的作用。例如关于历史研究者如何运用考古发掘报告、出土墓志在唐史研究中的意义及利用时应注意的问题、如何运用琐碎的史料归纳出概括性的结论等方面的论列,以及对学术界关注的一些热点问题或新旨趣的提示,诸如此类,都体现出书评作者和本刊编辑者强烈的学术使命感。
二至五卷发表的纪念文是《严耕望先生传略》并附《严耕望先生论著目录》(第三卷),与第一卷发表的对唐长孺和黄约瑟先生的纪念文章一样,体现了本刊的又一特色。
本刊书末所附中外文相关新书目对学人提供的快捷信息和其它便利也日渐显著。新书目数量呈直线上升的趋势,第一卷仅60余部,二至五卷分别是100、104部、135部、214部。由此看出本刊在搜集研究信息上的努力及其得到学界认可的程度。我们期望着以《唐研究》为依托的国际唐代研究信息库能够尽早建立。
附:《从〈唐研究〉(第一卷)看当前唐代研究动态》(《中国史研究动态》1996年第4期)勘误:第2页13行“历史的交流”作“历史的主流”,第3页9行“确实”作“却是”,第3页17 行“刘继明”作“刘健明”,第3页倒6行“国际化”作“国家化”,第4页6行“官文书”作“公文书”,第4页10行“九山裕美子”作“丸山裕美子”,第4 页倒5行“西州部分”作“西州部田”,第5页14 行“何德辛”作“何德章”,第5页16行“刘建明”作“刘健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