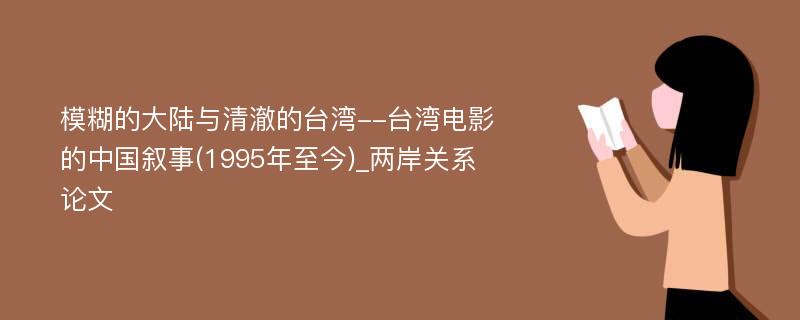
模糊的大陆与清晰的台湾——台湾电影的中国叙事(1995年以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台湾论文,中国论文,模糊论文,清晰论文,大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09年6月,大陆、台湾同时进行的一项名为“两岸民众互看”的同题民调显示,有超过半数的大陆民众视台湾为“家人与亲戚”,确信两岸会走向统一;过半台湾民众则认为大陆只是“生意伙伴”,两岸未来将会维持现状①。在台湾与大陆签署ECFA前夕进行的这项调查,清晰地折射了两岸关系的现状和实质,也反映了台湾在处理两岸关系事务时所持有的一贯视角。
21世纪的两岸电影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展开的。这种关系既不是1949年至70年代末的政治对峙,也非八九十年代的文化想象,而是一种不对等、不平衡的特殊关系。大陆所持的文化态度、情感立场和台湾所持的商业利益、现实政治立场,使两岸电影的他者叙事常常趋于分裂:台湾本岛电影制作饱含愈来愈浓烈的本土情绪和台湾意识,两岸合拍电影则以市场利益最大化为目标,掺和进各种混杂的大陆流行元素,所有以大陆为着眼点的电影元素操控均有明显的市场动机。在整个台湾电影的叙事系统里,大陆形象和中国意识逐渐淡漠,台湾形象和本土情绪正日渐清晰。
一、大陆:弱化的历史形象
1995年是两岸电影关系的分水岭②。1995年后,两岸关系的现实是:台湾当局奉行李登辉的“一中一台”路线,两岸政治对话陷入僵局。台湾当局借“飞弹危机”渲染大陆威胁,进一步将中国形象妖魔化。整个台湾社会在“两国论”的鼓噪下,激发出一股强大的“反统一、反中国”暗流。这股暗流在文化艺术界的表现,就是对大陆情感的刻意疏离,以及对中国历史的蓄意遗忘。似乎在顷刻之间,台湾银幕上对于大陆的乡愁家绪已随风飘散,换之而来的是天堂般的台湾社会和温馨快意的台湾人生。
1996年的《红柿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创作的。这部由王童导演的影片,将台湾描述为宜居的乐土,外省人的台湾体验也是温馨和诗意的。影片开头的一段黑白影像,匆忙交待了外省人因国共内战而随军迁台的历史。当这一群如丧家之犬的流民仓皇间涌入轮船、踏上台湾的土地,影片随之用彩色替代黑白,巧妙描绘了这群大陆人的快乐心情。
1949年冬天的台北,举目四望,是一片片绿野和结满了香蕉的丛林。虽然孩子们吃多了香蕉,都拉肚子,但这个“异乡”仍然是他们的乐园:台湾新同学的热情,校长在化解矛盾中展现出的亲切与耐心以及混在本省孩子中长大的快乐经历,都在强调台湾这个“香蕉天堂”,不再是大陆人暂时的栖身之所,而是外省人可以安身立命的“故土”。在这个以女人和孩子为中心的家庭里,男人们“反攻大陆”的伟业已经被当下台湾琐碎亦踏实的家庭生活消磨得无影无踪,爱台湾、为台湾、在台湾已经成为剧中人物的最高诉求。一切的情节铺陈都指向这一剧作动机:当大人们(父辈)忙着筹备“反攻大陆”的秘密会议,孩子们却沉浸于自己的童年时光,并已在台湾建立了自己的友谊圈。孩子们也不太喜欢父亲,宁愿他永远去打那场“反共”的仗,不愿他回来;冯副官和奶妈虽然在大陆都是有家室的人,但面对杳然无期的归乡期限,彼此中意的他们选择再婚,决意留在台湾生活。女人们的态度同样异常鲜明:妈妈发出的忠告——“半辈子都放在战场上也没打出个名堂来,该好好顾顾这个家了”!奶奶的生活宣言——“什么事情都是假的,唯有带好一家人好好生活才是真的”。这些都在强调台湾生活的意义,仿佛在向不堪回首的大陆岁月挥手告别。
正如焦雄屏所言,王童在此“透过一个外省大家庭在台湾的落籍,彩绘出大陆人的台湾意识”。片中的柿子树、柿子画,象征着一些失散的回忆,是大陆人早期在台湾的历史见证。《红柿子》不再有撕心裂肺的政治悲情,而是“由影像见证历史,由个人扩散为更大的族群典型”③,刻画了90年代中后期外省人对大陆与台湾的情感变迁。
如果说60年代《街头巷尾》(1963)中的台北不过是国民政府逃难至台湾的外省百姓暂居的住所,来到这里的人们随时等待回家(大陆);70年代的《家在台北》(1970)是“第一部明确地将台北呈现为国家都市的‘国片’”,预示着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已经在退守台湾十年后逐渐朝本土化方向发展④;80年代的《香蕉天堂》(1989)中,两个大陆老兵以虚假身份获得在台湾的立足之地,将个人的荒诞异化为历史的真实;那么,《红柿子》则宣告了新老两代大陆移民扎根台湾的决心。在台湾的“国片”史上,几部影片便串联起两岸关系变迁的历史。在这个关于“家”与“国”的寓言故事序列里,人物逐渐游离于大陆时空之外,活在愈加浓郁的台湾本土情绪里。中国的历史已渐走远,大陆的形象也已模糊,台湾电影中的人和事,正以一种告别历史的姿态凸显现时自我,和“去中国化”的现实政治生态形成微妙的互动。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台湾电影,与岛内的政治生态密切关联。2000年陈水扁上台后,执行民进党的“台独”路线和民粹政治理念,两岸政策被不断工具化,大陆形象被妖魔化,“中国”在台湾当局的政治表述中成为一个边缘、甚至被删除的概念。与此相应的是,台湾电影的叙事主题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大陆身影已然远去,台湾话语愈渐清晰,“忘却历史、正视现实”这一当局不断强化的执政理念,似乎正成为台湾电影叙事的主流。
在此语境下,90年代后期、尤其是2000年以来的台湾电影,已经缺乏叙写中国(大陆)的热情。年产量有限的台湾电影,基本上看不到大陆题材和中国故事,有关中国内地的地方故事接连在岛内滞销,整个电影圈已经没有创作中国主题的动力和氛围。从创作主体上看,台湾电影的新生代大多出生于60年代乃至70年代,他们的成长、学习经历基本上是与国共内战“绝缘”的。在90年代以降愈来愈扶植本土文化的台湾,本土导演逐渐成为台湾电影创作的主力,导演群里的“外省第二代”渐渐失去抒写故土的热情,创作者的视线更加内向化,这与80年代前的台湾电影形成了鲜明对比。
从观影主体上看,当前岛内观众的主力仍然是缺乏大陆体验或中国认知的年轻人,有关中国的历史记忆和大陆的传奇故事,已经无法获得他们的共鸣。偶有被包装成大片的历史传奇影像,其口味也已不是中国化的,而是一种视觉奇观的“西化”展示。总体上看,台湾的华语观众在电影类型上偏好“泛文艺片”取向,导致台湾本土电影的故事题材非常狭窄,本地观众的观影趣味正不断收窄。市场需求的畸形单一,导致创作者开始追逐越来越本土的情绪和故事。
对此,台湾导演王童表示,台湾观众不看大陆片,对大陆题材不感兴趣,可能与两地文化观念、行为习惯、生活方式的差异有关。两岸的观影口味不同,台湾观众有自己的选择性。他还不无调侃地说,台湾岛内的政治生态复杂,每天上演的政治事件像电视连续剧,比电影还热闹好看,还有谁会去看乏味的电影呢?《集结号》(2007)在大陆大卖大火,但台湾的观众就是不“集结”,大CAST也无用(两岸的明星认同也有差异),因为你讲的东西跟我无关⑤。因此,“地域色彩”和“可产生共鸣的经验”,已经成为主导台湾电影市场的竞争元素,而有关内地的一切,均与此无关。
因此,无论是市场需求,还是创作动机,大陆都已成为台湾电影里一个被不断弱化的形象。1996年以来的多部台湾电影,“中国”均已退居剧作的幕后,成为一种装饰性元素。《黑暗之光》(1999)中基隆女生康宜暗恋的男生阿平,是一个外省老兵的儿子,大陆在这里仅仅是人物的身份背景,剧情的展开已与此没有太多关联;改编自莫言小说的《白棉花》(2000),虽然有大陆演员宁静和台湾演员庹宗华、苏有朋的加盟,故事发生的空间是具有浓郁胶东风情的山东高密,但台湾创作者以“发生在大陆时空中的激情戏”为卖点,大陆只是沦为一种猎奇元素,其中的文化意味大大降低了。在侯孝贤的古装长片《海上花》(1998)中,华丽的影像格调和旧上海颓废浮靡的气氛相得益彰,成为世纪末风华的一种别样呈示。在这里,旧中国、老上海成为导演描摹历史风情、抒写怀旧心态的时空道具。与几年前《童年往事》等片中刻画的濒于凋零的大陆移民形象和伤感情绪不同,大陆的人和事已经被历史空壳化了。
2000年的纪录片《银簪子》是近年来较少正面涉及大陆题材的一部作品。这部以大陆去台老兵为表现对象的影片,尝试从子辈的视角进入父辈的精神世界,还原活在台湾的父亲对大陆原乡记忆的深刻体验。我们仍可清晰地感受到,作为“外省第二代”的萧菊贞导演,在面对“大陆父亲”的题材时,始终充溢着一种自我言说的焦虑和“叙事坐标无从下锚”的困顿。影片中,“外省父亲”已与当下的台湾时空脱节错位,并使下一代付出代价,“外省第二代”的身份已使人心生厌憎⑥。这种厌憎与尴尬情绪,正是此时岛内电影面对大陆题材心态的直接反映。在一个缺乏话语基础的政治文化生态里,有关中国、大陆的表述要么被放在纪录片这样的边缘体裁,要么挂一漏万、零星提及,被当作装点门面的材料,镶嵌在更加时尚、更加自我的台湾主流片种里。
二、台湾:强化的自我情绪
2007年,时任台湾“新闻局长”的史亚平在一篇序言中说,台湾电影已经“陆续走出历史悲情的沉重寓言,逐渐走出台北阴郁的水泥丛林,让观众耳目一新,也让台湾影坛有了一股复苏的春意。创作者已寻找出具有如彩虹般的多元文化融合及全然认同土地的创作方向,并将台湾独特的风土人情放进影片中,使之成为强烈的视觉图谱”⑦。的确,2006年—2008年间,台湾本土电影市场上的主打片,不管是《六号出口》(2006)、《练习曲》(2006)、《刺青》(2007)、《最遥远的距离》(2007)等市场表现尚可的影片,还是《松鼠自杀事件》(2007)、《夏天的尾巴》(2007)、《穿墙人》(2007)、《当我们同在一起(2)》(2007)、《沉睡的青春》(2007),包括市场上大展风头的《海角七号》(2008)、《不能说的秘密》(2007)、《囧男孩》(2008)等强片,都算是不折不扣的本土青春题材、新生代的面世之作。台湾电影仿佛在瞬间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转变:所有的创作者习惯于蜷缩在个人化的精神世界里,观察一片小小的诗意天空,而为台湾当局站台、为党国呐喊、为主流颂歌的时代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一)历史呓语
1996年前后,台湾电影仍有对历史的展演,只不过这些历史演绎已经全是个人化的视角,也多是一种历史情绪的宣泄。与60年代、70年代的政治咆哮、80年代的政策喊话、90年代的文化劝谕不同,这种历史情绪的抒写带有更多的呓语味道,它在格调上既不工整、也不肃穆,几乎是在散文化的历史片段里,完成了对台湾“历史孤儿”身份和“岛民”流离情绪的注解。毫无疑问,这样的呓语是极富台湾本土意味的。
这一时期吴念真的两部作品《多桑》(1994)和《太平天国》(1996),创作初衷基本上是从知识分子视野出发,掺杂了更多的个人生活印记。《多桑》无论是故事内容,还是镜语方式,都是极为风格化的,其对语言及其背后的族群、身份和政权图景的呈现,也极具情绪性。《太平天国》(1996)仍然是当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历史见解:“影响台湾文化最大的第一是日本,其次是美国,再次是流氓。”吴念真通过《太平天国》,想说明“台湾已经被美国文化殖民了,却不知道、不自觉,甚至以此为荣,被殖民的文化已经深入每个人的生活”,影片致力表现“美国的文化如何通过知识分子传布给所有人”⑧。这种站在知识分子立场上对知识分子的讽喻,作为一种解读历史的方式同样是个人化的。
林正盛的《天马茶房》(1999)同样是历史的个人化抒情。影片所使用的“两地书”形式、“戏中戏”结构,使其看起来结构流散、情节琐碎,充溢着个人主义的历史抒情气息。在类似生活流的叙事中,用小历史的场景植入大历史的景观,1895年—1945年间的多方历史势力交互杂错,操着各种语言的各色民众对历史怀有的情绪在此间渐次荡漾开来,台湾导演的历史纠结跃然银幕之上。无论如何,这一时期的影片创作基调都是极为感性的。与大陆、日本、美国有关的历史悲情属于个人,与台湾本土有关的现实温情同样属于个人,历史在这里已经不再宏大庄重,而变得楚楚动人起来。
(二)个人恋语
90年代中期开始,爱情成为台湾电影一个新的叙事热点。一时之间,与爱情有关的“美丽与哀愁”,在影像世界里展现了表意的丰富性和广阔性,也在现实世界里获得了热情的回应。台湾电影的表达欲望从国家政治,回归私密生活,情感的表达更加自如、放达。
1996年的《重庆爱情感觉》(《泡妞专家》)延续了朱延平一贯的喜剧风格,将爱情放至世俗的生活中进行调侃,将台湾电影引入多元化的恋语时代。随后陈国富的《征婚启事》(1998),格调上更加清新,剧作着力抖落的喜剧笑料,使其看起来更像是一部电视化的城市小品,零碎的故事和舒缓的节奏彰显了创作者松弛淡然的创作状态。十多年之后,它成了另一部大陆卖座电影《非诚勿扰》(2008)的故事原型。在《爱你爱我》(2001)中,导演林正盛的视觉经验虽然比较简单,但角色内心的爱情表达朴素而生动,影片对爱情生发的空间——台北的城市肖像描绘,依然走的是都市轻喜剧路线。2000年的《运转手之恋》,被认为是“一个憨男的幸福生活”的温情演绎,影片在紧凑的剧情中妙趣横生,都市温馨喜剧的气质一目了然。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台湾电影表现了异常持久的爱情抒写的热度和力度。不管是《爱情来了》(1997)中小人物的爱情浪漫喜剧,《对不起,我爱你!》(2008)中的爱情缘分游戏,还是《爱的发声练习》(2008)中有些猎奇的“爱情练习”过程,《不能说的秘密》(2007)中学生时代的纯情初恋回忆以及《蓝色大门》(2002)、《花吃了那女孩》(2008)、《漂浪青春》(2008)、《乱青春》(2008)等表现同性恋情的“奇情故事”,台湾电影中极具私密性的个人恋语从未如此包罗万象、富丽多姿。
我们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台湾电影中的主角们也已更新换代,在剧情中有着与上一代截然不同的情感主题。这些成长在新台湾的主人公,他们的成长经历、言行方式、精神世界,都是极为台湾化的。可以说,21世纪台湾电影的恋爱物语,是极度本土化的情绪展示,具有异常浓烈的个人情结。
(三)青春独语
2000年以后,台湾电影逐渐形成了两个类型方向。一种类型是诸如《双瞳》(2002)那样具有外资背景的跨区域电影,多是商业电影营销的典范;另一种则是诸如《蓝色大门》、《爱你爱我》那样的青春片,属于本土自制的泛文艺片类型。而后者已经成为十年来台湾电影创作的主流类型。不管是2006年的《练习曲》、《六号出口》,2007年的《沉睡的青春》、《最遥远的距离》、2008年的《九降风》、《海角七号》,2009年的《听说》,2010年的《艋舺》,还有近两年颇得口碑的《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2011)、《逆光飞翔》(2012)、《志气》(2013),几年来台湾本土电影票房的前十名基本都是青春片。
这些青春电影,形成一股巨大的创作潮流,显示了台湾本土电影创作的下潜姿态。从创作主体上看,2000年前后台湾电影界出现的大量新世代导演,正是这些青春题材影片创作的主力。这些新导演普遍将青春作为他们初登影坛的敲门砖,以便在日趋主流的岛内年轻观众中寻找机会。仅2008年一年,推出长片处女作的台湾导演就多达十四位,超过全年三分之二的片数,形成一股锐不可当的气势⑨。这些新导演,包括魏德圣、吴米森、郑文堂、钮承泽、杨雅喆、苏照彬、李芸婵、周美玲、陈怀恩、林书宇、林育贤、鸿鸿等,既有与老一代导演(杨德昌、侯孝贤等)合作拍片的经验,在文化结构和艺术教养上又展现出强烈的开放性。他们在日、韩青春偶像爱情片风格的影响下,尝试着结合本土题材,走有别于老一代影人的通俗电影道路。因此,这些青春电影的创作从一开始就是极具台湾风格的。
与此同时,这些立足于岛内社会的青春片,致力于走亲民的大众路线,将爱情、黑帮、励志、历史等类型纳入青春题材,在青春场域中呈现形形色色的台湾社会现象,以引起更广泛的社会共鸣。《囧男孩》中的隔代教养问题,《九降风》里的中学生态和“职棒”历史,《蓝色大门》中的“男同”话题,《乱青春》中的“女同”文化,《听说》中的听障爱情,《海角七号》中的日本情结,青春题材几乎成为所有社会议题和文化现象的寄生体、演练场。不管是黑色喜剧、都市轻喜剧风格,还是惊悚悬疑片、公路片、魔幻片类型,台湾青春片都依托恰当的风格或类型,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度。
青春片的流行,既反映了台湾电影创作和消费的代际更替,同时暗示了台湾电影内容更加本土、自我的趋向。除了一些个人风格强烈的创作外,这些影片基本上都是针对本岛年轻观众的“类型小品”,它们均有着清晰的目标观众和年龄层区分。这些影片所凸显的台湾经验,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地域特点和时间属性,与大陆时空呈现出越来越少的关联性。
三、两岸关系:不断简化的主题书写
在越来越弱化的大陆形象和愈来愈清晰的台湾话语背后,是台湾电影对两岸关系主题书写的疏远。在2000年以来的台湾电影里,很少有正面触及两岸关系主题的影片。两岸关系主题的不断简化,同样印证了台湾电影在精神世界不断内缩的倾向。
2001年连锦华、戴泰龙导演的影片《哥儿们》是一部少有的涉及两岸关系主题的作品。该片既有导演本人在大陆学习(北京电影学院)、生活的影子,又有明晰的关注两岸人情关系的剧作动机。一个被派往北京工作的台湾青年,在大陆频遭意外,却总能得到北京好友的倾情帮助。在这个充满了偶合的过程里,他收获了一段无私的友谊和短暂的爱情。爱情无法进行到底,因为对未来无法做出任何期许,但友情却可以天长地久,因为两岸的年轻人可以共合作、同患难。这正是这部影片对当下两岸关系表达的一种认知:“哥儿们”尚可,“恋人”未知。这部由两岸年轻人共同完成的电影(影片导演、摄影师、录音师和演员黄磊都是北京电影学院的同班同学),在轻松、诙谐的调子里,呈现了台湾年轻人对大陆的现时观感以及对两岸关系的审思:有时近在咫尺,情同手足;有时远在天边,变幻无常。这部带有学生作业气质的影片,表现了一定的纯正性和理想性,虽然有些稚嫩,但在两岸关系的叙述上是认真的。
更多的台湾电影对这一主题了无兴致。《五月之恋》(2004)、《恋爱大赢家》(2004)、《中国功夫少女组》(2003)、《追爱》(2011)、《宝岛双雄》(2012)等影片,要么将两岸关系简化为统一的大陆、台湾恋情模式,要么仅仅依靠两岸角色、演员的混搭,或者两地时空的跳转,为两岸关系作浅白注解。一些台湾合拍片中的两岸关系主题,则显现了具有明确的大陆指向的市场动机和盈利目的。
在这些台湾电影中,两岸关系主题已基本沦为市场的筹码和赚钱的工具,并被不断简化为道具、明星、置景等叙事外壳。横跨台湾、大陆两地的演员阵容,几乎成了台湾电影与大陆合拍的一种定式,有时候香港明星混迹其中,以尽可能获得除大陆、台湾以外进军其他华语市场的机会。徐小明导演的《五月之恋》瞄准两岸年轻观众,由陈柏霖、刘亦菲以及知名度较高的“五月天”乐团加入,剧情时空横跨海峡两岸;王毓雅的喜剧动作电影《中国功夫少女组》同样囊括了时尚的明星阵容,由台湾当年最受欢迎的青春偶像剧——《十八岁约定》女主角林依晨、新加坡创作歌手黄湘怡、具有“台湾偶像剧一姐”称号的“人气小天后”安以轩联合出演,香港影星袁咏仪、大陆明星陈坤同时加盟,影片辗转于苏州、台湾拍摄,这样的演员组合和外景安排,显现了片商同时兼顾两岸三地电影市场的雄心。这些影片都有明晰的市场谋划,其以大陆为主要市场面向的考虑是显而易见的。从投融资角度讲,台湾与大陆联手作业的特点也是十分明显的。但是,它们也仅仅是一种资本操作,在文化上找不到多少关联点,更谈不上对两岸关系和中国主题的认真表现。
与此相反的,是台湾电影对本土情绪、个人私密故事的执著。90年代后期以来活跃于台湾影坛的中青年导演,他们的创作基本上都集中在岛内社会生态和个体精神意趣等议题上。就这一时期最具国际知名度的蔡明亮导演而言,其电影的内容和形式也都是极为个人化的。他关于“现代都市综合症”的观察,诸如亲密亦疏远的复杂人际关系、精神孤独与爱情渴慕的矛盾感、核心家庭的坍塌等,是极富个人观感的,而其电影中持续不断的城市意象——水和门、入口与出口、楼梯、电梯和洞等门廊通道的反复映现和精心描绘,“以及性、身体和空间展示中所显现的私密性和公共性的怪异同化,对60年代老电影和歌曲的深情怀旧”⑩,都是其个人偏好的直接体现。蔡明亮的电影创作既没有强烈的历史感,也没有固定的政治语境,历史抒情和政治象征在他的创作实践中既无必要、也无根基。他的电影时空仅属于个人,历史已经彻底退场,只有个体在特定时空中的生活经验、身份记忆和精神感受是可以被反复言说的。在《河流》(1996)、《洞》(1998)、《你那边几点》(2001)、《天边一朵云》(2004)、《黑眼圈》(2006)、《脸》(2009)等片中,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台湾历史的流动影像,不是社会议题的时代倒影,而是个人化的心理执念和精神呓语,是一个生存个体对这个世界保有的体验性认知。这些创作无一例外地展现了他偏执性的主题和风格(11)。
2000年以后,金马影展专设了“台湾制造”单元,受益于国际影展获奖曝光的台湾当局,欲借此搭建纯粹本土电影的出口平台,电影政策也显示出更加明显的本土导向。
注释:
①这项由台湾《远见》杂志社与104人力银行、大陆爱德惠研市调公司合作完成的两岸民意调查显示,对于“两岸之间最后会变成什么关系”,53.6%的台湾民众认为大陆是“生意伙伴”,13.3%认为是“朋友”;大陆民众有52.3%认为台湾是“家人与亲戚”,认为是“生意伙伴”的占16.2%。对于“台湾未来会与大陆统一还是独立”,60%的台湾民众认为会“维持现状”,64.2%的大陆民众认为将“走向统一”。有超过79.6%的台湾民众自认是“中华民族一份子”。详细数据参看新闻报道《生意伙伴?家人亲戚?两岸民众互看民调大不同》,凤凰新闻网http://news.ifeng.com/taiwan/3/200906/06303531226935.shtml.
②关于1995年前台湾电影的中国叙事及两岸电影关系,参见拙著《中国怀想——台湾主流电影的中国叙事(1978—1995)》,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
③焦雄屏:《〈红柿子〉——外省人的台湾意识》,《中华民国电影年鉴》,(台北)“国家电影资料馆”1997年版,第6—7页。
④林文淇:《台湾电影中的台北呈现》,陈儒修、廖金凤编著《寻找电影中的台北(1950—1990)》,(台北)万象出版社1995年版,第80—82页。
⑤这是王童在2009年11月2日北京电影学院举办的第2届两岸三地电影院校学生作品展的一次研讨会中的谈话。笔者参加了这次面向北京电影学院研究生的座谈会。
⑥骆以军:《红色数字正在滴滴倒数——我读萧菊贞的〈银簪子〉》,《中华民国电影年鉴》,(台北)“国家电影资料馆”2001年版,第54—55页。
⑦史亚平:《中华民国电影年鉴·序言》,《中华民国电影年鉴》,(台北)“国家电影资料馆”2007年版。
⑧白睿文:《光影言语——当代华语片导演访谈录》,罗祖珍、刘俊希、刘曼如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279页。
⑨具体的处女作导演及其作品,参见廖振凯《2000年台湾新电影资料汇整》,台湾电影研讨,网址:http://ctl2.tnua.edu.tw/blogs/taiwancinema.
⑩Emilie Yueh-yu Yeh and Darrell William Davis:Taiwan Film Directors,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5,pp.219-220.
(11)关于蔡明亮电影的论述,参见拙著《颓废景观与病态美学——蔡明亮电影断想》,载《艺术广角》2010年第5期。
标签:两岸关系论文; 台湾论文; 台海时事论文; 电影市场论文; 两岸政治论文; 大陆文化论文; 海角七号论文; 蓝色大门论文; 太平天国论文; 红柿子论文; 台湾电影论文; 爱情电影论文; 剧情片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