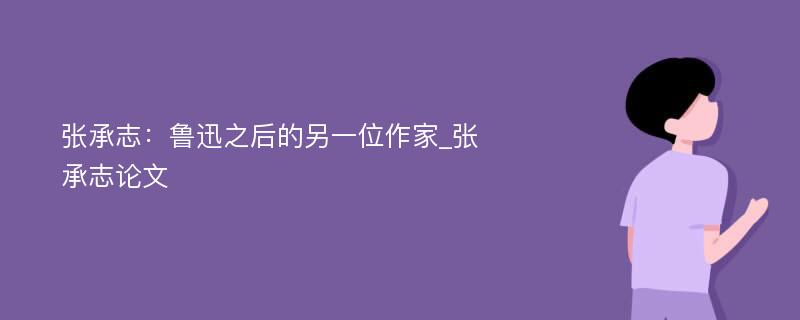
张承志:鲁迅之后的又一个作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鲁迅论文,作家论文,张承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9 文献标识码:E 文章编号:1002-0586(2012)02-0005-07
我身上的某种气质使我难以融入这个时代、这座城市,难以融入到知识分子和文人学士中间去。他们也强烈地感觉到我是一个异类。1989年我进入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师姐朱伟华说我是一个天生的“解构”主义者。理解张承志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尴尬的难题。多少年来,我一直抗拒着他,始终回避着他。在张承志极力要成为一个强者的时候,我一直在追求成为一个“弱者”。陈福民兄读出了我的文字中间迥异于张承志的“不屈不挠的反讽”意识。2005年,当我突然面对可怕的背叛和作弄,面对自己知识、道德和智慧的破产,身体和精神彻底崩溃(我似乎亲眼看见天在我的面前塌了下来)的时候,我终于明白,我一直在回避和拒绝的,实际上是与我自己相关的某些东西。
在许多年以后,我终于开始正视张承志开辟的文学道路。张承志和鲁迅是二十世纪两位前后交相辉映的文学大师和“真的勇士”,不仅在对待纯文学的态度上,而且在社会时代的处境上,他们两人都极为相似,更重要的是,他们最终同样都不得不放弃了虚构性的文学创作。
张承志是新时期文学中性格最鲜明、立场最坚定、风格最极端的作家。张承志自己曾经在《生命如流》中说:“别人创造的是一些作品,我创造的是一个作家。”他既不断地寻求突破,又始终坚定不移。他在《语言憧憬》中说:“我是一位从未向潮流投降的作家。我是一名至多两年就超越一次自己的作家。我是一名无法克制自己渴求创造的血性的作家。”张承志构成了新时期文学中一个巨大的存在,他以一个人平衡了整个时代。
我们谁都不会想到张承志是一位北京作家。老舍曾经说,“北平除了风,没有硬东西。”北京能够接受一切。张承志与他生长的这座城市以及当代文坛构成了巨大的反差。他对这座一代又一代接受征服奴役和“耍贫嘴”的城市没有丝毫的亲近和好感。
张承志是一位回族作家。1948年出生。他亲历了红卫兵运动,并且是“红卫兵”一词的发明者。1968年到内蒙古插队。1972年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1978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1978年以《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一举成名,步入文坛。1982年发表短篇小说《绿夜》、《大坂》和中篇小说《黑骏马》。1984年发表中篇小说《北方的河》。这些作品在当时发生了巨大的反响。1983-1984年到日本访问研究。1985年发表中篇小说《黄泥小屋》。1987年长篇小说《金牧场》出版。1991年出版长篇小说《心灵史》。此后,将主要精力转向写作散文随笔。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和文化崩溃的时刻,他“以笔为旗”,提倡“清洁的精神”,主张“抗战文学”,引起了文坛深刻的震动,更加鲜明地突出了他的精神个性。
从1978年发表的《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一开始,张承志便以一种强烈的理想精神鲜明地区别于当时的“伤痕文学”时尚。王蒙称他是“最后一个理想主义者”。理想主义贯穿了他后来的整个创作。王蒙在《清新·穿透与“永恒的单纯”》中说:“他坚持着他的理想主义,坚持着他的对于形而下的蔑视与对于形而上的追求。一种精神的饥渴、信仰的饥渴,乃至可以称作‘迷狂’(无贬意)的东西出现在他的作品里,令人肃然又令人惊心动魄。从《绿夜》到《黑骏马》,从《黄泥小屋》到《九座宫殿》,从《大坂》到《金牧场》,以及其他一切新作,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执着的精神追求者、一个精神领域的苦行僧、跋涉者、一个由于渴望得太多而痛感着精神匮乏的严肃到了特立独行、与俗鲜谐地步的作家的精神矛盾激化的历程。”王安忆在《孤旅的形式》指出,张承志的写作是表达心灵,草原上的黑骏马,蒙古额吉,北方河流,金牧场,疲惫的摇滚歌手,哲合忍耶,都是他心灵的替代物。“‘孤旅’是他常用的词,这使这些替代全带有漂泊天涯的形迹。”(王安忆《孤旅的形式》,《文学自由谈》1993年第4期。)朱伟指出,张承志似乎一直生活在他自己的过去。“张承志的梦境离不开两个极富象征性的意象,一个是骏马,一个是大坂,这两个意象都连接着英雄:骏马是英雄的坐骑,大坂白皑皑地耸立在那里,是英雄所要征服的目标。……骏马和大坂结合在一起,当然是一条英雄(或者说是勇士)的道路。”中国古代有“夸父逐日”的神话传说,而张承志的创作也始终包含着一个“寻找”的模式。
《黑骏马》和《北方的河》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品。短篇小说《绿夜》是《黑骏马》的雏形。在这篇小说中,过去与现实构成了鲜明的对比。主人公是八年前曾在内蒙古插队的回城知青,“冬天运蜂窝煤、储存大白菜,夏天嗡嗡而来的团蚊蝇,简易楼下日夜轰鸣的加工厂,买豆腐时排的长队”的日常生活让他禁不住怀念美丽的草原姑娘奥云娜。但是,当他回到草原以后,“我的黑眼睛的小天使,我明净的小河”变了样。他所寻找的却已不复存在,“生活露出平凡单调的骨架。草原褪尽了如梦的轻纱。”《黑骏马》体现了张承志典型的“寻找”的主题和叙事模式。小说叙述了主人公白音宝力格骑着黑骏马寻找昔日恋人索米娅的故事。白音宝力格和索米娅由奶奶抚养成人。他们青梅竹马,产生了自然、纯真、美丽的爱情。白音宝力格外出学习时,索米娅遭到黄毛希拉的奸污。白音宝力格无法忍受索米娅和奶奶对于这件事情逆来顺受的态度,愤而出走。当九年以后白音宝力格重返草原的时候,奶奶已经去世,索米娅也远嫁他乡。白音宝力格骑着当年他和索米娅养大的黑骏马四处寻找索米娅。《黑骏马》是张承志的小说中写得相对节制的一篇。古歌《黑骏马》所吟唱的是一个哥哥骑着一匹美丽绝伦的黑骏马,跋涉着迢迢的路程,穿越了茫茫的草原,去寻找他的妹妹的故事。周而复始、低回不尽的蒙古古歌《钢嘎·哈拉》控制着叙述和抒情的节奏,赋予小说独特的乐感。小说中美好的理想与残忍的现实之间构成了尖锐的冲突,现代的爱情悲剧与古老的歌谣遥相呼应。古歌用“不是”来结束寻找,铸成了无穷的感伤意境,充满了复杂的人生感悟。《绿夜》和《黑骏马》构成了一种“寻找—失落—感悟”的模式。
1982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大坂》和1983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北方的河》都表达了同样的征服和崇高的主题,表现了一种想要成为真正的男子汉的强烈的欲望和气质。大坂是一个象征。妻子流产与“他”去征服大坂构成小说故事的内核。它是对于自然也是对于生活的挑战,通过对于极限的挑战实现自我的确证。对于苍莽壮阔的北方的河的征服和礼赞是张承志抒情小说的一个高峰。他在《北方的河》后记里说:“我觉得自己像切开了自己的血管,直至小说发表了很久很久以后,我还觉得自己的血在流,这样的流血使我觉得自己衰弱了。这样的流血也使我逐渐滋生着我的骄傲。”王蒙当时在《大地和青春的礼赞》中感叹:“在看完《北方的河》以后,我想,完啦,您他妈的再也别想写河流啦,至少三十年,您写不过他啦。”北方的河成为了张承志强大的生命力量和青春激情的一个象征:“我就是我,我的北方的河应当是幻想的河,热情的河,青春的河。”他对大河的征服是青春的赞颂,是一种成人的仪式。小说表现了对于大地、历史和人生的沉思,以及知青一代的奋斗、挫折、思索和选择。小说象征和写实两个部分不甚协调,比起河的那种气势和壮美,现实叙述的部分显得局促、肤浅和薄弱。
1987年,长篇小说《金牧场》出版。张承志在《注释的前言:思想“重复”的含义》中对这部长篇小说的内容和形式作了如下说明:
《金牧场》一书的结构是,用70年代初的口吻,描写一次知识青年和牧民的大迁徙,同时描写知识青年的种种。在这个部分里插入对红卫兵时代长征的回忆和思考。全书的这一半,用表示蒙古草原的M为标号。另一半是用80年代的在国外求学的青年的口吻,描写一个解读古文献的研究过程以及异国感受;同时插入对西方国家60年代学生运动、前卫艺术的思考和对中国边疆的心情。书的这一半用表示日本的J为标号。书的两半两条线,始终并行对照。
这样,两条线和其中的回忆独白,概括了从60年代到80年代的种种最重大的事件及其思考。内容涉及知识青年的插队、红卫兵运动的内省、青年走进社会底层的长征与历史上由工农红军实现的长征、信仰和边疆山河给人的教育、世界的不义和正义、国家和革命、艺术与变形、理想主义与青春精神……企图包含的太多了。
小说主人公是一位身在异国的历史学者,在物质高度发达的日本东京,他与环境格格不入。他正在译释一部记载着一个少数民族的英雄们以生命和牺牲为代价去寻找理想的天国的古代文献《黄金牧地》。他曾经作为红卫兵,凭着一腔热血、理想、信仰和激情,重走长征路。后来又写血书上山下乡。《金牧场》采用了结构主义的方式,以巨大广阔的时空,以多声部的形式,构成了张承志作品反复表现的“寻找”主题,使不同时代、民族的人们寻找理想天国的历程结合为雄浑辉煌的交响,表达了他对于自由、正义、理想、青春和反叛的执着追求和礼赞:“我崇拜的只有生命。真正高尚的生命简直是一个秘密。它飘荡无定,自由自在,它使人类中总有一支血脉不甘于失败,九死不悔地追寻着自己的金牧场。”正如作者所言,这部作品涉及了红卫兵运动等许多重大事件和问题,是张承志一部带有总结性质的作品,是他对于青春、浪漫的最后倾诉,同时也是他进入哲合忍耶世界的关口。
在《心灵史》代前言《走进大西北之前》中,张承志将自己1984年冬走进大西北视为一种神意。他强调同西海固的遭遇所导致的脱胎换骨的改变。这一时期他先后创作了《残月》、《黄泥小屋》、《西省暗杀考》、《心灵史》等一批反映回族历史、生活的作品。他震惊于黄土高原恶劣艰难的生存环境,以及他们为内心的信仰所付出的惨重牺牲。《黄泥小屋》中苏尕三因无法忍受官家的威逼、欺凌,割了官家的脖子,过上了流亡的生活。《西省暗杀考》以悲壮的笔调展现了一群回族复仇者视死如归的反抗精神。
1991年出版的《心灵史》是一部令人震惊的奇书和空前的巨著。
对《心灵史》的分类和解释一直困扰着学界,它是叙事和抒情、启示录和诗篇、史诗和抒情诗的统一和融合。它本质上是诗,但是采取的主要又是一种历史的形式。它既是个人的,又是民族的。它既是叙事,又是抒情,既是历史,又是文学,又是哲学和宗教。他自己宣称:“这部书是我文学的最高峰。”张承志的写作无视一切写作的传统畛域,他的写作打破了同时也沟通了不同的领域。张承志重新思考什么是文学,重新思考“形式”和“书”的含义,重新思考写作与读者的关系。他在这样一种思考和写作中把一切问题推到根本上。
张承志是一个回族作家,同时是中华民族的儿子,中国文化的儿子。他在《美则生,失美则死》的访谈中说:“中国的回民是被中国文化养育的贫穷的儿子,他们所代表的是一种信仰的中国人,他们用自己的牺牲为母亲贡献了新鲜血液。只要这种信仰精神坚持于回民,迟早会以某种形式使中国文明丰富”。他在《无援的思想》中写道:“我出身源头在西亚的回回人血统与炎黄毫不相干,但我也是中国文化养成的作家”。他在《岁末总结》中说:“我虽然屡屡以反叛中国式的文化为荣;但在列强及它们的帮凶要不义地消灭中国时,我独自为中国应战。”不仅如此,他是在中国的现实和文化处境中写作,时代的力量有力地雕刻了他。他对于回族和哲合忍耶历史的关注是他一以贯之的反抗强权和关怀弱者的原则的体现。在反抗外国帝国主义的同时,他没有忽略内部各种压迫关系。哲合忍耶对于张承志来说是一种启示,一种依靠,一种资源,一种力量。他在《撕名片的方法》中写道:“今天我重视自己的特殊性。背靠着‘哲合忍耶’——我开始急速地自尊。这是我要求中国文化接受的一个外来语措词,尽管它诞生于中国母体之中。……我输入的是一种烈性的血,是一种义,是一种信,是一种叛逆的和坚守的素质。”他对哲合忍耶和回族历史的书写超出了狭隘的族群意义,而上升为一种普遍的人道。
张承志在《风雨读书声》的访谈中这样谈论《心灵史》:“它描写的和它经受的,一切都是最中国式的。至于我,无非是接受了百姓的委托,为他们执笔,写了他们的一部历史。这无非显示了我的气质和道路——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找到与底层民众结合的方式。”张承志将整个写作过程看作是对于自由理想,对于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寻找。“我以我的形式,一直企图寻找一种真正的人道主义。”(《心灵史·圣徒出世了》)
他强烈地反感主流知识界虚伪狭窄的人道主义定义。他提出“人,人性,人道,人心,这一切在中国应当通过另外的途径去发现。我预感到了。我不信任现代中国的知识界。太重要太本质的认识,至少要在相应的天地中形成。真知灼见永远不会是下贱肤浅的老鸦叫。它需要一片风土、一种历史、一群真正能为我启蒙的老师,还需要克拉麦提为我降临,才能够被我发掘出来。”(《心灵史·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将告诉你们的哲合忍耶的故事,其实正是你们追求理想、追求人道主义和心灵自由的一种启示。”他把哲合忍耶看作是这种人道主义的载体。“哲合忍耶是中国劳苦底层”,是一个“牺牲者集团”,是“坚守心灵的人民”,是一种“穷人宗教”,是从人民中间提炼出来的。“这里含有人、做人、人的境遇、人的心灵世界和包围人的社会、人性和人道。这里有一片会使你感动的、人的光辉。”《心灵史·走进大西北》)“在中国,只有在这里才有关于心灵和人道的学理。”(《心灵史·十八鸟儿出云南》)
张承志的人道主义有其独特的含义。这种人道主义是与底层人民的结合,这是对被压迫者的心灵历史的认同,是对于压迫者、统治者和官方历史的大举破坏和大胆挑战。哲合忍耶的魅力正在于它是“一种最彻底的异端”(《心灵史·仪礼》)。“我渐渐懂了,我是为一种异端的美而吸引。”他“把宗教的尔麦里感觉成了朝着历代统治的示威”(《心灵史·光阴》)。哲合忍耶教派在与专制国家,在与国家这种怪物,这种恐怖机器的对抗中爆发出来了最强烈的力量和美感。“中国人正以宗教反抗专制。”(《心灵史·抓住你的历史》)“一切宗教的和人道的火花都被他们击打出来了”(《心灵史·追随者》)。
张承志通过对于历史的重新书写,通过接近底层,通过对于被压迫者的心灵的历史的表述,去寻找真正的人道。他在赠送给杨怀中《老桥》一书时题写了如下宣言:“让历史就这样把重负压上肩吧!我们要推翻一种伪历史,让我们就这样把自己赶向艰辛吧!这艰辛中会有辉煌的意义。”(一丁《杨怀中谈张承志》,《民族艺林》1993年第2期。)张承志的《心灵史》和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都应当放在“寻根文学”的脉络上来加以理解。张承志和韩少功沿着“寻根文学”的轨迹与现代化的主流价值分道扬镳,一步一步地走向边缘和深入底层。张承志表现了对于统治阶级强烈的不信任。他们无法真正理解历史。“他们缺乏对于人的心灵力量的想象力,因此也不能获得秘密。而历史从来只是秘史;对于那些缺乏人道和低能的文人墨客,世界不会让他们窥见真相。”(《心灵史·黑视野》)
张承志曾经总结自己的创作说他有三块基地:内蒙古草原、新疆文化枢纽、伊斯兰黄土高原。他常常综合地调用民族学、历史学、地理学知识,对西部的人文现状作出冷静客观的记录和思考,充满了一种使命感和忧患意识。张承志在《〈美丽的瞬间〉自序》中曾经回忆说,“草原是我全部文学生涯的诱因和温床。甚至该说,草原是养育了我一切特征的一种母亲。”在他看来,“草原,以及极其神秘的游牧生活方式、骑马生活方式——是一种非常彻底的美”。张承志作为知识青年,在内蒙草原过了四年的游牧生活。草原是他人生的一个重要的阶段,是他人生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用日文出版的《蒙古大草原游牧志》即中文版的《牧人笔记》是一部特别的著作。此书按照民族学的框架,描写他所插队的汗乌拉草原游牧生活。他自己在《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中介绍说:“本书仔细叙述了乌珠穆沁游牧社会的季节、生产、家族及社会构成、家畜与牧人的关系、人的特征与情感形式。”作者强调他作为中国1960年代塑造的、从边疆居民内部产生的一部书的意义。由于中国的知识青年运动,一批与高等学术有缘的年轻人在身份和生存方式上突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牧民,这种改变带来了一系列可能,产生了一种新的学术。
《牧人笔记》细致入微地描述了游牧社会的生产、生活循环过程。在第二章“生命”中描述了草原牧民独特的生存方式以及他们对于生命的独特理解:“也许,蒙古牧民在这里凛冽的北国之春里,年复一年地感受到了更多的温暖、生机和希望,感受到了更多的关于生命的理解。从我与蒙古牧民结识的体验中,我深深感觉到:他们对于生命的理解,对生命的尊重都是极为独特的,极为宽厚和充满爱的。无论是对于一条老狗,一匹马驹,一只小鸟,一个弃儿或私生子,一个孤苦老人,一个异乡来客,都是这样。”第四章“喜庆”描写了蒙古草原上的娱乐庆典。在游艺祭典的盛会中,寄托和培养着一种蒙古民族的感情。第七章“血脉”描述游牧民族的家庭和家族形态,游牧世界存在着特点显著的家族、血缘、继承的概念和传统。家族与生产有着密切关系,是一种生产单位的自然结合。家族纽带被系在对游牧生产的巩固上。第三章“白色”描写奶季即夏季的牧民生活。夏季的牧业劳动虽然忙碌,但是,因为集体劳动,人们活动的核心却不在于劳动了,似乎交际的目的大于生产目的,游乐的气氛压倒了劳动的气氛。夏天最重要的任务是为冬天筹备查干·亦得——白色的食物。蒙古牧民对于白色的食物有着一种特殊的喜爱和尊重。从“查干”这个词,蒙古牧民发展了远远超出了颜色概念的思想感情。纯洁的白色是他们观念中的美的比喻物。牧民称心地好的人为“查干·色特格里太”,意即“有着白色的心的人”。
此书一个最鲜明的特点是书中大量引用蒙古语汇。语言成为深入理解蒙古游牧世界的线索。张承志通过语言的踪迹展开了蒙古草原独特的生活世界的内容。蒙古游牧世界独特的生产和生活方式形成了特殊的语言。反过来,语言又揭示蒙古草原游牧世界的秘密。第一章作者将汗乌拉称为“摇篮”。作者充满忧患意识地写道,自然气候条件、牲畜数目条件、劳动力和人口以及消费需要等条件都在要求汗乌拉草原出现一场变革,而这一变革也许将结束迷人的、古老的游牧传统。一切具有民族参考意义的社会、经济、生活状况及细节,也许已经要掀向它最后的一页了。
进入1990年代之后,张承志主要选择了散文这种文学形式。他说:“如今我对小说这形式已经几近放弃。……我更喜欢追求思想及其朴素的表达;喜欢摒弃迂回和编造,喜欢把发现和认识,论文和学术——都直接写入随心所欲的散文之中。”他在《岁末总结》中说,就思想的传达而言,散文高出小说。
张承志的散文反映了1990年代中国文坛的急剧瓦解和分裂。这个时代急剧的堕落提纯了张承志,同时张承志也必须付出极端、单调和疲惫的代价。朱苏进评论张承志的创作风格时说:“他的许多篇章既是猛药又是美文,在新奇意境和铿锵乐感中簇涌着采自大地的野草般思想。他的作品个性极度张扬,锋是锋,刃是刃,经常戳得人心灵不宁,痛字当头,快在其中。”(朱苏进《分享张承志》,《钟山》1994年第4期。)他意识到鲁迅以笔为旗的痛苦。他在《美则生,失美则死》中吐露:“当同时代的文学家写出一部部文学性的鸿篇巨制时,他不得不以一篇篇杂文为投枪匕首,进入战斗。其实,我是为鲁迅先生遗憾的,然则,那也是他的必然。”
他在1993年写的《以笔为旗》中对文学界及其所谓“纯文学”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张承志产生了一种自觉,走上了与中国文坛激烈对抗的道路。按照他在《离别西海固》中的叙述,早在1984年,他便与中国文学的主流分道扬镳,彻底决裂了:“在一九八四年冬日的西海固深处,我远远地离开了中国文人的团伙。他们在跳舞,我们在上坟。”他在《无援的思想》中表达了文化的堕落所带来的民族危机的忧虑,“山河突然逼近”。
1993年发表著名的《清洁的精神》,抗议“今天泛滥的不义、庸俗和无耻”,通过古代许由等人追求正义和清洁的故事,追寻“洁与耻尚没有沦灭的时代”。他不断地从历史中去寻找抵抗的力量。这种资源包括哲合忍耶教派、《史记·刺客列传》、鲁迅、屈原等等。他要寻找自己的“类”,自己的参照,自己的“血统”。鲁迅成为了他思想和反抗的重要资源,成为他反复书写和礼赞的对象。他在《清洁的精神》中这样勾画了鲁迅的形象:“所谓鲁迅,就是被腐朽的势力,尤其是被他即使死也‘一个都不想饶恕’的智识阶级、即中国知识分子的前一辈们逼得一步步完成自我,并濒临无助的绝境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他在《再致先生书》指出,“鲁迅象征着一种不签定和约的、与权力的不休止争斗。”他在《静夜功课》中说,“墨书者,我冥冥中信任的只有鲁迅。”他说他近日爱读的只有两部书,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和鲁迅的《野草》。对鲁迅的阅读和理解形成了张承志个人独一无二的“鲁迅研究”。他用最文学的方式接近鲁迅。这是心的考证,是用文学的巫术招魂。
理解张承志,有几个重要的词,比如美、正义、自由、人民,特别是在今天污名化了的“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这个被现代文明和意识形态污辱了的词,张承志通过他的反复书写的磨洗,重新恢复和焕发了原始正义的光辉和惊心动魄的美。他在《清洁的精神》中称赞司马迁的《史记·刺客列传》是“中国古代散文之最”,“美得魅人”。他称赞《史记·刺客列客》提炼了“中国的烈士精神”。他誓言“我要用我的篇章反复地为烈士传统招魂,为美的精神制造哪怕是微弱的回声”。他将荆轲刺秦的故事称为“古代中国勇敢行为和清洁精神的集大成”,是“弱者的正义和烈性的象征”,“一种失败者的最终抵抗形式”,“因此没有什么恐怖主义,只有无助的人绝望的战斗。”
在张承志看来,卢德运动比起“科学社会主义”,索菲亚比起“十月革命”,安重根比起朝鲜独立运动,秋瑾、徐锡麟比起武昌起义,荆轲、高渐离比起陈胜、吴广起义,是更美更壮丽的。恐怖主义是一种失败的政治,是一种纯粹伦理的美学的反抗。它具有一种浓烈无比的伦理的诗意和道德的美感。它是反抗的火种,革命的萌芽。比起组织化的革命来,它更具体、更直接、更壮烈、更鲜明、更强烈地直指人心、人性、人道,迸发出强烈的道德的诗意和美的光辉。张承志和张艺谋是艺术上的两个王者,当张艺谋对于主流意识形态和体制全面认同和臣服,越来越作为“中国形象”大红大紫地走向商业时代的中心舞台的时候,那个从“新时期”一起出发的张承志旗帜鲜明地走向了中国的边缘和底层,走向了没有历史的历史,走向了人民的文学。张承志在《心灵史·穷人宗教》中宣称:“我偏执地坚持,中国的一切都应该记着穷人,记着穷苦的人民。”
张承志的偏激和极端从根本上来说来自于红卫兵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无政府主义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乌托邦冲动,是对于令人窒息的现代性的激昂抗议,表现为极端的反体制精神。
他在《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中声称,他在《红卫兵时代》一书中充分肯定了红卫兵的造反含义和对特权阶级的敌对,为六十年代,为他自己所创造的红卫兵这个词,为红卫兵运动的青春和叛逆性质,为红卫兵的反体制形象,进行了坚决的赞颂。张承志在《心灵史》中指出,“人民造反”,“人民反叛的暴力”是统治者的“天罚的形式”(《心灵史·入海口》)。他宣称官“对于人道来说是最下贱的存在”(《心灵史·人民的暴力主义》),“哲合忍耶可以放弃暴力但决不放弃自己对于官府的异端感。永不近官,永不信官,这种心绪后来成了哲合忍耶的一种气质”(《心灵史·进兰州》)。张承志所强调的一直是“心灵自由”、“信仰自由”。张承志所追求的自由与1990年代流行的“消极自由”这类自由主义话语构成了一道不同的分水岭。张承志一直歌颂和赞扬具有恐怖主义倾向和强烈的道德乌托邦倾向的“密谋”和“暗杀”以及另一个极端——道德感化。他赞颂“牺牲之美”(《心灵史·入海口》),“牺牲是最美的事情”(《心灵史·董志塬》)。他描写华林山战斗,起义者绝处安营的行为甚至整个暴动都不像是军事行动,而是在“寻死”,是“为主道牺牲”(《心灵史·人民的暴力主义》)。尤其是石峰堡内的哲合忍耶回民他们等着官军在礼尔德节的时候来成全自己,“举意在尔德节圣洁的境界中飞向没有迫害欺侮的天堂”(《心灵史·书耻》)。
张承志在《南国探访》预言:
“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古怪的时代。”“豪富和赤贫,餍足和饥馑,脑满肠肥和瘦骨嶙峋,摩天楼和贫民窟——总之,一切对立和差别、正义和背义,都将在这个隆隆来临的时代并立共存。”他在《中原迷茫》中指出,我们需要面对着屈辱的历史,残暴的权势,苦难的人民,卑污的智识阶级。
随着中国越来越从“第三世界”中脱出,中国越来越“与世界接轨”,越来越融入到“世界主流文明”的秩序之中,所谓“新新中国”形成了自己的“底层”。张承志最受非议的是他对于红卫兵理想主义的执着。轰轰烈烈的“脱轨”的“漫长的二十世纪”在1979年匆匆结束了。张承志一直心仪于1960年代,这个反体制的极端年代,这个激情的年代、脱轨的年代。这构成了理解张承志的核心:造反,反特权,反体制,反对一切的压迫和不义。《心灵史》仍然属于这一精神脉络。张承志在《风雨读书声》的访谈中谈论《心灵史》的精神谱系的时候说:“我用这样的方式,表达了我对六十年代的忏悔与坚持,对体制和异化的大声抗议。”1960年代的红卫兵以及西方的造反运动都是与青春和叛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们的不会是红色也许是天蓝色的旗子上,我希望一开始就有人心、人道、对人的尊重;一开始就有底层、穷人、正义,一开始就有叛乱、选择、青春、反体制的底色。”(张承志《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无援的思想》第91页,北京华艺出版社,1995年)
张承志以一个人填写了巨大的空白。张承志的写作使人民、革命、底层、恐怖主义这些词语得到了磨洗和拯救,同时,也使自由、人道和美以及民间等概念的内涵得到了真正的确认。张承志背对着整个中国知识界,背对着中国这个“盛世”写作。在根本上来说,他面对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写作,面对着一种强横地灭绝任何差异性和抗议的世界秩序和霸权写作。他以具有广阔深厚的历史空间的大西北为根据地,以中国最广大的底层人民为依据,背对着灯火通明的城市繁华。
当有人指责张承志是“反智主义”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作为一个优秀的学者和作家,张承志不过只是拒绝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流行的知识,他不过是在组织另一种秘密知识,发掘地下的历史;同时,也在指示另一种人性,构建另一种社会理想。他在呼唤美的人性、人心、人道和真正的和谐、和平。正如《心灵史》中船厂太爷马达天的话:“你已经有了知识了。——你千万不要把你的知识的光芒熄灭,而使你自己坠回黑暗!”
张承志始终是一个极端的浪漫主义并且带有唯美主义倾向的作家,在外国作家中他反复提到梅里美和三岛由纪夫。当资本主义以贸易将地球变成世界,将整个世界都纳入到自私自利的交换和简化为交换价值的时候,浪漫主义最早树起了反抗现代文明的叛帜。它以文学的武器,以审美的割据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对交换价值、对商业文明进行绝望的反抗。这种绝望的反抗产生了“纯文学”,以至“唯美主义”。当资本主义对交换价值进行神化的时候,唯美主义对审美进行神化,当资本主义对商品进行神化的时候,它对艺术进行神化。它以艺术审美的王国反抗商业的王国。当资本主义进行全球征服的时候,浪漫主义起义和独立,在自己的艺术王国上空高高地飘扬起美的旗帜。浪漫主义是欧洲反工业化、反世俗化、反现代性的第一声预言,而张承志是中国浪漫主义一个悲壮的奇迹。
诗的激情和倾泻是张承志创作的最根本特点。他在《骑上激流之声》中说:“文学的最高境界是诗。无论小说、散文、随笔、剧本,只要达到诗的境界就是上品。”他在《三份没有印在书上的序言》中说:“我热爱倾诉。我狂热地喜欢一种能与行动匹敌的语言。”他在《美文的沙漠》中说:“也许一篇小说应该是这样的:句子和段落构成了多层多角的空间,在支架上和空白间潜隐着作者的感受和认识,勇敢和回避,呐喊和难言,旗帜般的象征,心血斑斑的披沥,它精致、宏大、机警的安排和失控的倾诉堆于一纸,在深刻和真情的支柱下跳动着一个活着的魂。”
张承志的小说被称为抒情小说。他的小说近于散文,也近于诗,往往以心理的流程代替客观的叙事,具有明显的心灵独自和激情倾诉的特点。后来,他直接采用更自由的散文的形式来抒发和倾吐激烈的内心世界。他的散文是一种心灵的独白,像凡高的绘画具有一种强烈地燃烧的辉煌壮丽的主观色调,释放出纵横驰骋、激烈狂热的内心世界。张承志把小说的形式看作是“桎梏”。
小说是一种随着现代资产阶级而兴起的艺术形式,是一种最为世俗的艺术形式。张承志放弃小说创作而转向散文写作与1930年代鲁迅文学创作所发生的变化有着明显的类似之处。对虚构的放弃反映了张承志内心的峻急、紧张和焦虑。我对张承志放弃创作和虚构感到忧虑和惋惜,同时,张承志放弃创作也使我们进一步去思考什么是文学等有关问题。
雪莱曾经认为,诗人是立法者。诗人是民族和时代的先知和预言者。张承志希望像摩西一样,向人们昭示另一个生存世界和另一种生存秩序。不论是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来说,张承志的写作都是一场彻底的绝处逢生的叛乱和起义。他在《为〈神示的诗篇〉而作》中写道:“完全是和平的攻战,完全是独自一人的义举”。他不断地转移自己描写的对象,不断地变化表现的内容,不断更新表达的形式。他以文学的方式向这个世界和时代挑战,呈现了另一种不同的价值和意义。
收稿日期:2012-04-20
标签:张承志论文; 蒙古文化论文; 文学论文; 鲁迅论文; 小说论文; 读书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清洁的精神论文; 北方的河论文; 金牧场论文; 黑骏马论文; 哲合忍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