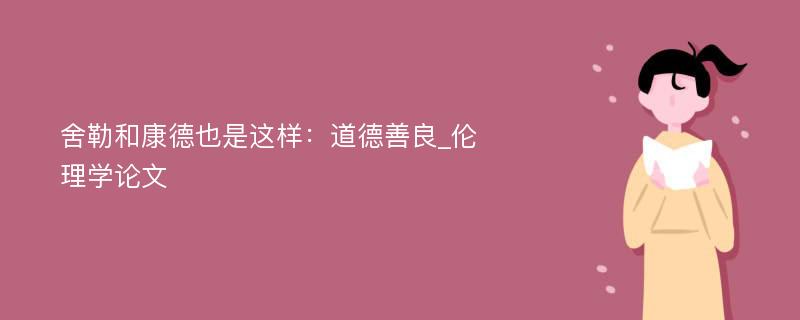
舍勒与康德,殊途同归:道德的善,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康德论文,殊途同归论文,道德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60(2009)04-0075-07
纪念M.S.Frings(1925-2008)
以下是对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1788)和马克斯·舍勒的《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1913/16,下文简作《形式主义》)二者之间一些基本差异的阐述,但在一篇文章的框架之内不可能详细阐述现象学分析和十八世纪的理性思考。实际上,如果有人要对这两部伦理学巨著进行详细比较的话,那将需要一卷的篇幅来公正地评判每一本书,并在整体上得出没有偏见的并且至少是近乎客观的结果。
在两位哲学家之间的比较总有某些不足之处。基本上,在这种比较中存在着四个人:被比较的两位哲学家、比较的作者和读者。这种情况往往使看上去已经很难的主题更加混乱,有时留给读者的是对这一个或另一个哲学家的“选择”。
我并不认为比较与哲学有很大的关系,尽管它们对理解某一思想家、对一个哲学“学派”或对于理解对相关哲学家做出比较的那个时代有所贡献。我也不认为哲学领域中的学派、特殊利益群体与哲学有很大关系,除非所涉及的基本思考被指向或来自存在意义问题。
康德的形式主义伦理学和马克斯·舍勒的质料的伦理学之间的“比较”会引起另外的困难。康德与胡塞尔、舍勒和海德格尔所导向的传统现象学相距一个多世纪。让康德面对现代现象学的裁判是不公平的,尽管康德以其资格很可能经受得住考验。同样地,反之也是不公平的,即因为其缺乏律令而指责舍勒的伦理学。
因此,我打算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处理康德和舍勒的伦理学:我不想以论证的规模来比较二者,而是想集中在一个不仅对他们二人是共同的、而且在任何伦理学中都是共同的关键点上,无论这一点是否已经被清楚表明:人的本质。因为必须坚持的是无论我们如何说明“善”与“恶”的存在,它们的载体都是人格。
但是,当我们考虑到自苏格拉底以来的道德意识的历史时,这一点也必须在一个有限的意义上被理解。因为有两种类型的伦理学在这一历史中产生并对人格的道德评价有直接的影响。(1)他律伦理学声称,道德的善被锚定(anchored)在人之外的某物上,并且人(在人类[der Mensch]这个意义上,且与性别无关)被置于依赖于这种外在权威的位置上。佐证之一是“神学”伦理学,在这种伦理学里道德的善不能与创造万物的上帝相分离;另一个例子就在马克思主义的和法西斯主义的社会主义之中。因为道德上善的行为是那些被限定于一个“阶级”并且仅仅“为了”那个阶级的行为,在无数情况下——甚至包括为了阶级利益的不道德行为——这些行为常常被这个阶级的理论家和领袖们证明是正当的。(2)相反,自律的伦理学声称,正是个人自身而不是个人以外的权威建立了道德的善。必须强调的是,无论康德和舍勒的观点有多不同,在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道德自律在人的意愿(康德)或人的爱的秩序(ordo amoris,舍勒)中都可以见到。
无论在康德和舍勒之间可以发现何种差异,他们都属于自律伦理学。第一个差异是关于道德行动(action)、行为举止(deed)和行为(act)的实践。当我们问及道德经验的本质时,这个问题就产生了。事实上,我们经验过善与恶吗?这个问题的答案又一次依赖于我们在伦理学史中所发现的若干立场:(1)有人提出道德的善处于理性、奴斯(苏格拉底)或心智之中; (2)有人提出道德的善处于意愿之中(康德);(3)有人提出道德的善处于人的内心之中(舍勒)。结果每一种情况中的道德经验都不同。例如,在第一种情况中,道德的善是通过“明察”被经验的;在第二种情况中,它通过意愿的意向被经验;在第三种情况中,它通过人格的内在的趋向被经验。我们还可以看到,在第一和第二种情况中,道德经验允许公式化律令的功能的决定性作用,而在第三种情况中则不是如此。因为我的内在道德趋向是既不能被命令——更不要说加以明确阐述和定义了,也不能“遵守”的。他律伦理学和自律伦理学之间以及道德的善在理性、意愿或内心中的定位之间的历史差异本该在对康德和舍勒的长期研究中加以思考。
由于本文篇幅的限制,我们将集中在舍勒伦理学中的人格的本质上,因为它使自身区别于康德的伦理学。因此,为了确定事实上舍勒关于人格的观点是什么,我将以《实践理性批判》(下简为《批判》——中译者)为前提。这将有助于我们根据康德的《批判》评价舍勒的立场,或者根据舍勒的现象学伦理学评价康德的《批判》。
“现象学伦理学”这个术语并不是舍勒的。这个词应当表明关于人格性本质的一些东西。康德和舍勒在人格概念上的一个基本差异是理性的作用。康德的理性观是,没有必要强调“理性”是永恒的、静止的和在历史上普遍的。对康德来说,理性被赋予一个不变的范畴装置,这意味着它对所有人、种族和文化在一切时代都是一样的。他暗含的主张是,实践理性也在一切世代拥有给予自身道德法则的能力。理性的这种能力在历史上既没有增长也没有减少。范畴功能和法则的稳定性——通过它混乱在纯粹理性中被综合地赋形(formed)——和实践理性中的意愿功能都意味着人格概念是“理性的”(Vernunftsperson)。理性人格处于人们以及群体之间所有文化的、宗教的、种族的和社会的差异背后。正是这个对历史上静止的、普遍的理性的假定引起了舍勒有时对康德的严厉批判。众所周知,舍勒有时通过引用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话来反驳康德的这个假定:“康德的范畴表只是一种欧洲式思维。”①也正是这个假定容许康德的律令的“范畴”本质作为照亮活生生的人格的整个道德舞台的中介。我们几乎找不到“范畴的”一词比在康德对它的使用中更有示范性的字面意义(categorial,kata=下去;agora=市场)。
康德如此表明了一个理性组织的庄严的稳定性(启蒙运动时代相当典型),而舍勒的理性概念正与此相反。对舍勒来说,理性实际上是历史地变化的。它并不限于一个静止的装置,而是与群体、文化、种族和人有关。理性并不是只有一个,而是有很多,多数理性与人的共同体化(communalizations)有关。实际上,通过在明察和经验之间的累积功能的理性的“成长”可以在《知识社会学》中被找到。②显而易见,对舍勒来说,不可能提出一个对所有人无论何时都有效的道德法则,相反,道德意识的命令受限于“时机的召唤”、时机(kairos)——人格正巧在这之中找到自身。我不想深入探究表面上在这里出现的伦理相对主义问题。在舍勒《形式主义》一书中,他很好的阐释了伦理相对主义的不可能性。我们的确想坚持的是,道德的善可以或者受限于“意愿”——因为善的意愿等价于道德的善业,或者受限于“内心”——因为道德的善在实现一个正价值的过程中,即在作为一种道德意识行为的“偏好”的过程(舍勒)中功能化自身。
首先让我们把“偏好”解释为与人格中道德的善的构成有关的行为。然后我们将能够看到,在现象学伦理学中,道德的善业不能与人格的行为—存在中的时间流相分离——这种联系在康德看来不会是重要的,因为时间对他来说是纯粹理性而不是实践理性的内感知的一种形式。
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价值“偏好”如何在缺乏道德律令的情况下解释道德的善?或者,用现象学术语来说:与其时间性的意向相关项(价值)相关的偏好的意向行为在缺乏由理性行为构成的道德律令的情况下如何解释作为时间意识流中一个组成部分的道德的善?
我们在《形式主义》一书中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概括起来说是这样的:道德意识没有推论出道德的善,意愿也不是道德善的最初来源。实际上,道德的善既不是理性行为或意愿的意向相关项,它自身也不是一个“客体”。正如我们在后面会看到的那样,道德的善发生在人格的行为—存在之中并贯穿于其中,而在这个行为—存在之中“偏好价值”行为发挥着核心作用。“偏好”既与价值领域相关,也与事物、善业和实践经验中价值的实际表现相关。经验中显示出的价值(如事物价值和善业价值)之间的关系必须与价值本身之间(即区域间的)的关系区分开来。
关于这一点,舍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价值所具有的与感知本身之间的类比。就像“看”这个行为和颜色相关, “听”这个行为和声音相关一样,感受中偏好这个行为和价值相关。颜色、声音和价值不能彼此互换,不能与它们各自的行为相分离。我不能听到颜色,也不能看到声音。我们可以超出舍勒的这个类比并补充说:我根据我没有看到的“光谱”颜色看到了在经验中显示出的颜色。这是一个特殊的光谱颜色秩序,它以从暗到亮的等级揭示可见的颜色。在这个意义上,价值领域也是“光谱的”:除了在它们在事物、善业和行动中的自身显示中以外,它们在实践经验中不能单独实存。光谱的价值领域可以说反映出爱的秩序——在它在价值领域的先天秩序中真正爱的和偏好的那些领域中——的光谱棱镜。例如,毫无疑问,加之于我的不正当这个负面价值在“人格的”感受中被感受到,而身体的不舒适这个负面价值在躯体中的感性和触觉感受中被感受到。这两种情况中的负面价值属于价值的不同“领域”。就像颜色对于看一样,价值与偏好感受的特定层面紧密相联。人格感受在其本质上已经和感性感受有着迥然之别了。
让我们回顾一下那些“客观的”价值领域(用舍勒的话说就是“样式”),即“爱的秩序”中先天的价值领域,它们排列如下:
(1)神圣的价值领域,
(2)精神价值的价值领域:
(a)审美价值,
(b)对与错或正当与不正当的价值,
(c)认知和知识的价值,
(3)生命价值的价值领域,
(4)有用性的价值领域,
(5)感性的适意性的价值领域。
(上面的等级也包括了相应的相反的和负面的价值。)
在我们详细评论偏好行为之前,必须得出关于以上价值领域的另一个意见。因为“善”与“恶”都不属于其中。其原因在于只有人格才是它们的承担者,而以上领域中的所有价值都可以由其它实体所具有。例如,从“适意到不适意”或从舒适到不舒适的最低领域包括了我们和动物共有的“感性的”躯体价值。“有用性”这个价值领域也是我们和动物共有的(如,筑巢),并且在事物中发生;生命价值这个价值领域的跨度包括了整个自然;精神价值的价值领域也适合于物质——例如油画中的颜料,适合于财产的分配或适合于作为认知对象的实体本身;神圣的价值领域也可以在被相信是神圣的善业和事物如太阳、月亮或神圣物中显示自身。
但唯独只有“善”与“恶”发生在人的行为的实行中;上帝不可能是善的和恶的,魔鬼也不可能是恶和善的。只有人是两者都有可能的。看起来人似乎处于道德世界中的那两极“之间”。在这个意义上,人格是在道德可能态之间的“运动”。舍勒在后期把这种运动称为“爱”(作为“恨”的基础,即,在价值领域及其显示出的价值中的错误偏好)。人的存在是“爱的存在”(ens amans),即,无论他会怎么偏离“有秩序的内心”,他的内心都注定首先是“爱”更高的价值。
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来谈偏好行为了。不时有人质疑:“偏好”某一个价值领域胜过另一个究竟是否能在道德善的构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一种反对的观点常常且直到最近还宣称,舍勒低估了意愿。③舍勒并没有低估意愿。在他《形式主义》一书中恰恰是意愿构成了“整个”人格。所谓的对意愿的低估开始出现时,舍勒对价值的“被给予性”的研究还没有被充分注意到,也就是他的论文《爱的秩序》还没有被看作是他的长篇巨著《形式主义》一书的核心。④他研究的总的结果表明,在奠基秩序中,所有意识行为都预设了或“经历了”认之为有价值(Wertnehmung)的行为,或者是我所称之为的“价值—感”;“价值—感”先于“感知”,作为一种认之为有价值的行为的偏好行为必须严格区分于“选择”以及日常谈话中“偏好”这个动词的通常意义和对它的使用。有趣的是我们要指出一点,尽管胡塞尔在《形式主义》时期或者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建立了他自己的价值理论(定位于布伦塔诺的价值理论),但他在读了这本书以后根本没有就此对舍勒进行批判。胡塞尔选择了运用算术句法对价值之间的关系进行算术的澄清。胡塞尔和舍勒在那些年里的通信表明,胡塞尔更希望在1913年的《年鉴》中出版舍勒的《形式主义》。⑤
假定偏好行为就是胡塞尔所谓的“突出的意向性”,我们可以试着说明价值之中的偏好与道德的善(及恶)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价值领域的“高度”以及在经验中显示出的其价值的“高度”处于偏好行为“之中”。这一高度在偏好行为中揭示了其“自身”。也就是说偏好的情感行为并不在价值中进行“选择”。选择某物意味着至少有两个供选择的项。但是,在偏好行为中,两个项并不是其发生的条件。偏好行为揭示了一个价值在行为本身“内”的“定位”以及高度,就像在前面提到的不正当和不适意中的那样。价值的高度在“偏好”中被“感受”到。
让我们提供一些例子,尽管当前读者对它们的理解行为会修正相关事态。在我的日常生活中我发现自己不断地与我周围有用的事物打交道,也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器具”,我周围的以及手边的“东西”。某一事物的实用性,比如我厨房里的一只杯子,在我伸手去拿它并把它拿在手里时就在对它的偏好“中”揭示了它的有用性价值(海德格尔在这之中只看到了杯子的实用特性,而没有看到在它实用目的中所包含的有用性价值)。或者,我可能会一直忙于整理我的屋子,忽然发现自己在给我的植物浇水。在这一刻且在这一刻“之中”,植物的生命价值显然比“有用性”更受偏好。在这种偏好中并不涉及慎重的选择。植物的价值使自己与器具相“分离”。它在它的亲切性(amiability)这一清楚的定位中揭示了“自己”是某个“有生命的”东西。价值定位在“认之为有价值”中揭示自身,就像认之为有价值本身揭示这一定位一样。当然这些例子都来自于外感知。而在内感知,尤其在道德经验中更加是这样。例如,人类很能够在他们良心的适当定位中感受到罪的“痛苦”。在这些情况中,是我们“应当”做但没能做的事,以及“应当”成为但没能成为的那样处在对这种应当的偏好“之中”,即使这种应当没有被意识到。的确,“应当”的经验以及我没有成为的和没能做的经验为痛苦的定位打好了全部基础。“偏好”为之痛苦的负面价值的定位正是在对应当的偏好“之中”被“找到”的。因此,在偏好行为“中”必须有一个秩序,它反映价值和负面价值内容的等级和区域,它是先天的贯穿于这些内容中并在其中的。无论多么困难,一个理性的、形式主义的先天都要在欠缺考虑和理性行为时指出对应当的偏好和对恶的痛苦的真正“开端”,坦率地说这是题外话。当对恶的痛苦出现时,它们已经被价值—感的情感开端所支配。关于这种情况的另一个例子可以在“一见钟情”中看到。这当中并没有与其他人格的“比较”。因为正是偏好行为发生的开端,被爱者的价值向我揭示“自身”。舍勒认为,爱不是盲目的,而是在它们的定位中揭示并打开了价值领域,爱“唤醒”了所有知识和意愿。
既然偏好行为、价值—感行为揭示了价值领域的定位以及它们在实际经历中显示出的价值,那么还缺乏形式的逻辑法则,它使至少两个项彼此相关成为必要。逻辑理解需要一个模型和形式主义来指出在逻辑意义上一个价值的定位。逻辑中的“思考”行为也需要有效的定义和固定,就像在算术中一样。无论价值何时被“思考”,它们都可以被操纵、纠正或调整,就好像经济上的商品和股票一样。但是,道德世界并不必然遵守形式逻辑,有时道德价值如此深奥地表现自己以致寻找它们发生的“理由”只是徒劳。一个人有时发现自己处在深刻的悲剧式的情境中就是这种情况,——戏剧中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当两种正面价值发生冲突,英雄——他是善的——死去,以及我们的悲伤被命运的无法说明吞没时。“心的逻辑”与理性、判断和推论的逻辑完全不同。帕斯卡:心有其理(le Coeur a ses raisons)。
在这一点上关于价值欺罔必须做一个评论。显而易见,偏好行为容易受欺罔。毕竟,我怎么“知道”我的偏好在任何时刻都揭示了价值领域之内正确的价值定位呢?舍勒非常专注于这个问题;实际上,他的论文《爱的秩序》还未完成,它接下来将是对价值欺罔——即“无序的内心”——的研究。但我们的确看到他关于怨恨的论文,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某种时间性欺罔的例子。⑥在那里,其观点是无论人格何时出现身体的、精神的、社会的和心智上的弱点,价值欺罔就会发生。它们存在于情感的减损之中,存在于偏好中(正确的)价值“降低”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存在于一个较低价值的情感的注入被降低的价值高度中。在妒忌、怨恨、恶意、敌意或嫉妒这些弱点面前,情况就是如此。在现象学上,这些情况相当有趣,应当在任何对“关于……的意识”的分析中考虑到它们。它们反映了通过弱点被破坏的偏好被引向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价值:一个“被憎恨”,因为它在有弱点的情况下不能被实现,另一个(错误地)被偏好和珍爱。在这种情况中,怨恨—人格往往会轻视或嘲讽真正的价值(“这真的值得去努力吗”),甚至可能会充满怨恨地对它进行诽谤。肯定价值的正确揭示可以说被弱点中可获得的较低价值——它然后表现为肯定价值——叠加于其上。在胡塞尔的术语中,这将意味着意向行为(偏好行为)能够具有两个价值—意向相关项,它们被包含在为激情所损害⑦的价值视域中。然而,使用胡塞尔的术语学并没有益处。舍勒很少使用它。我相信,在相关情况中更好的是谈“矢量(vectors)”而不是“意向行为”。偏好行为(“意向行为的”方面)是不能被从“为价值所吸引”中分离的。但是,在价值欺罔中,偏好行为却与它正确的价值目标分离了,因为情感意识流太“弱”以致不能实现肯定价值。偏好行为屈服于并转向更易获得和实现的价值。的确,被瞄准的偏好行为的正确价值与实际上背离这个方向而朝向一个可实现的较低价值这二者之间的这种矢量的张力是怨恨人格中“令人痛苦的矛盾”。这是由于被憎恨的肯定价值仍是所涉及的恨的整个情感构成的一部分。因此舍勒可以说:“怨恨总是具有真正的、客观的价值在错觉价值背后的这种‘明晰的’存在的特征——通过那种模糊的意识,即人生活在无法看透的虚假世界中。”我不想深入探究他的论文中所举的例子。我只想提一点,舍勒非常反对尼采的论点——基督教是这一怨恨—价值—欺罔最鼎盛期,因为它涉嫌把贫穷、遭殃、受苦等否定价值提升到美德领域中,而把肯定的生命价值放到恶行领域中。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看价值和时间之间的关系了。我们认为,道德的善不是一个“对象”,而是一个我们只在人格中发现的现象。这意味着道德的善本身必须作为“行为—存在”属于人格的本质。人格存在于像思考、意愿、感受、爱、恨、记忆、期望、原谅、感谢、遵守、命令等这些施行行为中。那些类型的行为对所有人类来说都是一样的,但它们的施行有个体上的差别。例如,没有两个人会以同样的方式“思考”。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如何”实行行为的风格和方式。正是这个实行行为的“如何”说明了每个人的个体性、唯一性和不可复制性。它被称作为人格行为的“质性方向”。因此,道德行为的施行服从于这种人格的质性方向,从而道德世界内价值的实现在人格之间以及群体之间是无限可变的,而价值领域仍然具有稳定的可偏好的秩序。从属于质性方向的不仅是在实际经验中显示出的以及在那些领域“之外”显示出的价值,还有那些在质性方向上被感受的“稳定的”领域。人格可能比“圣人”更“英勇”,可能比艺术家更“讲究生活”。这使舍勒建立了一个“理想的”人格类型——它们作为真实生存的人格的“模型”——来代表每一个领域。因此,道德的善也与这些领域理想的人格榜样紧密相连,这些榜样将人格的行为“吸引”到特殊的质性领域方向上。不管怎么说,舍勒主张,尽管道德行为有无限可变的施行,在理想上,所有事物、善业和行动在价值范围内都有一个唯一的定位,并恰好有一个有细微差别的心的运动与之对应。只要我们“符合”那些定位,只要心是它们的相应物,那么朝向最高价值的方向就存在于偏好行为之中,而我们的爱就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假如所有亲切性的定位在激情的影响下发生改变,那么价值领域的秩序就被颠覆,而爱就是“无序的”。舍勒以此把自己和康德区分开来:我们的情感世界不是一个要由非人格的律令和“理性”法则加以有序化的一片混乱。更确切地说,它还是“有序的”。人的本质不是“理性的”,而是“爱的存在”(ens amans),一个在爱之中并通过爱被指向肯定价值的爱的存—在(be-ing)。
先于意愿、原谅、遵守、承诺等这些道德行为的偏好行为的本质是一种爱的行为:可以说是通过偏好而对更高价值标尺(rods)的爱。这意味着,道德的善自身通过这种行为并在这种行为之中“生成”。它“骑在”爱的偏好行为以及包括意愿在内的所有其它道德行为的“背上”而“生成”。道德的善只在人格行为中“发生”:在别的任何地方都不可能发现它。它似乎是对价值领域的价值的偏好以及对按其顺序排列的价值领域本身的偏好的道德回音。
因此,道德的善的这种“生成”(相反地,恶的生成)必须具有时间特征。“生成”的这一时间特征必须具有和人格本身相同的特征——如果道德的善是人格独有的性质。
人格的时间特征不可能是“客观的”时间,即一个人格在其中行动的时间的特征。比如说,这种时间就是日历时间,是人们可以在其中计划、约会或重新安排会议等等的空的时间。在这种时间中,所采取的行动以及所有内容都可以放在其中,即客观时间段和内容是可分的。与此相反,有一种“生成”时间,在这之中内容和阶段是一致的。这种时间是一切自身激发(self-activation)的形式。例如,它可以在所有的“涌现”现象中被发现。在意识主动转向“已经生成”的饥饿之前,饥饿感就在我之中涌现了。在这种涌现中开端和生成都是不可预测的。它只是现在或以后能够得到满足的出现了的真实的饥饿。同样地,“我突然想到”一个明察,在我“像”这样把握它之前。明察具有已经被“接受”的特征。⑧甚至出生之前或此后不久的意识本身也正变成自我时间化并变成一个具有所有内容的“意识”。所有生物过程也都具有生成的形式,因此这一“时间”通常似乎根植于生命中心。在这个意义上,自我激发的形式是一种“生物的先天”,通常意义上的“时间”一词甚至都不适用于它。在后来的著作中,只要有作为“生成本身”内在形式的“时间”以及当内容和阶段一致时,舍勒都使用“绝对”时间这个词。在这个意义上,整个的人格行为—存在是绝对时间。人格不是客观时间中的“对象”,毋宁说,人格是在其通过行为(包括道德行为在内)并在行为中持续的生成中的绝对时间化。
由此,道德的善必须具有绝对时间的特征,就像所有行为的产生及其开端都具有这种性质一样。
结论与展望
从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自古以来被称作道德的善的内容依赖于对人的本质的评价。
我们只是对舍勒早期的作品进行了讨论,其手稿的时间跨度大致是从1910年到1913年。在那些作品以及他所有后期的作品中,人格是“精神” (这个术语中包括爱、感受、意愿、心智、意识、理性)的形式。只有某物的本质是人格的,我们才知道它有精神本质。若没有“人格”形式,那纯粹的精神、纯粹的意识、纯粹的理性对他来说都只是不可能的假设。
那么,如果人格被当作为精神本质的理性的载体,那么道德的善就不能与理性律令分离,当纯粹理性和实践理性被看作高于人格性时就更是如此(康德)。既然这样,人作为所有精神行为的统一整体就无条件服从于理性的道德法则,服从于责任和义务。
如果人格被看作为精神本质的爱的载体,作为有序的价值领域的载体——用舍勒的话说,它“拥有”人格,那么人格就不服从于道德法则,而是在通过爱而对价值的偏好(包括法则的价值和应当的价值)中的道德的善的施行者。
得出这个结论我们就接近了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在缺乏人格性的情况下,实践理性本身的律令的自身决定对所有时代的一切人而言都是道德的善的所在地吗?或者:善是由于每一个独特个体人格而以无限可变的方式和表现在其绝对时间化中的一个道德生成吗?
伦理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元—伦理学——在这儿面对着两个进一步的问题:有“一个”道德的善吗——自苏格拉底以来就是如此假设的——或者一个道德的善的统一是许多道德的善的理性本质吗?这个问题属于“一”和“多”的古老疑问。这就是在问:“这”所谓的道德的善只在人格的价值偏好行为和实践经验之间以生成的形式存在于功能的大多数中吗?在后一种情况中,为与具有独特的偏好价值之质性方向的人格一样多的可实现的道德的善留有余地。在这种情况中,“这”道德的善或法则或律令失去了它在日常生活的实践行动中的抽象特征:生活的世界。我并不乐意认为在偶发性地做好事的行为中有“这”道德的善或绝对律令的格言。这也将解释在生活的世界中常被忽略的事实,人格的无数善的行为,另外还有永远没有人知道从而非历史的行为,在道德世界中有着它们的位置,也就是那些没有特定的伦理学知识而进行的善的行为。
根据这一观点,道德的善的实存存在于多数个体的偏好价值的行为中。依此看来,人格的本质在于人格在每一时刻都作为爱的存在——即,作为“尚未”的实存——在通往道德的善的“途中”⑨,因为最高价值神圣必须通过无限之径来实现。
如果人格本身“生成”实存,那么无论怎么表达人格都不可能达到并实现“这”道德的善。因为“这”道德的善的完全实现就是它的毁灭。
道德的善的这种多元论观点将深深的影响上帝这个概念。如果上帝是人格,那么在经验中被给予我们的人格的本质也必须在宗教行为中适用于上帝。如果人格在本质上是绝对生成,而非一个事物—对象,那么一个完全的、完美的人格就上帝来说也是不可能的。
这种严峻的可能性是舍勒1922年以后所有手稿的核心之一:一个人在绝对时间中生成世界、上帝、人和历史的问题。直到1928年舍勒在54年的悲剧生活之后心碎辞世,他一直专注“人的永恒”这个问题。
注释:
①舍勒:《知识社会学问题》,M·S·弗林斯英译,斯蒂克斯(K.W.Stikkers)导论,劳特利奇和吉冈保尔出版社,1980年,第75页。德文版:《舍勒全集》,第八卷,伯尔尼和慕尼黑,1980年,第62页。
②同上,英文版,39页及以后各页;德文版,24及以后各页。
③罗马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在他近期关于舍勒的文章中坚持这一观点,而且他还认为,舍勒的伦理学和基督教的伦理学是不一致的。关于这些观点的评述,请参见我在他的《精神的优先性》(Primat des Geistes,斯瓦特出版社,斯图加特,1980年)这本书的“导论”(第19-33页) 中关于他的哲学作品的介绍。
④见舍勒:“爱的秩序”,D·拉赫特曼(D.Lachtermann)英译,收录在《舍勒哲学文选》,西北大学出版社,1973年;德文版:舍勒:《伦理学与认识论》,《全集》,第十卷,伯尔尼和慕尼黑,1957年,第345页及以后各页。
⑤参见舍勒在《形式主义》中对布伦塔诺价值理论的评论。英文版,M·S·弗林斯和R·L·方克(R.L.Funk)英译,西北大学出版社,1973年,第87页注释57;德文版,《舍勒全集》,第二卷,伯尔尼和慕尼黑,1980年,第104页注释3。这一评论也适用于胡塞尔。见A·罗斯(Alois Roth)的《埃德蒙德·胡塞尔的伦理学研究,海牙,1960年(现象学丛书,第7卷)。
⑥舍勒,《怨恨》,W·W·赫德海姆(W.W.Holdheim)译,纽约,1972年;德文版,舍勒:《价值的颠覆》,《舍勒全集》,第三卷,伯尔尼与慕尼黑,1954年,第33页及以后各页。
⑦此处原文为“poisened”,疑为“poisoned”之误。——译者注。
⑧参见舍勒,《形式主义》,英文版,第189页注释22;德文版,第197页注释2。
⑨我已经在《人格与此在:价值存在的存在论问题》(海牙,1969年,现象学丛书,第32卷) 中在舍勒的《形式主义》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的基础上探究了价值—存在和人格的存在论地位的可能性。此在的“尚无”特征和价值—人格中的是一样的。
标签:伦理学论文; 理性选择理论论文; 康德论文; 舍勒论文; 道德论文; 价值定位论文; 本质主义论文; 文化论文; 胡塞尔论文; 哲学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