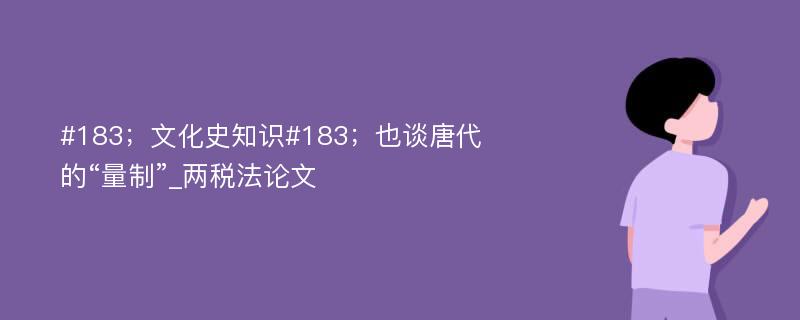
#183;文化史知识#183; 也谈唐代的“量出制入”,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文化史论文,唐代论文,也谈论文,知识论文,量出制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中国文化史上,“量出以制入”这一财政短语是由唐朝人首先概括出来的。所以,唐人首次揭橥的“量出制入”的财政内涵究竟是什么?其实践又是怎么一回事?颇受当今不少学者瞩目。《文史知识》1996年第1期发表《唐代的“量出制入”》一文, 作者们对这一命题再次作了基本肯定的评价,即是一个证明。不过,迄今论者在论述唐代的“量出制入”时着眼点是有不同的,多数把它和两税法改革联系在一起,看作是指导两税法改革的一项原则:视之为唐朝后期奉行的财政原则者则不多。这表明要在唐代的“量出制入”问题的学术探讨中取得比较接近的意见,首先应该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一番循名责实的考察,以免发生一些不必要的误解。下面从三个方面略陈管见。
第一,从实践来看,“量出制入”不是唐代的独创。
如所周知,一般地说,“量入制出”和“量出制入”本来指的是安排财政收支计划的两个不同原则。前者意为政府在安排预算时应根据收入的可能来制约支出;后者反之,意为根据支出的实际需求来决定征取多少财政收入。“量入制出”也叫“量入以为出”,此语早在先秦时期就见诸《礼记·王制》篇中。“量出以制入”一语则是迟至唐代中期才由杨炎首次明确提出。在实践中,“量入制出”是被称为“先王之制”的传统财政原则,似乎一直被中国古代封建政府奉为理财的圭臬。然而,事实上“量出制入”也是很早就被付诸实践的财政原则,在多数的场合表现为每当一定的岁入不能满足支出需求时,封建政府就强制性地扩大税收项目或数量。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尤其是王朝末期反复出现的赋税苛重和官逼民反现象,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说是“量出制入”的恶果。正如下面要引述的唐人陆贽之语所表明的,在多数封建政治家眼中,“量出制入”不啻是竭泽而渔,它的实施是为满足统治集团穷奢极侈或穷兵黜武的贪欲所驱动,并非因社会生产力发展、财源扩大所致,所以常常引发社会动荡或危机。当然,历史上通过“量出制入”来控制支出规模从而缓和社会矛盾的个别事例也间或可见。例如,据司马迁《史记·平准书》所述,汉初,天下已平,高祖、孝惠、高后执政时期,“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这是用于安排“赋”这一类人头税的收支计划时的“量出制入”方法,是汉初惩秦朝“收太半之赋”之弊而改行“轻徭薄赋”的一项具体措施。我们不宜说它“并没有真正实施”。唐代杨炎建议确定两税征收总额时要“量出以为入”,也是旨在通过控制支出总数来减轻安史之乱后百姓的沉重赋税负担。总之,尽管词语出现的时间有先后,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量入制出”和“量出制入”都是中国古代政府实用的财政原则,由统治者视当时的政治、经济、财政等条件而加以选用。从这个角度看,“量出制入”不是唐代的独创。
第二,唐人所谓“量出制入”的财政内涵各有不同。
“量出制入”作为实践中早已存在的财政原则既非首创于唐代,为什么学术界又会特别看重唐代的“量出制入”问题呢?通常以为是因为第一次明确提出“量出制入”这一财政概念的是唐人杨炎,并且是和中国赋税史上的重大改革——两税法改革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还不够全面。就流传下来的史料而言,唐朝人说到“量出制入”的起码有3人,即杨炎、陆贽和元稹。不过, 他们所说的“量出制入”的财政内涵及其运用范围各有不同。
杨炎在大历十四年(779)八月的奏对中, 先向德宗“恳言其弊”,指出安史之乱后各级政府赋敛无度,“科敛之名凡数百,废者不削,重者不去,新旧仍积,不知其涯,百姓受命而供之,沥膏血,鬻亲爱,旬输月送无休息”。然后“请作两税法,以一其名”,并提出:“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入。”(《旧唐书·杨炎传》)可见他提出的“量出制入”原则是为了纠正中央政府对全国赋税征收已经失控的弊端,其运用范围在于确定全国两税(户税和田亩税)的征收总额。而在两税法改革前后,唐朝中央政府的财政收入还相当倚重于榷盐即盐的专卖收入。显然,杨炎的“量出制入”并不包括榷盐在内。可见他所说的“量出制入”只是一种制税原则,而不是处理财政收支全局平衡问题的财政原则。
陆贽于德宗贞元十年(794)上《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 第二条为《请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始行两税法时,政府计征百姓的两税钱的方法是:“定税之数,皆计缗钱;纳税之时,多配绫绢。”后来由于通货严重不足,出现货币升值、物价下跌的“钱重物轻”现象。陆贽指出:“初定两税之时,百姓纳税一匹,折钱三千二三百文,大率万钱,为绢三匹……近者百姓纳绢一匹,折钱一千六百文,大率万钱,为绢六匹。”当时税户的实际纳税负担已经增长了一倍。所以他建议“两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作为解除“折纳”给纳税户带来额外负担的预算方法。为反驳所谓两税纳钱可以利用钱贵物贱而增加收入以满足支出需求的论点,他说:“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数,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为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接着,他列举卫文公、汉文帝、唐太宗等的节用和秦始皇、汉武帝、隋炀帝的骄奢竭耗之例,从正反两面加以佐证,最后指出:“今人穷日甚,国用岁加,不时节量,其势必蹙。而议者但犹财利之不足,罔虑安危之不持。”(《陆宣公奏议集》卷一二)可见他说的“量入制出”和杨炎的不一样,指的不是两税法的制税原则,而是历史实践已经存在的指导财政全局的财政原则。
元稹于宪宗元和初年在《钱货议状》中说:“自国家置两税已来,天下之财,限为三品,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皆量出以为入,定额以给资。”(《元稹集》卷三四)他所说的“量出以为入”与“定额以给资”是同义反复,指的是唐中央确定两税留使、留州份额的方法,用今天的财政术语来说就是“以支定收”,处理的是中央与州、使两级地方财政预算的关系问题,与杨炎、陆贽所说都不一样。
至于杜佑则没有说过“量出制入”的话语,他在《通典·食货七·丁中》写道:“自建中初,天下编民百三十万,赖分命黜陟使重为案比,收入公税增倍而余,遂令赋有常规,人知定制,贪冒之吏莫得生奸,狡猾之民皆被其籍。诚适时之令典,拯弊之良图。”后一句话评论的是两税法改革,而不是“量出制入”。
第三,唐代后期实行“量出制入”的具体情况。
搞清唐人所谓“量出以为入”的不同财政内涵之后,就可以区别不同的范围来考察唐朝后期实行“量出制入”的具体情况。
首先,杨炎提出的“量出以制入”,作为初行两税法的一项制税原则,唐朝经变通后有所采纳。
前已指出,杨炎提出两税法要“量出以为入”,用意在于通过控制支出规模来减轻安史之乱后百姓的沉重赋税负担,并收回下移地方的部分财权。不过,按他的设想,“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民,量出以制入”,那是要事先对全国各级政府的财政支出作出严格的数量预算的。若依据唐朝前期的财政法规,这种设想要付诸实施本来是可能的。因为,从出土的吐鲁番文书《仪凤三年度支奏抄》来看,唐朝前期有一种“八月都帐”制度,要求各级军政部门在每年八月上旬把本部门下个年度的开支预算上报中央的度支司,作为编制全国支出预算计划的基础数字。但是,安史之乱以来,唐中央集权严重削弱,财政管理一团混乱,用杨炎的话说是:“纲目大坏,朝廷不能覆诸使,诸使不能覆诸州。”即财务审计制度严重破坏。用陆贽的话说是:“纪纲废弛,百事从权,至于率税少多,皆在牧守裁制。”即征权下移地方长吏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根本谈不上有认真地进行全国年度支出数量预算的可能。但是,唐德宗朝廷又急于利用推行两税法改革之机来纠正地方政府赋敛无度的状况,缓和社会矛盾,于是就采取变通的办法,在实施两税法的方案中规定确定各州两税征收总额时要“据旧征税数”,却未指明根据的是哪一年的“旧征税数”。结果,如陆贽所言,分赴各州的中央使者“乃搜摘郡邑,劾验簿书,每州各取大历(代宗年号,共有14年)中一年科率钱谷数最多者,便为两税定额”。尽管各州两税定额的来源多有不同,但是杨炎建议固定全国两税征收总额的目的毕竟还是实现了。所以,就预算程序而言,杨炎提出的两税法要“量出制入”这一建议并没有被付诸实施;但他提出“量出制入”以固定全国两税征收总额的意图却是实现了。
其次,陆贽所说“量出制入”财政原则在唐后期是否被推行,则要区分财政法令以及处理入不敷出的具体手段两个方面来回答。
从财政法令上看,唐朝后期没有实行“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唐后期的财政收入有两大部分,一是农业税即两税;二是商税,主要是食盐专卖。它们的税额或税率的变化情况,应该是判断唐后期是否从法令上实行“量出制入”的基本依据。
两税法实行后,从长期的情况来看,它有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实行定额管理体制,即各州两税征收总额是固定的,然后再把它分成上供、留州、留使三个固定的份额。这显然是与“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捍格不通的。唐中央之所以推行这种管理体制,主要是出于限制方镇财权的目的。不过,德宗曾二次下令增加两税钱的税率。它们是否可以看作唐朝明令实行“量出制入”的证据呢?这要具体分析。第一次是建中三年(782),距两税法改革不过二年。当时唐廷与叛藩争战激烈, 战费严重不足,“淮南道节度使陈少游请于当道两税钱每一千加税二百,度支因请诸道悉加之”。这次是由地方节度使提出动议,度支正为战费所窘,遂顺水推舟,下令在全国加税。尽管此次加税不是出于度支主动的“量出制入”,但从实际效果来看,把它说成是唐朝推行“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的一次表现似乎也不妨。另一次是贞元八年(792), “剑南西川观察使韦皋奏请加税什二以增给官吏,从之”(《唐会要》卷八三)。这只是个别地区的地方一级地方预算的加税,恐怕很难作为唐朝财政全局是实行“量出制入”原则的佐证。除此之外,似乎很难再找到唐朝中央政府明令增加两税的事例。所以,就两税法的长期运作情况而言,它没有实行“量出制入”的原则。
唐后期的盐利岁入有明显的波动性,多者一年700多万贯, 少者不上300万贯。这是由于专卖价格的高低、中央管理的松紧、 地方政府截留的多少、走私活动的繁减等因素综合影响所致,跟“量出制入”原则没有什么关系。
不过,从处理入不敷出的财政手段来看,唐后期中央财政也不断地寻求在两税外加征的各种办法,主要是开征诸如榷酒、税茶之类的商税和杂税;地方政府则更是在辖境内搞“法外加征”。所以唐后期人民的实际赋税是在不断加重的,终于爆发唐末农民大起义。因此,从财政调度的全局来看,唐后期政府实际上和历史上的其他一些王朝一样,是不时地运用“量出制入”的财政原则的。这样做无异于杀鸡取卵,其结果自然谈不上是“解放与发展了生产力,推动了唐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反而是摧残了生产力,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晚唐的统治危机。
最后,元稹所说的“量出以为入”,作为唐中央限制地方财权的“以支定收”的预算手段,的确是实行了的。正如元稹在《中书省议赋税及铸钱等状》指出的:“每年留州、留使钱额,本约一年用度支留。”(《元稹集》卷三六)
综上所述,唐人所谓的“量出制入”实际上有三种不同的财政内涵,运用的范围也各有不同,必须仔细加以区别。否则,笼统地来谈论“唐代的‘量出制入’”,就难免会在对其内涵、实施和影响等方面的申论中产生一些偏颇或误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