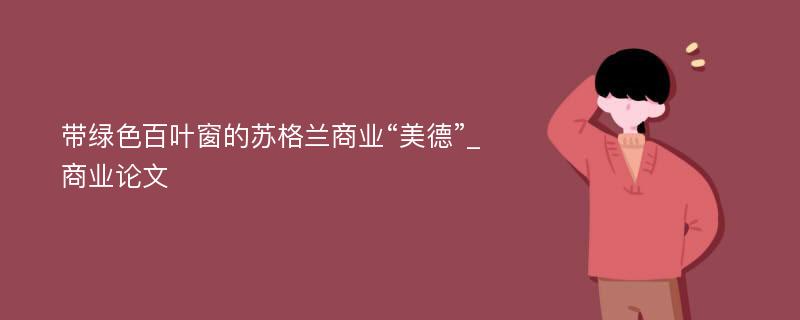
《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中的苏格兰商业“美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苏格兰论文,百叶窗论文,美德论文,房子论文,商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世纪90年代,正当苏格兰菜园派小说如日中天的时候,尚在牛津大学读书的乔治·道格拉斯·布朗(1869-1902)就对菜园派小说的苏格兰乡村书写表示了不满。他信誓旦旦地说:“我要写一部小说,告诉你们所有人苏格兰乡村生活是什么样子。”①1901年,也就是布朗辞世的前一年,这部名为《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的反菜园派扛鼎之作终于问世。布朗以堪与菜园派比肩的富有苏格兰地域风情的书写,展现了芭比小镇在铁路时代的沧桑巨变,“描述了另外一种农村生活”②。 何谓“另外一种农村生活”?要回答这个问题,还得先从菜园派小说中的乡村说起。诚如英国历史学家卡梅伦所言,菜园派展现的是“未受铁路、贫富两极分化和政治争端等现代性象征所侵袭的小镇和乡村苏格兰的、感伤的和性别化的意象”③。虽然铁路已堂而皇之地出现在麦克莱伦等人的菜园派小说中,但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古老的苏格兰乡村共同体依然稳固,顽强地抵制着商业及工业的侵袭。与麦克莱伦笔下神话般的德拉姆托奇蒂乡村不同,《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中的芭比小镇已阔步迈进铁路时代,铁路已经逐步成为人们生活的依托。顺势而为的“鼹鼠猎手”威尔逊从中发迹并登上行政长官的宝座,逆流而动的马车商人古尔雷不仅财富尽失,还赔上了全家的性命,他曾经引以为荣的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也沦为令人恐惧的空宅。古尔雷的悲剧固然有他自身的原因,用苏格兰商业“美德”标准考量,缺乏常识(即自控)是他致命的弱点。然而,与“小团伙”的风言风语相比,“美德”的缺失不过是小巫见大巫,“小团伙”的敌对才是古尔雷悲剧的催化剂,小说中“小团伙”的得势预示着作为苏格兰文化灵魂的乡村共同体的衰微。 一、马车商人的“美德”缺失 《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展现的是芭比小镇在铁路时代的沧桑巨变,而该巨变的标志是马车商人古尔雷的败落。在铁路尚未入侵之时,古尔雷垄断了全镇的运货生意,他的豪宅(即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是芭比小镇的靓丽风景线,让人心生敬畏。夏日清晨的芭比也宛如一幅菜园派笔下的静态画卷:“清新的空气,从红色的烟囱中冒出来的稀薄而遥远的烟,照耀在屋顶和两边山形墙上的阳光,黎明时分玫瑰色的清晰的万物——更重要的是,安宁和平静——使得芭比,一个通常没有什么可看的地方,在夏日的早晨成为非常宜人的、可供俯视的地方。”④作为商人,古尔雷无意欣赏美景,他驻足凝视是为了炫耀自己的生意兴隆。他特意安排马车商队同时出发,让浩浩荡荡的车队穿行在芭比的大街小巷,这种大胆的炫耀是他送给“他的敌人们的一记耳光”(House:3)。然而,事与愿违,马车商人的炫耀非但未能压倒商业敌手们的气焰,反而助推了他们奋发图强的“雄心”,炫耀的结果是古尔雷成了芭比商业世界的众矢之的与孤家寡人。 有趣的是,虽然古尔雷被冠以马车商人这个封号,但他财富的主要来源却并非马车生意。为了排挤竞争对手,他不惜以零利润为代价运送货物,直到对手无货可运,这种赔钱赚吆喝的生意之道不可能给他带来巨大财富。他的财富来源主要是泰姆普莱德缪尔租给他的采石场以及妻子的嫁妆。在芭比未受铁路侵袭的时候,泰姆普莱德缪尔出于朋友的义气和对古尔雷的敬畏,答应把采石场租给他12年。古尔雷凭借采石场发迹,还就地取材建造了他气派十足的豪宅。此外,古尔雷凭借自己非凡的男性气概,赢得了邻镇富人的欢心,把他并不喜欢的富家之女迎娶进门,获得了丰厚的嫁妆以及作为粮食经纪人的新生意。从商业经营的角度看,古尔雷赖以生财的采石场是一种借鸡下蛋的游戏,难以维系长久。铁路时代来临之际,泰姆普莱德缪尔在精明泼辣的妻子的唆使之下,决定不再续约,“摇钱树”物归原主,断了古尔雷的一方财路。与此同时,妻子带来的嫁妆未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升值,到铁路时代已经变得微不足道。 采石场被收回之后,古尔雷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马车商人。商业竞争是无情的,铁路发展也无法逆转。对于维多利亚时代的人而言,“一个更好和更快的铁路系统是一个更好和更快的不列颠的标志”⑤。1835年,连接伦敦和布里斯托尔的铁路开通。到了1850年,英国铁路运营里程已接近6000英里。铁路是社会进步的标志,但并非每个人都从进步中获益。殷企平教授将19世纪的英国铁路比喻成冷冰冰的“铁马”:“这种铁制的工具和它们所代表的‘进步’话语绝不会顾及人的身体与情感,更没有四条腿的马儿的那种忠诚。”⑥在无情的铁马来临之际,谁也挽救不了未能跟上“铁马”步伐的马车商人的厄运。作为马车商人,古尔雷运送的货物主要是乳酪和粮食,还有就是给建筑商吉布森运的建材。乳酪容易变质,是一种更适合铁路运送的商品。芭比进入铁路时代之后,威尔逊借助铁路运输开始抢夺乳酪生意,由于他出价更高,古尔雷很快在乳酪生意场败下阵来。粮食保质期较长,但盈利并不丰厚;更何况,古尔雷为了排挤对手不惜削足适履,经常干一些赔钱赚吆喝的傻事。 铁路时代让马车商人在商界风光尽失,但古尔雷的傲慢却丝毫未减。他试图东山再起,开始相信机遇,但“机遇总是背叛他”(House:236)。铁路的来临让他的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飞速升值,但他却一再错误地运用着铁路的便捷。为了挽救商业的败局,他冒险到城里把房产做了抵押;为了和威尔逊攀比,他在家庭资产已经捉襟见肘的情况下,把只对“傻傻的小说[低俗小说]有一种傻傻的兴趣”(House:64)的儿子送到爱丁堡大学去读书。不幸的是,在爱丁堡大学出人意料地获得某个校园文学奖之后,自小就不爱读书的小古尔雷便开始嗜酒如命,最终被校方开除。儿子被开除之际,恰逢古尔雷房产抵押已经透支、向朋友借钱频遭婉拒之时,他奚落了儿子几句,竟为此招来杀身之祸。随后,儿子、妻子和女儿相继服毒自尽。在服毒之前,他们从来自格拉斯哥律师的信件中得知,房产抵押已经透支,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即将不为他们所有。 布朗在小说第11章的开头浓墨重彩地推出了铁路时代的苏格兰商业“美德”,而这一章正是古尔雷行将败落、威尔逊迈向辉煌的关键节点。所谓美德,其实就是商业成功的三大要素:预见计划的想象、改正计划的常识、推进计划的能量。之所以被称为苏格兰商业美德,是因为“苏格兰人,也许比其他人,更多地具有商业成功的三大要素”(House:93)。在苏格兰的语境中,商业美德之说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出生于苏格兰东海岸的英国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列举的四种美德,即精明、正义、自控、善行。菲茨吉本认为,斯密的四种美德“是传统的斯多葛美德的别称,它们是(按同样的顺序)智慧、正义、节制、勇气”⑦。如果菲茨吉本的论断成立,那么布朗小说中的商业美德就成了对斯密四大美德的微妙改写:想象和精明(智慧)、常识和自控(节制)、能量和善行(勇气)基本吻合,而四大美德中的正义却被无情地抛弃。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是这样阐述正义的:“当我们禁止对邻居进行任何实质的损害,不直接伤害他,无论是他的身体、他的财产,还是他的名声,那就可以说我们对邻居是正义的。”⑧正义之所以被苏格兰商业“美德”无情抛弃,是因为到了铁路时代,人们已经不再读《道德情操论》,他们终日手捧亚当·斯密更有名的经济学著作。当被称为“漂白男孩”(bleach-the-boys)的校长被问及被父亲送往爱丁堡大学的小古尔雷是否能成才时,老校长不置可否,“走回他闷死人的小房间去研究《国富论》了”(House:164)。老校长埋头研究《国富论》,这预示着商业意识已经渗透到芭比小镇的每个角落,而为《国富论》奠定了心理基础的《道德情操论》却被人们抛到了脑后。 虽然正义(即不伤害他人)被苏格兰商业“美德”排斥在外,但布朗小说中商业“美德”的典范、古尔雷的直接商业对手威尔逊由于超人的自控能力,却自始至终未越过正义的红线。单从商业经营的角度看,与其说古尔雷的失败是由于商业对手的伤害,倒不如说是因为其自身“美德”的缺失。想象、常识、能量三大美德相互依存,一旦缺失了常识,想象和能量就有可能转化成商业的负能量。古尔雷缺乏常识,却有错误的想象和毁灭性的能量。在两个关键的节点,古尔雷完全失去自控,让冲动占了上风:其一、他在明知违约代价的情况下痛打吉布森并拒绝继续为后者运货,后者的一纸诉状把他推到了倾家荡产的边缘;其二、他在经济十分拮据的情况下,因为听不惯公共马车上小团伙的风言风语而做出“一生中最具灾难性的决定”(House:160),把自小就天天逃学的儿子送入爱丁堡大学。后者是他最失败的商业想象:他不顾儿子的抵制,不听好心人的劝阻,在儿子已露出酗酒苗头的时候,还用毁灭性的能量(抵押房产借钱)推进着自己的计划,终酿成家庭悲剧。 二、小团伙的“美德”评判 虽然常识(即自控)缺失是商人之大忌,但“美德”缺失本身并不足以导致古尔雷家破人亡的悲剧。按照小说预设的标准,想象、常识、能量三大美德是商业成功的要素,能将三大美德集于一身的商人固然会胜出,但单项美德的缺失并不意味着注定要失败。在小说所书写的三个商人中,威尔逊是三大美德的宠儿,他有先知先觉的商业想象、超级理性的商业常识、勇往直前的商业能量。阔别15年后,威尔逊带着一大笔钱荣归故里。凭着进城经商的经验以及对芭比小镇现状的洞察,威尔逊冒险在芭比小镇开办了自己的商店。他的商业目标十分明确:“不是赚暴利办小企业,而是靠薄利办大企业。”(House:82)他的商业策略也十分有趣:开业之初,他不辞辛劳地发告示、印传单,挨门挨户送宣传品。他让妻子在家卖货,自己去开展送货上门及分期付款服务。由于铁路时代来临,更多的男人外出务工,送货上门让留守家中的家庭主妇们感到十分温馨,而分期付款则为暂时囊中羞涩的消费群体提供了便利。作为商人,威尔逊的过人之处是他有着超级理性的常识(即自控)。他刚一还乡就受到古尔雷的奚落,被称为“鼹鼠猎手”⑨,但他并未因此而冲动。试想,如果威尔逊选择和古尔雷直接作对,从争夺古尔雷的货运生意开始,说不定最终人财两败就是威尔逊自己了。威尔逊从不意气用事,他先开商店,凭借精明和勤奋积累财富,而后在吉布森的帮助下争夺货运生意,兵不血刃地将古尔雷拿下。 威尔逊集想象、常识、能量三大美德于一身,而另一位成功的商人吉布森则略逊一筹。吉布森有着和威尔逊不相上下的商业想象和能量,但他不时会染上常识“缺乏症”。吉布森通过商业密谋坑了古尔雷,本该故意低调的他竟然在赶集时阴阳怪气地挑衅,结果被古尔雷隔着窗户摔进红狮子酒吧。然而,自控的缺乏并未阻止吉布森商业成功的步伐。芭比迈进铁路时代之后,吉布森凭借铁路公司的内线获得了一大笔建筑生意,他还凭借一双“慧眼”,背弃古尔雷而和威尔逊交好,帮助威尔逊获得铁路公司的大笔建材运输生意,从中获得丰厚的佣金。吉布森的个案说明,虽然常识(即自控)缺失是商人之大忌,缺乏自控极可能成为商业失败的诱因,但美德缺失本身并不会必然酿成悲剧。 那么,到底是什么最终酿成了古尔雷家破人亡的悲剧?除了古尔雷自身的缺陷,一个更为直接的动因是芭比小团伙的风言风语。小说这样描述小团伙:“在每一个小小的苏格兰共同体中都有一个特色鲜明的种类,叫做‘小团伙’……小团伙的种类有两种:‘无害的小团伙’和‘肮脏的小团伙’。芭比的小团伙大多属于第二种。”(House:33)古尔雷骂小团伙是“该死的老妇人”(House:33),但芭比小镇的小团伙其实没有女性,它的核心成员是前任行政长官、主祭以及消息灵通人士布罗迪等一堆大男人,它的主要职责是对芭比小镇的大事小情进行评判和传播。出于对古尔雷莫名其妙的、刻骨铭心的恨,即便在古尔雷事业辉煌的时候,小团伙在羡慕嫉妒的同时也没有忘记挖苦和诅咒。他们以先知先觉的姿态预言:铁路来临,古尔雷必败,古尔雷的儿子是一个完美的木头脑袋,绝不能从他那里期待什么。对于古尔雷来说,小团伙是毁灭个体的推手。铁路来临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人力无法阻挡;但是,在小古尔雷被强行送到爱丁堡大学并最终走上弑父之路的过程中,小团伙难辞其咎。首先,正是由于他们在公共马车上当着古尔雷的面夸赞威尔逊儿子的聪慧、指桑骂槐地嘲弄小古尔雷的愚蠢,才导致古尔雷做出了强行送儿子读大学的错误决定;其次,小古尔雷被开除之后,正是由于小团伙在集市上的热议以及主祭在红狮子酒吧对他酸溜溜的奚落,才致使小古尔雷酒性和兽性爆发,进而导致其弑父悲剧。 小团伙风言风语的焦点是对古尔雷和威尔逊的“美德”评判。“美德”一说绝非戏言,它是小团伙预言威尔逊和古尔雷成败的标尺。按照小团伙的评判,威尔逊是苏格兰商业美德的典范,连他的妻子也“集东方和西方美德于一身”(House:90)⑩,所以威尔逊的成功是必然的。在尚未成为新一任行政长官的时候,他就在小团伙的支持下在联名向铁路公司请愿的集会上扮演了领导者的角色。小团伙之所以不喜欢古尔雷,是因为他的成功“和他的美德完全不成比例”(House:11)。显然,此处的美德是一个反讽,它的所指是古尔雷的傲慢和偏执。按照小团伙的评判标准,古尔雷和“美德”毫不相干。小团伙的结论不符合小说文本中的事实。虽然古尔雷有许多缺陷,但他也有美德:他对心爱的马儿、对心爱的马夫不乏温情。当他心爱的马儿泰姆死去时,古尔雷表现出一种真切的怜悯之情;当他解雇最后一位马夫彼得时,已经囊中羞涩的他仍然表现得很有人情味儿,彼得走了很远,又回来和他说声再见,雇主与雇员之间的情谊着实令人感动。古尔雷那种再穷也不能亏待自己下属的精神,在铁路时代可谓弥足珍贵,不失为一种美德。 可惜的是,古尔雷的美德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美德,在小团伙的“美德”评判中根本派不上用场。小团伙的评判标准是苏格兰商业“美德”,威尔逊是商业美德的宠儿,自然受到小团伙的青睐;古尔雷是商业美德的弃儿,自然会招致小团伙中“小方面的大人物”的仇视。小团伙的评判在威尔逊和古尔雷的兴衰之路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威尔逊顺势而为,巧妙地运用小团伙的评判为其商店的开张做免费宣传、为其登上新一任行政长官的宝座打造声势;古尔雷逆流而动,他深知谣言越碰越可怕的道理——“你越是踩踏肮脏的东西,它扩散得就越广”(House:160),却一次又一次地踩踏谣言,在与小团伙的对峙中做出灾难性的决定,直落到家破人亡的地步。 哈特在《苏格兰小说》中写道,布朗“反菜园派的意图阻止了所有文雅美德的展现”(11)。初读起来,哈特的论断着实有些蹊跷。《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明明是一部书写商业“美德”的书,美德一词在小说叙述中随处可见,为何哈特却说布朗阻止了文雅美德的展现?其实,回答这个问题并不难。哈特并没有否认小说中的“美德”,但他所强调的是“文雅美德”,而小说中着力展现的苏格兰商业美德并不文雅。由于正义被所谓的商业美德无情抛弃,小团伙的“美德”评判已然成为古尔雷悲剧的催化剂。而且,更为可悲的是,“古尔雷的倒台对他的邻居们有着一种不神圣的吸引力”(House:257)。小团伙不仅热衷于缔造古尔雷的悲剧,还迫不及待地想见证他们所仇视的人如何一步步走向深渊。对于这种畸形的期盼,小团伙竟然没有负罪感,他们饶有趣味地讨论着古尔雷的败落,“既非邪恶亦非同情,只是好奇而已”(House:257)。 《国富论》中有段经常被人引用的话:“不是由于屠夫、酿酒师和烤面包者的恩惠,我们期望得到自己的饭食,而是从他们自利的打算。”(12)换句话说,自利乃经济学之本,自利本身无可厚非。既然芭比小镇已经步入铁路时代,商业成为铁路时代的热门话题,那么,在商言商,用商业“美德”标准去评判商业经营也算是理所当然。在保持正义底线的情况下,重视商业、甚至歌颂商业似乎也无可厚非。翻开英国文学史册,无论是在虚构作品还是在非虚构作品之中,都能找到对商业歌功颂德的案例。艾迪森在《观察家》中把商人奉为英联邦的中流砥柱,说他们“用好的行政的相互交流把人类编织在一起,分配自然的恩赐,为穷人找到工作,为富人增添财富,为伟人增添雄伟”(13)。同样,以历史小说闻名于世的司各特借《红酋罗伯》中英格兰商人之口,把商业书写成迷人而无罪的行业:“贸易有着赌博所具有的所有迷人之处,而且没有赌博的道德负罪感。”(14) 如果小说中只有始终未越过正义红线的商业“美德”典范威尔逊,没有制造谣言而且美其名曰“美德”评判的小团伙,那么,即便铁路时代的商业竞争愈演愈烈,也不至于将古尔雷推向家破人亡的深渊。铁路时代的冲击、商业敌手的暗算,远不如小团伙的风言风语致命。在芭比小镇的小团伙中,前任行政长官和主祭都赫然在目,小镇的居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们这样职位的人会与小团伙为伍。然而,正是由于前任行政长官和主祭之类名流的加盟,才使得小团伙的言论在芭比小镇更加顺畅地流传。如果小团伙真的只是在商言商,他们的评判亦无可厚非。可悲的是,他们拿着只在商业适用的“美德”去评判商业之外的东西,而且全然抛弃了亚当·斯密所倡导的以“不危害邻里”为准则的正义美德。正是由于正义的缺失,小团伙才成为了“肮脏的小团伙”,而小团伙的“美德”评判自然也就演变为马车商人悲剧的催化剂。 三、乡村共同体的衰微 罗伯特·克劳福德在《苏格兰之书:苏格兰文学史》中写道:“布朗展现了一个受制于金钱的共同体,在那里慈善极度缺乏。”(15)这句话道出了布朗小说的精髓。作为反菜园派的旗手,布朗对菜园派粉碎性的一击表现为他对苏格兰共同体的重写。在菜园派的笔下,古老的苏格兰共同体依然坚挺,顽强地抵御着铁路时代和商业社会的侵袭。而在布朗的反菜园派小说中,古老的苏格兰共同体日渐衰微,芭比小镇“肮脏小团伙”的出现就是共同体衰微的显著标志。 小团伙是一种畸变的共同体,它最为显著的畸变是慈善和正义的缺失。诚如弗朗西斯·哈特所言,共同体是苏格兰文学的主导神话,它是“个人价值的基础和救赎的条件”(16)。提摩西·贝克归纳了共同体的四个特点:它所指的是一个地方的、以地理区划为基础构建的区域;它具有可以共享的民族以及政治目标;它具有可以共享的道德和伦理方式;它能够创设人际关系和个体呈现自我的语境。(17)虽然表达方式略有不同,但哈特和贝克都在强调共同体要给个体提供呈现自我的语境,换句话说,就是共同体必须有助于或者至少不妨碍个人价值的实现。就这一点而言,芭比小镇的小团伙完全背离了共同体价值观,已然沦为个体呈现自我的阻碍,甚至成为毁灭个体的大舞台。小团伙成员热衷于制造谣言(他们的谣言成为古尔雷悲剧的助推剂);他们不仅危害邻里,还充满好奇心地期盼邻里悲剧的发生。就此而言,虽然芭比小镇的小团伙依然满足贝克所列举的前三个条件,但它颠覆了苏格兰共同体最本质的价值观,将其更名为“小团伙”可谓是恰如其分。 值得注意的是,克劳福德所说的“受制于金钱的共同体”不是专指小团伙,而是指整个芭比小镇的人。受制于金钱并非小团伙的专利,游离于小团伙之外的威尔逊与吉布森、与小团伙势不两立的古尔雷、红狮子酒吧的老板、终日研究《国富论》的老校长,都是受制于金钱的典范。连只会躲在阁楼上偷看低俗小说的小古尔雷都在梦想着早日接手家里的生意,以便彻底告别无聊的学校教育。商人乃至商人的孩子受制于金钱,还算是情有可原。但是,作为“教区道德执行者”(18)的主祭和老校长也一切朝钱看,就颇值得警觉了。主祭是小团伙的一员,他利用自己的地位,把自己的女儿送到红狮子酒吧供职,并因为嫉妒古尔雷的豪宅和财富而不断诅咒,直至后者家破人亡才肯罢休。更为可悲的是老校长,他不认真教他的希腊文,对小古尔雷等学生逃学一无所知,却整日闷在小房间里研究《国富论》。受制于金钱的共同体是反菜园派的徽标,是它和菜园派笔下苏格兰共同体的区分所在。 约翰·斯比尔斯曾经哀叹说,彭斯之后就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苏格兰文学,因为“佛格森和彭斯诗歌中暗含的古老的苏格兰共同体”(19)已被工业革命破坏。斯比尔斯所设定的时间节点有些过早,因为在菜园派的笔下,古老的苏格兰共同体依然坚挺。菜园派笔下的共同体不仅创设了个体呈现自我的语境,还缔造出令人感动的可塑之才(lad o'pairts)(20)的故事。麦克莱伦的《在美丽的野蔷薇丛旁》被认为是可塑之才神话的经典:家境贫寒但天资聪慧的男孩豪尔在德拉姆休为首的全体村民资助下到爱丁堡大学读书,他不负乡亲的厚望,为他们捧回了一大堆奖品和奖章。然而,没等成为一个出色的学者,年仅21岁的他就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德拉姆托奇蒂为豪尔举行了盛大的葬礼,在豪尔的墓碑上,除了名字、年龄以及辞世的时间,还特别刻着他的学位以及一句颇有深意的墓志铭:“他们将把整个民族的光荣和荣誉带给它。”(21) 英国社会学家麦克罗恩对可塑之才的文化蕴涵进行了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可塑之才所孕育的共同体的政治经济学是前资本主义的。赚钱被认为是过度被贪婪所驱使,而不是用理智和感情中立的方式去追求”(22)。菜园派所塑造的可塑之才神话的核心不是个人,而是一个崇尚平等主义教育、不受制于金钱的共同体。在这样的共同体中,商业成功不被称道。在列举多姆西校长的教育硕果时,商人被排在最后,而且被耐人寻味地加上了引号:“在多姆西时代,学校送出去的英才中有七位牧师、四位校长、四名医生、一位教授、三名公务员,还有许多‘将自己献身于商业追求’。”(23)菜园派笔下的共同体不受制于金钱,他们有着更神圣的目标:倾全民所有,培育可塑之才。校长把自己的钱都用在学生身上,家人宁愿几年不换新衣服也要成就求学梦,村里的富裕户舍得拿出比买一头牛还多的钱来赞助。在苏格兰共同体的语境中,培养学者是“为整个英联邦增添财富”(24)。 作为反菜园派的旗手,布朗毫不留情地撕开了苏格兰平等主义教育的面纱。本该互帮互助的共同体开始互相仇视,本该把爱心和金钱都用在学生身上的老校长埋头研究《国富论》,本该为乡亲捧回一大堆奖章的“可塑之才”小古尔雷只捧回一个校园文学奖就忘乎所以,开始嗜酒如命。尤其可气的是,这样一个可悲而又可恶的家伙竟然用彭斯的诗句“自由与威士忌同行”当作酗酒的护身符。尼尔·麦克林在《北方大学的生活》(1874)中写道,大学教育是苏格兰人的至善,苏格兰平等主义教育使得大学对穷人和富人都敞开大门,这是“我们国家的骄傲和荣耀”(25)。如果平等主义教育产出的是菜园派笔下豪尔之类的英才,那它无可否认地是国家的荣耀。但是,如果不幸产出了小古尔雷这样的败类,那就是平等主义教育的耻辱了。更何况,在苏格兰的语境中,可塑之才仅限于男生,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 布朗在展现受制于金钱的共同体的同时,还慢慢撬动了苏格兰共同体的根。菜园派笔下的苏格兰共同体之所以坚挺,是因为它的根牢牢地扎在乡村,就像麦克莱伦在《旧日好时光》中所写的那样:“他的根深深地扎在土壤里,如果你把它们拔出来,他的心就会枯萎和死亡。”(26)而在布朗的小说中,城市的黑手已触手可及。爱丁堡成为小古尔雷的堕落之地,是生活在爱丁堡的母亲的旧好引诱他贪恋杯中之物;格拉斯哥成为吸钱的黑洞,古尔雷错误地运用了铁路的便捷,到格拉斯哥用房产抵押借钱,让自己败落到无可挽回的境地。 一旦离开了乡村的土壤,共同体就不复为共同体。(27)一旦共同体风雨飘摇,苏格兰也就不再是真正意义上的苏格兰。这绝非危言耸听。麦克罗恩曾明确指出,对1890年代乡村教区学校的理想化(例如菜园派文学)其实是捍卫苏格兰性的体现,因为人们把平等主义教育神话“看做是苏格兰的一种特性,而它已经受到英国化的侵袭”(28)。对于苏格兰而言,共同体的衰微无异于民族精神的蜕变。布朗在1901年10月写给欧内斯特·贝克的书信中说,《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是一部“残忍的和血腥的书”(29)。时隔不久,他就不幸英年早逝。到底“残忍和血腥”应如何理解?后人只能依据文本去推断。从表面上看,马车商人的悲剧就足以将“残忍和血腥”囊括其中。但是,从更深层面审视,如果没有商业意识在受制于金钱的共同体中的弥散,没有缺乏慈善的小团伙的推波助澜,血腥的悲剧或许可以避免。从这种意义上说,恰是商业意识的弥散和乡村共同体的衰微,才使得《带绿色百叶窗的房子》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残忍的和血腥的书”。 ①James Veitch,George Douglas Brown,London:Herbert Jenkins,1952,p.57. ②王佐良、周珏良《英国20世纪文学史》,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299页。 ③Ewen A.Cameron,Impaled Upon a Thistle:Scotland since 1880: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10,p.9. ④George Douglas Brown,The House with the Green Shutters,New York:McClure,Philips and Co.,1901,p.2.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简称House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⑤Sean Purchase,Key Concepts in Victorian Literature,Houndmills:Palgrave Macmillan:2006,p.xii. ⑥殷企平《推敲“进步”话语——新型小说在19世纪的英国》,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504页。 ⑦Athol Fitzgibbons,Adam Smiths System of Liberty,Wealth,and Virtue:The Moral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104.斯密四大美德的英文词依次是prudence,justice,selfcommand,benevolence,在斯密时代这四个词的所指和今天有很大的差异,以prudence为例,当时的首要指涉是“精明”,而今天更多地是指“谨慎”。所以,菲茨吉本的阐释并非过度阐释或者曲解。 ⑧Qtd.in Athol Fitzgibbons,Adam Smiths System of Liberty,Wealth,and Virtue:The Moral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p.103. ⑨因为威尔逊父亲曾经靠捕捉鼹鼠卖皮毛赚些小钱,所以古尔雷将威尔逊戏称为“鼹鼠猎手”(mole catcher)。 ⑩此处的“东方与西方”是指苏格兰东海岸和西海岸。 (11)Francis Russell Hart,The Scottish Novel:From Smollett to Spark,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8,p.135. (12)亚当·斯密《国富论》,杨敬年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页。 (13)Qtd in Andrew Lincoln,“Scott and Empire:The Case of Rob Roy”,in Studies in the Novel,34.1(2002),p.45. (14)Walter Scott,Rob Ro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67. (15)Robert Crawford,Scotland's Books:The Penguin History of Scottish Literature,London:Penguin Books,2007,p.532. (16)Francis Russell Hart,The Scottish Novel:From Smollett to Spark,p.401. (17)Timothy C.Baker,George Mackay Brown and the Philosophy of Community,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9,p.5. (18)Francis Russell Hart,The Scottish Novel:From Smollett to Spark,p.404. (19)John Speirs,The Scots Literary Tradition:An Essay in Criticism,London.Faber and Faber,1962,p.15. (20)笔者曾就lad o'pairts的所指问题向斯特林大学苏格兰研究中心Scott Hames博士请教,他回复说:在苏格兰方言中,pairts意为“才能”,lad o'pairts类似于标准英语中所说的meritocracy(知识精英)。lad o'pairts已然成为一种重要的苏格兰文化传统。在这种传统中,通常由好心而且知人善任的教师发现并激励和培养有能力的学生(通常是男生),而后说服当地民众出钱资助学生继续深造(比如读大学)。没有这种集体的资助,学生自己的家庭是无法负担深造所需费用的。 (21)Ian Maclaren,Beside the Bonnie Brier Bush,New York:Dodd,Mead and Company,1894,p.55. (22)David McCrone,Understanding Scotland:The Sociology of a Nation,London:Routledge,2001,p.99. (23)Ian Maclaren,Beside the Bonnie Brier Bush,p.9. (24)Ian Maclaren,Beside the Bonnie Brier Bush,p.17. (25)Neil N.Maclean,Life at a Northern University,Glasgow and London:John S.Marr and Simpkin,1874,p.vi.为了表示正规,麦克林还特意将“至善”写成了拉丁文"summum bonum"。 (26)Ian Maclaren,The Days of Old Langsyne,Glasgow:Kennedy and Boyd,2008,p.30. (27)苏格兰共同体和乡村是“绑定”的,这在布朗之后的苏格兰小说更为明显:吉本的《苏格兰之书》把共同体从乡村一步步推移到城市,与城市越近,共同体的衰微就越明显。乔治·麦凯·布朗笔下的奥克尼共同体植根于乡村,就有着和菜园派相仿的和谐,而斯帕克的布罗迪帮(Brodie set)、韦尔什的吸毒男孩(skagboys)则植根于城市,共同体随之就变得畸形。 (28)David McCrone,Understanding Scotland:The Sociology of a Nation,p.94. (29)Qtd.in Ian Campbell,Kailyard,Edinburgh:Ramsay Head Press,1981,pp.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