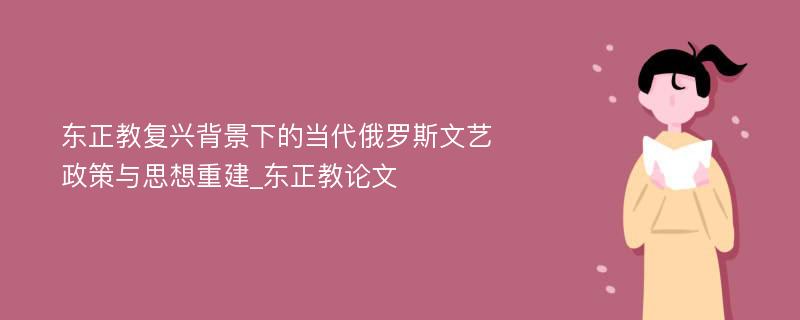
东正教复兴背景下的当代俄罗斯文艺政策与意识形态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东正教论文,俄罗斯论文,意识形态论文,文艺论文,当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文艺政策作为国家在文艺保护和发展领域实行的一整套制度化、理念化和行为化的政治主张,是政策主体用以调节文艺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基本杠杆,是国家意识形态和主导价值的基本体现和主要载体。普京执政以来,面对苏联解体后特别是叶利钦时代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为整合社会思想、提振民族精神、遏制道德滑坡、增强国家认同和文化软实力,将俄罗斯传统价值和现代性追求合二为一,提出了以“新俄罗斯思想”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战略。在这一战略实施中,俄罗斯政府借助东正教复兴的社会趋势,通过立法规划、教育宣传、战略外交等方式实施了一系列相关文艺政策,经过文化市场资本运作和文艺界参与的推波助澜,将东正教中蕴含的帝国崇拜、聚议共同、人道主义等核心文艺精神与意识形态重建诉求相融合,成为俄罗斯精神重建、道德净化和审美重构的重要力量之一。 叶利钦时代政治格局、社会体制和经济制度的激烈震荡造成了俄罗斯民众思想意识和文化心理的深刻矛盾、困惑和危机。“广泛存在的滥用职权、官僚主义、权贵垄断、寻租腐败等‘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和‘政府病’现象,造成国家形象和政府信任的双重危机。俄罗斯的社会意识领域呈现出一种精神迷惘的状态,以至于俄罗斯在长达近10年的时间里一直徘徊在社会改革基本道路抉择的问题上,陷入精神与意识形态的全面危机”(李景阳1-2)。这种意识形态真空造成的危机在大众意识中表现为一种“对核心价值的民族认同的丧失”,暴露出爱国主义淡漠、理想信念丧失、道德滑坡严重、主流文化式微等社会问题和病症。据2001年俄罗斯联邦政府制定的《俄罗斯联邦2001-2005年公民爱国主义教育纲要》显示:传统精神价值贬值对国内居民大多数社会集团和年龄层次的人都产生了消极影响,形成爱国主义最重要因素的俄罗斯文学、艺术和教育在对人的培养方面的意义急剧下降。社会正在失去传统的俄罗斯爱国主义意识,冷漠无情、利己主义、不知羞耻、无端的攻击性行为、对国家和各种社会机构的不尊重,正在社会意识中广为扩散。①意识形态的空洞在文艺领域集中体现为弘扬民族精神、爱国主义和传统价值观的严肃文学陷入低潮,以美国文化为代表的西方商业文化潮流严重冲击本土文化,高雅、严肃的影视、音乐等艺术作品鲜有人问津,“艺术作品中非政治化、非意识形态化、讽刺性模拟、享乐主义、娱乐因素明显增强,轻松的题材和体裁、风格‘秀’、色情表演和恐怖大行其道。原先被禁的得到解禁,恐怖和暴力变成游戏、情欲编入引人入胜的场景之中,戏剧‘秀’则与博彩业捆绑在一起”(贝文力34)。严肃文学和经典文学的刊物数量骤减,相关的出版机构及文化事业单位惨淡经营;因工资待遇不高,文艺工作者艰苦度日。乌兰诺娃的境遇便是一例,这位曾享誉世界的俄罗斯芭蕾艺术的象征和骄傲,在转型时期只能靠变卖家产来维持生活和支付医疗费用。② 面对俄罗斯精神的整体萎缩和困顿,在俄国具有近千年精神统治传统的东正教悄然复兴,它不仅以国家统一、国家集权和帝国信仰的历史感召重新登临了政治殿堂,更以末日救赎、道德至上和聚议共同的精神力量告慰着陷入迷惘的俄罗斯人。1997年9月国家杜马通过的《俄联邦关于信仰自由和宗教组织法》特别确认:“俄联邦为世俗国家,承认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俄国精神和文化形成与发展中的特殊作用”。2002年2月又通过《俄联邦传统宗教组织法》,进一步肯定东正教之于社会发展中的各方面作用,保障东正教组织展开正常活动等,东正教已经成为后苏联时期参与俄罗斯重建进程的重要力量。普京执政前,无论是教众规模上还是社会影响上,东正教都堪称全国第一大宗教。截止2002年,全俄共有128个主教区,管辖1.9万个教区和480所修道院,教徒遍布全国89个行政主体,自认为是东正教徒的俄罗斯人就已占到国民的60%,即超过8千万居民信仰东正教(A.Ефимов 635)。这为东正教文化促成普京时期国家意识形态重建提供了社会基础和环境前提。 普京总结叶利钦改革的经验教训,执政伊始便以“新俄罗斯思想”作为意识形态和文化战略的理论基石建构新的国家主导价值体系,以填补苏联解体后延续多年的意识形态真空。“新俄罗斯思想”是一个合成体,它把全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经过时间考验的俄罗斯传统价值观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两大支柱,一是“高于各种社会阶层、集团和种族利益的超国家的全人类价值观”;二是“被人们称作俄罗斯人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的价值观”。所谓“自古以来就有的传统的价值观”即包括“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作用”和“社会团结”四方面(普京,《普京文集2000-2002》7-10)。不难发现,这“传统的价值观”的内涵是19世纪30年代俄罗斯教育大臣乌瓦罗夫提倡的“东正教、专制制度和人民性”三位一体强国之道的当代回响,充分体现了普京回归俄罗斯传统文化寻求思想资源和价值支撑的政治诉求,其意图就是在大厦将倾时提振民族精神、统一社会思想、团结国家力量。东正教作为俄罗斯文化传统精神中的最重要内涵之一,在填补意识形态真空过程中责无旁贷地扮演了“新俄罗斯思想”建构者和实施者的角色,而其“之所以能够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不仅是因为苏联解体以及包括无神论在内的苏联式意识形态的退场,而由东正教填补信仰真空,而是因为俄国文化的独特性,以及俄国社会的历史进程一向和东正教相关联”(林精华121)。 俄罗斯由文化立族,东正教精神是俄罗斯文艺的根本,是俄罗斯的民族意识、思想观念、文化理解和生活经验的重要支点。尼·别尔嘉耶夫在《俄罗斯思想》中曾指出:“俄罗斯民族——就其类型和精神结构而言是一个信仰宗教的民族[……]出身于平民和劳动阶层的俄罗斯人甚至在他们脱离东正教的时候也在继续寻找上帝和上帝的真理,探索生命的意义。在俄罗斯人那里,连那些不仅没有东正教信仰,而且甚至开始迫害东正教会的人,在内心也保留着东正教形成的痕迹”(245-46)。历经千年的发展历程,作为民族精神代表的东正教绝不仅仅是一种宗教,而是一种不可阻挡的渗透进斯拉夫—俄罗斯民族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里的弥散性存在。东正教所蕴含的帝国崇拜心理、聚议共同思想和博爱人道主义是经由俄罗斯“黄金一代”经典作品缔造传扬的民族文艺精神之魂,是当下普京“新俄罗斯思想”的核心内涵,是其制定文艺政策实现重树强国梦想、凝聚民族精神和道德净化等意识形态诉求的深层动因。 “第三罗马”的帝国崇拜心理——文化强国的梦想之基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俄罗斯东正教称莫斯科为“第三罗马”,自15世纪以来“俄罗斯的使命是成为真正的基督教、东正教的体现者与捍卫者[……]俄罗斯是唯一的东正教王国,同时在这个意义上也是全天下的王国,正如同第一罗马和第二罗马一样,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东正教王国的强烈的民族性”(别尔嘉耶夫8)。于是,“第三罗马”学说成为莫斯科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建立的思想基础,其核心内涵是,俄罗斯是基督教世界的中心,是基督教的希望所在,俄罗斯民族是被上帝选定的优秀民族,定要历史性地完成上帝交给的捍卫俄罗斯和弘扬基督教的历史使命。18世纪彼得一世将这一思想演绎成“大俄罗斯主义”,其思想主旨就是俄罗斯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和国家,而且俄罗斯必然要成为一个强大的帝国,从而确立了俄罗斯的“强国之梦”。19世纪后,泛斯拉夫主义基于“上帝选民”的民族优秀论而持有的强势国家心理将克服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外部侵扰的顽强承受力作为生命本质,将促进富强和扩张的发展战略作为政治诉求,将唯我独尊和傲视一切的宗教自信作为精神优势,提出了独具俄罗斯特色的帝国崇拜式的“强国精神”。 这一精神在俄罗斯现代文学思想领域得到了充分弘扬和彰显,恰达耶夫、霍米亚科夫、果戈理、马雅可夫斯基、阿赫玛托娃、肖洛霍夫等都在其作品中表达过对于俄罗斯所肩负的救世使命的高度认同和对于国家历经苦难终将强盛的坚定信心。其中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长篇小说《少年》颇具代表性。小说中主人公维尔希洛夫以俄罗斯精英自居,他带着铁链在欧洲漫游布道,将传播基督精神视为自己的使命,以神圣俄罗斯的宗教感和弥赛亚观念承担起全人类的救赎事业。“我在法国是法国人,和德国人在一起,我便是德国人;和古希腊人在一起,我便是希腊人,所以我是地道的俄罗斯人。我所以是真正的俄罗斯人,并且尽了最大的努力为俄罗斯效劳,是因为我体现了它的主要思想。我是这种思想的先锋”(陀思妥耶夫斯基607)。维尔希洛夫的这番充满民族自豪感和救世精神的陈述,揭示了俄罗斯民族作为上帝选民的世界公民意识和优等强国心理。可见,“第三罗马”、“救世主说”和“大俄罗斯主义”的帝国崇拜心理一直是俄罗斯挥之不去的情结,并逐渐被岁月锤炼为俄罗斯人整体的强国信仰。因此,在国家面临整体衰落危机之时,帝国崇拜的强国梦想这一俄罗斯民族深层稳定的民族心理成为了重振雄风的最佳文化基因。正如普京在阐释“新俄罗斯思想”时才会强调“俄罗斯过去是,将来也还会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在俄罗斯整个历史进程中,它们还决定着俄罗斯人的思想倾向和国家的政策。即使在今天它们依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普京文集2000-2002》8)。 “聚议性”的民族认同力量——爱国精神的历史之维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成》一书中提出:“宗教可以通过自身信仰所表现出来的特有凝聚力,将社会的不同人、群体、社会势力等社会存在和社会发展的各要素联系起来,并在共同信仰、共同价值、共同组织形式、共同教义和共同利益规范的基础上实现社会整合”(579-83)。东正教的这种社会整合特性被19世纪的斯拉夫主义者霍米亚科夫称为“聚议性”(соборностъ)。“聚议性”是教徒们在共同理解真理和共同探索拯救之路的事业中以教会为基础的自由统一,是以对基督和神规的共同之爱为基础的统一(张百春55)。其原则就是统一性和自由的结合,这种结合建立于爱上帝和爱上帝者之互爱的基础之上,意味着许多人的自由和统一结合在一起。哲学家洛斯基进而将这一理论生发,认为“聚议性”发挥作用的条件是“只有在个别个人自愿服从绝对价值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只有个人拥有建立在对整体、对教会、对自己人民和国家的爱的基础上才有可能”(洛斯基23)。如此则形成了俄罗斯东正教独特的个人统一逻辑:主教以对上帝的爱的名义将俄罗斯个体统一到教会整体中,地主以对沙皇的爱的名义将俄罗斯个体统一到村社整体中,政府以对祖国的名义将俄罗斯个体统一到国家整体中。于是,教会-村社-国家作为绝对价值与主教-地主-政府作为通达路径均以三位一体的对应关系构成了对俄罗斯人个体的控制和整合,实现了从膜拜上帝到尊崇沙皇再到热爱国家的社会的三维重合,于是对于宗教的坚定信仰演化为对沙皇的绝对服从、对村社集体生活的依赖和对于国家的热爱忠诚,宗教的“聚议性”转化为国家的“聚议性”,在实现政教合一的基础上国家成为现实中的宗教,生成了俄罗斯“大国小我”的民族集体意识和“爱国主义”。 果戈理的长篇小说《塔拉斯·布尔巴》生动展现了这种“聚议性”爱国精神所产生的强大民族号召力和自豪感。布尔巴在波兰边境的战斗中对将士们激励道:“我们面临的是需要我们流血流汗,发扬哥萨克崇高的献身精神的伟大事业!那么,让我们来喝上一杯,伙伴们,让我们先为神圣的正教的信仰干杯,愿这一信仰最终有一天会传遍全世界,到处都只有这一种神圣的信仰,所有的异教徒都将变成基督徒”(果戈理46)。布尔巴正是通过强化俄罗斯东正教思维方式和主体精神的一致性,召唤起将士们捍卫“神圣罗斯”的力量和献身东正教的决心,从而激发起将士强烈的爱国精神和献身精神。自998年罗斯受洗以来,无论是蒙古鞑靼人入侵时期东正教教会领导教众的集体反抗举动,还是1812年卫国战争时期斯摩棱斯克圣母像作为整个国家圣物在征战中所起到的精神鼓舞力量,以及1941年全苏联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者时谢尔盖大牧首向全国教徒发出23份号召书,也的确印证了东正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所起到的重要凝聚作用(乐峰202-37)。 因此,当俄罗斯在全球化时代再次遭遇民族国家认同危机时,普京强调,“我们需要共同找到能团结整个多民族的俄罗斯的因素。除了爱国主义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做到。”③可见在普京看来,面对意识形态混乱、文化实力差距拉大、民族凝聚力弱化的现实困境,只有重启俄罗斯的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才能重燃民众心中的爱国火焰,焕发出民族整体力量,而这“团结整个多民族的俄罗斯的因素”无疑与始终握于俄罗斯精神掌心千年的东正教文化相关。 博爱怜悯的人道主义——道德净化的伦理之泉 东正教较多保留了早期基督教的上帝之爱和人道主义传统,强调弃恶行善的伦理准则、公道诚恳的处世态度、爱心宽容的道德传统等,特别体现于上帝“道成肉身”拯救人类和“爱上帝、爱邻人”的教义、上帝是父亲,人人是兄弟”的精神以及对社会不公的抗议、对弱者和受欺凌受侮辱者甚至罪人的同情和怜悯之中(雷永生55)。这种传统与俄罗斯社会的特殊情况相结合,经由世俗宗教思想家和文学家共同完成,深深扎根于俄罗斯的文化深层焕发着持久的精神力量。正是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白银时代的现代主义作家诗人如梅列日科夫斯基、维·伊万诺夫、梅列日科夫斯基、索洛维约夫等巨擘,通过《安娜卡捷琳娜》、《上尉的女儿》、《复活》、《罪与罚》、《被侮辱和被损坏的人》等名著生动描述了对于贫苦和弱小无助者的怜悯感和通过忍受苦难而赎罪获得复活的精神过程,以独特的宗教道德理想焕发出东正教长久的心灵震撼和精神反思力量,不仅形成了俄罗斯文学所特有的启示录式的思维方式和宗教虔敬感等鲜明特色,同时以其艺术创作为东正教提供了更具深度和广度的命题,深化和拓展了东正教道德净化的精神价值。因此,在面对理想信念丧失、道德急剧滑坡、主流文化衰落、极端个人主义泛滥等种种社会文化病症时,东正教文艺精神所提倡的博爱、宽容、良心、正义、责任、虔诚、纯洁、谦卑、希望和爱等道德核心价值观成为了净化心灵的良药,被教徒视为宗教生活和世俗生活的伦理准则。 正如普京在《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中强调的:“东正教在俄国历史上一直起着特殊作用,不仅是每位信徒的道德准则,也是全体国民不屈不挠的精神核心。以博爱思想、良好戒律、宽恕和正义为本。东正教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俄国文明的特性。千百年来,它那永恒的真理无时无刻不在支撑着人民,给他们以希望,帮他们获得信念。[……]我坚信,在我们进入第三个千年的今天,在我们社会中加强互谅和达成一致意见的基督教理想是可能达到的,也为祖国的精神和道德复活做出了贡献。”④无疑,在一时无法为民众提供更具信服力的道德资源,民众也无法安置因社会转型形成的迷茫心灵的状况下,东正教文化精神无疑是填补道德真空的最佳选择,自然在制定文艺政策重建意识形态的过程中居于重要位置。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伴随国家体制的根本转型,俄罗斯当代文艺政策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建构方式也由前苏联时期文化专制主义式的刚性灌输相应地向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柔性引导转变。作为普京“新俄罗斯思想”在文艺领域的重要体现,俄罗斯借助东正教影响实施的文艺政策主要以重塑国家形象、凝聚民族精神、遏制道德滑坡、增强国家认同和文化软实力为核心,运用法律手段、经济手段,辅之以行政手段等将市场经济的商业行为与国家政治导向巧妙结合,通过政策和资本运作调节积极鼓励东正教成为主流文艺的精神内涵并间接作用于大众文化,从而以潜移默化方式实现重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诉求,主要举措包括: 一、制定相关国家文艺和文化政策法规,为东正教重建意识形态提供法律保障和政策支持 俄罗斯政府高度注重东正教的社会整合与精神召唤力量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和重建的作用,颁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规和规划纲要在政策和资金方面保证东正教题材文艺作品在国家政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俄罗斯文化(Культура России)》(2000-2005年)、(2006-2011年)、(2012-2018年)是俄罗斯联邦政府自2000年起开始制定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规划纲要,是俄罗斯文化事业发展的指导性长期国策,集中体现了国家主体的文化意志。《俄罗斯文化》以国家计划项目形式通过招标竞标、财政拨款、社会融资和项目审核验收等环节落实国家文化政策优先支持内容:国家支持和保障文化创作、教育发展,有效保护和利用俄罗斯文化遗产,加强文化机构和文化活动对解决重要社会问题的作用,加强全俄统一文化空间基础建设等。⑤其中东正教文化保护和文艺事业发展被作为主要项目予以重点支持,主要包括:加强对具有东正教教会功能的历史和文化保护建筑的修复和重建提供资金支持;⑥全国文化和艺术机构为教堂、教学机构、启蒙和慈善基金、主日学在召开会议、诵读和各种见面会方面提供帮助;向东正教教会移交属于教会的建筑物供其无偿使用;⑦由国家组织举办国家教会节、复活节和斯拉夫文字和文化日等系列活动,每年节日活动会持续多日,举行包括以“东正教的俄罗斯”为主题的文学日、研讨会、电影展映、戏剧音乐演出等系列宗教文艺活动,在全国具有广泛影响;文化部组织资助国家大型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大学和科研机构编纂《东正教百科辞典》(25卷本)等俄罗斯文化经典典籍;文化部出资支持拍摄《普斯科夫任务》、《12》等强调作为俄罗斯民族精神内核的东正教情感,唤起民族良知和国家团结精神的历史题材电影。据2009年普京签署的《俄罗斯东正教(莫斯科东正教)和俄罗斯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实施联邦目标计划“俄罗斯文化”(2006-2011年)的合作安排》显示,东正教教会获得了国家通过公共和私营部门伙伴关系提供的预算资金近13亿卢布,主要用于保护东正教历史和文化遗产保存和发展,支持艺术教育、学术交流和青年人才培养,确保国际间东正教文化交流,发展宗教文化现代信息技术产品生产等。⑧国家奖项最能表征政策主体和主流意识形态对于文学发展的价值导向。在2013年6月12日于克里姆林宫举行的俄罗斯国家奖颁奖仪式上,普京亲自为俄罗斯当代文坛“传统派”主将瓦连京·拉斯普京颁发国家人道主义杰出成就奖,表彰他在文学创作中表现出的对俄罗斯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对俄罗斯文学宗教传统的继承和对东正教道德观念及救世精神的阐扬。⑨ 二、强化文艺教育,灌注东正教精神价值内涵和提供道德支援 普京时期,俄罗斯政府积极在国民教育特别是文艺教育中推行东正教文化理论,力图用爱国、正义、责任、虔诚、纯洁、谦卑、希望和爱等东正教深层价值观和道德观影响教育广大公民特别是青少年,以实现团结民族精神、强化道德培养、净化社会空气的作用。一是大量建立世俗宗教教育机构。全俄罗斯在幼儿园、普通中小学、东正教大学、世俗高校中建立大量宗教学部系和教研室,利用东正教和教会历史中的核心教义培养学生对祖国历史传统的情感和对东正教核心道德精神的敬畏,其资金来源独立于教会组织,包括教师培训、教学大纲的规划和教材编写在内的教学组织一般依托国家和政府主要来自国家财政拨款(刘超69)。2011年1月18日,俄罗斯第一所由东正教会创办的教会高校——俄罗斯东正教大学在莫斯科成立,其中设立文学院和艺术学院,莫斯科和全俄罗斯新任大牧首基里尔亲自进行注册登记,这标志着俄罗斯东正教正式进入高等教育系统(汪宁75)。二是强力推行《东正教文化基础》课程。20世纪90年代,斯摩棱斯克州最早在中学开设了东正教文化相关课程内容,2000年该课程引入莫斯科国立中学,2006年已经推广至俄联邦15个州,其中在4个州被确定为中学教学大纲中的必修课,在其他11个州是作为选修课。此间,叶·阿列克桑德洛夫和日·阿尔费洛甫等10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联名上书普京总统对此举提出强烈质疑,认为此举违背宪法,容易造成东正教沙文主义。普京则公开回应支持开设《东正教文化基础》课,他表示“作为人文教育,在学校应以选修课或必修课的形式开设《宗教史》课程,可以使孩子们更多地了解其他民族及其传统,有利于发展本国儿童对待民族和宗教的宽容态度”(Путин 7)。目前,俄联邦35个地区的万余所中小学都开设了这门课程,并在教学大纲、教师培养、教学方法和形式、教育内容、配套教材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套体系。⑩三是开展多种多样的东正教实践教育活动。上世纪90年代中期,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启动了高校间宗教启蒙规划,决定每年举办东正教文艺竞赛,竞赛内容涉及音乐、绘画、文学、应用艺术等多方面,竞赛结果会在达吉亚娜日公布。在中小学举办以“我的东正教祖国”、“我们为俄罗斯保存了神圣”为主题的参观朝圣地修道院、东正教艺术作品展览、音乐巡演、文学艺术节等等课外活动,有效提高了师生对东正教文艺的兴趣,培养了青年学生的文艺修养和道德情操(Епископ Зарайский Меркурий 37)。 三、实施文化外交战略,突出经典艺术的东正教色彩以重树俄罗斯国家形象 面对叶利钦时期整体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迅速衰退的艰困局面,普京时期俄罗斯当局提出以东正教同源文化为武器,通过彰显东正教赋予俄罗斯民族经典艺术的精魂和魅力,塑造良好国家形象,努力增强文化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国际影响力、竞争力和吸引力,积极拉近与独联体和中东欧原社会主义大家庭国家的关系,在收复东正教文化失地、重夺主导世界宗教话语权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与西方基督教文化抗衡、建立欧亚联盟的战略目标。在2005年度的国情咨文中普京明确提出:“俄罗斯与昔日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今日的独立国家,被共同的命运、俄语和伟大的文化联系在一起,不可能置身于追求自由的主潮流之外”(《普京文集2002-2008》189)。为此,2005年4月,俄罗斯专门成立了一个对外地区和文化合作局,由总统办公厅直接领导,其目的就是要发展与独联体国家以及周边国家的文化合作,通过包括文艺合作在内的各种文化交流形式弘扬斯拉夫文化,恢复、巩固和扩大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力(许华12)。具有世界影响的2014年索契冬奥会堪称俄罗斯当前文化外交战略和国家形象塑造的经典案例。在这场斥资500亿美元筹办的俄罗斯文化形象工程中,普京政府充分利用冬奥会这一文化传播效能最高的世界舞台,以强国复兴梦想为核心主题,彰显俄罗斯民族艺术中的宗教精神,实现了对外展示大国重新崛起姿态和对内提振民族自信心的创作意图。索契冬奥会开幕式上,无论是具有600年历史的斯瑞坦斯基修道院唱诗班以“圣咏”方式高唱俄罗斯国歌,还是以彩色气球再现的“圣巴希尔大教堂”、“伊萨基辅大教堂”等经典建筑,无论是创造斯拉夫字母的基里尔和梅福季图像展现,还是斯特拉文斯基的《诗篇交响曲》、拉赫玛尼诺夫的《彻夜祈祷》的配乐主题回响,无不向世人展示出“东正教所带给俄罗斯人四件最珍贵礼物:文字、绘画、音乐和建筑艺术”(贝文力6)的独特艺术感染力和文化吸引力,向世界宣示了一个昔日大国在经历20余年的转型阵痛、精神困顿和自信衰落后的高调回归。 “帝国的基础是艺术与科学。忽略它们,或者贬低它们,帝国即不会存在。帝国追随艺术,而不是如英国人所说的那样相反”(Frye 447)。普京时期,虽然由于宪法对去意识形态的规定使政府不能以专制话语和新闻审查形式强行干预东正教的文艺进程,但是在文化市场的运行规则下,国家却可通过文艺事业和文化产业的政策调节同样实现对文艺形态的间接引导和控制;另一方面,部分文艺创作主体作为知识精英出于自身对俄罗斯民族振兴的愿望、国家崛起的希冀和对斯拉夫价值观的忠诚也主动探寻东正教文化的民族根性,通过文艺作品复兴东正教文化为社会出示净化道德世界、建筑民族认同和解决民族危机的治疗方案;同时,在被迫进入文化市场后,文艺创作者出于生存需要,为增加公众对自己的产品兴趣也迫切希望借助政府的项目引导和政策支持而赢得声誉、获取利益。因此在这样独特的政策环境与自由话语之间,在创作欲望、社会效益和经济利益的纠缠和合谋中,文学、哲学、艺术、教育、大众传媒等自觉和不自觉地融入了当代俄罗斯意识形态重建的大潮中,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顺应和对抗中构成了当代俄罗斯文艺一道奇特的东正教文化景观。 文学作为“先知”首当其冲。普京时期,大量归侨作家、来自苏联的作家、新成长起来的作家普遍热衷于经由东正教视野去透视历史或现实,和主流话语之间构成某种张力关系,从而影响到当代俄罗斯人参与社会意识形态建构的进程,成为当代俄罗斯文坛不可忽视的重要思潮和现象。许多作家在对当代俄罗斯社会民族精神式微、理想价值混乱、伦理道德滑坡的忧虑和不安中,主动融入民族认同和帝国崛起的文艺复兴里,以历史主义精神积极挖掘东正教文化的民族凝聚力量和道德净化作用,将基督精神和思想作为疗救社会邪恶和不义的灵丹妙药创作了大量具有东正教色彩,借用圣经人物、故事和理念的文学作品,对国家意识形态重建起到了重要思想启迪和反思作用。如小说家别楚赫的《国家的孩子》(1997)中将布尔什维克革命与基督教视为同等的理想追求,进而将布尔什维克革命在俄国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实现古俄罗斯和东正教末世论建立公正王国的梦想,将乌托邦理想的最终堕落描述为因耶稣复活的日子尚未到来而造成的后果,小说中充满了俄罗斯民族性、俄罗斯灵魂、拯救世界的俄罗斯能力等神话隐喻,将基督启示录演绎成末世论进而对整个民族灾难进行反思,对民族新生充满希冀。再如沙洛夫的小说《拉撒路的复活》(2002)以荒诞手法描写了信徒库里·巴尔索夫幻想通过努力使哲学家费多托夫的科学复活方案变为现实,从而实现苏维埃乌托邦理想团结全体人民创造人间天堂的神话。沙洛夫把费多托夫的科学幻想、苏联秘密警察制度草菅人命同东正教和俄国传统的“复活”关联起来,从东正教复活理念出发否定了人脱离自然规律接受上帝恩典的幻想,以反讽手法对俄罗斯帝国发展重要动力的弥赛亚意识进行了审美阐释。相同题材的还有瓦尔拉莫夫的《沉默的方舟》(1999)、科斯塔马洛夫的《大地的天空》(1999)、库兹涅佐夫的长篇叙事诗《基督之路》(2000)等都是用宗教隐喻手法描写后苏联时期社会分裂、道德沉沦的状态,同时希冀依靠宗教救赎之路实现新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前文提到的应大牧首阿列克谢二世之邀、由文化部出资支持拍摄并在全俄社会引起巨大反响的电影《普斯科夫任务》就是由高尔基文学研究所副教授谢根尼创作的小说《流行明星》改编而成。因其所弘扬的卫国战争期间普斯科夫一处教会神父亚历山大在抵抗纳粹时的圣徒勇气和人道主义壮举而得到了来自政界、宗教界和社会民众的一致认可,堪称俄罗斯民族困顿和萎靡时期的一针强心剂,成为东正教精神重建帝国意志的重要文化事件。 文艺理论研究界也不甘寂寞,在还原东正教遗产的历史原貌中揭示其对俄罗斯民族精神和国家意识的建构贡献。包括宗教哲学家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舍斯托夫、神学家和经济思想史学家谢尔盖·布尔加科夫、M.格尔申棕、C.弗兰科、别尔嘉耶夫等在内的著作不断重版。它们和圣经一道,成为后苏联俄罗斯社会重建的最重要的精神资源(林精华114)。此外,教育部推荐的《东正教教会与俄罗斯文学》丛书(1997-2002)、莫斯科精神科学院杜纳耶夫教授的六卷本《东正教与俄罗斯文学》(1996-2001)、大祭司谢拉菲姆的《俄罗斯意识形态:东正教神学文集》(2000)、科学院古雷加教授的《后工业时代的俄罗斯思想》等集中阐释了东正教审美与民族精神复兴的内在关联、东正教信仰力量对于抵抗民族种种危机的独特机制、俄罗斯文化独特性根源于宗教信仰对世俗化生活的排斥、东正教文化抵御现代技术化时代的无纸化、程序化和平面化倾向等社会课题,为东正教重建国家意识形态提供了有力的学理支撑(冯绍雷 相蓝欣331-32)。 大众传媒更加推波助澜,大型文学杂志和流行报纸不仅时常刊载表达东正教文化俄罗斯帝国诉求的文学文本,而且通过开设批评专栏直接讨论俄罗斯问题。如格罗伊斯的《论俄罗斯文化认同的希望》就立足于帝国意识和东正教信仰,从俄罗斯帝国沿革史和世界联邦制国家的政治结构变化历程观察俄罗斯帝国复兴的路径。《东正教兄弟联盟》、《俄罗斯之家》、《俄罗斯通报》、《东正教罗斯》、《俄罗斯之线》等由斯拉夫书面文化国际基金会等东正教会及社会力量组建的包括电视频道和杂志在内的东正教-民族主义大众媒介相继开办;电视栏目《神父的话》、《东正教百科全书》、《圣经故事》、《教会日历》、《忏悔》、《东正教之晨》、《和神父对话》等,在国家电视台和地方台纷纷开播,在社会上营造了浓郁的东正教文化氛围,不但汇集表达了俄罗斯民族主义诉求,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俄联邦的政治导向和社会变革走向(林精华114)。 总之,在相关文艺政策的牵引和调动下,复兴东正教、重建国家意识形态成为了政治精英、经济寡头、文艺工作者、宗教人士乃至普通民众的精神共识。在满怀俄罗斯帝国情怀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东正教文化经过10余年终于再次成为了团结俄罗斯人民的精神纽带,在社会力量整合、精神凝聚和道德教育等国家意识形态重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成为当代俄罗斯思想文化重建的重要内容,产生了许多显而易见的现实性效果。 在肯定东正教建构意识形态的政策成果的同时,我们也考察到在俄罗斯社会激烈动荡、思潮纷乱复杂、利益多元分化、文化政策整体转轨的大背景下,与东正教相关的文艺政策持续推动国家意志统一时面临的困境。其一,政策先天不足。由于俄罗斯新文化政策体系还显年轻,承担健全社会文化重任的能力有限,存在诸如资金投入不足、大量政策规划配套实施细则缺乏、政策实施的必要条件缺失等棘手问题造成执行不力。其二,执行环境复杂。俄罗斯作为多宗教的国家,宗教矛盾自古有之。目前除东正教外,新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及苏联解体后出现的各种宗教在社会上也具有一定的影响,都希望在参与帝国重建过程中为相关利益群体赢得机遇,因此对国家侧重支持东正教而“违宪”产生了强烈不满,对其文化推广也造成了一定阻碍,甚至构成了社会稳定的破坏性因素,也不能不引起政策制定者的警惕和关注(李雅君8);其三,东正教自身局限。东正教教义中重精神轻物质的价值取向、聚合性中肯定集体主义倾向和苦修传统虽然在爱国主义、道德净化等方面具有建设意义,但其贬斥商业行为、个人竞争价值和推崇唯我独尊的选民意识与务实、开放、民主的现代市场经济价值观格格不入,容易造成文化保守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从而阻滞俄罗斯现代化进程——对帝国建构的另一精神维度造成严重龃龉(陈树林69-70)。此外,宗教民族主义势力干扰、东正教组织从事不法经营活动、相关邪教组织活动猖獗等问题也成为阻碍东正教文化政策实施中不得不面对的棘手问题。因此,有的学者指出:“在普京总统的努力下,俄罗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已逐渐步入正轨,政府正在建构更符合统治需要、更具实效的意识形态,羽翼日渐丰满的政府必然降低对东正教的倚重。东正教至今仍然是标识俄罗斯民族特有风貌的精神符号,在俄罗斯民族的精神生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其对国家意识形态的影响,对民众价值取向的导引已经由社会转型初期的巅峰状态恢复至正常国家秩序中宗教生活的一种常态,进入平稳发展时期”(王春英11)。 “意识形态的理论与价值是有序社会生活的基础。一个主权国家不能没有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任何追随他国的政策、简单机械模仿别国社会的意识形态模式都是行不通的,只有强大的意识形态才能缔造出俄罗斯的光明前景,发挥俄罗斯在世界上的重要作用,摆脱国家的混乱状态”(Тенекчиян Артур Арутович)。普京时期涉及东正教的文艺政策虽不完满但昭示我们,只有在反思文化专制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坚定民族文艺传统本位,才能在多元文化环境中构建具有生机活力的国家意识形态,才能始终保持主流文化的生命力、吸引力和向心力,有力推进国家转型和现代化进程。 ①参见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РОΓРАММА:"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Е ВОСПИТАНИЕ ΓРАЖДАН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ЁРАЦИИ НА 2001-2005 ΓОДЫ" Feb 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