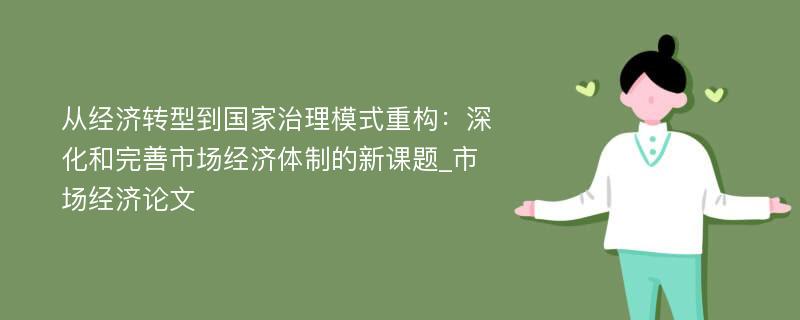
从经济转型到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转型深化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议题论文,市场经济体制论文,重构论文,模式论文,经济转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引言:观点的交锋与问题的聚焦
柏林墙的倒塌、前苏联的解体、东亚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开放,这一系列20世纪末发生的重要事件将世界上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带入一个“大转型”的时代。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转型被看作自工业化以来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①。尽管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代表了变革的一般趋势,但是转型还涉及更广泛层面的变革,如政治的转型、社会的转型,还包括文化、心理、认知等方面的变革。时至今日,转型即将走过第二个十年,但人们对于转型的认识和评价依然众说纷纭,其中,既有乐观的期许,也有悲观的批判,更不乏中肯的分析和评价。
以科尔奈为代表的转型乐观论者认为,尽管存在一些严重的问题和反常情况,但中东欧和俄罗斯的大转型取得了巨大成功。转型使得这些国家从偏离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回归正途,即民主和市场经济。在多重制度变革平行推进的条件下,转型国家以和平的方式在15~20年内就完成了西方国家曾花费几个世纪所进行的变革。因此,转型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②。
与科尔奈等人秉持的乐观态度不同,在许多学者看来,转型历经艰险,风雨兼程。其间,衰退、动荡、分裂、崩溃、苦难、不满、对抗等关键词成为对大转型的最好注解。转型的时间将明显拉长,其既定的目标也要反复修正。斯蒂格利茨、科勒德克、波兹南斯基都是转型悲观论的代表。正当批判和失望余音未了之时,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沉重地打击了几乎所有转型国家。欧洲复兴与开发银行(EBRD)的首席经济学家伯格洛夫在《2009年转型报告》中作出一番意味深长的判断:最近的经济危机使我们有必要对已有的有关转型目标和转型经济发展模式的观念作出检视,尽管危机并不意味着“转型的危机”,更谈不上改革的逆转,但是它很明显会延长转型的日程。
在转型的乐观论者与悲观论者之间,还有一批学者处于中间地带。他们认为转型是“喜忧参半”,一些国家取得了良好的转型绩效,另一些国家则在深重的危机中长期挣扎。这些学者们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指出转型出现了明显的分化趋势,这不仅体现在转型方式、道路、策略选择和经济绩效方面,而且体现在转型所形成的社会经济体制方面③。持中间立场的转型分化论者认为,由于各国在转型路径、绩效以及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因此,难以断言转型已经结束。几乎所有转型国家都要经历一个较长时期的“转型的第二阶段”④。
通过对以上三种观点的归纳,我们发现,不同观点的交锋大致聚焦在以下三个问题上面:首先,转型究竟是一个可以在短期内一步跨越的事件,还是需要经历长期的阶段性演化过程?其次,转型究竟是已经终结,还是正行之途中?最后,无论转型是否终结,所有转型国家都要经历一个不断完善其社会经济体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最为核心的任务是什么?对这三个问题的探讨成为本文的研究主题,并衍生出相应的分析思路与结构安排。
一、经济转型的路径演化与绩效解读
(一)经济转型的路径演化轨迹
转型之初,占据主导地位的转型战略主要关注改革的速度和全面性,也就是要利用转型的“机会之窗”,迅速而同步地推行全方位制度变革,实现从计划到市场的一步跨越。伴随着转型的推进,人们认识到作为大规模制度变迁的转型不可能一蹴而就,势必要经历长期的历史演化过程。
转型的动因来自于计划经济的低效率和西方市场经济的高效率给社会成员共有的传统信念系统带来的冲击⑤。信念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促使社会成员通过实验的方式搜寻新的信息结构与策略选择,并对自身的信念系统作出边际性调整。这体现为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到80年代末周而复始的改革周期。断断续续的改革并未扭转计划体制效率衰竭的趋势,社会整体的福利水平也不断下降,结果对原有信念系统造成更严重的“负反馈”冲击。最终,在80年代一系列重要事件和偶然性因素(如科技革命和全球化加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和冷战的终结;西方人权外交与传统宗教理念的大举渗透;经济增长的戛然而止等)的冲击下引发了传统信念系统的彻底崩溃,社会瞬间迈入一个“创世纪”的制度转型期。
转型启动后首先进入“制度危机”时期。由于原有的认知模式彻底崩溃,社会成员开始对新的决策规则进行集中搜寻,引发大规模的制度改革实验。这一时期由于涉及制度结构、利益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的剧烈重构,造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动荡。这在前苏东国家表现为休克疗法的全面推行以及随之出现的深度经济衰退。经济危机进一步反馈到政治领域,导致政府的频繁更替和不同利益派别的激烈争斗。然而,在社会进化选择的压力下,各种新的决策规则、信念系统和改革实验接受来自社会竞争的检验,那些比较有效的决策规则和制度安排在竞争中取胜,并通过学习、模仿在全社会扩散。当上述过程基本完成,新的主观认知模式确立,新的制度安排开始运转之时,整个制度变迁趋于平缓。这一阶段在前苏东地区表现为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主要转型国家走出转型衰退,社会动荡的局面开始平息。
在制度演化过程中存在着被称为转折点的关键时刻,这些时刻上的选择对未来的制度发展方向产生重大影响。这在转型中表现得十分明显,特别是转型初始阶段的策略选择影响了前苏东国家和中国转型路径的分化。在前苏东国家转型伊始,原有的执政党在内外压力的作用下放弃政权,导致社会主义宪法制度被取缔,西方资本主义制度被树立为转型的目标。结果,整个计划体制在瞬间被拆除,留下巨大的制度真空。在这一背景下,改革者不得不通过迅速而全面的改革来重建由新的共有信念系统为支撑的制度结构。因此,新自由主义激进转型战略备受推崇。经由该战略改造的经济体制必然沿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发展。中国在转型初始阶段的最大差异在于共产党保持了对国家强有力的领导,坚持了社会主义宪法制度,这就为中国的转型定下基调,并为各项改革的出台创造了稳定的制度环境。这种基本的策略选择,使得中国政府始终保持了对改革方向、速度的有力调控,稳健有序地将市场化不断推向深入。社会主义宪法制度的稳定性决定了中国未来的转型方向必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中国与前苏东国家转型路径的根本差异。
由此,我们将经济转型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1)转型的准备阶段,即社会主义经济改革阶段;(2)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该阶段可进一步划分为旧体制瓦解与新体制初创、转型战略调整与转型路径分化两个子阶段;(3)转型的深化与完善阶段。标示三个阶段前后相继的标志是转型中的三个关键转折点:(1)从改革走向转型之点(转型的正式启动点,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2)市场经济体制基本确立,市场化不可逆转之点(世纪之交);(3)比较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确立之点(转型的完成点,尚不确定)。确定转折点的标准体现在四个方面:(1)体制转型目标的确立与演变;(2)制度环境的变化(政治体制、意识形态);(3)基础性制度变迁(产权制度、交易制度和宏观管理制度);(4)经济发展状况的变化(经济结构调整、经济运行机制变化、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经济开放程度提高)⑥。对经济转型进行阶段性划分在于从长期历史过程中来寻找转型的一般规律,这并不意味着忽略不同国家转型路径的差异,而是在转型的共性特征基础上比较不同国家转型路径和绩效的个性差异。
(二)经济转型的绩效解读
转型初期,经济学家将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理论化为两阶段模型。在第一阶段,面对自由化政策的实施,一些技术落后,缺乏市场需求的企业、产业被淘汰,沉淀的资源被释放出来重新配置,产出可能出现一定的下降。当第一阶段的消极重组结束后,经济将进入积极重组阶段,投资开始扩大,企业重组加快,新的商品和服务进入市场,这将带动经济走出萧条⑦。然而,与乐观的预期不同,许多国家陷入严重的“转型衰退”之中,期盼已久的积极重组和经济增长迟迟没有到来。在转型的第一个十年间,中东欧平均产出下降时间为3.8年,平均累计的产出缩减幅度达22.6%;在独联体国家,产出下降更为严重,平均产出下降时间达6.5年,平均累计的产出缩减超过50%。前苏东国家整体的经济衰退程度,超过了“大萧条”时期西方国家的衰退程度⑧。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经济增长总算在前苏东国家出现。然而,这种增长究竟是对前一时期急剧下降的产出水平的自然反弹,以及因持续走高的国际资源价格带来的短期红利,还是经济体系内部已具备了实现持续增长的机制,仍是有争议的话题。近期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上述地区出现了明显的负增长,这些都给转型国家实现持续增长的前景增添了不明朗的色彩。
在所有转型国家里,中国是极少数的正面例外。自1978年以来的30年间,中国平均GDP增长率超过9%,按可比价格计算,2007年的GDP是1978年的15.1倍⑨。转型期中国经济增长的波动幅度较小,没有损害经济长期增长的潜力。伴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大和增长质量的改善,民众的福利水平也不断提高。对于明显拉长的转型衰退,以及经济增长分化原因的解读是转型经济研究领域讨论最为热烈的话题,并已形成了三种占据主导地位的解释范式。
1.初始条件决定论。这种观点认为,转型经济绩效可以由转型国家的初始条件加以解释,初始条件主要包括传统体制下形成的经济发展水平、经济结构、制度结构乃至政治、社会、文化和历史条件。“休克疗法”之父萨克斯是这一范式的重要代表⑩。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也吸收了这种观点。
世界银行将初始条件划分为三组因素:结构因素;经济扭曲因素;制度因素。通过回归分析发现,这三个合成指数可以解释转型国家1990~1994年平均增长率的51%,但只能解释转型前十年平均增长率的41%(11)。可见,初始条件对转型初期的经济绩效产生了较大影响,特别是经济结构、制度结构的扭曲程度越严重,面对市场化的逆向冲击,产出缩减幅度也越大。但仅凭初始条件并不能完全解释整个转型期的经济绩效,特别是不能解释经济恢复中产生的绩效分化,初始条件与转型绩效之间不存在完全对应的线性因果关系。
2.转型方式(或策略)决定论。这种观点认为,转型绩效受不同国家采取的转型方式的影响。相关研究特别关注为何休克疗法造成出乎意料的衰退。比较经典的解释是由布兰查德和克莱默提出的“非组织化”模型。他们认为,在计划体制中,企业依赖单一供应商提供关键生产要素。快速市场化导致投入—产出体系全面解体。供应商与买方要在新的环境中重新签署合同。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和不完全契约问题,谈判破裂的可能性激增。结果,专业化的生产链条发生断裂,产出必然急速缩减。由于转型国家市场发育不完善,发达市场经济中能够缓解这些问题的机制(如声誉机制)在转型国家并无用武之地(12)。
与激进市场化策略不同,渐进市场化的优势就是在保持传统体制的基本生产结构和存量资产不发生大规模崩溃的前提下促进市场部门的发展,以确保产出的稳定性。渐进市场化的好处还体现在政治层面,那就是减轻了改革的阻力,放松了事前的政治约束;同时便利了改革实验和事后纠错的机会,也放松了事后的政治约束(13)。渐进式改革还有助于个人和组织的适应性学习,避免了信息超载和信息损失,这些都是“休克疗法”不可避免的(14)。
转型方式决定论将对转型绩效的解释从历史、传统推向现实的政策选择。但与初始条件论相似,转型方式决定论在解释转型初期的绩效方面能发挥更大作用,但不能完全解释整个转型期的绩效变动。另外,激进转型论者与渐进转型论者都能举出各自成功的案例,如波兰代表了前者,中国代表了后者。这就使得转型方式决定论在政策层面可能得出模棱两可的建议。激进转型论者建议迅速推进全面的市场化改革,以跨越非组织化的鸿沟;渐进转型论者则始终对激进转型提出质疑,主张稳健有序的改革。
3.制度相关论。这种观点认为,转型绩效的差异在于转型国家能否构建一套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有效制度安排。在对转型绩效的研究中,制度分析越来越突显其重要地位。在理论层面,罗兰将演进制度主义作为与“华盛顿共识”并列的转型经济研究范式。在经验层面,制度对转型绩效的决定性作用也得到明确的检验。波波夫对1989~2005年间28个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及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最终结论是:导致转型衰退时间拉长、程度加深的重要原因是制度崩溃,即国家无法有效实施保护产权、维护法治的各项功能。制度崩溃程度的差异也是导致转型绩效分化的重要原因(15)。坎普斯和柯里斯利对转型经济增长的研究也证明了制度崩溃论的有效性(16)。
对于转型国家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学界也有争议。一些学者比较关注支撑市场经济的正式制度。另一些学者比较关注传统、习俗、文化、心理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17)。还有一些学者从中国经验中得到启发,开始关注一些过渡性制度安排的重要意义(如政府分权;乡镇企业;财政双轨制;价格双轨制等)(18)。制度相关论大大提高了转型经济研究对现实的解释力和政策建议的有效性。但制度相关论也存在不足之处。虽然大量研究基本明确了建立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矩阵”,但对于如何形成这些制度,我们依然知之甚少。随着博弈论的引入,人们更确信制度是一个长期自发演化的过程。然而,转型是“时不我待”的事情,单纯依靠自发演化的力量难以满足转型世界的迫切需求。即便在没有现成有效制度的条件下,转型国家仍需要一种维系基本社会经济秩序的结构与力量。这就引出我们对转型绩效加以解释的第四种观点——国家治理论。
转型是政府理性构建与民间自发演化相互结合的过程。政府作为制度变迁的推进器、社会秩序的稳定器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制度崩溃论的根源是政府治理的失败与国家治理的崩溃。政府治理失败的主要问题在于政府能力耗竭,这是导致转型绩效分化的重要原因。不论对初始条件的准确把握,还是对转型方式的有效选择,都与政府的作用和能力密不可分。政府目标偏好的灵活调整,角色与行为的适应性转变,对改革策略的明智选择,对社会秩序的有效掌控,都是确保市场化稳步推进,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政府能力构建取决于多种因素。除了政府内部必须保持结构完整、权力适度集中外,更依赖于政府与经济和社会的互动交流。因此,一种强政府(19)主导下的政治、经济及社会互惠共生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成为跨越转型鸿沟,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性要素。
二、经济转型深化阶段新的趋势和特征
世纪之交,转型进入第二个十年,转型国家的内部与外部环境发生了许多明显变化。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许多转型国家扭转了经济持续下滑的局面,经济开始复苏和持续增长。截至2008年,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经济总量均已超过转型前的水平,2008年该地区的平均实际GDP水平超过转型前的56%。俄罗斯也从1999年开始恢复了经济增长,1999~2008年间的平均增长率达到6.82%;截至2008年,俄罗斯的实际GDP超过转型前8个百分点。在东南欧、东欧和高加索、中亚地区,经济复苏的势头也比较明显(20)。在亚洲转型国家中,中国持续的强劲增长成为引领世界经济的火车头。
从制度改革进程来看,市场化在转型国家得到持续推进。根据EBRD的转型指数,在转型的第一个十年结束时,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市场化改革就已处于转型国家前列;在转型即将走过第二个十年时,这种领先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在俄罗斯,与第一个十年相比,市场化程度也得到提高,这在企业重组、贸易和外汇体制、银行改革和利率自由化、证券市场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基础设施改革等领域表现得比较明显。在东南欧一些国家,随着国内政治经济趋于稳定,市场化速度也开始加快。尽管在EBRD的转型指数中没有对中国这一亚洲最重要转型国家的市场化进行测度,但根据国内学者的评估,中国在世纪之交的市场化水平已超过60%,正处于从初级市场经济向高级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中(21)。中国已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支持市场经济运行的产权制度(公有制为主体的多元混合所有制结构)、交易制度(包括产品、要素市场在内的完整市场体系)以及宏观管理制度(运用财政、货币政策以及相关法律手段调节宏观经济运行和收入分配)基本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开始发挥基础性作用。
基于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转型的总体进展,2004年,欧盟接纳了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作为欧盟成员国;2007年又吸收了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入盟。接受中东欧加入欧盟反映出国际社会对这些国家转型成效的认可。鉴于俄罗斯从90年代后期开始的经济增长和市场化进展,美国和欧盟相继承认了其市场经济国家的地位。中国则于2001年加入WTO,成为对世界经济发挥举足轻重作用的大国。这些都意味着转型国家已深深融入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外部世界的影响日益同其内部的市场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市场化不可逆转基本成为公认的事实。
鉴于转型国家的上述重要变化,对转型是否完结的争论再度出现。从2004年开始,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每年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中,“转型国家”(countries in transition)这一分类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emerging market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前苏东转型国家均被归入这一新的分类中。无独有偶,世界银行1990年创刊并定期发行的介绍转型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杂志《转型通讯》(Transition Newsletter)也于2004年更名为《超越转型》(Beyond Transition)。据称更名的原因在于充分反映转型国家所处的环境已发生了极大改变。这也透露出国际上对待转型的一种新看法,即转型已经完成或接近完成。
应当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判断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处于第一阵营的“转型明星”——中东欧国家而言的。如果将视野扩大到所有转型国家,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一个差异性极大的世界。尽管加入欧盟标志着中东欧在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以及融入欧洲和世界经济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在东南欧、俄罗斯等前苏联地区,无论是制度改革、结构调整还是经济发展水平,都离真正的市场经济仍有很大距离。在这些地区,一些国家仍然没有结束痛苦的转型衰退,诸如转型性失业、实物经济、非正式经济等转型特有的问题也没有消失,更不用说建立起完善的公司管理制度、金融体制、强有力的政府治理和现代公民社会这些更深层的制度构建和国家治理问题了。即便是已加入欧盟的中东欧国家也依然面临着追赶欧盟老成员国的任务,而且它们已经建立起的市场经济体制尚不稳固,在面对内外冲击时依旧显得十分脆弱。因此,所有转型国家都要经历一个深化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毕竟完全的市场经济不等于完善的市场经济,初级的市场经济也不等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其间仍然有巨大的鸿沟需要通过深入细致的制度构建、结构调整才能得以跨越。
当前,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和经济危机对大多数转型国家造成严重冲击,这进一步暴露出转型经济体(特别是前苏东地区)内在的不成熟性、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这场经济危机预计将导致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2009年的平均实际GDP下降3.6%。其中,波罗的海三国受到的冲击最严重,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三国的GDP将分别下降13.2%、16%、18.4%。在东南欧、东欧和高加索地区,平均的经济增长率下降更加明显,分别为-6.2%和-8.7%。在俄罗斯,持续10年的经济增长也发生逆转,2009年预计产出下降达-8.5%。唯一的例外是中亚地区,2009年预计将有0.8%的微弱增长。前苏东转型国家2009年平均GDP增长率大约为-6.2%(22)。经济危机的影响不仅可能使得转型进程进一步延长,而且也需要对原有的转型目标、发展模式、改革战略作出调整。
转型之初,对于选择何种市场经济作为转型目标存在多种潜在的可能性。但在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公共选择过程中,一种“不带任何修饰语的”自由市场经济脱颖而出,成为前苏东国家向往的转型目标。这种市场经济实质上是一种主张最大限度的自由竞争,最大规模的私有化和私人部门发展,最开放的商品、资本要素流动,最小限度政府干预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显然,这不过是以美、英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另一版本。而且,在通向这种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一些中东欧国家的自由化改革甚至超过了老牌的市场经济国家。然而,过度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不仅在转型中引发了严重危机,而且在全球资本主义体系遭受重大冲击的今天又显得极度脆弱。在后危机时代,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模式的争论已在全球展开,转型国家也同样面临深刻的反思:经济转型不是单纯地创建市场,并将发展经济的责任完全从政府转移到私人部门,它同样需要发展政府的特定社会经济职能,特别是改进政府与私人部门的互动关系。危机的发生还突显了支持市场运行的制度和政策的重要性,特别是金融部门。尽管这未必意味着更多的规制,但可以肯定的是转型需要更好的规制(23)。显然,这意味着“无为政府+大私有化+自由市场+金融创新+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范式将作出必要的修正。
其次,转型国家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也需要进行重大调整。在新自由主义转型战略诱导下,前苏东国家出现了两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发展模式。一种是以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为代表的外向型的发展模式;另一种是以俄罗斯和中亚为代表的资源依赖型的发展模式(24)。这两种依附性极强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弊端在当前的危机中暴露无余。
在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外资流入和外贸增长是转型中的显著特征。对外开放与加入欧洲的经济整合过程成为推动这些国家制度改革与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该地区已形成了一种对外依存度极高的经济体系。在中东欧及中亚地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94年的20%上升到2008年的50%,比东亚和拉美发展型经济体高出10~15个百分点。这一地区所持有的外汇资产和债务总额占GDP的比重也在2008年达到30%,这一比例是东亚发展型经济体的两倍;在欧盟新成员国和克罗地亚,这一比例甚至高达45%(25)。与之相应,中欧和波罗的海国家在前期的转型中还形成了企业和银行的大量股权被外资持有的局面。过高的对外依存度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增加了这些国家遭受外部经济风险冲击的几率和严重程度,加之这些国家本身的市场经济制度尚不成熟,因此对外部风险的抵抗和吸纳能力十分薄弱。这一点在当下金融危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危机在中东欧转型国家的扩展主要由两股相互强化的力量推动。一是美国、欧盟金融市场的崩溃蔓延至中东欧国家,引发了这些国家的银行、资本市场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动荡。二是发达国家因经济衰退大量削减进口,这对于严重依赖欧美市场的中东欧国家而言,是对实体经济更沉重的打击。导致中东欧国家面临上述困境的深层次原因则来自于其采取的转型战略和路径。中东欧国家一向被看作忠实推行“华盛顿共识”的“转型明星”,不仅在转型初期严格地执行了价格自由化和宏观稳定政策,而且大刀阔斧地推行大规模私有化并积极融入欧洲整合进程。大规模私有化不仅导致本国企业、银行大量为外资所有,而且使私有经济部门在GDP中的比重异常升高。大量新兴私人企业的发展需要庞大的资金,这进一步诱导银行部门过度发放信贷,相应的金融衍生品和资本市场的泡沫开始膨胀,整个金融体制的系统性风险增加。为了迅速追赶欧盟成员国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实现“回归欧洲”的梦想,中东欧国家还增大了外汇债务的持有量,以刺激消费和出口,而基于本国内需的力量一直弱小,这进一步增加了整个经济体系的脆弱性。尽管危机的冲击不可能从根本上逆转中东欧国家市场化、对外开放和金融整合的进程,但很可能使这一进程放缓。因此,在EBRD(2009)对中东欧进行的转型评估中,几乎各个领域的改革指数都没有明显提高,甚至在某些国家的某些领域(特别是金融部门),市场化改革指数还有所降低。
俄罗斯代表的资源依赖型经济是另一种带有依附性的经济发展模式。俄罗斯原本是一个具备高度工业化生产能力的国家。但是,伴随着激进的经济转型,特别是大规模私有化,原有的工业体系迅速瓦解,企业的生产能力、技术水平大幅下降,以至于出现了学者们所说的“去现代化”、“去工业化”的趋势。结果导致俄罗斯只能根据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优势”原理,大量出口储量丰富的石油、天然气等资源产品来换取外汇,以满足发展本国经济、提高民众生活水平的需求。这意味着俄罗斯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的阶梯上出现了很大的退步,从一个工业大国走向一个资源出口型的低度工业化国家。对资源出口的依赖必然加剧俄罗斯对整个国际经济体系的依附性以及本身经济体系的脆弱性。这在当下的经济危机中得到有力证明。当前俄罗斯的经济衰退首先来自于全球资源商品需求缩减、价格下跌对其出口部门的打击,这直接影响到国内资源生产部门的投资和产出,进而严重动摇了经济增长的基础。这种冲击还连带影响到其他工业部门的发展,结果导致生产资本消耗巨大,但更新速度却极为缓慢,从而使俄罗斯陷入整体工业能力严重下滑的陷阱之中。俄罗斯在头十年的大规模私有化、自由化和对外开放过程中还形成了一套极度脆弱的金融体系。银行和金融机构出于盈利需要,将大量信贷投放于出口部门和其他金融投机领域,而对本国实体经济发展的融资功能则极其有限。由于出口部门的收益因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锐减,银行等信贷机构的负债基数也迅速增长。2005~2007年银行部门的负债总额以每年40%的速度增长,结果也增加了整个经济系统的不稳定性(26)。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俄罗斯出现了出口下降、银行和金融机构倒闭、资本外逃加速、经济增长大幅下滑并存的困难局面。这意味着俄罗斯在后危机时代必然要经历一个痛苦的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过程。
与中东欧和俄罗斯相比,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更具独特性。改革开放前,中国仍处于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阶梯较低的层次上。伴随着市场化和国际化的推进,中国正在利用其廉价的劳动力和“比较生产率优势”沿着发展的阶梯迅速爬升。尽管中国在许多核心部门和领域还缺乏自主创新能力,但大多数工业品不仅能实现自给,而且在国际市场上还具有相当的竞争力。虽然中国还不是一个制造业强国,但是制造业大国的桂冠则是实至名归的。这使得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较高的自主性。另一方面,虽然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和对外开放程度已经取得很大进展,但以西方的视野来观察,中国经济在许多方面具有“混合”性的色彩。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业部门市场化程度高,非农业部门市场化程度低,特别是由于没有采取大规模私有化,在公用事业、重工业、金融部门中国有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2)虽然制造业、外国直接投资和技术引进的国际化程度大幅提高,但要素市场的开放程度仍比其他国家低,如银行业、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等;(3)金融部门和金融市场的发育水平也较低,政府控制了债券、股票和银行市场;(4)政府与私人部门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政府仍主导着市场的运行(27)。基于上述特征,许多西方学者不知道究竟应将中国的发展模式归为哪种类型,只能冠之以“混合经济”、“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些多少带有贬义色彩的名称。然而,正是这种不彻底的市场化、不彻底的国际化的体制与发展模式,却在面对外部冲击时表现出比中东欧国家彻底开放型的市场经济模式更强的应对能力。一方面,对银行业、资本市场、外汇市场的管制将国际金融体系崩溃对本国金融体系的不利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内;另一方面,当危机从虚拟经济层面扩展到实体经济层面时,国家又可以通过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方案来缓解实体经济受到的冲击,确保增长和民生。尽管在后危机时代,中国面临着多方面的制度改革和结构调整任务(平衡外需与内需的关系,调整消费与投资的结构,强化金融部门及监管制度改革,提升产业结构和竞争力,协调经济、社会与环境发展等),但政府主导型的市场化与经济发展模式仍将发挥其潜在的优势,同时也为其他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提供了重要借鉴。
由此可见,对绝大多数转型国家而言,转型已经终结的论调是不符合事实的。相反,转型的道路仍然在向前延伸,转型国家实际上已经步入一个转型深化的崭新阶段。由于原有的制度改革并未结束,而新的困难又不期而至,因此,转型国家显然又再次站在了十字路口,面临着艰难的抉择和挑战。
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与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构建
转型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能使生活水平长期得以提高的繁荣的市场经济”(28)。达致这种完善的市场经济不仅需要经济层面的变革,更需要将变革深入扩展到政治和社会领域,这意味着经济转型深化势必带动整个国家治理模式的变革。经济的长期繁荣,民众福利水平的持续提升,需要政府、市场及社会的持续协调和互动。就转型国家而言,建立政府、市场、社会互惠共生的有效国家治理模式,是转型深化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任务,也是促使转型国家从严重的分裂与衰退走向持久的稳定与发展的制度基石(29)。
如前所述,造成转型绩效巨大波动和分化的重要根源在于制度崩溃的长期影响,制度崩溃的背后体现出转型中的国家治理失败。这种失败表现为政府失灵、市场失灵以及社会失灵相互影响、相互强化的系统性危机。
制度崩溃肇始于政府能力的过度削弱,即政府提供有效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能力急剧下降。具体表现为政府无法有效实施其规制,无法征收足够的税收,不能有效保障产权和契约的执行,更无法有效约束寻租、腐败、掠夺等机会主义行为。各种形式的“弱政府”成为转型国家实现最终现代化目标的主要政治障碍。转型国家弱政府的形成源于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1)激进的民主化引发剧烈的政治斗争,整个政治体系趋于解体,政府功能的衰竭自然不能避免;(2)自由化和私有化对微观经济实体造成的逆向冲击使政府陷入财政危机,政府财政汲取能力下降,使其无法维持基本的官僚体系和行政系统的正常运转(30);(3)中央政府权威衰落,无法控制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地方政府蜕变为“掠夺之手”(31);(4)内部人、寡头等强势利益集团对政府实施强有力的俘获,影响公共政策的公正性和有效性;(5)官僚系统的人力资本得不到迅速更新,旧的官僚阶层无法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削弱了官僚系统的有效性。
与“斯密主义”的“看不见的手”这一经典范式的预期不同,政府的削弱和退出并未被强有力的市场所填补。相反,由于缺乏政府的必要规约和扶持,一种功能紊乱和效率低下的畸形市场经济应运而生。价格体系的急剧调整导致资源配置混乱,企业资本短缺、技术退步,整个经济体系经历了剧烈的去现代化过程;正常的交易体系无法形成,大量低效的交易方式(如关系网络、以物易物)持续存在;非正式经济、影子经济、地下经济大量滋生,市场交易的信任系统难以确立;广泛而有效的所有者阶层形成缓慢,与之相应的是对国家和私人财产的严重掠夺;低效的公司治理和金融体制削弱了经济发展的微观基础,增加了经济的脆弱性和系统性风险;低下的竞争力和严重的资本外逃使本国经济在融入世界经济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依附性。
政府能力的削弱还导致其无法提供有效的公共政策,发挥必要的社会整合功能,结果弱市场进一步被日趋分裂的弱社会所包围。急剧的制度变革导致维系社会的传统信念体系瓦解,价值观念分裂,社会认同减弱;社会结构急剧分化,缺乏稳定的中间阶层支持,社会出现严重的极化,面临着断裂的风险;掠夺性团体、分利性联盟联合剥夺社会,社会缺乏新的有效整合机制;传统的习俗、规范、文化等社会资本迅速耗散,私人关系网络、庇护关系等不良规则大量滋生。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转型社会呈现出严重的“碎片化”和社会失序问题。
制度崩溃集中体现出从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向市场和民主框架下的新型国家治理模式转变中的混乱与无序。超越制度崩溃与治理危机,建立有效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成为影响未来制度转型路径与经济发展绩效的决定性因素。
从目前的发展看,转型国家构建现代国家治理模式存在三种路径:
1.中东欧的新自由主义路径。这种路径最符合“华盛顿共识”的转型战略,而且由于存在一种强大的外部力量(欧盟)的影响,中东欧国家的治理模式变革更具开放性和国际性。此后形成了一种强民主体制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相结合的体制结构。在这种体制的支持下,中东欧在经历了转型初期的动荡后,政府能力得到一定的恢复(32)。
2.以中国为代表的权威主义路径。这种路径的显著特点是在政治结构保持稳定性和连续性的条件下,由具备强大权威和能力的中央政府来主动推动市场化、社会化和国际化变革进程。在此过程中,政府主动地、持续地对其目标偏好、角色定位、制度结构、治理方式进行适应性调整。最终逐步从政治、经济和社会一体化的全能主义体制中走出,初步形成了一种政府、市场和社会三元并存与互补的国家治理格局。在这条路径延伸的过程中,政府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自主性和治理能力。
3.以俄罗斯为代表的国家治理模式重构路径。这一路径更加曲折,也缺乏连贯性,因此很难用一个简单的学术化概念加以概括。转型伊始,俄罗斯效仿中东欧采取新自由主义转型模式,但是由于本国特定的体制结构、生产结构和利益结构的约束,形成了一种不完善的民主体制,以及低效的市场经济和分裂的社会结构。普京执政后,俄罗斯回归传统,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领域都强化了国家集权,但仍难以在短期内形成稳定有效的国家治理模式。因此,在俄罗斯转型进程中,政府能力衰退的问题最为突出。
转型国家的制度崩溃与治理危机,以及此后的国家治理模式分化趋势表明,无论处于何种初始条件的约束,也无论选择哪种转型方式和战略,培育和增进政府能力都是首要任务。在现代社会,虽然存在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和网络,但政府作为一个集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为一身的治理主体,对于推动制度变革和经济发展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西方国家的历史经验表明,市场经济的建立和扩展离不开政府的扶持和推动。从统一国内市场到开辟海外殖民地,从保障产权到推动产业发展和技术创新,从镇压劳工运动到改进社会保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每一步都少不了政府的身影。因此,有西方学者指出:“强经济需要强国家。”(33)然而,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出他们的政策建议时,却严重忽视了自己国家所经历的这段历史,结果自由化政策的实施导致转型国家政府能力的严重丧失。
培育和增进政府能力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也不存在绝对唯一的治理之道。但根据历史经验,我们可以提出一些构建政府能力的基本策略选择。首先,要确保政府制度和组织结构的整合度、协调性和稳定性。政府是一个制度化、组织化的公共治理主体。它的权力运行与职能行使需要在一种相互协调、紧密配合的规则和组织体系中加以完成(如宪政秩序的稳定,政府不同职能部门的相互协调)。如果政府制度结构被拆散、组织体系被分解,那么国家势必无法发挥必要的治理功能,整个社会也将陷入无政府状态。其次,要对本国的政治制度进行合理有效的构建,主要包括有效配置国家权力,完善法治建设,规范民主机制。政治制度的核心作用在于规约国家权力的运行,控制其潜在的机会主义行为,更好地发挥政府的权能。再次,改革和完善政府行政体制运行,提高其有效性,主要包括政府行政体制能否促进信息交流、控制多层级代理问题;能否更新人力资本,建立理性的官僚体系并实现政府治理创新等。这些将直接影响政府的治理成本及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最后,要协调政府与社会的关系,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政府的制度供给和公共政策是否得到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理解和支持,这将影响政府的合法性及其政策实施的有效性;二是政府在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能否抵制强势的狭隘利益集团的影响,这也将影响政府的自主性和治理能力(34)。
在提升和巩固政府能力的基础上,转型国家需要采取更加广泛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来扶持社会的发展,构筑政府与社会相互促进的治理格局。这不仅有助于稳健有效地推进市场化改革,而且能够为国家制度建设与经济的持续、均衡发展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与社会达成了一种特殊的保护性社会契约。政府提供充分就业、低质量但覆盖广泛的社会福利来确保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降低他们的社会风险。社会成员将大部分的经济社会活动权利移交给国家,并通过国有企业、集体农庄、人民公社等制度安排被吸纳和整合到行政控制体系中,形成了政治、经济和社会高度统一的社会结构(35)。在这种结构中,社会分化程度较低,贫富差距较小。经济转型使得原有的社会关系面临重构,社会分化开始加速,多元开放的社会结构也在形成中。这虽然顺应了市场化和社会化的方向,但也增大了潜在的社会风险。
在前苏东国家,激进的变革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动荡和分裂。这不仅体现在生活水平急剧下降,贫富差距迅速扩大等显性层面,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人们对待转型的不同态度这一隐性的主观层面上。伴随着严重的转型衰退,前苏东国家的民众对改革的支持力度都不同程度地下降。在对待一些具体改革问题上,受益者与受损者的观点更加对立。在俄罗斯民众如何看待市场化改革的合法性问题中,绝大多数富人反对重新分割所有权,但三分之二的穷人支持重新分割所有权(36)。这种严重的分歧显然不利于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而且,由于社会的抗拒,导致了新生的市场制度无法协调有效运转。社会分裂和对改革的认同差异,更加深刻地反映出转型社会的治理危机。
与前苏东国家相比,中国在前期的转型中将社会结构变动的风险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但随着转型的深化,社会发展进程中也累积了一些矛盾,增大了潜在的社会风险。改革的推进必然导致社会利益分化重组加快。传统的和新生的利益集团(如行业和行政垄断部门)会利用权力资源干预政府决策,延缓关键领域的改革。同时,转型中形成的“弱势群体”(农村中的剩余劳动力、城市中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其他贫困人群等)将成为改革成本的主要承担者,如不予以适当补偿,必然削弱支持改革的社会基础。此外,在前期转型中,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衡,产生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城乡、地区发展不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等问题。这些都增加了转型中的不稳定因素。
化解社会分化和发展失衡带来的风险,将转型深入推进,需要政府对转型战略适时调整,为跨越转型鸿沟蓄积动能。政府也要对发展理念作出调整,即在关注市场化的效率诉求的同时,更加关注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使发展的成果惠及全民。在这方面,中国政府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显然是转型国家中的良好范例,对其他转型国家具有借鉴意义。
转型与发展理念的转变必然要求政府深入推进扶持社会的公共政策。在前期的转型中,几乎所有国家都面临着社会政策匮乏的问题。原有的社会福利体系被打破,新的福利体制改革漏洞百出,结果使得社会大多数成员的福利水平降低。这种状况在当前的危机时期表现得更加明显。经济危机给原本存在的贫困阶层造成更大的冲击。一是失业率迅速增长。在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俄罗斯、斯洛文尼亚和乌克兰,注册失业人口增长幅度在20%~40%之间。二是贫困人口数量也大幅度增长。在俄罗斯,贫困人口的比例在2008年第4季度至2009年第1季度间几乎增长了三分之一,有六百多万人处于贫困状(37)。对此,转型国家必须扩大社会支出的力度,通过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公共教育、社会救济、反贫困等综合性的社会政策来构筑起促进社会稳定的安全网络。此外,还需要对社会政策进行整体设计,使其相互配套。
在推行积极的社会政策的基础上,转型国家还需要培育成熟、理性、开放的利益整合型公民社会。随着市场化和政府治理方式的变革,公民社会的出现是一个长期的必然趋势。大多数研究文献都对公民社会的积极作用进行了阐释。如公民社会可以提高民众对制度改革和国家治理的参与程度,提高公共政策的透明度和有效性;可以改进公共物品供给质量,并能抑制政府权能过度扩张;可以培育社会资本,增进信任。这些都有助于克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确保转型兼顾效率和公正两大终极目标。然而,公民社会也并非没有缺陷。如果政府和社会没有采取有效的互动机制和构建方式,公民社会的发展也可能会加剧社会分裂,并削弱政府治理社会经济的能力。
在前期的转型中,许多国家采取了一种消极的公民社会建构方式。政府试图通过自己的迅速退出等待公民社会的自发型构。同时,新自由主义转型战略又推崇一种屏蔽社会、精英主导的改革策略,疏离了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结果导致政府的改革政策得不到社会的充分参与,也不能得到社会的理解和支持,大大降低了政策的有效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导致了政府与社会的对立、对抗。由于公民社会发育薄弱,往往被狭隘利益集团裹挟,成为俘获政府的工具。德塞对俄罗斯的研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她对俄罗斯当年的改革设计者盖达尔、丘拜斯、亚夫林斯基等进行了深入访谈,并归纳出叶利钦时代改革的四大特点:(1)叶利钦及其团队蓄意避免与共产党等左派立法者进行协商;(2)改革者大多不关心公众对改革的参与和接受程度,也不关心改革对失利群体的分配性效应;(3)叶利钦团队忽视了支持经济转型的不充分的制度基础;(4)叶利钦成功终结了旧的经济体制和政治模式(38)。可见,“华盛顿共识”主张的精英主导、避免社会参与的转型战略,与自由派改革者迅速瓦解旧体制的迫切需求奇妙而又复杂地相契合。这种改革模式导致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结盟,共同瓜分改革租金、剥夺社会财富、削弱公民社会的力量,从而使改革路线偏离社会民众,更加依赖于特殊利益集团。
转型国家构建公民社会大致可以采取两种模式。一种是自由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强调公民社会与政府的二元分立,公民社会的重要功能就是制约和对抗政府以保障个人权利不受侵犯。另一种是社团主义模式。这种模式强调政府与社会不是相互竞争的关系,而是相互合作的关系。政府与社会都不是自足的,只有在相互扶持、相互补充的过程中才能实现共同发展。社团主义虽然承认社会存在多元利益,但更加强调多元利益的和谐、共容和稳定的秩序(39)。在转型初期,许多前苏东国家试图遵循自由主义模式,建立一个绝对自由、自主的公民社会,但结果不仅导致了经济发展的凋敝,也造成了公民社会自身的功能变异与整合失灵。因此,未来的公民社会构建要更多地倾向于一种政府与社会互动交流、互惠共生的社团主义模式。为此,政府在构建公民社会的过程中不仅要通过完善法治建设保障公民的权利,为公民个人、组织创造自主发展空间,激励他们的自主性与自治能力;同时,也要指导、规范公民社会的发展,并综合运用政治、经济和社会政策,消除体制变革造成的社会裂痕,遏制权贵阶层对社会的掠夺,实现社会利益的有效整合,增进社会团结与稳定。
在刚刚过去的2009年11月9日,当西方大国在欢庆柏林墙倒塌20周年之时,整个世界尚未从全球经济危机的冲击中完全苏醒过来。重建、变革、调整已经成为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主旋律。对于经历了20年巨大变迁的转型世界而言,对此的理解恐怕要比世界其他地方更为深刻。
尽管市场与民主并非是永远遥不可及的目标,但是通向这一理想目标的道路却复杂而曲折,转型所需要的时间也将会更长。20年的变革历程表明,转型并非一个可以瞬间一步跨越的事件,而是需要经历一个阶段性演化的历史过程。不同的初始条件、策略选择以及各种偶然性因素的交互作用,必然使这一演化过程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轨迹。最终结果很可能是并不存在一套绝对具有普适性的最优体制模式,相反,不同国家需要根据本国国情来寻找更为有效的制度结构与治理模式。这也必将使全球市场经济体制家族更具多样性的特征。
根据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总体状况加以判断,主要转型国家已先后经历了转型的准备阶段、转型的启动和正式推进阶段,并且已经步入转型的深化阶段,在这一阶段转型国家面临着新的内部和外部环境。尽管主要的转型国家已经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仍然面临着通过更加全面、深入、细致的制度改革与结构调整,以建立起一种能够促进社会长期繁荣的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重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转型国家不仅需要对原有的市场体制模式、经济发展模式作出重要调整,更需要将变革深入推进到支持市场经济有效运转的政治和社会领域。其核心内容包括建立一个具备充分有效治理能力的强政府,以及一个具备利益整合功能的现代公民社会,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政府、市场及社会互惠共生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
注释:
①Erik Berglof and Gerad Roland (eds.),The Economics of Transition:The Fifth Nobel Symposium in Economic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p.1.
②参见Janos Korna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of Central Eastern Europe:Success and Disappointment",Economics of Transition,2006(14); Andrei Shleifer and Daniel Treisman,"A Normal Country:Russia after Communism",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2005(19).
③参见Erik Berglof and Patrick Bolton,"The Great Divide and Beyond:Financial Architecture in Transitio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2002(16); David Lane and Martin Myant(eds.),Varieties of Capitalism in Post-communist Countries,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7.
④Wladimir Andreff,"Would a Second Transition Stage Prolong the Initial Period of Post-socialis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to Market Capitalism?"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4(1).
⑤对经济转型路径演化的分析受到了比较制度分析学派的制度演化理论的启发,参见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版,第234~247页。
⑥对转型中的转折点及阶段的划分,参见景维民、张慧君等《经济转型的阶段性演化与相对市场化进程研究》,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第82~85页。
⑦叶夫尼根·雅辛:《俄罗斯走向市场经济之路》,载冯绍雷、相蓝欣主编《俄罗斯经济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23页。
⑧World Bank,Transition-The First Ten Years: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Washington D.C.,2002,p.5.
⑨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
⑩Jeffrey Sachs and Wing Thye Woo,"Structural Factors in the Economic Reform of China,Eastern Europe,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Economic Policy,April 1994.
(11)World Bank,Transition-The First Ten Years:Analysis and Lessons for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Washington,D.C.,2002,pp.11~20.
(12)Oliver Blanchard and Michael Kremer,"Disorganization",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97(112).
(13)热若尔·罗兰:《转型与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7~53页。
(14)Joseph E.Stiglitz,"Whither Reform? The Years of the Transition",Keynote Address to the World Bank Annual Bank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Washington,D.C.,1999.
(15)Vladimir Popov,"Shock Therapy versus Gradualism Reconsidered:Lessons from Transition Economies after 15 Years of Reforms",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2007(49).
(16)Nauro F.Campos and Fabrizio Coricelli,"Growth in Transition:What We Know,What We don't,and What We should",William Davidson Working Paper,2002,No.470.
(17)Gérard Roland,"Understanding Institutional Change:Fast-moving and Slow-moving Institutions",Studies in Comparativ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2004(38).
(18)Qian Yingyi,"The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of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ld Bank's Annual Conference on Development Economics,Washington,D.C.,28-30 April 1999.
(19)强政府既不意味着大政府,也不意味着无限政府,实际上这两种政府都不免会出现政府能力衰竭的问题。强政府的内核在于政府具备充足而有效的制度供给和秩序治理能力。
(20)Transition Report 2009:Transition in Crisis,参见http://www.ebrd.com/.
(21)参见李晓西等《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2003年版。
(22)Transition Report 2009:Transition in Crisis,参见http://www.ebrd.com/.
(23)Transition Report 2009:Transition in Crisis,参见http://www.ebrd.com/.
(24)景维民、孙景宇等:《转型经济学》,经济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230页。
(25)World Bank,Turmoil at Twenty:Recession,Recovery,and Refor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Overview,Washington,D.C.,2009.
(26)A.纳沃伊:《2008年俄罗斯经济危机特点分析》,《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9年第4期。
(27)阿萨尔·林德贝克:《转型期中国的经济社会互动关系》,载《比较》第33辑,中信出版社2007年版。
(28)世界银行:《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29)我们将国家治理模式界定为在一国领土范围之内,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相互耦合所形成的一种整体性的制度结构模式。政府、市场与公民社会各自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规则、组织和治理机制构成的制度系统,它们共同维系着一个国家整体的秩序治理,并在此基础上协调资源配置,促进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30)Lawrence King and Patrick Hamm,"Privatization and State Capacity in Postcommunist Society",William Davidson Institute Working Paper,2005,No.806.
(31)Olivier Blanchard and Anderei Sleifer,"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China versus Russia",NBER Working Paper,2000,No.7616.
(32)对转型国家政府能力的定量测度,参见Jeffery B.Miller and Stiyan Tenev,"On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Transition:The Experiences of China and Russia Compared",Comparative Economic Studies,2007(49).
(33)琳达·维斯、约翰·M.霍布森:《国家与经济发展——一个比较及历史性的分析》,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3~4页。
(34)Cynthia Roberts and Thomas Sherlock,"Bring the Russian State in:Explanations of the Derailed Transition to Market Democracy",Comparative Politics,1999(31);弗朗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3~32页。
(35)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孙立平:《社会转型:发展社会学的新议题》,《开放时代》2008年第2期。
(36)俞可平主编:《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中国与俄罗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37)World Bank,Turmoil at Twenty:Recession,Recovery,and Reform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and the Former Soviet Union,Overview,Washington,D.C.,2009.
(38)Padma Desai,"Russian Retrospectives on Reforms from Yelsin to Putin",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2005(19).
(39)张静:《法团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
标签:市场经济论文; 经济转型论文; 经济论文; 中国模式论文; 治理理论论文; 绩效目标论文; 绩效反馈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重构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经济增长论文; 经济学论文; 苏东论文; 休克疗法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