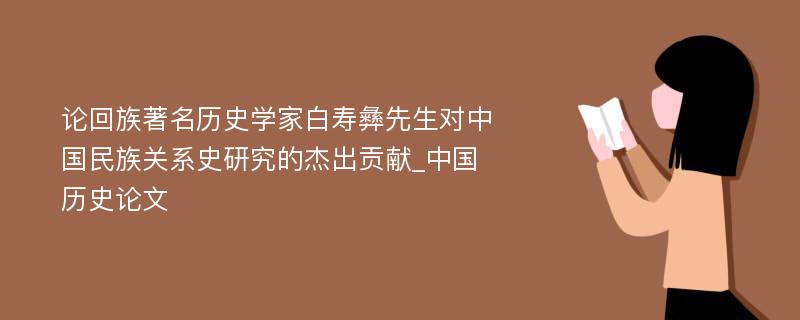
谈著名回族史学家白寿彝先生对我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杰出贡献,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回族论文,史学论文,史研究论文,著名论文,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D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14-(1999)02-0063-05
白寿彝先生是我国当代享有盛誉的著名回族学者、历史学家。在他近70年的学术生涯中,在多学科领域辛勤耕耘,于中国交通史、中国伊斯兰教史、回族史、中国通史、史学理论、中国史学史、中国历史文献学、中国民俗学、中国民族关系史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提出了许多颇有价值的卓越见解,对有关学科的开创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拟就白先生在我国民族关系史研究方面的杰出贡献,谈些个人的学习体会,谨作为晚辈献给白先生90华诞的一份薄礼。
一、应当把民族关系史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
白寿彝先生是当代治中国通史的专家,具有深厚的中国史基础。他主张应当在研究中国通史的基础上研究民族关系史,尤其要把民族关系史放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而不能孤立地看各个民族。早在80年代初期,他就撰写了《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的著名文章,明确提出:民族关系史的研究“重要的是要站得高,要从整个历史发展看问题。”还说:“一个是横着看,看在全国范围里起了什么作用,产生了什么影响;再一个是纵着看,看上下几千年,看一件事情是怎样发生的,怎样发展的,将来又如何,这样就有意义了。”从这样一个基本思路出发,他无论在主持编纂大型《中国通史》时,抑或在从事历史教学中,总是注意把民族关系史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加以考察和研究,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长期以来,史学界对我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归纳而言,大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友好合作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民族矛盾、民族纷争是民族关系的主流。对此,白寿彝先生在深入研究了中国历史上汉族和周边少数民族间关系的基础上,换了一个角度考虑问题,提出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独到见解。他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偏颇之处,因为在一定历史阶段,民族关系可能更多地表现为不同形式的友好合作,而在另一历史阶段,民族间的斗争又可能打得难解难分。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1] 民族友好合作和民族矛盾纷争都是民族关系的表现,但我们不能把民族关系完全归结为民族友好或民族矛盾。事实上,民族友好和民族矛盾这两种历史现象不但会经常转换,而且有时会以不同程度和不同形式同时并存。譬如在民族关系基本上友好相处的时期,有可能出现局部和短暂的民族冲突;而在统治阶级发动的民族战争中,也不排斥强势民族劳动人民对弱势民族劳动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的“题记”中,白先生开篇明义,对此问题阐述得更为透彻。他说:“尽管在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的民族斗争,甚至出现过不少的民族战争,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看,我国民族之间总是越来越友好。友好并不排斥斗争的存在,斗争也不能阻挡友好关系的前进。民族友好是我国民族关系史的主流。”[2]在这里, 白先生摆脱了形而上学的僵化的思想方法,不是从民族友好与民族矛盾二者之间非此即彼地进行选择,而是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考察问题,提出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是民族关系的主流。这种分析问题的独特方法,是白先生史识的过人之处,值得我们很好地借鉴和学习。
如何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发展阶段进行科学划分,也曾是史学界长期讨论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关于划分历史发展阶段的依据,论者提出过诸如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阶段斗争以及国家政权的嬗变等不同标准,但很少有人意识到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白先生匠心独具,认为在此问题上应当综合历史的多方面因素,其中包括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这样的观点,同样体现了他坚持把民族关系的发展变化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下来考察的一贯主张。一方面,少数民族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与汉族的交往;另一方面,少数民族的进步,同样是整个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从这样的思路出发,白先生非常重视少数民族的封建化。他认为,秦汉是封建社会的成长阶段,魏晋南北朝隋唐是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所谓发展阶段,其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是民族杂居地区进入了封建化。”宋元时期和明清时期,封建社会继续发展,在这两个阶段中,边疆地区和民族地区的封建化程度加深了。“事实证明,每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总是有少数民族的发展,总是有少数民族出了力量、作出贡献。同时,汉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对他们也有很大影响。这是不可能分开的。”[3] 白先生关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问题,在他主编的《中国通史纲要》的“叙论”部分和十二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中,同样有精辟而系统的论述。作为一家之言,白先生的上述观点,当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是,他认为划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阶段,应当把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历史作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加以考虑,则充分体现了他的远见卓识。
二、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也要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
研究历史,既要弄清历史事实的真象,又要对历史上的人和事作出恰当的价值判断。在后一个认识面上,史学家往往会自觉不自觉地带上自己的感情色彩,包括民族的、阶级的、个人的感情因素。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和评判历史时不带感情是不可能的,但一个优秀的史学家又必须能够超越自己狭隘的感情,以理性的精神客观地分析历史发展的进程及其后果。白寿彝先生是我国回回民族杰出的史学家,也是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我们从他的大量论著中,可以看出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研究本民族的历史,字里行间洋溢着对本民族炽热的思想感情。但他的这种思想感情又是和科学的理性精神结合在一起的。他既反对大汉族主义,也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在他的著述里,没有狭隘的民族主义感情。如他所言:“从历史上看,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汉族老大哥是带头的,但没有少数民族的发展,还是不行的。”[4] 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成为主体民族,需要有各个少数民族各方面的支持。汉族的形成是好多民族、部落形成的一个新的、大的民族。汉族不只有一个老祖,而是由好多老祖发展下来形成的。后来,汉族的不断发展,也是不断吸收各个民族发展的。同样,其他各民族的发展也同样受到汉族的影响。总之,“中国历史的发展,要靠汉族和少数民族的配合。”[5]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每当民族关系发展一步,我国的历史发展也就前进一步。”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近代化的过程,“这个时期,各民族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共同反对封建压迫,民族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6]今天看来,还是这样。 “我们现在搞现代化,如果民族地区不实现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还是很有局限的。”[7]白先生不止一次地告诫说,涉及民族关系问题, “要理解兄弟民族的思想感情”。[8] 他提出了一个十分新鲜的观点:“从整个国家历史的发展来看,凡是盛大的皇朝,没有少数民族的支持是不行的。”[9] 以汉朝和唐朝为例,都是跟少数民族搞好民族关系,得到了少数民族的支持拥护,才出现了盛世的局面。这就从民族关系的角度揭示了封建社会盛世出现的重要条件,这样的认识应当说是很深刻的。
白寿彝先生十分重视少数民族在历史上的重要作用,但他丝毫没有狭隘的民族关系情绪。他旗帜鲜明地指出:“汉族是中国历史上的主体民族”;“中国历史几千年连续不断,在世界历史上是少有的。这个功劳,汉族应居第一。如果没有汉族,少数民族做不到这一点。”他具体分析了汉族成为主体民族的历史原因和地理原因,指出汉族作为我国的稳定力量,“并不因元代是蒙古贵族的统治、清代是满洲贵族的统治而有所削弱,或受到排挤。”对于历史上少数民族领袖的“朝贡”和汉族天子的“和亲”,白先生也不带任何民族偏见地作出了实事求是的评价。他认为,封建社会时期的“朝贡”和“和亲”,不是尊卑荣辱的问题,应当看到,在这种政治外衣里边,蕴藏有各民族团结友好、全国统一凝聚的积极内容。“‘朝贡’干什么?朝‘天朝’嘛!因为‘天朝’各方面都发展得好”,边疆民族领袖得到封赠,“认为是光荣的,是‘天朝’看得起。”至于“和亲”呢,汉族封建统治者以及大多数封建史家一直看作是干弱枝强、不得已才使公主(其实不少人是宫女!)远走“边庭’、“下嫁”蕃王,认为是屈辱。其实,少数民族并不这样看,“一个少数民族领袖,为什么要娶一个汉族姑娘呢?为什么把这看作是光荣的事?他认为汉族姑娘好,汉族姑娘嫁给他是受到重视的表现”。总之,无论是“朝贡”还是“和亲”,都是少数民族“向往中原、钦慕汉族文化的反映。”白先生发前人所未发,把问题看得很深入。更深一层看,“即便是民族间战争,也或多或少反映出这种向往中原的心情。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都往中原来,为什么?还是觉得中原好嘛!”[10]白先生这种理性的科学论证,教育、感染了各族广大民众。有一位同志曾结合自身幼年随父母跟回族、朝鲜族长辈睦邻相处的儿时回忆时写道:“不管是实际的‘麻雀’材料,还是宏观的理论概括,我们都应理直气壮地、满怀热情地肯定我国各族人民友好团结的历史传统。这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方面,对我们搞好民族工作和民族研究的同志来说,也应是一种有益的思想感情因素。”[11]这是受到白先生民族研究直接影响的结果。
三、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要与民族史结合起来
早在50年代初期,白寿彝先生就率先提出把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结合起来的主张。他说:“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不只可能宽广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并且还深刻了、强化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内容。这一方面是通过爱国主义思想教育,而更加巩固了各族人民的团结;又一方面是由于各族人民团结的更加巩固,而大大提高了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效果。所以,爱国主义思想教育方在展开的今日,把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结合的问题提出来,有完全的必要。”[12]
民族史研究与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相结合是非常必要的,二者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只有从理论高度揭示出这一点,才能使我们自觉地把民族史的研究与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结合起来,而充分肯定各民族共同创造历史则是关键。
白寿彝先生亲自撰写了十二卷本《中国通史·导论》卷第一章,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讲各民族都是国家的主人,肯定了他们在创造中国历史中所占的位置,真正把通史写成多民族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纪录。白先生指出: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历史的问题,大家都认同,并且能例举许多事实和各民族所创造的业绩,但仅此还不够,还要有全面的眼光,如西藏、新疆在今天经济、文化水平发展比不上内地,从这方面说,水平比较低;而另一方面,在那样艰苦的地方,坚持建设几千年,那里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里有丰富的地下矿藏,这些值得我们佩服。有些民族小,只有一两千,有的今天刚刚摆脱渔猎阶段不久,我们都不能看不起他们,“人家是在那样艰苦的地方进行开发工作,汉族到不了的地方,他们做了工作,而且往往在国防前线。”我们要眼界放宽,这样就真正能看到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祖国的历史,即使在日常生活里都有民族交流。有这样的思想认识,就更能激发起我们对多民族国家的热爱。白先生在《谈民族史》一文中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要写多民族的统一,写各民族同汉族在相互关系上的发展,各族有各族的特点,但也离不开‘共同性’。第一点是对边疆的开发,少数民族出了很大力量。没有他们,边疆开发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在边疆地区繁衍、生息、生产劳动,经历了多少个世纪。旧的史书,把少数民族同汉族的关系,写成是少数民族不断文明化的过程,这是不对的,正是少数民族开发了那个地方。第二点是要大写我们少数民族如何捍卫我们的边疆。这两方面的材料可多可少,但内容很要紧。没有这两点,就没有今天的中国。”[13]固然汉族人口众多,经济文化发达,对少数民族有很大影响,而少数民族居地广阔,形势冲要,少数民族开发了边疆,建设了边疆,保卫了边疆。汉族和少数民族,都各有物质、精神成就。少数民族向中原地区、向中原朝廷、向汉族同胞不断供输各种物产、知识、文化、技术,汇总构建通常所说的“华夏文化”的整体内容。少数民族是在创造祖国文明的历史行程中走向发展进步的。历史的、地理的诸因素造成了各民族发展进步上的不平衡性,互相学习,取长补短,是优良的族际传统,但不等于说是汉族来“开化”少数民族,把文化“赐给”别的民族。白先生公允而精辟地指出:汉族不是“天赋独厚”,而是“得天独厚”。[14]
另外,我国各个民族在生产技术上,在政治关系上,在学术文化上都对祖国历史作出过历史贡献,而且许多少数民族有丰富的资料有待于整理,有的还要做大量翻译工作,让更多的人能阅读和研究。在各民族对历史所做的贡献问题上,先生说有一个问题需要重新认识,他以回族为例作了说明。回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回族人过去用汉文写了不少书,包括诗集、文集等等。这算不算回族的贡献呢?而且好多回族人的诗文里并没有多少回回民族的色彩,倒是有儒家思想,这个问题怎样认识呢?他说不能以狭隘的眼光认识这些问题,“民族特点是客观存在的,有些特点还应该发展,但少数民族的某些工作,表现不出民族特点却对各民族都有好处,这也是很好的贡献”。[15]这样来认识问题,就会觉得回族的贡献比过去所认识的还要多得多。
总之,只有对以下各方面有深层次的理解和认识,才能更好地开展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白先生语重心长地说:“我们要求青年人爱国,可是他们不知道这个国是怎么回事,让他们爱什么国,又怎么去爱呢?我们中国历史学家有个传统,就是察往观来:说明过去的事情,展望将来的事情。这是个好传统,比如宣传爱国主义,如果仅仅搞一些片面的、零儿八碎的,那没有什么用处。按照察往观来的原则,我们需要从整个历史的纵的方面和横的方面,深刻地说明我们国家的过去和将来,这样来宣传爱国主义,效果是不是更大一些。”[16]写历史、写民族史,就是“使广大的各族人民有机会懂得祖国的过去、本民族的过去,展望祖国的未来、本民族的未来。”[17]白先生从时代的要求,从理论的高度阐明了少数民族史研究是开展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也指出了要把握住爱国主义思想这个时代的主旋律开展少数民族史研究。
白寿彝先生对中国民族史关系研究的贡献是巨大的,是多方面和多角度的,其中还有大量丰富的内容是关于伊斯兰教史、回族史方面的精辟论述。如此丰富的内容,这非本文所能尽言,本文权当引玉之砖。
收稿日期:1998—09—07
标签:中国历史论文; 白寿彝论文; 爱国主义论文; 回族论文; 汉族文化论文; 历史论文; 中国古代史论文; 史学理论论文; 史学史论文; 思想史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