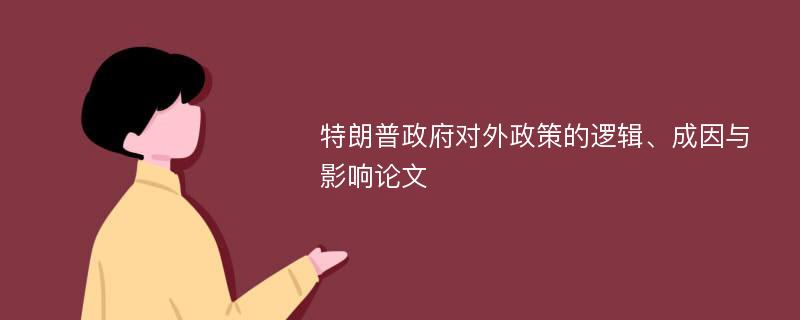
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逻辑、成因与影响
刁大明
[内容提要] 自上台以来,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及其影响始终备受关注。就过去两年多的现实观察,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逻辑体现为“大国竞争”的战略框架、“美国优先”的政策目标以及决策中的“碎片化分工”与“小集团思维”的“共振”组合。如此复杂逻辑的成因是美国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回应、美国国内身份认同的重构、特朗普所面对的选举政治压力以及特朗普与建制派精英的“合流”等因素同步交互共振的结果。目前,特朗普对外政策已造成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同时预示着美国对外战略与政策已进入重大方向性调整阶段。
[关键词] 特朗普政府 对外政策 大国竞争 美国优先 碎片化 小集团思维
2019年以来,随着新一届总统选举周期的启动,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利弊得失再次引发了聚焦与讨论。按照美国总统政治的一般规律,经历了两年多磨合与调整的特朗普政府应该在对外政策上展现出相对确定的总体目标与较为清晰的内在逻辑,进而为外界对其做出系统且明确的评价与预判提供了可能。(1) William B. Quandt, “The Electoral Cycle and the Conduct of Foreign Policy,”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 Vol.101., No.5., 1986, pp.825-837.从退出多个多边国际机制到向全世界挥舞贸易制裁大棒,从强调美国军事实力到施压盟友分担安全义务,从深度介入中东事务到以印太战略承接美国强化亚太地区主导地位的需求,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同步显现出不同乃至相互冲突的倾向,很难被贴上惯常使用的某个已知标签。尽管如此,对特朗普两年多来对外政策实践进行相对系统的总结还是有必要也是有可能的。
Microsoft Visual Studio2010主要是将既有程序进行有机集成,其以独立开发人员或小规模开发团队为主体,通过ASP.NET AJAX等Web包的开发,可以进一步丰富用户体验。
一、关于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讨论
自特朗普上台以来,外界对其对外政策的分析与预估就从未真正停止。相应地,在不同议题上迥异的解释与视角之间的争议也始终存在。
讨论焦点之一是特朗普个人因素与决策风格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塑造。一方面,外界普遍认为商业经历、反建制派倾向等特朗普个人层面的因素不同程度地牵动了其对外决策。(2) 楚树龙、周兰君:“特朗普政府外交特性及其影响”,《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8期,第23~30页。 比如,独特而单一的商业经历决定了对外决策中的“逐利性”,也导致了商业化的交易思维在政策中的广泛运用;又如,特朗普早年对军人的青睐被理解为与其对军人的重用以及对美国军事力量的重视密切相关。(3) 刁大明:“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外交评论》,2017年第2期,第65~84页。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个人因素直接反映在其最初对外决策团队的构建之中,进而自然会引出一定政策影响。外界认为,特朗普决策过程中商人、军人、缺乏政治经验的年长者以及更多白人而非少数族裔人士的参与,极大提升了其对外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总统个人本身的主导性。(4) 袁征:“试论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趋向”,《和平与发展》,2017年第1期,第17~33页。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个人因素的影响也显现出明显的局限性。就两年来的对外实践看,其政策要比最初预料的更为稳定,不但未出现由个人色彩带来的巨大不确定性,而且在一些议题上的政策选择也与竞选期间的政见宣誓差异较大。(5) Michael Nelson, Trump ’s First Year , Charlottesville, V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18, pp.114-120.其原因主要在于,具有总统个人色彩的政策倾向遭遇了来自决策团队内部不同利益、执行专业层以及两党建制派前所未有的挑战、重塑乃至修正,进而最终达成某种“妥协”。(6) 达巍:“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初步观察与分析”,《中国国际战略评论2017》,第72~83页。 在具体决策过程中,副总统迈克·彭斯(Mike Pence)、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以及白宫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约翰·博尔顿(John Bolton)等熟悉华盛顿政治与共和党外交传统的决策参与者也被认为正在以避免与总统公开直接冲突的方式来发挥关键的调节作用,甚至是部分主导作用。(7) Eloit A. Cohen, “American’s Long Goodbye: The Real Crisis of the Trump Era,” Foreign Affairs , Vol. 98., No.1., Jan/Feb 2019, pp.138-146.
本次研究中的因变量、自变量情况在前文中都已有所说明,分别为社会距离与教育年限、收入、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工作稳定度、住房保障度和公民性。而同时,我也将性别、年龄和年龄的平方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因变量和自变量的具体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讨论焦点之二是特朗普“美国优先”等特有政治理念在对外政策上的影响与体现。一般认为,特朗普政府内外政策的出发点是“美国优先”和“让美国再伟大”,在对外政策上折射出某种“新孤立主义”倾向。(8) 袁征:“试论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趋向”。 而这种折射过程本质上是特朗普的“美国优先”与其决策群体中其他理念(如博尔顿等“新保守主义”、建制派的“干预主义”等)之间平衡与妥协的过程。于是,所谓“新孤立主义”的“新”,在于强调自身国内事务、一切以国内利益为唯一导向,同时强调军事力量对国家绝对安全的关键意义;一方面避免不可控的军事介入,另一方面不排斥可以增进实际利益的对外军事存在。(9) Brian Bennett, “President Trump Showed His Contradictory Foreign Policy Doctrine in Iraq. Call It ‘Hawkish Isolationism’ ,” Time , December 27, 2018, http://time.com/5489044/donald-trump-iraq-hawkish-isolationism/.(上网时间:2019年4月25日)事实上,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地区既要完成反恐、控制叙利亚局势、遏制伊朗乃至所谓“世纪协议”等既定战略目标,又要竭力避免直接军事介入的矛盾性做法正是这一判断的典型体现。也是由于其中微妙的矛盾性,特朗普的“新孤立主义”也被冠之以“鹰派孤立主义”(Hawkish Isolationism)或“好战极简主义”(Belligerent Minimalism)等新的组合标签。(10) Marc Lynch, “Belligerent Minimalism: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nd the Middle East,”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 Vol.39., No.4., 2016, pp.127-144.
第二是以“美国优先”作为政治目标。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正如特朗普在竞选期间所言,“外交政策永远将美国人民、美国安全放在第一位。这将是我做每个决定的基础。……‘美国优先’将是主要且永远的主题”。(27) “Read Donald Trump’s ‘America First’ Foreign Policy Speech,” Time , April 27, 2015, http://time.com/4309786/read-donald-trumps-america-first-foreign-policy-speech/.(上网时间:2019年5月10日)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美国总统的对外政策都应该是“美国优先”的,但关于对外政策要服务的国家利益的界定则存在着差异。国家利益是政治精英或政策专才理解中的长远考虑,还是国内民众所关注的切实利益?即便是切实利益,到底是国内民众的普遍关切还是某些特定群体的特殊关切?这些问题决定了“美国优先”的程度与边界。
讨论焦点之三是对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逻辑及影响的评估。持负面态度者认为特朗普及其政府已对美国外交造成了极具破坏性的消极效果,特朗普政府目前的对外政策调整的影响是不可逆的,美国外交正在因特朗普所代表的国内政治极化、孤立与民粹趋势而无法恢复。(14) Daniel W. Drezner, “This Time is Different: Why U.S. Foreign Policy Will Never Recover,” Foreign Affairs , Vol. 98., No.3., May/June 2019, pp.10-17.特朗普政府的这种“破坏性强势外交”在一段时间内的顽固执行,必然对世界经济稳定发展、地区问题以及大国关系带来破坏、危害与危险。(15) 楚树龙、周兰君:“特朗普政府外交特性及其影响”。 当然,也有观点主张不能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过早做出简单否定。历史也曾经证明一些有缺陷的政策未必不会导致成功的结果,比如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或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在对外政策上的成功,相反,应该对其目标、战略、政策及其服务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绩效来进行仔细评估。(16) Robert D. Blackwill, “Trump’s Foreign Policies Are Better Than They Seem,” Council Special Report , No.84, April, 2019, https://www.cfr.org/report/trumps-foreign-policies-are-better-they-seem. (上网时间:2019年4月25日)
另外一种为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辩护的观点认为,如果放在美国外交战略总体演变趋势中加以判断,目前的政策只是当今美国“收缩”态势无法改变的延续,特朗普也只是在何为“收缩”以及如何“收缩”等选择上给出了自己的回答,(17) Eloit A. Cohen, “American’s Long Goodbye: The Real Crisis of the Trump Era,” Foreign Affairs , Vol. 98, No.1, Jan/Feb 2019, pp.138-146.他的这种选择并非彻底颠覆,其仍以亚太为重点,仍强调同盟体系的重要作用,反映出明确而稳定的延续性。(18) 袁征:“试论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趋向”。 保守派立场还指出,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从根本上只是纠正美国以往的错误,回归到了美国应有的常态,而且还采取了一种相对“软着陆”的方式。(19) Michael Anton, “The Trump Doctrine: An Insider Explain the President’s Foreign Policy”.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我们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与互联网紧密相关,“互联网+教育”就是当前教育领域新的发展模式。在此背景下,教师面临着来自信息技术、大数据、云计算等各个方面的重重挑战,而唯一的解决措施就是要加强教师的信息素质能力培养。因此,教师必须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了解并掌握现代信息技术,形成“互联网+”思维和“互联网+教育”理念,并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利用互联网收集、整理和分析数据来组织和管理自己的课程,设计出与学生实际情况相符合的教学环境、教学模式和方法,以更好地适应“互联网+教育”时代对高校教师综合素质的要求。
在那些符合大国竞争框架与“美国优先”目标的政策议题上,由于战略与政治目标明确一致,虽然存在“分权”可能,但将很快形成较为确定的“小集团思维”。比如,在对华经贸摩擦议题上,相对温和的商业精英、强硬现实的鹰派贸易官员以及有意识形态偏见的保护主义学者都参与其中并展开竞争,但最终呈现的是以贸易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Robert Lighthizer)、白宫贸易与产业政策办公室主任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等为代表的贸易鹰派占据主导的局面。(38) Michael Sheetz, “China Trade Negotiations Will Be Led By Robert Lighthizer and Include Trade Hawk Peter Navarro,” CNBC , January 28, 2019, https://www.cnbc.com/2019/01/28/china-trade-negotiations-will-be-led-by-robert-lighthizer-and-include-trade-hawk-peter-navarro.html.(上网时间:2019年5月10日)
二、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逻辑
在梳理主要讨论观点时可以看到,研究视角自然从微观到宏观,从特朗普个人层面等多变的短期因素到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等相对稳定的长期因素。但要完整搭建起一个展现所谓“共振”逻辑的框架,则应该回到决策过程的一般顺序。就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而言,本文将其基本逻辑归纳为战略框架上的“大国竞争”、政治目标上的“美国优先”以及决策过程中的“碎片化分工”与“小集团思维”倾向三个层面的嵌套。
第一是以“大国竞争”作为战略框架的核心内容。2017年年末特朗普政府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美国处于一个“竞争的世界”之中。虽然极端恐怖主义组织等反恐目标仍被提及,朝鲜、伊朗等所谓“流氓国家”也被列为威胁,但中国与俄罗斯被确定为“修正型力量”(Revisionist Power),构成美国的首要竞争对手。(20) The 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cember 2017, https://www.whitehouse.gov/wp-content/uploads/2017/12/NSS-Final-12-18-2017-0905.pdf.(上网时间:2019年4月30日) 如此清晰的转向在特朗普政府其后两年多的对外政策实践中得以具体落实:美对华政策日渐鲜明地表现为在经贸关系、台湾问题、南海问题、印太战略、意识形态等议题上的同步摩擦与角力;而对俄政策虽然最初因为特朗普个人的因素而乍现缓和可能,但在美国国内建制派精英的决定性塑造下又快速回到大国竞争的轨道。(21) Amy MacKinnon, “Trump May Like Putin. His Administration Doesn’t,” Foreign Policy , April 29,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4/29/trump-may-like-putin-his-administration-does-not-russia-policy-rapprochment/.(上网时间:2019年5月2日)
混搭的决策团队要遵循特朗普政府的总体目标,即在大国竞争的战略框架内实现“美国优先”的政治目标。一方面,决策参与者要遵循大国竞争的框架。一般认为彭斯、蓬佩奥以及博尔顿等人的存在维持并强化了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中大国竞争、特别是对华强硬的倾向。(36) Robert Sutter, “Pushback: America’s New China Strategy,” The Diplomat , November 2, 2018, https://thediplomat.com/2018/11/pushback-americas-new-china-strategy/.(上网时间:2019年5月20日)另一方面,决策参与者大都接受、至少不违背“美国优先”的原则。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美国优先”所回应选民诉求的变动性与宽泛性,不同决策参与者通过提出不同政策路径而展开竞争,试图在不违背特朗普政府总体目标的情况下实现各自的政策目标。这就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团队的个性特质是在大国竞争框架和“美国优先”目标的交互影响下发挥作用的。具体而言,其对外决策过程呈现出“碎片化分权”,且可能出现某些群体之间在同一议题上的竞争,并最终可能导致一个相对固化、封闭的“小集团思维”主导决策,其政策产出也不可避免地具有特定倾向和片面性。(37) [美]欧文·贾尼斯著,张清敏等译:《小集团思维:决策及其失败的心理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年,第227~228页。
虽然看似超越了传统的窠臼,但特朗普政府推行“美国优先”还是存在着内外两个维度上的显性约束。一方面,“美国优先”是在大国竞争的战略框架之内才能追求的政治目标。如果“美国优先”与大国竞争高度吻合,其政策议程将得到持续推进。如果“美国优先”妨碍了大国竞争,其政策将被最终叫停或重塑。当然,由于政策评估的滞后性以及总统外交权的主导地位,这种战略框架的“纠偏”未必能快速实现。另一方面,“美国优先”内部也具有优先次序,体现为“关键盘优先于基本盘”,即在确保基本盘不松动的情况下选择强化关键盘支持的政策。比如,面对贸易摩擦必然对美国经济与普通民众带来的负面影响,特朗普政府采取“强化关键盘优先于稳定基本盘”的选择。在农业利益群体受累而形成一定政治压力的情况下,特朗普政府并未回归理性轨道。为了持续得到蓝领中下层这一关键盘的支持,特朗普政府以承诺补贴等方式回应作为基本盘的农业利益群体,尽量避免其在选举中“跑票”。因为相比而言,以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持续满足蓝领中下层群体的眼前诉求,才是以“美国优先”稳定关键政治支持的更重要议程。从过去两年多的民调观察,民众对特朗普政府在贸易议题上的满意度与不满意度长期处于四成比五成左右的水平,与其执政以来总体满意度与不满意度几乎一致,甚至有时贸易议题的满意度还略高于总体水平。(29)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Polling Report , http://www.pollingreport.com/trump_ad.htm.(上网时间:2019年5月5日)这也说明,特朗普政府争议巨大的“美国优先”贸易保护政策远非是政治减分项,反而可能有助于稳定其政治上的关键盘,进而也决定了其政策调整可能性并不大。
从对“新孤立主义”的复合新界定出发,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在整体上也被认为是一种“转型体”或者“复合体”。所谓“转型”,是指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意味着其对外政策至少反映出了从自由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从国际主义转向本土主义的两大转变。同时议题导向也转为战略导向,以相对获益最大化为主要目标、以交易为主要手段。(11) 达巍:“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外交政策:初步观察与分析”。 而所谓“复合”,是将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理解为包含着“民粹主义”“自由国际主义”“国家主义”等多元素复合而成的独一无二的“特朗普主义”(Trump Doctrine)。(12) Michael Anton, “The Trump Doctrine: An Insider Explain the President’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 April 20,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4/20/the-trump-doctrine-big-think-america-first-nationalism/.(上网时间:2019年4月25日)当然,也有一些历史性的考察指出,如今特朗普政府在对外事务上所展现的现实、保守乃至孤立等特质并非历史罕见,其本质完全是所谓“杰克逊主义”(Jacksonianism)的再次回归与重现。(13) 石秋峰、杨卫东:“杰克逊主义与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外交政策”,《国际论坛》,2018年第1期,第72~78页;张建辉、郑易平:“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的调整、原因及前景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8年第6期,第27~44页。
工信部原材料司处长张文明表示:“我们国家在继续实施扶持国产钾肥发展的优惠政策,保障国产钾肥竞争力和提升自给率的同时也要加快境外钾肥基地建设,实现双轮驱动,巩固国内价格洼地,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引导企业有序推进‘走出去’步伐。对境外钾肥基地加大支持力度,形成双翼协同保障我国钾肥的稳定供应,提升我国在国际钾肥市场的话语权。”由于各方面条件限制,建设一个大型钾盐生产企业从勘探、设计、建设到出成品至少需要5-7年的时间,建设周期漫长且投资巨大。据了解,目前我国在境外已进入生产运营阶段的企业只有在老挝的中农集团和开元集团,它们是我国“走出去”找钾和采钾的企业佼佼者。
比较而言,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并不接受精英们关于国家利益的构建,而是强调回应在政治意义上对其至关重要的基本盘(共和党传统选民)与关键盘(蓝领中下层等可能出现摇摆的选民)群体。这些群体的诉求如果具有“全民性”(比如美国全民对朝核问题所引发安全隐患的广泛担忧),那么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随之反映“全民性”。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极具政治性,即将“美国优先”视为政治目标,这完全是因为美国政治中原有的党争不涉及对外政策的传统已被打破,任何“民粹化”的政策即便不具备共识,也只会遭遇到极化的抨击,而不会面对有悖于国家利益的压倒性阻力。(28) Stephen M. Walt, “America’s Polarization is A Foreign Policy Problem, Too,” Foreign Policy , March 11, 2019,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9/03/11/americas-polarization-is-a-foreign-policy-problem-too/.(上网时间:2019年5月10日)而“美国优先”也直接导致了特朗普对外政策中的“孤立主义”色彩。这种“孤立”一方面体现为更多放弃国际责任的冲动,代表性的倾向即在同盟体系中要求盟友分担更多义务。换言之,美国似乎表现出一种“不做加法”的领导,即不以投入新资源来持续并更新领导力,完全以其难以撼动的领导地位或体量来实现维持现状的“静态领导”。另一方面,“孤立”也体现为避免直接干预与深度介入、避免让美国陷入“新泥潭”的克制。这恰恰符合多年反恐战争后美国国内的民意状态以及集中资源投入大国竞争的必然需要。
需要指出的是,2000年小布什在竞选期间抛出的大国竞争理念更多是共和党阵营富有意识形态偏见的新保守主义世界观,其强调的是俄罗斯、中国等“他者”大国对美国安全的潜在威胁与挑战。相比之下,如今特朗普政府快速转向的大国竞争虽然也存在意识形态偏见与冷战思维,但其出发点已超越了对潜在威胁的防范,而完全是对维持国家实力地位现状与安全的迫切需求,直接体现在特朗普政府突出强调自身军力建设、提高军费特别是军事科技绝对领先地位的实际动作之中。换言之,基于新世纪以来的世界政治权力变动,美国逐渐形成了“中国、俄罗斯等大国对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秩序乃至美国自身发展模式构成了颠覆性挑战”的战略认知,其中综合国力与国际地位持续上升的中国无疑更具威胁。(26) 在2019年6月1日美国国防部正式发布的《印太战略报告》中已明确区分中俄:俄罗斯被界定为“复苏的邪恶力量”,而仍作为“修正型力量”而发起“全面竞争”者只有中国。参见 The Department of Defense, “Indo-Pacific Strategy Report”, https://media.defense.gov/2019/May/31/2002139210/-1/-1/1/DOD_INDO_PACIFIC_STRATEGY_REPORT_JUNE_2019.PDF.(上网时间:2019年6月11日) 这也意味着,如今以大国竞争作为重点的战略框架所反映的是美国跨党派政治精英的共同关切与情绪,是任何党派主导的政府都无法拒绝的基本框架,也是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中的最大遵循。
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实现政治目标,但其实际政策效果极可能被扭曲。一方面,“美国优先”所要实现的政策目标可能仅是让其政治基本盘和关键盘所满意,未必是问题本身的解决。比如,在朝核问题上,在特朗普政府上台之初,至少51%的美国普通民众将朝鲜视为美国“首要威胁”,(30) “Majority of Americans Now Consider Russia A Critical Threat”, Gallup , February 27, 2019, https://news.gallup.com/poll/247100/majority-americans-consider-russia-critical-threat.aspx.(上网时间:2019年5月5日)且共和党基本盘选民更具鹰派倾向,这也是特朗普就职后就马上要求军方制定直接打击方案的原因所在。(31) “Almost Half of Republicans Want War with North Korea, A New Poll Says. Is It the Trump Effect?” The Washington Post , October 15, 2017,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the-fix/wp/2017/10/14/almost-half-of-republicans-want-war-with-north-korea-says-a-new-poll-is-it-the-trump-effect/?utm_term=.10219192d40a.(上网时间:2019年5月5日)但随着国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特朗普政府转而采取极限施压与接触的方式,尽可能快速回应民意。2018年上半年,美朝领导人的成功会晤对美国民意形成了微妙牵动:五成左右的美国民众对特朗普政府在半岛事务上的处理表示满意,超越了其总体满意度水平。(32) “President Trump and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Polling Report .民意的改善助长了特朗普政府急于再度会晤的意愿。另一方面,“美国优先”所要回应的民意自相矛盾,也导致了相应政策的矛盾性。比如,在北约问题上,特朗普政府要求北约盟友分担更多义务,这显然符合48%的美国民众认定北约作为太少、49%认为美国没有义务保护不承担更多负担盟友的民意状态,但当面对俄罗斯的竞争时,美国民众中又有七成左右希望保留北约。(33) RJ Reinhart, “Majorities of American See the Need for NATO and the UN,” Gallup , March 4, 2019, https://news.gallup.com/poll/247190/majorities-americans-need-nato.aspx;Moira Fagan, “NATO is See Favorably in Many Member Countries, But Almost Half of Americans Say It Does Too Little,” Pew Research Center , July 9, 2018,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07/09/nato-is-seen-favorably-in-many-member-countries-but-almost-half-of-americans-say-it-does-too-little/; Phil Stewart, “Nearly Half of Americans Link Defense of NATO to Allies’ Spending: Reuters/Ipsos Poll,” Reuters , July 19, 2018,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8/07/09/nato-is-seen-favorably-in-many-member-countries-but-almost-half-of-americans-say-it-does-too-little/.(上网时间:2019年5月5日)于是,特朗普政府在维持乃至强化北约的同时,又要求北约成员国更多“买单”。再如,在反恐战争议题上,为回应美国国内的厌战情绪,特朗普急于宣布战胜“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急于从叙利亚撤军;但面对着59%的美国注册选民仍希望美国保持在叙利亚的军事存在的现实,又不得不很快调整了撤军计划。(34) Matthew Sheffield, “Poll: Most Americans Want US Troops in Syria,” The Hill , January 17, 2019, https://thehill.com/hilltv/what-americas-thinking/425803-poll-most-americans-still-want-a-us-military-presence-in-syria.(上网时间:2019年5月5日)
第三是决策过程中的“碎片化分权”与“小集团思维”。经过两年多的调整与磨合,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团队日渐稳定,共和党建制派色彩加重,对特朗普政府及其目标的“认同度”与“忠诚度”也更高。(35) Thomas Wright, “Trump’s Foreign Policy Is No Longer Unpredictable,” Foreign Affairs , January 18, 2019, 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world/2019-01-18/trumps-foreign-policy-no-longer-unpredictable.(上网时间:2019年5月20日)但即便如此,其决策团队内部成员还是在具体政策选择上倾向迥异,军人、商人、家人以及共和党建制派等不同“小圈子”并存,本土主义、新保守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重商温和派、基督教福音派、意识形态鹰派等诸多派别杂糅其中,这也决定了其对外政策决策生态与过程的复杂性。
事实上,转向大国竞争并非特朗普政府独有的调整,而是美国一个时期以来逐步酝酿、缓慢移动的对外战略重心调整的必然趋势。冷战落幕后,面对国际关系新现实与新世纪的挑战,成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陷入了外交与安全战略重新定位的摸索阶段。克林顿政府选择在经济全球化与人权等意识形态意义上维护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对俄罗斯与中国在总体上并未展现出很强的战略竞争性。(22) [美]史蒂文·胡克、约翰·斯帕尼尔著,白云镇等译:《二战后的美国对外政策》,金城出版社,2015年,第211~221页。 与民主党的理想主义倾向不同,共和党对外交与安全战略的新定位凸显带有冷战思维的现实主义。2000年大选期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就曾多次强调与中、俄之间的竞争。(23) Janine Yagielski, “Bush Lays Out Foreign Policy Vision,” Time , Nov 19, 1999, http://www.cnn.com/ALLPOLITICS/stories/1999/11/19/bush.speech/index.html.(上网时间:2019年4月29日)虽然“大国竞争”最终被小布什带入了白宫,但“9·11”事件却很快将美国的战略重点转向反恐。在小布什八年任内的两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俄罗斯与中国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负面表达,但总体上强调了积极合作的姿态,完全绕开了大国竞争。(24)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rchive , available at: http://nssarchive.us/NSSR/2006.pdf.(上网时间:2019年5月5日)随后的奥巴马政府期间,美国对外政策和安全战略呈现出从反恐到反衰落的加速调整,虽然抛出了旨在巩固美国领导地位的亚太战略,但仍未将大国竞争明确为战略重心。针对俄罗斯,奥巴马政府在强调应对俄罗斯在军事、地缘以及网络等维度上的多重挑衅的同时,仍旧重视全球军控合作;针对中国,奥巴马政府虽然多次对中国军力发展和地区战略存在表示关切,但也明确提出过美国“欢迎稳定、和平与繁荣的中国的崛起”。(25)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Archiv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http://nssarchive.us/wp-content/uploads/2015/02/2015.pdf.(上网时间:2019年5月5日) 而自2017年特朗普政府就位以来,虽然在内外政策上都显现出所谓“逢奥必反”的强趋势,但在战略选择上却颇有延续意味:一方面延续了奥巴马政府急于结束反恐战争、“不做傻事”以及“后排领导”(lead from behind)等基本倾向;另一方面强化了对奥巴马政府所提威胁关切的回应,明确推进对外战略重心从反恐转向大国竞争。
总体而言,关于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讨论虽然得出了不同的论断,但基本上反映出了针对两个方向上变化或不确定的关切。一是特朗普个人作为反建制派政治人物掌握核心权力之后,给美国政治现实以及内外决策过程带来的难以预期的不确定;二是当今美国在国际环境与国内诉求剧烈变动的情况下对自身国际角色的定位及其实现手段的长期调整所带来的不确定。两种“不确定”的交叉无疑增加了评价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难度,但同步形成的“共振”也为推进相关研究提供了相对完整的视角。
在不违背大国竞争框架、可以实现某些“美国优先”目标的政策领域,特朗普政府对外决策团队就更为明显地陷入“碎片化分权”。比如,在中东事务上,相对熟悉反恐战争的稳健派军人、力挺以色列的美国犹太裔精英和基督教福音派保守势力、持有意识形态偏见并崇尚军事介入的新保守主义者等不同群体之间爆发激烈冲突,最终导致前防长詹姆斯·马蒂斯(James Mattis)等关键决策参与者的离任。在对以色列政策上,出任总统高级顾问的特朗普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以及白宫国际谈判特别代表贾森·格林布拉特(Jason Greenblatt)等美国犹太裔精英以“小集团思维”扮演着关键角色,并在不违背大国竞争框架、有助于强化基督教福音派选民支持的情况下,推进了迁馆耶路撒冷、承认戈兰高地等一系列极端亲以政策。(39) Daniel C. Kurtzer, “The Illusion of Trump’s Mideast Peace Plan,” The American Prospect , April 16, 2019, available at: https://prospect.org/article/illusion-trumps-mideast-peace-plan.(上网时间:2019年5月15日)在对伊朗政策上,在共和党人反对伊核协议却并未形成有效替代方案的情况下,新保守主义者博尔顿更具主导作用,但其关于不排除通过军事打击来改变德黑兰政权的倾向却完全不符合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原则。(40) Dexter Filkins, “On the Warpath: Can John Bolton Sell An Isolationist President on Military Force?” New Yorker , May 6, 2019, pp.32-45.彭斯、蓬佩奥等人虽然出于共和党宗教保守派立场而在相关议题上不同程度地助长了库什纳、博尔顿等人的政策议程,但也存在一定差异。(41) Eliana Johnson, “Pompeo and Bolton Tensions Escalate as Iran Debate Intensifies,” Politico , May 17,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9/05/17/bolton-pompeo-trump-iran-1329833.(上网时间:2019年5月20日)
三、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成因与可能影响
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复杂逻辑,是对持续变动的国际与国内现实的回应,是多层面、多因素驱动的结果。具体而言,美国对国际环境变化的回应、美国国内国家认同的重构、特朗普自身要面对的特殊选举政治压力以及特朗普与建制派精英的“合流”等因素形成了“共振”,而其所产生的影响极有可能是不可逆的。
第一,美国正在针对加速变革的国际环境做出回应。自冷战结束之后面对“单极时刻”,继而经历反恐战争,如今面对中国与俄罗斯两个大国对手,对于剧烈变动的国际环境,美国必然要做出充分的战略回应。到目前为止,这种回应就是以维持领导地位为目标的大国竞争战略。虽然特朗普政府会延用这一战略框架,但特朗普本人的当选以及倡导的“美国优先”原则背后所代表的恰恰是在19世纪末到二战结束之间阻碍美国“登顶”的“孤立主义”倾向。换言之,如果将美国当年踌躇再三,最终下定决心领导世界的核心原因归结为国家安全观念的“全球化”扩展、对自身潜在威胁的必要遏制以及对孤立主义主张的抛弃等理念转变的话(42) 王立新:“踌躇的霸权:美国获得世界领导地位的曲折历程”,《美国研究》,2015年第1期,第10~33页。 ,如今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上的种种表现似乎正在解构这些支撑美国霸权的理念,回归到孤立主义的怀抱之中。
第二,美国国内各层面矛盾导致的身份认同危机外溢到对外政策上。某种意义上,美国的国家成长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断谋求共同身份认同的历程。历史上,美国曾有过从独立战争到南北战争之间的关于“何为美国”的思索,有过从罗斯福新政到民权运动之间的关于“谁是美国人”的叩问。而今面对着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国内经济与社会层面的多层次民怨,美国需要回答的新问题是“美国是谁的美国”。
自建自营模式是指港口经营人投资建设专用设施或固定式站点、岸罐、接收箱对船舶污染物进行接收,接收后将各类船舶污染物纳入其对应的转运、处置渠道,进行就地或异地处置。
虽然美国在目前状态下都不会放弃全球领导地位,也不会情愿放弃在中东等世界关键地区的主导权,但从趋势上看,美国是否正在缓慢地进入与“踌躇的霸权”相逆的“踌躇的收缩”阶段呢?这个问题可能只能留给历史来回答。但不可否认的是,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与地缘政治条件,美国始终是一个具有浓厚孤立主义情绪的国家。美国确实有可能陷入到一场逐渐退出(部分)领导地位的“收缩”之中,但这个过程也一定是“踌躇”乃至极不情愿的,而这种“不情愿”势必给世界带来各种不确定性。
应对这个新问题的新身份认同不再是美国国内各种群体的“化异为同”,而是每个群体都希望在保留一定特性基础上的有限趋同。而在美国国内各群体都在追问“美国是谁的美国”之时,也衍生出了“美国是美国人的美国,还是世界的美国”这样涉及对外政策的外溢问题。从这个角度看,如今“美国优先”背后的本土主义乃至民粹主义,正是针对目前新一轮身份认同危机的一种回应。(43) Ezra Klein, “How Identity Politics Elected Donald Trump,” Vox , https://www.vox.com/policy-and-politics/2018/11/5/18052390/trump-2018-2016-identity-politics-democrats-immigration-race.(上网时间:2019年5月23日)从以往历史经验看,身份认同危机往往会通过战争、通过扩大资源的占有、通过刺激经济增长的重大变革来化解。相比而言,目前身份认同危机的化解之道虽然仍不清晰,但必然在美国对外政策上投射出复杂的内顾与非理性倾向。
第三,特朗普所面对的特有选举政治压力也促使其选择民粹化的对外政策。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是美国历史上第五次出现选举人团票与普通选民票相背离的扭曲情况,即特朗普并未赢得更多的民意,这也为其连任蒙上了巨大阴影。历史比较而言,前四次类似情况中只有小布什最终得以连任。究其原因,与“9·11”事件给小布什带来的“危机总统”效应及其对民意的塑造密切相关。反观如今特朗普的连任前景,在不具备“9·11”事件等突发危机刺激选民支持的情况下,特朗普自竞选以来就相对极端的政策表达更无望吸引到坚定的民主党选民或温和派的中间选民,因而他扩展普通选民支持的唯一途径就是将共和党基本盘和蓝领中下层关键盘的支持最大化。
要实现这个最大化目标,就必须推进直接回应这些选民群体诉求的内外政策,即将“美国优先”操作为“基本盘和关键盘的优先”,在对外政策上的民粹化自然也就得到了充分解释。如前文所述,特朗普在贸易政策上为了回应关键盘的短期诉求不惜损害基本盘利益,但其筑墙等“零容忍”移民政策却又在强化基本盘和关键盘的支持度,甚至这些所谓“白人至上”的标签还更为广泛地针对白人群体动员,不排除具有扩大基本盘的作用。(44) Jonathan Allen, “Inside Trump’s All-About-That-Base 2020 Strategy,” NBC News , April 8, 2019, https://news.gallup.com/interactives/185273/r.aspx?g_source=WWWV7HP&g_medium=topic&g_campaign=tileshttps://www.nbcnews.com/politics/2020-election/inside-trump-s-all-about-base-2020-strategy-n991896.(上网时间:2019年5月23日)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内,特朗普的满意度始终稳定,并未出现明显下滑趋势,这也是其民粹化政策的直接效果。需要指出的是,如果连任成功,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将不再背负选举压力,届时其对外政策是否会减少“美国优先”、是否会因为对“政治遗产”的追逐而完全服务于大国竞争框架?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需要密切关注。
研究生经历了本科阶段的学习实践,具备一定的能力基础与专业积淀,且随着年龄的成长和学习的深入,对自身的定位与期望也更加明晰,也更为关注自身在研究生阶段的科研规划与未来发展[7]。但是,现有的许多新生对自己的研究生生活并没有明确的目标和计划,仰望星空者较多,脚踏实地者较少。此时的研究生迫切需要系统化的入学指导,帮助其构建较为明确的学术计划、职业规划乃至人生目标。因此,针对研究生发展需要的入学教育,则需要侧重于学生个人发展规划引导,帮助树立未来理想目标,并做出切实可行的人生规划。
第四,特朗普政府的“美国优先”和建制派精英的大国竞争理念呈现出“合流”态势。回应国际环境变动显然是超越党派的美国战略界精英的共同关切,而回应国内身份认同和最大化选民支持则是特朗普的首要目标,而这些互不相同的目标正在“合流”并形成合力。
在不违背大国竞争框架的前提下,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的强烈导向使得政策目标明显优先于政策路径,政策流程缺乏严格控制、甚至陷入漂流,进而也为建制派精英创造了实现某些其他目标的空间。于是,在同时符合大国竞争框架与“美国优先”目标的政策领域,特朗普政府采取了至少是接受了大国竞争框架的政策议程来追求“美国优先”的目标,但其真正实现的效果是大国竞争的必然快速加剧和“美国优先”的未必全部满足。
目前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就是这种“合流”趋势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个领域。在决策团队内部,特朗普以及强调“美国优先”的决策参与者更为强调对华施压、为美国实现相对获益最大化的贸易安排;但持有意识形态偏见的鹰派或保守派官员也深度参与其中:意识形态派以及国务院系统强调中美“文明冲突”,美军方强调印太战略推进,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和国防部分别直接分管对华政策的波廷杰(Matthew Pottinger)和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等人由于个人的强硬立场而共同驱动具体政策选择(45) 同样对华持有鹰派立场的前驻华武官戴维·史迪威(David Stilwell)也已被提名出任国务院分管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史迪威就位后,特朗普政府中相对专业的具体对对华政策操作层就将形成鹰派“铁三角”。 ,这些都是在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下不同利益群体推进自己政策议程的体现。而就特朗普政府与国会等华盛顿建制派的互动而言,在白宫对华战略尚未完全成型之际,国会两院两党就开始推出消极涉华议题,而特朗普政府却放任并签署批准了多个消极涉华立法。这些往届国会都难以被放行的立法,在特朗普政府看来却是丰富了其对华施压的“工具箱”,必然成为未来中美关系中很难被祛除的刚性障碍,无形中抬高了中美两国管控双边关系的难度与成本。(46) Henry Olsen, “Trump is Standing Firm Against China. Congress Must Stand with Him, ”The Washington Post , May 6, 2019,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19/05/06/trump-is-standing-firm-against-china-congress-must-stand-with-him/?utm_term=.86d06e8cd7cc;“Beijing Slams US Legislation Demanding Easier Access to Tibet for American Journalists, Tourist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December 14, 2018, https://www.scmp.com/news/world/united-states-canada/article/2177912/us-poised-ban-chinese-officials-unless-tibet-opened.(上网时间:2019年5月23日)
以上结果表明,从生成降水的条件来看,西太平洋暖池北部异常菲律宾反气旋西北侧的西南暖湿气流输送以及江南地区上空高层辐散抽吸作用导致的对流上升运动是造成江南雨季多雨的直接原因。
必须看到,虽然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复杂逻辑已初步成型,但仍处于变动之中,其政策影响仍难以评估。但不可否认的是,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中的“分权化”及其背后的“合流”趋势在某些具体政策上已制造了不可逆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除了表现在前文提到的消极涉华立法之外,在对中东的政策上也非常明显。特朗普政府公开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搬迁美国大使馆,以及通过签署总统公告等单边方式承认戈兰高地是以色列领土等一系列做法,导致了美国在以色列问题上的失衡。(47) Tamara Cofman Wittes and Ilan Goldenberg, “Trump’s Golan Fiasco,” Politico , March 22,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9/03/22/trumps-golan-fiasco-226102.(上网时间:2019年5月23日)未来两党任何一位总统及其政府几乎都没有余地来改变特朗普政府的这些决定,而且极度偏袒以色列的决定也并不符合美国在中东的长远利益。(48) Aaron David Miller and Richard Sokolsky, “Trump Isn’t Just Reversing Obama’s Foreign Policies. He’s Making It Impossible for His Successor to Go Back to Them,” Politico , April 23, 2019, available at: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9/04/23/trump-obama-foreign-policy-226708.(上网时间:2019年5月23日)
第四,过载,该故障是低压变频器跳动比较频繁故障之一,由于马达的过载能力比较强,因此如果低压变频器参数表的电机参数设置合理,通常不会出现马达过载的问题;而低压变频器自身的过载能力相对较差,因此容易发生过载报警,要对发生过载时的负载压力、流量变化等情况进行仔细检查,然后检查变频器的内部电流检测回路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目前,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也正在弱化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导地位。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18年年底公布的全球民调,只有31%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将在未来十年在国际社会中拥有更为重要的地位,而且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对美国及其政府所持的积极态度在2017年之后急剧下降。在美国形象持续受损的同时,有70%的受访者认为,与美国相比,中国会在未来十年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但却有69%的受访者在中美之间更愿意选择美国作为世界领导者。(49) Richard Wike, Bruce Stokes, Jacob Poushter, Laura Silver, Janell Feterolf and Kat Devlin, “Trump’s International Ratings Remain Low, Especially Among Key Allies,” Pew Research Center , October 1, 2018, available at: https://www.pewglobal.org/2018/10/01/trumps-international-ratings-remain-low-especially-among-key-allies/.(上网时间:2019年5月23日)这就意味着,美国的领导地位即便呈现出下滑态势,但难以想象其领导地位会被很快取代。而这也为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调整留出了足够的空间与时间。
结 语
“最近三四年来发生了许许多多事情,在1957年或者1958年时是完全无法预测的。”美国历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在《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中曾记录过约翰·肯尼迪总统的这样一句话。按照小施莱辛格的判断,肯尼迪从来不会接受关于未来趋势的任何教条结论,因为在这个世界的历史中出人意料和无法预测的事情实在发生得太多了。(50) [美] 小阿瑟·施莱辛格著,仲宜译:《一千天:约翰·菲·肯尼迪在白宫》,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第682页。
球形工频电场检测传感器采用球形电容检测感应电压的方法来检测电场,一维球形传感器的结构如图1所示,将一个空心金属球壳切割成两部分,通过绝缘物质将两个半球连接在一起,并在两个半球中间并联一个测量电容,两个半球分别构成了传感器的两个电极[6-7]。
有一种历史,用汗水写就,几多慷慨,几多希望;有一种成绩,用生命铸就,几多豪迈,几多辉煌。2018年是特殊的一年。这一年,既迎来了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又迎来了中国化肥流通体制改革20周年,同时中国氮肥工业也走过了60年峥嵘岁月。六十载风雨兼程春华秋实,几代人筚路蓝缕艰苦奋斗,中国氮肥工业在几代氮肥人分秒铸就中蓬勃辉煌。
事实上,肯尼迪的观点是在努力适应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家处境的剧烈变化,也正是因为要应对这些国际与国内交错的重大变化,肯尼迪在其短暂的白宫生涯中的决策特别是对外决策才是影响深远的。从这个意义上出发,特朗普政府目前所处的内外环境与当年的情况相比无疑呈现出更加剧烈的变革需求,其在过去两年多时间内的对外政策及其影响也必然更具指标意义。
如今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政策调整似乎是与奥巴马政府的某些调整一脉相承,这当然反映了美国的国家需要。通常认为,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在纠偏地追逐“平衡”,即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的平衡、美国领导与善用盟友之间的平衡以及在中东地区与在亚太地区投入资源的平衡。(51) 刁大明:“决策核心圈与奥巴马外交”,《现代国际关系》,2015年第5期,第23~32页。 这些“平衡”在对奥巴马政府对外政策“盖棺定论”时被认为是太过理想主义,并未能实现预期效果。(52) Stephen M. Walt, “Barack Obama Was A Foreign Policy Failure,” Foreign Policy , January 18, 2017, https://foreignpolicy.com/2017/01/18/barack-obama-was-a-foreign-policy-failure/. (上网时间:2019年5月25日)而今,特朗普政府的确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但其对外政策的做法却是全然“失衡”的。这种“失衡”虽然更符合美国政治经济关系与国际地位的矛盾性现实,但却完全背离了经济全球化进一步调整与深入发展的总体趋势。但必须看到的是,美国未来的调整趋势已决定了其将持续向世界输出这种“失衡危机”。这个趋势并非因特朗普执政而起,但却因特朗普政府的政策而加剧。如何评估并应对这种“失衡危机”,也构成了国际社会必须面对的长期挑战。
[作者介绍] 刁大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美国政治与外交、中美关系。
(责任编辑:王文峰)
标签:特朗普政府论文; 对外政策论文; 大国竞争论文; 美国优先论文; 碎片化论文; 小集团思维论文;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