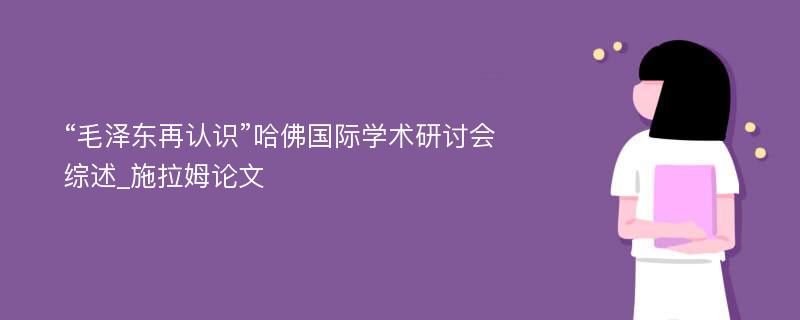
“哈佛大学‘毛泽东再认识’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哈佛大学论文,再认论文,学术研讨会论文,国际论文,述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0257-2826(2004)03-0088-05
为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并表彰斯图尔特·施拉姆(Stuart R.Schram)教授在毛泽东研究中的杰出贡献,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于当地时间2003年12月5-7日,召开了题为“毛泽东再认识”(Mao:Re-evaluated)的国际学术研讨会。
12月5日下午,大会开幕式在哈佛大学校园中心区内的博雅思通厅(Boylston Hall)举行。来自美国、英国、法国、中国、加拿大、瑞典、澳大利亚的毛泽东及中国问题研究资深专家、哈佛大学师生、国内部分访问学者约300余人,出席了会议。会议由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著名中国“文化大革命”史研究专家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主持。大会主席台的中央,摆放着1992年以来已陆续出版的毛泽东文集《通向权力之路》1-5卷和即将出版的6、7两卷的样稿。这是施拉姆教授花费了多年心血主持的、由许多西方学者精心编辑和翻译的杰作。它尽可能地收集到了目前所能收到的毛泽东手迹,以及其他重要手稿等。全书一共10卷,最后的3卷现在也已翻译完毕、等待出版。其编译和出版的全部工作,得到了美国国防部和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资助。这套装帧精美的巨译,使人们不由得对施拉姆这位将毕生的美好年华都献给了毛泽东生平及其思想研究且贡献卓著的西方学者肃然起敬,并由此引发对于毛泽东这位中国人也许永远无法忘怀的伟人认知与评价的无尽联想。
施拉姆教授1924年出生于美国,1944年毕业于明尼苏达大学,1954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长期执教于英国伦敦大学并兼任其东方与非洲学院现代中国研究所所长,1989年后任职于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他是西方世界研究毛泽东生平与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曾出版过《毛泽东的政治思想》(1963)、《毛泽东》(1966)和《未经修饰的毛泽东:谈话与书信(1956-1971)》(1974)、《毛泽东的思想》(1989)等许多有影响的论著。这次会议以纪念毛泽东诞辰和表彰施拉姆教授学术贡献为名再认识毛泽东,也可见西方学术界对其研究成就和学术地位的高度认可。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施拉姆的有关著作就曾被译成中文大量出版,他的名字在中国不仅为一般学者所熟知,许多关心政治和现代历史的中国人也并不陌生。然而在中国却很少有人知道,施拉姆在转向毛泽东研究之前,曾经是一个核物理学家,曾参加过著名的“曼哈顿计划”的工作,还是一个有出色语言天分的法国和俄国政治研究者。
在12月5日下午的会议上,著名的毛泽东传记作者、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教授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教授安瑟利·塞奇(Anthony Saich),耶鲁大学的乔纳森·史本思(Jonathan Spence)和戴维·阿帕特(David Apter),英国利兹大学的德里尔·戴韦因(Delia Davin)等人在发言中,都高度赞扬了施拉姆教授的功绩。来自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的逄先知研究员,对于施拉姆在研究、翻译毛泽东著作中所花费的巨大心血和所做的艰辛开拓工作,更是给以高度的评价,他认为施氏对于西方学者了解、研究中国革命及其毛泽东思想做出了巨大贡献。他还提到,施拉姆在其研究工作中,一直与中央文献研究室保持着很好的合作关系,并曾多次就毛泽东著作中有关版本的选择、时间的考证等问题求证于中央文献研究室,表现出了一个学者令人尊敬的严谨治学态度。在回答现场听众关于是否这套译著已经囊括了毛泽东的全部文稿时,逄先知说,尽管十卷本的译著出齐后,英文的毛泽东文稿将比中文已出版的还要多,但由于各种原因,它仍然无法彻底收全毛泽东的所有文稿。
在提交给会议的论文中,学者们也多从各自的角度称赞了施拉姆教授的贡献,尤其是他翻译毛泽东著作的成就。如弗吉尼亚大学教授布兰克利·沃马克(Brantley Womack)在论文中就强调指出:“关于毛早期政治思想的记录,由于施拉姆及其同事所编的《通往权力之路》的努力,而大大地增加了。我们可以循此记录,追踪其思想、活动之互动及其成功和失败的经历”。作为《通往权力之路》一书翻译的参加者,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提墨思·奇克(Timothy Cheek)更是充满感情地写道:“与施拉姆一起翻译毛的文本是一种荣誉,也是一种训练。我感觉翻译其中一卷已经是筋疲力尽,真无法想像施拉姆怎么能把整个十卷进行到底。然尽管如此,与施拉姆一道工作的过程中,当我们检查每一个文本、每一页、每一段、每个句子或用词之时,他那全神贯注的凝视,仍然长久地保持在我的记忆里”。他非常感谢施拉姆给予了他必要而珍贵的训练机会(参见其论文《整改延安道路》)。斯坦福大学现代中国研究权威范斯莱克教授(Lymanp Van Slyke)甚至认为:“正如人们无法想像中国革命离开了毛泽东一样,离开了施拉姆的工作,也将无法想像在研究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西方学者将如何理解毛泽东”。(参见其论文《反思毛泽东思想》)
如何宏观评价毛泽东,也是12月5日下午会议的主题之一。与会学者虽见仁见智,但都能客观地正视毛泽东及其思想的巨大影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露西恩·派伊教授(Lucian Pye)是西方毛泽东研究的前辈学者,向来被中国国内的同行视为“西方毛主义研究第三次论战”中的代表人物。他关于毛泽东个性意义的政治心理分析的有关研究,曾在西方世界产生过广泛影响。这次在发言中,他仍然强调心理分析对认知毛泽东的历史价值,并认为,尽管毛泽东的一生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历史性的缺陷,其本人也经受过许多失败,犯过许多错误,但他仍然称得上是一个民族英雄,值得人们尊敬。美国里海大学的雷蒙·怀利教授(Raymond Wylie)也是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的专家,他关于陈伯达与毛泽东思想形成关系的论著久为同行推重,这次在发言中则强调,毛泽东乃是一位革命的浪漫主义者,他由此给中国带来过深重的灾难,也留下了“极其复杂”的历史遗产,其功过是非难以简单评断,值得后人深入研究和反思。最后,80高龄的施拉姆教授作了总结性发言,他较客观地评价了毛泽东一生的历史功过,说明他在研究了中国问题和毛泽东的著作14年之后,认同了这样一个结论,那就是,毛泽东虽然在掌权之后犯过严重错误甚至“可怕之罪”,但他仍然不愧为是一位伟大的革命领袖。在回答现场关于为什么不能将“他的遗产”与斯大林等人相提并论时,他明确地回答说:“从许多方面看,毛力图为中国人民谋利益,只不过50年代以后,他在个人的情感方面,过于感情用事、固执任性和狂热,从而铸下大错,但尽管如此,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领袖,他总是想把最好的东西留给中国,我认为人们会因此而永远铭记他”。
国内学者李锐将近几年所写的两篇论文以《我曾写过的评论》为题,译成英文,提交大会印发。他本人则因为健康原因没有亲自出席会议。李锐在文中重提了他过去对毛泽东作革命、建设和“文化大革命”分开评价的观点,并认为历史学者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应以弄清历史真相、进而总结经验教训为目的,而不是进行道德的谴责,引起与会学者的关注。
如果说12月5日下午有关毛泽东的再认识还显得有些粗线条,那么接下来两天(12月6-7日)的专题研讨,则要细致和深入得多。大体而言,讨论主要涉及了毛泽东思想的形成与特征,毛泽东早期的政治理论与实践、毛泽东关于中国农民的思想及其由来,延安整风、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与评价,以及毛泽东的个性及其历史和现实影响等等问题。会议指定的主题发言人,几乎都是在毛泽东研究领域很有成绩的西方学者。而参加会议者和主持评论者,除了前文已经提到的之外,还包括国人熟悉的哈佛大学著名汉学家裴宜理、孔飞力和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弗尼德里克·泰伟斯(Frederick Teiwes)等人。泰伟斯教授也是澳大利亚著名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曾参与《剑桥中华民国史》的撰稿,并出版了关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思想政治运动的著作多种,在西方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问题,是本次研讨会最为主要的论题之一。斯坦福大学的范斯莱克、耶鲁大学的阿帕特和弗吉尼亚大学的沃马克等人的论文,在这方面进行了集中探讨。范斯莱克教授的论文题目为《反思毛泽东思想》。文章认为,毛泽东的思想在形成时期非常注重从实际出发,甚至表现出某种轻视理论、极端重视实践的实用主义倾向。后经过不断的总结,最终形成思想体系并被中共全党所接受。此后,从根本上说,它就不再开放和发展,因为它已经变成了“最后的话语”。这个特征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小红书”将毛泽东思想作为永恒正确的原则推向了教条主义的极端。尽管毛泽东始终倡导实事求是的原则,但这一主张后来实际上被掩盖了。文章还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详细地分析了毛泽东的思想怎样从具体的、重视实际的、灵活的思想向着所谓“抽象的、先验的、僵硬的”思想转化的历史过程。
阿帕特教授则从所谓“宗教”性角度来认知毛泽东思想。他坦承自己这样做基于两个原因:一是鉴于此一方面在当今中国已趋向于被遗忘,而随着经济的惊人发展,它在未来仍有可能以某种新的形式复活;二是鉴于在全球所谓各种“严肃的社会主义”离去之后,它所遗留的空间迅速被各式各样的宗教运动所占领的现实。在其所提交的《寻找证据:作为宗教的毛主义》一文中,他将“毛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宗教”(political religion)来看待。认为政治宗教之信仰,缺乏普通宗教那种自我充实和更新完善的能力,过期就会失去效能。要想维持住权威,只好使之仪式化,其内容越空,就越需要强调其理论的正统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义”就充分体现了这一特性。为了说明其观点,阿帕特苦心孤诣地选用了延安时期西方报道毛泽东的著名人物“三S”(斯诺、史沫特莱、斯特朗)的著作来作为分析论据,理由是:“通过考察与之构成同谋关系的某些外来者的观点,可能看到对毛主义的宗教维度之最佳描述,人们由此也能更好地了解在那个时代该主义的这一方面是多么的强烈”。尽管作者反复说明“政治宗教”和普通宗教存在差别,同时强调他并不想以此遮蔽“毛主义”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等其他方面特征,但其所谓“宗教”概念的使用仍然含糊不清,因此,其基本观点也难以得到许多学者的认同。会上,逄先知研究员就对此提出了明确的质疑。他强调宗教最基本的特征是承认超自然的神的力量,而毛泽东思想则从根本上就是彻底反对有神论的。所以它绝不是任何意义上的宗教,而是从实践中不断总结出来的革命理论。至于它曾经被神话,那则是另外一回事情。中共把一个被西方列强欺压奴役的破碎的中国,改造成一个有力量的国家,没有这一理论的指导,是不会成功的。
说起“意识形态理论”,不能不提到弗吉尼亚大学的沃马克教授。沃马克是西方毛泽东思想研究方面成绩突出的学者,被中国国内同行视为“西方毛主义研究第四次论战”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多年来,从“意识形态特征”角度来认知毛泽东思想,可以说是他一以贯之的重要着眼点之一。不过这次,在他所提交的论文《抓住旗帜: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之前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发展》中,他对这一问题的阐述,又采取了使用一种所谓的“政治(学)范式”(political paradigms)来涵盖“意识形态功能”,再次加以整合分析的新策略。他认为,这种“政治范式”不同于托马斯·库恩的正规科学范式之处,主要表现在两点上:“一是,正规科学及其范式变化之间的那种反差,在政治范式中却并非那样截然的两分;二是,也是更为重要的一点在于,科学范式中那种科学信念的假定品格,在政治范式中却被一种对意识形态的本体论真理之信仰所取代。意识形态的实践允诺和约定,意味着(科学范式中的那种)证实过程也被一种远为复杂的成功与失败的过程所取代”。也就是说,政治范式供给一种意识形态信仰,它在功能上,“能为政治行动提供一套必要的,具有一致性、整合性和可以理解的解释结构和组织框架”,但它本身并不需要在实践中被验证究竟正确与否,成与败乃是其实际准绳。沃马克表示,他的这篇文章,就是要从这种“政治范式”的角度,“来为毛泽东政治学说中理论与实践的互动,提供一种解释性叙述”。
在沃马克教授看来,1927年前毛泽东政治思想中理论和实践的变化幅度,要远比他后来50年还深刻得多。而其早期的政治思想的演变过程,恰好为理解政治学上的范式运动提供了丰富而生动的见证。他强调,毛泽东早期的中心思想和核心考虑,乃是要“抓住一面可供挥舞的旗子”,以解决“理论和实践互动的难题”。为此,毛从暖昧的个人主义,转到无政府地方自治主义,再到从意识形态和组织上转到共产主义,然后,再在这一大的框架下继续找寻,不断变化,直到1937年后确立一套自己独特成型的思想解说,最终完成能整合革命理论和实践的意识形态结构需要为止。
应当说,沃马克教授的有关阐释不无复杂性和深刻之处,但他那过于模式化的努力,同时又显示出某种刻板性和简单化的偏向。许多西方汉学家讨论中国问题时,都容易给我们留下这样一种印象。不过,沃马克的许多认识和思考,对我们认知毛泽东,仍是富有启发性的,如他在文章末尾的论评,就是如此:“毛泽东注重实践和行动的可行性,这使得他脚踏实地,同时,他对民众动员功效的信念,则为其政治学说提供了最为基本的导向。……或许这种重实践的灵活的一贯性,既是他1957年以前成功的关键,也是理解他后来悲剧的关键”。
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认知和反思毛泽东,不能忽视其对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的看法。本次会议上,法国科学高等研究院的资深研究员、著名学者毕仰高(Lucian Bianco)提交了厚厚一册的《毛的农民观》一文,颇引人注目。
毕仰高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写过《中国革命起源》的专著,又曾是《剑桥中华民国史》第13卷“农民运动”一章的作者,这次他提交的论文,不仅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较为系统地分析和总结了毛的农民理论及其在中国革命中的影响和地位,还很注意将毛对于中国农民和农村问题的看法,与同时代其他中共领袖以及社会经济学者的有关调查进行对照分析,以透视其特征。如他将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几乎同时代发表的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进行对比后就认为,彭湃对农民的革命性给以肯定的同时,对农民所表现出来的麻木和“宿命论”也多有描述,较为全面可靠地指出了农民在革命中所具有的积极面和消极面;而毛则更多地是对农民的革命性加以赞颂、对农民运动持更为积极乐观的态度。作者还将毛1930-1933年发表的几篇著名的农村调查报告,与同时代费孝通的《中国的乡村生活》、陈翰笙的《中国的地主与农民》等相比较,指出费、陈等作为社会科学家,比毛具备更多的专业知识和更为充分的条件从事较为系统严谨的研究,“他们的报告不是在匆忙和纷扰中依靠少数同情革命的信息完成的”;而毛作为革命家,则既无兴趣、更无时间去进行细致而全面的学术性考察,他的著作更关心的是:从农民和农村中去寻找发动革命的因素而已。毕仰高还指出,毛在农民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对我们了解他一生的个性和革命事业也有重要意义:“为了设计一个有效的战略,以便在正确的方向领导和动员劳动大众,毛总是过于乐观地强调事物发展的积极方面,这一点,也成为他日后发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起因之一”。
延安整风、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以及近些年为何出现“毛泽东热”,是这次学者们反思历史、再认识毛泽东的几个重点区域。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奇克、北京大学教授乐黛云和瑞典隆德大学教授迈克·斯考恩斯(Michael Schoenhals)和美国印地安纳大学教授杰弗瑞·沃思卓姆(Jeffvey Wasserstorm)等,分别作了主题发言,或以新方法新观点以及比较研究见长,或以亲身经历立论,引起了与会者的广泛兴趣。
奇克教授发言的论题是《整改延安道路:从概念史透视毛的整风文件》。他研究了延安时期毛泽东及其党内权威发言人的整风文件,通过透视其中习惯使用的围绕着“革命”、“党”、“整风”的一系列一般概念,如“宣传”、“党性”、“清算”、“思想”、“精神”、“态度”、“立场”、“观点”、“动员”、“纠正”、“自我批评”、“党风”、“学风”、“文风”、“党八股”、“理论家”和“自由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等等,从中得出其赖以依存的两个“基本的概念”,即他所说的“思想术”(the technologies of sixiang)之根据,也就是所谓行为上的“态度决定论”(attitudinal fundamentalism)和认识论上的“精英主义”(epistemological elitism)。这大概接近于我们中国人常说的基本“思维方式”。作者认为,即便是当时被批判的王实味,也并未逃脱这两个“基本概念”的制约。它们不仅有助于解释延安时期和其他时期中共的政治实践,甚至直到今天,依然是构成中国人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不容忽视的重要历史因素。从这一“概念史”分析的角度出发进行把握,作者还强调当时思想改造的宣传教育动员、组织上的纪律规训和安全部门的“审干”抢救运动,构成了延安时期整风运动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很看重自己这种“概念史”的研究方法,认为它通过概念分析,将文本和语境、观念和社会历史有机地结合起来,能够发掘出过去人们所不曾注意到的有意义的历史内容。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西方汉学家中重“政治文化”研究的一批人,已经逐渐具有了此类研究取向。如前文所提到的耶鲁大学阿帕特教授,1994年就曾与托尼·塞奇(Tony Saich)教授合作出版了《毛泽东中国的革命话语》一书,在美国汉学界很有影响,引用率颇高。
同样从广义的政治文化角度关注延安整风运动,来自中国大陆的乐黛云教授则把历史的镜头拉得更远。在《灵魂怎样被盗:从1942年的延安整风到1957年的反“右”运动——一个个人的视角》一文中,她从阅读孔飞力描述乾隆时代政治案的《叫魂》一书的感想出发,结合韦君宜《思痛录》的“审干”回忆和自己在北京大学反“右”运动中的亲身经历,进行了痛切的反思,期望杜绝此类悲剧在中国历史上重现。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李捷研究员,也就延安整风的情况和意义,谈了自己的看法。他强调对延安整风运动的反思,应该避免情绪化倾向,要以严谨可靠的材料说话。此外,迈克·斯考恩斯和杰弗瑞·沃思卓姆两教授,以《“我们何不武装‘左’派”》,《两种革命的神话:作为全球偶像的毛泽东和格瓦拉》为题作了发言,对“文化大革命”中武装“左”派的问题与毛泽东的关系,以及近年来中国的“毛泽东热”,进行了新颖的分析。
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上,既有缜密的论证,也有热烈的争鸣,特别是与会西方学者对于毛泽东及其有关中国问题的熟稔与精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每当主办方为中国学者配备的翻译(两位在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留学生),被“小农意识”、“武装割据”、“整风运动”、“教条主义”等类术语所卡住、一时不知如何传译之时,在场的绝大部分学者多能脱口而出、为之解难。会上,当来自国内的学者在延安整风等问题上发生激烈争执时,外国学者中竟有以“人民内部矛盾”当场劝解打趣的,并因此引来全场会心的笑声。大会召开期间,恰逢波士顿出现了近几年少见的大雪天气,市内交通几近瘫痪。笔者赴会,也只能头顶漫天飞雪、脚踏茫茫白路,一步步艰难地前往。沿途人踪寂灭,不乏孤畏之感。6日黄昏,学者们在厚达两尺多的积雪中步行出席在“常熟饭庄”召开的晚宴,一路上,会议主办方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负责人还不断以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话语”相激励,令人忍俊不禁。
参加三天的研讨会,特别是在后两天的研讨会上,凝听各国学者在熟悉的毛泽东话语中展开中西对话,不时地张望窗外纷飞的大雪,实在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至今追思,犹有所感。正可谓:异乡言说毛泽东,语境心思各不同;论评有别如飞雪,碧眼黑眸两相通。
标签:施拉姆论文; 毛泽东论文; 中国宗教论文; 中国近代史论文; 中国学者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宗教论文; 范式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