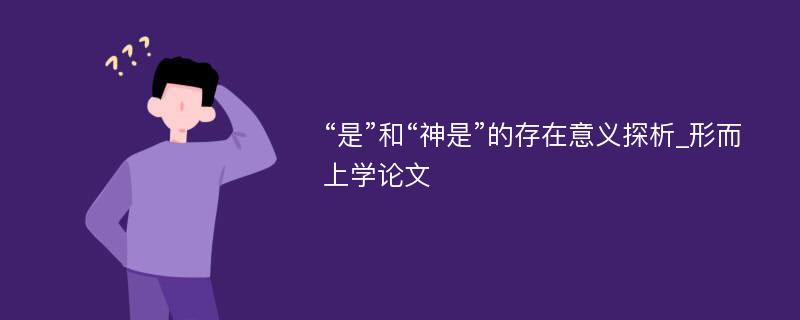
“是本身”与“上帝是”——“是”的存在涵义探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涵义论文,上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亚里士多德提出研究“是本身”(或“作为是的是”),开创了形而上学的研究。“存 在”是一个与“是”不同的概念,却是在“是”的研究过程中发展产生的。有关存在问 题的许多思想是在现代产生形成的,但是作为一个概念,它却是在中世纪被明确提出并 确定下来。我们可以简单地说,中世纪哲学(注:也可称它为基督教哲学。参见Armstrong,A.H.:《剑桥史:希腊晚期和中世纪早期哲学》(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Greek and Early Medieval Philosophy,Cambridge 1967);Kretzmann,N.:《剑 桥史:中世纪晚期哲学》(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Medieval Philosophy,Cambridge 1982);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人民出版社,1994年。)继承了亚 里士多德传统,发展出关于存在的论述。但是实际上,这里存在着非常复杂的现象和问 题。本文想就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而且主要是围绕着与是相关的问题进行探讨。鉴于中 世纪时间跨度大、人物众多、著作卷帙浩繁,本文将选择波爱修和托马斯·阿奎那进行 讨论。前者是从古希腊哲学到中世纪哲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过渡人物,他的思想对中世 纪哲学影响极大。后者是中世纪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代表性的哲学家。此外,本文还要 讨论一些逻辑学家的论述,这些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一
波爱修(480—525)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他翻译和注释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 著作,这些著作先后成为中世纪的基本教材。其中,《范畴篇》和《解释篇》很早就成 为基本教材,甚至是“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惟一教科书”(注:威廉·涅尔:《逻辑学的 发展》,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44页。),影响很大。他的翻译“极其忠实于原文,竭 尽全力逐词逐句把原文表达为规范的拉丁文句子结构”(注:Ebbesen,S.:《亚里士多德 注释家波爱修》,载《过渡时期的亚里士多德》(Boethius as an Aristotelian Commentator,in Sorabji,R.ed.:Aristotle Transformed,Gerald Duckworth & Co.Ltd .1990,p.375).)。由于他的这些翻译,他是中世纪哲学“最重要的语言创制者”(注:Schulthess,P./Imbach,R.:《拉丁中世纪的哲学》(Die Philosophie im Lateinischen Mittelalter,Artemis & Winkler Verlag Zuerich 1966,s.62.),他“将一些重要哲 学概念由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并规定了它们的标准定义”(注: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 500年》,第183页。),由此对中世纪哲学产生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他撰写了许多著 作,内容广泛,包括哲学、逻辑、数学和神学等等。他的这些著作不仅影响大,而且极 为广泛,有的甚至“被思想家和诗人称为杰作”(注:Marenbon,J.《早期中世纪哲学》 [(Early Medieval Philosophy)(480—1150),Routledge 1991,p.27]。)。
波爱修讨论神学问题的5篇文章构成《神学文集》(Opuscula Sacra),其中第三篇论文 专门探讨是这个概念。在这篇文章中,波爱修不仅对是的不同含义做出一些区分,而且 还提出了9条公理。在这9条公理中,第一条是关于公理的一般性质,主要说明公理的涵 义,即公理是一些陈述,它们一旦建立,一般就被接受。第九条公理是阐述愿望和善, 以及与它们对立的东西之间的复杂关系。其他7条公理则直接与是有关。这7条公理如下 (注:参见De Rijk,L.M.:《论波爱修的“是”这个概念》,载《中世纪哲学的意义与影 响》(On Boethius's Notion of Being,in Meaning and Inference in Medieval Philosophy,ed.By Kretzmann,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pp.18-21)。):
公理二:是和是者乃是不同的;确实,自身所接受的是尚不是;而接受了是的形式的 是者才是作为一个实体。
公理三:是者可以被其他某种东西所分享;然而,从是的自身考虑时,是却不能被其 他任何东西所分享;因为当某种东西已经是时,就产生了分享,而且当某种东西接受了 是时,情况就是这样。
公理四:是者除了它本身是什么以外,也能具备某种东西;然而,从是的自身考虑时 ,是却没有任何混合物。
公理五:仅仅是某种东西与是某种作为是的东西乃是不同的;前者确实表示某种偶然 的情况,而后者表示一种实体。
公理六:所有为了是而分享是的东西都为了是某种东西而分享“某种东西”,因此, 是者为了是而分享是,但是,为了分享随便什么东西,是者是。
公理七:所有简单的东西都有它的是和它的所是,二者是一样的。
公理八:所有复合的东西与是乃是不同的,它们的是本身也是不同的。
关于这7条公理,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它们的出发点是一个形而上学论题:对每一 个是者,是和是善的乃是一样的。其次,波爱修对这些公理的论述非常简洁,解释不多 ,他把合适的论证留给了“聪明的解释者”(注:Marenbon,J.《早期中世纪哲学》[(Early Medieval Philosophy)(480—1150),p.38]。)。第一点表明,这些公理的论述 与上帝有关。因为考虑这个形而上学论题的人实际上必须要区别两种东西:一种乃是是 善的,另一种则是善自身。而在神学家那里,善自身就是上帝。第二点表明,这些公理 被看作是自明的,因此没有过多的解释。这样,一方面我们需要依赖于字面的意思来理 解它们,另一方面也需要联系一些背景知识来理解它们。
在这些公理中,据我所见,比较清楚的思想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区别是与是者。不仅 公理二明确地这样说,而且好几条公理(如三、四、六)都阐述了它们的区别。其次是区 别是与是某种东西,如公理四、五、六等,并以此说明是与是者的区别。特别是,这两 种区别基本上构成了这7条公理的核心思想,因此值得我们认真思考。
从字面上看,理解“是某种东西”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它的表达方式乃是“S是P ”,这也符合我们的习惯。而理解单纯的“是”则会有些问题,因为它的表达方式乃是 “S是”,这不太符合我们的表达习惯。不过,如果我们可以习惯这样的表达,那么也 就不会存在理解的问题。假定这样的表达是正常的,那么“S是”与“S是P”当然是不 同的。从字面上看,是(esse)与是者(id quod est)显然是不同的。因此也应该没有什 么理解的问题。这样,结合“S是”与“S是P”的区别,一些基本的思想就清楚地表达 出来。比如,“是者是”与“是者是某种东西”是不同的。
应该说,以上理解是清楚的。但是,它仅仅是一种句法方面的理解。我们显然还应该 从语义方面进行理解。在这种意义上说,是与是者乃是不同的。因为是者分享是,是却 不分享是者;是者可以被其他某种东西所分享,是却不能被其他任何东西所分享。因此 ,是乃是第一位的东西。这样,单纯的是与是某种东西乃是不一样的。由此也就区别出 简单的东西和复合的东西。简单的东西有是和它的所是,而且它的是和它的所是乃是一 样的。但是复合的东西却不是这样,它与是不同,而且它们的是本身也是不同的。根据 这样的理解,是者和是似乎都成为思考的对象,而且是不同的对象。
如果我们把句法和语义的理解结合起来,就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我们可以说“一事物 是”,也可以说“一事物是某种东西”,然而它们是不同的。这里的区别主要在于“是 ”有不同的涵义和作用。
我认为,尽管波爱修的这7条公理还涉及许多东西,但是与本文相关,上述理解乃是它 们最主要的内容和思想。如果对比一下他与亚里士多德的相关论述,我们很容易发现, 他与亚里士多德有一点非常不同。亚里士多德在论述中谈到“S是”与“S是P”是不同 的,但是认为它们区别很小,并且主要论述的乃是“S是P”,而对“S是”并不怎么强 调(注:参见王路:《<工具论>与<形而上学>——理解亚里士多德》,载《清华哲学年 鉴》2001年。)。波爱修则非常强调“S是”与“S是P”的区别,并且突出“S是”的意 义与作用。鉴于波爱修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家和注释家,他的许多思想基本上也是 来自亚里士多德。因此一个直观的问题是,为什么在论述是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上,波 爱修会与亚里士多德有如此重大的区别?
我认为,这主要是探讨的对象造成的。前面我们说过,波爱修的这篇论文是为了论证 是与是善的之间的区别,而是善的乃是指上帝。因此,波爱修的探讨与上帝有关。为了 说明这个问题,我们还可以看一看波爱修在注释亚里士多德的《解释篇》中的一段话:
当我们说“上帝是”时,我们不是说他是现在,而只是说,他是处于实体中,在这种 程度上,这个(“是”)确实不是与某个时间,而是与他的实体的不变性相联系的。但是 ,如果我们说“这是白天”,那么它(即“是”)与“白天”这个实体没有关系,而是仅 仅与它的时间确立有关。因为这乃是“是”所表示的东西,一如我们说“是现在”。所 以,当我们使用“是”来表示实体时,我们在没有限制的意义上加上“是”;然而,当 我们以某种方式使用“是”,从而使某种东西被表示为现在时,我们在时态的意义上加 上它(注:De Rijk,L.M.:《论波爱修的“是”这个概念》,载《中世纪哲学的意义与影 响》(On Boethius's Notion of Being,in Meaning and Inference in Medieval Philosophy,ed.By Kretzmann,N.,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1988,p.14)。)。
波爱修作出这段注释是为了区别实体和现在时这种时态。关于时态的论述,他与亚里 士多德差不多。但是关于实体的论述,他显然有一些独到之处。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在 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时候引入了“上帝是”这样的例子,并且根据当时人们对上帝 的认识来论述是,这样,“是”就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意义,用他的话说,就是与上帝的 实体的不变性相联系,因此也就有了与一般所说的是的区别。如果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 波爱修的7条公理,也就比较容易理解为什么他一定要强调“S是”与“S是P”的区别。 因为“S是”不是无足轻重的,而是“上帝是”这个句子的句式的具体体现。
按照后来中世纪的讨论以及今天的一般认识,“上帝是”的涵义就是“上帝存在”。 因此这里似乎自然而然也当然考虑,波爱修所说的“S是”究竟是不是“S存在”,或者 说有没有“S存在”的意思?实际上,学者们在这一点上观点并不一致。比如关于公理中 所说“是者”的理解。有些人认为这里所说的是者乃是指存在者,这样的理解,尤其是 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是比较容易接受的。但是也有人认为,把是者(id quod est)翻 译成“存在者(that which exists)”乃是“严重的误解”,这里所说的“是(esse)” 与外界中的存在没有任何关系(注:参见同上书,第19页。)。我认为,究竟这两种看法 哪一种更有道理,乃是可以研究和讨论的。但是有一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虽然波爱修 在解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时引入“上帝是”这样的例子,虽然他带着关于“上帝是 ”这样的思考强调“S是”和“S是P”这样的句子的区别,因而强调“是”的不同涵义 ,甚至也许已经在存在的意义上探讨了是,但是他确实没有引入“存在”一词。因此我 们至少可以非常保守地说,他还没有明确地提出“存在”这个概念,也没有十分明确的 关于存在的讨论。
尽管波爱修没有十分明确的关于存在的探讨,但是他关于是和是者的区别,关于简单 的是与是某物的区别却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公理七,虽然他还没有明确地探讨 本质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但是这里已经“暗示”了后来所谓上帝的本质和上帝的是乃是 同一的思想(注:参见同上书,第21页。)。他的这些讨论“常常被13世纪参加关于本质 与存在之间的关系的讨论者所引用”(注:Kretzmann,N.:《剑桥史:中世纪晚期哲学》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Medieval Philosophy,p.393)。),产生了非常大 的影响。
二
托马斯·阿奎那(1224/1225—1274)是中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有人认为他是中世 纪最重要的哲学家(注:参见赵敦华:《基督教哲学1500年》,第364页。),也有人认 为他是神学家,“谁若是不把他作为神学家来理解或解释,就错误地理解他”(注:Thomas von Aquin:《亚里士多德译注序》(Prologe zu den Aristoteleskommentaren,uebersetzt von Cheneval,F./Imbach,R.,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93,IX)。)。这两种观点均有许多支持者。我想,评价这两种观点哪一种更有道理, 即使简单做一表态,也会涉及对哲学与神学本身的理解。这样的工作无疑超出本文的范 围。但是探讨托马斯的思想,肯定要涉及哲学与神学的讨论,因而无法回避对于哲学与 神学的理解。由于本文主要探讨哲学,因此我们关于托马斯思想的探讨也侧重在哲学方 面。鉴于这种考虑,我们不探讨他的《神学大全》。虽然这是他晚期的成熟的著作,是 他最重要的著作,尽管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他的哲学著作,然而这是一部神学著作乃是确 切无疑的。下面我想主要讨论他的《论是者与本质》。这是他的早期著作,尽管里面也 有许多关于神学的讨论,却无疑是他的哲学著作。有人认为这是托马斯“文选中最著名 的著作,而且毫无疑问是人们真正研究过的惟一著作”(注:Thomas von Aquin:《论是 者与本质》(Das Seiende und das Wesen,Lateinisch/Deutsch,uebersetzt von Beeretz,F.L.,Philipp Reclam 1987,s.110)。),显然它也是十分重要的。除此之外, 它与本文所讨论的内容直接相关。
《论是者与本质》不长,主要探讨如何理解是者与本质。在开篇处,托马斯指出讨论 这一问题的三个难点。第一,是者和本质这两个概念是什么意思?第二,本质在不同事 物中是如何体现的?第三,本质与属、种、种差等逻辑概念是如何联系的?该书的论述基 本上是围绕这三个问题展开的。前三章分别讨论了这三个问题,后三章进一步讨论了第 二个问题。所以,托马斯重点讨论的是第二个问题。
理解托马斯的思想,第一章至关重要。它解释了是者和本质的含义,成为后面几章探 讨的基础。我认为,这一章有三段话值得我们认真思考。首先是下面这段话:
[引文1]正像哲学大师在《形而上学》第五卷所说,是者本身乃是以两种方式谈论的。 以第一种方式它分为十种范畴。以第二种方式它表示命题的真。
……
本质这个词不是取自是者这个词的第二种意义。……本质乃是取自是者的第一种意义 。(注:Thomas von Aquin:《论是者与本质》(Das Seiende und das Wesen),Lateinisch/Deutsch,ss.4-5;Thomas Aquinas《论是者与本质》(On Being and Essence,tr.By Maurer,A.,The Pontifical Institute of Mediaeval Studies,1950,pp.26-27)。)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托马斯的论述是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出发的。由此也说 明,他对是者和本质的解释基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具体地说,他把亚里士多德关于是 者的论述简单地归结为两种意义,并由此得出本质的意义。是者可以在表示范畴的意义 上理解,也可以在表示真的意义上理解,而本质只能在表示范畴的意义上理解。在这种 意义上,本质表示某种东西,这种东西对于某一种类中所有事物乃是共同的。本质常常 被用来表示一事物是什么,这种是什么有时候也被称为形式,或被称为本性(自然)。托 马斯引用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五卷的话说,每一种实体都是一种本性。由此出 发他认为:
[引文2]在这种意义上,本性这个词似乎意谓事物的本质,一如它与事物的专门活动有 关,因为任何事物都不是没有其专门活动的。而是什么一词来自定义所表示的东西,但 是本质意谓这样的东西,通过它并且在它之中一个是者具有是(注:《论是者与本质》( 德文版),第8—9页;英文版,第28页。)。
引文2之所以重要,乃是因为其中对本质得出了新的意义,即通过本质,或者在本质中 ,一个是者具有是。尤其是对照第一段引文,这种差异看得非常清楚,因为那里没有这 样的描述。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下面的引文中,还可以看到这种新的意义:
[引文3]此外,一些实体是简单的,一些实体是复合的,并且本质是在二者之中。但是 ,在简单实体中,本质表现得更真,更完善,因为它们也具有更完善的是。就是说,它 们是复合实体的原因,至少第一简单实体,即上帝,就是这样。(注:《论是者与本质 》(英文版),第8—9页;第29页。)
这里不仅又提到了本质的新性质,即“具有是”,而且对实体和本质也有了进一步的 说明。实体分为简单的和复合的,本质在简单实体中,也在复合实体中。此外还说明, 简单实体是复合实体的原因。
从这三段引文可以看出,托马斯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思想出发,对本质提出了新的 解释。清楚了这一点,我们大致也就可以明白,后面他的论述都是为了说明他在这里所 说明的东西。
阐述和解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思想,或者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和思想出发,阐述自 己的思想,是中世纪哲学家的普遍做法。因此,中世纪哲学家的许多思想是与亚里士多 德的思想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在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应该指出的是 ,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前分析篇》、《后分析篇》等著作传入欧洲中世纪较 晚,大约12世纪的时候开始可以见到这些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到了13世纪,这些译本才 开始广泛流传起来。人们一般认为,托马斯的《论是者与本质》这部著作大约写于1254 —1256年。因此从时间上看,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大约刚开始流传起来。亚里士 多德的《形而上学》无疑有对是、是者、实体、本质等等的探讨,因而也有对形式与质 料,定义、属、种与种差的探讨。特别是,这部著作明确提出研究是本身。因此托马斯 从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出发来探讨是者与本质,乃是最自然不过的。
尽管托马斯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出发,但是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理解与亚里士多德 显然是不同的。亚里士多德对本质有比较明确的说明。虽然对本质的说明涉及形式与质 料等一些问题,有时候也比较复杂,然而比较简单的说明乃是定义表达本质,而定义由 属加种差而形成。因此人们大致也可以体会什么是本质。这种本质也就是一种是什么。 比如说,动物是人的本质,或者说,理性动物是人的本质。但是,无论复杂还是简单, 亚里士多德对于本质都没有托马斯所说的“具有是”的解释。我认为,这里有一个问题 是值得认真对待的。一方面,我们不能断然地说托马斯曲解了亚里士多德,另一方面, 我们也不能简单地说托马斯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关键是,无论亚里士多德的思想 有什么样的问题,比如属加种差是不是能够表达本质,属和种差是不是清楚,等等,至 少本质表达出是什么,这一点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本身来 看,本质这个词的字面意思也是“是什么(ti esti)”(注:参见王路:《“是”、“所 是”、“是其所是”、“所是者”——关于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几个术语的翻译》 ,载《哲学译丛》2000年第2期;载王路:《理性与智慧》,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 。问题是,从是什么能不能得出“具有是”?也就是说,托马斯的这种新意是不是从亚 里士多德关于本质的论述自然而然地得出来的?
我强调这里的问题绝不是想小题大做。因为托马斯对是(esse)与本质(essentia)的区 别是非常出名而重要的,在中世纪哲学家的相关讨论中也被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这一 区别不仅与后来的存在与本质的区别相关,而且被认为促成并导致了这样的区别。托马 斯的有关思想是在后来的著作中发展起来和全面阐述的,但是该书的英译者认为,他在 《论是者与本质》中“正在制定形而上学中一场革命的纲领”,简单地说,这场革命就 是使形而上学家一直留恋于形式和本质的兴趣“转向了存在的活动”(注:参见Thomas Aquinas:《论是者与本质》(On Being and Essence),译者序,第8—9页。)。基于这 种认识,英译者甚至把该书中“具有是(habet esse)”这一表达式直接译为“具有存在 的活动[has its act of existing(esse)]”(注:同上书,第28页。),尽管译者承认 这个在书中经常出现的术语是“未定义的”(注:同上书,第11页。)。我认为,英文的 具体翻译是有问题的,但是上述评价却是可以接受的。
后来托马斯确实对表示活动的是有明确的说明。他认为,是(esse)的意义来自动词是( est),是本身的意义并不指一个事物的是。它首先表示被感知的现实性的绝对状态,因 为是的纯粹意义是在活动,因而才表现出动词形态。是这个动词的重要意义表示的现实 性是任何形式的共同现实性,不管它们是本质的,还是偶然的(注:赵敦华:《基督教 哲学1500年》,第375页。)。他明确地说:
是指谓一种特定的活动;因为说一事物是,不是因为它是处于潜在状态,而是因为它 是在活动中。(注:Copleston,F.S.J.:《哲学史》(A History of Philosophy),The Newman Press 1985,Vol.II,p.332.)
是这个词具有在活动的意义,在托马斯的这些论述中表达得清清楚楚。正是根据这一 点,托马斯区别出本质与是的两种不同的含义,而这种具有活动意义的是表达的就是存 在。在上述《论是者与本质》一书的第二段引文中,我们还看不到这样明确的说明,但 是,有一点却是清楚的:托马斯似乎确实想表示出是这个词具有表示活动的性质和特点 。因为他谈到“任何事物都不是没有其专门活动的”。以此类推,他大概是想说,是这 个词所表达的东西也应该是有专门活动的,或者说,由于任何东西都可以表达为是,因 而是乃是它们的一种专门活动。尽管他没有非常明确的表达,但是这一思想与后来的思 想差不多是一致的。
假定以上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可以说托马斯的思想是清楚的。但是在这里仍然存在一 个问题。托马斯这种关于是的理解虽然是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出发的,与亚里士多德的 思想似乎却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亚里士多德没有这样的思想。虽然托马斯引用亚里士多 德的话说到本性,似乎自然地谈到“与事物的专门活动有关”,并由此与本质联系起来 进行解释,但是却有些牵强,因为他并没有像后来那样明确地把“是”解释为一种活动 ,因此这里关于是的解释与“事物的专门活动”似乎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至多也只是 可以让人们去体会其中的意味。非常保守地说,托马斯的思想也许是杰出的,但是这里 的解释本身至少有些不那么自然。我觉得,如果他不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出发,直接阐 述本质表达了使一事物具有是的含义,就像他后来的解释那样,反而可能会更加自然。
关于简单实体和复合实体的区别,我认为是自然的。虽然关于谓述、实体、本质等思 想在字面上都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有关,但是由于这里没有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因此 我们不必考虑它们是不是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相符。这里,最重要的乃是对简单实体的 强调,即它更真,更完善,而且更完善地具有是。有了引文2的论述,这里的论述也是 自然的。
综上所述,三段引文反映了《论是者与本质》第一章的主要思想,也说明了托马斯所 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即关于是者与本质这两个概念的解释。这三段引文的思想基本上 是清楚的。但是引文2的思想有些不自然的地方。由于引文2涉及托马斯形而上学中最重 要的思想部分,因此这种不自然就值得我们认真考虑。我认为,这种不自然主要是因为 托马斯有一个强烈的前提,他时时刻刻要考虑这个前提,并且要回答与这个前提有关的 问题,这就是上帝的问题。这从引文3看得非常清楚。此外,虽然引文2没有提及上帝, 但是仅仅在字面上就可以看出它与引文3在这一点上的联系。引文2提出“具有是”,这 是它的新思想。而引文3则讲“更完善地具有是”。如果说引文1是出发点,引文3是托 马斯主要想探讨的问题,那么引文2则是一个过渡,因为从引文1无法直接到引文3。有 了引文2的过渡,尽管不那么自然,但是终究是可以谈论引文3了。
如果我们具体地看一看该书后面几章,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第四章主要讨论一般实 体与纯粹精神实体的区别。第五章则专门探讨上帝。在第四章,托马斯认为:“是与本 质或是什么不同,也许除非有一个是者,他的是什么就是他的是。只能有一个这样的是 者,即第一者。”(注:Thomas von Aquin:《论是者与本质》(Das Seiende und das Wesen,Lateinisch/Deutsch,ss.48—49);Thomas Aquinas:《论是者与本质》(On Being and Essence,pp.46)。)而在第五章,他明确地说:“有上帝这样的是者,他的 本质就是他的是本身”(注:同上书《论是者与本质》(德文版),第54—57页;英文版 ,第50页。);“上帝的这种是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对它不能加任何东西。所以,正是 由于它的纯粹性,它是一种与各种是不同的是”(注:同上书《论是者与本质》(德文版 ),第56—57页;英文版,第50—51页。);“上帝在他的是中具有所有完善性”(注: 同上书《论是者与本质》(德文版),第58—59页;英文版,第51页。)。托马斯对上帝 的这些性质进行了详细的讨论,论述了上帝与一般实体和一般精神实体的不同,阐述了 自己的独特看法。在他的论述中,是的纯粹性,或者说具有这种纯粹性的是,乃是他思 想的核心。以此他论证了上帝的性质。因此也可以理解,他在第一章从亚里士多德思想 出发,并为向论证上帝做出准备。这一过渡,可谓用心良苦。
所谓用心良苦,我认为,大概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或者说,这是中世纪哲学的主要 特点之一。在中世纪,哲学家与神学家虽然不是没有任何区别,因而也不是不可区分的 ,但是首先要考虑上帝,这一点对于他们大概没有太大的区别。因此,哲学家的论述即 使不完全是为神学服务的,至少也是在神学的指导下进行的。而神学的核心就是上帝。 哲学家们关于上帝的表述自然是来自神学家,而神学家关于上帝的表述是来自《圣经》 。上帝告诉摩西的话“我是我之所是”乃是人们知道的关于上帝的惟一表述。从这句话 里,人们知道,上帝是什么就是什么,换句话说,人们仅仅知道“上帝是”,因为他说的那个“我之所是”仍然仅仅表明“上帝是”。神学的讨论是从相信出发的,关于上帝是不能怀疑的。因此,根据这个“上帝是”,既不能随便说上帝是什么,又要相信有这样一个上帝,因此这个“是”就成为上帝惟一独特的性质。此外,神学家们还必须从这里出发论证上帝的至高无上性、完美无缺性、全知全能性,等等。神学家们是如此,哲学家们大概也不会例外。
这里,有一点值得我们特别注意。一方面,从“上帝是”出发来论证上帝,在中世纪 关于上帝的讨论中乃是贯彻始终的。另一方面,中世纪哲学家的讨论往往是从亚里士多 德的著作出发的。因而,随着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的引入,他们开始从《形而上 学》的内容出发,他们的讨论也就产生了大量与之相关的内容。这样一种变化,至少从 托马斯的《论是者与本质》这部早期著作来看是清楚的:它明白无误地说明是从亚里士 多德的著作出发的。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提供了许多思想和术语可以供人们讨论 和使用,比如关于第一哲学,关于是本身,还有是者、是、形式、质料、本质、属、种 、种差等等。这些概念和思想无疑极大地丰富了中世纪哲学家们关于上帝的讨论,但是 ,由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不是神学著作,他的论述也不是关于上帝的专门理论,因此在 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运用到关于上帝的讨论时,能不能那么合适就是值得考虑的。以托 马斯为例。表面上,他是从亚里士多德出发,他似乎也对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进行了许多 解释,但是他最终仍然是为了探讨上帝。即使在《论是者与本质》这部专门的哲学著作 中,这一点也是显然的。如果说在这部著作中我们只是感到他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出发 进行的过渡有些不太自然的话,那么从他后来在神学著作中的论述则可以更清楚地看出 他的自然的思想。
托马斯在他最重要的著作《神学大全》中谈到与我们考虑相关的问题。他认为,“他 之所是”(注:关于“上帝是”的说法有许多种,阿奎那这里的说法是用的间接引语, 因此不是“我之所是”,而是“他之所是(Qui est)”。参见St.Thomas Aquinas:《神 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vol.3,tr.By Herbert McCabe,O.P.Blackfriars 1964)。 )是上帝最合适的名字。他说:
“他之所是”是比“上帝”更合适的,因为它使我们可以在第一意义,即他是(esse) 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名字,因为它以一种不加限制的方式表示他,还因为它的时态,正像 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但是当我们考虑用这个词表示什么意思时,我们必须承认,“上 帝”是更合适的,因为它被用来表示这种神圣的本性。更合适的甚至是“他是他之所是 ”,它被用来表示上帝这种不可传达的实体,或者表示上帝这种个体实体,如果我们可 以说这样的东西的话。(注:St.Thomas Aquinas:《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vol .3,pp.92-93)。引文中标出拉丁文“esse”的地方,英文翻译为“existence”。)
表面上看,阿奎那提供了三种理由,说明“他之所是”是上帝的名字,有时候甚至是 比上帝更合适的表达。第一是由于它的意思,因为它不表示任何特殊的形式,而只表示 是(esse)本身。第二是由于它的普遍性,因为其他任何名字都要么不太普遍,要么至少 会增加一些细微的意义差别,这样就会限制或确定原初的意义。第三是由于它的时态, 因为它是现在时,而上帝恰恰既不是过去的,也不是将来的。但是实际上,这三种理由 不过就是一个理由:用“是”来表达,乃是最普遍、最没有限制的,而这恰恰符合上帝 的性质。
三
托马斯讨论了是与本质的区别,在这一讨论中他发展出关于“是的活动”的讨论。人 们认为这是他关于存在的讨论,有人甚至认为他所说的“是的活动”也就是“存在的活 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论是者与本质》中,存在(exist)一词出现得并不多, 而且都不是在解释是与本质的区别之处(注:英译本由于把esse翻译为“存在的活动(act of existing)”,因此通篇都把esse译为“存在”。在德文译本中,基本都译为Sein,“存在”的翻译较少。根据我的阅读,拉丁文原文只有三处用了“存在”,分别 表示“存在的种(speciei existens)”、“自身存在的原则(principium in ipso existens)”、“存在的事物(res exsitens)”。但是,这三处“存在”都不是动词。 参见Thomas von Aquin:《论是者与本质》(Das Seiende und das Wesen,Lateinisch/Deutsch,s.16,20,32)。)。应该说,存在一词的出现乃是一种重要的哲学现象。这种 结果与人们探讨是乃是相关的。作为史学研究,比较直观的问题是,“存在(exist)” 这个术语和概念究竟是什么时候产生的?它在什么时候广为流行并为普遍使用?对于这个 问题,本文不做详细探讨。但是,区别表示存在的是,对本文的研究又是至关重要的。 我想,看一看当时一些逻辑学家的论述,大概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问题。
希雷斯伍德的威廉(约1250)可能是与托马斯大约同时代的人。他在《论助范畴词》这 部著作中有三章专门讨论“是(est)”。其中有一章探讨作为助范畴词或不作为助范畴 词的是,与我们讨论的问题直接相关。
把是作为一个助范畴词进行讨论,用威廉自己的话说,“不是因为它是一个助范畴词 ,而是因为它被许多人假定为助范畴词。他们依赖亚里士多德的说法,即‘是’意味某 种特定的组合方式,没有组合物,就无法理解这种方式”(注:William of Sherwood:《助范畴词论》(Treatise on Syncategorematic Words,tr.By Kretzmann N.,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1968,p.90)。)。但是另一方面,人们又认为它不是 一个助范畴词。这是因为“一个命题是由一个名字和一个动词形成的,因此‘是’本身 乃是一个动词。所以,它被说成带有意义,不是因为它与另一个词一起表示意义并且是 一个表达式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因为它意味着它与它主要表意的东西组合在一起” (注:同上书,第91页。)。
在逻辑研究中,中世纪逻辑学家形成了著名的助范畴词理论。他们认为,词分为两类 ,一类是范畴词,另一类是助范畴词。范畴词是自身有意义的词,比如名词、动词、形 容词。助范畴词是自身没有意义的词,它要和其他词结合在一起才有意义。威廉关于是 的讨论清楚地反映了中世纪的助范畴词理论。当然,由此也反映出中世纪逻辑学家对是 这个词的认识和看法。把是归为助范畴词,显然是认为它自身没有意义,一定要与其他 词结合在一起才有意义。在这种意义上理解,是这个词就不可能有存在的意思,因为它 自身没有任何意义。相反,把是本身看作是一个动词,显然是承认它自身有一种意义, 理解它不用借助其他词,因此它就不是助范畴词。有专家认为,把是描述为具有助范畴 词的特征,威廉大约是最早这样做的(注:同上书,第90页,注1。)。由于处理中世纪 文献的复杂性,这种说法是不是正确仍然有待考证。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在威廉这 里,也就是说,大约在托马斯的时代,关于是已经有了以助范畴词理论为基础的明确说 明。
卢鲁(1235—1316)也是一位与托马斯大约同时代的人。他在《新逻辑》这部著作中专 门论述了是。他认为应该以三种方式考虑是。第一,有潜能的是与现实的是。第三,可 以根据一和多来考虑是。第二种方式则与我们的讨论有关。卢鲁认为,第二种方式又可 以分为两种,一方面,“是被看作是者,它在自身是某种它所是的东西,就像比如自身 乃是是者的实体,因为它通过自身存在(quae in se est ens,eo quod per se existit )”(注:Lulls,R.:《新逻辑》(Die neue Logik,Lateinisch-Deutsch,text von Lore,C;uebersetzt von Hoesle,V./Buechel,W.,Felix Meiner Verlag 1985,ss.6-9)。), 另一方面,“是被看作乃是在另一个是者中的是者,因为它不是通过自身存在(eo quod per se non existit)”(注:Lulls,R.:《新逻辑》(Die neue Logik,Lateinisch-Deutsch,text von Lore,C;uebersetzt von Hoesle,V./Buechel,W.,Felix Meiner Verlang 1985,ss.6-9)。)。这里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卢鲁引入了“存在”这一术语来进 行区分,而且这里的“存在”是动词。“通过自身而存在”这一表达式还在其他地方出 现,比如“实体是通过自身而存在的是者(quod per se existit)”(注:同上书,第12 —13页;85页。)。这样,通过是者与存在的区别,他关于是也区别出两种含义。可以 看出,卢鲁的讨论与威廉的讨论有十分明显的不同。卢鲁没有使用助范畴词理论,而威 廉利用了助范畴词理论。卢鲁使用了存在概念,而威廉没有使用这一概念。不过,他们 两人区分所得的结果差不多是一样的。
波利(1275—约1344)是比托马斯稍晚的逻辑学家。他在《论逻辑艺术的纯粹性》这部 著作中也专门探讨了是。他认为,“联结体现了谓述词项与主项的统一或联系。这样, 联结通过动词‘是’被表达出来,同样也通过以有意义的形式从‘是’导出的动词表达 出来,比如‘曾是’、‘将是’,如此等等”(注:Burleigh,W.:《论逻辑艺术的纯粹 性》(Von der Reinheit der Kunst der Logik,Lateinisch-Deutsch,uebersetzt von Kunze,P.,Felix Meiner Verlag Hamburg,1988,ss.160-161)。)。(160—161)因此,他 不仅把是看作是主项与谓项的一种联结方式,而且把是看作一种动词。对于是这个动词 本身,波利指出,“动词‘是’可以以两种方式来理解。首先,它是作为第二个补充物 进行谓述的东西,比如‘人是’;其次,它是作为第三个补充物进行谓述的东西,比如 ‘人是动物’。当‘是’这个动词作为第二个补充物进行谓述的时候,它表达的乃是在 自身所是的东西,也就是一种现实的是,或者一种存在的是(esse existere)”(注:同 上书,第162—163页。)。他特别强调,“当‘是’这个动词作为第二补充物被表达出 来的时候,它自身涉及一个范畴表达,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作为谓词或作为自身包含谓 词的东西而起作用。而且它还表达一种特定的本性,即作为存在的是(esse existere) ”(注:同上书,第162—163页。)。在推理中也是一样,“当‘是’这个动词作为第二 补充物进行谓述的时候,它表达了一种绝对的是,即一种事实的是或者存在的是(esse existere)。而当它作为第三补充物进行谓述的时候,它不表达绝对的是,而是表达一 种如此是,即一种如此确定的是,一如它通过那个谓词所表达的一样”(注:同上书, 第162—163页。)。
从波利的论述可以看出,他的论述有两点与亚里士多德有些相像。首先,他论述了是 这个词所表达的时态性,这显然具有语言方面的考虑。其次,他也把是分为两类,一类 乃是“人是”,另一类则是“人是动物”,尤其是他所使用的一些术语,比如第二个补 充物、第三个补充物等等,几乎就是亚里士多德使用的。但是,他的论述也有与亚里士 多德明显不同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对是的区分上。他通过引入“存在”这一概念,明 确说明为什么“是”可以单独作一个谓词,在这种情况下它表示什么意思。这样的思想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确实是看不到的。
一般来说,以亚里士多德的《前分析篇》、《后分析篇》等逻辑著作的引入为标志, 中世纪逻辑经历了两个时期。前一个时期的逻辑被称为旧逻辑,后一个时期的逻辑被称 为新逻辑。这两种说法一方面表明中世纪逻辑在晚期较之早期有了非常大的发展,有了 根本的改观,另一方面也说明中世纪逻辑学家对于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想和理论依赖很 大。实际上,中世纪逻辑正是在解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思想和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我们介绍的几位逻辑学家都属于后一个时期。这一点甚至从卢鲁的著作名称就可以看 出来。虽然我们的讨论仅仅限于他们关于是的论述,但是也可以说明,这反映出他们比 较成熟的逻辑理论和思想。
在上述几位中世纪逻辑学家关于是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比较有意思的特征。 首先,他们与托马斯不同,在进行严格的说明时没有使用“上帝是”这样的例子,也就 是说,他们没有以“上帝是”作为典型的句式进行讨论。当然,在逻辑学家们的具体讨 论中,有时候我们也会看到“上帝是”这样的例子,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它与“苏格拉 底是”这样的例子乃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我们把托马斯看作是哲学家的代表 ,那么可以说这一区别反映了逻辑学家与哲学家的不同。哲学家大概首先是要从上帝出 发来进行探讨,虽然他们也会从亚里士多德著作出发,比如像托马斯那样,但是首先并 且时时刻刻要考虑的大概还是“上帝是”和与之相关的问题。逻辑学家首先要考虑的是 推理和与之相关的句式,而且他们还要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出发。比如,威廉显然明确 地提到亚里士多德。卢鲁和波利虽然没有明确地提到亚里士多德,但是他们关于考虑是的三种方式的划分、关于“人是”和“人是动物”的谈论方式,显然是从他的论述出发的。
其次,这几位逻辑学家之间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区别。威廉依据助范畴词理论,对“S 是”与“S是P”进行了区分。而其他两人没有依据助范畴词理论,而是引入“存在”概 念进行了区分。我认为,这一区别是很大的。助范畴词理论是中世纪形成的逻辑理论。 这一理论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区别出什么是助范畴词,什么不是助范畴词,而且也在于 指出逻辑要考虑的是助范畴词,而且逻辑所考虑的一些助范畴词是与真相关的。依据这 样一种理论对是进行考虑,自然会考虑它是不是助范畴词,是则怎样,不是则又怎样。 这样的考虑无疑是清楚的。认为是乃是助范畴词,则说明它自身没有意义,因此它具有 一种语法含义或功能,这显然是在“S是P”的意义上理解它,或者说把它理解为系词。 如果认为它自身有意义,那么显然不能把它看作助范畴词。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对它提 供其他说明。威廉也是这样做的。这就说明,是这个词本身可以具有两种性质,一种是 句法方面的,另一种不是句法方面的。逻辑研究的乃是它句法方面的性质。它的非句法 方面的性质,则不是逻辑研究的东西。
不依据助范畴词对是进行思考,显然没有这样明确的句法说明。在这种情况下,引入 存在这一概念,主要是一种语义解释,说明是本身具有这样一种涵义。无论是“绝对的 是”,还是“如此是”,都是一种语义说明。它主要是想表明,是的表达有不同涵义。 尤其是当它单独地、不加任何东西表达的时候,它表示什么意义。在这样的说明中,我 们看不到是这个词的句法作用,或者说,我们至少无法非常清楚地看到这个词的句法作 用。逻辑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要提出一些规范的东西。在这样意义上,依据助范畴词理论 当然更好一些。因为所得结果不仅更为规范,而且这种规范的结果也会让人看得更加清 楚。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的确清楚地看到,逻辑学家们引入了存在这一概念,并且以它对 是做出明确说明。应该指出,尽管逻辑学家做了这样的工作,却绝不能说这是逻辑学家 们创造性的工作,因为他们只是总结或利用了中世纪有关这个问题长期研究讨论的结果 。然而,由于这是在逻辑著作里谈的,因此我们大致也可以说,是的存在意义已经得到 了明确的规范意义上的探讨,得到了人们的认同。限于文献的考察和把握,即使我们无 法断定是的存在意义是不是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至少也可以说,这样的认识得到了一 些人的认同。从这样的论述来看,这与托马斯的论述,与托马斯以前哲学家的论述,与 前面我们说明过的波爱修的论述,显然有了根本的区别。具体一些,一种方式是说,“ S是”中的“是”与“S是P”中的“是”乃是不同的。另一种方式是说,“S是”中的“ 是”表示存在,“S是P”中的“是”不表示存在。这两种方式的区别当然不是无足轻重 的。因为,引入一个新概念,或者产生一个新概念,无疑会对哲学的讨论产生重大的影 响,带来极大的变化。
我觉得,对于存在这个概念,至少有两点是值得认真对待的。第一,它究竟是什么时 候引入的?从一些文献来看,至少在阿伯拉尔的著作中就已经提到了。比如他认为,从 “彼得是人”到“彼得是”的推理与对是这个动词的解释并不相干,也许与“人”的谓 述方式有关系,而这里的这个人“只是一个存在物(existentis rei)的名字”(注:De Rijk,L.M.:《彼得·阿伯拉尔的语义学及其“是”之学说》(Peter Abelard's Semantics and His Doctrine of Being,in Vivarium,
XXIV,2,1986,p.122)。)。如上 所述,用存在来修饰事物,在托马斯的著作中也提到了。第二,从什么时候开始,存在 从形容词演变成动词,并且得到了如同上述逻辑著作中那样的规范说明(注:专家们认 为,一部关于本质和存在之间关系的争论的完整历史仍然有待于撰写。但是,在托马斯 之后,在吉尔斯(Giles)、哥德弗雷(Godfrey)和亨利(Henry)的著作中,“存在的是(esse existentiae)”和“本质的是(esse essentiae)”经常出现,有人为了方便起见 还把它们看作是同义的。参见Kretzmann,N.:《剑桥史:晚期中世纪哲学》(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Later Medieval Philosophy,p.392,注37;p.400,注74)。)? 阿伯拉尔和托马斯的论述显然还不是针对是这个概念本身,还没有把存在作为一个动词 来说明是,还没有形成在存在的意义上对是的规范说明。我们看到,从波爱修关于是的 论述到波利对是的论述,形成了关于是的规范说明。这种规范的说明显然有一个从没有 使用“存在”这一概念到明确使用“存在”这一概念的发展过程。这一过程无疑显示了 中世纪关于是的讨论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
四
根据前面的论述,不难看出,有关是这个问题,中世纪的研究有两个特征:其一,他 们依据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其二,他们引入存在解释是,并形成对是的存在意义的说明 。我觉得,这两个特征是显著的,而构成这两个特征的原因却是比较复杂的。既然中世 纪的哲学家和逻辑学家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出发进行解释,就很难说这不是亚里士多德 思想研究的结果,当然更不能说这样的结果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没有关系。但是我们清 楚地看到,在解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时候,比如在托马斯的论述中,存在着十分明显 的不自然的地方。因此我们也就不能说,这样的结果是亚里士多德思想解释的必然结果 。既然从是这个词分析出存在这种涵义,似乎当然可以认为这个词本身确实具有这样的 涵义。但是我们清楚地看到,存在这一概念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引入的,而是经历了一个 过程,尤其是,作为逻辑的规范意义上的说明,它确实经历了很长时间。因此我们也就 无法断定,存在这一概念自始至终就应该属于是。我们至少可以问:为什么会引入这样 一个概念来解释是?我以为,这两个原因都与神学有关,即与上帝的讨论有关。下面我 想从两个角度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首先我从解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来考虑这个问题。亚里士多德从逻辑的角度、从形而 上学的角度对是都有论述,并且形成不同的理论。因此理解和解释他的思想,要从他的 这些不同论述出发。在论述形而上学的过程中,亚里士多德也谈到神,但是他所说的神 与中世纪所说的上帝是有很大区别的。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不少地方有关于神的论 述,比如在《物理学》中,他探讨了宇宙万物的层次,谈到了第一推动者,这个第一推 动者不被其他东西所推动。在《形而上学》第12卷的几章他也有相应的讨论和论述。由 于这些说明与中世纪关于上帝的说明比较接近,因此人们也用它们来支持关于上帝的说 明和论证,并认为这些章节是亚里士多德的神学著作,形成中世纪神学的思想来源。当 然,人们对亚里士多德这些论述的评价是多种多样的。在众多评价中,我比较同意两种 看法。
一种看法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神“不是宗教的神,而是哲学的神”(注:汪子嵩: 《亚里士多德关于本体的学说》,三联书店1982年,第83页。)。从亚里士多德自己的 论述来看,“神是赋有生命的,生命就是思想的现实活动,神就是现实性,是就其自身 的现实性,他的生命是至善和永恒”(注: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七卷, 苗力田主编,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79页。)。因此确实可以说,在亚里士多德 这里,神属于理性范围,而不是空间中的东西。这与中世纪的神的观念显然差距极大。
另一种看法认为,亚里士多德所讨论的神不是单一的,而基督徒讨论的上帝总是单一 的,这就说明,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上帝占据独一无二的特殊地位,而在亚里士多德的 世界里,神远远没有这样的位置。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关于神的思想与中世纪关于上帝的 思想非常不同(注:参见Gilson,E.:《中世纪哲学的精神》(The Spirit of Medieval Philosophy,tr.By Downes,A.H.C.,Sheed & Ward,London 1936,pp.45-50)。)。
我之所以赞成这两种观点,不仅是因为它们非常有见地,而且因为它们给人深刻的启 示。因循这两种观点,我们可以深入思考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形而上学乃至哲学与宗 教的区别,另一个问题是上帝的核心地位与是本身的核心地位的区别。限于篇幅,这里 不考虑前一个问题,而仅考虑后一个问题。
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明确提出研究是本身,并围绕这一思想,形成了他的形而上学 理论。是本身乃是一个哲学问题。与此相关,有关于范畴的探讨,有关于实体的探讨, 有关于本质的探讨,有关于形式与质料的探讨,有关于四因的探讨,等等,形成了丰富 的内容和理论体系。在所有这些探讨中,核心的东西乃是那个是本身。一切都是围绕这 个是进行的。特别是,为了这样的探讨,亚里士多德还提供了一套逻辑理论。而这套逻 辑也是围绕着是而形成的(注:参见王路:《<工具论>与<形而上学>——理解亚里士多 德》。)。这样一种形而上学包含了事物、事物的表达和人们对事物的认识,形成了相 关的哲学理论。因此,亚里士多德所说的研究是本身的学问,乃是在爱智慧层面上的东 西,反映出一种对普遍知识的探求,充满了理性的精神。在这样的讨论中,虽然谈到神 ,但是,神不是核心的东西,不是讨论的出发点,更不是讨论的依据。
与亚里士多德的讨论不同,在中世纪,由于神学的影响,上帝是核心的东西。正是由 于上帝的核心地位,上帝不仅是讨论的出发点,而且是讨论的原则。在这种精神指导下 ,虽然人们也从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出发,但是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人们坚持那 些与上帝学说相符的思想,而修正与上帝学说不符的思想。核心仍然是上帝,而不是亚 里士多德的思想。这种做法不仅表现出与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差异,而且也形成了中世纪 独特的理论。比如,托马斯关于上帝名字的说明非常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又比如,关 于本质的说法,在亚里士多德那里是比较清楚的,本质就是属加种差。而且这是定义所 必须具备的。但是,这样的思想和理论到了中世纪就出了问题。而这个问题又恰恰出在 上帝身上。因为对上帝不能定义,或者说不能以属加种差的方式下定义。人们无法说出 上帝的属是什么,也无法说出上帝的种差是什么。人们只知道“上帝是”(“我是我之 所是”,或“他是他之所是”),因而也只能说“上帝是”。为了上帝,为了人们所知 道的这个“上帝是”,必须修正已有的理论和方法,必须在这个“是”上说出一些新的 东西来。结果,是被解释为一种活动,与本质区别开来。在这种意义上,是本身就表示 本质。但是,它只在上帝这里表示本质。因此,在上帝这里,是与本质融为一体。特别 是,托马斯区别出本质与存在的不同,但是他仍然要说“上帝是”,而且这是中世纪哲 学家们的普遍做法。这就说明,即使这里的是具有存在的涵义,也只能说或者必须说“ 上帝是”。我想,所有这些,都是因为要从上帝出发。
应该看到,这里确实有语言方面的问题。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从柏拉图的时代起 ,无论‘是’可能会意味什么,至少本质总意味‘是那种是所意味的东西’。在所有哲 学语言中,无论希腊文还是拉丁文,‘本质’这个词很少脱离它的词根,而它的词根就 是动词‘是’。当一个希腊人说一事物是实体(ousia)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那事物是 实在的。当一个拉丁人说某一事物是本质(essentia)时,他也是在指那事物的现实性。 ”(注:Gilson,E.:《是与一些哲学家》(Being and Some Philosophers,Medieval Studies of Toronto 1949,p.82)。)根据这样的解释,一方面,是与本质具有天然的 联系。在这种意义上,不能说中世纪哲学家关于是本身的分析没有道理。另一方面,当 希腊人和拉丁人说是或本质的时候,并没有存在的意思。在这种意义上,中世纪关于是 的存在涵义的解释确实是一种创造。问题是,这样的创造是从上帝出发而产生的结果, 而不是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出发产生的结果。这里我们可以考虑一个反例。奥卡姆在《 逻辑大全》中也有一章专门论述是。他也谈到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关于表示本 质的是和表示偶性的是的区分。他说:亚里士多德“做出这种区别不应该被理解为意味 着一些东西是本质的是者,而另一些东西是偶然的是者。相反,他做出这种区别乃是在 指出,一个东西可以通过‘是’这个媒介谓述另一个东西”(注:Ockham:《词项理论》 (Theory of Terms,tr.by Loux,M.J.,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74,p.123) 。)。他论述的东西与依循的著作与托马斯是完全一样的。但是他的解释却与托马斯不 同。当然,这里的原因可能有许多,而且奥卡姆也晚于托马斯。但是,他的论述至少是 一种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解释,而且更接近亚里士多德本人。这至少说明,从同样的思 想可以解释出不同的结果。对照之下,更可以说明,托马斯的解释是从上帝出发的。
最后我从逻辑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在中世纪,逻辑与语法和修辞并列为三大基础 学科,并称“三艺”,是学生的必修课。中世纪逻辑是在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基础上建立 起来的,对亚里士多德逻辑著作有许多注释和解释,同时又有许多自己的发展(注:关 于中世纪逻辑的研究,参见王路:《中世纪逻辑的现代研究述评》,《哲学动态》1990 年第1期。)。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在波爱修注释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的时候 ,引入了“上帝是”这个例子,但是后来到了卢鲁和波利的逻辑著作中,在专门论述是 的问题时,这个例子却不见了。另一方面,在波爱修论述是的7条公理中,讨论了是的 不同涵义,但是没有引入存在这一概念。而后来在卢鲁和波利的逻辑著作中,明确引入 了存在概念,并用它来说明是,特别是说明“S是”这样的句式的涵义。概括起来,在 中世纪逻辑研究中,人们引入或考虑了“上帝是”这样的例子,最终形成了用存在对是 的解释。我认为,这个现象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表明了与亚里士多德逻辑十分重大的 区别。
首先我们看“上帝是”这个句子。从字面上看,它表现为“S是”这样的句式。在亚里 士多德的逻辑论述中,也有这样的说法。但是,亚里士多德在逻辑论述中谈到“人是” 和“荷马是”,而没有谈到“上帝是”(注:参见王路:《<工具论>与<形而上学>—— 理解亚里士多德》。)。其实,问题并不在于亚里士多德没有使用“上帝是”这样的例 子。即使他使用了这个例子,比如把“荷马是”这个例子换成“上帝是”,对于形成他 的理论,对于我们现在所得到的他的逻辑理论,也没有任何影响。在亚里士多德那里, “荷马是”不过是一个例子,是他探讨与“荷马是诗人”之间关系的一个例子。如果把 它换成“上帝是”,大概依然会是一个例子,以此探讨与“上帝是如此如此的”之间的 关系。而“人是”则不是一个简单的例子。更多的时候,它主要是为了凸现句子的形式 结构,表达出句式,即“S是P”。此外,“荷马是”与“人是”有一个重大区别,即前 者是以个体词作主词,而后者是以类名作主词(注:参见王路:《<工具论>与<形而上学 >——理解亚里士多德》。)。二者可以导致重大的逻辑区别。正因为这样,亚里士多德 的逻辑理论排除了个体词作主词,只保留了类名作主词。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逻辑理论 不会给个体词留下位置。这也是亚里士多德逻辑的一个显著特点。最为重要的是,亚里 士多德逻辑研究命题,即含真假的句子。他研究的乃是普遍的形式,也就是说,具有普 遍性的东西,逻辑上最重要的东西。在这种意义上,“上帝是”这个句子没有进入他研 究的视野,至少说明,在他的时代,上帝还不是人们必须要考虑的东西,这样的句子还 不是反映真假的最主要的句式。
到了中世纪,这种情况得到根本的改变。随着神学的发展和逐渐占据支配地位,“上 帝是”成为人们谈论的中心问题和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正因为这样,在研究逻辑的时候 ,同样是研究句式,必须对它进行考虑,而且还要作为一种主要句式来进行考虑。从逻 辑的角度看,“S是”与“S是P”明显不同。自亚里士多德以来,“S是P”得到了比较 明确的说明,而“S是”则需要新的说明。也就是说,必须对“上帝是”中的“是”进 行说明。这样的说明自然会形成相应的论述,即关于“S是”的论述。比如,依据助范 畴词理论,人们可以说“S是P”中的是乃是助范畴词,而“S是”中的是则不是助范畴 词。从是本身出发,人们也可以说“S是P”中的是乃表示如此是,或某种确定的是,而 “S是”中的是则表示存在。即使在后来一些规范的逻辑著作中,人们不用“上帝是” 这个例子,而用“人是”这样的说明,而且“人是”与“人是动物”、“第二补充物” 和“第三补充物”等等表达在字面上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几乎没有什么两样,但是我们 仍然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这样的论述与亚里士多德的论述是有根本区别的。这里的区 别不在“人是动物”上,因为它与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是白的”是一样的,它们都指 “S是P”这种句式。区别主要是在“人是”上。尽管从字面上看,中世纪的论述与亚里 士多德的论述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它们表述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在波利的著作中,“ 人是”表达的是“上帝是”这样的句式。而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至少在绝大多数地方, “人是”乃是“人是如此如此的”的省略表达,与“S是P”表达的差不多是一样的。确 切地说,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人是”的主项仍然是类名,而在中世纪这里,“人是” 的主项主要是专名。无论是不是清楚这里的逻辑区别,亚里士多德在他的逻辑中排除了 个体词作主词,从而保证了他的逻辑理论在这方面没有什么问题,而中世纪的逻辑学家 保留了个体词作主词,从而也留下了这方面的问题。
就存在本身而言,也是有问题的。亚里士多德没有使用这个概念来说明是,而是明确 地说“是”在句子中是系词,联结主词和谓词。这样就从句法方面规定了是的作用和涵 义。这种做法不仅清楚,而且也符合逻辑自身的特性。但是在中世纪,人们用存在来规 定和说明是的涵义,尽管不能说这不是一种说明方法,也不是没有起到说明的作用,但 它毕竟仅仅是一种语义的说明,没有形式说明那样清晰明白。比如,它甚至不如依据助 范畴词理论的说明。因为,根据这一理论,如果是这个词自身有涵义,它就不是助范畴 词。“S是”中的是自身有涵义,因此不是助范畴词。至于它有什么涵义,那是另外一 个问题。逻辑可以不予考虑。而用存在来解释,由于存在自身有涵义,因而可以表明这 样的是与系词的区别。但是这样的解释却超出了逻辑的范围。更重要的是,“S是P”与 “上帝是”的句子形式是不同的。前者的主项是类名,后者的主项却是专名。因此前者 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表达了类与类之间的关系。而后者却不是这样。这里的区别涉及到个 体、谓词和存在的关系,这样的关系中存在着较为复杂的逻辑问题。中世纪逻辑显然还 无法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因而它根据存在的语义所提供的解释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实 际上,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的问题,确实是在中世纪产生的,而且也一直留传下 来,直到现代逻辑问世以后才得到新的解答。
综上所述,无论中世纪哲学有多么大的发展,不管中世纪哲学带来多少问题,有一点 是非常清楚的:中世纪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上帝,而这样一种考虑的核心是“上帝是” 。由于神学的强大影响,“上帝是”这个“非哲学陈述从此变成哲学史上一个划时代的 陈述”(注:Gilson,E.:《上帝与哲学》(God and Philosophy,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1,p.40)。)。正是这样的思考方式,带来了对是的解释的变化,产生了存在这一概 念,也形成了中世纪独特的哲学。虽然亚里士多德的著作是中世纪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研 究的基础,尽管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中世纪学者的思想交织在一起,但是其间的许多区 别还是可以看得比较清楚的。吉尔森认为,中世纪哲学的核心的东西乃是“不得不使用 希腊人的技术来表达一些从未进入希腊哲学家头脑的观念”(注:同上书,第43页。)。 我想,这一解释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