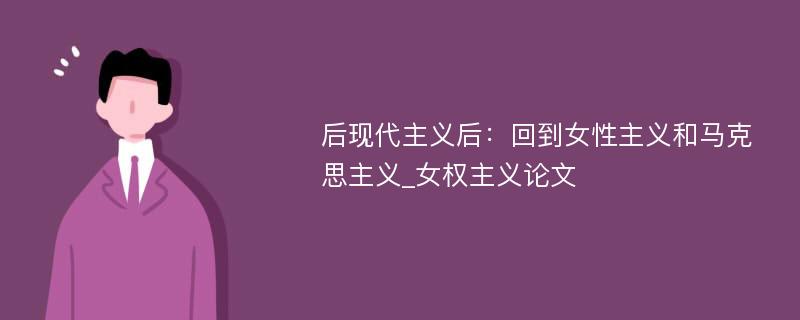
后现代主义之后:回到女权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权主义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米凯莱·巴勒特(Michele Barratt)在《当今妇女所受压迫》修订版(Women’s Oppression Today,1988)导言中写道,她已经中止了原有的研究课题,即试图探寻非还原的(non-reductive)马克思主义与女权主义之间可能有的共通性的课题。她放弃了这一课题,而不是解决了这一课题;她之所以放弃这一课题,原因在于后现代主义对研究环境的影响。她解释说,后现代主义是以明确否定而且是有理有据的否定宏大叙事为前提的,而“社会主义”和“女权主义”就定义来说无疑都是宏大叙事,但是她也说,后现代主义不是人们能够支持或反对的事物。它是一种研究立场,更是一种文化氛围,是一种学术时尚更是一种政治现实,这决定了女权主义研究将不得不围绕后现代主义这一核心立场展开。
不久之后,巴勒特在女权主义理论中发现了一种文化转向,同时发现这一特征的学者还有伦纳德(Leonard)、本哈比(Benhabib)、沃尔比(Walby)等。女权主义理论与文化理论(尤其是话语分析)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已经超越了其与社会科学之间的联系的紧密程度。此外,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中也出现了同样的趋势:由社会结构模式转向现象学和解释学。在《后现代的状况》中,哈维(Harvey)评估了新左派的文化转向的影响。他认为,文化政治学转向与无政府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联程度要比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关联程度高。左派由于支持新的社会运动,放弃无产阶级是变革的代理人这一历史唯物主义信念,从而失去了批判自身及社会进步的能力。另一方面,文化政治学转向也不是毫无成效的,它把性别问题和种族问题、差异政治问题、无能政治问题、殖民化的野蛮主义和审美政治等问题凸显出来。然而,潜在的问题是,文化理论(或后现代主义)是否掩盖了资本主义文化中的深层转型。
后现代主义已经被定义为一个历史时代,一个与新的生产方式——后福特主义生产方式——相符的历史时代;一种审美或一种态度,一种描述和体验这种更现代的生产方式(如果比发达的生产方式还要发达)的方式。如果生产方式没有重大变化,那么人们不禁会想到一个问题,即如果我们的社会政治环境仍然保持原样,人们是否可能与他们原有的思维方式决裂,采取一种新的态度?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假定现代性的环境仍然存在,后现代性并不代表一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社会组织形式。现在,如果说后现代主义是从某种斗争中(也许是从分裂的事实中)获得了它的审美标准的话,那么确定这样一种分裂事实为何能够成为现代体验的一部分,以及为何这种体验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在不断积聚,就变得非常重要了。后现代主义中存在一些紧张状态,如被表达的内容与其表达方式之间的紧张状态,隐性和显性之间的紧张状态,在女权主义理论中这些紧张状态也有相应的表现形式,我对这种紧张状态非常感兴趣。我的观点是,与任何其他的思想体系一样,女权主义的后现代主义也有其内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在20世纪80年代不断加剧,目前正在逐渐显露出来。
后现代女权主义理论在英国的蓬勃发展已经对现有理论提出了挑战。它已经破坏了先前那些确定无疑的范畴;鼓励理论家们去分析权力的重要性和权力关系,质疑一元化的普遍概念,彻底开放了有关主体性、性和性别的讨论。但是也有人指责这种试图颠覆普遍概念的做法抽掉了女权主义得以存在的根基;因为如果个体不再被看作属于一个特殊群体的女人,那么就不可能期望围绕她们共同关注的问题、共同的政治身份把她们动员起来。事实上,已经有人指出,概念的这种不确定状态也使女权主义者无力对权力的“结构”背景和主体性条件(主体的经济条件、社会条件、心理条件或语言条件)等问题展开讨论。这一点对于诸如莱斯利·海伍德(Leslie Heywood)和珍妮弗·德雷克(Jennifer Drake)等的第三波女权主义者来说尤其棘手,她们试图通过揭示第三波女权主义视角如何既由经济全球化和科技文化创造的物质条件塑造,又由与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相连的思想塑造,来把第三波女权主义放在大背景中进行研究。
在某些人看来,将各种各样互不相同的理论统称为“后现代”,是一种令人反感的整体化转向。但是,正如詹姆逊指出的那样,只是到了最近,这种理论转向才被看作是令人反感的。先前,抽象被看作是一种“战略”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看到现象之间的差异。这篇文章意欲指出,在最近的女权主义理论教规化潮流中有哪些内容被包含进来,有哪些内容被删节,有哪些内容被抹掉,以此表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对唯物主义的排斥已经导致了一种“文化”女权主义的形式,“文化”女权主义的反现实主义主线使女权主义无力阐明它所处的环境,也无力对它所处的环境进行调研和分析。然而,人们必须要注意,不要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被女权主义理论内在化的许多矛盾已经说明了女权主义得以产生的环境的某些真实情况,这些真实情况是不可能通过简单地回归到旧知识中而得以解决的,也不是通过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归于它们的物质起源便能够解决的。事实上,近来在马克思主义内部出现的关于90年代末的经济危机的讨论表明,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内的一些争论已经被排除在“主流”之外,被放弃了而不是得到了解决。
女权主义理论近史:构建一个规范
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在她有重大影响的文章《女性时代》(Women's Time)中指出,女权主义运动可以分为三个清晰的阶段:自由主义女权主义(存在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和激进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最近出现的被称为第三波的女权主义理论者,反对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女权主义理论内部的排他倾向,主张内在于第一波和第二波中的本质主义导致了对差异的根除。在批判本质主义的过程中,第三波女权主义者自始至终反对“适合一切群体的身份”这样的有诱惑力的主张,认为坚持女性的共性非但不能为政治力量提供土壤,而且还将导致对差异的忽视,甚至抹煞差异。①自此以后,这些主张形成的压力导致了一种“害怕陷入种族中心主义或‘本质主义’的越来越麻痹的焦虑状态”②。这种对本质主义的焦虑的结果之一就是使关于女性结构共同点的讨论的优先性不再具有合法性。③把女权主义理论(尤其是60、70年代的理论,也包括80年代的理论)一概描述为本质主义加以拒绝是有问题的。抛开政治结果不算,不允许讨论有关社会关系、经济决定因素和干预因素的话题将导致一种对文化的特殊论述;而对文化的论述本身实际上正需要那些被抛弃的分析。因此,在这里,我想回顾一下第二波中的一些争论以说明一点,即如果这些争论可以被认为是一波中的一部分,那么第二波女权主义的主流观点及其对立观点仍旧具有影响。
莉迪娅·萨金特(Lydia Sargant)在80年代初指出,历史正在被重写,大学生从来没有听说过舒拉米斯·费尔斯通(Shulamith Firestone),但他们却听说过“抢衬裤”(美国大学男生突袭女生宿舍以夺取女生衬裤为战利品的玩笑活动。——译者注)。今天,我们能够在一点上达成共识,即尽管学生们可能听说过巴特勒(Butler)、威蒂格(Wittig)、盖腾斯(Gatens),但他们可能从未听说过费尔斯通,这似乎证实了那种把女权主义理论的历史比作波的观点,一波让位给另一波。但是如果每一波中的争论无法用同一标准进行衡量,或者社会问题还没有解决,那么用波这种比喻来说明线性历史进程就没有意义。下面,我将带领大家简要回顾一下激进女权主义,提醒我们为什么解决经济剥削和性别剥削的交叉点问题异常重要。
第二波女权主义者意识到,妇女从来都不是被简单地排除在社会契约之外,现代社会结构设法通过一种方式将女性包含到政治秩序中来,即在不对社会结构作重大变革的情况下满足将女性包含到政治秩序中的形式要求(这种方式也是自由主义女权主义者所遵循的方式)。受包括弗里丹(Friedan)、米勒特(Millett)和费尔斯通在内的美国女权主义理论家的影响,激进女权主义者开始分析家庭、性倾向和各种文化表现形式。她们推断,第一波女权主义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政治成果,因为传统的结构和价值观没有被改变,而正是这些结构限定了男人和女人的角色,赋予妇女和男人不同的价值观:在传统结构和价值观中,女性是他者,受男性的统治、压迫和剥削。父权制被定义为男性之间的一套社会关系,这套社会关系有它的物质基础,而且尽管这套社会关系是等级制的,但它却使男性之间相互依存、团结一致,使男人能够统治女人。
激进女权主义的特征是,不仅关注不同的性格和特征,而且关注男人与女人的差异,权力与权威的差异。“无名问题”、“女人的问题”,被作为一系列问题揭露出来;强奸、家庭暴力、色情文学、低工资、劳动分工、家务劳动、虐待儿童、社会排斥和政治排斥等,以及所有这些问题与性别表现之间的关系,也被揭露出来。本质主义者和反本质主义者都认为,自由政治口号“平等但是不同”隐匿了一个事实,即男性比女性更受重视,男人对女人的统治是被批准的。这些结构本身需要被修正,需要根据不同的价值观来修正。有人主张,合适的价值观是那些与女性气质相关联的价值观。其他人主张,女性气质是现存体制的产物,因此需要“对所有的价值观进行重新评估”。这些争论的共同之处是都相信真正的道义平等,相信男人和女人各有各的价值。与这种对所有人的“形而上”的平等信仰并存的观点是,认为两性在生物学意义上是不同的,由于社会体制随着时间不断改变,因此作为这一社会进程的产物的人的能力和特征也是不断变化的。这一关于变化的人(由她的社会关系构成)的理论标志着与自由主义和存在主义的“抽象个体”的决裂,这将使女权主义研究丧失为人道主义道德立场辩护的能力。安·布鲁克斯(Ann Brooks)指出,第二波女权主义和第三波女权主义之间越来越大的差别似乎是以激进女权主义内出现了本质主义的和反历史的(ahistorical)多样化立场为前提的。
这些问题曾在70年代困扰着第二波女权主义者,当她们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时,关于父权制的本质和压迫的根源问题的争论就变得异常重要了。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也受到了妇女运动中的这种激烈争论的影响。从根本上说,她们希望分析父权制和资本主义的物质结构,但是,要想做这种分析,她们不得不首先决定是否应该把父权制作为一种与资本主义制度完全不同的、具有其自身的历史和起源的社会制度来分析。如果资本主义制度可以被定义为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劳动的占有和剥削的话,那么父权制是否可以被定义为一个阶级(男人阶级)对另一个阶级(女人阶级)的劳动和性的占有呢?如果可以这样定义,那么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特别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父权制之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关系是什么样的呢?是资本主义造就了男性统治还是资本主义只是男性统治的一种表现?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试图在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生产和再生产的框架中来确定性别关系;女人在斗争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她是工人,而不是因为她是女人。二元体制理论者主张,父权制和资本主义是两种不同的体制,只有在资本主义的父权制这一点上才有交叉。一元体制理论者主张,资本主义理论和父权制理论只是描述了同一社会体制——存在性别偏见的资本主义——的不同方面。反体制理论者主张,女权主义者应该到马克思那里去寻找答案,不是寻找一种分析性叙述,而是寻找对于特殊历史事件的有启发意义的解释。
尽管流行的女权主义史学把唯物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描述为是经济主义的,但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实际上已经意识到,经济分析范畴倾向于把所有权力问题都归结到谁拥有和控制生产资料、谁创造的剩余价值被别人榨取这一点上来。把纠正这一点作为目标,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者试图确认性别关系是一种历史唯物主义所理解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正是在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两性相区别或者相联系。马克思的剥削概念、异化概念、劳动价值理论及其暗含的交换原则,被用来阐明私有部门和公有部门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是如何通过物质条件交织在一起,又是如何依赖于物质条件的。举例来说,巴勒特分析了家庭的形式和结构,主张不仅仅是核心家庭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出自身的结果,甚至更激进地认为就连家庭这一概念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为了避免陷入这种自然主义,人们最好研究一下家庭和家族思想。这种分析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它明显倾向于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区分开来,经济基础即指经济结构,上层建筑即指信仰及文化表现形式。巴勒特在她的导言中担心,她的家庭思想本身对不同国家和不同族系的家庭中的种族差异不够敏感。
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可以被称为一种一元体制理论,但是诸如贾格尔(Jagger)和扬(Young)这样的理论学者却试图把性别压迫看作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必要特征。如,沃格尔(Vogel)强调,马克思主义就目前来看是一种不胜任的理论,必须被改造;否则它将无法解释劳动过程的动力机制的问题。扬这位一元体制理论者用劳动分工理论取代阶级分析理论,试图阐述一种性别歧视的资本主义理论,在性别歧视的资本主义中,阶级关系和性别关系是一起演化而成的。她认为,关注劳动分工的理论,才有可能对种族歧视的劳工市场中的种族差异感觉敏锐。她主张,女性的边缘化,以及女性的次级劳动力地位,是资本主义核心的基本特征。另一位马克思主义者艾伦·伍德(Ellen Woods)则不这样认为,她主张,资本主义并不关注它所剥削的人口的社会身份,弱化了人们之间种族和性别的差异,同时也弱化了人们的种族和性别身份。当处于最底层的工人阶级与诸如性别和种族这类的经济外身份正好一致时,压迫的根源似乎就在经济之外了。但是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在资本主义社会运转良好,因为它们有利于工人阶级中的某些成员在劳工市场的竞争环境中占据优势地位。
这一讨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关于家务劳动的争论中达到顶峰。这一争论主要关注家务劳动的功能及其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角色,这一争论提出了男人就其本身而言受益于女人受压迫的事实的问题。最初的争论在两派中进行,一派是以恩格斯对前资本主义劳动的性别分工的推测性评论为依据的理论者,另一派是主张基于性别的劳动角色始于资本主义的理论者。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内,这些争论非常重要,因为只有那些身处生产劳动中的、创造商品和剩余劳动的人,才被看作革命阶级的一部分。争取家务劳动工资的领导人主张,家务劳动实际上生产出了资本主义的核心商品——劳动力。基于这一原因,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达拉·科斯塔(Dalla Costa)以及其他一些人建议为家务劳动支付工资。这一建议除了表明家务劳动的生产本质之外,也致力于抨击一种核心假设,即主要的工资劳动者(即男性工人)已经被支付了家庭工资。这一点正好与诸如朱丽叶·米切尔(Juliette Mitchell)和玛丽·麦金托什(Mary McIntosh)这样的二元体制理论者的观点相交。不仅男人从来没有得到过“家庭工资”,而且家庭工资这一概念本身隐藏了一个事实,即即使说女性只是辅助的工资劳动者,无疑她们也是工资劳动者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即使女人和男人做“具有同样价值的”工作,女人的工资也要比男人的工资低。这些观点不可避免地使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运动与工会运动和劳工运动相冲突。正如贝亚·坎贝尔(Bea Cambell)和巴尔·查尔顿(Val Charlton)在1979年指出的那样:“劳工运动试图把对平等工资的承诺的要求与对家庭工资的承诺的要求结合起来,但两者是不可兼得的。”
二元体制理论者(通常被称为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将经济关系和性别关系区分开来:将性别分析置于对父权制的阐述之中,而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分析方法来回答上述问题。父权制和资本主义可以被看作两种完全不同的体制,各有其自身的利益、运行规律、矛盾模式和矛盾解决方式。这两种体制的交叉点是不确定的、不规则的。但是这种两种轨迹的方法可以弥补马克思主义理论看不到性别区分的缺陷,从而使男人和女人的关系的体制特征更为清楚。马克思主义无法回答为什么女人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家庭外都从属于男人这一问题,也无法回答为什么不是颠倒过来,男人从属于女人这一问题,然而,根据哈特曼(Hartmann)的说法,女权主义分析能够揭露父权制在男人对女人劳动力的控制方面有其物质基础这一事实。上述关于家庭工资的争论是解决关于妇女劳动力在父权利益和资本主义利益间的纷争的例子之一。米切尔主张,这两种体制在理论上是无法还原的,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存在一种归纳主义倾向,即把再生产的功能和角色、性取向和社会化看作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事实上,在《心理分析和女权主义》(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这本书中,她表明,妇女受压迫的根源深植于人类的心灵之中。
关于成熟主体的身份获得问题被提了出来,很具启发意义。如果我们接受成人主体想要的实际上是能够维持现存社会体制的那些事物,如果我们相信性、性别和性取向的和谐是确保这些愿望得以实现的各种进程的结果,相信我们对于自己是谁的判断依赖于这些信仰、愿望和行为,那么,寻找一种能够描述个体被指派到社会秩序中的某个位置的方式的理论就显得异常重要了。通过延伸和发展马克思关于意识的论述,我们似乎可能对妇女的“错误意识”有所理解。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二元体制的理论者们求助于阿尔都塞的马克思主义,希望能够在他的“质询”理论中找到关于意识形态的论述,以用父权制意识形态力量之外的原因来解释妇女的“错误意识”。米切尔本人也试图把结构语言学的理解与心理分析结合起来,以使对主体身份的分析更加完善。她早期的观点是,妇女与生产、低工资、兼职工作和经济依赖性之间的关系是压迫的根源,但是这种关系是与生物社会学考虑和社会中流传的有关男性气质和女性气质的更笼统的思想共同发挥作用的。她对父权制所作的心理分析,假想的从一元原因分析到多元原因分析的过渡,预示了向后现代主义的转变。
激进女权主义者关于主体身份的复杂性的观点,关于异性爱维持社会稳定运转的方式的观点,对二元体制理论者和一元体制理论者之间的争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与性倾向相关的问题在一些著作中被推向了政治日程的最前沿,并在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关于女性同性恋关系的争论中达到顶峰。英国左派关于主体身份和性倾向问题的争论逐步转向哲学领域,将心理分析和多种形式文化的重要性的理论囊括进来。这一转向,尤其是朱丽叶·米切尔和杰奎琳·罗斯(Jacqueline Rose)的拉康心理分析转向,也受到了来自亚当斯(Parveen Adams)等人的挑战,但是从这种转向中,还是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洛弗尔(Lovell)提出,文字向社会历史分析的聚合使文化研究成为女权主义理论的“自然生长环境”,这正好与本哈比的“文化转向”的描述相契合。
文化研究有一种折衷主义倾向,人们对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经济主义解读让位于人们对诸如葛兰西、阿尔都塞、拉康、巴特和福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兴趣。当时,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似乎就是,社会主义的历史是否应该包括将人类主体性历史化的观点。科拉·卡普兰(Cora Kaplan)等人告诫说,如果符号学家和心理分析理论家不保持他们的唯物主义分析和阶级分析,创造的至多也只能是一种“反人道主义的浪漫的激进观点”。因此,对主体的批判,以及认为表面的统一的主体身份实际上是先前的语言进程和性别心理进程的结果的观点,引发了一系列关于心理分析的本质的争论。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有三个基本的共性特征。一是它们都声称自己是科学的、唯物主义的,二是它们都质疑没有价值倾向的科学方法的生命力,三是它们都对社会化的人的主体感兴趣。然而,尽管马克思主义和心理分析关注变革过程,关注斗争和解决方式,但他们在变革过程的本质这一问题上却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那些受心理分析理论影响的理论家主张,马克思主义者把导致斗争和侵犯的结构社会化了,而且马克思主义者对商品崇拜和商品意识的解释从根本上说是一元的。马克思主义者主张,心理分析崇拜主体性,将人的动机自然化,而且假设人的心理结构是不变的、通用的,但事实上,心理分析是对异化的悲惨境遇的个体化回应,而且把异化体验从它产生的大背景中抽象出来的做法导致了一种个体与现状相调和的理论。如果事实证明心理分析理论不仅是误导的而且是错误的话,那么文化理论和女权主义将面临什么状况,这是一个值得思索的有趣问题。
身份理论:转向后现代主义
身份理论出现于80年代,体验(几乎是经验主义的一种极端形式)在激进女权主义中的轴心作用,以及70年代向心理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左转和向法国文学批判主义的左转,都在理论上预示了这一理论的出现。20世纪80年代,人们目睹了英国政治文化领域发生的巨大变化,其中就包括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女权主义的消亡的事件。这里,我只关注英国,美国有它自己的内部动力机制。在撒切尔主义(“自由市场”的财政政策)的兴起和左派的分裂(女权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消亡、身份政治以及几乎是排他的强调身份问题的身份理论的出现)之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有人提出,英国女权主义的独特特征是,它植根于60年代和70年代的高层工人阶级运动。在80年代,工会运动和劳工运动普遍衰落。导致女权主义的政治消亡的因素之一,是女性解放运动内部已经积聚了10多年的张力。激进女权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之间的冲突,中产阶级女权主义者和工人阶级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冲突,黑人女权主义者和白人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异性恋女权主义者和同性恋女权主义者之间的冲突,在地方组织中、在会议中以及在各种编委会中都显露无疑。这些冲突迫使女权主义者认识到他们自己的位置,承认女权主义思想内部的普遍趋势。那种认为某个个体因为具备了某种性别特征就应该与某一特定的政治运动结盟的主张已经不再可行,作为一项政治运动的女权主义目标的正当性变得难以证明。当在女权主义行为的合适位置这一点上的分歧根深蒂固的时候,就出现了这种认识。有些人,如希拉·罗博特姆(Sheila Rowbotham)和希拉里·温赖特(Hilary Wainwright),试图从女权主义内部改变劳动政治主张,而其他人则主张,一种更开放、更民主的政治运动与旧式的劳工政治群体或工人政治群体是不相容的。
与作为一种政治力量的女权主义的灭亡相伴而生的是学院女权主义的巩固和加强。学院女权主义曾被相应地称为去激进化的女权主义理论,这是与“市政女权主义”(municipal feminism)的兴起相关联的,“市政女权主义”是把女人和女权主义理论逐步渗入公共机构(包括高等教育机构但不仅限于高等教育机构)的女权主义。有两个原因可以说明为什么高等教育机构中女性数量的增长与女权主义理论的去激进化相关联。第一点原因引导我们去关注公共机构对工作类型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方式。第二点原因引导我们去关注广为流行的学院理论的类型。下面我们先来看第一点。一个公共机构可以被定义为一种实体组织形式,这种实体组织包含了沉淀其中的权力关系和资助管理概况。某种学术实践“准则”和“理想的”学术实践者的图像逐步渗透进来。学术实践规则限制或告知了学科的主体研究内容。人们默认的事实是,所开展的学术研究类型就是能够确保得到资助和发表的研究类型。此外,一个公共机构的首要任务就是传授策略。人们用不着成为福柯就能理解,构建一套准则的教学动力是如何提出研究哪些问题和排斥哪些问题的。
对于理论的去激进化的第二种解释是关于理论本身的本质的问题。女权主义学术理论已经在从文学理论到认识论、从建筑学到地理学、从生物学到法学的各个领域蓬勃发展起来。但是身份理论却占据了最高统治地位,后结构主义已经对女权主义内部的方向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而这又带来了战略问题和理论问题。有人主张,女权主义关于差异的讨论已经使女权主义丧失了作为一种政治主张的根基。这有两方面原因。第一,一旦人们认识到妇女的差异性,并把妇女的差异性置于一致性之上,那么任何一种集体的有明确目标的行动能否开展起来都成问题。第二,女权主义理论的主旨变成了其自身,而且这一理论的目标变成了对内部分野和矛盾的主体地位的反思和质问。
将社会复杂性理论化
这里,我想提一下安·布鲁克斯的观点,即后现代女权主义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批判理论,致力于批判女权主义理论分支中的本质主义、种族中心主义和反历史主义。我的观点是,女权主义理论只有在抛弃了它的一些核心主张的情况下,似乎才可能成为一种批判理论。首先,有必要澄清几个概念,即普遍主义、本质主义、自然主义和生物主义,我先暂且不说关于身体和性别的问题,因为我认为,只有先澄清以上这些概念,才能正确地阐述这些问题。
伊丽莎白·格罗斯(Elizabeth Grosz)在《关于本质主义和差异的笔记》(A Note on Essentialism and Difference)中直截了当地对这些概念作了区分,她主张这些概念都是用来证明女人的社会从属地位的正当性的。本质主义、生物主义、普遍主义这些概念总是结合在一起支持现存的权力关系,证明现存权力关系的合理性。但是有一点不清晰,即为什么本质主义或普遍主义或漠视传统(ahistoric)必然是不好的,实际上本质主义也可以借助联盟的力量;人们强调普遍主义,但也可以维护个体的个性特征;人们漠视传统,但也可能是一个马尔库塞理论的信奉者。另一点不清晰的是,做一个生物现象论者意味着要坚持本质属性或普遍属性;人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的相似点来思考个体。这种主张通过把生物学和生物主义结合起来,把自然和自然主义结合起来(尽管可能是无意识的),其表述往往不能反映真实情况。
她主张,女权主义者面临的两难处境涉及研究严谨的目标(避免本质主义和普遍主义)与女权主义政治斗争(致力于解放作为女人的女人)之间的冲突。她相信,女权主义理论必然涉及一系列的复杂谈判,如果女权主义理论在政治上不能摆脱父权制框架、方法和假设的影响的话,那么就需要承认这种影响。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失去影响力似乎有三点原因:一是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可能建立在对类存在物进行自然主义叙述的基础上);二是它的科学主张;三是它的历史研究方法。
普遍主义和本质主义之间的关系也是伊丽莎白·斯佩尔曼(Elizabeth Spelman)探寻的目标,她列举了艾里斯·默多克(Iris Murdoch)的《好与善》(The Nice and The Good)中的标志性段落以说明,把许多特殊个例归纳为具有独特的普遍特质的事例的内驱力是对经验世界的混乱状态的一种心理反应。为了将特殊个例包含在普遍特质之中,必须优先强调相似性而非差异性,异质性被归纳为同质性,总是要预先假定一个适合于所有事例的本质。于是,为了将个体归属到一种普遍概念之中,我们必须假设每一事物都必然具有一些属性,这些属性是所有事物都具有的普遍属性。斯佩尔曼坚持认为,这是一种形而上学的错误,将导致极为严重的政治后果。首先,她认为,个体不是普遍适用的属性(种族、阶级和性别)的总和。由于不存在个体共有的永远不变的属性,因此人们认为,“女人”这一词条并不能代表一个自然群体。按照这一思路,由于关于普遍属性或一般属性的断言是错误的,因此普遍属性起作用的方式也变得值得怀疑了:利益分类被作为一种中性标准提了出来,根据这一标准对各种事物作出判断。这不仅是女权主义理论的内部问题,也是女权主义理论的外部问题,在女权主义理论中,从某一个别立场归纳出的准则被错误地认为是适用于所有同类的其他个体的;通常,享有特权的女性的特征和经验被概括为所有女性的特征和经验。④
如果我们对这种个人主义及其与某种政治形式的一致关系有些担忧,那么我们就会回答说,人们可以抵制闭合式的定义,不接受这种唯名论,使决定群体身份归属的利益关系更加明晰。作为一名唯名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尼古拉·斯托利亚(Nicola Stoljar)为人们呈现了一个女权主义内部的唯名论的最好例子,但是如果人们还想描述将个体区分为各个群体的划分方法背后的机制的话,那么还需要有一点本体论的知识,本体论包括意识独立机制和认识论。这两者都是莫伊拉·盖腾斯(Moira Gatens)研究的内容。
当代女权主义者不愿意在她们的名字前面加上另一种理论的名称,如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按照盖腾斯的说法,这表明了女权主义者对社会政治理论的深度怀疑。女权主义者不再相信这些理论能够解释或阐明妇女的地位问题,因为这些理论已经被破坏了,不是被表面的无视性别差异所破坏,而是被更深层的某些东西所破坏。(1)理性:理性被定义为与女性气质或传统的女性角色相对的特性。马克思主义也是如此:科学主张、终极目标、辩证法。(2)二分法:如再生产/生产、家庭/国家、个体/社会。她说,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不能在二分法之外思考问题。二分法从本质上说是一种等级划分法,把女性分成了不同层次的女性。(3)权力:被看作是某人拥有或没有的某种东西,主要表现在对政治经济关系的调节和控制上。(4)压迫:倾向于假定一个团体受到了性别歧视。这是哈拉韦(Haraway)在她的《电子人》(Cyborg)中的观点。
要想使对理性和身份原则是父权制的固有特征的说明具有说服力,还需要作大量的工作,事实上,劳埃德(Lloyd)的哲学叙述是有选择性的,歪曲了某些哲学立场,并没有说明盖腾斯认为迫切需要说明的那些问题。但是这种说明也压制了任何批判性借鉴的内容。不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我们甚至无法开始讨论其他的主张。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滑入浪漫的反人道主义的先锋主义倾向,在这种倾向中,思想是固定不变的,认识与现状是和平共处的。
米瑞杜拉·查克拉博蒂(Mridula Chakraborty)主张,“波/阶段/以波为基础的意识”的观点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主体意识形态建构,这种欧洲中心主义的主体意识形态建构试图把对其的质疑囊括进来。钱德拉·莫汉蒂(Chandra Mohanty)断言,当女权主义的一致性受到威胁,受到某些群体的抵制时,占主导地位的女权主义不得不坚持说,这些种族群体在政治上既不是一个团体也不是一种有效力量;这是用本质主义方式来构想女性团体问题的表现。白人女性的特权仍然完好无损,而用来缓和差异造成的紧张状态的主张却变得越来越世故,越来越神秘莫测。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现了另一个持有相同观点的人哈索克(Harstock),他问道:“为什么会是这样,正当西方历史中先前沉默的人开始发表她们自己的意见,为了她们自己的利益说话的时候,主体这一概念以及发现/创造一种解放真理的可能性变得令人怀疑了。”
关键的问题在于,如果现代性的环境仍然存在,那么女权主义是否可能是后现代主义的。第三波有一个预设条件,那就是承认,女权主义理论不得不意识到女性不仅有一个位置,而且有多个位置,压迫的根源不只是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不得不承认女权主义思想中种族主义倾向的普遍化,不得不对个体被包括在一般中的事实进行说明。对位置和地位的批判性思考能够防止陷入诱人的对身份的闭合性思考之中,能够指出把同一性强加于相似性之上,把相似性强加于差异之上的机制,但是只有当这种批判性思考是现象学的思考,是利用了本体论和认识论的批判性思考时,才能达到这些效果。
资本的全球发展的本性提出了第三波女权主义者必须给予解释的深层问题,要解释这一问题,第三波女权主义就要到她们的女权主义历史中去找寻答案。是否存在一种经济向下流动的普遍趋势?或者说是否存在一种全球贫困的女性化趋势?是否必然存在一种劳动力的女性化趋势,或者存在一种劳动力的同质化趋势?家庭是一个法律单位和意识形态单位吗?或者说家庭是一个反抗场所吗?儿童贫困和家庭结构之间是什么关系?跨国公司对地方经济有何种影响?劳工市场分化(以种族和性别为分类标准)了吗?劳工市场的分化是有效的剩余价值榨取的一部分吗(即是剩余价值榨取导致的吗)?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进军中东和中东战争?当性别关系问题悬而未决之时,性倾向问题是否站到了最前沿?我们如何使别人了解和理解我们对虐待儿童、家庭暴力、诱奸、强奸和色情影片的态度,以得到回应和资助?不仅第二波女权主义者抛弃了这些问题,而不是解决了这些问题,而且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新左派也同样如此。
海伍德和德雷克提出,第三波女权主义所处的全球背景是跨国资本、公司规模缩小、转向服务经济、经济地位方面普遍的下向流动和技术文化;所有这些都与女权主义的反资本的、地方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行为主义的新形式相符。第三波女权主义试图引导出一个事实,即在全球商品化的生产圈和消费圈之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因此第三波女权主义者批判性地与消费文化结合起来,颂扬消费文化。按照珍妮弗·鲍姆加德纳和埃米·理查兹(Jennifer Baumgardner and Amy Richards)的说法,第三波女权主义者把女孩划到了具有显著生产力的女性文化中。这往往涉及到对流行的女性气质——包括芭比娃娃、化妆品、时尚杂志、高跟鞋——的颂扬,第三波女权主义者说,使用这些产品并不表示“我们被愚弄了”。这真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女权主义。
因此,文化的或者说民粹主义的第三波女权主义者被认为是接受了她们的女性身份及其表现的女权主义。这种女权主义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个阶段能否具有重要意义,取决于女权主义能否抓住自我代表的代理人,以及能否利用这一力量。因此,关于把女性美商品化这一问题的争论变成了关于是否应该把限定价格等同于物化的争论。我们如何判断最近对于差异的评价,对于痴迷于艺术激情、自我肯定和思想新潮的少女的力量的评价,是否是对特殊社会环境的正确回应?对权力的创造性利用可能会证明美感屈服于现代商业逻辑的事实;尽管是同一商品,但是其形式要保持常新。我们重复差异、多样性和多元主义越多,我们听到的现代主义的回声就越多,警告我们,这种行话的使用似乎已比同质化还要多。
美国曾有学者在1988年就已指出,后现代主义已经终结。在此之后,加里·波特和乔斯·洛佩斯(Garry Potter and Jose Lopez)于2003年宣称,后现代主义是一种正在衰退的“过时”的状态,这不仅因为后现代主义的大多数激进主张在今天已经显得非常陈旧,而且因为后现代主义不足以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作出回应。他们提出,现实主义提供了更合理更有用的框架,从这一框架出发,可以理解本世纪的哲学挑战和社会挑战。因此,是现实主义而不是后现代主义提供了真正能够富有成效地解决各种学科的问题的方式。还有很多人持有与她们一样的观点。除了批判现实主义者,如卡罗琳·纽(Caroline New)之外,诸如戴维·哈维(David Harvery)、琳达·阿尔科夫(Linda Alcoff)、特雷莎·德·劳雷蒂斯(Teresa de Lauretis)等人也呼吁不是回到旧的知识中去,而是寻求一种新的知识;这里我提出我的观点,我支持哈维的观点,这种新的知识将是一个注入了新活力的历史唯物主义。莉迪娅·萨金特(Lydia Sargent)在她《马克思主义和女权主义的不快乐的联姻》(The Unhappy Marriage of Marxism and Feminism,1981)一书的导言中写道:“今天,我们正在进行一场运动。我们有了理论和实践的起点。”“女性问题”再也不会被称为“没有名字的问题”,“我们有名字”。1988年,丹尼丝·赖利(Denise Riley)提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我属于那个名字吗?”现在我们应该认识到,正如我们不属于那个名字一样,我们也属于那个名字。
(本文经作者授权发表,原文标题为“After Postmodernism:Feminism and Marxism revisited”)
注释:
①See M.Shildrick,"Sex and Gender" in Gillis Howie ed.,Third Wave Feminism:A Critical Exploration(Palgrave,2004),pp.67-71.
②S.Bordo,"Feminism,Postmodernism and Gender Scepticism" in L.Nichdson ed.,Feminism/Postmodernism,(London,Routledge,1990)p.142.
③Ibid.,pp.135,142,153.
④E.Spelman,Inessential Woman:Problems of Exclusion in Feminist Thought(London:Woman's Press,1990),pp.1-5.
标签:女权主义论文; 马克思主义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后现代主义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家庭结构论文; 社会问题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经济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