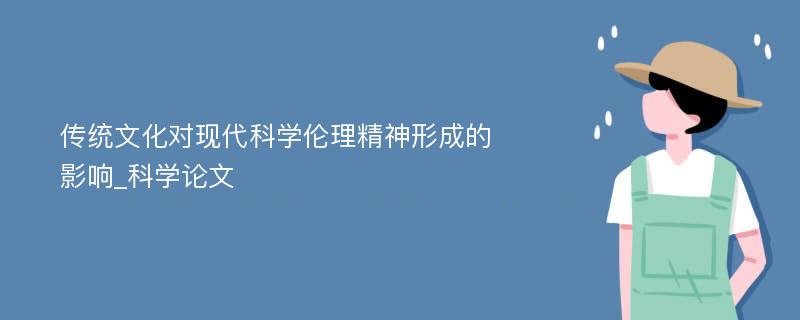
传统文化对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生成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传统文化论文,伦理论文,精神论文,科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国传统天人观的伦理意蕴对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生成的启示
现代科学伦理精神是科学精神的升华。如果说科学精神是以理性为本性,以求真为核心,以合理怀疑为动力,以创新为宗旨,以务实为依归,那么现代科学伦理精神则是以理性—伦理为本性,以臻善为核心,以责任为激励,以完善人格为宗旨,以协调发展为依归。因而,科学精神体现的是科学活动主体认知—求真的需要与实现的程度;现代科学伦理精神体现的则是科学活动主体的臻善需要与实现程度。前者主要在科学领域,体现了科学活动主体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的历史使命,后者则超越了科学领域,进入了科学—社会领域,体现了科学活动主体对科学成果合理应用的道德责任意识、促进科学发展和人—自然—社会系统的协调发展的道德使命。那么,科学精神是如何向现代科学伦理精神升华,实现这具有历史意义的跃迁的呢?其关键的转折点是基于科学活动主体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再认识。近代以来,科学的勃兴,使人在与自然关系中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即由原来受制地位变为支配地位,自然成了被认识、征服和支配的对象。英国科学史学家李约瑟博士认为,人主宰自然的狂热是欧洲科学思维中最有破坏性的一种。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干预自然的能力愈来愈强,人与自然的对立日渐尖锐。人类不仅破坏了自然界的自我调节机制和动态平衡,同时也使自身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而对这一严峻的现实,人们,尤其是科学活动主体不得不重视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传统的天人观的伦理内涵重新受到人们的关注。
我国传统的天人观是一种伦理化的天人观,它是以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为原型,建构天人关系并推测天人关系的种种特征。首先,这种天人观十分强调天与人在基质上的同一性。如《管子·内业》认为,“精也者,气之精也”,“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为人”。王充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认为,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和万物一样,也是禀受元气而成。他说,“然则人生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①]这种天人观具有质朴性,正如恩格斯所说:“它在自己的萌芽时期就十分自然地把自然现象无限多样性的统一看作不言而喻的,并且在某种具有固定的形体的东西中寻找这个统一。”[②]人与自然的统一是我国传统天人观的出发点。其伦理意义就在于,它不把人看作凌驾于自然之上,而是居于自然万物之中,并与其和谐共处于统一体中。其次,由于人与万物处于同一系统之中,人就须兼爱万物。因为,在我国古代思想家看来,人虽然是自然的一部分,但又不同于其他万物。《尚书·泰誓》曰:“惟天地,万物之母,惟人,万物之灵。”荀子将人与万物作了比较以后,阐释道:“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③]。因而,人在天人关系的运作中负有“至诚”、“尽性”的道德使命。《礼记·中庸》曰:“自诚明,谓之性。”“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这种赞天地之化育,在实践中则表现为兼爱万物。《孟子·尽心上》曰:“君子之于物也,爱之而弗仁;于民也,仁之而弗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要求人们从爱亲人到爱百姓,然后将爱扩展至万物。这一过程便是“度”,正如荀子所说:“圣人者以己度者也,故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④]之所以能“以类度类”,是因为“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我有之得私也。惟大人为能尽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爱必兼爱,成不独成。”[⑤]故而,作为一个有崇高德性的人应周知万物,兼爱万物。再者,我国传统的天人观还提出了“与天地合德”的思想。我国古代哲人不仅看到了天(自然)与人的一致性,而且在长期的实践中体悟到自然规律的先在性和对人的行为的制约性。如《周易·乾》曰:“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所谓“先天”即为天之前导,在自然变化未发生以前加以引导,所谓“后天”即遵循天的变化,尊重自然规律。若不尊重自然规律即“动不以道,静不以理,则自夭而不寿,妖孽数起,神灵不见,风雨不时,暴风水旱并兴,人民夭死,五谷不滋,六畜不蕃息”[⑥],总之,会有种种灾难降临。因而,人须体天意,循天理,遵天命。在《礼记·祭义》中,有这样一说,“断一树,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这就把人与人之道德规范推至自然领域,以制约人们滥伐树木、滥杀生灵的行为。第四,在天人相谐的基础上,提出了“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荀子认为,虽然“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⑦],但是人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变自然,给人类造福。他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⑧]他指出,“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谓能参”。“圣人清其天君,正其天官,备其天养,顺其天政,养其天情,以全其天功,如是,则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矣。”[⑨]这是指,人若能够正确运用自然所赋予人的职能,正确掌握自然规律、充分发挥自然的功用,就能使天地万物为人服务。尽管我国传统的天人观有其质朴性、直观性、臆测性,但是其中蕴含的伦理内涵对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生成有着深刻的启示。
首先,科学活动主体应该汲取我国传统天人观的天人一致的思想。当代人与自然的关系之所以会出现尖锐的矛盾是由于人类在处理这一关系时,只注意人工自然(即人创造或改造的与人的生存直接相关的生存环境)的优化,而未从人—社会—自然的整体性方面进行系统的思考、规划,从而导致了人—社会—自然系统的次优化,破坏了人与自然(天人)关系的和谐状态。这从反面说明,人类要使自身及其社会得以生存发展,必须以天人相谐为前提,否则,不但使自然遭到破坏,而且人类及其社会也难以生存和发展。这样,原来的人与自然这对非伦理关系(认识与被认识、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变为一种同处一个利益共同体中的伦理关系。其次,制定“兼爱万物”的生态伦理规范。现代生态学认为,尽管人类组织了结构复杂的社会,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并把自己与其他生物区别开来,然而,人类和周围环境与其他生物仍然是不可分割的整体。无论人为了维持生命而摄入的食物,还是进行社会活动所使用的能源都与自然生态系统紧密相关。不仅人类生存和社会活动离不开自然,而且人类的实践活动还受生态规律的制约。一旦人类破坏了这种生态制约性就必然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失调,进而危及人类的生存。因而,“兼爱万物”不仅成为科学活动主体处理天人关系必须遵守的伦理原则,也是成为其自觉的道德意识。再次,全面探索天人协同的内在机制和内在规律,将“制天命而用之”付诸实施。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不仅像在意识中理智地复现自身,而且能动地、现实地复现自身,从而在他所创造的世界中直观自身”[⑩]。随着科学活动主体对人—社会—自然系统内在奥秘探索的深入和对这一系统规律的全面把握,人类将“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还能“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11)]真正达到“范围天地文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的境界。这便是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实践德性。
我国传统认知观的情理内涵对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生成的启迪
我国传统文化不仅对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生成有天人观方面的启示,而且有认知观方面的启迪。前者体现了我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生成的一种潜移的宏观效应,即在本体论上的引导性,而后者则表现为一种潜移的微观效应,即对科学活动主体的单元——科学共同体运作的引导性。
我国传统的认知观十分强调情理感通性。这里所说的“情”非情欲之情,而是血缘之情、伦理之情;“理”亦非理性之理,而是人情之理、伦理之理。这种情理感通性包括人与人之间的感通,今人与古人的感通,人与天(或物)的感通。正是依据这种认识的情理感通性,人们在认知客观对象、了解人际关系时,总是十分讲究“以情动人”、“以理服人”,通情以达理;在与人相处或协调人际关系时非常重视将心比心、以心换心的感化换位法则,使人们情有所归,知有所达,意有所向;在与人交往中,讲究施—受—报的情理义务。应该说,这种情理感通性在主要是以伦理训练,而不是以法律精神治理国事的我国封建社会,“每一个人首先考虑的不是遵从国家的法律,而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中履行伦理义务:臣对君尽忠,子对父尽孝,妇对夫尽顺,弟对兄尽悌”[(12)],同时君、父、夫、兄也有相应的义务,而这些义务大量地是通过认知的情理感通实现的,从而维护了封建宗法社会的和谐。尽管现已时过境迁,然而,我国传统文化认知的情理感通性在当代仍有其特有的伦理功能。
现代科学伦理精神在其生成过程中,应汲取我国传统认知观的精华,即将传统的情理感通性运用于科学共同体之中,能使科学共同体更具有凝聚力、竞争力和创造力,进而推进科学的发展。在现代,科学共同体是从事科学信息创造、进行科学研究和科学应用以及协调人—社会—自然系统的科学活动主体单元。因而,科学共同体内部的人际关系和谐与否,直接关系到科学共同体自身的凝聚力、竞争力和创造力的强弱。情理感通性作为一种伦理认知方式对于科学共同体具有以下三个方面的伦理功能。首先,调节认知。通过情理感通使科学共同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对这一共同体的伦理精神、奋斗目标、制度、伦理规范产生认同感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内心信念和职业理想,从而使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为实现共同体的奋斗目标、执行制度、履行规范而努力。其次,沟通情感。科学共同体在运作中一般经过以下三个环节:一是感化情致。所谓情致是指科学活动个体对社会伦理规范和科学共同体的奋斗目标、规章制度、伦理规范的积极的、肯定的情感体验,其中包括个体对科学共同体奋斗目标的认同感、对规章制度的遵从感、对伦理规范的尊崇感等。通过情致的感化,能促使共同体成员积极履行伦理规范,参与共同体的探索与创新活动,与此同时,对自己在科学共同体中的地位、角色和所应当承担的任务有一定的了解。二是疏导情愫。如果说情致是个体进入共同体后想很快适应共同体氛围、成为共同体一员而产生的积极的情感体验,那么情愫则是个体在了解了共同体奋斗目标实现的艰巨性、规章制度的严格性、自己在履行伦理规范、处理各种伦理关系中,由于心理基质与外部要素的非同构性而引起的负性情感体验,如困惑感、焦虑感等等。科学共同体通过(正式的与非正式的)舆论方式及时排解个体的负性情感,使其从困惑、焦虑中解脱出来,正视客观现实,增强组织感、义务感和心理承受力,使个体情感逐步趋于社会化和成熟化。三是培养情操。情操是个体对自身、他人、社会及科学共同体的现实伦理关系认知的基础上,对情致和情感的统摄而升华的一种高级情感。科学共同体通过情理感通,培养其成员的情操,使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科学活动有一种自尊感,对奋斗目标的实现有自信心,将伦理规范不看作是一种外在的强制,而将其内化为自身的内在的需求,对科学的发展与科学成果的合理应用有强烈的责任感。这时个体既能在科学活动中感受到科学共同体奋斗目标实现的艰巨性、履行伦理规范的使命感,又能体验到奋斗中的幸福感和履行了伦理规范以后的自足感、自由感。由于情理感通促使个体情感与科学共同体的整体情感相适应,进而使个体情感升华。再者,凝聚意志。科学共同体还通过情理感通凝聚其成员的意志,使他们团结一心,奋力攻关,实现目标。
我国传统价值取向的仁智相蓄性对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生成的启发
价值取向是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核心,它对现代科学的发展和科学成果的应用起着一种导向作用。因而,科学活动主体在确立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价值取向时,应注重从我国传统的价值取向中汲取伦理的精髓。
在我国传统文化中有智仁勇三大德之说,充分肯定了仁与智相互依赖的关系,形成了必仁且智的德性价值取向。如子贡说孔子是“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13)]诚然,这种对于“智”的解释是采取了广义的形式,但其中也包括了科学知识,如《礼记·中庸》曰:“成己,仁也;成物,知也”。这种必仁且智的德性价值取向具有丰富的伦理内涵。首先,必仁且智是人作为价值主体的特征。孟子认为,人之所以有别于动物,就在于明人伦即理义。他说:“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14)]人何以有理义呢?孟子以为这是靠思维的作用。他说:“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15)]故而,理义是思之所得。孟子认为,人能思,则能认识自己固有的价值。不仅如此,孟子还认为,人的心与性具有统一性。他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16)]戴震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进一步阐发了价值主体的仁智特征。他认为,“人以有礼义异于禽兽,实人之知觉大远乎物则然”[(17)],这是因为心不仅能“辨理义”,而且能“悦”理义,这种能辨理义而且能悦之的能力,便是德性。他还在阐述人的德性发展的同时,论述了德性(仁)与智的相关性,他说:“试以人之形体与人之德性比而论之,形体始乎幼小,终于长大;德性始于蒙昧,终乎圣智,非复其初矣。”[(18)]其次,必仁且智德性价值目标的实现有两种方式。孔子主要从个体至善的角度阐发了这种价值目标的实现,他提出“君子以义为上”[(19)],“好仁者,无以尚义”[(20)]的命题,强调了仁即德性的至上价值。孔子又说:“仁者安仁,知者利仁”[(21)],“安仁”即安于仁而行之,“利仁”即以仁为有利而行之。仁者实行仁德,不是以仁为有利,即不以仁为手段,而是以仁为目的。“知者利仁”是有所为而为;“仁者安仁”则无所为而为,因而“仁者安仁”具有内在价值。在处理仁智关系上,孔子认为,“志士仁人,无以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这是说,仁者安人,知者利仁,在安仁、利仁的情况下,仁与生并无矛盾,但在一定条件下,生仁不能两全时,应牺牲生命,以实现仁(德)。后来,董仲舒进一步提出了对后人影响较广较深的命题:“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22)]王充则从国家至善的角度提出了“德力具足”的仁智观。他说:“治国之道所养有二:一曰养德,二曰养力。养德者养名高之人,以示能敬贤;养力者养气力之士,以明能用兵。此谓文武张设,德力具足者也。”[(23)]
我国传统文化必仁且智的价值取向对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价值取向之设定具有启发性。首先,就现代科学研究和科学成果的社会应用来说,坚持必仁且智的价值取向具有重大实践意义。无论是从当代科学研究还是科学成果的应用来看,其中既有智的问题,又有仁(德)的问题。就智的问题而言,科学成果的社会应用之所以出现负效应,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人们对自然、社会、人自身的内在奥秘的探索远非完全而系统,对许多科学成果应用于人—社会—自然系统以后将会产生的深远影响了解得还很不够。由此科学活动主体产生了继续探索真理的需求,以便从客观事物发展的规律上、从人—社会—自然内在协调的规律方面寻求科学成果应用的途径。再就仁(德)的问题来说,从以往科学的发展及其成果的社会应用所导致的负效应来看,其中固然有知识的不足,从而使人们的认识受到限制(智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从事科学研究与应用的社会集团、阶级等的价值目标不纯正或不正确。具体表现为,他们在进行某一项目的研究及其成果的社会应用中,只顾少数人或本阶级、本集团的利益,而不顾及多数人或全人类的利益;只顾当前,不顾长远;只重经济效益而轻视或根本不关注社会效益。由于当代科学的发展及其成果的社会应用“对于为善和作恶,都有无穷的可能性”[(24)],因而,端正其价值目标——坚持必仁且智的价值取向是时代的要求,也是科学活动主体所作的明智的选择。一方面,科学活动主体要以仁导智,即以至善——造福人类为指向,以人类的长远利益和人—社会—自然系统的协调作为科学发展及其成果应用的目标,争取最佳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另一方面,又要以智促仁,积极探索人—社会—自然系统运行的规律以及这一系统内三要素之间的依存关系,预测科学研究及其成果应用对于当前的与长远的、直接的与间接的影响,从而掌握对科学研究及其成果合理应用的主动权,尽可能地扬善抑恶,趋利避害。其次,科学活动主体还应从个体至善和社会至善的角度提倡道德责任的至上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科学之合入社会的过程越来越明显和强化了。”[(25)]一方面,科学研究设备的精致化需要更多的外部资助,同时也导致了科学活动的群体化和工具化的社会过程。从而使个体在自主条件下进行无功利的研究越来越不可能,不仅如此,科学群体(共同体)在经费短缺的条件下进行科学研究,不得不更多地考虑社会的需要,以获得有关机构或社会的资助;另一方面,现代科学研究成果的获得及其应用之同的间隔,比过去大大缩短。这就迫使科学活动主体不得不通过多种环节和多角度对其研究及其成果应用的可能性进行预测。这就说明,现代科学活动(科学的研究、应用与开发)已不再是一个独立的自给自足的认知活动系统,而是社会活动的一个环节。随着社会的发展,科学活动的社会内涵不断增加,科学成果的社会应用范围越来越广,对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和对人类与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因而,科学活动主体在科学活动中坚持道德责任的至上性不仅是社会的客观要求,而且愈来愈成为科学活动主体内心的自觉要求。一方面,科学活动主体努力实现科学“利仁”的外在价值,根据客观规律按照“任何一个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怎样处处把内在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26)],关注科学成果的社会应用并促使其尽可能地造福人类即仁的方面。维纳说过,“我们这些对于控制论这个新的科学有所贡献的人,因此都处在一个道义的位置上,这个位置至少是很不安适的。我们促进了一个新的科学的发轫”,“我们甚至无法制止这些新学科的发展。它们属于这个时代。我们所能做的最高限度,是制止把这方面的发展交到那些最不负责任和最唯利是图的工程师手中去。”[(27)]为此,科学活动主体应当主动参与科技政策的制定,在提出建议和论证方案时发挥自身的知识优势,与此同时,积极参与科学成果合理应用的社会宣传,强化人们合理应用科学成果的道德意识,创造良好的舆论氛围以指导和约束人们研究与应用成果的行为。另一方面,科学活动主体积极实现科学“安仁”的内在价值,注重自身的道德修养,形成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将小我融入人—社会—自然系统这一大我之中,在实现社会价值的同时实现善我性。
以上我们分别从天人观、认知观和价值论的角度探讨了我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生成的影响,显然,这种影响具有潜移性、渗入性的特征。现代科学伦理精神的确立应该充分汲取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但这决不意味着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简单重复,而应是在当代高科技发展和应用的背景下更高层次的升华,从而不仅在价值观上引导现代科学的发展及其成果的合理应用,而且陶冶和升华人们的思维品性和道德品性。这样一种思维取向的确立,对于我们重新认识我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道德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①《论衡·物势篇》
②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1页。
③《荀子·王制》。
④《荀子·非相》。
⑤《正蒙·诚明》。
⑥《大戴礼记·易本命》。
⑦⑧⑨《荀子·天论》。
⑩(11)(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6~97页。
(12)冯天瑜、周积明:《中国古文化的奥秘》,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7页。
(13)《孟子·公孙丑上》。
(14)(15)《孟子·告子上》。
(16)《孟子·尽心上》。
(17)《孟子字义疏正》卷中。
(18)《孟子字义疏正》卷上。
(19)《论语·阳货》。
(20)(21)《论语·里仁》。
(22)《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
(23)《论衡·非韩》。
(24)(27)维纳:《控制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第28~29页。
(25)邱仁宗:《科学技术伦理学的若干问题》,《自然辩证法研究》1991年第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