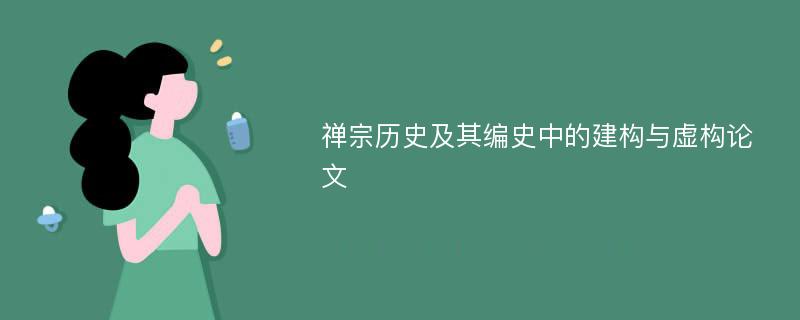
禅宗历史及其编史中的建构与虚构*
罗柏松 著 杨昌杰 译
在上个世纪,禅宗研究历经了大量卓有意义的改变① 译者注:“禅”的原文为“Zen/Chan”;本文原作者的解释为,文中所讨论的两本书的作者都用了“Zen”这一日文翻译,但是他们实际讨论的却主要是中国禅宗,因此本文原作者用“Zen/Chan”这种形式来指称一种更加广泛的禅宗概念,但是当仅讨论中国禅宗时,只用“Chan”。 。如今,我们都知道,禅宗传统最初被认为是东方“先验唯灵论”的巅峰;并且,由于受到一些东方学家的幻想和理想化意图的影响,一群禅宗护教论者将禅宗传统视为对抗西方“唯理论”和“唯物主义”的有效手段。他们这种关于所谓“纯粹”禅宗的理想化图景带有“反偶像、反制度”的色彩,并且,这种观念在二十世纪初随着敦煌藏经洞中大量材料的发现开始受到批判性地审视。于此,无需回顾整个禅宗研究史,我们只指出其发展过程中的几个关键节点。以下是一些具有开创性影响的学者:保罗·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胡适(1891-1962)、保罗·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谢和耐、入矢义高(1910-1999)、柳田圣山(1921-2006)。他们是提出了崭新问题与历史方法的新一代禅宗史学家② 比如,胡适,“The Development of Zen Buddhism in China,”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5.4 (1932):475-505;胡适,“Ch'an (Zen) Buddhism in China:Its History and Method,”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1 (1953):3-24;胡适,《神会和尚遗集——付胡先生最后的研究》,台北胡适纪念馆藏,1968;Paul Pelliot,“Notes sur quelques artistes des Six Dynasties et des T’ ang,”TP 22 (1923):215-91;Paul Demiéville,“Le miroir spirituel,”Sinologica 1.2 (1947):112- 37;Paul Demiéville,Le concile de Lhasa:Une controverse sur le quiétisme entres les bouddhistes de l’ Inde et de la Chine au VIIIe siècle de l’ ère chrétienne (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52);Jacques Gernet,Entretiens du Maitre de Dhyāna Chen-houei du Ho-tso (Paris:Publications de l’ Ecole francaise d’ Extreme-Orient,1949);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东京:法藏馆,1967。关于更完整的西方学术的书目,请参阅Bernard Faure,“Chan and Zen Studies:The State of the Field (s),”in Chan Buddhism in Ritual Context,ed.Bernard Faure (London:RoutledgeCurzon,2003),pp.1-35。 。而下一代西方禅宗学者,包括恩斯·艾普(Urs App),杰弗瑞·布雷顿(Jeffrey Broughton),罗伯特·巴斯威(Robert Buswell),伯纳德·弗雷(Bernard Faure),格里弗斯·福克(T.Griffith Foulk),皮特·格雷格利(Peter Gregory),约翰·麦克雷(John R.McRae),罗伯特·沙尔夫(Robert H.Sharf),戴尔·瑞特(Dale Wright),以及菲利普·扬波斯基(Philip Yampolsky、1920-1996) 在内,都受到过柳田圣山和新发现的敦煌写本的影响,他们都曾从历史学的角度批判地提出关于禅宗起源的观点,并试图在校订过的历史叙述中重新刻画出禅宗的重要人物① 关于这些发展的简明讨论,请参阅:John R.McRae,“Buddhism,”JAS 54.2 (1995):354-71;Faure,“Chan and Zen Studies”。也可参阅Cahiers d’ Extreme-Asie 7 (1993-1994)中收录的著作,他们都将自己的作品题献给了柳田圣山。 。受这些突破性研究的启发,禅宗学者们从批评禅宗历史的“起源”转向了关注其较后阶段的发展。这些学者证明,在很大程度上是宋代文本使我们认为唐代是禅宗传统的“黄金时代”② 可参阅:T.Griffith Foulk,“Myth,Ritual,and Monastic Practice in Sung Ch'an Buddhism,”in 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 ang and Sung China,ed.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Peter N.Gregory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1993),pp.147-208;Albert Welter,Monks,Rulers,and Literati:The Political Ascendancy of Chan Buddh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6);石井修道,《宋代禅周宗の研究》,大东出版社,1987;以及Schlütter,How Zen Became Zen。 。现在,学者们已经可以使用大量细节完善且可靠的历史和文本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不但展现了许多新的理论及方法论,也提供了基础文本的翻译,此外,它们还表明了对各种禅宗传统之重要文本及事实的一般态度③ 比如,可参阅:温迪·埃德梅克(Wendi L.Adamek),The Mystique of Transmission:On Early Chan History and Its Contexts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T.Griffith Foulk and Robert H.Sharf,“On the Ritual Use of Ch’ an Portraiture in Medieval China,”Cahiers d’ Extreme-Asie 7 (1993-1994):149-219;约翰·乔金森(John A.Jorgensen),“The ‘Imperial’ Lineage of Ch’ an Buddhism:The Role of Confucian Ritual and Ancestor Worship in Ch'an’ s Search for Legitimation in the Mid-T’ ang Dynasty,”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 35 (1987):89-133;J John A.Jorgensen,Inventing Hui-neng,the Sixth Patriarch:Hagiography and Biography in Early Ch'an (Leiden:Brill,2005)。 。
科尔(Alan Cole) 的《父其父》(Fathering Your Father) 以及莫舒特(Morten Schlütter) 的《禅何以为禅》(How Zen Became Zen) 促使我们反思当代禅宗研究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同时,这两部著作也反映了近年的学者正努力推动禅宗研究向一个崭新方向前进。科尔的著作着眼于禅宗发展的最初阶段直到唐代。而莫舒特的著作则着眼于禅宗传统之后的发展阶段,直到禅宗成为中国佛教主流的宋代。尽管现在已经没有新发现的文本能使我们从根本上改变对禅宗历史和教义的理解,但这些研究也给我们提供了新颖的阅读和研究方法。
4)外业调查:本系统利用RS技术来对土地利用图进行更新,因此,需确定变化图斑的边界与土地利用类型。这一系列工作可在内业完成,但判读确定部分土地利用类型的卫星数据与TM数据则必须要通过外业调查实现。
带着如今禅宗学术研究中的普遍态度,上述两位作者都将他们的研究称为对一种颇流行的过度理想化的禅宗印象的破斥,这种印象试图使禅宗过于唯心化。他们在前言中所作的免责声明虽然对该领域的专家来说显得没有必要,但对于谨慎的普通读者而言仍旧有用,它提醒读者们这些著作不同于大部分禅宗书籍,从而升华了主题。
科尔虽然始终小心谨慎,但似乎仍在尽力与大众读者群进行沟通。毋庸置疑,《父其父》的行文生动形象,但那些对禅宗研究不熟悉的人则会对书中繁冗的学术论争失去耐心。如果普通读者觉得科尔提出的阅读禅宗文本的方法论述令人费解,那也不必沮丧,毕竟,即使是专业学者,也会为科尔错综复杂的阅读手段而挠头。
科尔坚称其方法的基点在于,对具有普遍意义的禅宗基础性文本进行“精读”。他在重评禅宗早期文本的过程中使用了这种新的阅读方法,但是他关于该方法的描述十分晦涩,且几乎不可能得到验证。比如说,科尔称:“虽然文本D 看似仅被节录以作为对文本C 的回应,但它的作者也知道文本A 和B,因而,文本A 对D 的影响不是简单地通过‘A>B >C >D’ 进行传递,也可以是通过‘A >D’ 直接进行,亦可以是通过‘A>B>D'间接进行。”然后,在试图说服我们“想通这一点并不是太难”后,他注释道:“当文本E 是在作者知道A 和D 的情况下写的,并在考察D 从A中获取了什么后,又继续考虑D 曲解了A中的哪些内容时(此时通过间接分析D 对A 作了哪些改动),事情会变得更麻烦。”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Cole,p.14)。实际上,科尔只是需要一个范例来使读者明白:他所讨论的禅宗文本及其思想是从之前的文本中复刻、借鉴、剪接的。他声称,禅宗大厦只是矗立在流沙之上。但是,纵使他已经清楚地阐明了他所设想的文本关系的类型,他关于具体文本的讨论依然艰深难懂。此外,由于我们对他所用文本的版本和流传情况知之甚少——遑论其作者信息——且又因为科尔的解释是建立在因果链上,解释起来就更加困难了。
至于《父其父》一书如何能被该领域的学者们所接受,则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性格和对科尔的古怪类比及他那种通过为七八世纪的人们冠以种种动机来想当然地重构彼时历史场景的行为的宽容度。而读者也需要习惯科尔使用各种新词却不加以清晰定义的做法,如所谓“具真实性的人”(men-with-truth) 和“真实性祖师”(truth-fathers)。
相反,莫舒特并未提出一种新的阅读策略。他反倒不赞成扩展禅宗研究的文本基础。他所作的禅宗文本研究可以说是使用“数字化文献大规模检索”这一新方法的范例。他首先从最新的宋史研究成果中获取灵感,然后,他向我们展示了彼时禅宗史是如何同社会、文化、经济盘根错节地交织在一起的。为了实现自己颇有雄心的计划,他高效地利用了多种曾被禅宗史学者忽视的文本,包括“政府档案、正史、寺院的纪念碑文、高僧墓志、文集、游记、私人信件以及其他诸多佛教文献”(Schlütter,pp.4-5)。
莫舒特谙熟贯穿于科尔书中那段时期的历史及教义发展的情况;因此他解释了为何这部关于宋代禅宗的书叫做“禅何以为禅”。关于此书,他阐释道:“宋代对整个东亚禅宗产生了确确实实的影响,本书就是关于发生在这一时期的一系列禅宗重大发展事件的”(Schlütter,p.1)。在182页的篇幅内,他不光给出了严密的论证,也向我们展示了证据充分的关于大量新材料的研究,此外,他还成功地修正了关于宋代禅宗主要发展情况的叙述。
所谓的脾气好,并非没有原则的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而是得理且饶人,日后好相见,是退一步海空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
尽管这两本书看起来有许多共性和相同目标,但不管是风格、技巧还是基调都十分不同。此外,它们以截然各异的方式将自己与禅宗学者们积淀下来的传统联系起来。《禅何以为禅》被直接置于悠久的禅宗学术传统中;它是一部克制的著作,几乎没有包含任何激进的明确批判或观点。莫舒特试图在已有的宋代禅宗史研究基础上进行完善和创新,尤其是立足于西方及日本的新一代学者(包括石井修道、竺沙雅章、格里弗斯·福克,以及阿尔伯特·威尔特) 的成果。
根据一份关于过去六十年间禅宗研究情况的调查,我们可以明白,科尔夸大了他对禅宗早期历史的激进反思的必要性,并且,他关于禅宗传统的观点早已被近期的禅宗学者所讨论。在此不可能一一列出这些学者的名字,不过,毫无疑问,鉴于科尔处理的是历史上的真实与虚构,以及它们与禅宗思想的关系,会有人认为他的态度与1953年发生在胡适和铃木大拙之间的奠基性辩论有关。这场辩论涉及两种对立观点:“禅宗的‘真理’ 与形而上地位”(铃木);以及“禅宗应该被作为历史学课题进行研究”(胡适)② 胡适,“Ch'an (Zen) Buddhism in China”;铃木大拙,“Zen:A Reply to Hu Shih,”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3.1 (1953):25-46。 。
对偶句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是极得作家青睐的,它句式整齐,读起来朗朗上口。据笔者统计,《卜算子》中不仅对偶句数众多,且对偶形式丰富多样。
科尔毫不犹豫地为他的书定下了论争的基调。一翻开《父其父》,读者就会停在题献页上,其上写道:“献给弗里德里希·尼采。”紧接着就是《人性的,太人性的》(Human,All Too Human)中的两句格言。虽然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了尼采对佛教的赞扬兼批评,但我们却很少见到题献给他的学术著作① 本杰明·艾尔曼(Benjamin A.Elman),“Nietzsche and Buddhism,”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44.4 (1983):671-86。 。在本书中,科尔致以尼采的敬意远比他在其较早作品《以文为父》(Text as Father)中对英国音乐家埃尔维斯科斯特洛(Elvis Costello) 的题献更有分量② Alan Cole,Text as Father:Paternal Seductions in Early Mahāyāna Buddhist Literature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5)。 。一些读者可能直接翻过这几页而毫不深究,不过,我们仍想停下来问问:这一题献到底想向读者传达什么信号? 关于题献,杰拉德·热奈特(Gérard Genette) 解释为,允许“作者建立一个知识谱系而无需向其以此种方式私淑的先辈咨询……题献永远是关于流露、炫耀、彰显的:它表达一种或学术性或私人性、或实质性或象征性的关系,并且这种表达总为其学术工作服务③ Gérard Genette,Paratexts:Thresholds of Interpreta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132。 。”就热奈特的观点来说,题献后引用的格言则给作者“对(另一) 著名传承谱系的赞颂,它本身是一种文化信号(意在作为一种标志) 和通达先贤的密码④ 同上,第169页。 。”
如果热奈特有些道理的话,那科尔想通过题献给尼采传达什么信息呢? 作为引言来源的《人性的,太人性的》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在对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 的抨击中⑤ Friedrich Nietzsche,Human,All Too Human:A Book For Free Spirits,trans.R.J.Hollingdale,with an introduction by Richard Schacht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p.ix。 ,尼采将本书题献给了伏尔泰。科尔是否也试图表达一种攻击性的批判姿态? 换句话说,《父其父》一书是否试图弑杀禅宗研究之父呢? 尽管科尔从未清楚地告诉读者们尼采怎样跟全书论点搭上边,但他似乎在暗示,尼采能给禅宗学者和一般宗教提供某种重要的东西。通过告诉我们为何“宗教‘太过人性的’ 起源也能成为一种相对于象征性秩序的自由灵活性的基础”(Cole,p.314),“而这种灵活性,则是在意识到那些秩序是如何被创造和利用后产生的”(Cole,p.314)。科尔力劝那些仍在想着通过阅读禅宗文本获取一切有价值之物——但最后只能以失望收场——的不明真相的普通读者和学者们,去“更冷静地思考渐修创造的真理、觉悟、圆满”(Cole,p.314)。从拿起书的那一刻起,读者就会意识到,科尔想把《父其父》变成一部具有争议的作品。
科尔的激进还体现在他抛出的一个赌约中:
在我眼里,骨骼远远胜过娇嫩的花朵,为了使骨骼长期保存,必须先彻底剔除腐肉,我的隐秘晒台上有时整整齐齐地摆满了大小不一的白骨,如同纯洁的花朵盛开得愈发娇艳可人。
禅宗传统最初关于何物? 通过它,我们又能知道哪些中古及现代人类连结真理、权威、觉悟的方法? 对于这两个问题,几乎没有读者能在不提出一系列质疑的情况下放下本书。并且,正如本书题目所显示的令人难受的自反性,要搞清楚“禅宗诞生”所涉及的机制,需要搞清楚“真实性祖师”概念中的几种妙想和对现实的逃避。(Cole,p.xii)
接下来我会解释这段话,它包含了两重信息,并涉及到研究那些材料的现当代系谱学家和学者。
科尔意图证明:在可追溯至唐代的禅宗最早的谱系记录中,“禅宗的开悟和据此而来的传承如何建立在一个巨大的零上——这是一个空无的深渊,其上是一座承诺保存禅宗传统内核的纸牌屋”(Cole,p.307)。在揭露早期禅宗谱系的虚构和谎言后,科尔想通过重构精读所提供的证据,新开一种历史叙述。他相信,这些精读的文本对600-750年这段时期内的禅宗风格话语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关键作用。(Cole,p.xv)
科尔从宗教史学家的角度来处理这些禅宗谱系文本,这需要他“试图弄清楚某种确定形式的宗教信仰如何形成及其原因,而非假设仅仅是宗教体验造就了宗教”(Cole,p.xi)。他自称不同于其他学者——他认为学者们仍在继续“将早期禅宗文本……主要视为中国宗教体验之新形式的产物”,科尔称,通过阅读那些早期谱系文本,他可以明白早期禅宗文本中的虚构部分如何塑造我们关于禅宗高僧的印象。因此,他的目的是揭露学者们使用的错误方法,他认为,学者们被那些文本诱导后自认为能“发现某些确凿而令人鼓舞的东西”(Cole,pp.xi,314)。
对比来看,发达国家积极倡导新一代贸易协议规则并严格执行和谈判是有理论依据的,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大的收益,且如果仅从实际执行效力的影响系数来看,新一代WTO-X法定承诺率每增加1%,发达国家人均年GDP增长1.3万美元,而发展中国家由于实际执行的难度和发展条件限制对经济增长没有显著的影响。
在《父其父》的开头,科尔列出了禅宗学术的奠基者们——扬波斯基、柳田圣山、弗雷、麦克雷、福克以及其他一些人。他坚称自己与这些学者具有同样的学术传承,但同时,他又意欲强调自己与他们的根本性分歧。在为他的工作如此定性后,他要求我们想象一种乡村集市中的结婚照比赛:通过分析以往胜者的成功之道,参赛的摄影师们对自己的作品作出相应的调整,以符合评委们口味,因而他们不再那么关注婚礼的真实情景。由此,即使这些摄影师尽力让自己的照片看起来真实并掩盖矫饰的成分,他们的作品也显示出“同化的主题定位”(Cole ,pp.xii-xiii)。通过这个比喻,科尔批评道,那些学者看似是作为毫不知情的旁观者来阅读谱系文本,但可能已经看过以往的“结婚照”,因而误以为自己能捕捉到某些真实的历史信息。他认为,现当代的学者们——正如前现代的禅宗谱系学家——有着他们自己的“乡村集市比赛,且被诱导着修改了他们的‘照片’ 以使自己胜出”(Cole,p.13)。科尔这个“结婚照”与“禅宗研究史”之间的比喻显示,他将自己在本书中的任务比作一个“大胆的摄影师”,力图走出陈规旧俗以开创一条新路。
科尔毫不掩饰地将自己的工作摆在以往禅宗学术的对立面,不过他所作的批判将对读者产生何种影响,则主要取决于读者们是否同意他对禅宗研究史及当前状况的评判。科尔认为某些学者持有如下观点:“禅宗是绝对属于佛教的,但同时也是不受传统束缚的,它沐浴在一种作为宗教而超越宗教的阳光中,拥有着超越对错的独特真理,以及一种恰好不可言传的思想……将宗教和政治看作分开的活动,并想象真理(以及承载它的文献) 就是来自于真理本身而非其他不那么令人鼓舞的东西”(Cole,p.1)。那么,科尔的这种看法真的准确吗? 现代的禅宗学者们真的持有这种观点吗?
如果当代的学者们真的困扰于禅宗和庸俗的社会、经济、政治领域之间的联系,那我们该如何解释越来越多的学者正在分析禅宗僧侣、政治人物以及文人精英之间的联系? 正如近期几本著作所明确显示的那样,学者们已经开始严谨地考虑禅宗史中的社会政治因素。比如,莫舒特的《禅何以为禅》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将对教义和宗教问题的关注与对“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的明确讨论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政治、社会和经济力量造就了我们现在所知的禅宗”(Schlütter,p.1;p.175)① 参Welter,Monks,Rulers,and Literati and Jorgensen,“The ‘Imperial’ Lineage of Ch'an Buddhism”。 。科尔认为,学者们没有注意到社会和政治方面的问题,因为他们只是单纯地阅读材料;并且,即使在他们进行批判性阅读的时候,也怀有一种潜在的渴望,想从那些不可靠的描述中获取超验的真理。然而,就过去约四十年的禅宗学术史潮流来看,这些严厉的批评很难得到支持。实际上,《父其父》一书之前有许多杰出的学者,但科尔从未参考或讨论他们的作品。甚至会有人反驳道,科尔持有的许多自以为激进的观点已经被纳入到禅宗学术的主流中了。
鉴于科尔著作的副标题是“唐代佛教中虚构的禅宗”(The Zen of Fabrication in Tang Buddhism),我们会惊讶于它从未提到永岛隆行的 《宗教中的真实与虚构》(Truths and Fabrications in Religion),这是一部更早的批判禅宗史的书,它与科尔的著作一样,怀有一个激进的目的,试图揭露禅宗史和文本中的虚构本质② 永岛隆行,Truths and Fabrications in Religion (London:Arthur Probsthain,1978)。 。可以肯定的是,永岛隆行的这本书有很严重的历史学及方法论问题③ 同上,第105页。例如在比较王维为慧能作的碑记时(Cole,pp.215-21),科尔声称禅宗文本是虚构的,且剽窃了已有的捏造文本,而永岛隆行的观点则是,该碑记“使用了以往著作及经文中的历史事实及虚构成分”。 ,在该书中,永岛隆行通过展示较后期文本如何编造六祖慧能(638-713) 的传说,试图证明慧能是虚构的人物。虽然这个例子比较极端且采用了一种自觉的批判观点,但科尔竟告诉我们在禅宗研究领域中从来没有这种观点。在永岛隆行著作的序言中,麦克·派伊(Michael Pye) 抓住了其批判性的本质:“对一些人来说,禅宗是一种永恒的关乎个人修行和不可言说之见解的东西。同时,禅宗大德之间的传承形成了一种传统范式,这种范式在禅宗信徒心目中具有权威地位”,派伊继续补充道,“对于那些把关于早期大德如慧能和神会的虔诚传说当真的人来说,这将是一种挑战。他详细地展示了这些传说是如何由忠实的信徒在各种原型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在早期的禅宗故事中有很多虚构的成分”① 永岛隆行,Truths and Fabrications in Religion (London:Arthur Probsthain,1978),p.viii (斜体字)。 。
而《父其父》的结构和内容显示,该书主要面向专业读者,其目的在于,对正在进行的禅宗历史及其学术传统之批判性分析作出贡献——如果不是公然挑衅的话。正是这一点引来了批评的声音。
科尔可能觉得胡适与铃木之间的论争已经过时而不值得讨论,但我们仍很难理解科尔为何连约翰·马里奥多(John Maraldo) 那篇影响深远的论文都不提及,该文题为《禅宗是否有历史意识》(Is Ther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Within Ch'an?)。其中,马里奥多预示了许多《父其父》中出现的核心观点,这些观点关于禅宗编史及其解释:禅宗文本中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内核、将这些文献视为文学作品而非信史的转变,以及那些禅宗信徒的新观点的影响。马里奥多的这篇文章以总结1985年的禅宗研究成果开始,“由于一些新发现的推动,一种关于增强禅宗历史意识的观点正在觉醒,由此,在本世纪里,禅宗史正在被重新书写”③ John C.Maraldo,“Is Ther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Within Ch'an?”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12.2/3 (1985):141。 ,他紧接着又指出这一点对那些想要探寻禅宗传统之历史真相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什么,“对那些关注现代禅宗学术成果的人来说,一个新的挑战出现了。尤其是在对早期传法历史的怀疑目光中,禅宗信徒们需要重估历史传承对他们修行的意义,并重新审视那似乎包含了虚构与敌意的历史④ 同上,141-42页。 。”
马里奥多的文章在揭示禅宗谱系文本的准确关切方面起了很大作用。正如下文所表明的那样,禅史学家们很早就意识到,有必要在阅读早期禅宗文本时采取批判性态度:
北京市餐饮业品质提升工作的原则是政府推动、市场引导、企业自律、社会监督,目的是全面激发餐饮企业主动提升品质、持续规范管理、不断优化服务的内在动力,形成市民充分信任阳光餐饮、市场积极选择阳光餐饮的氛围,逐步由以政府推动为主转变为市场自我发展、行业自我约束,打造餐饮业品质不断优化、健康发展的局面。
因此,我们抛开精神性内容和遵守现代经验主义史学的理想不谈,敦煌文本中引用的“历史”及宋代《传灯录》似乎是为了某种利益服务的,它关乎高僧、宗派、教义的政治合法性而非事实真相。这种合法性通常来自于以下几点:表现一种来自于佛陀的直接传承、声称继承自达摩祖师的袈裟、从经文中引用的支持性段落(通常是伪造的)。当分歧出现的时候,作者可能将不同观点贬为异端(如神会对北禅宗所做的那样);或是在他的师父和某位有政治地位的高僧之间建立一种传承关系(如在《历代法宝记》中无住同金和尚联系在一起)。这些文本汇集了它们的历史证据,似乎给了其宗派高僧一种底气,以表示“我是真正的宗师,我的教言与他人不同,而我是正确的那个”……但是当这些文本被当成信史阅读时……现代批评家们会认识到,事实被频繁地歪曲,它既来自不正当的动机,也来自信息的匮乏或是某种虔诚的宗教意图① John C.Maraldo,“Is There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Within Ch'an?”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 12.2/3 (1985):154-55页。 。
在这一段内容中,对更早的“纯粹”禅宗的追怀和对超验真理的渴求在哪里呢?
如果谁还需要更多的材料来证明学者们已经发展出了多种多样的对禅宗传统的批评态度,那他只需要去阅读麦克雷的《透视禅宗》(Seeing Through Zen)中的相关部分,或者考虑莫舒特的《禅何以为禅》③ John R.McRae,Seeing Through Zen:Encounter,Transformation,and Genealogy in Chinese Chan Buddhism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 。莫舒特在其书中简评道:“所有宋代之前的谱系都被认为是虚构的,它是一种服务于使宋代禅宗合法化,服务于支持宋代禅宗所谓拥有特殊传承之声明的宗教历史。即使是在宋代,禅宗谱系也同样处在从属地位,它服务于使某位具体高僧及其传承系统合法化的一连串改动和重释,或被用于支持宗教论争”(Schlütter,p.15)。在科尔那里不存于禅宗学术领域的批评态度,恰恰是莫舒特学术工作的精妙开端。
由图 1可以看出,利用基于经验模态分解的信号去噪,可有效消除信号噪声,提高数据可用性,为下一步基于时间序列分层聚类的故障识别提供有利条件。
如果科尔认为柳田圣山——以及其他早期禅宗学者——真的怀有太多对“禅宗精髓”的眷恋,那么,人们会问,难道他没有向读者介绍关口真大那激进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想吗① 参关口真大《达摩の研究》(岩波书店,1967),及《禅宗思想史》(山喜房,1964)。 ? 关口的观点是,所有早期禅宗历史都是虚构的;这种观点太过于激进,以至于柳田圣山严厉地批评它基于不可靠的方法论② 柳田关于该书的评论可参其著作《破るもの》,第226-39页。参John R.McRae,The Northern School and the Formation of Early Ch'an Buddhism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1986),p.276 n.5。 。另一位效法关口真大的学者甚至断言:“只有虚构之物和虔诚的(以及不那么虔诚的) 谎言留存。”③ Bernard Faure,Chan Insights and Oversights:An Epistemological Critique of the Chan Tradition(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107。 有人可能会为科尔辩护,称他之所以遗漏关口真大的作品,是因为他主要考虑西方的禅宗学术流变。但是,关口真大的作品实在是太著名了,而且它还与科尔的评论,即所谓禅宗文本是一个“巨大的零上——一个空无的深渊”有着深切关联,为科尔辩护的人应该希望他至少告诉学者们他与关口真大的联系是什么。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英语世界的禅宗学术已经发展出了大量严谨的方法论。1986年,弗雷发表了一篇开创性的论文《作为文本和宗教范式的达摩》(Bodhidharma as Textual and Religious Paradigm),其中采用了系统化方法处理达摩传说。弗雷明白过度的历史决定论所带来的问题,这种方法试图挖掘出达摩的连贯传记。他指出“形成这部详尽传记的过程,与它所依赖的其他大德的传记编纂过程有着重要的相似之处。”④ Bernard Faure,“Bodhidharma as Textual and Religious Paradigm,”History of Religions 25.3(1986):189。 基于此,弗雷把达摩的生平故事看作文学作品,他甚至未在这篇文章中提及禅宗教义。而科尔指责弗雷是在想象“这些文本可以被解读为真善的教义”(Cole,p.9),显然,这种指责是不合理的。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早期,禅宗学者们也已经可以参考福克的《中国中古时期的禅宗:关于宗派、世系或其他》(The Ch'an Tsung in Medieval China:School,Lineage or What?)⑤ T.Griffith Foulk,“The Ch'an Tsung in Medieval China:School,Lineage,or What?”The Pacific World 8 (1992):18-31。 。此书概述了关于“达摩世系、其与法如(638-689) 墓志铭之关系及其谱系”的研究情况。尽管法如的墓志铭在科尔的分析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从未引用福克的文章,福克在该文中写道:“似乎法如的信徒们只是通过先选择印度僧人菩提达摩,然后从《续高僧传》中选取其弟子慧可,简单地创造了这个世系……并将他们用作连接印度的方便法门⑥ 同上,第21页。 。”福克也承认“我们只知道法如的信徒们创造了这样一个可追溯至印度的密不外传的言传世系⑦ 同上,第21页。 ,除此之外,我们对法如及其后继者几乎一无所知。”
由文[1]表7.1可知,满足Ax.3则对于数学模型(3)有X=P,k∈{1,2};满足Ax.5,对于模型(3)有k=2;满足Ax.6,对于模型(3)有X∈{N,P,S,T};于是仅须考虑模型
福克的这篇文章面世一年后,弗雷发表了他的《禅宗洞见与漏见》(Chan Insights and Oversights),在该文中,他进一步强调了研究早期禅宗历史叙述结构的必要性,并认为“经典”禅宗可以被认为是取代了“早期”禅宗,或者也可以说是继承了它。将禅宗“传统”与“内核”看作理所当然之物正是为了忘记它们,正如保罗·维尼(Paul Veyne) 所指出的那样,“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从不与不朽之人如国王和愚蠢之人下棋:因为正是他们构成了棋盘① Faure,Insights and Oversights,p.120。 。”那么,福克与弗雷对早期禅宗谱系的定位和科尔所谓的“弟子们创造了他们的祖师”的理论有何区别呢?
Study on the extraction and antioxidant activity of polyphenols from sweetpotato leaves
为了强调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及进入千禧年之后的禅宗批评方式变得多么规范,我们可以考察威尔特(Welter) 的文章《僧侣、统治者和文人》(Monks,Rulers,and Literati),该文比《父其父》早三年发表,在文中,威尔特指出:“关于传统叙述的研究不能再只停留在字面价值上,而必须连同其背后支持者的动机一起阅读。禅宗超越性的概念——即“纯粹”禅宗不受时间和地点限制——已经受到挑战而成为另一种为某些组织及支持者的利益服务的思想形态② Welter,Monks,Rulers,and Literati,p.4。 。”这些评论表现了2006年前后许多禅宗学者所怀有的忧虑。
科尔的确采用了日本学者柳田圣山的成果,但他试图将后者与自己的方法区别开来。他承认,柳田圣山的“编辑、出版以及翻译”工作对包括扬波斯基在内的一些早期学者有重要影响,这些学者后来又影响了他自己。但同时,科尔又用了一段单独的说明来贬低柳田圣山严谨的具有历史性和诠释性的学术工作,并因此让读者觉得柳田圣山的学术充满了一种“怀旧”(Cole,p.8) 的味道,而他的这段说明则是来自一场在旧金山禅宗中心举办的座谈会。相较而言,弗雷则对柳田圣山所采用的方法作了更加公允的评价:“对柳田圣山来说,尽管传统的史学难以提供一种确凿的叙述,但也不能被当作一种空洞的捏造而被完全摒弃。弗雷同时批评了《灯录》中的虚构性叙述以及过度历史主义的去虚构化行为,并试图强调那些“发明”中的宗教创造力② Faure,“Chan and Zen Studies:The State of the Field (s),”p.3。 。”因此,柳田圣山谨慎地走在介于胡适与铃木之间的钢丝上③ 迪蒙斯·巴瑞特(Timothy H.Barrett),“Arthur Waley,D.T.Suzuki and Hu Shih:New Light on the ‘Zen History’ Controversy,”Buddhist Studies Review 6.2 (1989):116-21。 。柳田圣山对于禅宗史始终保持了一种审慎(并且幽默) 的态度,这一点反映在卡尔·比勒菲尔德(Carl Bielefeldt) 的记录中:当柳田圣山“刚刚发表一篇关于道元的文章时(在这篇文章中,他声称这位离经叛道的和尚离开寺院而去镰仓与一位将军的妻子会面),我问他是怎么发现这一点的,他说,这只是个谎话。在短暂的停顿后,他补充道,‘总之,禅宗史就是谎言史’。④ Carl Bielefeldt,Remembering Yanagida Sensei,该文刊于《柳田圣山先生追悼文集》中,京都:花园大学,2008,第9页。 ”柳田圣山的所有作品都具有一种复杂性,它们不应被简化为对禅宗核心的随意表述或一种随口的评论。
在《禅何以为禅》的核心章节中,莫舒特用了大量篇幅阐述禅宗与政治精英的关系,而这正是科尔所称的一个被学者们回避的讨厌话题。莫舒特关于禅宗历史的详尽叙述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佛教与宋朝政府关系的必要背景,这种关系给予佛教寺院经费、用地许可、高僧的显赫地位以及翻译印刷佛教经典的补贴。
然而,宋朝政府的支持是以牺牲佛教利益为代价的,官方要求佛教为其政治利益举行各种华丽的仪式。莫舒特指出,尽管宋朝政府“明白僧人和佛寺的出现有利于国家的稳定和繁荣,但它也同时担忧佛教潜在的威胁,因而政府认为极有必要严控僧团,以确保其中只有‘纯洁’ 的僧尼”(Schlütter,p.32)。因此,政府打击那些拒绝服从的僧团,监控寺院的各种活动,并要求只有经过登记的组织可以进行活动,同时,政府也通过赐匾额来保护和支持一些大型寺院。那些受赐匾额的寺院可以得到少量的权力和保护,然而作为回报,它们需要放弃自主权。莫舒特关于佛寺受监管一事的分析,强有力地表现了政治对禅宗历史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尤其体现在对佛寺的两种分类:“ ‘传承寺院’ (甲乙制寺院,或称徒弟制、度弟制寺院) 和‘公共寺院’ (十方制寺院)”(Schlütter,p.36)。
莫舒特一方面借鉴高雄义坚、黄敏枝及竺沙雅章的成果,另一方面结合自己对《庆元条法事类》的阅读理解,为我们提供了英语世界里关于两类寺院的最清晰广泛的讨论(Schlütter,pp.36-49)。“传承制”寺院通常是中小规模,其影响力主要辐射当地,这种寺院是僧尼的合法财产。其居住者组成“僧侣家庭”,且住持和管理机构在一种被莫舒特称为“佛教家庭谱系”的传承中延续下去(Schlütter,pp.55-58)。莫舒特指出,宋代以前的大部分寺院都是“传承制”的,但直到宋代才取得合法地位及特定权力——甚至可能包括对其土地所有权的保护。同样的,这些权利也伴随着对政府的义务以及接受政府监管的要求;政府甚至不惜颁布法律以管理寺院的继承(Schlütter,pp.36-38)。
对两种寺院区别的讨论是莫舒特工作中至关重要的内容,因为正是朝廷对“公共”寺院的扶持使禅宗成为宋代精英佛教的领导性宗派(Schlütter,pp.38-39)。“公共寺院”与所谓“僧侣家庭”没有关联,任何合格的僧侣都能住在里面,且住持从最佳候选人里面挑选,不过通常来自于寺外(一条规则是所有现任住持的弟子不得当选为新住持,以防该寺变为“传承制”寺院)。莫舒特将这种精英佛教组织称为“流动家庭”(Schlütter,p.56)。
有宋一代,“公共寺院”的数量有所增加,同时一些“传承寺院”被转化为前者。关于后者为何会愿意放弃自主权,莫舒特认为,这些转化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政府和当地精英人物的影响,他们意识到“传承寺院”会影响“公共寺院”;他解释道:“ ‘公共寺院’ 更像一种政府机构,其住持也被视作政府官员”(Schlütter,p.39)。最终,“公共寺院”与政府的紧密联系很好地维护了禅宗的长期利益(Schlütter,p.50)。
莫舒特指出,当地精英文人在这种转化中起了很大作用,它们将寺院的住持之位“拍卖”给出价更高的“竞拍者”,从而在住持的继承上有了一定话语权,同时也为寺院提供支持和赞助(Schlütter,第三章)。这几点十分正确。然而,由于天台宗和华严宗的挑战,禅宗在十一世纪拥有的特权地位在十二世纪走向衰落。在整个北宋时期和南宋初期,由于文人对禅宗的支持不断减少,且宋徽宗转向支持道教,禅宗在宗教领域的地位受到影响。由以上内容我们可以看到,莫舒特自始至终都注意到了社会政治力量对塑造禅宗历史的影响。
二是秉承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树立“大土地观”,打造土地质量地质调查的升级版。要充分发挥地球化学测量多目标、高精度和信息化程度高的技术优势,不断拓展调查的深度和广度,不断丰富土地质量的内涵,不断创新成果的表达方式。在问题和需求的引领下,着力做好知识储备、技术储备、人才储备,快速提升服务支撑能力,以满足自然资源管理对科技工作的需求。
莫舒特非但没有为这种禅宗与世俗精英之间的关系感到惋惜,他还进一步分析了禅宗寺院内部的发展情况。他着重研究了两种“家庭”组织形式的不同之处:对于“僧侣家庭”,其继承发生在“直接的核心家庭成员”中,因而它不需要通过追溯其他谱系或族谱来证明其权力合法性(Schlütter,p.57);而对于“流动家庭”,传法谱系则显得格外重要。虽然传法谱系这个话题已经受到很多学者的重视了,但莫舒特仍提出了一些新的证据,它们显示传法谱系源于僧侣谱系。其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关于天台宗早期传法谱系的讨论,以及他的翻译与科尔翻译的不同之处。科尔称,这种传法只不过是灌顶(561-632) 试图创造一位中国佛陀——智顗(538-597) 而所作的努力。但相反,莫舒特将那些材料解读为灌顶创造的传法谱系,因为当智顗的寺院被他的三位弟子接管时,他已经去世了(Schlütter,p.58)。“流动家庭”以及他们自称拥有的自佛陀以来未曾间断的谱系,形成了一种禅宗传统里塑造权威的最独特的途径。
学者们已经指出“拈花一笑”的虚构性,且它反映出禅宗僧人试图创造一种独立身份的努力;同样,科尔也将法如的碑记定性为一种试图掩饰自身杜撰成分的“高度虚构”的甚至“不正当”的作品(Cole,p.84)。科尔指摘学者们在阅读该碑记时带有一种所谓的“天真期望”,然而,基于禅宗研究目前的成熟状态,科尔的这种说法令人感到诧异。科尔坚称“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谈及这一点的时候,总是将禅宗视为中日的‘地标’,因此,它在具体层面上绝不会是杜撰的,”而后,他补充道,“在假设禅宗的这种‘已经永远存在’ 的本质时,我们会很自然地忽视掉一种胆大妄为的情况,即总是有人自称拥有禅宗的正统法脉”(Cole,p.74)。在此,他仍旧没有具体指出到底是谁会带有这种“天真的过时思维”(Cole,p.85)。
鉴于莫舒特对禅宗传统所呈现的批判态度,人们可能会问,谁是科尔的批判对象呢? 又是哪些学者困扰于所谓“敦煌引起的失望浪潮”(Cole,p.314)? 可惜,科尔并没有在他那大范围的攻讦中指出谁是其批判对象。实际上,对禅宗史的批判早已存在于学术界,因而,科尔对那些学者们已经不再持有的态度的攻击就显得毫无意义。
笔者猜测,科尔的许多历史观点在一些学者看来似乎是真的。这并非因为他获取了某些新材料进而提出了新论点,而是因为他所讨论的很多东西都已经得到了很好的解释,并且这些解释也符合目前禅宗领域的公认立场。然而,他对这些材料的组织仍值得继续批评。《父其父》对禅宗学者来说可能的确是个麻烦——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不过不一定是由于他预期的原因。
科尔没有以唐代的某些具体禅宗著作开始他的分析,而是以他提到的它们在隋朝时的“前辈”开始。这些“前辈”包括试图将天台宗四祖智顗与三阶教领袖信行(540-594) 塑造为中国准佛陀的谱系文本。这些文本与后来试图以同样方式将禅宗高僧塑造为佛陀的禅宗文本相似。科尔的观点是,通过这两位六世纪的高僧,我们可以“领略到多种策略来将整个传统以令人信服的方式集于某一人——也就是早期的试图创造中国佛陀的努力”(Cole,p.72)。科尔承认,这部分结论建立在琳达·潘克文(Linda Penkower)、筱原亨一、陈金华,以及杰米·哈伯德(Jamie Hubbard) 所作工作的基础上,这些学者都曾为禅宗研究做出过重要贡献。但是,一如科尔对一些更早期禅宗学者所保持的沉默,他也缺乏对天台宗历史及其与禅宗之可能联系的讨论① 在里昂·赫维兹(Leon Hurvitz) 关于智顗的著作及斯坦利·韦恩斯坦(Stanley Weinstein)关于智顗与隋朝政府关系的基础性著作中,有大量丰富的材料,但科尔并未提到它们。参:Leon Hurvitz,Chi-i (539-597):An Introduction to the Life and Ideas of a Chinese Buddhist Monk (Brussels:Melanges chinois et bouddhiques,1962);或参Stanley Weinstein,“Imperial Patronage in the Formation of T’ang Buddhism,”in Perspectives on the T’ ang,ed.Arthur F.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p.265-306。 。科尔称,智顗通常不被认为是早期禅宗的先驱(Cole,p.13),但该观点与胡适的意见相悖:“为了使天台宗成为中国佛教的正统宗派,天台宗高僧们声称自己与大乘佛教论师龙树有直接的传承关系。为证明这种精神谱系,智顗利用了一部伪作——《付法藏传》……但这也为谱系之争开了一个坏头,因为这些争论,在八世纪时,僧人们“创造”了大量的祖师以使禅宗成为正统② 胡适,“The Development of Zen Buddhism in China,”p.492。 。”此外,一些日本学者也已经对禅宗的天台祖师进行了广泛的研究③ 关于天台及禅宗传统的关系,参见关口真大,《禅宗と天台宗との交涉》,收于《大正大学研究纪要》,44 (1959):39-75;关口真大,《天台小止观の研究》,山喜房,1961;山内舜雄,《禅と天台止观:坐禅仪と<天台小止观>との比较研究》,大藏出版株式会社,1986。此二者的关系也在莫舒特著作的第18页有被提到。 。
人们或许会进一步问,在未参考五世纪教义发展的情况下,科尔关于谱系文本中使智顗和信行成为中国佛陀的观点是否仍能成立。比如,五世纪时,《涅槃经》的诸版翻译才在中国出现,由于这部经提出佛性存在于一切有情众生中(包括动物和一阐提),它为中国佛陀的存在创造了条件。由此,恐怕我们不会惊讶于灌顶——科尔在关于智顗及其成为中国佛陀一事的讨论中着重提到了他——为《涅槃经》作了注,且神会(d.758) 在之后用了该经中的一段以作为他成佛的依据④ 灌顶的《大般涅槃经玄义》在高楠顺次郎所编《大正新修大藏经》(et al.100 vols)中(1924-1932)。后文都将用T 代指《大正新修大藏经》,除非仅提供该经中的文本编号,所有引文格式都将如下:T卷号.页码.行号及边码(a、b、c)。比如:T 51.1070a.10-15。科尔在第253页中讨论了神会引用的《涅槃经》。 。
当科尔提到他所分析的主要文本时,他表示他将对这些文本进行“精读”,但他却并未明确指出他所使用的版本和最初来源(且也未在参考文献中列出)。这样的遗漏会使那些想参考或检查他所使用文献的学者感到失望。到目前为止,笔者能够确定科尔参考的“早期禅宗谱系著作”包括:
1、七世纪时法如的碑记《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科尔主要用了柳田圣山的校订本① 参柳田的《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pp.487-96),该书被科尔间接引用过,其本身根据《金石继编》的第六卷。 。
3、净觉(683-750?) 著《楞伽师资记》。该文本的翻译主要在克利瑞(J.C.Cleary) 的《禅宗黎明》(Zen Dawn)中,科尔常将该翻译与《大正藏》中收录的该文本(T 85.1283a-90c) 进行对照。此外,他也提到了柳田的版本,并将其与《大正藏》本放在一起讨论③ J.C.Cleary,trans.,Zen Dawn:Early Texts from Tun Huang (Boston:Shambhala,1991);柳田圣山,《初期の禅史:楞伽师资记:传法宝记》,筑摩书房,1976;Bernard Faure,Le Bouddhisme Ch’an en mal d’ histoire:Genèse d’ une tradition religieuse dans le Chine des T’ ang (Paris:Publications de l’ Ecole francaise d’ Extrême-Orient,1989)。 。
2、杜胐(生卒年不详) 著《传法宝记》。科尔似乎仍使用了柳田的版本,但他所引用的翻译部分主要来自于麦克雷② 柳田的《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主要给予敦煌写本(伯希和编号3559),以及McRae,The Northern School,pp.255-69。 。
4、四篇关于神会的残本。科尔没有在参考文献中将其列出,仅是让读者参考扬波斯基列出的书单及现存的版本④ Philip B.Yampolsky,The Platform Sū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pp.24-25。 ,以及关于这些文本的现当代出版物。科尔的讨论仅限于扬波斯基清单中的前三项有关神会的文本,且他主要通过胡适的抄本和谢和耐的法语翻译来间接引用⑤ 胡适,《神会和尚遗集》。科尔引用了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的版本。 。
科尔关于法如碑记的分析对其广泛的论证来说显得十分重要,因为他在其著作的后半部分有对其他禅宗文本的阐释及对它们叙述技巧的讨论,而该分析则为这些讨论奠定了基础。所有现代禅宗史学者都已承认法如碑记的重要性,并常引用之,以作为“表现自身世系传承”的第一个实例。该世系,即从达摩到慧可(485-555)、僧璨(生卒年不详)、道信(580-651)、弘忍(501-674),直到法如的传承谱系。
笔者同意科尔关于法如传记中所用修辞的大部分分析,就该文本对禅宗传统的影响来说,笔者也相信大部分禅宗学者会认同他的观点。科尔指出了文本中的各种“隐喻”和“留白”,实际上,这些都是禅宗文本的常见特征。比如,学者们已经注意到,禅宗传统声称其解脱思想来自于佛祖对摩诃迦叶的传法,即“拈花一笑”的典故⑥ 这个著名的故事被发现于无门关(J.Mumonkan),T 48.293c。参:Albert Welter,“Mahākā yapa’ s Smile:Silent Transmission and the Kung-an (Kōan) Tradition,”in The Kōan:and Contexts in Zen Buddhism,ed.Steven Heine and Dale S.Wright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p.75-100。 。对于那场“特殊传法”中振聋发聩的“沉默”,已经有很多阐释了,而这种传承则通过二十八位印度高僧留传下来,并最终由达摩传至中国。在科尔的讨论中,我们得已再次窥见:通过声明自己的“特殊传法”是无声无形的,禅宗传统是多么不情愿透露自身的“秘密”。正如威廉·巴蒂福德(William Bodiford) 的解释:“一位新佛陀的诞生在精神层面上是一个巨大的秘密。它既不能用语言,也不能由科学和因果来解释① William M.Bodiford,“Dharma Transmiss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in Zen Ritual:Studies of Zen Buddhist Theory in Practice,ed.Steven Heine and Dale S.Wright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p.264。 ”。
莫舒特进一步解释道,禅宗领军人物在士人群体中取得的地位,是十一世纪曹洞宗传统成功复兴的主要原因;同时,这种复兴也包括了对其传承谱系和祖师传记的书写,以及一种独特参禅法门——默照禅的创造。随着曹洞传统于失传边缘的复兴——这可归功于一些高僧如芙蓉道楷(1043-1118) 和大洪报恩(1058-1111) ——其历史新阶段的基础已经形成。在这里,莫舒特对曹洞宗谱系历史之重建与固化的详细分析变得相当密集,并且,他对关键人物的背景介绍也十分有用。然而,莫舒特也揭示了曹洞宗传统在支撑其传法谱系时,有时的确使用了一些该谱系之外的材料,甚至直接建立不相干人物之间的联系。比如,我们知道,有一对师徒的关系是在两个未曾谋面的人之间虚构出来的,其中一人甚至在另一人出生之前就已圆寂——即投子义青(1032-1083) 以及大阳警玄(942-1027)。此外,义青通过法远(991-1067) 间接从警玄那里得到了传承,而法远甚至都不在警玄的传法谱系之内,他实际上是临济宗的法嗣。这样一来,这个间接传承就等于是警玄对义青的身后传法;其中,法远只是作为一位暂时的保管人,以确保传承内容真实无缺,直到一位合适的曹洞宗法嗣出现(Schlütter,pp.88-90)。
《父其父》中有如此多的史学论点,以至于笔者无法一一分析之,且这些论点的论述方式决定了很难对它们进行证明或反驳。尽管如此,其中一些章节的问题还是太大,因而不得不加以评述。法如碑记的主要内容之一是它所传达的政治信息,科尔坚称他已经通过“精读”把这一点揭示出来了,而学者们,则因为所谓的“天真期望”将它忽视了。
科尔断言,法如的传记是“政教对话”的一部分,其原因在于“碑记中包含了政权对法如师承之真实性的肯定”(Cole,p.81)。他继续指出法如及其师承是“政治盟友批准的传承”,且这一点已经得到了“朝廷的承认”,同时他们也受到“朝廷的限制”(Cole,pp.88-89)。科尔这种强烈政治导向的解读假定了法如及其师承有“朝廷认可的身份”,而这种假设仅仅是基于法如墓志铭中的一段:“每个人都说,‘自魏(代) 至唐(代),已经有五位皇帝的代表(帝代) 了,这经过了大约两百年——(在这些年中) 贤人不断涌现,来为所处时代的德行下定义。他们赠与我们这些后辈以无上伟大的宝藏(无上大宝)’”(Cole,p.87)。
科尔并未告诉我们这段引文来源的准确位置,他只是粗略地注释道,所有法如传记的翻译都基于柳田的《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这段文字的中文原文为:“佥曰:始自后魏,爰降于唐,帝代有五,年将二百,而命世之德,时时间出。咸以无上大宝,贻诸后昆。”② 柳田的《初期禅宗史书の研究》,在487-489页提供了完整的传记,且该段出现于488页。 科尔将“帝代”翻译为“皇帝的代表”③ 译者注:原文为imperial representatives。 ,但他并未提供任何参考资料或注释来支持此种翻译。这个复合词似乎从未出现在任何主流词典中(如《汉语大词典》和《大汉和辞典》),因此,需要一些文本来支持这种翻译① 汉语大词典编委会编《汉语大词典》(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6-90);诸桥辙次编《大汉和辞典》,大修馆书店,1955-1960。 。在这段引文的前后文及其他佛教文本中,“帝代有五”仅仅意指北魏至唐的五个“朝代”(其中“帝代”意为“朝代”)② 比如,可参《历代三宝记》(T 49.94b.6)中的用法:齐梁及周帝代录者;或参《集神州三宝感通录》(T 53.409c.21):未知古老所传周文是何帝代。 。由此,笔者将这段所讨论的文字译为:“从北魏到唐,已历经五个朝代(帝代有五),其历时约两百年。”简言之,这段文字本身不能用于支持科尔的观点,即其关于法如世系以及所涉之人物的观点。
此外,科尔关于净觉《楞伽师资记》的讨论也有问题,尤其在于他对该文本来源的选择以及他对克利瑞所作的有问题的翻译的过度信赖,该翻译与科尔引用的《大正藏》版本(p.181 n.14) 并不匹配③ J.C.Cleary,Zen Dawn.The Taishō passage is also incorrectly cited;it begins on 1284c.14 and ends on 1284c.18。 。至于克利瑞所著《禅宗黎明》中引文的问题,麦克雷已经讨论过了,他曾私下要求克利瑞补充所引文本的来源信息④ John R.McRae,“Thinking about Peace and War,”Eastern Buddhist 19.2 (1986):138-46。 。他意识到,克利瑞的翻译并不是根据《大正藏》,而是基于金九经辑录的《姜园丛书》中所收录的版本,这部书帮助我们理解了《大正藏》本与克利瑞版本的不同之处,而科尔却将二者引于一处。科尔对不可靠翻译的依赖和脱离前后文的引用,将会对他关于净觉“虚构性”语言的进一步讨论产生巨大影响。科尔认为,通过虚构,净觉试图“形成一种新的‘口述传统’ 来证明那些高僧的事迹并非文学杜撰”(Cole,p.180)。然而,他所谓的“虚构性”可能恰好来自于断章取义的引文和不可靠的翻译⑤ McRae 误作《姜园邺书》,笔者于此已纠正;且柳田在《初期の禅史》中误印为《姜园双书》,此处简体字“双”应为“叢/丛”。金九经录于《姜园丛书》中的《楞伽师资记》实际上有更早的版本,即待曙堂出版社于1931年在北京出版的《校勘唐写本楞伽师资记》。关于金九经版本《楞伽师资记》的历史可参柳田,《初期の禅史》,第1 章,第40页;以及Faure,Le Bouddhisme Ch'an en mal d’ histoire,p.38。 。
至于科尔为何会相信克利瑞的成果,我们不得而知⑥ 科尔也引用了Bernard Faure 在Le Bouddhisme Ch'an (pp.112-14)中的法语翻译,但这显然未能提醒他关于这段文字的解读。 。同样,我们也不清楚科尔为何不使用麦克雷对更完整文本的翻译,毕竟,在科尔此书中,他多次采用了麦克雷的翻译(通常施以少量修改)⑦ McRae,Northern School,p.92。兼参John R.McRae,“The Antecedents of Encounter Dialogue in Chinese Ch'an Buddhism,”in The Kōan,pp.56-57。 。麦克雷非常赞同柳田对关口真大关于《楞伽师资记》之观点(关口认为其中的片段与公案很像) 的批评,此外,麦克雷也认为,这些片段应该“同禅宗在八世纪末发展出的独特对话方式相比较,此类‘关于各种事物的问题’ 展示了这种宗教对话方式的最早记录”⑧ McRae,Northern School,p.93。 。麦克雷的这两种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由此看来,科尔所引片段似乎是关于“弘传佛法之无情众生”的系统表述,而不光是他所称的“怪诞虚假言语”的一个例子。正如罗伯特·沙尔夫指出的那样,在早期禅宗中,关于无情众生是否具有佛性本身存在巨大争论。因而,《楞伽师资记》赞成无情众生具有佛性也就不奇怪了① Robert H.Sharf,“How to Think with Chan Gong’ an,”in Thinking with Cases:Specialist Knowledge in Chinese Cultural History,ed.Charlotte Furth,Judith T.Zeitlin,and Ping-chen Hsiung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2007),pp.205-43,esp.pp.216ff;Robert H.Sharf,Coming to Terms with Chinese Buddhism:A Reading of the Treasure Store Treatise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2005),pp.247-48。 。
同时,科尔也坚称《楞伽师资记》的虚构文本以及对禅宗高僧的描述尤其不可信,其原因在于净觉“从未标出那些高僧语录的出处,而这些高僧皆圆寂已久”(Cole,p.181)。此处科尔对净觉的批评延续了其早先对杜胐的文本所谓“创造”的批判。他判定净觉“拒不承认对法如墓志铭的依赖是一种缺省之罪”(Cole,p.170,斜体部分)。在这两个例子以及《父其父》的其他引文中,科尔都指责禅宗谱系著作的作者在辑录时未标明所用材料的出处。他同时也批评当代学者,称他们无视这些文本中具有的与过去及过去历史的荒谬联系。科尔称,所有早期禅宗著作几乎都无视史实,而且也不为滥用材料和捏造高僧以填入谱系感到愧疚。此外,他认为那些文本既表明其作者不情愿讨论禅宗教理的具体情况,也不愿精确描述在禅宗传统的创造与再创造中,弟子到底从师父那里继承了些什么② 参Anthony Grafton,Forgers and Critics:Creativity and Duplicity in Western Scholarship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p.123。 。由于在汉语传统中,作者普遍基于现有文本著书立说而不注明出处,科尔因而将那些作者称为抄袭者和伪造者。然而,现代的抄袭判断标准和引用规范并不适用于早期历史著作。正如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 所言,抄袭“在当时被普遍视作一种再正常不过的行为。彼时的史学作者和宗教编年史家们并不为使用前人的著作感到羞耻③ Marc Bloch,The Historian's Craft (New York:Vintage Books,1953),p.95。兼参Anthony Grafton 的近期作品The Footnote:A Curious History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9。 。”
奶可以给宝宝提供优质蛋白质和充足的钙,宝宝一天的需要量在200~300毫升。三餐里喝不到奶,一般幼儿园会在上午加餐牛奶,下午加餐水果。这样孩子一天在幼儿园只能喝到全天所需要奶量的一半。
中国的谱系学家具有私自使用已有著作的习惯,但其原因与促使毕加索说出那句著名格言——优秀艺术家照搬,伟大艺术家偷窃——的原因并不一样。相反,在使用之前文本的同时,该著作本身就构建了一种新的合法性④ William Alford,To Steal a Book is an Elegant Offense: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see also pp.12,18。 。而对于抄袭,如果我们将其定义为“使用已有成果内容以作为自己所拥有之物”的话,那它已经被约翰·克什涅克(John Kieschnick) 在关于《高僧传》的讨论中解释过了,该传的编纂者们“直接地,逐字逐句地(或加以增删) 使用他们可获取的材料而不加以注明⑤ John Kieschnick,The Eminent Monk:Buddhist Ideals in Medieval Chinese Hagiography(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1997),p.10。 。”正如克什涅克指出的那样,这种挪用“在史书编纂时并不仅限于佛教传记领域,同时也存在于世俗领域① Kieschnick,Eminent Monk,p.152 n.36,罗伯特·康帕尼(Robert Ford Campany) 也指出了葛洪在《神仙传》中是如何使用已有传记而“不将自己的辑录归功于(它们)”的;To Live as Long as Heaven and Earth:A Translation and Study of Ge Hong’ s Traditions of Divine Transcendent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p.103;而且史蒂芬·博肯坎普(Stephen R.Bokenkamp) 也指出了在道教灵宝文献中类似的借用现象;“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in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A.Stein,ed.Michel Strickmann (Brussels:Institut bel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1983),pp.437-38。参丹尼斯·维切特(Denis Twitchett),“Problems of Chinese Biography,”in Confucian Personalities,ed.Arthur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24-42。 。”
关于禅宗文本的挪用问题,学者们已经广泛讨论过了。戴尔·瑞特在关于著名的《景德传灯录》(1004) 的研究中提到:“ (辑录者们) 通过实质性的编辑、改写、重构,已经组织起了一本崭新的著作,同时也建构了关于传统的新认知……在大量使用前人著作的同时,这些辑录者并未标明参考文献。他们从前人著作中抽取出大量片段以编织成一部新的著作,但并没有加上脚注或参考文献等其他表明所用材料来源的说明② Dale Wright,“Historical Understanding:The Ch'an Buddhist Transmission Narratives and Modern Historiography,”History and Theory 31.1 (1992):42。 。”如果科尔将他研究的材料置于历史背景中,他可能会发现这种挪用是古代的通行做法。
为了纠正大家关于“精英文人对佛教所持之态度”的误解,莫舒特证明了精英文人在宋代并非“坚定反佛教的新儒家”(Schlütter,p.27)。莫舒特在关于此点的讨论中——同时参考了马克·哈普林(Mark Halperin) 近期关于宋代文人对佛教所持态度的研究成果——用了大量篇幅来描述佛教在宋代文人生活中所占的位置① Mark Halperin,Out of the Cloister:Literati Perspectives on Buddhism in Sung China,960-1279(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6),尤其是第2 章。 。诚然,一些重要的文人,如朱熹(1130-1200) 的确极力反对佛教,但是,正如莫舒特所言,这并非“宋代文人的普遍情况”(Schlütter,p.28)。
在抛出这个观点后,科尔又开始批评过去的禅宗学者们,这次他的批评点在于,他们忽视了所谓的读者“在那些文本所需要的思想交流中起到”(Cole,p.25) 的重要作用。科尔给那些所谓的读者冠以各种名字,如“阅读公众”“普通读者”或是“其他人”,并将他们描述为被虚构文本说服的“虔信的读者”。他声称,“阅读公众”中的每个人都对谱系中高僧所掌握的东西充满憧憬,且“现代批评研究”未能注意到“高僧们作为受追捧的对象而被展示在读者面前”这一事实(Cole,p.29)。他进一步断言,这些谱系著作“不仅仅是被作为‘其他人’ 的消费品;而且也被禅僧或相关人士持有和传播,同时,他们明白,只有当‘其他人’ 信服时,他们号称的禅宗正统才有效。由此,很自然地就会想到,这些文本应当被解读……为是作者为了迎合‘其他人’ 关于真实的追求而编纂的作品”(Cole,p.3)。在科尔看来,一种对禅宗高僧所掌握之物的“相互模仿的渴望”非常普遍,且它塑造了禅宗理论的发展过程① 关于“相互模仿的渴望”,参瑞恩·吉拉德(Rene Girard),Violence and the Sacred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7),尤其关注第6 章。 。那么,他的这些观点能否得到社会历史事实的支持呢?
《父其父》中的这些见解引起笔者在数个层面上的怀疑。那些文本真的曾在精英僧侣及编纂者这个小圈子之外流传过吗? 我们真的知道它们的传播情况吗? 它们又是否被广泛阅读过? 当我们在讨论这些文本时,我们真的能举出某个具体的“其他人”或所谓的“普通读者”吗? 科尔所讨论的所谓禅宗文学作品真的曾作为禅宗内部产物而扩展到公共领域吗? 即使某些文本曾流出僧侣这个有限的圈子,那么,是否有证据可以证明俗人曾渴望获取大德们所掌握之物呢? 科尔三番五次强调串通好的公共“读者群”(或“普通受众”),但这仅是未被证实的猜测罢了。我们对早期禅宗文本的传播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对谱系文本就更知之不多了),因此,笔者尚未发现有证据可以表明那些文本曾被大范围传播或阅读过。莫舒特在《禅何以为禅》中指出,主要的“如今已知的早期禅宗文本在宋代以后就销声匿迹了,直到二十世纪才被重新发现”(Schlütter,p.16)。科尔提到《六祖坛经》可能曾在公众读者群中传播(Cole,p.296),但即使是这部远比谱系文本知名的经文也仅在后期才从有限的禅宗领域流传开来:根据卡尔·比勒菲尔德以及李维斯·兰卡斯特(Lewis Lancaster) 的观点,该经似乎在明朝才从“秘传文本变为普遍的师传宗教著作”② “T'an Ching (Platform Scripture),”Philosophy East and West 25.2 (1975):198。 。
莫舒特关于宋朝印刷禅宗文本的影响的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禅宗文本只在后期才被作为公共文本进行传播。正如他所证明的那样,只有印刷版的禅宗传法文本——比如著名的《景德传灯录》——才广泛流通并接触到公共读者群。但同时他也指出,这些文本的读者群也只是扩展到精英文人圈而已,并且,“宋朝的大部分人并不关心禅宗的谱系、修行、证悟及对佛教教义的解释等内容”(Schlütter,p.5)。由此,除非有进一步的相左研究,否则我们只能得出结论,那些虚构性的谱系文本并未得到广泛传播,也无巨大的读者群。科尔坚称每一位禅宗谱系作者的后辈作者都像他们的前辈那样伪造,如果这一点是正确的,那我们必定要问:到底是谁被这些伪作欺骗了?
科尔在《父其父》中通过一系列类比和隐喻复述了禅宗历史上的虚构,那么我们又能从中了解到什么新的东西呢? 至少,我们能看到科尔对他所讨论的历史时期的描述,但是这些描述似乎与早期的研究并无太大不同。长期以来,我们都知道禅宗内部各个相互竞争的宗派都坚持自己是达摩嫡传;而科尔的观点只是产生于一种新的努力和文本,并试图为禅宗冠以一种“不正当”的意图和动机。尽管科尔讨论的许多东西都已为大多数禅宗学者所熟知,但如果这些讨论是作为一种对“过度历史主义的潜在危险”及“我们面对已有成就的自满”的尼采式的警告的话,那它的确可以作为研究生研讨会上的一个论点——且它必定会招致大量的驳斥。
《父其父》意欲揭露禅宗谱系文本中种类繁多的虚构形式,并表现禅宗与政治间的可鄙联系,这种联系让学者们忽略了上述文本的虚构。实际上,这种历史学意义上的修正与批判同样出现在莫舒特的作品中,但他却使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方法和口吻来表现。莫舒特通过揭示其所认为的影响禅宗发展的核心因素,处理了宋代禅宗文本中存疑的叙述,人们通常将唐代视为所谓的“黄金时代”,而那些文本则被看作“黄金时代”后“衰退时代”的产物。这个话题已经有太多的讨论,在此无需赘述。不过,新的学术风向对莫舒特来说具有重要意义,因为正是在宋代,新的力量塑造了他所称的“成熟”禅宗① Peter N.Gregory、丹尼尔·格茨(Daniel A.Getz),Jr.,eds.,Buddhism in the Sung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1999)。 。这种力量中的一部分来在禅宗外部,如政治、精英文人;而另一部分则来自其内部,如十二世纪时临济宗与曹洞宗之间的教义之争。这些争论将曹洞宗的核心“静默的启示”(默照禅) 对立于临济宗的核心“观察有深意之词句”(看话禅),莫舒特将其译为“观察语言”。
因此,莫舒特必须首先纠正两个误解:其一,禅宗的宗派之争发生在北宋时期;其二,宋代精英文人坚决反对佛教。首先,他讨论了禅宗传统中的“特殊传法”和早期谱系文本的本质;紧接着他补充道,在禅宗开始普遍承认每一代只有一人能继承这种法脉后,所有的纷争都开始平息。同时,他认为,只要其传承能追溯到慧能,那么禅宗各派系“似乎都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彼此的合法性”(Schlütter,p.20)。一些学者开始试图用“一种意义重大的发展形成了传自慧能的五种传统”这一标题来说明,在北宋时期一直存在者完全不同的禅宗思想与修行法门。
但是,莫舒特论证了宗派纷争与宋代禅宗并无关系。尽管《祖堂集》描述了禅宗传法的分支情况,且《景德传灯录》也记载了五宗的孕育,但五宗体系被禅宗接纳的最初证据却在《天圣广灯录》(1039)中(Schlütter,p.22)。这五个宗派并非是敌对关系,毕竟他们拥有相同的目标,且五宗的弟子相互交叉,文人也与五宗都保持着联系(Schlütter,pp.24-25)。因此,并没有证据显示北宋存在宗派主义。莫舒特花了如此多的笔墨来揭示所谓宗派主义的真相,其原因之一可能在于:一旦我们厘清北宋禅宗的历史记录,那其后的“默照”与“看话”之争及其在派系分裂中起到的作用都将显而易见。
总的来说,科尔关于“禅宗文本的低劣伪造”的论述主要是基于他对这些文本的一种认知——即这些文本都是有相应受众的。他的这种认知似乎是受到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一篇文章的影响,且他也引用过这篇文章。在该文中,布迪厄认为艺术界的运作是建立在“消费公众”的基础上的,艺术家及艺术品商人们编造了一整套谎言以欺骗公众,即他们不承认自己的商业利益③ Pierre Bourdieu,“The Production of Belief:Contributions to an Economy of Symbolic Goods,”in Pierre Bourdieu,The Field of Cultural Production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3),pp.74-111。 。或许正是因为对布迪厄这篇文章的笃信,科尔才将禅宗的成功比作“利用公众的诡计”(Cole,p.310)。然而,科尔并未明确指出哪部著作包含了这种假定的受众,但他似乎将读者视作禅宗著作及其所传递信息的消费者。
但是,随着新一代高僧的涌现——包括宏智正觉(1091-1157) 以及真歇清了(1088-1151) ——曹洞宗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并开始表现出对正处巩固期的云门宗与临济宗的威胁。十二世纪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变迁促发了新曹洞传统与固有的临济传统之间旷日持久的义理之争。这场论争围绕大慧宗杲(1089-1163) 对“默照禅”的著名批判,这种修行方式与他所提倡的新方法“看话禅”背道而驰,他将“默照禅”的修行者批为异教徒。虽然如今众所周知的“默照禅”与清了也有关联,但它通常会与曹洞宗高僧宏智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关于这个话题已经有很多讨论了,但莫舒特仍总结道,曹洞宗修习某种被称为“默照”的法门,且它成为了临济宗高僧大慧的批评对象——笔者认为此总结颇具说服力。
基于负载和互感参数摄动的电动汽车无线充电控制//王立业,岳圆,王丽芳,廖承林,张玉旺//(15):178
在参考宏智著名禅诗《默照铭》的基础上,莫舒特简要解释了默照禅的宗旨:它是一种精神修行,其根据在于,每个人都必定有证悟的可能性,其目的并非试图达到“作为突破性经历的证悟”(Schlütter,p.147)。之后大慧的批判可能会让人觉得,偏离正统的曹洞宗理应招致批评。为了矫正这种误解,莫舒特指出,曹洞宗基于传统的修行方式——完全符合长芦宗赜的坐禅仪——且同样根植于佛性的正统解释,而大慧宗杲的方法,完全是一种创新。
莫舒特解释道,大慧创造的看话禅“要求注意力凝聚于核心词句或公案话头”,它可以在坐禅时或日常活动中修行(Schlütter,pp.107,115)。大慧想要强调证悟是一种确实的经历,它能被修行者确凿地体验到,而看话禅无疑是获得这种体验的最好方法。根据莫舒特的观点,大慧将默照禅视为一种“缺乏智慧的寂静主义修行”(Schlütter,p.116)。这里尤其有趣的是莫舒特关于大慧忧心之处的解释:他可能害怕默照禅在僧人中的传播所带来的恶劣影响,但他“更担心它对俗人的吸引力”(Schlütter,p.125)。因此,大慧在写给学者或文人的书信及讲法文稿中保留了对默照禅的尖锐批评。此外,他对默照禅的批判和对看话禅的推崇主要针对文人,我们并不清楚同样的批判是否针对僧侣(Schlütter,p.181)。
莫舒特卓越的研究——尤其体现在将各种材料置于不断扩展的曹洞僧人所处的更广阔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减少了我们对这场发生在十二世纪的论争的误解,以免我们认为它至少发生在大慧和宏智之间;实际上,大慧十分尊崇宏智(Schlütter,pp.134-136)。然而,我们所确知的是,那时曹洞宗与临济宗之间的论争成为了日本禅宗史中的重要篇章。
2.3 两组患者妊娠结局比较 观察组胎膜早破、产后出血、巨大儿、新生儿窒息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早产与低体质量儿发生率显著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3。
虽然《禅何以为禅》有许多优点,但是一些读者可能会发现莫舒特在论点的呈现和全书的整体结构方面,都显得杂乱无章。莫舒特在完整列出将要攻击的早期材料之前,就开始对它们进行批判。我们最初通过大慧的批判来了解宏智的默照禅。此处的危险在于,作者先突出批评对象,然后再去寻找能支持其观点的具体内容,这就会让读者们觉得这种批评是强有力的。虽然莫舒特提到了宏智的许多作品,但他仍将大部分讨论限于《默照铭》,这会让读者们猜测,是否宏智的其他作品会提供与大慧之批判点不同的观点。
由于莫舒特对宋代历史的修正主义式讨论所具有的平衡性质,评论家会惊讶于他竟然减省了对五代十国的讨论。我们很清楚禅宗史家是如何通过宋代材料来想象唐代的情况的。或许现在也是时候承认一些关于五代十国时期佛教地位的错误猜想了。中国的史学家通常不甚重视五代十国,他们在讨论五代十国时总是将其视作唐与宋之间的混乱过渡期。可能正是受这种观点的影响,莫舒特将这段时期描述为“一团各个敌对国家快速互相取代的乱麻”(Schlütter,p.26)。
我们现在逐渐明白,一直试图强调统一的中国会让我们产生对古代中国的盲点,这会导致缺乏对分裂时代的研究① 王赓武的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 已修订并重新发行,新版本为Divided China:Preparing for Reunification,883-947(Singapore:World Scientific Press,2007);兼参Richard Davis,Historical Records of the Five Dynasties(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4)。 。当代的学者们似乎仍旧被笼罩在始自欧阳修(1007-1072) 的思想阴云下,他对佛教的分析充满了消极意味,同时这些学者在梳理中国佛教发展史时也总是倾向于忽视五代十国时期② 早期中国佛教研究著作并未提及五代十国时期,比如肯尼斯·陈(Kenneth Chen),Buddhism in China:A Historical Survey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4);亚瑟·瑞特 (Arthur F.Wright),Buddhism in Chinese History (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帕特丽夏·艾伯瑞(Patricia Buckley Ebrey)、Peter N.Gregory,eds.,Religion and Society in T’ ang and Sung China (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1993)。、 。如果我们抛开欧阳修的消极观点,就能更清楚地理解宋代佛教在不同地域的发展对彼时禅宗所取得成果的意义有多大。
新一代学者对特定地方的佛教——尤其是禅宗——历史的关注,已经引出了对现有学者们关于彼时宗教地位的论述的问题③ 中日学者在五代十国研究领域的开创性成果包括鈴木哲雄,《唐五代の禅宗史》,山喜房,1985;柳田圣山,《唐末五代河北地方に於ける禅宗兴起の历史的社会的事情について》,日本佛教学会,25 (1960):171-86;杨曾文,《唐五代禅宗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如威尔特所言:“唐末五代时期可以被看作中国的第二次 ‘战国’ 时代,因为在某种意义上,二者对中国未来的影响程度相似④ Welter,Monks,Rulers,and Literati,p.9。 。”
莫舒特著作的主要内容,是论证宋代禅宗传统的一系列关键发展如何塑造了之后的禅宗历史及我们对禅宗传统的看法。他并没有考虑他所发现的材料将会对当代的学者产生何种影响。但科尔却在其书的总结章中引出了这个问题。该章大胆地以“分析一切开端的漏洞”为题,科尔提出了一个他认为所有学者和宗教人士都必须回答的问题,且他自认为已将这个问题在该书中抛出了:“我们认识到禅宗的开悟及传承建立在一个巨大的零上——一个空无的深渊,其上是一座承诺保存禅宗传统内核的纸牌屋,在这种情况下,当一个人自称开悟时,我们要如何评判呢? ……简言之,一旦我们认识到早期禅宗‘创造某人之祖师’① 译者注:原文为“fathering one’ s father”,与书名相对,此处根据其文义意译。 的动机,那么从那些文本中获取关于真理、人性及历史的努力都将是不可能且荒谬的”(Cole,pp.307-9)。
审慎的读者多半会问,谁又会去从禅宗谱系文本中获取所谓的“真理、人性和历史”呢? 如果早期禅宗谱系文本真的如科尔所说的那样,“在哲学层面上显得粗糙啰嗦、自相矛盾、不完善,且带有现实政治目的”(Cole,p.308),那么谁又会期盼他们能作为开悟真理的承载者,或是包含对人类存在性问题的讨论呢? 难道仅因一些早期禅宗谱系著作是由更早期材料拼凑而成的,且与禅宗“体验”或真理毫无关联,我们就能说它们使整个禅宗传统和修行基础变得不可靠了吗? 科尔似乎的确是这样想的。他声称,他所揭露的捏造谱系文本的不正当动机“进一步批判了现存的传统,这种传统已经因敦煌禅宗文本而蒙羞了,敦煌文本昭示了中国的所谓开悟的复杂而堕落的起源”(Cole,p.183)。
即使我们承认禅宗谱系文本是一种虚构的可疑的历史事实,那也依然存在问题:我们如何理解它们对禅宗发展至今所起的作用? 禅宗人士面临着一个问题,即一种关于削弱文本历史意义的史学意见。而关于科尔所讨论的“拈花一笑”公案,现代研究已经证实其虚构性,当代学者柴山全庆也评论道,“这个故事可能并没有历史的支撑,但这并不意味着教徒之间的传法是可疑的……这个故事是否能被历史事实支持是个史学和目录学问题,它与禅宗传法的事实毫无关系。也就是说,禅宗传法的事实超越了历史学关切,由此,这个公案对今天的禅宗来说仍有巨大的意义② 柴山全庆,The Gateless Barrier:Zen Comments on the Mumonkan (Boston:Shambhala Publications,2000),pp.58-60。 。”
宗教史学家对这种视角并不陌生,它促使我们反思历史与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二者之间的相悖关系触及了宗教传统的局外人与局内人之间的持久问题。前者与后者的观点往往并无关联,前者通常不考虑那些赋予宗教传统生命力的宗教教诲与体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 在他关于历史事实与基督教信仰的讨论中解决了类似的问题。“这听起来很古怪:用史学的话语来说,关于《福音书》的历史叙述可能被证明是假的,但宗教信仰并不会因此而有所损失:不过,并不是因为它考虑‘普遍的理性真理’! 而是因为史学证明(即史学的证明游戏) 与信仰毫不相干③ Ludwig Wittgenstein,Culture and Valu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32e。 。”维特根斯坦在解释历史事实与宗教信仰的不同时,又进一步阐述:“基督教不是基于历史事实的;相反,它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历史) 叙述并说:现在就去信仰! 但不要带着一种适合于历史叙述的信仰去相信这种叙述,而是在历尽甘苦之后,相信这是你唯一能做的生命的结果。于此,你可看到一种表述,但不要对它持有一种与对待历史叙述相同的态度! 请在你的生命中为之划出一块最独特的空间① Ludwig Wittgenstein,Culture and Valu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p.32e。 。”如果将我们的讨论困囿于“宗教体验的真理”(局内人的观点) 或者“历史的真理”(局外人的观点),那么我们几无可能跳出铃木与胡适之辩的死胡同。
在《父其父》和《禅何以为禅》中,对“传统”人物的传承讨论都是很重要的内容,但两位作者都没有使用某些至关重要的理论及方法论著作,这实在令人不解。但相较而言,这一点在莫舒特那里不那么奇怪,毕竟他并没有明确涉及方法论或理论问题。然而,基于科尔使用的方法,如果他认定自己的作品与爱德华·谢尔(Edward Shil) 关于“传统”的著作及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特伦斯·兰杰(Terence Ranger) 关于“传统的创造”的著作有密切关联的话,那我们很难想象他已经将禅宗对传法历史的创造和虚构看作是例外了。对于熟悉那些作品的读者来说,禅宗似乎是另一种传统体系,或看起来像被传统拥护者制造出来的② Edward Shil,Tradition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1);Eric Hobsbawm and Terence Ranger,eds.,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 。正如霍布斯鲍姆指出的那样,并不存在一个“没有‘发明’ 传统”的历史时期③ Eric Hobsbawm,“Introduction:Inventing Traditions,”in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ed.Hobsbawm and Ranger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3),p.4。 。
在对关于传统的早期著作进行评论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 就已经发问:一旦将我们自己从对证悟的偏见中解脱出来,我们要如何理解“传统”? 他立足于霍布斯鲍姆和兰杰的成果,解释道,“创造出的传统和习俗是被用作实现权力的手段,且它们自古以来就不存在。无论对于历史意味着什么,它们很大程度上都是假的……很明确的一点是,传统定义了一种真实。对于那些传统的修行者来说,无需考虑其替代选项④ Anthony Giddens,“Tradition”(BBC,Reith Lectures,1999),www.bbc.co.uk。 。”对谙熟这些思想的读者而言,莫舒特书中的历史材料显得更有意义,而科尔关于禅宗“传统”的批判则像是陈词滥调。然而,他们可能会惊讶于科尔传达出的某种情绪(或许我们可以称之为浪漫或者怀旧?),他希望传统可以或者应该成为创造物以外的任何东西。
科尔将“传统”视作一种尖刻批判的对象,但紧接着又说他的书将“揭示某种关于人类的普遍之物”(Cole,p.207)。然而,通过对禅宗谱系文本的研究,他到底想告诉我们关于真理和人性的什么东西呢? 他似乎在说,那些文本作者的虚构历史(而非是文本自身内容) 让他得已揭示人性的某种黑暗面——这与禅宗的拥护者们,如铃木及其拥护者所推崇的禅宗积极的思想相悖。接着,在将读者拉进“一切开端的漏洞”(或许我们应该称之为洞穴) 后,科尔(如柏拉图般) 试图引导人们从阴影中走出来并向人们解释他们是如何被欺骗的。
相比于关注何以为“真理”,关心“真实”会显得更谨慎一些。甚至早在宋代时,禅宗那些虚构的谱系就被当作是“真实”。正如莫舒特所言,“传承的内容当然完全在宗教领域内,但传承的谱系自身却是被理解而且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历史事实。”(Schlütter,p.14) ——正如今日的中日韩那样。相比于沮丧地跟着科尔坠入开端的漏洞中,禅宗学者们或许更应该思考,虽然禅宗的虚构起源并未将我们引向关于人性的普遍真理,但它为何能投射出如此真实的以至于需要历史分析的阴影。
科尔似乎建构了一个能囊括当代学者和宗教人士的图景,它不像是安东尼·格拉夫顿(Anthony Grafton) 讨论的那种图景,在后者的描述中,文艺复兴时期的学者们致力于剔除虚假的经典宗教标准。格拉夫顿巧妙地描述了这幅图景:“一列载满希腊人和拉丁人的列车里,真假权威们紧挨着坐在一起,直到这趟列车停在‘文艺复兴’ 站。铁面无私的人文主义者登上列车,查验票证,然后将冒牌货一群一群地从门窗中扔出去。当然,这群冒牌货也因此走向被世人遗忘的垃圾堆——那里塞满了历史与人文主义的赝品① Grafton,Forgers and Critics,pp.102-3。 。”科尔当真认为那些禅宗信徒在目睹谱系文本的抄袭者和捏造者们被扔出窗外后,会从蒲团上跳起来放弃他们的信仰吗? 难道当代学者们关于禅宗的想法会——如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的铁路转撤员——将传统置于通往“遗忘”的道路上吗? 不会,至少现在不会,而且在短期内,这列火车似乎不会跑在通往那个方向的铁轨上。
*本文为“书评文章”(Review Article),原文发表于《哈佛亚洲研究学报》,2011,pp.311-349。所评原书为两本,分别是:Fathering Your Father:The Zen of Fabrication in Tang Buddhism by Alan Cole.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9.Pp.xix + 340.$65.00 cloth,$29.95 paper;How Zen Became Zen:The Dispute over Enlightenment and the Formation of Chan Buddhism in Song-Dynasty China by Morten Schlütter.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2008.Pp.x + 290.$48.00 cloth,$27.00 paper。著者罗柏松,美国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教授,译者杨昌杰,浙江大学哲学系本科在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