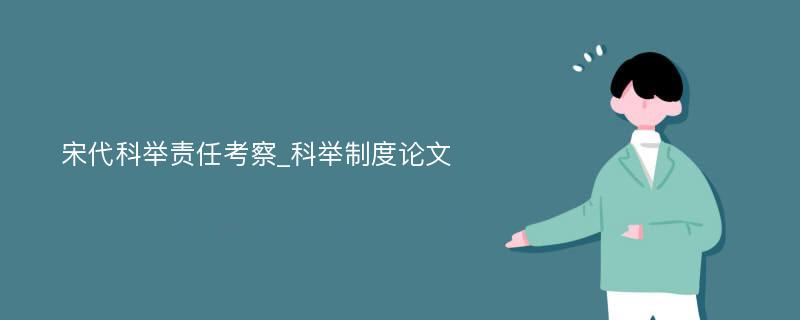
宋代的科举责任追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科举论文,宋代论文,责任追究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近一二十年来,宋代科举制度研究日益全面深入,涉及举子资格、考官资格、考试内容、考试时间、考试场所、解额分配、及第授官等方面,对科举防范措施和科场处罚也有相关或专门的研究①,但对于科举责任追究虽有所论及,但尚未深入系统,是一个新的课题,需要进行探索性研究。宋代的科举官吏,主要有权知贡举、同权知贡举、编排试卷官、封弥官、点检试卷官、详定官、巡铺官等考官。此外,科举期间的保官——知州、通判、升朝官等,他们有担保举子的权力,并负有担保的责任,也是科举官吏的组成部分。他们分工明确,责任清晰;相互制约,临期差遣。科举官吏是科举的组织者,又是责任的承担者。本文在以往宋代科举制度基本事实和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一定程度上借鉴行政管理学、行政法学等理论方法,侧重科举的过程并兼顾准备、保障等多方面来初步探讨宋代的科举行政责任追究。
一、准备保障性的责任追究
宋代制定了一系列科举的防范措施和原则,无论考生还是考官,违反了这些规定就要受到相应的责任追究,这实际上为科举责任追究奠定了制度性的前提。同时,宋代又在科举地准备及其过程中的保障等方面对考官规定一些职责,并追究其失职行为,保证科举的顺利进行。
考题是考生回答问题的依据,拟题则是考官的职责,也是一项严肃细致的工作。宋代科举有解试、省试、殿试以及常科、特科等各级各类的考试,考试的内容、门类、场次都有所不同,也时有变化,情况较为复杂。如元祐时三省奏请的进士、新明法科考试分别有四场、五场:“考试进士分为四场,第一场试本经义二道、《论语》或《孟子》义一道,第二场试律赋一首、律诗一首,第三场试论一首,第四场问子、史、时务策三道。以四场通定去留高下。新科明法依旧试断案三道、《刑统》义五道,添《论语》义二道、《孝经》义一道,分为五场。”② 尽管科举考试如此复杂,宋代对具体考试的拟题范围、形式等还是作了一些正面或限制性的规定。北宋时,仁宗要求“自今试举人,非国子监见行经书,毋得出题”③,哲宗时要求“考试官于经义、论、策通定去留,毋于《老》、《列》、《庄子》出题”④、“秘阁试制科论题,于九经兼正史、《孟子》、《扬子》、《荀子》、《国语》并注内出,其正义内毋得出题”⑤。绍圣时礼部、国子监亦说:“其所试《春秋》,许于三传解经处出题。虽缘经生文,而不系解经旨处,不许出题。”⑥ 南宋时,也有一些相似的规定,孝宗下诏曰:“自今岁试闱,六经义并不许出关题,亦不得摘取上下经文不相贯者为题。”⑦ 其实,这些要求或规定,往往是在臣僚批评科举出题不当之后提出的,有时针对解试,有时针对省试,如孝宗的要求就是在国子祭酒沈揆批评“关题”之后下了上面的那一道诏书,他说:“六经自有大旨,坦明平正(道),不容穿凿。关题既摘经语,必须大旨相近。今秋诸郡解试,有《书》义题用‘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关‘舞干羽于两阶,七旬有苗格’者。据此题目,判然二事,略不附近,岂可相关!谬妄如斯,传者嗤笑。此则关题之弊。有《易》义题云:‘时乘六龙,以御天也;云行雨施,天下平也。’至此当止矣,而试官复摘下文‘君子以成德为行’相连为题。据此一句,其义自连下文,若止已上四句为题,有何不可?此则命题好异之弊。”⑧ 后来,宁宗嘉泰元年(1201)仍有臣僚批评命题,“治经以经旨为主,文辞为辅。近者经学惟务遣文,不顾经旨,此非学者过也,有司寔启之。盖命题之际,或于上下磔裂,号为断章;他处牵合,号为关题。断章固无意义,而关题之显然浑成者,多已经用,往往搜索新奇,或意不相属,文不相类,渐成乖僻。士子虽欲据经为文,势有不可,是有司驱之穿凿。乞今后经义命题,必本经旨。如所谓断章、关题,一切禁约。庶几学者得以推原经文,不致曲说”⑨。直至嘉定时,国子博士钟震还在指出地方命题中的问题,“后缘外州场屋命题,多是牵合字面求对,更不考究经旨。如以‘在璿玑玉衡,以齐七政’合‘七旬有苗格’之类,但合七字,更无义理,岂不有碍经旨?所以关题自嘉泰元年后不曾再出。今来奏请以全题有限,自后场屋若问题关题,理亦可行”⑩。为此,关题未见尽废,但对这种命题的不当和失误,则应予纠正,并追究考官的责任。
宋代对拟题失误的处罚是比较严厉的,即使在一般考试命题,如“引试上舍”、“公试上舍”中,如有不当也是重罚。徽宗政和五年(1115),“河间府考试官引试上舍,出《书》义题‘无轻民事惟艰’作‘为难’字,陛下赦其过失,止从薄罚”,尽管“今看详于经意别无违戾”,但“系公罪事理稍重”,后来还是“诏元出题官特冲替”。又如政和八年(1118),“泸州公试上舍题目,内有差漏并错引事迹,及试经义题目,失先后之序”,显然情况要严重些,于是,“所有考试官,资州龙水县尉王行、合州司录钱挺显不子细出题,致有差错违误。诏行、挺并放罢”(11)。他们所受到的放罢处罚,自然也比冲替重一些。至于科举命题更为重要,如有失误更应追究责任,严惩不贷。如南宋乾道七年(1171)十一月,“诏四川类省试院进题目,考试官何耆仲所撰第三场第三道策题,用事差错,特降一官放罢,今后不差充试官”(12)。可见,不仅罢免此官,而且还取消了他日后担任考试官的资格。当然,也有针对特殊情况的出题责罚,建炎四年(1130)九月,“诏利州试官宋愈、陈协各特罚铜十斤。臣僚言:‘驻跸会稽,是为首善之地。愈出策题谀宰相,为得王佐,夏旱秋霖,而协以为雨旸时若。导谀如此,何以求切直言?’故有是罚。”(13) 因而,宋代对考试的拟题比较重视,设置了点检官进行校阅试卷(当然也从事其他监察性的工作),同时,针对考试、点检上存在的问题,又加强对考试官和点检官的管理,正如南宋庆元时臣僚所奏:
诸郡与漕闱考官,必差一员为点检主文,凡命题与所取程文皆经点检,以防谬误。比年以来,徒为具文,一时考官各骋己意,异论纷然,甲可乙否,以致题目多有乖谬。去岁秋举,诸州所申义题,或失之牵强,文理间断而不相续。或失之卤莽,文理龃龉而不相类;赋题、论题,或失之破碎,文理捍格而不相贯,以至策问专肆臆说,援引失当,皆由点检官不择才望之士,考官中有矜能挟气者,不同心商确,故有题目出于一人之见,其他官旁睨,不欲指其疵类。及有摘发其失,出题之官独被谴责,而无点检之名。乞今后漕臣若非由科第,即别委本路提刑、提举、总领有出身者,每举从朝廷专委一司选差试官,须择其素有文声名望、士论所推者充点检官,专以文柄责之。诸考官先供上题目,点检官斟酌审订,择其当理而不悖古训,兼通时务者,然后用之。及考官所取合格试卷,点检官仍加详校,公定去留。礼部俟其申到题目及程文,再行点检。如有乖谬,将点检官重行黜责。(14)
宋宁宗听从了这个建议,强化了出题和试卷的管理以及程序,明确了考试、点检官的责任,如有失误,将被重行黜责。
命题固然是科举考试的关键环节,而在考试之前及其过程中还有一些准备和保障工作要做,并且也有相应的责任。政和五年(1115)二月,翰林学士兼侍读王甫等,“乞每岁锁院前十日,令诸司官及管勾贡院什物库官,具排办足备文状,申尚书礼部,差郎官一员专行点检,保明申尚书省。内贡院见管什物与举人就试书案,岁久数多,应办不足,所存亦皆弊坏,乞特命有(司)措置添修”(15)。徽宗听从了这建议,并且还制定了专门的法规,做好考试的物质准备。后又针对场屋怀挟、传义之弊和伪冒滋长的现实,加强监门官和点检官的职责,嘉定十六年(1223)正月臣僚言:“臣紬绎诸弊为日久,如门钥当责胥吏收买牢固者,监门官点检,不容灭裂。其引试日引放既毕,每日辰酉请门官监开,传送饮食。”(16) 保障的工作和责任很具体,甚至包括考场周围的防火,如元丰八年(1085)五月,“正议大夫、户部侍郎李定,承议郎、给事中、兼侍讲蔡卞,奉议郎、起居舍人朱服,各降一官。坐知贡举日,开宝贡院遗火。权知开封府蔡京、判官胡及、推官李士良,各罚铜八斤。坐救火延烧寺,延及人口,虽会赦,特责之也”(17)。这类保障性的工作属于事务性的,十分烦碎,必须仔细认真才可避免差错,否则,招致相应的责任追究。如试卷封弥差误就会遭到严惩,宣和五年(1123)御史惠柔民等言:“准敕应充府监发解别试所考官,九月二日,具武士合格字号奏闻。数内字号系内舍试上舍试卷,其当行人为是同场引试,却误同外舍试内舍印子,致有差误。除已改正,将当行人施行,并元封对号官已举觉外,所有臣等罪犯,伏望重行黜责。”于是,“诏惠柔民可罢殿中侍御史,柳约罢著作佐郎”(18)。再如。政和三年(1113)八月,臣僚言:“窃见以谓凡试院之事,虽尽在主司,至于关防周悉,全籍封弥官谨密详察。号既已定,岂容复有差互……显见封弥所并不子细点检,对二人卷子重叠用号,所失甚大。伏望重行黜责。”“诏管号官朝请郎周劲特降两官,依冲替人例施行,系公罪,事理稍重。”(19) 在科举考试过程中,需要做的防范性工作很多,若不能尽职,即会招来责罚,嘉定九年(1216)“诏知荣州杨叔兰放罢,朝奉郎刘光特降一官。以潼川提刑、权运判魏了翁言‘荣州解试拆号后,士人赵甲等诉试院欺弊事。叔兰系举送官,关防不谨,以致官吏作弊。朝奉郎刘光不能训其子,使抵冒法禁’故也”(20)。至于未能履行保障职责,甚至纵容作弊,更严加惩罚,绍兴二十六年(1156)闰十月,“诏鄂州通判任贤臣监试不职,容纵举人假手传义,特降一官”(21)。可见,在科举中出题失误,保障不足,监试不力,都会受到行政责任追究。
这类考务性责任是在考试的具体过程中直接产生的,追究往往是在事中或事后进行。而有些追究则是针对违反限制性规定或预防性规章的,以起到防微杜渐的作用,保障考试的顺利进行。如违反锁宿限制,大中祥符七年(1014)八月就有诏云:“今后所差考试、发解并知举官等,宜令閤门候勅出。召到,画时令閤门祗候引伴指定去处锁宿,更不得与臣僚相见言话。如违,仰引伴使或閤门弹奏,并当重行朝典。如候鞍马未至,即閤门立便于左骐骥院权时供借。”这个诏书是有其原因的,“先是,王曾等授勅知贡举,与李维偶语于长春殿阁子,至审刑院伺候鞍马,迟留久之。押伴閤门祗侯曹仪虑其请嘱,因以上言,即令曾、惟演分析,与李维词同,特放曾等。乃有是诏”(22)。又如绍兴八年(1138)五月诏,“楼玮为贡院对读官,规避妻党,牒试托故出院,特降一官”(23)。所以,在科举过程中,锁院时与大臣相见言语、主持考试时不回避亲戚等会受弹劾、降官等追究。其中科举回避应当是宋代行政回避制度中的亲属、职事回避规定的组成部分,与执政和御史“不应交通”,以及“禁同省往来”等限制十分相似。这种追究,显然是为了克服人际关系、职事关连中的障碍,保障科举顺利进行。
二、判卷录取时的责任追究
解试的通过及发解与否,直接取决于评卷和考第,这也决定举子的命运和仕途,为朝野广为关注。
在科举判卷时,考官一般根据举子回答的内容和程度,给予通、粗、否的等第,然后决定发解和及第与否。真宗咸平元年(998)五月礼部贡院言:
窃见诸州府及贡院考试诸科举人,于义卷上多书粗字。盖试官庇容举人,免作十否殿举。今后并须实书通、否,不得依前以粗字庇容,如有固违,乞行朝典……自今后不问新旧人,并须文章典雅,经学精通。当考试之时,有纰缪不合格者,并逐场去留。如有容庇,发解、监试官并乞准前条勒停。(24)
礼部贡院针对考试官为了逃避责任、庇护举人而在判卷时多书“粗”等的现象,要求实书“通”或“否”,明确态度,否则,如有包庇,徇私不公,发解官、监试官都将被依法勒停。因为不恰当或不公正的判卷,必然直接损害考生的切身利益,造成考生的不满或怨恨,以至上奏诉说,考试官也会咎由自取。早在大中祥符五年(1012)九月,《毛诗》学究王元庆就诉贡举官判卷不当,结果,“贡院考试官、前宁州司法参军、国子监说书王世昌勒停,知贡举官晁迥、刘综、李维、孙奭并赎铜三十斤”(25)。天禧三年(1019)二月,“礼部下第举人陈损诣登闻鼓院诉贡举不公,诏龙图阁学士陈尧咨、左谏议大夫朱巽、起居舍人吕夷简等于尚书都省召损等,令具析所陈事理及索视文卷看详考校,定夺以闻。继而进士黄异等复讼武成王庙考试官陈从易不公,诏尧咨等如前诏详定。尧咨等言:‘礼部所送进士内五人文理稍次,武成王庙进士内二人文理荒缪,损等所讼亦有虚妄。’诏损、异等决杖配隶,连状人并殿两举,惟演等递降一官”(26)。天圣元年(1023)十一月,又有举人上诉开封解试不公。结果,“降侍御史高弁为太常博士,职方员外郎吴济为都官员外郎,太常丞、直集贤院胥偃为著作佐郎,监察御史王轸为太常博士,监兖州、涟水光化军、郢州酒税,左正言刘随罚铜五斤”(27)。可见,宋代对此类因判卷不公而导致的责任,予责任人以罚铜和降官、降差遣的处罚,是比较严厉的,而对举子上诉不当,处以配隶,更是重罚。
在判卷录取中,考试官的职位不同,职责不同,处罚也有所区别,庆历四年(1044)六月,“诏进士诸科点检考试……经科举人如有过落不当,具考试、覆考官,于知举官下减等定罪”(28)。而责罚的轻重往往取决于判卷失当或违法判卷的程度,宋代对此似有具体的规定:
五年,诏士曾预南省试者,犯公罪听赎罚。令礼部取前后诏令经久可行者,编为条制。诸科三场内有十“不”、进士词理纰缪者各一人以上,监试、考试官从违制失论,幕职、州县官得代日殿一选,京朝官降监场务,尝监当则与远地;有三人,则监试、考试官亦从违制失论,幕职、州县官冲替,京朝官远地监当;有五人,则监试以下皆停见任。举送守倅,诸科五十人以上有一人十“不”,即罚铜与免殿选监当,进士词理纰缪亦如之。(29)
这道诏书指出了考试判卷过程中不当的行政行为,并且根据责任的大小,规定了处罚的相应方式和程度。不同阶段不同类型的考试责任又有所不同,如前述天圣时刘随等解试不公被罚铜五斤,而熙宁、元丰时省试不公的责罚要重得多,熙宁九年(1076)三月诏,“殿试进士,初考官:翰林学士陈绎,集贤校理孙洙、王存,崇文院校书练亨甫、范镗,审官东院主簿陆佃,各罚铜二十斤;覆考官:翰林学士杨绘、龙图阁直学士宋敏求、同修起居汪钱藻、秘阁校理陈睦、崇政殿说书沈季长、检正中书刑房公事王震,各罚铜十斤。并坐考校第一甲进士不精也”。元丰五年(1082)三月,“诏御试所考官苏颂等六人,覆考官安焘等六人,详定官蒲宗孟等三人,各罚铜三十斤。颂等考黄裳等(第)下等,上亲擢为第一,故罚之”。其中有“不称旨命”,也有“高下失实”的问题,主要在于考核不精,定等不当(30)。至北宋后期有些变化,贡举时只责罚点检官而不坐考官,故绍圣元年(1094)正月,右通直郎蔡安持建言:“欲于贡举勅内改‘点检’为‘考试官’字,庶几条约均一,士无遗滥。”于是将点检和考官涵盖在考试官之中,使之都承担相应的责任(31)。政和时,责任追究的实施可能差一些,出现“唐开祖程试纰缪,主司校考不精,宜有薄罚,未见施行”的情况,但在大臣的奏请之下,最后还是有所改正(32)。可见,在北宋后期政治秩序较为混乱的情况下,科举责任追究并没有停止。
南宋科举判卷录取上的问题,从《宋会要辑稿》的记载来看,较北宋要多一些,问题也严重一些,如考校不精、对读脱漏,“经义但看冒头,诗赋仅阅一二韵,论策全不过目”(33),尤其四川的漕试、解试以及类省试“私取之弊”为多(34)。为此,对考试官的责罚也屡见于史载,如绍兴十五年(1145)四月,“诏太学博士杨邦弼御试进士,对读试卷,有所脱漏,罚铜十斤”(35)。而大臣们对此类责任也密切关注,并且有的还及时上奏,提出自己的看法,如嘉泰元年(1201)二月,右谏议大夫程松言:“若有司所取不当,他时上彻听闻,则考官降黜,所取驳放。”(36) 嘉定六年(1213)八月,臣僚言:“乞今(令)礼部速牒诸州,严责考官精择,正解之外待补卷子亦加精考,并要分明批抹,与选者批文理何处优长,黜落者批文理何处纰缪,卷首具考官职位。开院后,将所取草卷解发运司点检,如有卤莽,定加责罚。”(37) 后来绍定时,针对“举人程文雷同”的情况,“命礼部戒饬,前申号三日,监试会聚考官,将合取卷参验互考,稍涉雷同,即与黜落。或仍前弊,以致觉察,则考官、监试一例黜退”(38)。也就是一旦发现判为合格的答卷雷同,不只黜落考生,而且要黜退考官、监试官。
三、发解举解中的责任追究
发解或举解是科举过程中联结解试与省试,即地方与中央考试的关键环节。宋代对发解条件的规定是比较全面的,考生即贡生既要通过解试,解试成绩真实有效,又要符合其他解送条件(包括考生的主体资格等),才能发解,参加省试。如果不应解而解,或解后又发现其他问题,则解送及考试官吏都必须承担解送的行政责任。正如宋太祖时,权知贡举卢多逊所言:
伏以礼部设科,贡闱校艺,杜其滥进,是曰宏规。所以发解之时,必积程试,取其合格,方可送名。岂有经试本州,列其贯籍,考其艺能,动非及格,殊乖激劝之道,渐成虚薄之风……仍解状内开说当州府元若干人请解,若干人不及格落下讫,若干人合格见解。其合申送所试文字,并须逐件朱书通、否,下试官、监官仍亲书名。若合解不解、不合解而解者,监试官为首罪,并停见任,举送长官,闻奏取裁。(39)
卢氏所云涉及州府发解的目的、人数、名额和考试结果、考官署名等一系列发解要求,以及监试官、举送官的职责和责任。这是对一般发解的规定,至于发解锁厅应举者也有相似要求,如太宗雍熙二年(985)六月,“中书门下言:近日诸道州府解到官吏去官赴举者,礼部贡院考试,多是所业未精。欲望今后锁厅应举者,须是文学优赡,才器出群,历官无负犯之尤,检身有可观之誉,即委本处先考程试。如文艺合格,以闻待报,解送礼部考试。如所业纰缪,发解官、与(举)送长官必置重罪,本人免所居官”(40)。至十二月又下了相关诏书,“诸科举人,省试第一场十不者殿五举,第二、第三场十不者殿三举,其三场内有九不者并殿一举。其所殿举数,并于试卷上朱书,封送中书。请行指挥及罪发解试官、监官。又卷头子上,如有虚书举数场第及诈称曾到御前者,并驳放殿举。……监官、试官如受请财物,并准枉法赃”(41)。可见,举人参加省试,如有“十不”之类,固然要受到殿举之罚,而发解试官等因虚书受请也会受到法律制裁。所以,端拱元年(988)三月,翰林学士、知贡举宋白说:“考试贡举人内,有墨义十不者,请责罚举送官,以诫滥进。”太宗听从了这个建议(42)。真宗天禧二年(1018)也有类似的诏书,“自今锁厅应举人所在长吏,先考试艺业,合格者始听取解。如至礼部不及格,当停见任。其前后考试官、举送长官,皆重寘罪。至天圣时除其法”(43)。到南宋庆历四年(1044)八月,礼部贡院仍云:“今请解送举人,有保明行实不如式者,知州以下坐罪,仍以州县长吏为首。解试日,有试院诸般情弊,止坐监试官考校不精、妄有充荐。至省试日,拖白纰缪十否,止坐考试官。若所差试官非其人,考校不公,坐所差官司。若试官因缘受贿,有发觉者,其所差官司,于不按察罪名之上,更加严谴。其考试官坐罪,即不分首从。”(44) 这进一步把发解官与主持考试官员的责任区分开来,以便准确地追究责任,至于考试官“因缘受贿”,已属较为严重的犯罪,也就不分首从,都将严惩不贷。当然,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发解责任的落脚点在于解试结果以及举子的解试成绩能否经得起省试的检验。这些相关的发解要求,不断重申,无非表明解试后的发解问题常常存在,而朝廷也非常重视,并归责考官。至于考生在举解时也是有责任的,“至省试程文纰缪者,勒停;不合格者,亦赎铜放,永不得应举”(45)。又如,“先朝时,锁厅举进士者,时有一人,以为奇异。试不中者,皆有责罚,为私罪。其后,诏文官听应两举,武官一举,不中者不获罚”(46)。举子考试责任,以今天观念来看也属行政责任,但这里主要探讨考官的行政责任,故考生举子的责任略及而已。
在史书中,确有不少宋代官吏因发解受到追究的记载,除前面提及的外,又如:真宗咸平元年(998)六月,“密州发解官鞠傅坐荐送非其人,当赎金,特诏停任,仍令告谕诸道,以警官吏”(47)。天禧二年(1018)九月,任布“等后以解送不当,递降诸州监当,复罚铜三十斤”(48)。至崇宁时,一度停罢科举,地方的解额拨作贡额,但贡举中也有责任追究的规定,“贡士至辟雍不如令者,凡三十有八人,皆罢归,而提学官皆罚金”(49)。这些发解官、解试官等多因“送非其人”、“解送不当”、“不如令”而受到罚金、停任、罢黜等责罚,也就是由于解试不当、解送不实而导致的行政责任追究。
发解不当的科举责任,实际上主要基于解试本身要求而形成的,如上述解试的判卷考第失误,就有可能成为发解责任的根源。而解试时的问题又难以及时发现,举子得以蒙混过关,相关官吏也侥幸免责,至省试时,举子的考试成绩以及其他问题被发现,如前面提及的天禧二年诏书所云“其前后考试官、举送长官,皆重寘罪”,也就是说,“锁厅举人试不合格者并坐私罪”(50)。尽管这一规定后在天圣、景祐时曾被废除过,但宋代发解责任追究基本存在。当然,这种发解责任有其特点,往往解试时的问题至省试时发现,从而回溯追究原来考试官、发解官的责任。因而,咸平元年(998)礼部就提出,加强解试考第的评定和举子身份的核实,以免差误,否则,或“如有固违,乞行朝典”,或“发解、监试官,追一任”,而南省考试官“不得庇容,如失举行,并当连坐”(51)。至五年(1002),翰林学士李宗谔言:“准诏分定监试、发解官荐送纰缪十否九否举人刑名。”制定了具体的解试失误的处罚标准,处以勒停、殿选、与远小处监当停见任、罚铜等(52)。考试官解试时的责任有相当一部分是到省试发现后才予追究的。如嘉祐时针对川、广解试之弊,要求贡院严加考核,诏曰:“应明经诸科省试三场以前九否十否者,今(令)贡院再考校本处解送试卷。若其问以否为粗,以粗为通,出义不依条制,致有妄荐者,以旧条坐之,不在末减。若考校通粗及出义,依条别无差谬,省试三场以前有九否十否,即考试官与于元条下减一等定罪,旧条合殿选者与免选,选人该冲替者十殿一选,京朝官勒停者与冲替,冲替者与监当,监当者与远处差遣。”(53) 这与发解要求和处罚原则是一致的。
在发解中,发解官除了要保证应举者考试等第的真实有效外,还要核实和保证他们学识、品德、负犯、籍贯以及解额等方面内容符合解送的条规,否则,也要承担相应的发解责任。这可称之为发解担保责任。如前所揭雍熙二年(985)六月中书门下所提出的“锁厅应举者”的文学、才器、负犯等方面要求(54)。不久后,淳化三年(992)诏书对应举者的身份规定更为具体:
应举人今后并须取本贯文解,不得伪书乡贯,发解州府子细辨认。如不是本贯,及工商杂类,身有风疾,患眼目,曾遭刑责之人,并不在解送之限。如违,发解官当行朝典,本犯人连保人并当驳放。如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55)
在核实考生文解时,发解官对籍贯(乡贯、户贯)尤为重视。考生的寄籍或冒贯是长期困扰宋代科举的问题。这直接挤占奇籍地区的解额,加剧该区域的科举竞争,从而引起本地举子不满甚至骚动,故宋代要求发解官仔细核辨籍贯。不能妄保,否则课以重责。天圣四年(1026)八月诏,“解发举人,窃虑妄有保委寄贯户名,宜令开封府下司录司及诸县,并依前后条贯施行,更不得妄保寄户名。如有违犯,重行断遣”(56)。在两宋之际,尤其南宋初期,由于时局动荡,人口迁徙,户籍散佚,核实难度加大,举子籍贯问题陡增,引起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如建炎四年(1130)六月,礼部言:“欲下转运司令遍下所部州军,候发解开院毕,具合格人数、姓名并试卷,及缴连本部元立定解额指挥、真符赴部。如曾经兵火州军,令当职官及考试官结除名罪,人吏结编配罪保明;若稍涉虚冒,不依元立解额,致大放举人,虽已出官,令行改正,仍乞不以去官赦降原减。”(57) 籍贯等方面失实的处罚,当职官为除名,人吏为编配,并“不以去官赦降原减”,这是严厉的行政或刑事责任形式。绍兴二十六年(1154)二月诏,“若已后发解就试人多,不得过绍兴二十六年所取之数。仍立为定制。若已用流寓户贯得解之人,许自陈,并入东南户贯。其已得举数,即合通理。如有违犯,并依贡举条法。若州军辄行大解,当职官吏并发解官依法徒二年科罪,举人即从下驳放”(58)。可见,当职官吏、发解官必须根据户籍依额发解,否则,处以“徒二年科罪”的刑罚。当然,这类编配、徒刑等发解责任形式为刑罚,但又是由发解的行政不当或不作为所致,应属行政性的刑罚,而非因刑事罪名而承担的刑事责任。
在此还必须指出,上述发解担保责任是宋代科举行政责任的一种重要形式和组成部分,并且处在宋代科举行政责任的基础性地位。而担保责任几乎贯穿科举整个过程,涉及解试、省试以及制举、特奏名、经明行修科等类科考,它在维护科举法制,净化科举环境,实现公平竞争,促进社会安定和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受贿贪赃导致的责任追究
在上述科举准备、判卷和发解等过程中,考试官吏的失误失职,有的是客观的,有的是主观的;有的是过失,有的是故意。而考试官吏在科举中的受贿贪赃则是主观、故意的违法。乃至犯罪行为,往往予以行政直至刑事处罚,或者直接处以刑罚。这类处罚在科举法律责任追究中是最为严厉的,与一般的刑事责任没有很大区别。这可能与我国古代特别注重“赃罪”有一定的关系,“我国封建刑法是抓住‘赃’这一具体鲜明、可以计量的特征,将一切与‘赃’有关的犯罪一概计赃定罪量刑”,它的侵犯客体是公私财物或正常行政(59)。不过,在科举中受贿贪赃与直接侵占、盗窃公私财物又有所区别,它是在特定的科举行政过程中形成的法律责任,即利用或因为手中的权力而谋利或获得钱财,从而徇私枉法(或徇私不枉法),破坏科举法制和秩序,损害考生利益,乃至危害政权。考试官在此所承担的责任形式基本上是刑事的,但是在古代仍然属于广义的行政责任,处罚的形式和方法也如前提及的行政性刑罚。
早在太宗时,雍熙二年(985)十二月诏,“监官、试官如受请求财物,并准枉法赃论”(60)。在法律上,“枉法赃”与“不枉法赃”都是罪名,并且前者较后者的法律责任显然要严重得多,当然,具体处罚的程度则要视其受赃数量和情节而定,科举责任的追究就是如此。咸平元年(998)九月,“淄州邹平县令正可象坐考试举人受钱三万,法当绞。诏贷死,决杖配少府监役,知州、通判各停官”(61)。该县令因主考时受贿三万依法当判绞刑,只因皇上开恩贷死决杖配役,知州、通判则承担相应的连带行政责任而停官。这类科举违法犯罪为举子深恶痛绝,也极为朝野重视,如在景德元年(1004)九月,“令御史台谕馆阁、台省官,有以简札贡举人姓名嘱请者,即密以闻,当加严断。其隐匿不言,因事彰露,亦当重行朝典”(62)。庆历四年(1044)六月,朝臣亦言:“科举所以收天下之英俊,且为孤寒之地。比年百计徇私,内而省闱廷试,则有暗记牢笼之弊,如黄度、罗点辈私取陈亮以魁多士是也;外而诸路,如福建考官黄广被差之后,受金入院,寻即事发,为言者论列是也。属当大比,来岁春闱,万一考官私相结约,阴取党类,接受贿赂,欲与计偕者,并令监试留意举觉,不得容令复蹈前辙。春闱委在院台谏官觉察,否则事发,并坐其罪。”仁宗听从了这个建议(63)。同时,又有不少大臣竭力主张严惩科场贪赃徇私,如包拯上奏说:“乞特降约束,其逐处试官、监试官如稍涉徇私及请托不公,并于常法外重行处置;不然,令别定刑名,庶使官吏等各知警惧。”(64) 这些都表明了宋朝对这类科举嘱请和受贿的态度,一方面加强台谏的监督,另一方面“重行朝典”,“并坐其罪”。科举官吏的受贿贪赃,影响恶劣,社会危害大,以一般的行政责任追究难以奏效,只有严刑重罚才能起到震慑作用。所以,宋代科场又以重罚著称,如上面的邹平县令考试时受贿三万,法当绞死。
但是,严刑重罚还是禁止不了科举中受贿贪赃案的发生,尤其在政治较为动荡的时期,如南宋中后期的情况就比较严重,但朝廷并没有放弃严惩的态度。宁宗嘉定初,就有臣僚指出:“仰惟国家数路取士,得人最盛,莫如进士设科。近年奸弊滋甚,据权势者以请嘱而必得,拥高赀者以贿赂而经营,实学寒士,每怀愤郁。”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考校差官,要当精择。盖考官精明,去取允当。否则,是非易位,遗才必多。乞诏大臣精加选择,无取昏谬,充数其间”(65)。这个建议实际是强调科举时的用人,在他们看来,任人比任法还要重要一些,但关键仍在于依法科举,严惩违法犯罪。对何周才发解受赂一案的处理就反映科场情况和朝野态度。这一案件的处理和过程是这样的:
(嘉定)十一年十一月十一日诏“荣州发解监试官、承直郎、签判何周才特贷命,追毁出身以来文字,除名勒停,免真决,不剌面,配忠州牢城,免籍没家财。考试官石伯酉、扈自中、冯寅仲各特降一资,并放罢。刘颐并徒二年,私罪赎铜二十斤,仍照举人犯私罪不得应举。杨元老徒二年,私罪荫减外,杖一百,赎铜十斤。刘济特送五百里外州军。刘颐、杨元老特分送三百里外州军,并编管。”以周才充发解监试,受刘光赇赂,用杨元老之谋,约以策卷中三“有”字为暗号,取放光之子颐(改名宜孙)及其孙济二名。既为赵甲经漕司告试院孔窍之弊,下遂宁府,鞫得其寔,具按来上,从大理拟断。于是臣僚言:“周才、光等罪犯皆得允当,伯酉、自中、寅仲不合擅令周才干预考校,又听从取放,乞并镌罢。”故有是命。(66)
在这一案件中,发解监试官何周才受刘光贿赂,通过试卷标记暗号,而取放刘颐等,终被举发,何周才受到除名、勒停、配役等行政、刑事处罚,同时相关考试官也受到相应的行政、刑事处罚。这反映了科场问题的严重性,也表明了朝廷惩治的态度。就其相关责任人承担的责任形式而言,有编管、勒停、降资、放罢、赎铜,以及不应举等行政责任形式,还有配役、徒、杖等刑事责任形式,并且二者结合起来追究责任,行政处罚的特色很浓。当然,宋代追究行政责任时,各类责任形式往往相互配合。
为了防止科举官吏受贿贪赃,宋代十分重视对这些官吏的选拔和监督,如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对发解官就有专门的诏书:“诸路转运司所差发解试官,务在尽公,精加选择。如所差徇私及庸缪不当,令提刑司按劾,御史台、礼部觉察闻奏。”(67) 这种专门的监督,主要针对考试官的选任及其品行作实时监控,追究相应责任,保证科举的正常进行和科举责任落到实处。又如嘉定十三(1220)年,殿中侍御史胡卫针对知贡举的选任和监督就说:“照得知贡举一员,同知贡举二员,皆择禁从近臣,儒学时望,又以台谏参之。嘉泰间,谓司谏司考校,不无迎合,乞专纠察,而于议题去取高下勿预焉,即增置同知贡举一员……乞将台谏同知贡举一员改作监试,其校文之官有勤惰不一者察之,执事之吏有内外容奸者纠之。”(68) 可见,宋代让台谏以及礼部监察科举,旨在保证考试、判卷、发解等的公平公正,防止各种弊端的产生。宋代科举中的受贿贪赃即使无法杜绝,而朝廷的严惩、朝野的态度则是鲜明的,至于特殊时期的科场状况以及皇帝法外开恩则又另当别论了。
宋代是一个重视科举的时代,所谓“天下之治乱,由于人材之盛衰;人材之盛衰,由乎科举之当否”(69);“国家取士,惟进士得人为盛。故于三岁大比,每加详而致意焉”(70)。这种对科举的称赞,是有所根据的,与宋代科举法制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宋人既肯定科举的成果,也称颂科举制度,如嘉定十五年(1222)右正言龚盖卿说:“本朝科举之法最为严密,将试而委官,已试而锁院。虑考官之容私也,胡(故)立糊名、誊录之法;虑士子之饰欺也,故立代笔、传义之法。三百年间,名卿才士皆此涂出。”(71) 同时,宋代科举问题又比较多,上述许多科举责任追究的制度或措施,正是针对科举中的问题而设置或制定的。
毋庸置疑,宋代的这些制度、措施的形成和发展促进了科举制度的发展。据前所论,宋代的科举行政责任追究制度,主要包括科举准备和后勤保障不力、判卷和录取不当、发解失误、举解落第、担保不实、受贿贪赃等方面的责任追究。若进一步深入考察,则会发现,这一科举责任追究制度,涉及解试、省试、武举、制科、特奏名等类型及其过程,最为关键者在解试和发解阶段,这一阶段相关的科举责任追究诏令制条也特别多;针对科举官吏的准备、保障、考判、发解、担保方面存在的问题,规定了相应的科举法律责任;采用的追究责任方式虽无具体定罪量罚的标准,但大致来说,对于一般违法犯规的行为,处以罚俸、罚金、降官、罢官,而对于情节严重、手段恶劣的犯法行为,则往往处以杖刑、徒刑、配役等。总之,宋代在科举的过程、方法、类型、主体、对象等各方面都有相关的责任追究的规定,比较详细、系统,基本上得到落实施行。所以,即使宋代科举在某些时期出现问题,责任追究也形同虚设,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成功的。
注释:
① 参见冯陶:《北宋初期科举制度研究综述》,《晋阳学刊》2003年第1期;郭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全国第三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会议综述》,《教育与考试》2007年第1期;高桂娟等:《国内科举制研究的脉络及其进展》,《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王曾瑜:《宋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陈高华等:《中国考试通史》第二卷,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朱瑞熙等:《宋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②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元祐二年十一月庚申”,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9899页。
③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二“宝元元年四月乙未”,第2872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四“元祐二年正月戊辰”,第9593页。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七三“元祐七年五月癸巳”,第11284页。
⑥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五五,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⑦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二一。
⑧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之二一。
⑨ 《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二四-二五。
⑩ 《宋会要辑稿》选举六之四二。
(11) 《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九之二三-二四。
(12)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十之二一。
(13)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十之三。
(14)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二之十五。
(15) 《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九。
(16) 《宋会要辑稿》选举六之四八。
(1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五六“元丰八年五月丙辰”,第8502页。
(18)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七之二四。
(19) 《宋会要辑稿》诜举十九之二三。
(20)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六之三二。
(21)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十之十二。
(22)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九之六。
(23)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十之五。
(24)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四之十七。
(25)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十八“大中祥符五年九月庚午”,第1784页。
(26)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九之七。
(2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天圣元年十一月己未”,第2343页。
(28)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三十。
(29) 《宋史》卷一五五《选举一》,中华书局本校记指出,“五年”疑为大中祥符五年,第3610页。
(30) 《宋会要辑稿》选举八之三五。
(31)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九之二十。
(32) 《宋会要辑稿》选举四之八一九。
(33) 《宋会要辑稿》选举六之十七。
(34) 《宋会要辑稿》选举六之二四。
(35) 《宋会要辑稿》选举八之四三。
(36) 《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二三。
(37) 《宋会要辑稿》选举六之十七。
(38) 《宋史》卷一五六《选举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3637页。
(39)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四之十三-十四。
(40)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四之八。
(41)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五。
(42)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六。
(43) 《文献通考》卷三十《选举考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88页。
(44)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五之十二-十三。
(45)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五,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68页。
(46) 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50页。
(47)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十三“咸平元年六月庚寅”,第912页。
(48)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九之六。
(49) 《宋史》卷一五七《选举三》,第3666页。
(50)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一四“景祐元年四月壬辰”,第2672页。
(51)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四之十七。
(52)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四之二三。
(53)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五之十六。
(54)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四之十。
(55)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四之十五-十六。
(56)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五之六。
(57)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六之三。
(58)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六之九。
(59) 叶孝信等主编:《中国法律史研究》,北京: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4页。
(60)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五。
(61)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九之三。
(62) 《宋会要辑稿》选举三之七。
(63) 《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二十。
(64) 包拯撰,杨国宜校注:《包拯集校注》卷一《请依旧封弥誊录考校举人》,合肥:黄山书社,1999年,第16页。
(65) 《宋会要辑稿》选举六之一。
(66)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六之三二-三三。
(67) 《宋会要辑稿》选举二十之十一。
(68) 《宋会要辑稿》选举六之三六。
(69) 《宋会要辑稿》选举五之十六。
(70) 《宋会要辑稿》选举八之二四。
(71) 《宋会要辑稿》选举十六之三四。
标签:科举制度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