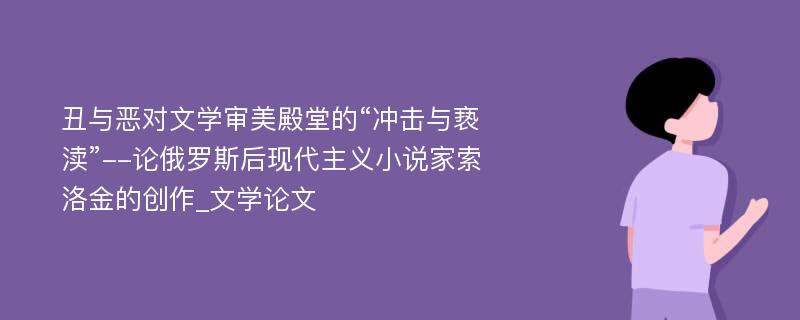
丑与恶对文学审美圣殿的“冲击和亵渎”——俄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索罗金创作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国论文,后现代主义论文,小说家论文,文学论文,索罗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5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29(2008)02-0003-07
索罗金是同时头顶“光环”与“恶名”的俄国后现代主义小说家,当代俄罗斯文坛上“天才的另类”,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事者”,几乎他的每一个行动都会引发一个事件,每一部作品都会引起一场喧嚣。
出身书香门第、大学教授家庭的“天资卓越”的青年,曾是个毒品的吸食者,而且还是在刚刚受洗、成为东正教徒后不久;十四岁的中学小男生居然在他的文学习作《苹果》中写尽了一对因排队购买苹果而邂逅相遇的男女狂郁、躁动的情欲,让同年级的少男少女新奇不已;短篇小说《萨尼卡的爱情》描叙了同名男青年在心爱的姑娘死去后的“破贞仪式”,索罗金由此赢得“恋尸癖”的臭名;剧本《地球之女》遭到东正教女批评家科克舍涅娃的怒斥,因为作品使用下流的语言糟蹋耶稣和圣母;长篇小说《蓝油脂》一发表立即遭到“抵御淫秽、捍卫俄罗斯主流价值”的青年“同行者”们①的抵制,并因此引发了一场轰动社会的诉讼官司,弄得美国国会出来要为俄国的“言论自由”说话;长篇小说《冰》入围俄语布克文学奖,却遭到索罗金的鄙弃,他声称“布克奖——这是一个尚在娘胎中已经烂朽的胎儿”。(Соколов,2006:541)
索罗金及其小说——震撼俄罗斯文坛与社会的这一文坛“奇观”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小说家及小说样式的开始,提示着一个文学新现象的生成。俄文版《花花公子》的评论称,“如果说早先的俄罗斯文学如同一个心地善良的画家,画给人们看的是鲜花盛开的林中旷地,那么索罗金的书向人们展示的却是另一种可怕的现实……”(Соколов,2005:23-24)。他的小说无法归结到传统的故事范畴中,他常常将传统文化、文学经典与生活庸常交熔于一炉,文学经典、政治领袖、文化精英成为他嘲弄、嬉笑、游戏的对象,排泄、性交、凶杀,甚至食粪、吃人都是他小说中难以或缺的情节元素。他把转述一种历史的文化话语当作小说写意的基本内容,把传达社会转型期一种尚未充分显现的俄罗斯民族的心理和情绪当成自己的使命,从而表达历史文化与社会政治霸权话语下伦理的、人格的异化,社会对于自然的和独立的人的“遗弃”。
如果要用最简洁的方式概括索罗金早期短篇小说与此前及同时代苏联小说的区别所在,大概莫过于评论界用得最多的两个词“丑恶”与“绝望”了。此前,俄、苏小说中的“丑恶”主要还在于精神层面,人物即使卑污,终究还能有清除卑污的正义与良心,还有希望在,即使现实的一切都糟透了,但还有作家的激情在,这激情本身就是人对自己、对现实的一种承诺方式。但是,在索罗金的作品中满目的丑恶,通篇的龌龊,正义与良心、希望与激情彻底地消散了。作家不动声色地将现实与人物丑陋化、粪土化、妖魔化了,而人们接受丑恶,安于丑恶,欣赏丑恶,不但连本能的挣扎式的反抗都没有,反而当作对生活与生命理解的合理、有效的“共识”。这是作家对俄罗斯文学美学传统观念的反拨,对和谐优美的俄罗斯文学审美圣殿的“冲击和亵渎”。
20世纪俄国社会理性完美的破灭,“新人”神话的破产,使得一种悲哀颓废的情绪在相当多的当代俄罗斯小说家的心中流淌,成为当代小说表现的一个重要内容。索罗金承继了现代派文学的审丑艺术实践,以一种极致的方式表现了丑恶,确立了当代小说的审丑理念,审丑理念的确立是索罗金艺术意识的基础。普希金把幸福与爱,把尽善尽美作为创作的最高原则,以情理均衡的原则实现和谐的审美理想。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都以对丑恶的否定为主旨,通过对美丑、善恶的激烈冲突,来实现崇高的审美理想。索罗金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丑恶的艺术形象作为正面对象来反映,这种丑恶不是作为美和善的陪衬,而是成为一种独立的艺术表现对象,以扭曲的、丑陋的外观形式,强烈地刺激人们的感官,激活人们麻木的感觉体验,折磨读者的审美期待。
从名字看,长篇小说《排队》似乎是一部相当生活的小说,其实不然,它充满了深刻的历史文化隐喻。商店前绵延数个街区的长长的购物队伍——对于经历过物质匮乏的中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小说的新奇之处恰恰在于作家以排队方式表达的“静候”与“希冀”成为俄罗斯民族独特的生存寓言。有人说,苏联人一辈子当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用在排队上。“排队”是作家对苏联市民生活方式的一种戏谑性的表达,也是对俄罗斯民族生存方式的一种概括。“排队”意识深深地扎根在苏联人的头脑,甚至生命基因中。索罗金说,“我之所以对排队感兴趣并非因为这是社会主义的一种独特现象,而因为这是一种独特的话语实践的载体,非文学复调的丑八怪”,“我们永远在排队等候着什么。早先是光明的未来,购买香肠,现在则期盼新的俄罗斯国家思想或是为了摆脱危机,为了繁荣,为了民主……”(Соколов,2006:549)
长长的队伍没有统一性,站队人职业各异,生活方式不同,“为了同一个目标”站在一起并不意味着有着一致的追求和同样的生命理想。他们各有各的声音,这是一种嘈杂、喧嚣,杂语共生,没有和谐、统一的“偶合社会”的表征。小说中“排队”具有一种独特的话语能指功能,但失去了共同性为所指的支撑。排队的人流中既会有冲突发生,也会有爱的萌生。排了整整两天的队伍中,一个叫瓦季姆的男人对队伍中的两个女人有过好感。一个是年轻漂亮的姑娘莲娜,两人的调情随着排队结束而结束,另一个年龄稍长,面容也娇好的柳达与他有了感觉。晚上他把她领回家中,成就了一夜欢娱。精彩的结局在于第二天一早,瓦季姆因错过了排队叫号的时间而大为懊丧,柳达却安慰他说,“你根本就不会晚的,我们今天就不卖货!”女人柳达并不以家、事业、工作为归宿,回归女人角色的表现是把性当作游戏与享乐,看作女性生命的最高追求,这是一个牢牢地把“幸福”的缰绳攥在自己手中的女人。而瓦季姆则相反,追求身心愉悦的同时还时时被生活庸常的俗念所纠缠。邂逅相遇的柳达毕竟使他有了对生存方式的一种全新的认识:排队未必是获得美好生存的惟一。在索罗金这里,排队是作为生命欲望的对照物呈现的,小说中作为一种不无荒唐的游戏式的表达——性,显然具有远远大于性的叙事意图:用它来唤起生命的“真实感”,是一种“真实的恶心”,即以催人恶心的方式来唤起生命的真实感。
长篇小说《玛丽娜的第三十次爱情》是一部“纯粹”写性的作品,写性爱对人肉与灵的“救赎”,但其中的性有着浓郁的政治、文化蕴含。
女主人公是一个年轻的女音乐教师,美丽、善良,童年时被父亲强暴。长大后,她开始放纵自己。也许是幼时的心灵创伤未能愈合,她从未在与异性的情爱中有过满足与快乐。这先是导致了她的同性恋取向,之后又促使她成了一个性冷淡者。更为奇崛的是,性爱的错乱竟然导致了她政治思想的“堕落”——性欢乐的无着导致了她从未有过的精神上的无所皈依。她开始与持不同政见者来往,参加持不同政见者的会议,散发他们的地下出版物,她甚至与他们当中的一个邋里邋遢的、用红色颜料将“臭大粪”的绰号涂抹在额头的弹唱诗人有染。她觉得生命走进了死胡同。
玛丽娜遭遇了第三十次爱情,一个名叫鲁缅采夫的男人为她开拓了一个肉与灵的新天地。这是一个与工人阶级打成一片,努力工作,热心并忠诚事业的小型压缩机厂的党委书记。在雄伟的国歌声中,在与他的性爱中,玛丽娜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了高潮与愉悦。她深深地认识到男人生理上的坚挺与思想上坚定的一致性。夜晚,她聆听他充满激情的教诲,懂得了许多政治上的道理。从此,玛丽娜开始把自己破碎的灵魂整合起来,过上了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在鲁缅采夫的调教下,女教师终于由一个放荡的女人变成了贞洁自爱的苏联女性,她彻底融入了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她参加了共产主义劳动突击队并获得了流动红旗的嘉奖,成了人们效仿的榜样。从此,玛丽娜成了一个“标准的”苏联女人,《真理报》社论的文本成为女人玛丽娜意识流动的主要内容。
小说贯穿着“性”与“政治”两大元素。显者是性,隐者是政治。生理满足的是性,精神满足的是政治。玛丽娜成了真正性别意义上的女人,但也因此失去了她作为独特女性的个性特征,最终完成了由“个性化”向“从众化”的转变。性取向的复归成了一种莫大的反讽,玛丽娜对鲁缅采夫的献身也拆解了政治的神圣与崇高。女人肉体之身的拯救是与精神之心的拯救同步实现的。具体地说,玛丽娜性取向的复位与她政治上的递进有着一种对应关系。玛丽娜的爱情与性是和她对党、国家、意识形态的爱与忠贞相对应的。是党委书记拯救了玛丽娜的性,也拯救了她的政治生命。当她的女性能力在鲁缅采夫这个男人那里获得证明之后,她也踏上了走向政治新生之途。作家通过知识女性的性史,表达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文化人与生俱来精神本质的羸弱,表达了社会和意识形态范式对个性的异化与扭曲。
小说对女主人公身处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文化语境与精神状态下的叙写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叙述文体。作者说:
这是一部关于主人公自我救赎的长篇小说。玛丽娜要从她自我个体,分裂的个性,性的不满足,非传统的取向中摆脱出来。她融进了集体的“我”中。这是一种可怕的救赎,然而这正是20世纪向人们提倡的救赎。这是关于人的选择的长篇小说:成为自我或是丧失自我。(《独立报》)
对凶杀与死亡叙述的强烈兴趣始终是索罗金小说中一个十分引人注意的现象,长篇小说《罗曼》是索罗金“死亡叙述”的经典文本,不仅是人的死亡,更是一种时代文化、经典文学神话的死亡。作者把这种死亡当作了盛大的节日和精彩的故事,寄寓着神话的再造与新生的重塑。
长篇小说的前半部分描叙的是19-20世纪之交,位于伏尔加河畔的恬静、宁谧、富有田园诗意的贵族庄园生活,庄园里的人们纯洁真诚,可亲可爱,相互的关系融洽和谐。新郎罗曼不仅杀死凶恶的大灰狼上演了英雄救美的壮举,还奋不顾身地从大火中抢救出了圣像,新娘塔基雅娜纯洁无瑕,敢爱善爱。他们青春美丽,精神崇高,爱得热烈无私。全庄园的、连农民都来参加的狂欢化的婚礼洋溢着“天下一家”的博爱精神。然而,就在婚礼的当晚,新郎却抡起了斧头,在高喊着“我爱所有的,所有的人。我希望所有的人都相互爱,所有人都像我们一样幸福”的新娘的配合下,砍杀了所有前来参加婚礼的客人,连参加婚礼后在家中沉睡的农民也未能幸免。人们无声无息地走向生命的归宿,连原因也不知道。死亡就像一张蛛网,一个作者早已安排就绪的预谋,情节悬念只是诱惑人们读完这个关于死亡的故事。索罗金还大肆渲染死亡的场面,新郎杀死并肢解新娘整整花去了小说八页的篇幅,而罗曼自戕的情景竟用了整整四十行来描述。索罗金不放过任何有关杀人的想象性细节和现实性细节的描写,用有声有色的文字来刺激读者的感官,以激发人们钝化了的对荒谬、残酷和死亡的感受。作者在让读者惊恐的同时,又欣赏和迷恋于这砍杀生命的盛景:一种对文学历史和现实的毁灭性的杀伤。
作品所呈现的,没有具体社会历史语境的温馨、祥和的贵族庄园生活是19世纪俄罗斯经典文学的翻版,思想崇高、精神圣洁的人物是经典文学形象的化身。律师、医生、教授、学者、上校、神甫、农人……小说中众多社会面具式的人物呈现出19世纪俄罗斯文学描绘的浓郁的文化氛围,俄罗斯现实主义文学的诸多传统——对风景描写的重视,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述,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关注——在小说中得到了滑稽的再现。小说中苏联时期“农村文学”的传统也未能逃脱被戏弄的遭际。死亡结局中唯独存活的一个人是农夫——“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守望者”。然而他智障,还是个酒鬼、小偷和恶棍。
索洛金在答记者问中说:“取名为《罗曼》的长篇小说试图提供俄罗斯长篇小说的一个具有平均值的范本”。(Сорокин:116)
《罗曼》中事件的发生并非是时间意义的,而是某个文学空间意义的。……对于《罗曼》而言,重要的,作为酵母的是俄罗斯文学空间,对于许多俄罗斯人来说,这一空间取代了现实。考虑到俄罗斯人总是生活在过去、将来,而从来不是生活在现实中,他们总是靠某种神话生活,而文学恰恰要求弥补现实的不足。所以我们这里对文学才有如此出奇的虔诚,文学才有如此巨大的发行量,这在西方是不可思议的。(Соколов,2005:76)
精心“再现”的俄罗斯“长篇小说”像是一个庄重的后现代的告别仪式,向曾经在俄罗斯发展道路中成为重要精神资源的现实主义文学的告别,向俄罗斯作家投入过巨大激情、创造力的一个文学时代的告别,也是文学“认识论断裂”的表征。索罗金的死亡叙述体现了他对俄罗斯文学古典人文精神的极度绝望。作家反其道而行之,混淆了创造性的想象与现实之间的界限,从而凸现了一种莫大的文学悲剧。索罗金解构并颠覆俄罗斯长篇小说艺术世界的故事本身似乎要表明经典现实主义长篇小说思想、精神、文体的毁灭与消亡,展现一个“俄罗斯文学的末日”:俄罗斯文化传统文学中心主义的终结,人道主义思想的虚妄和乌托邦,其导师功能的丧失,对文学认识现实本质可能性的怀疑。
被评论界视作索罗金20世纪90年代顶峰之作的《蓝油脂》是另一部更具“宏大性”的、融汇了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因素的长篇小说。索罗金以当今世界的经济、科技、文化发展为依托,虚构出的一部带有科幻色彩的“神话”故事,是他对俄罗斯民族文化乃至人类专制历史的探究,是对未来的一种预言性的警示,是对人类无法克服的荒谬和困境的隐喻。
这是一部兼具“寓言性”和“预言性”的小说。21世纪后半期,世界由美国的天下被“中国的天下”所取代。如同20世纪末的俄语充斥着美式英语一样,21世纪的俄语中有大量的汉语出现,不少用俄语和俄文拼写的中文写成的小说片段不啻是在诉说着作家对未来世界的一种不无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体察。“生命语文学家”格洛盖尔和他的同事,一批具有同性恋取向的科学家,在西伯利亚某地的秘密实验室从事克隆俄罗斯著名作家的研究工作,在克隆研究的过程中提炼出了“蓝油脂”——权力与自由的聚合物,一种能使人永生的具有超能量的物质。小说故事的这一主干衍生出多个情节套叠的结构。
一个情节是说,被克隆出来的作家,如19世纪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20世纪的诗人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小说家普拉东诺夫、纳博科夫等,创作了各种不同的新文本。而新文本无不是对原作家文本的一种反讽,帕斯捷尔纳克创作了咏赞女性生殖器的颂诗,普拉东诺夫的主人公坐在用人肉块作燃料的火车头上前进……故事力图说明,企图取代生活真实的文学,一旦成为千百万人认定的现实生活,那就为社会与个性的不自由提供了文化土壤。只有当一个社会中的文学仅仅是文学,而不再是意识形态范式的时候,文学才不会遏制社会与个性真正自由的发展。
第二个情节说的是,预示着给人类带来幸福与自由的“蓝油脂”被脱离现代文明、在西伯利亚种地的移民盗走,格洛盖尔和实验室的其他研究人员被杀。这批斯拉夫血统的男性生殖器崇拜者在神奇物质的作用下,靠着倒转时间的魔力,于1954年把蓝油脂送给了斯大林。此时,仍然活着的斯大林和希特勒已经结为联盟,在用原子弹打败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后统治了整个世界,正准备分配对世界的霸权。为抢夺蓝油脂两人发生争斗,斯大林把蓝油脂注射进自己的脑髓中,于是天才的能量“癌变”为一种恶的意志,一种意欲摧毁整个世界的狂想。由此开始了人类的一场巨大的灾难。
此外的一系列杂沓纷乱的情节都是第二个情节的延伸。斯大林带着全家,拿着蓝油脂来找希特勒,两个左右过人类命运的历史巨人的相遇演绎了令人啼笑皆非的一系列荒唐故事。希特勒与斯大林女儿发生了不齿于俄罗斯民族的性行为,斯大林为了确立霸权而应允无语;黑发美男子的斯大林与他忠实的战友贝利亚成了狂热的同性恋者,还与他的继任者赫鲁晓夫有染,而成了伯爵的赫鲁晓夫竟是一个喜欢吃有自虐倾向的美少年肉的魔鬼;女诗人阿赫玛托娃成了一个疯疯癫癫、匍匐在斯大林面前的老太婆,在莫斯科的一独栋别墅中,在一次几乎绝望的难产中生下了一枚枚黑蛋,吞下黑蛋的名叫约瑟夫(斯大林的名字)的胖男孩居然成了一位“大诗人”……小说的结尾是,无论是克隆人,“蓝油脂”,还是复活了的历史人物,都是虚妄的。“蓝油脂”,本意精粹的“油脂”,一种可以使人强健体魄与心智的食物,恰因是按照俄罗斯作家的精神所炼制,功效虚幻。小说中注射了“蓝油脂”的斯大林发现自己竟成了一个年轻美男子的奴仆,而这个青年恰恰是格洛盖尔的同性恋伙伴,而神奇的“蓝油脂”也不过是一件闪闪发光的斗篷,美男子穿上蓝油脂制成的斗篷只是为了出席复活节的舞会。索罗金说,“我们的作家总是追求对民众的精神抚育。而我们的老百姓靠什么填饱肚子?靠面包与油脂。而所谓的精神食粮,也就是说,是悬空的,故而我就产生了这样的隐喻。”(Соколов2006:616)
以外观论,小说似乎具有很强的故事性,故事似乎也有其背景与人物作为支撑,但读完作品,你却不知道这是怎样的一个完整故事,因为似乎所有作为悬念而引起的阅读期待到最后都是无底之谜,“故事迷宫”中缺失了最重要的东西——人物与情节的发展逻辑,所以根本构不成故事。索罗金与其说是在讲故事,莫如说他从一开始就在解构故事。以讲故事来反故事,以反故事的“后现代操作”来解构故事的“在场”,这就是小说之所以给人有神秘倾向的来由。作为集后现代主义手段之大成的这部长篇小说具有众多扑朔迷离的语义密码,融神话、口头文学、东正教、语言、多神教迷信、哲学、文化学等各种文体于一炉的文本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解析难能穷尽的密码系统。
短篇—长篇,长篇—短篇,短篇—长篇的体裁转向既是索罗金的后现代主义小说体裁的探索之路,更是他文化解构的心路历程。《盛宴》是此后小说家最负盛名的短篇小说集,被批评界视作2000-2001年度十佳图书之一。十三个“天方夜谭”式的故事独立成篇,构成了一个“吃”主题的“系列性长篇”。我们不妨用梗概的话语方式来描述其中最具特色的几篇小说的故事化外观。
《娜斯佳》上演了一场否定尼采哲学的父母与好友一起同食亲生女儿的“人肉宴”。“被吃”成为美少女娜斯佳十六岁的成年仪式,用俄罗斯式的烤炉烹制、品尝、食用、欣赏女孩肉体的美味成为小说的故事主体,被作家高度“精致化”和“艺术化”了。而故事发生的时间正是尼采辞世的那一年,“离20世纪只剩下半年的时间”。《合成人》中的主人公是三个同时操用俄、汉、美国英语三种语言的未来“合成人”,他们分别是二十四岁的男青年、十九岁的姑娘和十五岁的少女。他们奔赴餐厅、夜总会,乘坐出租车,飞向天空,把玩的是食用经典文学作品人物的“内脏”的游戏。文本涉及的作品有《罪与罚》、《红楼梦》、《丧钟为谁而鸣》、《战争与和平》等,三个主人公从各个器官钻进主人公的身躯,食尽其内脏,不断地排泄出粪便,任其皮壳随处飘落。《马肉糊糊汤》的时代背景是从勃列日涅夫死去到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病故,从苏联解体到1993年俄罗斯的动荡岁月。俄罗斯姑娘在一个前劳改犯、被她叫做“马肉糊糊汤”的几近疯子的男人的诱导下,只能对着空盘子进食,而无法消化普通食物,以一种模仿吃的行为,一种对食物的精神满足来替代生理需要。《灰烬》讲述了在莫斯科鲁日尼基体育场举行的、由俄罗斯总统主持的一场体育比赛。这场“全俄脓血角逐冠军赛”被总统誉为“融合了俄罗斯壮士角力与东正教伟大苦难的民族文化传统的标志与民族振兴的象征”。两个身高两米多、体重二百多公斤的满身脓疮的力士,在痛苦的哀嚎中被剥去粘连着脓血的披风,赤裸着相互击打疮痂。拳台上脓血迸流,拳台下呼声雷动。随后冠军被一批凶恶的罪犯炸死,他的“里脊”肉被割下运到日本烹制,然而连同用男人其它器官制成的香气扑鼻的美味终被焚毁,成为灰烬。
上述由作家精心策划的一个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构成了“吃文化”的奇观。小说家以“吃”说事,讲述的却是一种离奇的文化寓言。它们固然可以被看作是对“食人”的20世纪的隐喻(《娜斯佳》),对俄罗斯文学和人类文化的反讽式的寓言(《合成人》),对时代文化荒漠、精神贫乏的烛照(《马肉糊糊汤》),对流淌着“脓血”、已呈腐态的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昭示(《灰烬》),但同时,这些隐喻、寓言、烛照、昭示并非单纯意识形态的,并非批判现实的。小说主要的不是对现实的批判,而是对现实的新的阐释;不是讽刺,而是反讽;不是社会心理的分析,而是哲学的与美学的解构。索罗金在用一种荒诞的形式表达他对社会悲剧真相的大胆无畏的追思,对社会病态DNA的追索。当索罗金放弃了对各种丑恶现象的社会历史成因的探究时,他的这些叙述就成了俄罗斯民族乃至人类的一幅幅末世图:一个绝望的、无法救赎的世界,一群理应遭到天谴,而事实上也在遭到报应的族类。
索罗金对人类生存的苦难是高度关注的,对文明秩序的现实是憎恶的,他没有,也无须探讨什么样的政治文明与社会秩序才能既符合人的天性,又能体现出对于权力的足够警醒和制约。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在索罗金看来,那就是人类的意识既是追求理性的,也是趋向本能的,两者的冲突便构成了人类生存永恒的,而又无法消释的矛盾,实现两者的和谐与统一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共时性命题。索罗金说:
抑制人天性的文化的(不是宗教的)努力从康帕内拉②、卢梭开始,经由尼采一直延续到我们这一世纪。在20世纪,人们很快就发现,集体主义的方式无法造就新人,因为人的天性要比集体强大得多,一切极权体制都被这一天性击得粉碎,人尽管已经被扭曲不堪,但还是像先前一样,仍然是聪慧的。……我想,人类将追求与其他的、非人类的共生共存。我们在思想意识上已经有了这种准备。后现代主义和新的法国哲学,对集体主义和实际上对人没有帮助的弗洛伊德的失望为我们做好了这样的准备。(Тух:288)
作家同时又始终声称文学只是文本,而不是生活的教科书,只是自我实现的一种方法。他说“对于我来说,艺术不是什么,而是如何”,生活与艺术完全是两码事。(Соколов,2005:35)“文学是一个自由的动物,它应该在它喜欢的地方进食和拉屎”,(Соколов,2005:32)“我深信,真正的艺术家,真正的创作者应该并可以允许自己在纸上做一切事情,否则就没有意义坐下来写作”,“我以为,纸上不应该有任何的禁忌”。(Соколов,2005:107)。作家的这一系列论说表明,文学艺术形式的“革命”是他创作追求的惟一目标。
任何一个世纪末都会产生一种灾难感。20世纪末出现了某种接受疲劳,人对自己的疲劳。……文化成就不再刺激我们的神经末梢,不再引发一种先前伟大的文化作品给予我们的那种忘我的感觉。“人为的,过分人为的东西”让人感到厌恶。(Тух:284)
寻找新的文学话语的表达方式是后现代主义小说家的共同追求,而索罗金旨在消除审美接受疲劳的艺术探索应该说是有其积极意义的,因为它符合了文学的“陌生化”本质。然而,对传统人文精神和文化秩序从根本上的怀疑,对一切人文理想和道德价值的彻底否定导致了这位后现代主义先锋小说家永无休止的反叛和终无定所的漂泊。索罗金的小说创作在哲学层面是反中心的、反理性的、反整体性的,在文化层面上是反历史、反体制、反传统的,在美学层面上是反美、反规范、反诠释的,在文本层面上是反体裁、反结构、反时空的。他拒绝接受既往文化所提供的任何意义与价值规范,却又无法为当下的世界确立意义与价值,他始终在实施着政治的、文化的、道德的解构与颠覆,他因此只能在解构与颠覆的游戏中永无止境地漂泊。
注释:
①20-21世纪之交一批俄罗斯热血青年组织的政治团体,旨在抗拒对俄罗斯优秀文化传统的背叛。据传,这一团体有克里姆林宫的政治背景。
②17世纪意大利哲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