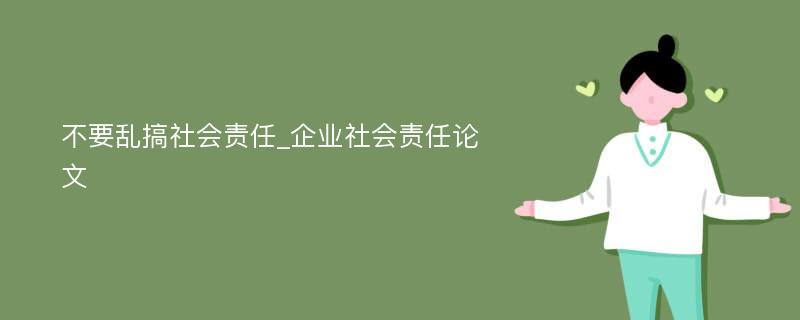
企业不要乱揽社会责任,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社会论文,责任论文,企业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企业家的最基本责任是为股东盈利,因此,企业家不要随便把社会责任往身上揽,政府也不要把社会责任往他们身上推。现在各方越界争抢责任,导致了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配的混乱。而对责任的争抢,往往正是为了争抢本来不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无论是企业管理还是社会管理者,都经常会提到“责、权、利”,责在这里排在第一位,这意味着只有先确定责任,才能确定其用于履行责任的权力及其所应得的利益。也就是说,任何一个需要合作的事情或组织,确定责任边界是其成功的前提。
抢责源于抢权
中国很多领域出现的混乱,根本原因都在于未能厘清相关者的责任界限。各方越界争抢责任,抢到最后分不清是谁的责任,也就导致了权力格局和利益分配的混乱。当然,反过来也可以认为,对责任的争抢,往往正是为了争抢本来不应该属于自己的权力和利益。
比如,自从提出“经营城市”的概念后,市长们就越来越像总经理,他们每天研究的重点不是政府本来应该做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和公共政策,而是如何招商引资,如何促增长,控通胀;教授们越来越像议员,更多的精力不是用于教授学生、搞研究,而是忙于走穴:学生自然也就越来越不像学生,而像党校培养的青年干部。为什么中国人做什么不像什么?因为他们承担的责任不像是自己的责任。
那么,企业家本来的责任是什么?熊彼特认为,是为股民赚钱,或者说是为股东盈利。我认为,这至少应该是企业家最主要、最基本的责任。因此,企业家不要随便把社会责任往身上揽,政府也不要把社会责任往他们身上推。
乱尽责等于不负责
有些官员、学者以及媒体认为,企业也需要为控制通货膨胀尽一份责任,因此在经营成本上涨的情况下,也应该尽量不涨价,甚至某些企业家也发表过类似观点,并做出不涨价的公开承诺。我非常钦佩这些企业家的政治觉悟高度,但是我认为这是一种对企业和股东们不负责任的行为。因为,在成本上升尤其是刚性成本上升的时候,只有通过涨价才能保持利润率,才能给股东创造足够的回报。否则,一方面物价上涨,一方面企业利润下降导致股价下跌,股民们岂不雪上加霜;另一方面,企业利润和现金流下降,必然导致企业无力提高员工收入甚至减薪、裁员,那么这些员工靠什么抗通胀?此外,企业利润下降,必然导致缴税减少,政府税收少了必然削弱对低收入阶层的帮扶能力,中央政府收入少了必然导致赤字增加,只能靠印钞票填补,那么岂不进一步推动了通胀?
因此,企业在成本上升的时候不涨价,不仅是对股东、员工的不负责任,也是对中央银行不负责任。
根据经济学基本原理,通胀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就是货币超发;所以,政府控制通胀的根本措施也只有一个,就是紧缩银根。但这次央行在紧缩银根方面,可谓是犹犹豫豫,走走停停,以至于造成通胀预期的长期无法控制。于是政府就把央行的责任推给企业家:不仅呼吁企业为尽企业责任而不能涨价,还直接祭出准行政手段——约谈,谁涨价就约谈谁。既然政府把央行的责任推给了企业,那么如果企业真是帮助政府来控制通胀,自然就是对央行的极其不负责任,因为这使得央行会认为滥发货币没有关系,反正有人帮着控制。
因此,我们不能把本来各守其责的责任体系打乱,而是应该让他们各自回到本来的责任与权力位序上。比如,一个教授就应该老老实实地在书斋里研究、在课堂上授课,到社会上做调研而不是在社会上走穴。当然,教授走穴也是迫不得已,因为工资待遇太低;因此,如果政府加大对教育部门的投资,给教授们涨一些工资就可以避免这种事情。但现在教授们走穴就等于让社会与教授们承担改善学者待遇的责任,使得政府愈发认为自己不需要增加教育投入,从而导致了恶性循环。
请市场分配责任
除了通胀,绿色低碳与技术创新是中国经济的另外两个热门的话题。但就中国经济目前的状况看,我同样认为其主要的责任不在企业家。
因为企业家只能是把股东盈利视为第一目标,所以,只有也只要外部环境使“绿道”有利可图,企业一定会走绿色之路,一定会为此开展创新。现在一些企业之所以不注重环保和创新,正是因为外部环境不对,而这个责任只能在于政府,也有一部分责任在学者(因为学者没有给政府提供很好的政策建议,但主要责任是在政府)。这主要体现在中国政府的政策目的和政策手段的不一致,甚至可以说是相互矛盾。
绿色经济,不仅是中国,也毫无疑问是所有国家的长远发展目标。但是我们的政策手段却不是绿色,而是“黑色”的:所谓绿色,就是低能耗、低资源消耗。但是,由于市场机制的缺失,中国现在不能充分通过市场调节进行生产要素的配置。我们的水、电、煤、油的价格都是政府管制,这些管制的价格不能够真实反映资源的稀缺性。换句话说,在鼓励经济增长的指导思想下,重要资源和要素的官方定价统统偏低,这样就鼓励企业大量地消耗资源、消耗能源。
绿色经济的一个重要指标和特点是经济结构越来越轻,但是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在过去十年间,重工业总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上升了10个百分点,导致经济结构越来越重,能源消耗、资源消耗越来越多而不是越来越少。于是,中央政府制定的节能减排指标只能靠拉闸限电来实现,而不能够靠企业自觉的行为:在价格信号的引导下,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减少能源资源的消耗。而实现后一种情况的前提,就是创造一个更为开放的市场,让市场来决定资源、能源的价格。而创造这个外部环境,无疑是政府而非企业的责任。
同样,如何控制通胀,中央银行应该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它的职责,继续紧缩银根;而在物价上升,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发生困难时,政府则应该承担起扶贫救困的职责,比如向低收入阶层提供帮助和补贴,而不是拉闸限电,约谈企业。这样只能把各自本职的责任全都搞乱。
那么,如何才能厘清市场各方的责任界限?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尊重和顺从市场规律,尤其是要认识到市场应该发挥比政府更大的作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企业是主语,社会责任是宾语,千万不能喧宾夺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