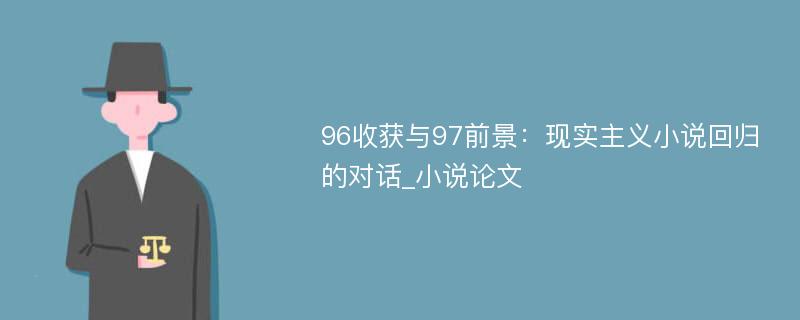
’96收获与’97展望——关于“现实主义小说回流”的对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主义论文,小说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时间:1997年1月21日上午
地点:北京魏公村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
一、’96现实主义小说创作的扫描与评估
肖:所谓现实主义的回流或“冲击波”已然成为了1996年中国文坛的一个最热门话题。首先是何申、谈歌、关仁山“三驾马车”一系列中篇小说有如集束手榴弹般地抛出,一下子就吸引了读者和论家的目光。何申的《穷人》,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九月还乡》,谈歌的《大厂》、《〈大厂〉续篇》等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作。
朱:其实,这个“冲击波”还可以追溯到更早,1995年何申的《年前年后》系列就已经拉开了序幕,而且,我们稍作追根寻源将不难发现,“现实主义的回流”也罢,“冲击波”也罢,它的蓄势发端于八十年代末的“新写实”小说。刘恒、刘震云、方方、池莉、刘醒龙、毕淑敏、阎连科等人的创作一直保持了比较强烈的现实品格。特别是刘醒龙的《凤凰琴》、《威风凛凛》等直面当下农村现实生活的作品,无疑对“三驾马车”具有直接启发作用。割断历史的连续性,孤立地看待’96现实主义回流是不够全面的;同样,仅仅把现实主义回流完全归功于“三驾马车”的崛起,也将是片面的。上述诸位中不少人在九六年度都有不俗的表现。比如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和《挑担茶叶上北京》,较之以前就有了一些变化,有了一种大文化的背景和思路。比如阎连科的《黄金洞》,在故事性中又渗透了一种寓意性,恰如题目所示,他企图概括当下社会现实中金钱和物欲对人性的挑战。还比如池莉的《午夜起舞》、毕淑敏的《源头朗》等等,都是不可忽视的现实主义之作。
肖:我完全同意你这个看法,纵向而言,“三驾马车”们接续与强化了“新写实”的平民意识与现实精神,而且也汲取了后者的不少写作手法与艺术经验。横向而言,除了“三驾马车”及上面提到的作家之外,还有一批老中青作家也都不约而同地汇入了这股现实主义的潮流之中。比如老作家李国文的《涅槃》和《当令》、中年作家王安忆的《我爱比尔》、梁晓声的《学者之死》司马敦》、李贯通的《天缺一角》等等,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品格,只不过他们关注与表现的是经济转型期中知识分子的失落心态和变异的众生相,传达出了一种文人的尴尬与无奈。与此不同的是李佩甫的《学习微笑》,他从人物命运出发写工厂改革进程中的艰难和工人生存景况的窘迫,但却写得比较超越,在我个人看来,是同类题材中的佼佼者,将工厂改革小说推进到了一个新境界,读来有柳暗花明之感。
朱:说到这儿倒使我想起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徐坤在九六年度的“转向”。此前她一直是比较具有先锋色彩和个人化写作倾向的,但去年她却突然写出了像《沈阳啊沈阳》、《四月的诗篇》、《狗日的足球》这样关注工人和底层普通人物命运的新变之作,与人们印象中的“徐坤风格”大异其趣。尽管她的这种“转向”是否成功、得失如何,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讨论,但至少说明了一点,即现实主义冲击波有挡不住的魅力和诱惑。
肖:这种诱惑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现实生活的召唤,二是当下写作的魅力。但作家们也不宜因此而“硬转”,还要因人而异,扬长避短。我个人觉得徐坤转得就有点“硬”,她对沈阳大中型企业的了解多少还有点走马观花的意思,至少不如她对文人圈子那么熟悉,她的新作虽然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但在艺术上很难说对她此前的创作有什么超越。她这么一味“转”下去有两种可能,要么是开出一片新天地,要么就是失去自我。相比较而言,我认为迟子建在关注现实生活与保持个人风格的关系上处理得更为自然流畅一些。她的《白银那》、《雾月牛栏》,既保持了一种古典情调,而又比较深刻地揭示出了调整之后的生产关系,对于传统道德和价值观念的剧烈撞击。同样的特点在新派小说家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中也有所体现,由于在先锋化书写中融入了现实生活,跟读者的沟通也就更宽泛得多了。
朱:从艺术的精练和老到程度看,我比较推重李贯通的《天缺一角》和李国文的《当令》,他们对所描写的对象都非常熟悉,但却没有像“三驾马车”们那样对人物和生活采取“散点透视”与平面罗列的写法,而是有高度的提炼和非常艺术化的处理。前者在一块古碑石上面浸润了文化和人性的思考,把这一个“道具”的作用发挥得淋漓尽致,而且在人物性格的刻画、意境的营造、语言的表达方面都做得比较到位。后者则是一个非常地道的传统经典式短篇作法,从开篇的悬念到最后的抖包袱,一气呵成,干净利索,很有点欧·亨利的遗风。显示了老作家的功力和修养。与他们相比,“三驾马车”们的东西就显得比较糙了。
肖:在横向扫描’96文坛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支生力军不能够忽略,与上述出道早的著名或知名作家相比,他们的名字也许还不大为人们所熟知,但他们的作品以扎实而厚重的生活质感显示了自己的特色和潜力。比如丁凯的《荣调前后》、彭瑞高的《本乡有案》、张继的《黄坡秋景》、刘益令的《仕途》、柳建伟的《都市里的生产队》、谢志斌的《扶贫》、远山和纯晖的《困惑》等等。
朱:我还可以补充一个方面军,即军队作家。多年来,对现实军营生活的疏离始终是困扰军旅文学振兴的一个难点。但近一二年来这种状况有所改观。仅就《小说选刊》所选载的作品来看,就有赵琪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张惠生的《旱舟》、石钟山的《5182兵站》等等。他们的风格追求也许各不相同,比如赵琪和石钟山的空灵、何继青的深沉、张惠生的扎实、黄国荣的高亢等等,不同的声调组成了一支现代化进程中的人民军队进行曲。
肖:如此说来,在去年纪念长征60周年背景下出来的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也不能不提。比如邓一光的《大妈》、赵琪的《苍茫组歌》等,虽然写的是历史,但表达的却是当代人的当代思考,与前辈作家王愿坚等人写革命历史大不一样,在揭示那场战争的伟大性的同时也没有省略其复杂性和残酰性,在塑造人物英雄气慨的同时也没有忌讳人物的平凡心态和七情六欲。以当代眼光重新审视历史,应该说也贯注了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朱:还有军队青年女作家刘静的《寻找大爷》,也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通过“寻找大爷”寻找的是一种在极左的斗争和政治运动中失落的人情和人性,它无意中触及了一个严峻的革命和温和的人道主义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这样一个敏感而深刻的命题。只可惜挖掘还不到位。
肖:总体来看,在九六年的中国文坛上,虽然还有“边缘化”、“私语化”、“通俗化”等多种写作的继续活跃,但就中短篇小说创作而言,现实主义的回流已经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朱:那么,“三驾马车”作为其中最为醒目的现象,我们是否可以进行一点稍微展开深入的分析,探讨一下他们崛起的原因以及目前创作中存在的不足呢?
肖:这个话题很有意义,我们不能满足于已有的成绩与收获,如果能从中找出一些带有规律性和普遍性的问题,不仅仅对于“三驾马车”会有所启示,也许对整个现实主义创作的进一步深化与拓展都能有所助益。
二、“三驾马车”们勃兴的原因、局限及其潜在危机
朱:在我看来,“三驾马车”之所以能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引起文坛的广泛关注,主要有两点原因。第一点是他们的集群出现方式,互为呼应与支撑,有一种集团效应,多少给人一点流派的意味,形成了一种势头,一种气候;第二点也是更为主要的,即他们共同表现出来的强烈关注现实的当下品格,而且把目光和笔触直接切进了当前改革的两大正面战场:大中型企业和基层农村。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说具有填补空白或断层的意义。众所周知,由于域外现代文艺思潮的影响等诸多原因,八十年代中期的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和探索文学先后转入了历史、文化、哲学追问和形式探索,这对中国小说的现代化进程和审美化追求无疑产生了极大的推力,但它付出的沉重代价却是逐渐疏离了现实,远离了读者。今天现实主义创作的回流正是对这种倾向的一种反弹。而且,八十年代出道的作家,在一度创作喷发期过后,生活积累开始告罄,尤其随着名气的增大和地位的上升,也有逐渐浮出生活水面之虞,或者叫做对生活的深入不够。具体表现在两个向度上:一是对底层生活深入不够,二是对改革前沿或中心深入不够。这也是导致他们创作“转向”的原因之一。而“三驾马车”们与他们相比最大的优势就在于生活积累的丰厚。
肖:尤其是对当下基层生活的稔熟,已为他们的前代作家所不及。这跟他们仍然生活工作在基层或生产第一线直接相关。比如张继,至今还是一个地道农民,谈歌则始终处在工厂基层,何申利用工作之便,几乎跑遍了承德地区的所有乡镇。所以,他们处于能迅速敏锐地观察与把握当下现实生活进程的最佳位置,能深入细微地体察民情,就普通百姓所关注所焦虑的问题及时地作出文学反映。
朱:换一种说法,“三驾马车”们目前正处于创作的“一度喷发期”,虽然他们也汲取了此前不同文学探索阶段的积极成果,但是严格说起来,除了生活本身的优势之外,他们在思想深度方面和艺术水准方面,并不能说对前代作家有多少超越之处。比较而言,如果说前代作家有对生活深入不够的问题,他们的问题则在于对生活的超拔不够。这一点具体来说,他们多少也受到“新写实”小说的某些负面影响,如“一地鸡毛”式的琐碎、“不谈爱情”式的缺乏激情等等。对这种现象,我曾经概括为“四多四少”,即多深刻的调侃而少崇高的呼唤;多冷静的描写而少激情的投注;多世俗的生活而少理想的光照;多生动的人物而少典型的塑造。
肖:对此我也深有同感。虽然他们的作品比之“新写实”更加强化了现实品格与理想精神,但是平面罗列生活现象的弊端依然随处可见,包括写得比较好的作品如《分享艰难》、《大厂》等等,都存在这个问题。作者还未能站在时代的美学的哲学的高度来鸟瞰生活、穿透生活、以小见大,反映出生活深处所蕴藏的社会变革的心律与脉动。此外,对人物的散点透视方法也障碍了典型人物的塑造,仅此而言,恐怕还达不到蒋子龙时期的高度。
朱:格局狭小是他们的普遍问题,看不出大气象、大手笔的苗头。而且他们美学目标的定位还比较暧昧,风格追求的界限也比较模糊,个性化色彩不甚鲜明与强烈,彼此之间的风格距离不大,掩盖其作者名字,你将不容易判断谁是谁。语言质地也常常显得粗糙。
肖:造成这种种缺憾的原因,除了他们在思想、艺术、学识诸方面的准备不足之外,我想还有很具体的一条客观原因就是近一个时期以来写得太多太滥。由于被各刊物普遍看好,组稿、约稿、催稿、逼稿的情况可想而知。加上多少带有商业化的“炒作”,也使他们难以自持,穷于应付,疲于奔命。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开始出现重复:或者自己重复自己,像谈歌;或者相互间交叉重复,像关仁山的《大雪无乡》与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其人物设置、矛盾冲突都不无相似之处。
朱:还是要讲究精品战略,还是要提倡大气追求,还是要鼓励厚积薄发。在当前现实主义热潮中,我觉得“三驾马车”们自己应该降降温,冷静下来认真反思与检讨一下所走过的创作道路,注意借鉴吸收其他作家的成功经验。比如同样是写改革,周梅森的长篇小说《人间正道》为什么就显得大气磅礴;李贯通、李佩甫近年来主要精力都放在长篇创作上,为什么偶尔出手一个中篇如《天缺一角》和《学习微笑》都是精致独到而又韵味绵长。除了一个功力的问题,恐怕还有一个创作心态和状态的问题。不能太浮躁太急躁。
肖:当然,“三驾马车”自有他们的贡献和意义。由于他们的出现,给当前文坛注入了生机与活力,并以他们的崛起为醒目的标志,宣告或预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回流与繁荣。这一切都是人们有目共睹的。但是也不能因此就将他们放到一个不恰当的高度,冷静、客观而理智地给他们一个定位是必要的。尤为必要的是实事求是地指出他们的优势与局限以及存在的问题,以利于他们更加长远的发展,这是对他们负责任的态度,也是对我们文学事业负责任的态度。
朱:是的。爱之愈切,责之愈严。正是因为对他们寄予厚望,我们才希望他们对已然暴露的种种不足引起高度的警觉。我最担心的问题是,一旦当他们把生活的积累写完或者日渐从生活中浮出水面,也就是说“一度喷发期”完成之后,而思想、艺术和学识修养又跟不上去,他们的创作前景又将如何?再换一个方式发问,随着现实主义的回流和不断走向高潮,他们是可能继续走在潮头上引领潮流呢,还是难以为继、成为倏忽一闪的流星呢?这将是他们面临的严峻考验,也是他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的潜在危机。
三、’97现实主义创作发展的几种可能
肖:不管“三驾马车”们对以上问题能否警觉、克服和改进,在新的一年中,即使是依靠一种惯性滑行,他们也还会继续走俏,继续“当令”。这是社会的需要,阅读市场的需要。但是,由他们独领风骚的局面将会被打破,可能出现“皇帝轮流坐,明年到我家”的新格局。比如一批中老年作家可能会从长篇热中脱身出来参与中短篇创作。因为现在长篇过热并不正常,据说95年突破了700部,每天以两部的速度出版,质量大为可疑。李国文就说过,现在似乎人人都在写长篇,这实在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从精品战略来看,九七年的长篇热可能降温,这样就会有一批中老年作家腾出手来以中短篇创作介入现实。而且,长篇中也可能出现部分反映现实生活的力作,以更加浩大的声势来为现实主义回潮推波助澜。
朱:我估计情况没这么简单,长篇热恐怕还得持续两三年。“长篇运动”一哄而上,实际上有悖于精品战略,也是违反艺术规律的。长篇小说不是人人都能写得了的,更不是人人都能写得好的。有的作家就只适合写中篇或短篇,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而是一种双向选择,作家选择体裁,体裁也反过来选择或制约作家。但要认识到这个简单的道理有时却必须付出实践的代价,如果相当多的作家作品,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两方面都碰壁之后,长篇热就有可能从总体上冷却,出现理智的调整和作家的自我重新定位。当然,我这样的判断并不排除仍有一部分中老年作家坚守中短篇阵地或者偶尔杀一个回马枪。比如汪曾祺、林斤澜就一直在短篇领地里孜孜以求,李国文也主要是写中短篇,而《小说选刊》第一期刚选发了张洁的中篇新作《梦到好时成乌有》。
肖:对,张洁的这个中篇可以说是厚积薄发,发现了作家新的思考和探索。另外,叶蔚林的中篇《秋夜难忘》,描写文革动乱年月中普通百姓之间那种相濡以沫的感情,写得很动人。这批作家艺术修养日臻炉火纯青,再加上对生活的沉淀,一旦出手,肯定不俗。如果有他们的加盟,九七年的中短篇将更加看好,从张洁、叶蔚林的新作中可见端倪。
朱:这一点我无异义。但具体分析来看,我认为更主要的生力军恐怕还会是新人。这是因为:其一,新人都身处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对现实的感应必然快捷。其二,在他们驾驭不了长篇的时候,他们一般靠中篇来打天下。比如像韩东、何顿、邱华栋、鲁羊、朱文、张旻、述平、刁斗、东西等人的创作,从题材到人物一向都比较边缘化,他们本身在当前文学格局中的位置也是比较边缘化,那么,他们在新的一年中会不会发生像徐坤那样的变化,感应现实的召唤,从个人化、边缘化的书写中走出来,也来关注一些平常百姓感兴趣的问题、事件或人物,从而以更富于现实主义精神的风貌来重塑自己的形象呢?
肖:完全可能。江苏青年作家祈智的中篇《亮相》,猛一看,跟刘醒龙、何申的路子基本相似,写的是变革时期农村中的“官场现形记”,写得也非常生活化,但他又不是按那个路子一写到底,他给人正面、积极的东西更多一些,塑造了一位优秀县委书记形象,同时又避免了类型化和公式化,显示了一种新的色彩和生机。而另外有的青年作家则调整了自己的艺术参照系,注意从古典文学传统中汲取营养。比如广西青年作家李冯的《卖油郎独占花魅》和《墙》,两篇作品都是以现代生活和意识来重新诠释古典,显得别具一格。
朱:我看《小说选刊》今年第一期选了一个叫《出手如梦》的中篇也有这种古典意味,从意境到语言都可读出古典文学的浸润,但贯穿小说的情绪线却是意识流式的、梦幻式的,这好像也是一个青年作家写的。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进程总是以西方或拉美文学为参照,而很少有人借鉴与学习自己的传统。要么是非此即彼,或者一味追踪西方或者一头扎进古典,像《废都》那样的完全倒退到明清小说的叙事策略和语言表述。能不能走一条兼收并蓄的道路,中西融会的道路?当然,要这样做,大多数青年作家首先要补一补中国古典文学的课。
肖:这也是一个课题,我们很多青年作家对古典文学是缺乏功底甚至毫无修养的,要写出中国气派的优秀之作来,不补补这个课恐怕也不行。这也是今天现实主义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营养源。
朱:我们说来说去,话题似乎大都围绕着中篇转。事实上,新人靠中篇打江山,中老年作家靠长篇守江山,而短篇小说无形之中被冷落了,这是九十年代区别于八十年代的一个新现象,短篇已不再受重视了,不能再指望一个短篇就成名,因此我们也很少有人像契诃夫或者汪曾祺那样一辈子致力于短篇追求,而常常是利用一点中长篇的边角料来写短篇,这个情况你怎么看?九七年的短篇创作能有新的转机吗?
肖:短篇创作确实不太景气,但也不必过分悲观。九六年还是有一些给人印象深刻的作品,比如李国文的《当令》、史铁生的《老屋小记》、迟子建的《雾月牛栏》、阿成的《小酒馆》、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等等,都还不错,实际情况应该说比舆论和批评界评价的要好,只不过人们把它忽略了。短篇不能像中篇那样常常可以改编成影视作品而扩大影响,这也制约了它的传播。但这个现象已经引起了大家的注意,《北京文学》、《滇池》等刊物都在采取一些举措以图振兴短篇。
朱:今年《解放军文艺》第一期也重点推出了陈怀国的短篇三题,据说这是一个全年性计划。我在《西南军事文学》上也主持了一个“军事短篇小说精选”的栏目,第一期也组发了余飞、俞进军等军队新人的几组短篇。看来振兴短篇也是普遍的呼声。如果再恢复由你们刊物组织的全国短篇小说评奖活动,将对短篇繁荣起到一定的导向和刺激作用。
肖:总之,在社会生活的感召下,九七年现实主义潮流的进一步高涨是可以期待的,你以为如何?
朱:我的总体判断是,经过九十年代前半期商品大潮的洗礼和经济转轨的动荡之后,作家们已经重新获得了一种平静与明彻,找到了回应现实挑战的勇气和逼近世纪之交的紧迫感,渐渐地凝聚起了一股精气神准备发起新的冲刺。这可能是结束多年来文学低迷与徘徊的一个契机,而现实主义则正是文学突围的一条生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