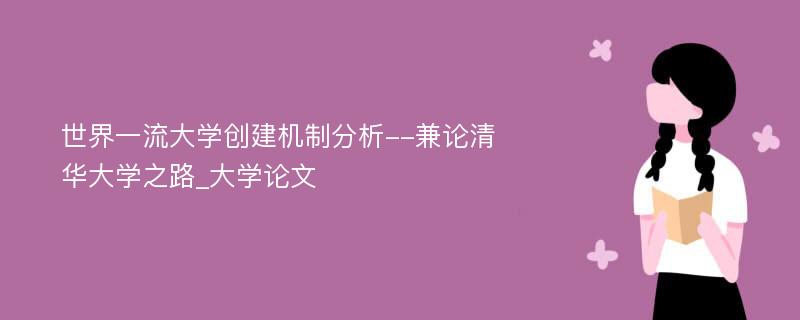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机制分析——兼论清华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清华论文,机制论文,世界一流大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519(2002)06-0028-08
高等教育领域目前最热门的话题之一便是创建世界一流大学,清华自在候选之列。应该说,一所没有理想的大学算不得好大学。只是,在我们开始埋头苦干之前应该弄明白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大学是怎样产生的?并以此来判断我们所定的目标是不是合适,我们离目标还有多远。
一、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知识论的分析
在回答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之前,我们必须先弄清什么是大学。
众所周知,大学是实施高等教育的社会机构。如果我们以金字塔来描述整个教育机构体系,则大学是居于顶端的一类。不过,在我国的高等教育范畴内,除了各种类型的大学、学院之外,还有一个体系完整并且相对独立的科学院系统。它在从事研究的同时,也进行研究生的培养。而且科学院系统的地位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还在大学系统之上。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新中国建立时,国家对知识领域的活动旨在进行重新规划。各大学的顶极人才被集中安置在新创立的科学院的各专门研究所里,被赋予各领域内知识创新的使命;大学则被规划为向学生传递各专门领域高深知识的社会机构。也就是说科学院系统在国家的严密控制与导向下对知识体系进行整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大学系统则向各部门输送大量专门人才。这种体系在短期内而言,能使国家资源得到更集中的使用,既在尖端科学与技术上有所突破,也在工业化的大平台上得到更多专门化人才。当然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后果,即新规划实际上确立了国家在知识的社会性使用上的垄断权。
客观地说,建国后的几十年既是我国大学教育迅速扩大规模的时期,也是我国高精尖端技术成果累累的时期。正因为如此,中国模式在70年代作为模范被世界银行所激赏并向整个第三世界推广,一时被认为给死气沉沉的世界教育体系带来了一缕清风。(注:Pepper,Suzanne.Radicalism and Education Reform in 20th-Century China:the Search for an Ideal Development Model.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6.Refer to the introduction part.)但是由于毛泽东对教育过于激进的理解,及由之而来政策实践,导致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教育体系的崩溃,大学系统也未能幸免。
这一体系有一定的适应性的社会合理性,但也存在两个根本的问题:(1)它过细地分割了知识的领域;(2)它割裂了知识的传递与知识的创新这两个本来有机相联的过程。而这两点都直接导致一个后果,使得整个知识体系的活动很快便失去活力和后劲。这便是威廉·冯·洪堡在他那篇著名的关于创建柏林大学(他称之为“柏林知识机构”)的建议书所论及的,如果没有知识的创新,那么知识的传递将变得毫无生气。“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洪堡从知识体系自身内在的要求提出,作为传统意义上的高深知识传递与讨论的大学机构应该在系统地进行知识创新的基础上传递高深知识,以维持该机构不息的生命力。这便是今天我们所说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如果说新中国创建的科学院体系在缩小规模并实验室化运作之后,仍非常有存在的价值;那么新中国所创建的大学体系在今天则必须有一个格局上的调整。综合化、研究化是必然的方向,但做到这两点却又未必然会产生出世界一流大学。事实很清,柏林大学模式一经产生,模仿者如云,但如今多少淹没于平庸中,那么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呢?
虽然我们不能明确指出哪些大学位列世界之首,因为关于大学的评估即使是在同一社会文化体中,也是个复杂的问题(注:在美国,他们有一些非官方的学校认证机构,通过同行评估等主要方式,对学校的绩效进行评估和监管。他们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指标体系,有兴趣的读者可参看他们的报告书,例如Annual Report of the West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Schools and Universities.),遑论对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大学做一比较与判断。不过,撇开具体评价,我们从知识论的观点出发,还是可以得到一个关于“世界一流大学”的理解,那就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进一步加快,正在整合的不仅是世界的市场,还有不断突破语言障碍的人类知识体系。而有一些大学,不但对这个日渐整合的知识体系有结构性的贡献,比如通过生成新的学派,研究范式(paradigm)或是通过开发新的研究领域从而“引领”整个人类知识体系的发展;而且经由培养出高素质的人才(即知识的载体)从而在不同的领域内“引领”人类的实践。简而言之,“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的获得就是在人类知识体系内领导位置的确立,和由此产生的对人类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多领域的辐射影响。在一些权力系统开放的社会中,大学还对知识的社会性运用进行规范与引导,而且这个趋势正在不断地加强,人们称此为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历史地来看,大学作为一个知识的场所,经历了从对自身社会的知识体系进行整理,传递与丰富,到不断融入整个人类知识体系并进行传播与创新的发展过程。“世界一流大学”称谓的产生其实就是这一全球化过程的结果。
大学在欧洲产生的初期,完全是国际性的,但在民族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大学日益成为民族和国家的机构,自此,也就很难说有什么“世界一流”的大学。不过,在大学民族化的同时,人类知识进步的内在力量也推动着世界的大学走向同质化。20世纪以来,知识进步所产生的强大力量正在塑造着知识经济的新时代,不但推动和造就了世界政治、经济的全球化,而且推动和造就着“世界一流大学”。
二、世界一流大学的产生——历史的考察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哪些大学能跻身“世界一流”之列呢?很显然,它不纯粹是大学自身努力的结果。丁学良指出,在英国领导世界工业革命的时期,牛津、剑桥成为世界最有影响的大学;在德国工业快速崛起的时期,德国的大学模式一时成为世界的楷模;而当美国在二战与冷战后逐渐成长为霸主的今天,美国的高等教育被誉成世界一流。(注:丁学良.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J].高等教育研究.2001;(3):4-9.)于此,大学和所在社会体的经济政治地位二者之间的相关已十分显然。不过笔者认为,这二者之间相关的性质既不是如丁学良所说,一流大学引领所在社会体的经济政治的发展,也不仅仅是如机械唯物主义者所判断,一流大学的产生是所在社会体政治经济地位提升的必然产物,而是二者进入良性互动的产物。
大学要与所在社会体进入良性互动,首要的条件便是,大学必须使自己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考察世界大学史,我们发现,尽管现代大学的模式最初产生于欧洲,但由于欧洲主流大学一方面过于执著于“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这两个理念,另一方面过于珍视大学产生时整个社会所浸淫着的人文传统,使得他们在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革命的过程中失去了领先地位。英国高等教育的两大巨子,牛津和剑桥,直到政府采取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减少对大学的拨款而导致财政危机不断加剧的今天才被迫放下“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这两个理念下的追求“纯粹学术”的理想,决定要开放大学体系,服务社会(注:这是与伦敦大学教育学院的一位教授谈话时他告知的。)。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的高等教育体系。由于实用主义哲学的影响,最初美国在试图建立一些欧洲大学的模仿品的同时,还大量地兴建服务于本土经济的农业机械学院。即便是欧洲大学的模仿品也在后来的日子里不断变革着自己,以适应美国本土社会的需求(注:郭键.哈佛大学发展史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47-49.)。长期以来,美国的高等教育作为一个体系都是服务于本土社会的。美国大学之所以能超越欧洲前辈,而今称雄于世界,在我看来得益于它一直以来开放的体系,以及它和与社会的良性互动。
细考起来,美国大学的崛起主要是发生在两个危机时期,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是冷战时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方面,战争的危机大大加强了因为实行自由市场体制而相对弱化的国家功能,另一方面,对大战一直保持着观察并对美国国家利益十分关心的部分学者,开始自发地考虑大学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对于当时既没有国家科学政策,又没有国家科学院的美国政府,在面对纳粹德国正在研制潜艇和原子弹等新式武器的情报下,要在科技上遏制对手,能够依靠的唯一力量便是大学了。国家的资金和大学的知识与人才在战争危机压力下的结合,促成了一个知识的投入与产出的良性互动体系。国家得到了维护国家利益的武器;大学在国家大量资金的投入下,得到机会革新知识体系。应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腾飞了美国经济,促成了美国政府在世界政治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而且使得美国大学在整个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美国大学崛起的第二个重要时期,便是冷战时期。如果二战的战争危机与在此之前的经济危机一起改变了美国的社会结构,使得国家主义开始抬头,那么这之后的几十年的持续冷战让美国的国家功能开始空前地强大起来。在二战中初尝科学技术带来的直接政治经济甜头的美国,开始有意识地关注科技的发展。它不仅开始制定国家科学政策,创建国家研究机构,而且意识到科技的发展的根本在于高层次人才,而高等教育无疑是高层次人才的最直接的供给者。于是国家开始对高等教育进行大量的投资。教授的工资得到快速增长;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大比例地获得助学金和奖学金,加之大量的研究基金的发放使得大学成为科学研究的理想之地。但是不久(1957年),前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美国上下顿时陷入科技落后的危机感中,二战的经验让他们对科技落后的可怕后果比谁都清楚。既然他们已对大学和国家研究机构进行了大量的投入,这一次他们把科技的落后归咎于教育的问题,从而颁布了“国防教育法”,以提高教育中的数学、科学、外语等课程的教学,并为立志成为这些方面中小学教师的大学生发放学习金。由此可见,在这些特殊时期,美国的大学始终成为国家利益的焦点所在(注:沈红.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形成与发展[M].武汉: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9.43-109.)。不过,90年代初,冷战以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失败而告终,西方的市场终于统一了全球,美国国家对科技的需求因此暂时告一段落,大学和国家几十年以来形成的伙伴关系也告结束。国家对大学的拨款开始大幅度地减少(注:Breneman,David W.Higher Education:On a Collision Course with New Realities.Washington,D.C.:Association of Governing Boards of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美国的大学无一例外地遇到不同程度的财政问题,连著名的加州伯克利大学都差点关门大吉。这时,大学才意识到,国家不再像以前那样是大学知识的主要购买者了。他们开始不约而同地把注意力转到学生,这群大学知识与文凭的稳定购买者身上。于是,过去长期对本科生视若无睹的所谓研究型大学,包括MIT在内,都开始大谈特谈重视本科生教学(注:清华教育研究所编,MIT校长报告.),以巩固生存基础。此外,不少大学还通过向第三世界国家贩卖自己的课程和文凭获取额外收入,用以补给学校财政。而这,又在客观上服务于统一后的市场。大量的MBA课程和课本的兜售,既充盈了大学日渐瘪下去的钱包,也把西方市场运作的原则灌输给了第三世界。所以,回顾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我们可以看到鲜明的一点便是,与欧洲注重“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传统不同,美国的大学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并通过服务社会而获得生存与发展。创造性的与灵敏的适应是美国诸多大学在今天能跻身世界一流的真谛所在。
总结起来看,大学能否与所在社会体的政治经济发展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在理念上来说至少要具备以下条件:(1)在大学方面,它是抱着“学术自由”与“自治”这两个传统大学理念而固步自封呢?还是选择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不仅专注于知识自身的传递与创造,还积极地参与对知识的社会性使用进行规范与引导)?另外,大学是固守其“人文价值”传递的传统角色,还是更专注重于基于“经验性事实”的科学的发展?如果说前者是关于大学体制的选择;则后者是关于知识体制的选择。大学只有在这两方面的观念上进行很好的平衡,才能进入良性运作。(2)在大学所在的社会体方面,无论是国家还是公民社会,是否对大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至高地位予以承认,并因此要得到大学在该方面的服务,而进行投资并获取收益?事实上,如果大学所在的社会体对大学在知识体系中的地位予以承认,并进行投资而且期望回报;如果大学在维持一定的“自治”与“学术自由”的底线的同时,选择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系统,并更多地经由其基于“经验性事实”的科学研究成果而回报社会的投资,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一个在外在社会需求推动下进入良性运动的知识体系,而不是一个固步自封和因为缺乏外在需求压力而变得暮气沉沉的系统。而这正是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今天能成为世界一流的根本原因——它与其社会共呼吸,并与其所在的社会并户成长。
三、大学体制——权力论的分析
什么是大学的体制?大学的体制实际上就是大学内权力关系的结构化表现。考察世界大学史,我们发现,西方大学的主要利益群体有三:学生、教师(faculty)、校外影响团体(其构成随历史而有所变化)。这三者围绕大学权力的角逐,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使得大学的权力关系呈现出不同的方式。概括起来说,基本上有三种模式:(1)学生权力模式;(2)教授权力模式;(3)学校行政权力模式。
学生权力模式主要发生在12-15世纪的欧洲,尤其是意大利。那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任何一个城镇的人口和财富的状况,都不足以提供足够的既有时间又有金钱还有学习高深知识渴望的年轻人,因此大学的生源来自意大利各地此外还有其他的一些国家。他们人生地不熟,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结成行会。如果与当地居民发生了严重冲突,或与教授发生了严重分歧,他们就集体迁徙到另一个城镇,重新租赁房屋聘请教授,另行开张。学生行会的势力在当时十分大,因为他们的迁徙,可以“影响居民们的生意,打破教授们的饭碗”。(注:约翰·范德格拉夫等编著,王承绪等译.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比较[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7.)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城镇的产生与成长,城镇的经济和人口都有长足的发展,大学开始有固定下来的生存条件了。而一旦教授们与居民们懂得把大学固定下来时,学生权力模式的时代就结束了,相反教授权力模式的时代开始了。
教授权力模式的产生最初发生在德国的19世纪,并在20世纪初达到鼎盛。那时在“学术自由”与“大学自治”的精英主义理念下,柏林大学等新一批的现代大学开始创办。柏林大学的创办者洪堡认为大学除了教学还应进行系统的研究工作,为了使这一新功能得以实现,他主张改革大学的体制。他提议大学应该由各个研究所构成,而研究所的运作则有赖于精英式的学术带头人——讲座教授(chaired professor)。他认为,由于教授们是各知识领域的专家,所以应该由他们来决定自身知识领域的发展方向,并由他们来决定人员的聘任和资金的使用以服务该目的。这种模式产生之初,起到了对抗教会对大学的长期渗透与控制的积极作用。但是长期运作下来,也产生了很大的副作用。由于教授终身占有大学各研究所的唯一领导位置,使得与他观点不一的学者无法在该研究机构获得职位,且他们又多半任人唯亲(即聘用自己的弟子),研究所的学术日渐变得固步自封。在教授权力模式中,大学的权力在各系所,学院是个空架子,学院的院长,大学的校长都由教授中推选,使得院委员会和校委员会成为教授的俱乐部。教授权力模式影响很深远,20世纪上半叶欧美大多数的大学都不同程度地是其制度的模仿者。像香港大学现在仍是该体制。各系所只有一位教授,他不退休,别的教师就永远也成为不了教授。后来闹出张五常教授与其继任者对簿公堂也就不奇怪了。
但是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时代的到来,这种狭隘的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不断膨胀的学生的数目与学生对知识多元化选择的需求。20世纪60年代,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学生骚乱,德国、法国、意大利、美国无一例外。在德国,柏林的学生骚乱持续了两年(1967-1969),学生们反对教授对大学权力的垄断,提出大学的决策机构中的席位学生代表占1/3,助教占1/3,教授占1/3的民主化要求(注:约翰·范德格拉夫等编著,王承绪等译.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比较[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30.)。而在美国,学生们对不断上涨的学费影响大学入学机会十分不满,而掀起大规模的运动,反对大学精英教育理念将出生平民的年轻人排斥在大学之外。学生与大学发生严重冲突后,社会各政治势力都趁机参与斡旋以增强自己在民众中的影响,而多方势力的参与又使得本来严重的问题更趋紧张。从本质来看,这次运动的核心是攻击大学精英主义框架下的自我封闭。各政治势力期望借此机会对大学进行渗透,而学生则期望能增加入学和参与大学管理的机会。在一片混乱中,国家权力被迫参与协调,最后的结果使得参与这场权力角逐的各方,学生、教授、各政党都失望而回。结果是,大学行政系统作为大学与外界社会,尤其是与政府的沟通中介,成为大学新兴的权力代行者;而各地方政府也从中央教育部手中分得了部分的权力。学校行政权力模式在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产生了,即校长负责制(注:约翰·范德格拉夫等编著,王承绪等译.学术权力-七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的比较[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62-63.)。
以上三种模式的描述基本上是基于欧洲的情况,美国的情况则稍有差别。由于美国高等教育体系的多样性,大学的权力机制也因此各不相同。基本上来说,美国只有很少数的大学实行的是教授权力模式,大部分的大学,尤其是州立大学实行的都是学校行政模式。哈佛等一批私立大学行的是双院制,即校方行政体系加校外名流组成的董事会(Board of Overseers),二者共同实施对大学的管理(注:郭键.哈佛大学发展史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47-49.)。
那么我国的大学权力模式又是怎样的呢?我国大学行使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初看十分类似哈佛的双院制。党委决策并监督,校长领导行政体系进行运作。但仔细地考察我国大学的组织构成,却发现我们的党委与美国的学校董事在大学的结构与功能上是不同的。我们的党委不仅存在于大学层面,在学院层面还有院党委,在系层面还有系党支部,甚至在学生的每个班级或年级,也有党的支部机构。也就是说,大学作为一个社会组织被另一个目标不同因而性质也完全不同的组织——政党组织——穿透(penetration)。这种穿透与美国大学的开放体制不同,美国的开放体制是通过州或联邦政府的财政或法律政策来调控大学的行政运作,再经由校方的行政运作(主要是指大学层面的,而不是学校基层的)来调控系所的学术与教学活动。也就是说,董事会只是在大学与政府和社会之间充当一个协调机制。我国大学的情况则不一样。党组织对大学的穿透,使得它的正式或潜在的成员形成了一个利益群体。也就是说,在欧美大学内,主要的利益群体只有学生和老师;而在我国大学内,主要的利益群体除却学生、教师,还有党的干部与成员(在激进的年代还包括积极分子)。虽然欧美大学内的权力分布也十分不均,比如19世纪教授独揽所有的权力,后来虽有民主化进程,不过教授仍是大学权力主要的行使者,但是权力的性质是一致的,都是学术权力;而我国大学内党的干部与成员的权力合法性主要来自于其对党的意识形态的信仰,因而本质属于政治权力。虽然又红又专的路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将二者结合起来,但二者的目标毕竟是有差异的。而一个有效的组织行为应该是共同指向组织目标的。其实,这背后涉及了不同的理念,如果政府与大学的关系被假设为伙伴关系,政府需要获得大学在知识领域的服务,那么政府会承认大学的自主权(没有自主权,大学怎么能全效运作?),并通过财政和法律政策等方式对大学的运作进行渗透,以保证大学运作的方向服务于政府;如果政府假设大学主要是一个意识形态的领域,那么穿透便是最有效的控制方式。因为组织的穿透,可以通过一个强势利益群体为中介,保证来自外在的政策路线在大学内能够得以实施,而不会遭到大学成员的抵制。
四、清华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有多远?
以上,我们从大学的概念、大学兴起的历史条件和大学的体制三方面对世界大学的发展进行了一个轮廓的勾勒。从中发现,美国的大学体系虽比欧洲大学体系的出现晚了很多,但是由于美国高等教育秉持的开放和服务本土社会的理念,由于美国大学权力机制同时具有开放性和自主性的特点,使得大学与政府能在国家危机时刻结成伙伴关系,从而拉动大学知识的传递、创新和社会性运用的活动,结果大大提升了美国大学在人类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当然一些独特的有利条件也是美国大学体系能够后来居上的很重要的原因:比如美国经济政治地位在世界的持续上升;二战中大量高素质的人才避难并留居于美国等,这些都为美国大学在20世纪的崛起提供了必要的资金、人才和国际背景。总结起来说,世界一流大学的产生既需要这些社会性背景因素,也需要大学个体方面的因素,如大学自身的积累,以及大学对环境的弹性和创造性的能力。
以此为基础,我们再分析一下清华在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上还要走多远。
首先,清华具有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所必须的开放理念和创造性的能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就意味着成为前无古人可借鉴,后却有众多来者相追随的大学中的领导者,所以开放的理念以及创造性的适应成为大学组织为后来者开辟前路的核心能力。这点只要略读清华校史便可知。清华最初只是个留美预备学校,虽然庚子赔款的巨额数目使清华一时办学条件优越,但当时的清华领导人却能够未雨绸缪,考虑到一旦赔款用尽,学校便会面临关门的境地,于是致力于将清华学堂升格为大学,后又在国内领先地创办研究院,从而最终奠定下与北大齐名的地位。清华与留学教育的深刻渊源,使得精英主义的教育理念在清华盛行,教授治校的学术权力体制在中国真正得到实施的便是清华(注:苏云峰著,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1911-1929.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后来在新中国建立后,院系调整完毕,清华成为一个单纯的理工院校,学校的损失很大。但是清华新的领导人,却秉持着开放的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提出清华应该成为培养又红又专的工程师摇篮,结果为新中国的初步工业化输送了大量的与体制结合良好的人才。今天,这一培养目标的正确性已得到检验。清华培养的人才中成为国家现代化领导者的超过其他任何大学。20世纪90年代中,我国宣布要实行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很快清华校园内便展开了一轮教育思想的讨论,讨论涉及的范畴很多,但核心直指旧的培养目标。应该说,王大中校长时期是清华实行又一次转变的时期。转变主要发生在两方面:1)培养目标的转变;2)大学结构的转变;而二者又是相一致的。虽然清华目前并没有提出一个蒋南翔式的明晰的培养目标口号,但新的培养目标确已建立起来,而且大学在原有的工学院的基础上,创建了许多新的专业学院:如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法学院、医学院、公共管理学院、美术学院、新闻及传播学院等,清华至此进入后蒋南翔时代。旧的秩序被瓦解,新的秩序正在形成中。不过目前还只是在大学结构层面上的操作,以后重点应放在知识层面上,进行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识创新,并致力于服务本土社会。
其次,目前清华有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历史机遇。目前,中国经济的持续高增长已有一段时间的积累,国家对大学的理念也发生了变化,开始充分地认识到科技对社会发展的重要而且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大学在其中作用。此外,我国目前在国内面临着社会转型和经济高速发展而出现和众多社会问题,在国际上又面临着帝国主义国家的排斥性的竞争,加之台湾问题等的干扰,我们的国家在未来充满机会的同时也充满着深刻的危机。大学作为知识整理、创新与社会性运用的重要机构,是国家冲出困境重要的依赖。清华长期形成的与政府合作而不是批判的传统,使清华在未来的道路上可以扮演更重要的角色。目前,国家对几所大学进行重点投资,清华也在其中,这在本质上来说就是资源集中,资源集中必然带来人才的集中,这些都为清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可以断言,国家的重点投入以及清华大学本身的服务国家的传统,为清华在未来形成与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以及清华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那么,清华离这个目标还有多远呢?笔者认为,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过程基本包括三个步骤:1)资源集中;2)制度创新;3)在新的制度框架下提供弹性和自由的创造空间。显然,我们还处在第一个阶段,而最难的莫过于制度的创新。前文已谈到我国大学体制中存在的由于被穿透而带来的新利益群体对大学主流目标的干扰与障碍的问题,如何创造性的解决这个问题,是很关键的。既保留党对大学的领导,又使大学获得专注于主流目标的起码自主权,是大学层面的难题。在学院层面,各专业学院如何创建适应本专业的严格有效的训练制度,也是个难题。在系所层面,如何为学者个体提供既严格又有弹性的空间,使他们的学术知识活动更有效,也是个难题。而清华,目前正在进行的教师教学和科研系列的分化是不妥的。一则它人为的分割了知识的传递、创造与社会性运用的过程,是有违大学之道的计划性管理行为;二则,即使此分法是为了达到对教学的加强,其实际效果将是南辕北辙的。因为,关于大学聘用人员的标准在历史上多有争论,但今天人们基本公认的一点就是知识的创新能力,即所谓的publish or perish(不发表就滚蛋),因此学术能力是大学教师聘用的根本条件。重视教学是重要的,前文也论证了这个问题,但是,教学的重要性应该体现在“学而优则教”。这方面可以设立非终身的讲座教授制度,选任有声望而年高之士讲授基础课,并给予优薪。因为声望高可以引起后生学子的崇敬,而年高一般表明他对本领域的知识已十分详熟系统。此外,大学应该建立教师培训制度,最终使得最有创造力的研究人员最终也成为热心并合格的教育者。因此单纯教学系列的保存实在是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清华是一所充满生命力的大学,具备很好的条件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如果能够在大学制度和功能上进行创新,并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为人类知识体系的进步作出标志性的贡献,那么清华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将水到渠成。
标签:大学论文; 世界一流大学论文; 大学教育论文; 人才理念论文; 美国教育论文; 知识体系论文; 清华论文; 社会体制论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