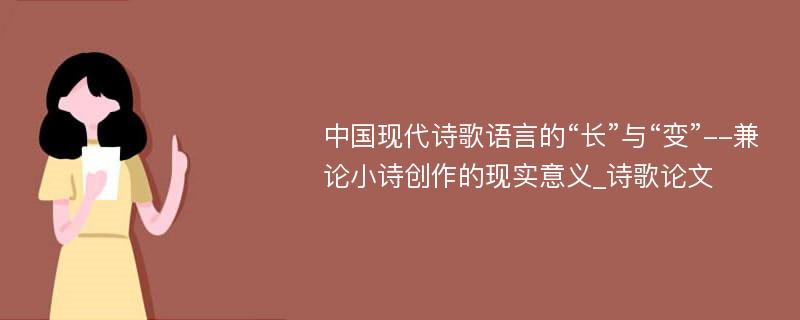
现代汉诗语言的“常”与“变”——兼谈小诗创作的当下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小诗论文,意义论文,语言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416(2002)01-0001-06
一
现代汉诗语言变数太多,居无定所,只见探索,不见守护,以至完全失去了其本质特 征的参照,正成为一个越来越绕不开去的大问题。
研讨这个问题是颇令人尴尬的。就创作而言,短短80余年的新诗发展,其实各方面仍 只是刚刚起步,处于生长发育阶段,自由放任惯了,不宜过早去框定什么,以免伤筋动 骨或有妨根性元气。但就理论与批评而言,却又不能因此也自由放任,或只是跟着创作 后面“打扫战场”,该有自己的目的和任务;这任务不是空对空地自我完善,更重要的 是要有问题意识。这些年理论与创作的脱节现象日趋严重,很难于实际的诗歌发展生发 作用,大多是各行其是,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常常是来自诗人们自己的一些说法,从而 导致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也一再延搁在那里,这其中,最突出的便是语言的混乱。诗是 语言的艺术,诗的实现首先是生命意识的内在驱动,是自由呼吸中的生命体验与语言经 验的诗性邂逅,但其落实于文本则最终是语言的实现。这种实现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是 有其基本的美学元素作参照的,并逐渐形成了中国诗歌的语言传统和精神传统,正是这 传统滋养了古典诗歌的辉煌,且至今仍滋养着某些传统艺术(如中国书法、水墨画等)的 生存与发展。然而到了今天的现代汉诗创作中,语言的实现则完全无“常性”可言了, 一味“移步换形”,既失去了老传统,也疏于对新传统亦即朦胧诗、第三代诗某些优良 品质的发扬,只讲差异、讲个人化,结果反而面目不清,空前的散文化、非诗化,同时 也导致当代诗歌在整个文学及文化格局中的自我迷失与边缘化。
诗歌创作一时惟求新求变是问是无可厚非的,理论与批评则应从“变”中求“常”, 从激进的“拓进”中求稳重的“守护”——基于上述指认,本文试图寻找现代汉诗的语 言演进中,是否仍有可确立的一些不变元素,进而追索中国诗歌的语言特质,并想以对 小诗创作的当下意义的思考,来寻求发扬中国诗歌语言传统的新的切入点以稍稍改变我 们的困境。
二
按照陈仲义《扇形的展开——中国现代诗学谫论》(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的 总结,现代汉诗至今已呈现16种分支形态,包括“偏重于西洋移植嫁接的意象征诗学、 超现实诗学、智性诗学”,“完全本土化的新古典诗学、禅思诗学、意味诗学”,“90 年代兴起的语感诗学、摇滚诗学、日常主义诗学”,以及“势不两立的解构诗学和神性 诗学”等等,真可谓移步换形,日新月异,其变数之大,前所未有。尽管这里是作为诗 学的分类,其实语言的变数也已包含在内。如今尘埃落定,就要在新的一个世纪里“变 ”了,回首来处,不免就想起一句西方的谚语——“滚动的石头不生苔”。
现代诗本质上是“自由诗”,“不自由毋宁死”。自由则生变,不变何来自由?但这种 自由也许在某种有限度的约束下才会生发更有价值的成就,亦即只有具有一定约束能力 的诗人才有权并更有效地行使这种自由。这里的关键是,“变”并非只在创新、只在拓 展,它同时还附带有修正、填补、完善那个可能存在的“常”的属性。因变而“增华加 富”,生发新的生长点,这是“变”的正面效应,但同时变得太多,伤及常性,也就难 免生出“因变而益衰”(朱自清《诗言志辨》)的负面效应。是以“变”与“常”的关系 ,应是既冲突又互补的关系,“变”为“常”生,“常”久则生“变”,再“变”更新 “常”,“常”在“变”中,“变”才有意义的归宿。有如“移步换形”,“移步”是 必须的,今人不能作古人,必须接纳新的人生经验,进入新的文化语境,表现新的精神 世界,不移步不行。但“移步”的同时是否一定要亦步亦趋地去“换形”呢?古典汉诗 从《诗经》“移”至唐诗,千年之移,其间精神变故应该不算小,但其语言形态也只是 由四言“换”到七言。再往后“移”至宋词,也只“换”到“百字令”,基本上,是一 种守护中的演进,至少,那点简约、精微的语言根性,是从不换的。现代诗的问题是深 受百年来进化论、不断革命论的影响,创新求变的欲望压倒一切,把“新”和“变”摆 在一切价值的前面,始终难以形成一个基本稳定的诗美元素体系作根本,以便得以在守 护中拓进的常态发展。古语讲:常人求至,至人近常。诗也是这样:常人求至而至诗近 常。这里的“常”含有两层意思:一是寻常,本色、本真、不着迂怪、同中求异、从心 所欲不逾矩,是一种风度,一种境界;二是常规,本质、本源、规律性、共认共守的艺 术特质,所谓由限制中争得自由,由规范中见出生气,一种专业风度,一种化境。读诗 读久了,自会发现,真正优秀的作品反而是那些在形式上看去并不怎么特别而近于平常 的作品。也就是说,真正优秀的诗人,总是能持一种守常求变的立场来深入语言的经营 ,在某种有限度的约束下寻求创新的自由,这种约束看似消极,实则反而带有创造性和 解放性。一味求新求变不求常,看是积极、是自由,实际上隐藏了另一种不自由——心 性的不自由,将革命弄成了目的,驱动转化为迫抑,为新而新,为变而变,“因变而益 衰”,也就谈不上有“常”可守了。古典诗歌在那样逼仄的形式框架中,反而显得心性 自由,游刃有余,容纳了那样漫长、广阔而又丰富的精神历程,而今日的自由诗却以其 “类”的丰化导致“度”的递衰,只能表明,我们的诗歌语言机制出了问题。正如艾略 特曾经指出过的那样:“文体极端个性化的时期将是一个不成熟或者一个衰老的时期。 ”而“任何民族维护其文学创造力的关键,就在于能否在广义的传统——所谓在过去文 学中实现了的集体个性——和目前这一代人的创新性之间保持一种无意识的平衡。”[1 ]
其实这种“平衡”,这种在变中守常的创造机制,在现代汉诗的进程中一直不乏存在 ,只是总易于被惟新惟变为上的时代潮流所冲淡,疏于认领。譬如被马悦然称誉为“中 华文化的一面里程碑”[2]的台湾现代诗,到位的研究者都知道,其总体艺术成就,至 今还应说是其前行代诗人们的创作最具实力和经典性,高标独树,领一代风骚。而若稍 做考察便可发现,这一代诗人们,无论其属于哪一流派、何种路向,是《创世纪》、《 现代诗》还是《蓝星》,是“超现实主义”、“新古典”还是“现代派”,诸种面貌, 各种体式,极尽探求,但其作品背后的语言基质,却带有明显的一致性,很少变化。正 是这种一致性,形成了台湾诗歌语言守常求变的良性机制,有一个评判诗歌品性的基本 标准,大家都在这一基本标准下用心用力,常态发展,而不致“各领风骚三两年”。除 了其它各种因素之外,这一点,恐怕是前期台湾诗歌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原因之一。而 后来的中生代、新生代诗歌之所以未能取得超越性的成就,除文化形态变故、工商社会 迫抑及前辈影响之焦虑诸原因外,语言机制的变数逐渐增大,花样翻新,失去常性,恐 怕更是关键所在。
在大陆诗坛,近年也有不少实例。譬如非非诗派创始人周伦佑,在80年代的诗歌创作 中,语言变革创新可谓最激烈也最极端,有《自由方块》、《头像》等实验作品令诗界 瞠目结舌,乃至遭遇“只有理论没有作品”的非议。但到了90年代的写作中,经由“在 刀锋上完成的句法转换”(周伦佑台湾唐山版诗集名),换回到常态语势,杂糅叙事、口 语、意象、抽象、解构、结构、象征等修辞策略,整合融会,颇有控制感地创作了《刀 锋20首》精品力作,令人刮目相看。其中不少代表作,不但成为诗人自身创作的精华, 也是大陆现代汉诗创作中十分难得的佳作。更有意味的是,诗人用并不怎么“先锋”的 常态语言,却能直抵为一个非常时代之重大创伤作诗性命名的深境,其意义更值得我们 深思。再如于坚,一贯被称之为大陆先锋诗歌的重要代表,于坚自己却不买这个账,甚 至经常宣称自己是“向后退”的诗人——不是退向保守,而是退向常态,退向整合。为 此,于坚在完成了他极端性实验文本之长诗《○档案》后,潜心创作了另一部长诗《飞 行》。仅就语言品质而言,这部长诗最大的特点是其复合性的品质,一种“软着陆”式 的整合与创化,几乎运用了现代汉诗写作的各种修辞手法,中正平和,一点也不“前卫 ”。诗人甚至重新引入被先锋诗人们放逐已久的抒情之维和意象思维,与其擅长写实、 精于叙事的看家语感一起,融汇为集原创与整合于一体的复合语境,让我们不仅切实地 领略到现代中国人自己的现代意识,也真正领略到融铸了东西方诗质的现代汉语诗语特 有的语言魅力和审美感受,不失为现代汉诗的精品力作。可以看出,对于坚而言,实验 从来就不是目的,先锋也只是一时的姿态,正如他自己所言:“反传统的诗人,负有双 重的使命,他既要在传统的反叛中创造历史,又要让这历史成为一种新的传统得以延续 。”[3]从不断革命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同路人所说的,《飞行》相对于《○档案》是 一种“别有野心”的大倒退;而从守护中拓进的立场去评价,《飞行》则是一次划时代 的整合,一次由“变”而“常”的飞跃。实则于坚的“野心”一直并不在什么先锋的位 置或时代的前列,而是要经由自己的创造,来建立现代汉诗写作的新的传统、新的语言 典范,“成为经典作品封面上的名字”(于坚语)。同样有意味的是,多年来,于坚的创 作、于坚的语感风范,很少见大量的仿写者,总是“高处不胜寒”,独来独往。这其中 ,既有难度的存在,更因为于坚在本质上是一位综合性的诗人,“坚持那些在革命中被 意识到的真正有价值的东西”[4]的诗人——在这样的诗人这里,“变”是手段,是过 程;“常”是根本,是目的。
三
那么,到底什么是汉诗诗语的“常”之所在呢?也就是说,经历百年淘洗后,汉诗诗语 的基本属性有哪些是不能再“变”而须加以悉心守护的呢?可以说,这不仅是个难题, 而且是多年来诗学界一直回避的问题,即或有涉及者,也总是拽着古诗来谈,一触及现 代,就少言寡语或言不尽意。现代汉诗是用现代汉语写作的,其西化的成分很重,但它 毕竟是汉语,并没有完全同古典诗语的语言基质“恩断义绝”,还是有不少一脉相承的 “基因”可言的。这些“基因”,按海内外论家一概而言之(不分古典与现代)的诸多说 法概括之,至少有这么几点:
1.简约性:言简意赅,辞约意丰,少铺陈,不繁冗,以少总多,不以多为多;
2.喻示性:意象思维,轻逻辑,重意会,非关理,不落言诠;
3.含蓄性:非演释,非直陈,讲妙悟,讲兴味,语近意邈;
4.空灵性:简括,冲淡,空疏,忘言,重神轻形;
5.音乐性:节奏,韵律,抑扬,缓急,气韵生动。
上述“基因”,尽管已是最基本的几个“元素”了,但其实也已大多在当代汉诗写作 中丧失殆尽,无“常”可守的了。汉诗语言的过分西化,使我们在一个日益变得无根无 基的世界中,更加难以听到我们自己的声音,辨认自己的精神家园,而说到底,诗本应 是辨认民族精神和语言的指纹呵!当然,必须承认,上述“基因”中,确实已有不少成 分与现代诗的本质(现代意识与现代审美情趣)要求相去甚远,乃至十分隔膜,已无必要 “守护”,但作为诗之所以为诗这一门艺术的语言品质,总还得有一点与其它文体相区 别开来,最终唯诗所凭恃的成分,同时又不失为汉诗语言的指纹所在吧?我想,至少“ 简约”这一点,是应该作为“底线”来加以守护的。
简约是中国诗歌最根本的语言传统,也是中国文化及一切艺术的精义。闻一多曾指出 :“中国的文字,尤其是中国诗的文字,是一种紧凑非常——紧凑到最高限度的文字。 ”[5]即或如提出“作诗如作文”的胡适,在谈及自己的诗歌追求时也特别提到:“要 抓住最精彩的材料、用最简练的字句表现出来。”[6]卞之琳则说得更明确:“诗的语 言必须极其精炼,少用连接词,意象丰富而紧密,色泽层叠而浓淡入微,重暗示,忌说 明,言有尽而意无穷。”[7]尽管三位汉诗先贤在做这样的指认时,大体依然是以古典 诗语作参照,但这一简约之根性,并未在他们以及整个早期新诗创作中有多少减弱,卞 之琳更是以四句《断章》独步百年而无人企及。当代汉诗尤其是90年代以来的大陆先锋 诗歌,许多创作路向则几乎是背道而驰,由约而博,由简而繁,由含纳而铺陈,由精微 而粗糙,由跨跳而爬行,由灵动而沮滞,松散冗长,臃肿不堪,可以说,已无最基本 的“底线”可守,只剩分行而已。台湾诗人余光中曾说“许多新诗人昧于简洁之道”, 不幸言中且现今已发展成普遍现象。因此郑敏先生在特别强调“汉诗的一个较西诗更重 视的诗歌艺术特点就是简洁凝炼”的同时,更特别指出“在近百年的新诗创作实践中, 始终面对一个语言精炼与诗语表达强度的问题”[8]。
看来简约确实是汉诗语言的“底线”,是第一义的诗美元素。当然西诗也讲简练,庞 德在谈到诗的语言要求时,就一再提到简练和硬朗,反对“把文章拆成一行一行”的“ 诗”法,并且还借用一点“中国功夫”,写出两行《地铁站上》的名诗,恐怕是西诗最 短小精简的了。但从语言根性上来说,西诗的简约与汉诗的简约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不然,这么多年“西学”为上,却反而越学越松散,越学越丢了简约的根本了呢?(这细 说起来,得有另一篇大文章。)总之,再怎么折腾怎么变,“简约”这个底线不能丢。 诗的简约之起码要求不仅是对语言的高度浓缩形式的要求,以合乎文体要义,也是对生 命体验的高度浓缩形式的要求,以免于成为公共话语或体制话语的平均数。在这里,简 约已不只是语言品相,更是一种精神气质。正如欧阳江河在论及北岛时所指认的:“… …北岛和他所喜爱的德语诗人保罗·策兰(Paul Celan)一样,对修辞行为持一种甚为矜 持的、近乎精神洁癖的态度,常常将心理空间的展开以及对时间的察看压缩在精心考虑 过的句法和少到不能再少的措辞之中。这种写作态度与当代绘画中的极少主义和当代建 筑中‘少就是多’的原则在精神气质上有相通之处。‘少’在写作中所涉及的并非数量 问题,而是出于对写作质地的考虑,以及对‘词的奇境’的逼近。”[9]另外还应看到 ,在当代文化语境中,简约本身也是一种特别的力量,既是直击人心的力量,又是亲和 的力量。近年大陆先锋诗人中得此要义而获大益的典型例子就是伊沙,其作品广受读者 欢迎,且引发大面积追随乃至成为“公害”,最主要的一点,就在于他恢复并提升了简 洁的力量,短小精悍,打的是“直拳”,却又不乏直击后的渗化兴味,且读来不隔不绕 ,颇为亲和。进一步需要说明的是,强调简约,当然不是强调诗行诗篇的长短繁简,而 是说要讲究语言的质地和表现的强度,别太水,太绕弯子以至散漫无羁而致乏味,尽量 以最少的文字来聚敛并表现最多的涵义与韵味,以有限浓缩无限。只是这种讲究,对于 “昧简洁之道”甚久的当代汉诗来说,恐怕不借助于某种外在形式的约束,是很难有所 改观的——由此自然便想到了小诗。
四
有如简约是汉语诗歌的正根,小诗其实也是汉语诗歌的正根,只不过一种新文学总是 先放才收,依然在过渡途中的中国新诗,很难一时归宗于哪种体式。小诗的兴盛,也只 是在冰心、宗白华几位前贤中,于20年代小试牛刀而倡扬一时,此后便未再举盛事,更 乏善讨论。
到了80年代,先行遭遇大众文化“洗劫”和工商社会挤迫的台湾诗界,面对现代诗空 前的“消费”空缺,才转而直面现实,探讨为诗“消肿”,回归简约以求亲近读众,从 而开始持续不断地关注和倡扬小诗的创作。1979年由罗青编选的《小诗300首》(上、下 册)尔雅版隆重登场,反响不错。作为小诗运动的一直积极推动者张默,80年代初,便 在《创世纪》诗刊专辟“小诗选专栏”,编发小诗作品,随后又潜心编著了《小诗选读 》,1987年仍由尔雅出版社出版,一年内三印、颇受欢迎。1997年,由向明、白灵编选 的《可爱小诗选》,再度由尔雅出版社推出,并以“像闪电短而有力,像萤火虫小而晶 莹”的标举,引起广泛阅读兴趣。白灵在该书序文中指出:“诗之所以为诗,应是深深 挖掘,轻轻吐出,所谓‘深入浅出’是也,但诗人甚多不明‘浅出’不仅是词语之浅近 ,还应包括字数之节省。雷霆万钧之力常只宜将能量发挥于一瞬,拖沓太久,则早涣散 殆尽。不论闪电也罢,萤火也好,其能引人注目,即在于一瞬,因一瞬乃不易把持、易 具变化和新鲜之感,因闪烁不定故可引世人之好奇、注目。此即小诗有机会成为新诗大 宗之利基。”有“诗魔”之称的洛夫,可谓当代两岸诗界最能于限制中创造语言奇迹的 诗人,在多年多方位的创作中,一直醉心小诗,不单将其视为“意象体操”,更作为诗 质饱满的“小宇宙”去精心打造,并于1998年出版了《洛夫小诗选》(小报出版馆版), 成为“现代绝句”的经典展示,也是自有新诗以来,小诗创作的集大成者。洛夫在其题 为《小诗之辨》的代序文章中说:“……中国古典诗从诗经发展到近体诗的五七言绝律 ,都是小诗的规格……所以,如说中国诗的传统乃是小诗传统也未尝不可。”进而直言 :“我认为小诗才是第一义的诗,有其本质上的透明度,但又绝非日常说话的明朗。散 文啰啰嗦嗦一大篇,犹不能把事理说得透彻,不如把它交给诗,那怕只 有三五行,便可构造一个晶莹纯净的小宇宙。”
基于上述共识和实际性的推动,小诗创作在台湾已逐渐形成传统,也确实有效地改善 了现代诗的“生存危机”,且大有成为“新诗大宗”的趋势。为此诗人们还就现代小诗 的规格提出各种议案:罗青主张以古典律诗行数的双倍即16行为最大极限;张默主张以 10行为限;洛夫认为12行较妥;白灵则认为小诗规格与行数无关而与字数有关,提议以 100字为限。尽管如此细究,稍嫌牵强,但这种不可为而为之的敬业精神和科学态度, 确实令人感佩。
反观大陆诗界,对这方面则很少关注,或偶有涉及,也一直未形成热点、拓开局面。 这其中,一是长期疏于对现代汉诗的诗体研究,任其“自由”发展;二是一贯漠视阅读 境况,尤其是非专业性、非研究性阅读境况的反应,自管自地“高视阔步”,或以“生 存危机”为“宿命”,不图改善;再就是从心理机制上就瞧不上小诗创作,认为不是正 宗,成不了大气候,同时也怕因诗体所限,伤及诗思的展开与诗艺的发挥。确实,小诗 看似好写,其实最难,既难工,又难有份量,弄不好就将简约弄成寡淡,将精微弄成轻 浅,成为小摆设、小饰物,难以涵纳更深邃、复杂的现代意识和现代审美情趣。但问题 是,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在商业文化的挤迫下,诗已不再能充当现代人精神之号角或 灯塔的角色,而很可能只是物化世界之暗夜中的萤火虫,以微弱而素朴的光亮引发人们 对她的重新认知和热爱。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真正优秀的小诗也并非就挑不起“大梁 ”。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如前文所举卞之琳的《断章》、还有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就 很典型。当代作品中,昌耀的《斯人》,周梦蝶的《刹那》,痖弦的《上校》,余光中 的《乡愁》,洛夫的《金龙禅寺》,罗门的《窗》,郑愁予的《错误》,北岛的《迷途 》,多多的《从死亡的方向看》,严力的《还给我》,于坚的《避雨的鸟》等,都在百 字左右,而尽能于刹那间见终古,在微尘中显大,象清意沉,骨重神盈,闪电般的照耀 后,更有无尽的悬揣意趣令人神往。而女诗人夏宇的《甜蜜的复仇》:“把你的影子加 点盐/腌起来/风干/老的时候/下酒”。只短短5行19字,却已写尽爱之沧桑,可谓现代 情诗之绝唱!当然一般而言,小诗还是多以轻灵取胜,但若轻的是一只飞鸟而非一片羽 毛,也不失为一种可贵的价值。洛夫的小诗就大多能表现这种妙趣,看似信手拈来,不 着经营,实则用心良苦,深得汉诗语言之精义,于方寸之间,融铸生命关照,时见禅意 ,又带反讽,妙姿神韵,融古通今,极具形式美感,又充满现代意识,让人对小诗不敢 轻视。
五
就诗学研究而言,试图提出一个新问题,是个诱惑,而试图解决这个新问题,则不免 是个陷阱。因而必须指出的是,上文对小诗的强调,绝非要设计一条什么新的出路,而 只在提示,经由对小诗创作的重视,或可改善某些困境,弥补某些缺失。至少,其一: 可以增强我们的诗体意识,不致过于散漫无羁,变得没了根本;其二:为越写越长越松 散的现代汉诗“消肿”,重新找回并确立汉诗诗语简约、精微的本质特性;其三:拿小 诗来“练功”,提高语言的控制能力和表现强度,补充一点“基本功”,以求心里有底 ,笔下有数(小诗很难“掺水”做假,得见真功夫,而当代诗人比起许多前辈诗人而言 ,语言功底和艺术修养确实逊色太多);其四:以小诗“闪电”与“萤光”的艺术魅力 ,或可在非专业性、欣赏性阅读层面亲近读众,“收复失地”,进而增进与扩展现代人 对诗的关注与热爱。
当然,对于多年为“移步换形”、变动不居所困扰的现代汉诗来说,仅借小诗作收摄 ,以简约为旨归,难免有些偏狭或将问题简单化——或许,以变动不居、混乱杂交的语 言和体式,来表现变动不居、混乱杂交的现代精神,正是这时代的必然选择亦即无法脱 身他去的创作机制?而寻求“变”中之“常”,又是否会伤及刚刚获得的多样性与差异 性,使其还包含着更多没有开发而需要更长时间来实现其可能的潜在资源受到不必要的 限制?但我依然想说的是:越是变化最剧烈的时代,越是要保持自我的存在——我们已 迷失太久,是该找回我们借以安身立命的现代汉诗之精神指纹和语言归所的时候了。而 上述的思考,也只在提示:这可能不是一个必要的“出路”,却不妨是一个“出口”。
收稿日期:2002-01-19
